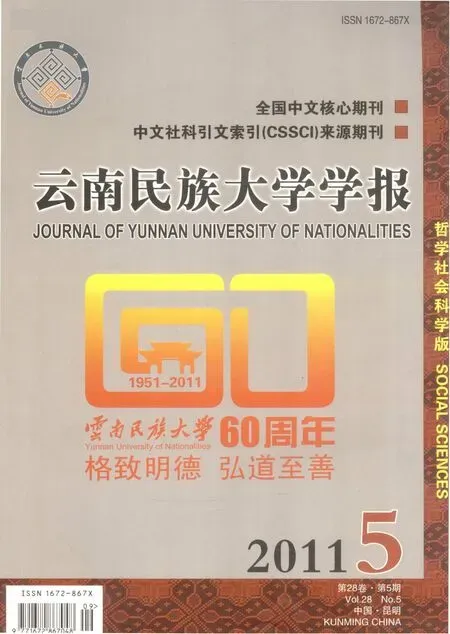克木语使用状况调查研究
张宁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2月发布的新版“世界濒危语言图谱”显示,在目前存世的6700种语言中,预计将有200多种语言会在50多年内灭绝,另有538种语言处于垂危状态,502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632种语言处于危险状态,还有607种语言处于不安全状态。如此大量的语言处于濒危乃至消亡的状态,引起了国际语言学界、人文学界的普遍关注。语言衰退和消亡的主要原因是,整个社会正在向政治、经济、科技上更具影响力的语言转移。有语言学家估计,到本世纪末,世界大部分语言的交际功能将陆续让位于国家或地区的通用语言。语言的多样性以及文化多样性将面临严峻挑战。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国家,少数民族语言少说也有129种①20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主编的《中国的语言》就具体描写了129种语言。[1],相对来说,使用人口都比较少,有的甚至很少。据有关专家估计,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已有几十种处于濒危状态,还有近一半处于衰退状态[2]。语言消失的背后是文化的失落,正如中央民族大学戴庆厦教授所说:“一个物种的消失,只让我们失去一种动人的风景;一种语言的消失,却让我们永久失去一种美丽的文化。”[3]
容易濒危或面临濒危的语言一般都是使用人口较少且无文字的语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2008国际语言年》报告也说明了这一点。报告指出:“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导致语言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有的语言已经或者正在逐步消失。世界上6000多种语言当中,96%的语言使用者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3%,并且95%以上的语言很可能会在几代人之后消失。在教育领域和公共领域中占重要地位的语言,实际上只有几百种,而数字传媒领域使用的语言则不到 100种。”[4](P355~356)原因很简单,使用人口少且无文字的语言,在强势语言的冲击下容易走向濒危。
然而,使用人口少且无文字的语言未必一定在“一体化”环境下迅速衰退或消亡。如居住在云南中缅边境的独龙族人口不足5000人,由于高黎贡山的阻隔,他们很少与外界接触,因此独龙族大部分是单语人。如果这种居住状况不会很快改变的话,独龙语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不会很快消失。②孙宏开2008语,参见2008-2-2《北京日报》路艳霞:《全国56个民族有129种语言》。又如,主要居住在广西环江县以茅南山为中心的重峦叠嶂间的毛南族,由于长期受到壮语和汉语的强烈影响,已有57%的人逐渐转用壮语或汉语,只有约43%的人还保留并使用自己的母语毛南语。但在毛南族聚居中心下南乡,人们对自己的母语都非常热爱,以说毛南语为荣,他们在家庭里无一例外地都使用母语,在集市上或开村民大会时也主要使用母语,因此,在下南乡形成了一个毛南语稳定使用的语言岛。[5]又如,历史上“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生,现在实行定居放牧并居住在内蒙古和黑龙江大兴安岭一带鄂温克族聚居区新村的鄂温克族,鄂温克语“在民族聚居地区还保留着交际功能,大部分鄂温克人相互之间都用本族语进行交流,尤其是在鄂温克族的家庭内部,鄂温克语仍然是人们日常的交流语言”[6]。再如,居住在云南江城、墨江两县部分地区的哈尼族西摩洛支系,人口只有8000人左右,但西摩洛语使用健康,保存完备。戴庆厦教授认为,是我国的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西摩洛语;是西摩洛人聚居的环境相对不容易丢掉本民族语言;是西摩洛人热爱自己的母语,以说自己的语言为自豪。[5]等因素便只有几千人使用的西摩洛语没有走向濒危。
以上所举的语言使用实例说明,看语言是否濒临灭绝,不单是看使用人口的数量,还需要从語言使用者的历史背景、空间分布、地理环境、居住模式、使用狀況、母语感情等方面看。克木语是克木人使用的语言,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克木语支。克木人被国际学术界看作一个跨境民族共同体,主要分布在中南半岛北部,包括老挝、泰国、越南、缅甸的部分地区以及我国西双版纳的部分地区,总数在60万人以上,其中,不少于50万的克木人生活在老挝北部。我国境内的克木人分布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的10个村寨和景洪市的4个村寨,人口约2500人。
一
笔者自1995年以来至今,在西双版纳克木人村寨进行民族社会学方面的间断性田野调查,足迹遍及克木人的所有村寨,在有的村寨住的时间还比较长,所到之处听到的语言有3种:克木语、傣语、汉语。除个别村寨外,绝大多数的克木人男女老幼之间均稳定、熟练地使用自己的母语,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交流时使用汉语或傣语。笔者深切地感受到,克木语在克木人家庭和村寨中还保持着使用功能,“还有相当的使用范围和使用环境”[8]。
目前,克木语所以“还有相当的使用范围和使用环境”,笔者认为有下列诸多因素:
1.克木语是一种跨境语言,国外主要是毗邻的中南半岛北部,克木语的使用人数在60万以上,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个人、家庭乃至整个村寨往来迁徙是常事。目前,我国境内的克木人与境外克木人特别是老挝北部的克木人相邻而居,互通婚姻,走亲串戚往来密切,因而文化认同感比较强。所以,就大语言环境看,这个语言母体的存在,对我国境内克木语保持活力无疑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2.西双版纳地处我国西南边陲,是个以傣族为主体的民族区域自治州,世居民族有傣、哈尼、拉祜、彝、布朗、基诺、景颇、瑶、回、苗、佤、壮、汉等13个民族,大体上各民族都聚族而居,形成一个本民族小聚居而与其他民族大杂居的局面,民族关系的主流一直是亲善友好的。由于各民族频繁交往,互通语言的情况很普遍,不仅创造了良好的各民族语言的使用环境,使语言不易丢失,而且促进了边疆各民族的团结与繁荣。总之,双语(多语)是西双版纳包括克木人在内的各民族传统语言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各语言在长期的互动中已形成稳定、和谐的多语生活态势。克木人在西双版纳虽然属于只有2500人的弱势群体,在与傣族长期相邻共处的情况下,他们的房屋、衣着等都受到傣文化的强烈影响,以致不知道内情的人往往把他们误认为傣族。但他们热爱并尊重自己的母语,历史上并没有因为傣语是当地强势语言而发生语言转用,而是选择了兼用,而且,兼用傣语历史悠久。近60年以来,在国家通用语汉语的强势冲击下,克木人仍然没有放弃母语仍是选择兼用,逐步由克木-傣双语人转换成为克木-傣-汉三语人或克木-汉双语人。由于兼用语与母语互相补充,各自在不同的情景使用,使克木人既保存了母语的使用功能,又达到了族际间的沟通,为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短短60年间,他们便顺利地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跃入天然橡胶种植的现代农业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3.我国境内的克木人有“克木泐”、 “克木老”和“克木交”之分。克木泐为勐泐 (西双版纳)原住民,勐腊县的曼种、曼回结、曼回伞3个村寨属于克木泐;克木老为勐老 (老挝)移民,勐腊县的曼王士龙、曼东洋、曼中南西、曼迈、曼岗、曼蚌索、曼暖远7个村寨属克木老;克木交为勐交 (越南)移民,景洪市的曼播4寨均属克木交。历史上勐腊、景洪两地克木人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自然没有来往。直到20世纪90年代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民族文艺汇演,两地克木人因为语言相通,才彼此认同。进入21世纪后,勐腊县克木人各村寨连年联合举行“玛格勒”节(传统芋头节或丰收节)庆祝活动,同时也邀请过去从不来往的景洪4寨克木人参加。在“玛格勒”节庆祝活动中,人们唱克木歌,跳克木舞,打克木拳,舞克木刀,吃芋头、粽子等克木传统食品,老人们聚在一桌用细长的竹管吸饮克木坛酒,用传统歌咏的方式罚酒取乐,可谓盛况空前。这种情况与历史上克木人各村寨自行过节的惯例相比,我们看到克木人的族群意识逐年增强,而族群意识的增强正是建立在母语认同的基础之上,又反过来增强了母语的活力。
4.民族聚居为克木语创造了理想的生存环境。20世纪50年代以前,克木人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阶段,血缘关系是其社会结构的基本形态,土地为村寨公有,村民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刀耕火种农业,有土地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刀耕火种是一种高强度低产出的游耕农业,克木人常因追逐森林耕地或躲避瘟疫、猛兽、战争和其他自然灾害而举寨搬迁,村寨规模小而分散,又多位于深山老林的山箐边,与主体社会距离较远,再加上经济生活单一,仅靠狩猎和采集所得补足,与外界联系很少,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因而能长时期在族群内部通行母语,保持自己的语言习惯。80年代前后,附近国营橡胶农场主动上门扶持克木人种植橡胶,均被各村寨拒绝,有一位老村长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我们吃大米,不吃橡胶!”守旧的观念维系着传统的刀耕火种,封闭的村寨生活延续着母语的生命力。即使到了今天,克木人的经济生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母语仍是村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领域可以说60年来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5.历史上克木人实行民族内婚与氏族外婚制,不与外族通婚,家庭和村寨内仅使用母语,母语环境相对纯净。现在,由于民族外婚开禁,一些外民族人进入克木人家庭,母语环境已不那么纯净,但使用母语的绝对人数仍占优势,母语在家庭和村寨中的权威地位并没有被动摇。
6.母语的代际传承不存在问题,克木人的孩子一出生就在家庭和村寨里长大,第一语言获得均来自母语,母语所承载的传统文化也伴随着他们的一生,为他们提供本民族独特的认识事物的方式和行为准则,以母语为载体的民间故事、历史传说、民歌、谚语、谜语等口头文学,也一代代通过口传心授,滋润着他们的心灵,给他们带来愉悦和创作的灵感,保留并发扬了克木人优秀的传统文化。本世纪初,笔者曾在一次克木聚会中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一位老人忧伤地唱起祖辈因躲避战乱从老挝迁来勐腊途中的艰难经历,讲述细致,旋律婉转哀怨,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泣不成声。笔者虽暂不懂他唱的什么,但还是情不自禁为之感动——这就是活生生的民族历史在流淌,在传承,这就是克木语生命力最真实的体现!
7.关于我国境内的克木语是否存在方言差异的问题。我国学者陈国庆认为克木语没有方言差异,泰国学者苏葳莱认为中国境内的克木语有方言差异。二位学者不同的看法是由于语言采点的村寨不同造成的。陈国庆先生采自勐腊县曼王士龙1个村,不易觉察方言差异[8];泰国学者苏葳莱采自曼回结和曼蚌索2个村,她发现曼蚌索讲老式克木语,没有声调,但词首辅音有浊化与浊化较弱的对立;而曼回结的克木语则有高低2个声调的对立,但词首辅音没有浊化与浊化较弱的对立,其不同声调的对立替代了曼蚌索克木语中词首辅音的浊化对立。因此她认为云南克木语有两种方言[9]。据笔者实地调查了解,曼王士龙克木语与曼蚌索克木语比较接近,这两个村都属于克木老,而曼回结则属于克木泐,按克木老村寨的人的说法,只是感觉克木泐村寨的人讲话带有一点拖音。两种方言虽有所差异,但差异不大,并不影响克木人之间的交际,人们无需选择其他语言来补充母语方言差异造成的交际功能的不足。
8.克木语没有相应的文字,历史上曾使用实物书信进行寨际间的交往。例如,用烟草加槟榔表示邀请,用辣椒加火把表示事情危急,用辣椒、火把加麩炭表示拒绝等,民族历史、传统知识及口碑文学只能依靠口耳相传,因而克木人对自己的母语怀有深厚的心理认同感与强烈的依恋情结,以能熟练地说自己的语言而自豪,不愿轻易放弃。即使是外出打工的人 (克木人外出打工的人很少),即使是学龄儿童和少年,他们在打工地、在学校说汉语或傣语,但回到家里、村寨里他们仍然熟练地使用自己的母语。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克木人对笔者说:“我们回家必须说母语,否则老人会骂我们忘本。”总之,笔者在克木人村寨听到的最强音就是:“我们的语言是我们民族的标志,是我们民族跟其他民族不同的特征,是祖宗传下来的财富,如果放弃,我们的子孙怎么知道自己是哪一个民族?我们到国外亲戚家说什么话?”克木人对自己母语所倾注的深厚感情,正是克木语得以冲破强势语言的包围保存着活力的源动力。
以上克木语的使用状况说明,一种语言尽管使用人口少,但只要该语言的生存环境仍然存在,只要该语言的绝对多数使用者对自己母语有深厚感情,仍然把该语言作为主要的交流语言,这种语言就可以看作保持着活力的语言。
二
随着地区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我们也看到我国境内克木语的活力已经出现下降趋势:
1.历史上克木人没有受教育机会,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母语占据着他们生活的全部。进入现代社会生活后,母语仍只局限在家庭和村寨内部使用,政府机构、立法机构、集市、商店、学校等场所多使用当地汉语方言或傣语,电影、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体语言和官方用语都使用汉语或傣语,克木语使用范围相对萎缩,交际功能开始下降。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景洪克木交4寨受傣文化影响更大,他们笃信南传上座部佛教,寨寨有佛寺、和尚、佛爷,村民们四时赕佛,老人们在关门节至开门节期间入住佛寺周围临时搭盖的小茅寮,静心听经敬佛,把生命和希望寄托在佛的身上。他们跟傣族一样过泼水节、关门节、开门节,男孩7、8岁就进佛寺当和尚,现在男孩在接受国家义务教育的同时仍入寺修佛经、学傣文。因此,较之信仰原始宗教、过克木人传统节日的勐腊县克木泐、克木老10寨,兼用傣语更流利、使用范围更广。
2.掌握母语的单语人很少,仅限于幼童,而大多数克木人属于双语人或三语人。过去,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受教育程度的加深,儿童和青少年逐步获得第二语言傣语和第三语言汉语;现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已成大势,一些40岁左右的人甚至不能听说傣语。
3.目前尚无自治州或自治县一级的自治机构制定并推动语言规划,而克木人由于一直使用母语,对母语仅存在热爱的感情和使用的惯性,尚未产生保护母语的明确意识。
4.没有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媒介体。政府机关行文、布告、牌匾等都使用傣文和汉字;没有本民族语言的广播,极度缺乏本民族教师 (仅2人),因而也没有汉-克木双语教学 (小学一年级实行汉-傣双语教学或汉-单语教学)。但已村村通路、通水、通电、通电视,手扶拖拉机、摩托车、汽车、新式家具、太阳能、电话、手机、电视机、DVD也已普及,不少村民还盖起了砖混结构小洋房,客厅、餐厅、厨房、卧室、卫生间等样样齐全,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已进入克木人村寨。与此同时,与现代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汉语借词大批进入克木语,由于生计手段的改变,与传统刀耕火种生计方式息息相关的原有母语词汇便渐渐退隐,渐渐失去使用价值。
5.居住相对比较分散,村寨之间最近相距约3公里,最远相距约100公里。克木人村寨与傣族村寨和国营橡胶农场的生产队犬牙交错,许多人与傣族或汉族农工结拜为“老庚”(兄弟),一起切磋橡胶技术,互通有无,交往密切,人际关系越来越广,使用多语特别是汉语的场合也越来越多。
6.传统的族内婚开禁后,通婚范围逐渐扩大到傣、汉、哈尼、彝、苗、瑶、壮等民族,且大多是来自与西双版纳邻近的普洱市墨江、镇沅等县的农村人口以及四川、湖南、河南、广西等外地男性务工人员,他们以克木人传统的上门婚 (入赘婚)形式留居克木人村寨,族际婚姻的比例逐年加大。据笔者2010.12-2011.1的调查,在14个克木人村寨的556户中,已有168户克木人家庭成为不同民族的混合家庭,占克木人总户数的30%。其结果是克木人混合家庭和村寨内的语言环境开始变得复杂起来。总体情况是,男性外来家庭成员无论是哪一个民族都使用汉语,根据结婚年限的长短只能或多或少听说一点日常的克木语。因此,混合家庭中的克木人成员和村寨中的克木人与他们交流就只能用汉语;女性外来家庭成员则由于与婆母及村中克木人妇女交流较多,大都能听说克木语,孩子的第一语言获得也大都是克木语。其中,有3个村寨的情况比较特殊:一个是曼东洋。该村寨址上世纪60年代初被洪水淹没,人民公社统筹将这个村寨的村民全部安插到附近的一个傣族村寨。两个村寨合并为一个村寨长达3年之久,克木人与傣族之间相濡以沫、互通婚姻,家庭内交际和寨内交际多使用傣语,以致曼东洋从傣寨分出重新建寨后,克木人仍保持在大多数场合使用傣语而很少使用母语的状况,中青年以下的克木人傣语的熟练程度大都超过了母语。这个村寨混合家庭占全村总户数34户的47%,家庭内几乎都使用傣语或汉语,与寨内外的本民族人则根据语境的不同或使用傣语或使用克木语。这个村一位70多岁老人的语言态度很有代表性,她对笔者说:“人家跟我说克木语我就说克木语,人家跟我说傣语我就说傣语,人家跟我说汉语我就说汉语,尽管我的汉语很差,需要别人的帮助。”由此可以看出,曼东洋克木人开放包容的语言态度。另外两个是曼迈和曼岗,两村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曼迈村1983年曾连人带地被吸收进属于勐腊县乡镇企业的青年农场 (后改为勐腊县热作实业公司),这个农场以橡胶、咖啡种植为主,克木人农工与农场原有的其他民族农工一起劳动,互通婚姻,直到2008年公司解散,曼迈村回到所属乡镇。目前,曼迈村的混合家庭多达34户,占全村总户数69户的49%,家庭外来成员包括傣、汉、哈尼、彝、拉祜、瑶等民族。曼岗村是个只有16户的小村寨,混合家庭就有10户,占全村总户数的62.5%,而且外来家庭人员几乎都是来自墨江、镇沅等县的哈尼族,6男4女,结婚年限大都在15年左右,他们都说汉语。这两个村寨,克木村民之间都说克木语,与外来民族成员特别是男性成员交流大多都使用汉语。显然,由于混合家庭的逐年增多,使克木语的使用功能开始下降。
7.随着边境多民族社区开发程度的加大,中老、中缅国际通道的开通,大大改善了克木人村寨的交通状况,他们的村寨大部分位于国际通道边,其余也有乡间公路可通。这就促使克木人更多地接触汉语和傣语,也更多地使用汉语和傣语。
从以上情况看,克木人的社会生活领域在扩大,他们聚居的村寨逐渐向多民族杂居的格局发展,语言生活也随之丰富起来,加之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深入与国家主体语言的推广,克木语的交际功能便不可避免发生变化,整体效用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共使用环境、使用范围的发展趋势不容乐观。
三
通过上述分析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克木语语言接触过程中,由于受强势语言影响,正处在由稳定使用状态向不稳定方向发展的变化之中,虽尚未处入濒危状态,但依据戴庆厦教授的观点,已属于“衰变语言”[5]。
保护濒危语言已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那么,对克木语这样处于濒危之前的衰变语言,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来保护它呢?戴庆厦指出:“一种语言真正达到濒危状态,要想挽救已经很难,能做到的更多的是对濒危语言的抢记。因此,挽救保护应该在‘语言衰变’时期就开始”[7]。徐世璇指出:“一种语言不能等它濒危了才采取抢救措施,而是应该从现在起就要提倡双语,从现在就开始强调不要丢失本民族的语言。如果能唤醒全世界人们对语言文化的重视,它的意义要远远大于成功挽救了一两种濒危语言。”[7]
提倡双语生活可以做到语言功能互补,对保持母语的活力具有重要意义。60年来,由于国家推行民族平等、语言平等政策,双语生活 (多语生活)已逐渐成为我国民族地区基本的语言生活。克木人正是双语生活的受惠者,其双语生活历史悠久,确实起到了保持母语活力的作用。但双语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使用人群的语言态度发生变化不愿继续使用母语,就可能导致语言转用,造成母语濒危乃至消亡。前述事实说明,克木语已经处于衰退过程之中,因此,目前迫切要做的工作,就是要通过各种有效措施,增强克木人对母语文化价值的认识,以强化母语使用意识和母语保护意识,促进双语(多语)传统延续下去。
强化母语使用意识和母语保护意识绝非一日之功所能实现,需要全社会的持续关注与切实行动。这其中,国家的政策、地方政府的行动、学者的介入,尤其是本民族全体成员的参与都缺一不可。
在当今高科技迅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语言已经被提到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的高度来看待,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指出:“公民的语言能力应看作国家重要的语言资源,看做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语言能力主要指母语能力和外族语能力”。那么,国民语言能力有哪些标准呢?李宇明指出“国民语言能力标准,其实也就是义务教育阶段的语言能力教学标准”,并对此提出了“几个关键点”,其中,与少数民族相关的有:1、“在基本上是双语的少数民族地区,应实行双语或三语目标。双语目标是:一门少数民族语言加上汉语;三语目标是:一门少数民族语言加上汉语和一门外语。” “多语种能力应在义务教育阶段完成”。[10](P1-6)为此,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扶持及教师培训,持续倡导、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民族语言文字的“双语教学”。
到目前为止克木人在义务教育学校中仅有2位教师,他们都只用汉语进行教学。所以,摆在民族语专家学者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就是加紧运用现代信息手段,收集、整理克木语语料,灌制音档保存,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一套辅助性的克木语拼音书写系统 (拼音方案),用以编写并出版汉-克木双语教材和普及读物,提供给克木人学习。同时,地方教育局应着力培养克木人教师,以便尽快在有克木人学生的学校开展汉-克木双语教学。此外,地方政府应成立专门机构,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展保护克木语的工作。例如,可以通过一年一度的“国际母语日”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通过决议,把每年的2月21日定为世界母语日,提倡使用母语,以保存语言和文化多样性。金观涛、刘青峰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从名词使用和观念转移的角度论述了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当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分子的的世界图式由“天下”转为“万国”,又转为“世界”时,他们所要再造的政治共同体,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王朝国家,而是一个由国民让渡主权而形成的“民族国家”。参见《从“天下”、“万国”到“世界”——兼谈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页。,设计有针对性的不同主题的纪念活动推广母语教育,鼓励人们掌握母语和国家通用语;可以通过克木人的“玛格勒”等传统节日庆祝活动,编演提倡使用母语的节目,以激发人们爱母语、说母语的热情;可以鼓励混合家庭的家庭成员互教互学彼此的语言,尤其要鼓励其中的克木人家庭成员珍惜自己的母语,稳定使用自己的母语,等等。正如孙宏开教授所说:“建立一个和谐的语言社会,就是在一个多语言的社区内,所有成员除了使用母语外,还能够熟练地使用社区内所有成员的语言,而且自己母语的活力不会降低。这是一个理想的境界。语言学家们应该努力,政府官员们应该努力,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们应该努力,所有社区的成员应该努力。”[11]
语言的活力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一个语言的使用范围和使用功能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濒危现象日益凸显的今天,我们不能坐等某一语言已经濒危才去做保护或挽救工作,而要在普遍调查了解的基础上,首先筛选出像克木语这样的还活跃在人们口头上的“活态”语言,采取适宜的保护措施,调动人们的母语情结,那么,即使这种语言整体效用呈现下降趋势,也不会急剧衰退,也不用到濒危时再花更多的人力物力去挽救。
[1]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中国的语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徐世璇.濒危语言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3]渐逝的文明——拿什么拯救你,少数民族濒危语言[J].中国社会科学报,2008,11(7).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8国际语言年报告[A].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2008)[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5]戴庆厦,张景霓.濒危语言与衰变语言——毛南语语言活力的类型分析[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社版),2006,(1).
[6]哈斯巴特尔.保护没有文字的濒危语言[N].中国科学报,2009-11-18.
[7]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纪要 [J].民族语文,2000,(6).
[8]陈国庆.克木语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9][泰]苏葳莱.(中国)克木语词典[M].曼谷,2002.
[10]李宇明.保护和开发语言资源——序《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8)[A].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8)上编[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1]孙宏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程度排序研究[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社版)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