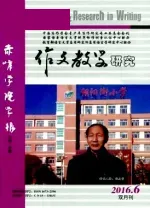“对语理论”背景下看教材经典对作文教学的启示
浙江 杨春城
一、“对语”理论的内涵
中学语文教学的发展产生了“语言教学论”、“言语教学论”、“对语教学论”三种理论,“对语论”不是对“语言论”和“言语论”的否定,而是一种扬弃和超越,甚至是在更高层次上的涵盖。
“语言教学论”和“言语教学论”在语文教育界已经兴起多年,它们为语文教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缺陷和弊端也日益显现,这里不再赘述。在总结前两种教学理论、借鉴巴赫金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语文教育家王尚文先生提出了“对语教学论”的理论设想。与此同时,围绕着这个话题,一些语文学者也发表了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实践构想。
巴赫金学说最为核心的一个概念是“对话”,构成对话的话语是“对语”,即“对话语言”。巴赫金认为,我们平时的言语表达都是有对象的,而言语作品也是如此,任何一种言语表达都是“主体间性”的,没有无主体或绝对单一主体的言语表达,任何一部作品都是一个“对语”。综合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对语”是对话中的言语,它发现了听者的价值和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对文本是以意图、立场、观点、思想为单位进行解读,如果我们能从对语的角度,以一个新的思路来审视并合理安排我们的作文教学,将大大提高语文作文教学效率。
二、“对语论”对作文教学的启示
巴赫金在论述对语理论时总结出了对语的四个基本特征:体式性、情调性、诉诸性和应答性。一部好的作品应具有这四个特征。“对语论”带给语文阅读教学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我们所学所教的作品都是以对语的形式存在的,作品里面不仅有叙述者(作者),更有听者(读者)。叙述者的遣词造句、谋篇布局、抒发感情、发表议论等等,都是有针对对象的,无论在文中这个对象是具体的真实的,还是抽象的虚拟的,它都是无法被否认地存在着。所以我们应该知道,作品中的语言就是对话中的语言——“对语”。我们可以看到教材中的优秀作品一般都具有这几个表现特征。
反过来说,我们在与阅读教学密切相关的写作教学中若能自觉地注意到这四个特征,那么学生的作文兴许就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语言风格、明确的针对性、真实的情感和打动人心的力量。
(一)体式性
根据巴赫金和王尚文的论述,“体式”一词的含义要比“体裁”宽泛得多。对语的体式性特征是指当我们在说话写作时,不仅要掌握所用语言的词汇、语法体系等,更要遵循某种形式,服从某种社会化的规定,即巴赫金称之的“言语体裁”,王尚文称之为“体式”。例如,同样是“如何防范火灾”的主题演讲,在分别面对成年人、中学生、小学生时,演讲者的说话语气、口吻,选择词语的深奥浅显程度肯定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叙述者采用的言语体裁不同,即作品的体式不同。反过来说,我们对某类作品的体式越了解越熟悉,就越容易深入地理解该类作品,并在写作中学习模仿。
2008年温州市高三第二次适应性测试中的第5题,要求选出语言表达得体的一句,其中B选项是:中国政府历来主张地区间的矛盾应以和平方式加以解决,反对以武力相威胁,千万不可话不投机就动刀动枪、兵刃相向。这句话考察的就是我们对语言体式的理解,如果学生能够凭阅读的经验意识到,这其中的前半句是正式的公文体,后半句是一般口语,二者体式不同,那么就可以明确知道这句话表达不够得体。我们来看下面高中课本里的两段文字: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 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 ——余秋雨《道士塔》
传说中第一个清高之人,恐怕要数许由了。据说唐尧要把天下禅让给他,他认为这话污染了耳朵,因而跑到颍水边上去洗耳。此事不知真假,但在古代却传为美谈。这美谈又反映了古代士人相当混乱的价值取向…… ——金开诚《漫话清高》
同样是因年代久远而变得模糊的历史事件,余秋雨采用设想还原的方式,深入细节描写,让王道士的愚昧无知如电影画面一般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金开诚对许由洗耳这件事却用简洁直接的语言完成材料叙述并表明自己的观点。那么,二者的语言组织方式是否可以互换一下呢?当然不可以!《道士塔》侧重于叙事抒情,《漫话清高》侧重于说理,虽然二者都是借助历史材料来完成的散文,但体式不同,所以材料使用方式也不同。
这种体式问题看似简单,但我们是否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呢?我认为没有。看看我们学生的作文就清楚了。有的只会简单生硬地概述材料,有的恰好相反,文中堆砌的是大篇幅的编造史实,而且很多学生在高中三年里写作风格几乎没变化,难道我们在高中课本只选了一种类型的文章吗?问题出在哪里?我想就是我们平时作文教学中对作品的体式关注不够,从而导致学生只会用一种体式来写作,甚至只会按照几年一成不变老套的体式来写作,毫无变通。对语体式性的重要性,不容小觑。
(二)情调性
在对语论的审视下,我们会发现,任何作品中的文字都是处于交流或交流的意向中的,而这其中的语言,是带有说者的个人情调的,包含着说者的感情和意图,因此对语具有情调性的特征。在理解一篇作品时,必须要注意到它的情调性特征,即要理解它的文字意义,更要揣摩说话者的心态,这样才能准确全面地理解作品内容。请看下面的文字:
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看天空被夕阳烘成桃花色的薄云……天已快夜,别的雀子似乎都在休息了,只杜鹃叫个不息。石头泥土为白日晒了一整天,草木为白日晒了一整天,到这时节各放散一种热气。空气中有泥土气味,有草木气味,且有甲虫类气味。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来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
——沈从文《边城》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
——鲁迅《祝福》
《边城》和《祝福》在我省所用的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都有选入,这两段文字也为我们所熟悉。对比这两段文字,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不同,但实际上在阅读过程中,最能打动我的是它们截然不同的语言情调。同样是描写傍晚景色,第一段语气自然舒缓,我们可以身临其境般地体会到清新、纯朴的湘西风光,也能体会到翠翠无聊失落而又有所期待的心情,这正是《边城》独特的语言情调。很多人喜欢《边城》,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沈从文的魔笔赋予作品的特殊的情调,对于一般的读者,与其说喜欢《边城》中的人物、故事,还不如说是沉迷于作者的叙述情调带给我们的独特的审美体验之中。第二段文字是鲁迅的小说《祝福》的开头部分,作者描写了年底鲁镇压抑的气氛,渲染出祥林嫂的悲剧命运。对文字稍有些体会的人,读到这一段,肯定不会简单地认为作者是在向我们展示年底鲁镇的热闹气氛,相反一定会有一种沉闷的感觉。而这种阅读的体验是从文字的情调中获得的。鲁迅用朴实、生动的文字编织了一张叙述之网,形成了作品的情调,在读的过程中,沉闷又有点压抑的感觉渗入到读者的心绪之中。
我们平时的作文教学中,是不是引导学生注意学习借鉴优秀作品中的特定情调并留心笔下流淌的情调呢?一个人,他的写作习惯可以是相对固定的,但他的作品中的情调不应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应该是与作品内容相一致的。
(三)诉诸性和应答性
对语是对话中的言语,对话就要有针对的对象和陈述的任务,所以诉诸性就是作者要通过作品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诉诸某人。有的时候,叙述者并不仅仅是在向对象倾诉什么,反而像是在回答听者提出的问题,这就是对语的应答性特征。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更好地以意图、思想、观点等为单位真正深入地理解作品了。
对语的诉诸性和应答性体现得最为明显的是李密的《陈情表》。它是李密呈给皇帝的奏折,所以有明确的陈诉对象,有强烈的诉诸性。文章的一开头,李密先向晋武帝陈述家庭的不幸和祖母的恩情,悲惨凄切的语言让每位读者为之动容,也让晋武帝由愤怒峻责化为同情怜悯。而第二段的应答性更为突出些,李密害怕晋武帝不理睬他的遭遇,进而紧紧逼问“你牢记祖母恩情,难道我对你就没恩可言吗”,李密就是在设想晋武帝的提问之下开始了第二段的应答——缕述皇帝之恩,继而倾诉自己进退两难的处境。第三段提出了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纲领,再次强调自己的处境,打消晋武帝的疑虑,所以本段以诉诸性为主。最后一段具有明显的应答性。李密似乎想到晋武帝也许会问,“你要尽孝不能离开祖母,难道就不尽忠了,就不理我这个皇帝了吗”,于是明确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先尽孝后尽忠,并提出确切的理由,再次诚恳地表达自己的忠心。这篇奏折正是因为有强烈的诉诸性和应答性,所以感动了晋武帝,也感动了从古至今的读者。
“对语”总是要诉诸某人,针对一定的对象来表达思想、交流情感。这对象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群人;可能是清晰的、明确的,也可能是模糊的、不具体的,但不管怎么说,“对语”有一定的受话人这个事实是抹杀不了的。“表达的诉诸性”是我们当前写作教学迫切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当前写作教学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写作对象的缺席,从而导致了整个写作行为的虚假。学生在课堂上的写作有对象吗?又有几个学生在作文里真诚地表达自己,反省自己的内心世界呢?很多情况下,他们写的是连自己也不信的编造之词。然而,学生在写作教学之外的写作行为却是有实实在在的对象的,他们写日记的对象是自我,写信、发电子邮件的对象是某个朋友或亲属,写情书的对象则是某个暗恋已久的同学……如果我们的学生在写作时能有一个针对的对象,哪怕是一个虚拟的对象,借以叙述议论抒情,他的作文怎么可能枯燥、单调,而无真情实感呢?
“对语”理论的提出,为我们的作文教学开辟了一片新的思考空间。
[1]黄琼.言语教学论的两个误区.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07.3.
[2]徐默凡.语言还是言语.语言学还是言语学——从“言语教学论”的争议谈起.语文学习.2007.3.
[3]蒋成瑀.一个虚拟的教学教育理论命题——“语文教学即言语教育”辨.语文学习.2007.2.
[4]俄国.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5]王诗客.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三种理论评述.语文学习.2007.11.
[6]周燕.“听者”的重要性──巴赫金“对语论”对语文教学的启示.课程·教材·教法.2007.12.
[7]周燕.语言·言语·对语——关于语文教学本体的思考.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07.3.
[8]于龙.理解语文:从语言、言语到对语.湖南教育.2007.12.
[9]周芙群.阅读教学实践中不可忽视的“对语”.现代语文.2007.8.
[10]王尚文.黄琼.巴赫金“对语”的启示.语文学习.2006.11.
[11]黄琼.对语的情调性特征.语文学习.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