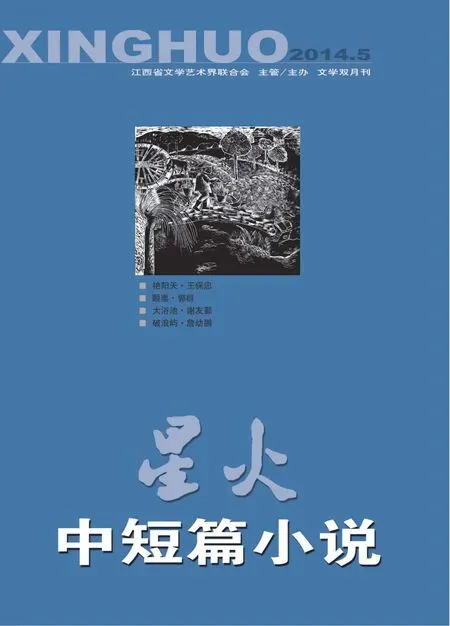紫河车
□ 颜德良
来来,抽我的!
土狗掏出烟,一屋子的人,他一个个地散,轮到钩子时,他只瞟了钩子一眼,就想笑,抿紧嘴才把烟递过去。钩子接过来,二指夹着,啪!打燃火,瘪起肚子,深吸一口,直到锁骨都露出来了,才睁开眼,噗——!长吐出一口烟,咂嘴道,好烟!
那样子,好像在吸溜毒。
一屋子的人,都在谈论吃,听土狗吹,哪哪的菜好吃,哪哪的馆子又开张了,柴火灶,鼎锅饭,土家菜,风味独特,够威够辣!说是帝王大酒店,新出一道汤,是用一只陶罐,在大瓮里用炭火煨制而成,放的是一种秘制原料,那汤,格外地清香,奶一般浓郁,喝起来,那个鲜啊,崽!三天以后嘴还是香的!说得钩子他们一个个两眼放光,哈喇子流得丈把长。
钩子舔了舔嘴唇,骂土狗,你个狗屌的,属猪,就会吃,上不亏嘴巴,下不亏鸡巴,这湘州城里的馆子都给你吃遍了,你活十年,硬当得老子一世!
土狗说,你傻逼么!现在太平盛世,不吃干什么?把钱留给你老婆嫁人呀!现在又不要你献身,又不要你解放全人类,亏待自己干什么?吃好喝好身体好,就是对社会的贡献。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老师教的,忘啦!
土狗的能吃会喝,是家道渊源。他祖上三代开饭店,就是到文革前,他父亲接手时,都还是饮食公司经理,既便是在物资馈乏的七十年代,他家也没断过荤腥,少过油腻。人家是想着如何粗了吃,他家是想着如何细了吃。他从小锦衣玉食,食不厌精,到了煤炭局后,习性变本加厉。同样一只鸡,人家或炒或炖,就这么样吃了,他不,他要吃出花样来,鸡胸割下来炒着下酒,鸡骨头剔出来炖着喝汤,鸡腿鸡翅剁下来烤着吃肉;鱼,要去了皮,剔了骨吃;青菜只吃心;带须的豆芽是不吃的;胡萝卜必切成薄丝才行;吃汤,他也要滗去上面的那层油,捞去肉渣,就喝那“水”,说是既营养,又不油腻,喝起来,是格外的清爽。在外交际,他更是专拣好吃食处逛,哪里出了冷僻菜,哪里就有他。
阿水一下跳起来,叫道,好,老土!你这是腐化堕落,老子要去告发你!
土狗笑道,哈!你去告好了,你还不是和我一样的!
钩子椰榆道,他这不是腐化堕落,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
土狗却嗤鼻道,嘁!有没有搞错。这也叫灯红酒绿?那还有吃人体盛宴的呢,你见过么?人家日本,拿一美女,全身脱得精光,不着一根纱,躺在那里,把身子当碗,盛菜给你吃,我在扬州重庆就见过呢!那才叫剌激!才叫过瘾!才是灯红酒绿呢!
钩子惊叫道,我崽!那是吃菜啊,还是吃人啊!
土狗剜他一眼,说,你管别个吃什么,人家那是一种享受,是吃的最高档次,食文化,晓得吧!像我们这等俗人,图的不过是一时快活;人家超凡脱俗的人,追求的那就是一种境界了。象你钩子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钩子红着脸,说,你当我真舍不得?我是不想糟蹋钱,想留一点给崽女,晓得吧!不然的话,我哪天潇洒给你看!
土狗大笑,说,你拉倒吧!你死卵样子,崽女还要你的钱?等到你想要潇洒时,黄土埋到脖子了!还哪天?下辈子吧你!
土狗与前妻生的是女,归前妻,不要他管,所以他过得轻松自在。
钩子不服气,红着脸顶他,你出色!你有钱!你有钱就请我们去潇洒呀!
土狗张大嘴,失声哑笑,说,嗨呀!好大的事啊!不就一餐酒嘛?好像我冒请过你们似的!哪天就请你们到帝王大酒店去,让你开开洋荤,见识见识那道汤,那不光是鲜美,而且还滋阴壮阳,十全大补。你尝过了,你才晓得,你不枉来世上一趟了,冒白活!末了,却不无惋惜地说,可惜!你钩子不能吃!
钩子瞪着眼,问,为什么?
土狗猛一下冲他说,你要是吃了,你屋里的辣厉婆就遭秧了!
众人轰地一下笑开了。
狗屌的,你以为我像你!钩子红着脸骂了句难听的话,又说,吹牛皮不犯法!你说说叫什么汤?我倒要看看它到底有多牛逼!
土狗故意逗他,天机不可泄露。到时候去就晓得了。
钩子不齿他,脸一扭,说,死开!懒得跟你讲!要去,明天就去。我来一趟不容易,正好明天辣厉婆也休息,她早就想去看她了,她不是明天快要生了吗?明天去。省得大家到时又多跑一趟!阿水,你说是吧?
阿水一连迭声地附合道,对对!铸钟不如撞钟,明天去!
土狗一副被宰相,骂自己,操!我傻逼啊!死钩子原来是算好的!
众人都笑道,嘿!开玩笑,我们钩子岂是跟你打鸟耍的?
妇产医院就在市区的西边,靠河,河两岸是沿江风光带,坡堤上是绿地,植有花草,被隔成各种几何图案。河边是成溜的垂柳,柳条在阳光下泛着绿,枝头爆长出嫩芽,在微风中轻拂着,柳条下砌有石凳石椅,供路人歇息。时近正午,有不少的护士陪着孕妇在那里散步,闲聊,看波光粼粼的河水在阳光下缓缓地流淌。
马路的这一边就是医院,是喧嚣繁华的闹市,鳞次栉比的酒楼饭店。
土狗老婆的病房是单间,宽敞明亮,有空调,带卫生间和热水器的那种,房间里摆满了各种水果和营养品,并专门请了两个陪护在侍候。一个白天,一个晚上。因为是保胎待产,也就没有多少事可做,显得很闲,不需要操什么心,土狗三天两头的来打个转,问候问候,其它时间,乐得在外逍遥。
钩子老婆拉着土狗老婆的手,在轻声说话,俩人亲得跟什么似的,吃吃吃地笑,酸儿辣女的,说着女人之间的私房话。男人们都插不上嘴,就显得多余。土狗像个木头似的戳在那里,摇来晃去的,好像一个不倒翁。钩子耐不住这种场合,就退出来,站到走廊上去抽烟。
不知什么时候,土狗站到了身后,一口接一口地吐着烟,满脸的无奈,说,生又不生,在这里磨死人!
钩子咧嘴笑了笑,不好说什么。土狗虽是一个小科员,但与钩子是发小,是死铁,就利用工作之便,与他合伙倒腾锰矿,生意上,钩子主内,在山里开矿洗矿;土狗主外,负责出外联系销售,俩人做得隐秘,配合得默契。可生活上,却是一个喜欢晒富,一掷千金;一个喜欢叫穷,一毛不拔,习性截然相反。
钩子与老婆是原配,一天不吵,浑身就痒;土狗与老婆虽是老少配,俩人却一拍即合,意气相投。
那天,帝王大酒店为了扩大影响,招徕顾客,在酒店临街口设了一个啤酒擂台。谁能在一分钟之内喝完三瓶啤酒,当场奖励一万块钱。
一时间,人头攒动,打擂者如云,其中就有土狗和他现在的老婆。但那些打擂者,不管是生男猛女,还是啤酒大汉,没有一个不超时的,都在第二或第三瓶上卡了壳,不是噎得作呕,就是呛得喷鼻,一个个灰头土脸,狼狈不堪,在哄笑声中低头鼠窜,惟独土狗一人顺利闯关。就在土狗正要走向领奖台时,只听底下一声,踩一脚!应声,就跳上来一个风摆柳似的姑娘,说,这里还有一个呢!也不打二话,扭转身,就拿过三支酒瓶,撬开盖,一声计时开始,仰着头,像吹喇叭一样,将三支酒瓶成扇形展开,同时对准嘴,一时间,四周鸦雀无声,万众瞩目。只听得一阵咕噜咕噜冒泡声,好似灌水一般,酒从喉咙里进,气从鼻孔里出,不呛不噎,一口气,三支啤酒一气吹完,时间不长不短,正好一分钟。
看得土狗目瞪口呆。
四周哗地响起一阵尖叫声,掌声似鞭炮一般当街炸响。
土狗心里暗暗称奇,他酒经考验,却从没见过,这么一个瓷瓶似的靓妞,竟有这般功夫,实属罕见,真个是巾帼不让须眉,算是开了眼了。就对姑娘说,美女,还能喝吗?,要不,我们换个地方再喝?
姑娘毫无惧色,微笑道,换个地方就换个地方,我还怕你不成!
土狗就把姑娘带到自己公司,拿来两只敞口塑料酒杯,倒上酒,又倒满两小盅白酒,连盅带酒分别沉到塑料杯里,说,我们不用手,各自用嘴叼起来喝掉,不跌不洒,先喝完的算赢。怎么样?
姑娘笑了,说,这不就是喝潜水艇酒吗?有什么稀罕?喝就喝!
好,我先来!土狗率先叼起酒杯,张开双手,耍杂技一般地,小心翼翼,颤颤微微地咬住杯口,缓缓抬起头,伸长脖子,吱——吱!小口地吱溜着吸。姑娘学着样,也慢慢地叼起酒杯,咬紧牙,涨红着脸喝,喝不到两口,姑娘咬不动了,杯一晃,噗哧一声呛鼻了,酒杯咣当跌在地上,酒,淋了一脖子,她笑岔了气,抹着胸口,咳着说,哎呀,累死我了。这样不公平,欺负我们女孩子!
土狗停下来,眨巴着眼问,那你说怎么喝?
干脆!姑娘将旁边一件啤酒搬上桌,说,分开,一人一半,喝不完的才算输!
随你!土狗很爽快。两人就这样,并不要菜,你一瓶,我一瓶地拼起酒来。不过一个时辰,两人都面如关公,烂醉如泥,一个趴在桌上打鼾,一个躺在桌下哼歌,鼾声此起彼伏,擂鼓一般,桌上竖满了一桌的空酒瓶,犹如一片小森林。
从那以后,土狗就与姑娘好了起来。后来,不知用了什么法子,慢慢把姑娘从桌上弄到了床上,做了自己的新娘。
老牛吃嫩草,土狗自是恩爱不尽,但姑娘正值青春年少,土狗已过不惑之年,哪里是姑娘的对手,实在是银样蜡枪头,每晚的功课,就做得十分的吃力,精力渐感不支,几个回合下来,便有些气喘嘘嘘的了。老婆就打趣地在他腮帮子上拍打着说,下去吧老头,别硬撑着了,怪累的!
弄得土狗狼狈不堪的,好不懊丧。
早上起来,土狗呵欠连天,浑身酸疼,对着镜子一照,自己都吓了一跳,皮泡脸肿的,眼圈发黑,好似一张熊猫脸。
土狗一下有了危机感,这以后,就注意上了养肾,除了药外,常辅以食疗,不断从外面找一些补品来吃。工作应酬,也忘不了点一些乌龟脚鱼一类的菜肴,可那东西饲养的多,野生的少,大都是激素催大的,营养有限,收效甚微,起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本地的餐馆吃遍了,土狗就把眼光投向了邻近的县市。
一日,他不知从哪里打听到邻县的山寨有一家牛肉馆,有一道菜叫牛宝,不仅味美,还极是温肾,就奔了去,吃过之后,果然不错,接着又去一次,过后仍未尽兴,就弄来一根带回家,按照记忆中的方法,又把一些鹿茸蛤蚧肉苁蓉冬虫夏草什么的,都丢进去,象炖鸡一样的一锅炖了。炖得烂烂烀烀的,香味四溢,钩人馋虫。这家伙是饕餮之徒,又滋补心切,竟就着一瓶好酒,有滋有味地全吃了。大概这东西是个发物,药下得过猛,就补过了头,这一顿吃下去,坏了事了,躺在家里,整个的人出不得门了。
一连两天土狗不来矿里,钩子犯了嘀咕,就寻到家里去了。刚进门,就见他老婆低着头往外走,偷人似的,连招呼也不好意思打。再一看土狗,涨红着脸,弯腰曲膝,双手抱腿地正坐在沙发上,难受得直不起腰。
钩子吃了一惊,忙问,怎么了,病啦?
土狗埋着头,没心情理他。
钩子一探手,哎哟,额头烫手呢。忙说,走!赶快,我送你上医院!
土狗把手一甩,不去!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钩子叫道,那怎么行,在发烧呢!
土狗大声说,我说不去就不去!
钩子一怔,看这样子,不象是生病,就问,你到底怎么啦?
土狗四处望了望,见没外人,就把吃牛宝的事,照实说了。
钩子两眼瞪得溜圆,说,全吃了?
土狗低声说,全吃了。
我崽呀!钩子一声惊呼,紧接又着问,那现在怎么样?
土狗苦着脸说,底下又胀又痛。
钩子要扯开他裤子来看,土狗两手护着腰带,死命不让。钩子只好摊开手,站在一旁看着他。
土狗可怜巴巴地望着钩子问,怎么办?
钩子说,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还不赶快去搞一盆冷水,把毛巾打湿,敷在上面,再吃点清凉降火的药试试看。
土狗赶紧跳下沙发,弯腰哈背的,两手捂着裆,一路小跑着,朝浴室跑去。那鬼鬼崇崇的样子,好象在做贼。
看着土狗的背影,钩子忍不住骂了一句,什么卵东西都吃,吃死你!
事后,一想起这事,钩子就忍不住要笑,笑得土狗恼怒交加,冲着他吼,你笑死!笑摆子!你再笑,老子阉了你!
走廊上,俩人抽了一阵烟,土狗见钩子着实无聊,就对钩子说,行了,看望一下就可以了。反正她还冒生,冒什么事,你们就先过酒店去吧,我等一下再过来。
钩子说,那也好,免得大家都傻子一样的呆在这里。
几个人走进包厢,见包厢里装修得富丽堂皇,好不气派,钩子就不住地咂舌,崽崽!豪华豪华!阿水拉开包厢的后窗帘,朝外乱望,见后面就紧挨着妇产医院,与酒店的隔墙中间还留有一道栅栏门,如果穿过这道门,就能直接走到酒店来,可以少走一截冤枉路。阿水就叫道,哎呀,我们亏大了!早晓得,我们从这后门直接过来就好了!
土狗随后走进来,一听就说,嘿!那门不是给你们过的!
钩子说,不给我们过,那给哪个过?
土狗说,人家自己过,不行呀!
钩子又纳闷了,那还隔开干什么?
土狗呛了他一句,你管呐!人家高兴!
钩子受到抢白,眨巴着眼,哑喉了。
这时门一推,服务小姐轻步走进来,开始斟茶倒水。
土狗拿出派,敞着衣,斜靠在椅子上,把小腿弯着,平架在另一条腿上,打开菜谱开始点菜。说,美女,你这里有什么经典菜啊,推荐一下吧!
小姐笑道,王科长,你是熟客,你知道的!酒店小姐是逢人封官,逢女减寿。
土狗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说,那倒也是。就飞的跑的游的,各式特色的菜点了十来个。
钩子在一边直嚷道,够了够了!才几个人,点那么多干什么,到时又吃不完,倒掉又可惜了。
土狗说,吃不完怕什么?正好给你打包呀!末了,他就说,好了。每人再来一份紫汤,就把菜谱一合,说,先就这些,不够再点!
小姐仔细核对了一遍,欠着身说了句,王科请稍等,就退出去了。
土狗老婆在一旁早就不耐烦了,叫道,架起架起!
几个人就架起麻将桌,土狗老婆哗啦一下,把麻将往桌子上一倒,唏哩哗啦地洗开了牌。
不一会,服务小姐又进来了,俯在土狗身边说,王科对不起,紫汤没有料!
土狗不高兴了,冲着小姐说,冒得紫汤,我到你这里来干什么?我别的地方冒饭吃啊!
小姐陪着笑说,王科长,真的很抱歉!一时没有原料。这个,你也知道,它是算不到的,也霸不得蛮的!
土狗就怔住了,望着钩子,好像在求援。
钩子在一旁懵懵懂懂的,不知他俩说的什么,就问,什么?
土狗就说,就是我给你们说的那道汤。是这个酒店的招牌菜,在我们省也是独一无二的。现在一时冒得料。
钩子听了就冲小姐嚷道,你们这叫什么招牌菜?干脆自己把牌子砸了算了!
小姐闻言就陪着小心说,先生,实在对不起!要不稍等等好吧,也许等一下就有了呢!有时候就这样,这料,要么不来,要么接二连三地来。
钩子作了不主,就望着土狗。
土狗就说,好。那就照点吧!
小姐直起身,又退出去了。
几个人又坐下来,像摸螺蛳一样地搓开了牌。钩子老婆与阿水对桌,土狗与——,哎,土狗一抬头,见钩子还愣着不动,就叫他,还不坐下来,你还站着干什么?
钩子却说,我不打!
土狗瞪起眼,你发癫!我们三缺一,你不打,哪个打?
钩子说,我冒带钱,打不起!
老婆冷着脸,坐在一旁不出声。他们夫妻是AA制,钱,各自为政,互不干涉。
土狗放下手,走过去就在他身上乱摸,他低头摸了半天,怎么也没找到口袋,原来钩子将四个口袋都缝死了。土狗怄得吐血,使劲朝他腰上掐了一把,痛得钩子杀猪般地叫。土狗骂道,你嚎死!我硬是造了孽咧,碰到你这号角色!说罢,从怀里掏出一沓钱,数出几张,啪地拍在钩子面前,说,我不要你出钱好不好?嘞!输了从帐里扣,赢了再还给我。这总可以了吧!死钩子,天天死人,又不死你!
钩子揉着被掐痛的地方,眉一扬,得色地说,唉!冒办法,这命长,想死都死不了!
土狗没好气地说,去投河唦,那河高头又冒盖盖子!
钩子一亮牌,说,嘞!冒得空,被人拖下水了,逼良为娼,要陪人打牌呐!
土狗扭头冲他老婆说,辣厉婆!你怎么嫁给这号人哪——硬是缺的德!
他老婆就板起脸,冷冷地说,我前世冒做好事,这世遭报应呐!
哦?钩子一脸惊世骇俗的模样,极具夸张的表情。
摸了几圈,土狗的手机唱起来,他歪着头,用肩和耳朵夹住手机,边打边说,是我。啊?生了?生了个崽?土狗一下冲起,哎呀!好!好好好!哦——剖腹产呀!嗯,好!那你们俩个还守在那里吧,随时有事,随时喊我。土狗嗯嗯啊啊地应答着,笑得嘴巴都歪起。大家都一下停住手,不吱声,一齐望着他笑。待他通完话,大家把牌哗啦一推,都站起来,说,走走!不打了!不打了!我们到医院看月婆去!土狗满面春风地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她现在在监护室里,重点保护着,要过二十四小时才能出来哩!我们去了也看不到。我们还是打我们的吧!来来来,你们放肆玩,等下吃完饭,我们就去K歌,去蹦迪,全部我拣单!
说话间,窗外的梧桐树上,凑巧飞来几只鸟,在枝头上跳来跳去的,嬉戏着,啁啁啾啾地叫着,清脆宛啭,歌吟一般的动听。
钩子笑着说,好兆头啊,老土,鸟都在恭喜你呀,后继有人了,添了个满崽!
土狗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嘴上却说,嗨,又多了张嘴!
钩子笑着打趣道,又多了个小酒鬼!
钩子老婆呀地一声尖叫,好像中了奖,大笑道,哈!我就讲是个崽吧,你老婆偏不信,硬讲是个女。怎么样,我讲准了吧!哎,崽长得好不好看?像谁?有好重?
土狗正在亢奋中,站在那里打转,手脚冒地方放,不晓得做什么好,光晓得笑,不晓得答,满脸喜气洋洋的,那模样,好像又要入洞房。
阿水在一边见了,忍不住笑,说,哎,醒醒!你想给崽起个什么名字啊!
这下倒把土狗问住了,他挠挠头,嘿嘿傻笑,呵呵!还真冒想到这个事呢!大家就七嘴八舌地出主意,钩子脱口就说,这还不好办!就取娘一个名字,伢(爹)一个名字。叫王好。好是由女和子字组成的,人生就是由男和女组成的,有崽有女也就是好!他老婆瞪他一眼,立马打断说,那是妹子的名字,应该叫王海,海,浩瀚宽阔,气势澎湃,男人就应该有这个胸怀;阿水抢着说,我看叫王鹏也蛮好,志向高远,鹏程万里,有寓意!一时间,几个人你争我吵,叫得热火朝天的,起什么名的都有。奇怪的是,都喜欢起单名,没一个起双名的。把个土狗欢喜得什么似的,连说,都蛮好!都蛮好!
就在这时,只听见门外咚咚两下,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服务小姐一闪身走进来,快步走到土狗面前,欢快地说,王老板,紫汤来料了!
土狗大喜,叫道,好!那就快点搞上来,我们吃饭!——不打了!
不久,菜,就被一道一道地端上来,摆满了一桌。
土狗说,我们今天喝什么酒啊?
钩子老婆嚷道,喝红酒,喝红酒,红酒喜庆,又不伤身。
好。那就喝红酒,照顾女士!
不!是庆祝老土又升了一级!钩子老婆嚷道。
于是大家都斟满酒,站起来,一连迭声地向土狗敬酒,笑着给他道喜,祝贺他新添一子,以后大福大贵,鹏程万里,他们这些叔叔伯伯阿姨们,以后也好跟着沾点光。
说得土狗心花怒放,一时兴起,不知哪来的狗屁,又酸了一句,将进酒,杯莫停。干!说毕,一仰头,全干了。
几个人就这样有说有笑,边吃边喝,渐渐地,酒,也就喝得差不多了,土狗红着脸,冲着一旁的小姐嚷道,汤呢,怎么还不上汤!小姐一听,赶紧转过身,拉开门就出去了。
不一会,小姐就端进来一个托盘,上面摆着四个杏黄细瓷碗,一人面前放一碗,掌心朝上,一摊手,说声,紫汤来了,请慢用!就退出去了。
土狗连忙招呼说,来来!快尝尝!这就是我给你们说的那道汤,滋阴壮阳,十全大补,驰名省内外。很多外地的人都慕名而来,就是为了这道汤。
钩子用小汤匙轻轻搅动着,只见那汤,真如奶一般浓郁,异香扑鼻,小啜了一口,果然鲜美无比,忍不住又啜了一口,咂巴咂巴嘴说,嗯,好喝,真的好喝!我恨不得连舌头都想咽进去了!他舍不得一口喝掉,就喝酒一样地抿,小口小口地啜,细细地品味。
大家见了,都忍不住一阵好笑。
土狗笑道,那当然。好货不便宜。光这道汤就二千块哩!每人五百块钱一碗!
钩子的手一晃,险些泼出汤来,叫道,我崽!这是你请啊,公司请啊!
土狗直眼瞪着他的,气得想骂人。
吓得钩子不做声了,赶忙低着头喝汤。房内一时寂静无声,只剩一片的啜汤声,间或传来鲜、鲜的赞叹声。喝着喝着,钩子一抬头,见自己老婆坐在那里纹丝不动,就问,你怎么不喝?老婆就浅浅一笑,说,我吃饱了。你喜欢喝,等下就给你喝!
没有人理会他俩在说什么,都低着头,在吸溜吸溜的喝自己的汤。
钩子说,正好,给我带到矿里去喝。终于喝完碗里的汤,并将碗底剩下的肉,也一仰头,统统刮进嘴里,嘎吱嘎吱地嚼动着,舌头还在一个劲地细心揣摩,说,这到底是什么肉啊?又脆又嫩,好像有点像肚尖!
土狗就骂他,土鳖!怎么是肚尖?这是紫河车!
钩子就问道,什么是紫河车?
土狗又骂道,傻卵!紫河车都不晓得,紫河车就是胎盘呀!
话未落音,只听哇的一声,钩子一口将嘴里的东西全吐在了碗里,奔进盥洗间就呕,呕得翻肠倒肚,涕泪横流,苦胆水都呕出来了,那样子好像是害了喜。他走出来,擦了一把眼泪鼻涕,说,老土啊,这个东西你也敢吃啊?你这不是在哄我们吃人肉嘛!唉呀,我的崽呀,也亏你咽得下!
阿水一听也慌了,慌忙跑进盥洗间里,把手指往喉咙里抠,张大嘴,对着马桶,也哇哇地呕吐起来。
土狗站在一旁,好不尴尬,他又好气又好笑,骂道,冒卵用的东西!吃个卵胎盘有什么关系?民间吃胎盘的多的是。医院里还有胎盘针打哩!你们冒吃过猪肉,还冒见过猪跑啊!俩个傻卵,这又不是吃你自己的崽,怕什么!
猛地,他心里咯噔一惊,一想不好,一股凉气从脊梁直冲头顶,五脏六俯直往上涌,只觉得一阵恶心,哇地一声,就飞也似的奔进盥洗间,扒着马桶也大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