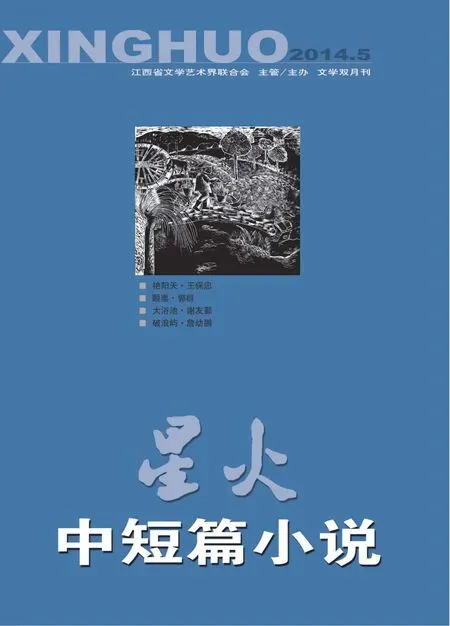进城割麦子
□ 路玉荷
一
时令过了芒种,西南风便不断溜儿的一阵连着一阵,不停地朝麦地上吹。感觉也就才几天的功夫,地里已是满目金黄了,沉甸甸的麦穗,挓挲着粗壮的麦刺儿,倒竖的箭矢一样,随风连片地起舞,滔滔滚滚,一浪连着一浪,此起彼伏,一望无际。一看就知道该收割了。
性急的一些人,早就到地里看了一趟又一趟,并大约估算出张三家的收成,李四家的产量了,所以,还在七八天以前甚至更早,村子里家家户户照例就在做收割的准备了,人人都大步流星,连空气似乎都充满了匆忙。
黄连祥和他的女人杨秋爱自然也不例外。他们拉着石碌碡,一圈又一圈,吱扭吱扭地碾场。把场碾细了,碾平了,碾实了,又收拾桑叉、簸箕、草绳子、麻袋,到镇上买清凉油、毛巾、草帽,打油、称盐、推面,一锅一锅地蒸馒头,紧张地做着所有所有的准备,生怕哪一项没弄好,到时把割麦子的大事给耽误了。
镰本来是从商店里新买的,镰刃都白白地闪着耀眼的锋芒,但黄连祥还怕不快,用洗脸盆子盛了些水,把两把镰拿过来,蹲在院子里的那棵梧桐树下,将镰刃摁在细磨石上,哧啦哧啦地来回磨。磨一阵子,将镰刃竖起,大拇指横在上面,来回轻轻蹭几下;磨一阵子,将镰刃竖起,大拇指横在上面,来回轻轻蹭几下,直到感觉锋利得不能再锋利了,并从头上拽起几根头发,用镰刃试了试,见头发刚稍稍挨到镰刃,便全被齐刷刷地割断,才满意的将镰收了起来。
捆麦子用的草绳子,已经一把一把地分好了,只管到时用就行了,杨秋爱还是不放心,又坐在大门洞里,一把一把地细细捋了捋。
今年割麦子不同往年哩,不仅要在村里的自家地里割,还要上城里去割,而且还那么老大一片,足足有二十来亩啊,准备工作不提前做细做实做透,恐怕根本不行。
当然,城里本来是不长麦子的,城里宽宽的马路边,只长高高的能顶到云彩的大楼,长晚上亮得晃眼的路灯,长琳琅满目的霓虹灯广告,长非常好看的城市雕塑。到处都是水泥地,与种麦子是搭不上边的,能种点麦子的地方,也不是长着绿油油的草坪,就是长着一棵一棵的好看的树,但黄连祥和他的女人杨秋爱还是种上了。
二
黄连祥和杨秋爱在村子里种着二亩地,这是村里分给他们的。严格地说是二亩一。他们还有一个正上初中的儿子。
地在村南,过了黑狗河上的那座康熙年间的老石桥,朝左边一拐就是。地的这头是黑狗河,那头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四五米宽的土路。土路两边,各长着一排碗口粗的白杨树。这么一点点地,对黄连祥和杨秋爱来说,侍弄起来,跟玩一样。
他们都四十来岁,他们都身强体壮,这里不疼,那里也不痒,连个疖子都不长,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
秋天来了,他们把那二亩地里的玉米掰下来,运进家里,把地里的玉米秸砍了,把地耕了,打上垄,种上麦子。第二年芒种,他们再在麦地里套种上玉米,然后将麦子收了,给玉米苗施上肥,玉米又一天天长起来了。
年年这么循环。
最早,这二亩地收也好,种也罢,都是杨秋爱一人。
那时,黄连祥在很远的一个山里的炭窑上,给人家掏炭。钱挣得还可以,但就是太危险。那是个私人开的炭窑,老板只知道赚钱,新来矿工临下井前签生死合同,安全措施根本谈不上,死人的事经常要发生,而一旦死了,顶多给个三万五万的便了事。有一回掌子面上塌方,和黄连祥一起在井下的十几个矿工,一次死了六个,杨秋爱便说什么也不让黄连祥去了。杨秋爱说,不去了,不去了,说什么也不去了,回来安安生生的和我种地吧,钱是啥人是啥,一旦把命给搭上了,你就是挣座金山银山,又有什么用呢?
从此,黄连祥便不再去了。
当然,杨秋爱不让黄连祥再去掏炭,除了安全因素以外,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次要原因,就是她那方面的欲望特别强,离不开黄连祥。这点黄连祥也知道,尽管他没有说破。
杨秋爱在夫妻那件事上,基本上隔上个三两天,就要要一回,而且每一回还都要要上两次,有时甚至三次才能彻底满足。也多亏了黄连祥身体好,杨秋爱要几次,他给几次,而且每次还都能叫杨秋爱爽得云里雾里,透心透骨。
黄连祥在炭窑上掏炭,一去就是半年,甚至时间还长,杨秋爱熬不了。
那年黄连祥从炭窑上回来过春节时,杨秋爱在和黄连祥做完了那事后,躺在黄连祥的胳膊上,偎在黄连祥的怀里说,连祥,你再在外面吧,再在外面,我受不了了,晚上想了,就找二拴子,给你戴顶老大老大的绿帽子。二拴子是村里的一个光棍,长得人高马大,有一膀子力气。黄连祥一听,心里咯噔了一下,尽管黄连祥知道杨秋爱说的那是玩笑话,当不得真,凭杨秋爱的为人,也肯定不会那么做,但黄连祥还是决定不去了,不了。
杨秋爱一人种都当玩的那二亩地,加上黄连祥这么个大男人,就更不在话下了。草又不用天天锄,肥又不用天天施,那么多那么多的时间,不能总是闲着呆着呀,他们就买了个蹦蹦子三轮车,到城里收起了破烂。啤酒瓶子、矿泉水瓶子、易拉罐、报纸、书本、纸壳子,还有旧电视、空调、洗衣机、床、柜子……什么都收。有些,他们收来后直接到收购站或镇集上去卖了,换成钱了;有些,他们则擦一擦或修一修,自己用上了。他们看的那台电视,就是花五十元从城里的一户搬家的人那里收来的。那户人家买了新房子,嫌才买了几年的电视不跟形势了,老了,又买了液晶的,超大的,就把旧电视给卖了。这台电视在商店里买,少说也要一千好几。黄连祥两口子看得非常好,人是彩色的,图像也非常清晰,比他们原先的那个黑白的强多了。他们的儿子黄清华睡的床,也是他们从城里收来的,席梦思。还有他们骑的自行车,用的电风扇,做饭的锅,穿的一些衣服,送给黄清华他姨家的小孩玩的很多玩具,都是收来的。
三
这些年,城里的房地产火了,呼呼的,很多地方拆了旧楼盖新楼,拆了矮楼盖高楼,拆了窄楼盖宽楼,到处都是挖掘机的轰隆声,到处都是旧楼推到后荡起的烟尘。
旧楼推到了,里面的钢筋便裸露出来了。黄连祥和杨秋爱买了大锤、小锤、錾子,在收破烂的同时,哪里的楼推到了,他们就闻讯到哪里扒钢筋。黄连祥用大锤咣一下,咣一下地将水泥板砸碎。杨秋爱用小锤和錾子,把已被黄连祥砸得七零八落的碎水泥块敲一敲,錾一錾,一根根钢筋就出来了。最多的一次,他们一天就砸出了上百公斤钢筋,卖了好几百元。
有时,他们见推倒的楼里的砖好,也扒砖头,他们的西屋就是用扒来的砖头盖的,他们的院子的地面,就是用扒来的砖头铺的。
村子里别人家的院子的地面,每逢下雨,总是一踩一脚泥,扑哧扑哧,但他们家的院子里却干干净净。雨水一冲,地面上一丁一跑的互相勾着缝的红砖鲜鲜亮亮,叫人羡慕。
夏天的夜晚,吃过晚饭后,他们常常在院子里用红砖铺的地面上铺领草席,躺在上面,望着天上的星星,听着院墙上绽放的丝瓜花丛里的蝈蝈的叫声,打着蒲扇,论论年景,话话桑麻,也说些两口子说的话,做些两口子做的事。儿子上学住校,他们就无所顾忌,反正院门关着,这方天地是他们的,动作不免能有多大就多大,叫声也能喊多高就多高,哼哼唧唧,哎哎哟哟,让梧桐树上的知了都羞得藏到树叶后面,不好意思朝这边看。
四
他们每次进城收破烂必经的城乡结合部有一个村子,叫双岭。因村东有两个并排着的土岭而得名。这两个土岭,形似两只鞋子,长四百来米,宽七八十米,高三四十米,上面长满了高大茂盛的槐树、杨树,树杈上挂着一个个的喜鹊窝,喜鹊成群结队,唧唧喳喳。据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当年领兵征战时路过此地,下马歇息,见马靴上沾满了征尘,左右跺了一下脚,结果他跺下的两脚征尘,在他和他的兵们走后,便成了这两个土岭。
村子里四五百户人家,一千多口子人,基本都是范姓,以种植玉米、小麦为主,村边、地头、土坡旁,间以谷子、芝麻、高粱、向日葵、吊瓜、茄子、辣椒。
2003年的时候,县里决定从日商、韩商、台商引资,在这里建工业园,和乡里一起做双岭村的工作,给双岭村一定的补偿,并在城里为双岭村新建了一处居民小区,双岭村便搬走了。
当时正是玉米蹿红缨的时候,顶多也就过个十天半月的,玉米棒子就可以煮着吃了,但县里调来四五台前头挂着大铲的链轨车,喀喀喀的彻夜不停地工作,三天后,一片一片的青玉米,全都碾在了地里。接下来,是测量、规划,然后挖下水沟、修柏油路、竖路灯、盖大楼、安路标。工业园派出所搬进来了,工业园工商、税务搬进来了,大酒店、洗浴中心开业了。
然而,仅三四年的工夫,这里便如同退潮的海滩,冷清了,苍凉了。留下了一幢幢只起了个框架的半拉子楼,一座座只盖了一半的厂房,一个个只圈了一圈的院墙。
资金不到位,很多的仅仅是这个那个的商们在被热情招待、酒足饭饱后,签的个投资意向而已。只有三两家企业在那里运作起来了,还有生意红火的三个大酒店、两个洗浴城、四个足浴中心,据说是有特殊服务,小姐非常漂亮。很多人把这里不叫工业园,而叫鸡窝。
去年夏天的时候,黄连祥和杨秋爱到城里收破烂回来,开着蹦蹦子三轮车路过工业园,从振兴路上由南往北,穿过东西走向的上海路不久,黄连祥感觉需要方便了,停下车,踩着黄昏,朝旁边豁了一个口子的一处院墙里而去。城里正常时间不允许黄连祥开的这样的蹦蹦子三轮车通行,所以黄连祥进城出城必须是一早一晚,赶在交警未上班或下班时。
那处院墙上的那个豁口,是大前年的时候,一辆吊车在那里调头,司机不小心,用吊臂撞出来的,一直豁着,而且渐渐增大。
这天的收获不错,不是收了多少破烂,而是黄连祥帮一个少妇挪了挪橱子,调了调床后,得到了丰厚的报酬。
早晨六点半的时候,黄连祥用蹦蹦子三轮车拉着杨秋爱,还有一水壶热水和三个馒头,一块疙瘩咸菜,一个搪瓷茶缸子——他们的午饭和吃午饭的家伙,来到了城里的怡心园生活小区。这也是他们固定的收破烂的地方。
你别看在城里收个破烂,也各有各的地盘,否则就要遭收拾,抢走收的破烂不说,轻则让你鼻孔里流血,重则让你断几根肋骨。这个地盘,也是黄连祥两口子经过多年的打拼占下的。
在花坛旁的那棵大柿子树底下,黄连祥放好蹦蹦子三轮车,拿下电子秤,铺张纸壳子,坐了下来,等待小区里送破烂的人来。杨秋爱则坐在一旁,翻一本昨天收的她留起来看的《读者》。杨秋爱是初中生,有点文化。
一上午过去了,然后半下午又过去了,却没有几个人送破烂过来。他们收破烂常常这样,有时多,有时少。黄连祥百无聊赖地打着哈欠,杨秋爱则在柿子树紧跟前另铺了张纸壳子,打起了呼噜。
柿子树挺大,几个成人合抱方能抱过来,是小区建起来后,从山里花钱挖来的,树龄已有几百年。
一个非常漂亮的少妇从那边袅袅婷婷地走过来,问黄连祥,帮我挪挪橱子,行吗?黄连祥想也没想说,行!起身对杨秋爱说,你在这里看着,跟着少妇去了。
前边绕过那片草坪,黄连祥跟着少妇进了一座楼的二楼。这是套复式的住房,上下两层,二百多平方。二楼是大会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沿着木梯上到三楼,是书房、卧室。房间里装修、布置得相当豪华和考究,缅甸进口的木地板,黄花梨的家具,水晶吸顶灯,雕花床,黄连祥感觉跟进了皇宫一样。酒柜里那一瓶瓶带洋字码的白酒、红酒,在柜灯的照射下,闪着宝石般的璀璨的光辉。黄连祥呆了一样,站在地上,沐浴着空调送出的凉爽,不敢动了。
少妇说,你过来,过来呀,领着黄连祥到这个房间里说,看到这个橱子了吗,你把它朝里挪挪。然后又领着黄连祥到那个房间里说,你把这床朝这边稍调一调。她看看黄连祥,能行吗?黄连祥伸伸胳膊说,没问题。然后,弯下腰,开始一样一样地干。少妇指挥着,说朝这点,黄连祥就朝这点,少妇说再过一点,黄连祥就再过一点。少妇说又多了,黄连祥就再往回动动。
只用了半个来小时就好了。少妇让黄连祥坐在椅子上,给黄连祥磨了咖啡豆,煮了咖啡,然后加上冰块、奶酪、白糖,把咖啡端给了黄连祥。黄连祥第一次喝咖啡,被这么招待,受宠若惊。刚开始感觉苦,但越喝越香,不禁一杯接一杯。少妇就一次又一次地给黄连祥煮。还边煮咖啡,边收拾出一堆嘎嘎新的男人的皮衣、大衣、裤子、皮鞋什么的,用一条大床单包了,让黄连祥带走,说她看见这些东西就心里堵得慌,气不打一处来。黄连祥就知道了,少妇的男人是有钱人,在外面又有了女人,然后带着十三岁的儿子,把少妇像扔抹布一样地扔了,同时扔给少妇这套房子,还有一堆钱。
真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黄连祥感叹,看上去这么漂亮幸福的一个人,原来也有一肚子苦处。
人呐,唉!
喝了一肚子咖啡的黄连祥起身告辞,少妇拿出三百块钱给他。黄连祥本来背着那么一大堆好东西,感觉就赚大便宜了,见少妇还要给钱,坚决不收,黄连祥说,不就是帮了点小忙吗,毛毛雨而已。况且,在下面闲着也是闲着,谁都有个需要帮一帮的时候。可少妇不依,二人推来推去,这样,不免就有了肢体接触,你碰了我的手,我碰了你的胳膊。黄连祥感觉少妇的手是那么的白,那么的软,身上是那么的香,手背在推来推去中还不小心触到了少妇的胸膛上,黄连祥心里咚的一下,跳得简直不行了,赶紧接过钱,走了,他怕再那么推来推去,他控制不住自己,会把少妇一下搂在怀里,犯错误。他和少妇离得太近了,脸上都感觉到少妇呼出的香香的气流了。少妇太好了。
一般在进城或回家的路上,黄连祥是不停下蹦蹦子三轮车方便的,但今下午在少妇家喝了那么多咖啡,憋不住了。
黄连祥从院墙上的豁口进去了,第一感觉是,哎哟喂,怎么这么大一片闲地呀,太大了!里面除了疯长的各种杂草,什么也没有。黄连祥在急急地拉开裤门,对着一丛狗尾巴草一阵猛泚后,打了个微颤,痛快了。痛快了的黄连祥就不由背上手,在暮色里,对院墙里圈的这片空地,来回细细进行了查看,乖乖,有二十来亩哩,这可是一片插上筷子都能发芽的好地呀,要是种上庄稼,一年得收多少?比如种麦子吧,少说也要收几万斤呐。
庄稼人的本能,使黄连祥一看到地,不由想起了庄稼,并产生了联想。
回家后的黄连祥,晚上睡不着了,院墙里的那片地和那片地上的绿油油的杂草,老在眼前晃。他想,村里的地那么少,人们想种都没有,急得连村口上、水渠旁、路边上都点上几株豆,种上几棵高粱,城里为什么就这么大方的将那片地那么闲着,让它长草呢?而且,看样子得有个四年甚或五年了吧?
黄连祥把睡梦中的杨秋爱叫醒,说爱,爱,我们去种了它。杨秋爱揉着眼睛说,半夜三更三更半夜的种什么呀种?黄连祥说,种地,种地啊。黄连祥把黄昏在工业园里见到的那片地对杨秋爱说了。杨秋爱摇摇头,说那不是咱的地,咱能种吗?黄连祥说,闲着也是闲着,咱又不是去偷去抢。杨秋爱说,理是这个理,可我觉着不太行,要不咱们去问问吧?黄连祥说,问?问谁呀?再说了,一问事儿就麻烦了,不如装着什么都不知道,直接种,反正咱们就是一老百姓,还能怎么样?杨秋爱看着黄连祥,那咱就种?黄连祥说,种!接着起身。杨秋爱说,要种也得等天亮了啊,再说了,种什么,怎么种,也得好好合计合计不是?
五
经过反复悄悄勘察,并结合庄稼所适应的节气,黄连祥和杨秋爱决定把那片地收拾起来,种上麦子。
他们先不收破烂了,从城里的一处拆迁工地上捡来些转头,和上沙子、水泥,把那个墙豁口连同锁已生了锈的院大铁门门口全都给堵上了,一来怕这里离自己的村子远,一旦种上庄稼,顾不上照看,被野狗野猫的进去糟蹋;二来,毕竟是偷着在人家的地上种庄稼,还是不要明晃晃的让别人看到好。有完整的高达三米的墙挡着,安全一些,隐蔽一些。
那么以后出入院子怎么办?黄连祥从家里找了几根木头,用斧头砍了砍,削了削,做了个简易但又非常结实的木梯。他们入院子时,先把蹦蹦子三轮车在附近锁好,瞅瞅四周没人,把木梯架在墙这边,蹬上去以后,再把木梯抽上去,架到里面,沿着木梯,就进去了,悄没声息。
刚开始几天,黄连祥和杨秋爱还有点忐忑,怕被撵走,几天过去后,见没有什么动静,也没有人来问,放松下来了。
黄连祥脱光了膀子,只穿条裤衩,抡动大锄,对着杂草,噗嚓噗嚓地使开了力气,感觉是虎进深山,马入草原般的畅快与通透。庄稼人嘛,还有啥比种地而更踏实的事呢?黄连祥不由哼起了小曲:
妹妹你坐船头,
哥哥在岸上走,
恩恩爱爱纤绳荡悠悠……
正在后面使一把小锄的杨秋爱赶紧摸起块土坷垃,砰地打在了黄连祥的背上。黄连祥顿时会意,将恣嘛洋腔的小曲戛然打住,猫着腰警觉地朝四周看了看,见一切正常,对杨秋爱做了个鬼脸。
午饭就在地头上,是煎饼、大葱、香椿芽咸菜,黄连祥、杨秋爱大口大口地咀嚼着,吃得满口生香。
地里的草已经全都弄完了,接下来该用耘锄耘一耘了,两口子看着那么一片连做梦都想不到的老肥的好地,心里要多欢心有多欢心。黄连祥说,咱们成地主了。杨秋爱说,可不咋的。黄连祥说,还是大地主呢!哎,等麦子收了,几万斤,哎呀,你说村里该怎么羡慕咱们,怎么羡慕咱们呐!杨秋爱说,还用说吗,肯定都眼热坏了。黄连祥说,你就准备好麻袋和瓮可着劲地装吧。麻袋和瓮装不下,咱就直接放到屋地上,让麦子在屋里堆成山。黄连祥畅想着,到那时,咱就躺在麦子上睡觉。让儿子也上最好的大学。盖水刷的二层小楼,苏州杭州的出去旅游。
黄连祥啧啧着咂嘴。
啧啧完了,黄连祥见杨秋爱正端着搪瓷缸子喝水,鼓了鼓眼睛,一把把杨秋爱手里的搪瓷缸子拽出来,抱起杨秋爱,到了地当央,三把两把,退下了杨秋爱的裤子。杨秋爱知道黄连祥要干那事了。每逢黄连祥高兴时,都要用这种方式庆贺。但这是在外面,城里,比不得家中,要是被人看见就麻烦了。杨秋爱阻挡说,干什么干什么,你疯了?但根本阻挡不住,进入了。杨秋爱只好由他。黄连祥本来就猛,这次比在家里还猛,嘴里喊着,爱,咱有这么多地了,要收好多麦子了,咱有这么多地了,要收好多麦子了。刚开始,杨秋爱还有点慌张,不停朝四周的墙上撒目,怕有人,渐渐地,身体飘起来了,就闭上眼,不管了,一下一下,喊出了声。
六
麦种是在秋分时开始下的。其实,地早在之前半个月已经耘好了。没有耕。耕一耕当然好了。不过这么好的地,甭耕就很行。再者,一旦耕地,又用犁铧又使牛的,动静太大。这也是黄连祥、杨秋爱最担心的。
之所以选在秋分后开始下麦种,不是别的,节气使然。谚语云: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麦种下早了,天暖和,麦苗出来后会不停地生长,到天冷时,麦子已经拔节了,地一上冻,冻死了;而麦种下晚了,麦苗出来后,尚未来得及打墩,就过冬了,影响麦子的收成。春分把麦种下到地里,麦苗出来后,刚好稳稳妥妥地打好墩,第一场鸡爪子霜也来了,接着又被大雪覆盖了,不早不晚,正赶趟儿。
黄连祥到镇上买的上好的麦种,回来后杨秋爱又用簸箕将麦种一簸箕一簸箕地簸了,把麦种在簸箕里反复进行了挑选,秕秕的,扭扭的,颜色不正的,过大的,过小的,全都一个个地扒拉了出来。黄连祥还不放心,又抽查似的,从麻袋里把麦种捧出来几捧,仔细进行了验看。
播种用的耧是个小耧,单腿的。为了方便。
杨秋爱把绳子套在肩上,抓着耧杆在前面拉,黄连祥在后面扶着两根耧把,不停地摇着,播。耧锤来来回回的不停地悠,麦种在耧锤的左右悠打中,顺着耧腿唰啦唰啦的朝地里落。黄连祥弯着腰,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朝耧腿里落的麦种。不能过密,密了麦子长不好,还多使麦种;也不能稀,稀了影响麦子的产量,造成地和人力物力的浪费。
黄连祥、杨秋爱起早贪黑,贪黑起早,一连五六天。终于,麦子种好了。他们又拉着一个小铁耙,把种了麦子的地耙了,一遍怕不行,还耙了二遍。麦子不怕草,就怕坷垃咬,如果不耙细,有土坷垃,影响麦种的出苗率。
这一些都做好了,黄连祥、杨秋爱才又收了村里自家地里那玉米,种上了麦子。
那地就二亩,比起城里的这一片来,就简单了。
之后,黄连祥和杨秋爱又在城里收开了破烂。
怡心园里的住户把一堆堆的报纸、纸壳子、易拉罐、啤酒瓶子拎出来,放到黄连祥他们面前,抱怨说,这两个来月,你们也不来,做什么去了,啊?再不来我们家里的破烂都快盛不下了,我们就要交给别处收破烂的了。黄连祥也不答话,嘿嘿几声,忙着数易拉罐的个数,对报纸过秤。杨秋爱则付钱。他们知道,城里人是理解不了庄稼人对于土地的那份感情的,所以,也就没有把种那片地的喜悦事儿说出来,和城里人一起分享。再说了,种那地,也有点偷偷摸摸,必须保密。
破烂照收,那片麦子,黄连祥出城进城的,也不断查看。十来天的时间,鹅黄还有点淡绿的麦苗出来了,齐刷刷的,甚是好看,而且见光长,接下来,分蘖了,再接下来,打好墩了。然后是随着冬天的过去和春天的到来,拔节了,蹿穗了,杨花了,麦粒能搓上手了。
前天一看,哇塞,该收割了!
汗珠子没有白甩,力气没有白使,希望成现实了。
黄连祥激动了,一蹦老高,一蹦老高,连着四五下,接着又四五下。
回来啪嚓啪嚓地打开啤酒,竖起瓶子,扑噔扑噔地朝嘴里吹。把杨秋爱扔到床上,院门都来不及闩,一连和杨秋爱做了三次那事进行庆贺,带动的床都幸福地欢唱。
七
把割麦子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好后,第二天天不亮,黄连祥、杨秋爱就兴奋地起来了,给蹦蹦子三轮车轮轴上打上油,朝车上放上镰、草绳子,用摇把把蹦蹦子三轮车嗵嗵嗵地摇起来,挂上档,加上油门,一路激动着,朝城里去了。
村庄被绿树掩映着,似一堆浓重的云。空气里,麦黄杏的香气缕缕飘散,间或还有米黄色枣花的甜香。谁家的狗,汪汪几声,停了。谁家的驴,又啊呀啊呀地叫。东边西边,布谷鸟一声接一声地谷谷。这里那里,公鸡喔喔喔地打鸣。
心情好,三轮车跑起来也欢畅,这个时间路上车又少,不到一小时,到了。黄连祥、杨秋爱兴高采烈地跳下车,把蹦蹦子三轮车放好,架上木梯,带着镰、草绳子什么的噌噌上墙,然后下进了院里。
然而,院里的麦子却没了。
黄连祥、杨秋爱以为没看清,揉了揉眼睛,呀,的确没有了!
韩国的一个商人有来工业园投资,建乳品加工厂的意向,招商引资办安排韩商今天上午到这个院子里进行考察。为了不影响今天韩商的考察,昨天,招商引资办的人提前先来这个院子进行查看时,见院子里竟长了一院子麦子,就立即安排推土机,全部推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