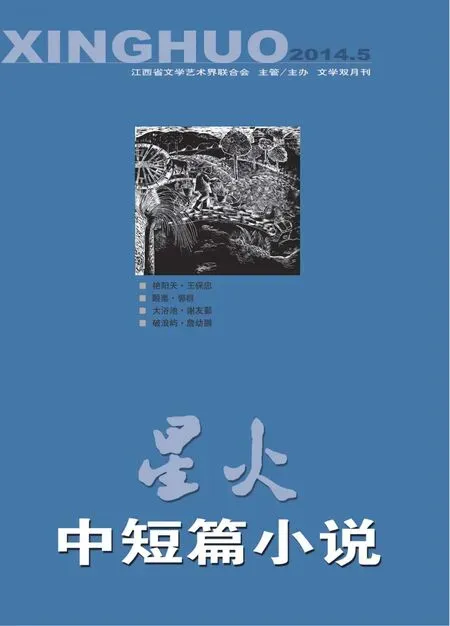孤儿
□ 鬼 金
如同你,我们走向阴影指示的地域;如同你,我们没有归宿。——雨果《暴风雨》
悲伤起1
宝坠有一个妈妈,有三个爸爸。这个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奇妙但也带着凄楚,宝坠能说什么呢?这不是他能决定的,他希望只有一个妈妈,一个爸爸,可是,不能,他没有这个决定权,这个决定权在他妈妈的手里。宝坠妈对宝坠说,叫这个男人爸爸,宝坠就只好叫那个男人爸爸,要是宝坠不叫的话,宝坠妈可能会眼泪汪汪的,有时还会踢宝坠的屁股,要不就会揪住宝坠的耳朵说,叫爸爸。就这么回事。那些爸爸是宝坠妈给宝坠的,尽管宝坠不愿意,但为了不让妈妈伤心,宝坠只好叫那些男人爸爸。
——爸爸。
——爸爸。
……
这就是宝坠的童年。
宝坠妈生宝坠的时候,宝坠第一个爸爸已经死了,宝坠妈是在去煤矿上看宝坠爸的路上生下了宝坠。宝坠妈那天正腆着大肚子给圈里的猪喂食,一个邮递员把一张电报交给她。她看到电报后,愣了愣,然后,冰山倒塌般地嚎哭起来……
邮递员吓了一跳,连忙扶住宝坠妈问,怎么了?怎么了?他看了宝坠妈手里的电报,怔住了,像一个木头桩子。他叹息着说,大妹子,你还怀着身孕,要为孩子着想啊!后来,那个邮递员走了。宝坠妈开始收拾东西,去矿上。她不是一个人,还有宝坠。只是宝坠还在她的肚子里。但,宝坠感觉到了母亲的悲伤,她的悲伤让宝坠活动的世界里的羊水都变得冰冷了,宝坠蜷缩着身体,瑟瑟发抖,被那根脐带牵扯着,还好,宝坠没有冻死在那羊水的世界里。也许因为母亲的悲伤,宝坠提前降生了。
那应该是深秋了,道路两边的庄稼都收割完了。零散的牛羊在地里,还有一群乌鸦。宝坠妈瘫软在路上,她挣扎着生下宝坠,咬断脐带,把宝坠包起来。她已经没有力气了,趴在地上看着远处的路,看不到尽头。一辆过路的马车救了他们。赶车的是一个中年男人,他看见宝坠妈躺在地上,就吆喝着他的马停住了。
宝坠妈有气无力地说,大哥,帮帮我们。
宝坠妈说的是我们,自然她已经把宝坠当成一个人了。
中年男人说,上车吧。
宝坠妈艰难地想站起来,可是又坐在了地上。中年男人只好搀扶着宝坠妈,上了马车。
中年男人问,大妹子,这是要去哪啊?
宝坠妈嘴唇颤抖着,眼里泛起了泪花说,去矿上。
中年男人瞪大眼睛问,矿上出事了?你……
宝坠妈泪光闪烁,带着哭腔说,是娃他爸……
中年男人愣了一下,眼睛里现出一丝同情的目光。他“驾驾”地吆喝着他的马,那语气仿佛充满对煤矿的仇恨。
宝坠哭了,第一声啼哭,在空旷的原野上回荡着,仿佛让那些沉睡的万物苏醒,让那些即将要沉睡的猛醒。凛冽的哭声,如一道闪电划破深秋的沉寂。凛冽的哭声,如坠落的种子愤怒地飘落到泥土深处。
中年男人说,这小子哭得还真有劲,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后来证明,中年男人的话错了。
你们不会想到,宝坠妈竟然在宝坠不会说话的时候叫他对着一个死人喊,爸爸。
中年男人把他们带到矿上的时候,矿上集聚了很多人,还有哭声。
中年男人说,我走了。
宝坠妈说,谢谢您大哥,我也没什么谢您的,是您救了我们孤儿寡母的,我给您磕一个头吧。
宝坠妈抱着宝坠就要给中年男人磕头。
中年男人连忙扶着宝坠妈说,不用,不用……
宝坠妈还是坚持着要给中年男人磕头。
中年男人走了,宝坠妈抱着宝坠,对着中年男人背影磕了三个响头,宝坠妈还对着还什么都不懂的宝坠说,孩子,这是好人啊,将来,我们要是遇上了,一定要好好感谢人家,要是没有人家,我们母子俩可能就死在路上了……
宝坠妈抱起宝坠开始向人群挤去。人挨人,人挤人,哭声从人群里面流水似的哗哗地流淌出来。
“挤什么挤?”有人说。
宝坠妈说,我找我家男人。
人们听到这句话,开始让出一条道路。
他们小声地说,又来了一个家属。看看,那怀里的孩子,还那么小,老天爷真是作孽啊!
宝坠妈挤进人群,看见十几个躺在地上的尸体。宝坠妈懵了。她不知道哪个是宝坠爸。有的尸体旁边有亲属在哭。
一群苍蝇嗡嗡的,像一块舞动的黑纱。
这时候,走过来一个戴眼镜的马脸男人,他问宝坠妈,你找谁?
宝坠妈说,我找马路生。
戴眼镜的马脸男人说,正等着你来呢,本来应该矿上派车去接你的,可是矿上实在困难,现在又出了这事,您受累了……
宝坠妈问,我男人呢?我男人呢?
戴眼镜的马脸男人说,你别急……
宝坠妈说,电报上说,我男人出事了,他到底咋样?是不是……
戴眼镜的马脸男人慢吞吞地说,是这么回事……
宝坠妈眼含着泪,推开戴眼镜的马脸男人,冲向那些尸体。
宝坠妈喊着,路生……路生……我来看你了……我来看你了……我还带来了你的儿子,你的儿子,你有儿子了……路生……
宝坠妈喊着,在尸体中间找着。
这时候,被辨认出来的尸体被抬走了。那些家属跟着,他们的哭声也紧随着,贴着地,撞着天。地上,还剩下五、六具尸体,但都面目全非,看不清楚是谁。宝坠妈抱着宝坠,喊叫着,路生……路生……你要是有知的话,你就给个动静……你现在是有儿子的人了……你当爹了……你知道吗?我怀孕的时候,你不是给孩子起好名字,叫宝坠吗?现在,我和宝坠来看你了……你给个动静……
尸体仍静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宝坠妈对宝坠说,你喊爸爸,你喊爸爸。
宝坠怎么喊,宝坠还不会说话。
后来宝坠妈意识到自己懵了,她拧了宝坠一下,说,你哭……你哭……你爸就会听见,就……
宝坠没哭。宝坠哭不出来。宝坠妈拿宝坠也没办法。那毕竟是一个婴儿。一个刚刚从她的子宫里爬出来不久的孩子。
一个苦命的孩子。
后来,一只苍蝇在宝坠脸上嗡嗡地飞着,宝坠咧开嘴哭了。这一哭,就没有停下。宝坠的哭声撕裂着悲伤、凝滞的空气,直到……
现在想想,也许那只苍蝇是带着宝坠爸的魂。
宝坠的哭声像冬日河水里的冰凌,蔓延着。宝坠妈抱着他,在尸体间穿行着,突然,发现一个男人的脚动了动,她抱着宝坠,扑过去,她把宝坠放到地上,用手擦着那个男人的大脚,她仿佛看到了什么,哭声哗地从她的身体里冲出来……
宝坠妈哭喊着,路生……路生……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就这么扔下我们……你看看……你有儿子了……你看看……
宝坠妈抱起宝坠,叫地上的那个男人看。宝坠妈说,路生,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啊!你有儿子了……你当爹了……你不是早就想要一个儿子了……你怎么能这么狠心……你睁开眼睛看看啊!路生,你看看啊!你看他的眼睛多像你……
宝坠的哭声像哗然坍塌的银河,砸在尸体上,但那个男人都没有睁开眼睛。但奇迹还是发生了。只见,从他的鼻孔里、眼睛里、耳朵里、嘴里,突然,涌出了一股红色的液体,像无数的根须爬出来。后来长大后,宝坠知道那是七窍出血。那也说明,他见到亲人了。他在冥冥之中知道有宝坠这个儿子的存在。
宝坠没有想到,第一次见到爸爸,爸爸却是那个样子,他在宝坠以后的生活中是模糊的,也可以说是没有的。真正让宝坠感觉到爸爸的温暖的是宝坠的第二个爸爸,宝坠也当他是真正的爸爸。
2
宝坠四岁那年。有一天,邻居王姨来了,和宝坠妈在屋子里说着什么。宝坠蹲在地上看妈从镇上买来的一个马蹄表,听着它嘀嗒嘀嗒的声音。宝坠对它充满了好奇,那两个剪刀似的指针一下一下地转动着。宝坠甚至拿起来,晃了晃,可是,仍旧嘀嗒嘀嗒地响着。宝坠妈说,别弄坏了。宝坠小心地放在了柜子上,对着它发呆。手还是禁不住痒痒的,想去摸,去摸那闪亮的金属外壳。那嘀嗒嘀嗒的声音仿佛跑了出来,在屋子里响着,又仿佛跑进了宝坠的身体里。在宝坠屏住呼吸的时候,宝坠的耳朵能听见它在身体里响着。宝坠吓坏了,说,妈,这马蹄表跑到我的身体里了。宝坠妈笑了。王姨也笑了笑。宝坠说,你们笑什么?不信,你们听。宝坠撩起衣服叫她们听。她们哈哈地笑着。她们的笑声淹没了马蹄表的声音。
宝坠爬到窗台上,看着窗外的落日。落日像一个烧着的火球,先是烧着了天空,然后烧着了山,山上的火和天上的火烧到了一起。那时候,宝坠想太阳也是要睡觉的。它的妈妈也在等着它。还有,它的爸爸。可是,宝坠没有爸爸,宝坠只有妈妈。王姨什么时候走的,宝坠不知道。当宝坠回过头,看妈的时候,妈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她拢了拢头发,抿了抿嘴,又笑了笑。她笑得是那么好看,就像有一朵花,开在脸上。宝坠肚子咕噜噜地叫起来。宝坠喊叫着,妈,我饿了。妈冲着宝坠笑着,那微笑看上去是那么的甜美,感觉就像是吃过的棉花糖。宝坠妈说,妈这就去做。
落日不见了。
天黑了。
远处的山峦像野兽般潜伏在那里,有一丝恐惧从远处逼近宝坠,从窗台上下来,盯着马蹄表里那把剪刀,听着它咔嚓咔嚓地剪着什么。
第二天,王姨来了,把宝坠妈带走了。
宝坠问,妈,你们干什么去?
宝坠妈的脸羞红了。
还是王姨嘴快说,去给你找爸爸。
宝坠愣了一下说,我爸不是死了吗?
关于宝坠爸死的话题,是妈告诉宝坠的。因为宝坠在村子里跟小朋友们玩,他们都说宝坠是一个没爸的孩子,宝坠就回家问妈,宝坠妈说,你爸死了。
宝坠妈听了王姨的话,站住了。
王姨看了看宝坠妈说,咋了?又想起你那个死鬼了啊?四年了,你这么为他守着,也是他的福气,你不能为一个死鬼活一辈子啊!一个女人,总得需要一个男人来疼的……不是吗?再说了,你们孤儿寡母的,这日子也成问题……再说了,晚上,天黑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连个暖脚的人都没有……难道你就认了吗?再说了,朱河是我远房姑姑家的孩子,我知根知底的,结过婚,但媳妇死了好几年了,是一个本分、老实人,你要是嫁了他,对你们孤儿寡母的也是一个照应不是?再说了,人家朱河还是城里户口,还在轧钢厂工作……
宝坠妈站在那,一动不动。
王姨过来拉宝坠妈,说,走吧,去看看,说不定就是一个你中意的呢?
宝坠不知道王姨说的是什么,但宝坠知道可能要有一个爸爸了。宝坠的腰杆子一下子就直了起来,大声地说,我要有一个爸爸,那么二胖子他们就不会欺负我了,他们要是敢欺负我,我就叫我爸揍他们。
王姨说,秀枝,你看,孩子都这么说了,还是走吧?为了孩子你该考虑再走一家了。
王姨拉着宝坠妈,走出屋。宝坠妈回头对宝坠说,别出去瞎跑,就在家呆着,妈一会儿就回来。
宝坠小眼珠转着,佯装答应。
在她们走出屋后不久,宝坠就偷偷地跟了出去,瞄着她们的身影。她们绕过村里的人家,向草湖走去。宝坠猫着腰,不紧不慢地跟着,就像一个幽灵。她们越过铁路,来到草湖旁边的公路上,站在那里等着。宝坠妈的头上还系了一个红手绢,看上去就像是一团火。宝坠趴在铁路旁边的小山坡下,看着她们。等了一会儿,宝坠看见妈要往回走。王姨拉着她,两个人撕撕扯扯的。后来,两个人不撕扯了,坐在了湖边。宝坠看见妈还往湖里面扔着石子,看着那好看的涟漪,宝坠手也痒痒了,想冲过去,也打几个水漂,但,没有。宝坠趴在那里像一个侦察兵在注意着周围的动静。很长时间不来湖边玩了,因为二胖子他哥前不久淹死在湖里了,宝坠妈就不让宝坠到湖边来玩了。就是那次,二胖子在苞米地里把宝坠揍了,应该是昏了过去,直到宝坠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在家里,是宝坠妈把从苞米地里把宝坠找到的,还是小细米告诉宝坠妈的。后来,宝坠就听到二胖子他哥出事了,淹死在湖里了。从那以后,宝坠妈对宝坠说,你要是再敢到湖边玩,我就打折你腿。宝坠害怕了,尤其是妈的目光,还有妈说话的语气,怕是真的。
一列火车呼啸着,从铁轨上开过去。带过来的风,呼呼的,宝坠连忙闭上眼睛,身体里充满了车轮碾着铁轨的声音……
十几节车厢的火车很长时间才开过去。
当宝坠睁开眼睛,看见一个推着自行车的男人站在王姨和妈旁边。宝坠匍匐着,爬过铁轨,向前又进了一步,但宝坠仍看不见那个人的脸。他背对着宝坠。宝坠的目光张牙舞爪,企图搬过他的身体,可是,宝坠的目光跟他的年龄一样,是弱小的。宝坠只好趴在那里,等待着。看那个男人的背影,宝坠想这个人要是对付二胖子他们,应该没问题。还有他的自行车,宝坠好想坐上去,让他带着。小细米他爸就有一辆。可是,小细米他爸不是宝坠喜欢的人,他是一个酒鬼。有一次,小细米央求他爸让宝坠也坐一下他的自行车,可是他爸笑着对宝坠说,你回家问问你妈,要是你妈同意和我睡觉,我就带你,连你妈也一起。尽管宝坠很小,也知道,那不是什么好话,宝坠低着头,瞪着他,突然尥开两脚,嘴里骂着,我操你妈!宝坠骂完就跑了。小细米他爸骑着自行车追宝坠,嘴里骂着,小兔崽子,敢占老子的便宜,看我追上你,不打折你的腿。正好妈从地里回来,看见了,他掉转车头,走了。宝坠妈问宝坠,是不是他欺负你了。宝坠咬着牙说,没有。宝坠害怕说出小细米他爸说要和妈睡觉的话。其实跟宝坠说过,要跟妈睡觉的男人有很多。有一回,王痞子半夜闯进宝坠家,被妈用菜刀逼着赶走了。赶走王痞子,宝坠妈抱着宝坠就哭。宝坠对妈说,等我长大了,我要给你报仇,谁再敢欺负你,我就打折他们的腿。宝坠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说,其实宝坠的性格是怯弱的。
宝坠看见王姨跟妈他们摆手,顺着来路返回来了。宝坠怕王姨看见,连忙躲进路边的草丛里。宝坠看见那个男人推着自行车和妈,沿着湖边的公路走,后来,妈竟然坐到了自行车的后座上。他们离宝坠越来越远,宝坠蹿出草丛,在公路上跑着,追赶着,眼看着他们躲进庄稼地里的一堆苞米秸秆里。宝坠跑得满头是汗,当宝坠确定他们在苞米秸秆垛里的时候,宝坠放慢了脚步,轻轻地走过去。宝坠看见他们坐在苞米秸秆垛里说着话。他们抱在一起。
宝坠抽冷一嗓子,喊着,妈……妈……
宝坠以为那男人欺负妈,才喊的。宝坠的手里甚至捡了一块石头,要砸过去。他们慌张地松开了。妈看见宝坠问,你怎么来了?宝坠说,妈,他欺负你了吧?妈说,没,我们闹着玩呢。宝坠看到妈的脸是红的。妈拢了拢头发,整理了一下衣襟。男人看了看宝坠说,你叫宝坠吧?宝坠瞪着他,没有回答。男人从兜里翻出几块糖果,递给宝坠说,宝坠,吃糖。宝坠一挥手把糖块打落在地上。宝坠拉着妈,倔强地说,我们走,我们走。宝坠妈尴尬地看了眼男人,从地上站起来,宝坠妈对男人说,要不,到家里吃顿饭吧?男人说,不了。宝坠妈说,你也看到了,我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会给你拖累的,你要想好了,想好了,你就来接我们母子。男人笑着说,不用想,我决定了,过几天,我就过来接你们。宝坠妈眼含着泪,嘴唇微微颤抖着说,你不后悔?像你这个条件,完全可以找一个姑娘,我……
男人说,别说了,我决定了。男人伸过手来要摸宝坠的头,被宝坠扒拉开了。宝坠妈呵斥着宝坠说,宝坠,你这孩子咋这么不懂事呢?宝坠梗着脖,没吭声。宝坠妈领着宝坠从苞米秸秆垛走出来,男人跟在后面。他们来到马路上,男人骑上自行车说,过几天,我就过来接你们娘俩。男人骑车走了。宝坠妈对着男人的背影挥着手。宝坠的手里还握着那块石头,发现没用了,狠狠地扔进路边的湖里,只听“嘭”地一声,溅起片片水花,接着,一个个涟漪,由小变大地蔓延开去。
这时候,宝坠猛然想起什么,挣脱妈的手,飞快地向苞米秸秆垛跑去。
宝坠妈喊着,宝坠……宝坠……你干什么去?
宝坠没有回答。宝坠跑到苞米秸秆垛里,在地上捡起那几个糖块,吹了吹糖纸上的土,放在手心里看着,并且迅速地剥开一张糖纸,把晶黄色的糖块放到嘴里。宝坠嘴里含着糖块,慢慢地走回来。只见,妈站在湖边,对着茫茫的,水波起伏的湖面怔怔地发呆。宝坠对妈说,吃糖。宝坠妈没有说话,看着宝坠,突然抱住了宝坠。宝坠妈哭了,眼泪像水管子似的,从她的眼睛里流出来。宝坠懵了,连忙问,妈,你怎么哭了?宝坠妈紧紧地抱着宝坠,紧紧地抱着,眼泪落在宝坠的脸上。宝坠问妈,是不是宝坠惹妈妈生气了?宝坠乖还不行吗?宝坠也哭了。宝坠一边哭着,却一边给妈抹着脸上的眼泪。宝坠对妈说,宝坠乖,妈,不哭。宝坠不再惹妈妈生气了。宝坠乖还不行吗?宝坠妈抱着宝坠的头,紧紧地贴在她的胸脯上。宝坠剥了一块糖,放进妈的嘴里,宝坠说,妈妈,甜。宝坠妈笑了,宝坠也笑了。至于宝坠妈为什么哭,在当时,宝坠那幼小的心里根本无法知道。
3
那几天,宝坠妈老是站在门口去瞅,但每次都灰溜溜地回来。然后,在屋里疯狂地干活。宝坠妈给宝坠做一件棉袄,把旧棉袄里的棉花扯出来,放到地上,用棍子抽打着,飞舞的棉花落了宝坠妈一头。宝坠妈的头发白了。宝坠好奇地蹲在妈的身边,拿过妈手里的棍子,敲打着棉花。宝坠妈说,别捣乱,一边玩去。宝坠对妈说,没人跟我玩,小细米她爸不让我跟她玩,二胖子他们老欺负我,叫我做驴,让他们骑,还让我学狗叫。宝坠妈骂着,都是小王八蛋。宝坠对那个马蹄表也失去了兴趣。因为早上,宝坠梦见那马蹄表里的那把剪刀自己动了起来,从里面飞出来,先是剪他的耳朵,然后剪他的鼻子,再后来是手指头,脚趾头……
当宝坠吓醒后,发现马蹄表一动不动地放在窗台上,宝坠胆小地偷看着它,不敢靠近。
后来,妈对宝坠说,我教你唱歌吧。
宝坠妈开始教宝坠唱《小燕子》:
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春天来到这里
我问燕子你为啥来?
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宝坠看着妈,说,妈,你真好看,我长大了,也要娶你这样好看的媳妇。宝坠妈笑了,说,臭小子,学会说好话了。你才多大啊?才脱几天活裆裤啊,就想媳妇了。宝坠对妈说,二胖子他们看我和小细米好,都说小细米是我媳妇。小细米倒是好看,可她爸是一个大坏蛋,一个大流氓,我不喜欢。妈,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不能对别人说,你保证。宝坠妈郑重地说,我保证。宝坠说,有一天,我们玩藏猫猫,我看见小细米她爸和二胖子她妈在苞米地里,小细米她爸光腚压在二胖子他妈身上,二胖子他妈像杀猪似的叫唤。我吓坏了,就跑了。宝坠妈连忙说,小孩子别瞎说。宝坠委屈地说,我真看见了。宝坠问妈,他们在干什么?宝坠妈怔了一下说,小孩子别管大人的事。妈不理宝坠了,宝坠趴在妈身边,两手支着下巴,看妈做棉袄。突然,宝坠妈“啊”地叫了一声,宝坠看见针扎在妈的手指头上,一个血珠渗了出来,滴落在白棉花上,只见那一小块白棉花一下子变红了。宝坠妈连忙把手指伸进嘴里,啯了几下。宝坠问,妈,疼吗?宝坠妈说,不疼。宝坠抓过妈的手指说,妈,我给你啯啯。宝坠含着妈的手指,舌头感觉到血的咸味在舌尖上跳。宝坠妈另一手搂着宝坠,在他的毛头上摸着。一滴眼泪落在宝坠的脸上。宝坠问妈,是不是我啯疼了?宝坠妈说,不是。宝坠问妈,那你怎么哭了。宝坠妈说,我没哭。宝坠强硬地说,你哭了,你的眼泪都掉我的脸上了。宝坠妈不言语了。后来,宝坠妈说,别啯了,没事了。宝坠妈站起来说,我去你王姨家一趟。
宝坠看着妈滴在棉花上的那血,像一枚纽扣,钉在棉花上。
宝坠连忙爬起来,跟了出去。宝坠发现妈并没有去王姨的家,而是去了湖边的公路,站在公路上,向远处看着。宝坠知道妈在等那个男人。宝坠悄悄地离开了,在家附近,看见小细米,他们玩了一会儿,宝坠就回家了。宝坠妈还没有回来。屋子里只有那个马蹄表在响个不停,宝坠拿起来,使劲晃着,那声音始终没有停下。宝坠妈进来了,看见宝坠发疯地晃着马蹄表说,你干什么呢?宝坠说,我要晃出里面的声音。宝坠妈笑了笑说,傻孩子,那声音是晃不出来的,除非钟停了,别晃了,小心整坏了,挺贵的。宝坠沮丧地放好马蹄表,没意思透了,就找了一张破纸,坐在炕上,叠飞机。一口气叠了四、五个。叠完纸飞机,宝坠跑到屋外,爬上屋顶,飞着纸飞机……它们交叉飞着,其中一只径直飞了出去,就像施了魔法……
飞……飞……飞……
这时候,宝坠看见那个男人出现了。
多年以后,宝坠一直相信,是那只纸飞机把他带来的。
宝坠从梯子上连忙爬下来,冲进屋里,对妈喊着,来了……来了……
宝坠妈愣了一下问,什么来了?
宝坠说,那个男的……
宝坠妈有些不知所措,在屋子里转了两圈,拢了拢头发,才走出去。宝坠妈看上去异常紧张。宝坠妈还是拉住宝坠的手,两个人一起走出屋。
他们站在门口。
那个男人渐渐地走近他们,宝坠一眼就看到男人手里的纸飞机,跑过去说,这是我的纸飞机,怎么跑你手里了。
男人说,是这纸飞机把我带这来的啊。
宝坠狡黠地笑了笑。
拿过纸飞机,回到妈身边。
宝坠妈声音很低,几乎是颤抖着说,你……来……了……
男人说,本来早上就要来的,可是厂里出了点事。本来,我还请了一个吹唢呐的,可是,后来都不能来了,我只好,一个人,来了,你不会怪吧?
宝坠妈没吭声。
过了一会儿,宝坠妈说,进屋吧。
宝坠妈转身进屋了。男人拥着宝坠,也进屋了。
宝坠妈说,你坐。
男人坐下了。
宝坠在玩着那个奇妙的纸飞机,甚至看了看它,纳闷,真的是你把那个男人带来的吗?
宝坠妈说,你想好了吗?我就是这个情况,一个人带着一个孩子,别的我什么都没有。
男人看了眼宝坠妈说,我娶的是你的人,我要的是一个家,一个有温暖的窝,其他重要吗?我又有什么呢?
宝坠妈说,你要是决定了,我还有话要说,你必须对我的孩子好,如果可能,我会再给你生一个,如果你对我们娘俩不好,我……
宝坠妈哽了一下。
男人说,哪会呢?我不是那种太会说话的人,看表现吧!看行动吧!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慢慢你就会知道我是一个啥样人。至于孩子嘛,我实话跟你说,我没有生育能力,这你完全可以放心了,我一定会拿宝坠当我的亲生儿子对待。
宝坠妈不吭声,好像在想什么。
宝坠妈说,你就这么来了,要说过日子也就是过人,但人还是要点脸面的吧?你这样就把我们娘俩接走了,以后,我在乡亲面前怎么抬头?好像我想男人想疯了似的……我不要你什么媒妁之言,不要你什么彩礼,但你总不能就这么把我们娘俩带走吧?我们又不是牲口……
宝坠妈感觉到自己的话说重了,表情黯然了一下。
男人低着头说,也是。你说吧,还需要什么?我过两天,一定准备好,我也觉得,有些匆忙了……
宝坠妈说,我虽然不是什么大姑娘了,但总得放一挂鞭炮什么的吧?这样也喜气,也让我能在乡亲的面前体面一些……我不想听她们嚼舌头……我要光明正大地走出这个村子,而不是偷偷摸摸的……是,我离开这里了,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可,人活的就是一个人气,是不是?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和你领结婚证的,如果你不想领,我们就拉倒,我想名正言顺地……
宝坠妈在那一刻变得格外冷静,仿佛以后生活的每一个细枝末节她都考虑到了。但宝坠妈不能想到,人有些时候能主宰自己,可是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庞大的力量,也在主宰人。人是世界的中心,但人也是世界上最渺小的生物。像蝼蚁。
灵魂承
4
你们相信灵魂吗?
也许你们相信或者不相信,但我要告诉你们,现在对你们讲述的就是我的灵魂。或者说,这是一个灵魂的回忆。也许这样说,你们会感到耸人听闻,没有必要,也许这个世界上,一个灵魂的声音才是真实的。
现在开始。
5
我叫朱河。
一个我喜欢的流淌的名字。
我在轧钢厂工作,开吊车,没有工厂经历的人,可能不知道吊车是什么。我开的那种叫桥式吊车,在厂房的半空中架上两条铁轨,在有限的距离和有限的高度行进和起落,一般长度一百多米,高二十多米吧。我的工作性质是倒班,也就是三班倒,白班、中班、夜班。每个班八个小时。
除了工作,我喜欢画画。
工作是一种生存的需要,画画是内心或者说精神的需要。
就这么回事。
我喜欢的画家是:文森特·凡高。
我的精神教父。
这一切,在那个年代,都是不合时宜的,但没办法,我需要一种精神的生活。本来,我爸是让我去当兵的,可我不喜欢战争,我爸通过他老战友的关系把我弄进了轧钢厂。
至于画画,我是跟陈岚他爸学的,他爸是画家。一个倔强的老头。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老头。他后来成了我的岳父,而陈岚,自然成了我媳妇。也许,红颜命薄,陈岚在几年前,突然离开了我。要不是我家草湖的那个亲戚跟我妈说起相亲这件事,我也不会去。我害于母亲的唠叨,去看了那个女人,也就是秀枝,还看见了秀枝的那个儿子。我没想到,在我第一眼看到秀枝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也许这就叫一见钟情吧,真的,那种感觉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怦然心动。就是当年跟陈岚,也没有,陈岚更像是活在另一个世界上的人,而不是生活之中,陈岚是一个没有烟火味的女人。陈岚就仿佛活在画中。而秀枝打动我的,也许就是她的烟火味,她真实,让人一下子能抓得着,摸得到。我没想到,我会那么冲动,在那苞米秸秆垛里,我竟然抱住了她,还在她的脸上亲了一下。你们应该知道,在那个年代这些行为,似乎是下流的,但对于我来说,那是我的本能,或者说是动物的本能。要不是秀枝儿子的出现,我想我会犯更大的错误。
嘿嘿。
我仿佛在坦白什么。
是吗?
不是的。
看到宝坠那臭小子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虎头虎脑的劲。还有他的目光。在他看见我和她妈抱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目光是小兽的目光,小公兽的目光。我还注意到了,他手里握了一块石头,他可能是想要砸我。他在捍卫他的母亲。一个小男子汉。不错。他骨子里那股劲,很像我。我喜欢。
我和陈岚,没有孩子,医生说,是我的原因。至于陈岚的死,也许在后面,我会说上一些,现在,先不说。
宝坠的目光让我看出他的倔强,他的孤独,他的怯弱。这些,我想,可能是没有父亲的原因。一个缺少父爱的孩子。一个没有主心骨的孩子。老话怎么说,父爱如山,他的心里没有山,顶多有点水,还是小溪。或者说是即将干涸的小溪。但,也不好对付,要慢慢降服。都说做后妈难,做后爹可能更难。人心都是肉长的,相信,我能做一个好爸爸。
反正,我是喜欢上这个臭小子了,还有他妈。
你们可能会窃笑我,还不是惦记人妈,才这么说的。话说回来了,没有他妈,也没有他,这叫爱屋及乌。
6
话说,我从草湖骑车回镇上的路上,我发现了一大片向日葵,看上去能有一亩多地,它们在深秋的地里,耷拉着脑袋,像是在接受某种审问或者惩罚。我停下车,看着,我仿佛感觉它们是有生命的,它们在低语着。我看见有两个农民在收割,也可以说,他们在割向日葵的脑袋。在黄昏的日光中,我仿佛看到血液在流淌;我仿佛看到它们猝然跌落的头颅;我仿佛看到它们在日光的悲怆中,抖落愤怒的种子;我仿佛看到它们最后一次抬起头,张望着西去的落日……张望它们灵魂的光源。
风吹着它们,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集体的哭泣。
我冲动的身体,在发抖,血液变得冰冷。
我仿佛在看一场黄昏的杀戮。
我冲进向日葵森林之中,我想阻止,可是,我知道是徒劳的。那一刻,我想到了凡高画的向日葵的疯狂。我看着两个挥舞着镰刀的农民,我问,还要割几天才能割完?一个黑脸的农民说,两天吧。你要干什么?我说,我想画下来。他说,那你就赶快来吧?我飞快地骑上车,回到家,拿起我的画箱,还有画架,飞快地赶回来,在黄昏的暮色中,我企图在画布上还原那些向日葵的怆凉。如果你们看到我画的向日葵,相信你们一定能感觉到我笔触的愤怒,还有,向日葵的愤怒。天黑了,我就在农民的窝棚里睡了一宿,连夜班都没去上。在那个夜晚,我梦见了葵花的幽灵,在田野上呜咽。第二天早起的时候,我继续画着,两个好心的农民还给我带了一点吃食,我表示感谢,继续,在画布上,为那些割去头颅的向日葵,安魂。
两个农民成了我画布上的刽子手。
我承认,我在画布上创造了他们,而且丑化了他们。在这里,我想对他们表示我的歉意。
两天过去了。
过去了。
我含着泪,看见他们把最后一棵向日葵的头颅砍下来。而我,也在画布上的黑色中,填了几笔血的颜色。我承认,在那一刻,我的身体是虚脱的。
“咔嚓……”
在那最后一棵向日葵的头颅落下来的时候,我感觉我的颈椎也响了一下。
临走的时候,两个农民对我说,明年来画吧?现在看上去一点都不美,明年,你早点来,在还是花朵的时候来,金黄金黄的,看上去美丽极了……
我点了点头,仿佛失去了话语的能力,推着车,和我的那些未干的画,回到了家。我整个人都病恹恹的,不愿说话。失语了好几天。
几天没上班,自然要被扣工资的,还被车间主任狠狠地批了一通。我耷拉着脑袋,什么都没说。有活没活的时候,我都一个人呆在我的吊车驾驶室里,除了吃饭,下班,我都呆在车上,呆在二十几米的半空中。
说实话,要不是我妈到我家来,问起我去相亲的事,我几乎忘记了这件事情。我妈这么一问,我才感觉我这病恹恹的身体,有些蠢蠢欲动了。这怎么解释?我想只能说是,孤独。在这几天,我经历了极大的孤独。它们几乎侵入到了我的血液里,骨髓里……
我妈问,去看的那个女人怎么样?
我说,不错。
我妈说,那就是你中意了。
我说,嗯。
我妈说,那你想怎么办?
我说,当然是娶过来,和她过日子。
我妈说,我听说那个女人还带了一个孩子。
我说,嗯。
我妈说,只要你中意,当妈的不好说什么?其实凭你的条件,完全可以……
我说,嗯。
我妈看见了我画的那些向日葵说,怎么看上去有些阴森?好好上班得了,画这些干什么?又不当饭吃,当觉睡。
我说,嗯。
7
第二天歇班的时候,我骑车去接秀枝。在路上,我又看到了那片被砍去头颅的向日葵秸秆,它们在风中,因为失去头颅,看上去显得悲凉。我怔怔地看了很长时间,才动身来到草湖,我不知道秀枝家具体在哪,在我想向人打听的时候,我看见了一只纸飞机,我跟着那只纸飞机走着,竟然神奇地来到了秀枝家。
我是一个简单的人,或者说是一个不羁的人。我认为两个相互喜欢的人在一起就行了,不需要那些形式上的东西。可是,我错了,我发现秀枝是一个憨厚中带着精明的女人。或者说,她在捍卫女人的某些东西,比如说,尊严。这更加让我另眼相看这个女人了。
我们开始去办结婚证,领着孩子,去照相馆照相,简单买了一些家里常用的东西。秀枝还做了两床被。可以说,为了节俭,陈岚留下的东西几乎都没有扔。尤其是一件紫色的旗袍。她甚至笑笑,穿在身上,对着镜子看着。
我说,都扔了吧?
秀枝说,扔了多可惜。如果,你忌讳的话……
我说,没什么,只要你喜欢。
我还领他们去了我的地下室,也就是我画画的地方。他们娘俩都惊呆了。臭小子还揭开一张我蒙着的画布。秀枝和他都瞪大了眼睛。那是我当年给陈岚画的一张女人体。秀枝的脸腾地一下红了,目光躲闪着,连忙蒙上了。她可能从来没有见过。
当看到那些向日葵的时候。
秀枝说,这不是我们草湖路上的那片吗?
我点了点头。
我相信,这一切对于她们是陌生的。因为,我企图让她们融进我的生活之中。
婚礼还是很简单,我用自行车驮着他们娘俩,放了几挂鞭,就把他们带到我的住处。我妈来了。我没有告诉我的工友。他们来了,也是瞎闹,我不喜欢。我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
第一个夜晚。
洞房之夜。
秀枝把宝坠早早就哄睡了。她烧了水,洗着自己,后来坐在床边,静静地洗脚。她的脸上仍存留着羞涩,绯红,看上去像一个姑娘。我冲动地蹲下来,静静地给她洗脚。她先是拒绝着,说,男人不应该干这个,应该是女人给男人洗脚才对。她拗不过我,任我给她洗脚。我们对性都不陌生,但,我还是感觉到了她的紧张,颤抖。可以说,性在这一晚上,是一种仪式。肉体交融,让两个人成为一个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床上,秀枝玉体横陈,我有些发愣,那细嫩白皙的皮肤,让我看到了瓷器的光芒,看到了环绕着的肉体之美,是瓷实的,而不是虚无的。
秀枝看我发愣说:“发什么愣呢?现在,我是你的,一辈子是你的。”
当我们沉浸在欢愉的世界之中,宝坠光不出溜地站在地上,瞪着两只大眼睛,喊:“妈……”
我们僵住了。我连忙从秀枝的身上下来。秀枝也连忙披了件衣服,爬起来问:“怎么了?宝坠,做噩梦了吗?”
宝坠敌视地看着我说:“嗯。”
宝坠说着,一头扑进他妈的怀里说:“妈,我要跟你睡。”
这时候,我多少有些扫兴,我起来看着宝坠说:“以后,你就要一个人睡。”
宝坠不理我,赖在床上。我抱起他,把他送回到他的小床上,他惧怕地看着我,嘴里喃喃着:“妈妈……”
秀枝歉意地对我说:“小孩不懂事。”
我说:“没事。”
后半夜,我们又做了一次,做了很长时间,但我感觉到了秀枝的歉意,我温柔地贴着她的耳朵说:“他现在对我还是陌生的,等他和我熟悉了就好了。”
秀枝的眼泪,唰,流了出来,她紧紧地,抱着我。
第二天早晨,秀枝早早就起来了,做饭,为我准备中午带的饭菜,然后喊我们起来。我伸着懒腰,那一刻的腰部是酸的。我说,我真不想起来,就这样躺在床上。秀枝笑着说,那可不行,你现在是我们娘俩的天,我们娘俩还等着你挣钱养活呢。我开玩笑地说,是啊!从今天起,我就要为你们娘俩做牛做马,给你们扛活。秀枝的脸色黯然了一下,忙活着给宝坠穿衣服。吃饭之前,秀枝郑重地对宝坠说,叫爸爸。宝坠看了看我,倔强地梗着脖子。秀枝又说了一遍,叫爸爸。宝坠看着秀枝,轻轻地喊了一声,爸爸。对于我,这一声爸爸,不亚于一声惊雷,爸爸两个字像钉子一样,钉在我的心上,但我感到舒服。
我怔了一下,连忙答应着:哎……
我抓过他的小手说,过来,吃饭吧。
宝坠还是板着脸。也许他的心里从来就没有爸爸这个空间,现在突然挤进去一个爸爸,还需要时间。就像一个人的胃,突然塞进去一个硬物,要慢慢消化一样。我这个爸爸,也要他慢慢消化,但,我想,我这个爸爸不会变成粪便一类的东西,而是营养,一种影响他成长的营养。嘿嘿。
有女人和没女人的生活就是不一样,整个家里仿佛也充满了人气。真实。温暖。还用什么词语来形容,我一时想不出来了。
我说过,我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但,那种安静更多属于我的内心。这并不矛盾。
吃着秀枝做的饭菜,我仿佛第一次感觉到真正意义上的家。在以前,都是我伺候陈岚。
我一个劲地说,真香,真香。
秀枝说,慢点吃,还要吃一辈子呢,只要你不烦就行。
我说,怎么会呢?
陈岚死后,我对婚姻一直心灰意冷的,主要是对女人,像陈岚这样的女人,陈岚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我暂且不说。我要说的是,我怎么都没想到,我会遇上秀枝,并且过上了一段有限的人间生活。可以说,秀枝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让我内心的愤怒,在慢慢地消解,还有那股子神经质的疯狂,也得到缓解,我仿佛变得大气、磅礴。也可以说,我从一个暴躁的动物,变得驯顺了。尽管当年跟陈岚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是驯顺的,但我是装的,我装成了一只羊,可内心里我确是一匹狼。现在,完全不同了。那句话怎么说?女人是水做的。是的。秀枝是水做的,而且流淌成一条河,任我遨游。但,水也是一根绳子,你们可能没看见过水做的绳子,但它实实在在地在生活中,拴着你,缠着你,绕着你,还让你感觉不到。
鲁迅在《伤逝》中说,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可,对于我,这一段的爱和幸福是凝固的……
这是怎么回事?后面慢慢说。
有些伤感了。
8
宝坠刚到我家,没几天,我从厂子里给他做了一个铁环,他跑到院子里跟几个小孩子玩滚铁环。没想到一个别院的大男孩揍了他,还抢走了铁环。宝坠哭着回到屋里,当时我正在睡觉。我感觉他碰了碰我说,爸,爸……我懵懵懂懂地睁开眼睛,仿佛还在梦中,我揉了揉眼睛,看见宝坠真实地在我的床边,还抽泣着。
我说,怎么了?
宝坠说,铁环被人抢走了。
宝坠嘴咧得像瓢似的,哭得很伤心。
我光着膀子,坐了起来说,你怎么叫他抢走了?你跟他抢啊?
宝坠委屈地说,他比我大,还揍我。
这时候,我才发现臭小子的脸是青紫的。我的火腾地一下涌上脑门,我说,你怎么不揍他?
宝坠说,我揍不过他。
我从床上,下地,拉着宝坠说,走,我们出去看看,去把铁环抢回来。
来到院中,我看见一个胖胖的大男孩正在滚着铁环,我冲过去,抬起脚就把他踢倒在地上。
那胖男孩爬起来,瞪着我问,你打我干什么?
我说,我就打你了,怎么的?
胖男孩说,你等着,我回去叫我舅舅,你妈的,你要是有种,你就别走。
我说,我等着,不过现在你还不能走。
胖男孩看着我问,干什么?你害怕了吗?
我笑了笑说,你就是把你的舅姥爷找来,我也不怕。
胖男孩站在那里不敢走。
我对宝坠说,去,揍他——
宝坠看着我,眼光怯怯地。
我吼着,过去,揍他,他是怎么揍你的,你就怎么揍他。
可以看出,宝坠从来没揍过人,他还是害怕。
我说,快点,过去揍他。
宝坠磨蹭着,我急了,拎起他的脖领子,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把他拎到胖男孩的跟前。
我说,揍他。
宝坠看了看我,挥动着小拳头,轻轻地打在胖男孩的胸脯上。
我生气地说,他是这么打你的吗?
宝坠摇了摇头。
我说,他怎么揍你的,你就怎么揍他。
宝坠矮那个胖男孩一头,他突然充满了勇气,又打又踢,胖男孩一动不敢动。
我说,你打他的脸啊!
宝坠蹦起来,用拳头杵着胖男孩的鼻子。胖男孩的鼻子流血了。
我说,行了,宝坠,饶了他吧,记住了,以后谁再欺负你,你就这么揍他们,记住了吗?但我们不能先欺负别人,要是我知道你欺负别人,那我不会饶你。
宝坠怯怯地点了点头。
我看着那些胆战心惊,面色惶恐的孩子们说,以后你们谁要是再敢欺负我的儿子,你们也看到了,是什么下场。
我对胖男孩说,滚吧!
胖男孩转身跑了。
我对宝坠说,你们玩吧,我回去睡觉。
宝坠看着我的眼神是飘忽的。他好像不希望我走,他还有些害怕,我抽了根烟,光着膀子,看了会儿宝坠在滚那个铁环,他滚得一点都不好,我走过去,教他,在铁环哗啦哗啦的声音中,他喊着我说,爸,你玩得真好。
后来,我回屋了,没去睡觉,而是到画室里画起画来。
一道阳光从排气窗照进来,落在我的身体上,我看上去是一个那么阳刚的男人。
嘿嘿。
我在画室里还没画几下,我就听见宝坠的哭声,丝丝缕缕的,铁丝一般扎心。我冲出画室,我看见胖男孩果然回来了,领着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男人。这个时候,宝坠正被胖男孩摔倒在地上,用脚踢着。那个胖男孩领来的男人站在墙角抽着烟,看着。还不时地冒出一句,给我打,我还没听说在镇上谁敢欺负我杨大光的外甥的呢!打……狠狠地踢他……
有小朋友喊着,宝坠,你爸来了。
宝坠趴在地上哭喊着,爸……爸……
宝坠的喊声像一把碎玻璃扎进我的耳朵里。
胖男孩也听见了小朋友的喊声,停住了。宝坠鼻青脸肿地爬起来,跑到我的身边。我心疼地看着,摸了摸他的脸,他嘴里嘶嘶的喊着,爸……疼……
胖男孩有了靠山,他连忙蹿到那个男人跟前,指着我说,舅舅,就是这个人打我,你要给我报仇。
那个男人吐掉嘴里的烟,凶狠地看着我。我也不示弱,我们的目光交接在一起。我们没说话,身体紧跟着目光,我们打在一起。他也不过如此,几拳就被我杵得晕头转向,被我抵在墙上。
这时候,秀枝买菜回来,吓呆了。她看了看宝坠,明白了发生了什么,连忙扔下手里的菜篮子,过来劝架,说,别打了,别打了,小孩子打架,怎么大人也打起来了?快松开,快松开……
我正在火气上,说,男人的事,女人少管,滚一边去。
秀枝仿佛没有听见,仍在说着,快松开,快松开。她掰着我的手。我还是松开了,没想到那个男人是一个小人,转身在墙上抓过一个砖头,一下拍在我的头上,血哗地淌了出来,流到脸上,我发疯地揪住他的头,往墙上撞着。男人开始求饶说,我服了,我服了……
我松开了手,吼着,滚——
男人说,你好样的,够男人,我叫杨大光,发电厂的,这么多年,在镇上还没碰到过对手,今天我栽在你的手里,我认了,不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的……
男人喊着胖男孩说,走,我们走。
男人的眼睛瞄了一眼秀枝,走了。
秀枝拉着我和宝坠回屋了。秀枝连忙找纱布给我包着头,嘴里说,大男人的怎么也像小孩似的,小孩打架,你跟着一般见识什么?
我说,我不能让人欺负我的儿子,你知道吗?不能!欺负我的儿子,就是欺负我。
秀枝不吭声了,眼泪掉豆子似的,噼哩啪啦地掉下来。
我说,哭什么哭?
秀枝说,你说这一砖头要是拍中了,你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娘俩可怎么过?
秀枝给我包扎完了,又看了看宝坠,目光剜着说,再不许在外面打架了。
宝坠倔强地说,是他们打我,以后谁再打我,我就往死了揍他们。
秀枝刚想发作。一个邻居的小女孩站在门口,拎着秀枝扔下的菜篮子说,婶,你家的菜篮子。
……
时间就像这个省略号,直到有一天省略了我。
两年。三年。四年。
宝坠八岁了。
9
有一天,我领宝坠去轧钢厂洗澡,这小子在澡堂子里好一顿欢实。像泥鳅在澡堂子里游着,扑腾着,撩着水。他对那些工友两腿间黑乎乎的东西看着,笑着,还看了看我的。我弹了他一个脑嘣,喊着他,别疯了,快过来,给你搓搓,不给你洗净了,你妈回去又要说我了。宝坠乖乖地过来,让我给他搓着身上的泥球。他嘿嘿地笑着说,痒,真痒。工友们开玩笑地跟我说,朱河,你真不赖,就这么捡了一个大儿子。我说,你们有能耐,你们也去捡啊!
从澡堂子出来,宝坠欢实地蹦跳,像一头逃出兽笼的小动物。
一群麻雀落在厂区路边的树上,唧唧喳喳地叫着。突然,从厂房上的一个大喇叭里传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宝坠吓了一跳,站住了。
宝坠喊着:“有人在喇叭里……有人在喇叭里……”
树上的麻雀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也飞走了。我怔怔地听着,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安上去的大喇叭。我听着,不寒而栗。我拉着宝坠,推过我的自行车,带着宝坠,往家走。那一刻,我是惶恐的。
在街上,我看见一群带着袖标的孩子在喊着:
“文化大革命万岁!”
“…………”
我带着宝坠,躲到一边,我看见当年那个杨大光在队伍的前面,挥舞着胳膊,领着头,喊着口号。
宝坠好奇地看着,问我:“爸,他们干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不知道。
这时候,我看见一个我的朋友,也是画画的,宁昌平,在队伍当中,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牌子,距离有些远,我看不到上面写的什么。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身体像触电似的抖了一下,推着宝坠,快速溜走了。回到家,我喊着:“秀枝,秀枝,出事了。”秀枝惊讶地看着我问:“出什么事了?”我说:“运动来了。”秀枝问:“什么运动?”我说:“文化大革命。”我说:“赶快,把我地下室里的那些画都烧了吧!”秀枝说:“那不白瞎了。”我说:“宁昌平,你记得吧,以前来过咱家,他已经被游行了……”秀枝的脸色吓得苍白,看着我说:“真的,要烧吗?”我说:“烧!烧!”我说:“秀枝,你带着孩子回草湖避一避吧,说不定,马上他们就会闯进咱家,我看他们都疯了……”秀枝说:“我们不走。”我说:“我怕连累你们,你还是快点带孩子走吧?”秀枝说:“我们不走。”宝坠在旁边也说:“我们不走。”我说:“你们还是走吧?要不你们可能会跟遭殃的。”秀枝说:“遭殃,也在一起。”我说:“秀枝,现在不是犟的时候,你还是快点带孩子走。”秀枝说:“除非你不要我们娘俩了,要不我们不会走的,不会。”宝坠在一边竟然哭了,嘴里喊着:“爸,你不要我们了吗?爸。”我拉过宝坠说:“不是的。”我也说不明白。我跑进画室,开始烧那些我一笔笔画的画,看着火焰中那些变成灰烬的画,我哭了,号哭起来。仿佛烧的不是画,而是我的身体,我的心。我的心抽搐着,泪光中,我看见我画的那些葵花疯狂地站立起来,在风中飘摇,哭泣着。烟雾弥漫。我任火焰烘烤着我的面孔,火焰深处让我感受到了某种凄怆而且饱满的悲伤的情绪,隐约还夹杂着一丝神圣。
在烧陈岚的那张裸体画的时候,我还是不忍心,几乎是颤抖着,把它投进了火中。毕竟曾经夫妻一场,尽管……
(陈岚的故事与本小说关系不大,我就不多说了。)
宝坠站在秀枝的身边,拉着秀枝的衣襟,呆呆地看着我。他看见我哭了,他也跟着哭,呜呜的,就仿佛我们的亲人刚刚逝去。火光映在他的脸上。
当我想把我临摹的那张凡高的 《自画像》(割耳朵的那张)要投进火里的时候,宝坠冲了过来,抢了过去,抱在怀里说,你看这个人多可怜,你不能烧了他,不能。我愣住了,怔怔地看着宝坠,说不出话来。我犹豫着,还是决定留下这一张。我坐在地上,看着火焰,跳动的火焰,像心脏。哭干了眼泪,整张脸紧绷绷的,像一张纸,随时都可能崩裂。我相信,在那一刻,秀枝不能理解我真正的内心的痛苦。但,她站在我的身边,一声不吭。从她的眼睛里,我感觉到她在心疼我。这就够了。黑色的灰烬。死亡的颜色。我开始清理着,然后倒出去。我身体里的某一部分,在丧失,或者说,在那一刻,我是一个孤儿,精神的孤儿,我的父亲,精神之父,已经被我焚烧。半个我在疼痛。半个我在颤抖。半个我在抽搐。半个我在痉挛……
晚上,我像一个孩子,瑟瑟地蜷在秀枝的怀里,低低地抽泣着。我的脸紧贴着她柔软的乳房,甚至,在黑暗中,叼住她的乳头。突然,我变成了魔鬼,开始进入她,企图撕裂她。现在想起来,我为我的行为感到羞耻。我承认,那一刻的性,疯狂带着愤怒,不是针对秀枝,而是……
后来,我疲惫地爬下来,我发现秀枝哭了。我什么都没说,一个人浑浑噩噩地睡了。我梦见熊熊的大火,是的,大火烧着了成片的向日葵,它们发出噼啵的声音,还有葵花种子爆裂的声音。向日葵们奇谲瑰丽,它们在火中呻吟着,呼号着,扭曲着。它们哈哈大笑,它们号啕大哭。呼啸的火焰在舔食着它们,在吞噬着它们,成为火焰的一部分,或者全部。燃烧的葵盘像头颅似的耷拉着,掉在地上。我怀抱着凡高的《自画像》狼狈地从燃烧的葵花丛中,仓皇地逃出来。突然,我听见燃烧的葵花丛中,有人喊叫,我停了下来,我听见那是宝坠的喊叫声。宝坠在火中喊着:“爸爸……爸爸……”。我转身冲进火中,在烟熏火燎中寻找着宝坠,可是,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除了火焰,还是火焰,它们像一双双飘摇的手臂,在阻拦着我,阻拦着我。我冲进火丛中喊着:“宝坠……宝坠……”。没有回音。没有。只有火焰的呼啸声,像一团站立的血,以火焰的形状,张牙舞爪。我看见一个幼小的影子,在晃动着,在企图突出火焰的重围,可是,火焰抱着它,推着它,不让它出来。我喊着:“宝坠……宝坠……”。仍旧没有回音。没有。我坐在地上,哭着,大声地哭着。四周一片黑暗。黑暗在塌陷,我仿佛囚禁在黑暗坑底的一个困兽。我哭醒了。秀枝听见我的哭声,问我,怎么了?我说,做噩梦了。我没有告诉她,梦中关于宝坠的事,我怕她担心受怕。这个噩梦像一个木楔子深深地钉进我的大脑里,直到我死。
关于我的死,应该是死亡,我不说了,不说了。
我的灵魂累了,我想让它歇一歇,我还要上路。关于我死的故事,还是由作者来完成吧。我相信他真实的笔触。他会给我一个真相。但,作为宝坠的爸爸,我是留恋这个人间的。因为,宝坠,也因为秀枝。因为人间的一切美好。
疯狂转
10
我们一群戴着红袖标的孩子,在杨大光的带领下冲进了宝坠家,我们像一群凶猛的野兽。我看见宝坠坐在窗台上摆弄着一个马蹄表。他是第一个看见我们这些戴红袖标的人闯进院子的,他的手抖了一下,马蹄表掉在地上,摔碎了。宝坠从窗台上跳下来,跑到他爸的床前,喊着:“爸,来人了,昨天我们在大街上看到的那些人,那些戴着红袖标的人。”朱河听了宝坠的话,一激灵,连忙穿上衣服,坐起来。朱河凛然地对着墙上的镜子看了看自己,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朱河的目光看到掉在地上摔碎的马蹄表,他看见其中的一个指针摔得弯曲了。他看了看宝坠,仔细地看着。甚至宝坠的每一根毛发都被他的眼睛保存在他的大脑里了。
他拉过宝坠说:“儿子……”
宝坠抬头看着朱河问:“干什么?爸。”
朱河继续说着:“儿子……”
宝坠继续问:“干什么?爸。”
“儿子……”
“干什么?爸。”
“儿子……”
“爸,你怎么了?妈——你过来看看,爸怎么了?”
我们这群人潮水般地涌进来,声音的巨浪撞击着空气,几乎能听见撞击的声音。我们像闯进一个无主的房屋,四处翻着,开始抄家。杨大光看了看朱河,笑了笑说:“你也有今天……”
朱河没动,身体像一座雕像坐在那里。
宝坠嘶声喊着:“妈……妈……家里来坏人了……”
秀枝听到宝坠的喊叫,连忙从厨房跑出来,她惊呆了,嘴巴张得大大的,像嘴里被塞了什么东西。她怔着,颤抖地问:
“你们干什么?”
杨大光说:“干什么?你说我们干什么?你丈夫是资产阶级余孽,你知道吗?”
秀枝愣了愣说:“我们都是穷人,什么资产阶级的,我不懂。”
杨大光说:“你丈夫画画,就是资产阶级余孽,有人揭发他了,还说他画那种女人光屁股的画……”
秀枝看了看杨大光说:“谁他妈的在放狗臭屁?说我们画光女人屁股的画,画他妈的屁股吗?还是你妈的……”
秀枝的话让朱河一愣,他还第一次听到秀枝骂人,他脸上笑了一下,但很快收敛了。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像一个在等待圆寂的僧人。
“你说什么?”杨大光立棱着眼睛问,“你再说一遍,你别以为我没听见,要不是看你是女人,我非扇你大嘴巴子不可。”
杨大光的话音刚落,一个小红卫兵就冲过来,跳起来,扇了秀枝一个嘴巴。又有几个小红卫兵也冲过来,揪着秀枝头发的,踢她的,踹她的,抓她的,像一群野狗。宝坠冲过去帮着秀枝,被一个红卫兵蹬在地上。这时候的秀枝已经被按倒在地上了。她的手正好按在马蹄表的碎玻璃上,血一下子呲了出来。
朱河看了看杨大光说:“别打他们,我跟你们走……”
杨大光喊着:“别打了,搜到什么没有?”
一个红卫兵抱着那张凡高的《自画像》走了出来。
秀枝挣扎着企图站起来,可是她感觉全身的骨头都碎了。杨大光上来要搀扶她,没想到秀枝一口血唾沫吐在杨大光脸上,杨大光没生气,擦了擦,喊着那些小红卫兵:“走啦!走啦!把朱河给我带走,把这个资产阶级余孽带走……”
我们押着朱河,走出屋去。
秀枝在地上爬着,身边跟着宝坠。
秀枝喊叫着:“你们不能带他走?你们不能带他走……”
宝坠在喊着:“爸……爸……”
宝坠的喊叫是用他身体里的血在喊,仿佛一条飘扬的带子,企图挽留住正被人带走的爸爸,可是,徒劳。沉沉的,沉沉的喊叫,砸落在身体的某一处。心脏,随之颤抖。
那个捧着凡高《自画像》的红卫兵从宝坠的身上踩过去,他的样子看上去就像在捧着一个人的遗像。
秀枝披头散发地爬到门口,一下子抱住了杨大光的腿,她说:“求求你,放了他吧,求求你……”
杨大光企图从秀枝的双臂中抽出自己的腿,可是秀枝紧紧地抱着,缠绕着,就是不松开。杨大光看着秀枝,抬起另一只脚,轻轻地贴在秀枝的脸上,然后,狠狠地,把秀枝的脸踩在地上,从他那偶尔一闪的凶猛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在暗中打量这个女人,他的目光像一根粗糙的绳子,绕过她的脖子,拂过她的肩膀,在胸部的停留……然后,缠绕上去,紧紧地,勒着。他看着痛苦的秀枝,心里腾起一股莫名的快感,他的绳子在收紧,收紧,勒进她的肉里,勒——勒得越紧,他越感觉到一丝快感,在心里面兔子般地蹦跳着,在那些红卫兵的眼皮底下,他还是收敛了,他说:“你个资产阶级余孽的女人,难道也想被带走吗?你要与这个男人划清界限,你知道吗?”杨大光的脚抬了起来。秀枝的脸还贴在地上,变了形状,两只眼睛突兀着,几乎要被挤出来。朱河扑了过来,被杨大光拦住了。朱河吼叫着:“宝坠妈,起来,你带着孩子回你的草湖去吧!回去……”宝坠不知道什么时候爬到了杨大光的两腿之间,狠狠地咬住了杨大光的腿肚子,像一条小狗,狠狠地咬着。杨大光抬起腿,整个宝坠也被抬了起来,杨大光一踢,一甩,就把宝坠摔了出去。朱河喊着:“宝坠……宝坠……”宝坠被重重地摔在地上,一动不动。杨大光骂了一句:“狗崽子,叫你咬人,摔死你个狗日的。”宝坠摔在地上之前,先是撞到了墙上,然后弹了回来,摔在地上的。他的头撞破了,血流了出来,在脸上,蚯蚓般地蠕动着。秀枝啊地叫了一声,向宝坠爬过去。杨大光看着秀枝撅着屁股,像一头母兽,而他的目光,在那一刻,变成了一头公兽,跟了过去……
秀枝把宝坠抱在怀里,眼泪哗地流了出来,像一颗颗疼爱的种子,落在宝坠的脸上。泪滴落在血上,红色在变淡,变薄。宝坠的脸上,像蒙了一块红黄相间的手帕。宝坠闭着眼睛,仿佛在睡觉。秀枝哭喊着:“宝坠……宝坠……你醒醒,你醒醒……”秀枝的目光匕首般投向杨大光,和杨大光猥亵的目光碰到一起,就像攮在了肉上,然后,深深地剜进杨大光的眼眶。杨大光开始退却,在退却中他坚硬的目光,变得柔软起来,带着欣喜,仿佛垂杨柳。他喜欢上这个女人了。这个女人的愤怒和倔强,让他蠢蠢欲动。杨大光喊着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们把朱河带走。浩浩荡荡的队伍推搡着朱河,就像一群猎人的鹰犬,走出院子。朱河几次想转身,都被扭过头去。一个红卫兵叫嚣着,推搡着说:“再回头,再回头,扭断你的脖子。”
11
我被杨大光留下,潜伏在宝坠家,偷听他们的消息,然后及时报告给他。
宝坠问,妈妈,爸爸还会回来吗?
秀枝说,会的。
宝坠问,他们把爸爸带到哪去了?
秀枝说,还不知道。
宝坠问,他们会打爸爸吗?会往爸爸头上扣那种尖尖的帽子吗?
我趴在窗户外面,感觉那个屋子是那么的黑,而他们娘俩,也成了黑的一部分。他们都没吃晚饭,他们好像不饿。宝坠哭着睡了。秀枝呆呆地,像一个木头人。我饿了,我跑回轧钢厂俱乐部,报告了杨大光,没有什么情况。
12
在轧钢厂的俱乐部内,我看见朱河被绑着,脖子上挂着梵高的那幅《自画像》,他们先是让他捧着,让后又挂在了他的脖子上。在捧着的时候,看上去好像在捧着一副遗像。
杨大光问,你知罪吗?
朱河说,什么罪?
杨大光问,你自己不知道吗?你是资产阶级的余孽。
朱河摇着头说,我不知道。
杨大光问,你脖子上挂着的这个外国老头是谁?他是你的亲属吗?还是你的国外亲戚,你难道不是里通外国的特务吗?
朱河说,不是,他只是一个画家,他已经死了。再说了,我也不可能认识他。
杨大光说,那你留着他的画像干什么?他的耳朵是怎么回事?
朱河说,我喜欢他的画。
杨大光说,你怎么喜欢外国的?他们都是大毒草,你不知道吗?看来你被资产阶级的思想毒害得很厉害。他的耳朵到底是怎么回事?
朱河说,可能是为了一个妓女,自己割掉的。
杨大光兴奋地说,你说什么?他竟然为了一个妓女割掉了自己的耳朵?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不是不认识他吗?
朱河说,我在书上看到的。
杨大光说,书上说他为了一个妓女割掉了耳朵吗?
朱河说,是的。
杨大光竟然咧着嘴笑了,牙齿上闪着亮光。但,很快,他就闭上了嘴,他控制住了自己的笑。他仿佛意识到了,那是不合时宜的笑。他铁青着脸,看着朱河,他想到当年,被朱河打的情景。他恶毒地,是恶毒,他又一次笑了笑,笑容里藏着恶毒。
杨大光说,为了表示你与资产阶级的决裂,现在,我命令你,也割下你的一只耳朵。
朱河愕然。
其他的小红卫兵野兽般地叫嚣着,让他割下他的耳朵,让他割下他的耳朵……
我们的声音,像一个苍蝇的军团,嗡嗡作响,让朱河的脑袋都大了,随时都可能爆炸。应该说,那个声音里,没有我的声音。我也不知道杨大光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是在茫然的冲动中,才跟他们在一起的。
这时候,一个孩子冲上去。他手里拿了一把小刀,他是王屠户的儿子,他手拿着的是他爹的牛耳尖刀。刀刃闪着白光。他对朱河说,你自己来,还是要我帮忙。我爹说我杀牛什么的不行,但我想,我割一个耳朵还行吧。他吹了吹刀刃,看着朱河。
台下面的人们,仍旧发出苍蝇军团般的嗡嗡声:割掉他的耳朵……割掉他的耳朵……那个外国佬割一个,我们要给两个都割了,让他彻底的决裂……决裂……
朱河淹没在苍蝇军团的喊叫声中。他的心抽搐了一下,痉挛了一下,整个身体也跟着哆嗦起来。
一声惨叫,接着是另一声惨叫。
两只耳朵像受伤的蝴蝶,翩翩落在地上。在地上蹦跳着。一个没有了耳朵的人,一个血人,看上去是那么的难看。只见朱河疼得嗷嗷地叫着,两手捂着割下耳朵的地方,血从他的手指间淌出来,我吓得闭上了眼睛。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见他躺在台上,身体看上去是僵硬的。我问旁边的一个人,他死了吗?那个人说,脑袋都开花了,能不死吗?我说,不是只割了两只耳朵吗?那个人说,他疼得撞在柱子上了……
朱河就这么死了。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时期,死人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但在后来,我却听见杨大光编了一个谎言。这个谎言是对秀枝说的。这要回到那两只耳朵中其中的一只。有一天,一只耳朵摆在了秀枝的面前。是杨大光带给秀枝的,他说,朱河与他们划清了界限。这只耳朵就是最好的证明。还说朱河逃走了。秀枝看到那只耳朵的时候,整个人都懵了。宝坠哭喊着说,这不可能是爸爸的耳朵。秀枝拿在手里看着,她发现了耳朵后面的一块黑痣。她嚎啕痛哭。
可是不久后,我发现,杨大光竟然出入秀枝的家。我还听见,秀枝叫宝坠叫杨大光爸爸。我感到愕然,我不知道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不久后,我们在铁路桥下发现了杨大光的尸体,至于是谁杀了杨大光,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其他人的带领下,烧毁了镇上的教堂,赶走了那些牧师。有一天,我们搜捕一个牧师,他竟然躲到了宝坠家,是我看见那个牧师藏在一个角落里,战战兢兢的,我没有报告。因为我看见宝坠用他几乎要杀人的目光看着我,我想到了他死去的朱河爸爸,我悄悄地离开了。
再后来,秀枝也死了。我看见那个牧师领着宝坠,把秀枝的尸体和朱河的尸体埋在了小镇的东山上。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朱河被埋在轧钢厂俱乐部旁边的几棵树下的。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把朱河的尸体找出来的。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宝坠。
我为我是那个年代中的疯狂的一份子而忏悔。
这也是我对你讲述的理由。
悲伤合
13
你小说里写的宝坠就是我,但小说开头,那可能不是我。因为,我记事后,我就没有父亲。至于你虚构的,我想我的过去,也许是那么回事。也感谢你的虚构,让我知道,我可能的过去。也许我的过去就是那样的。我是说你虚构的我的第一个父亲的死亡。至于后面,简直就是我的生活,不过我的第二个父亲不叫朱河。他叫耿长喜。在我的记忆里,他才是我真正的父亲。可以说,我现在,把凡高的那幅《自画像》作为他的遗像供奉着,因为我没有他的一张照片。你可能会问,我在后来怎么突然就消失了,这我要跟你说说。我和牧师埋葬了我母亲后,牧师收养了我,带着我回到他的国家。英国。你知道吗?也许人是通灵的,我常常梦见我的父亲,你写的朱河,他没有耳朵的面孔,在黑暗中呼喊着。
我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哽咽。我想说句什么安慰的话,可是我不知道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我问,那么你的第三个父亲是你杀的吗?他没有吭声。沉默了很长时间。他才低声说,是。他的声音仿佛带着杀气。尽管这是我的意料之中的,但我还是感到一丝的惊愕。我想继续追问,但我没有。我想他会自己告诉我的。
他说,要不是你的小说,可能一辈子我都会把这件事情藏在心里,直到埋进土里。可是,你的小说打开了我的记忆之门,我心怀着罪,在对你说。
自从杨大光把你写的朱河的耳朵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都惊呆了。他说这是朱河与我们决裂的见证。也就是说朱河抛弃了我们。我和我妈都哭了。先是我妈捂着脸号啕大哭。然后是我的哭声。杨大光怒吼着对我们说,人家都不要你们娘俩了,你们还哭什么?哭个屁。可是,我妈还是哭。她说,朱河不会不要我们娘俩的,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我妈在不停地摇头。她的头像一个拨浪鼓。她不相信。她还说,就是打死她也不会相信。她要当面听朱河把话说清楚了。我站在一边说,一定是你害了我爸爸,你是仇人。我说着就要上去咬他。可是,杨大光一脚就把我踹在地上,嘴里还骂着,小兔崽子,我踢死你。他把脚狠狠地踩在我的脸上。我的脸贴在地上都变形了,眼珠子几乎要被挤出来了。杨大光得意地看着我妈说,你还不相信吗?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我今天就踩死你的儿子。我躺在地上喊着,妈妈,救救我。我妈看着我被踩得那样,心软了。她轻轻地说,我信了。这时候,杨大光才放开我。我两眼冒火地看着他。我骂着,我操你妈。杨大光反手给了我一个耳刮子,我的脸火烧火燎的。整个身体也火烧起来。我还是骂着,我操你妈。我相信,你能理解一个儿童那时候的仇恨和恶毒。他说,当时要是我有一把刀的话,我一定会当时就杀了他。可是,我和我妈是弱小的。杨大光顺着窗户,把那两个耳朵扔了出去。我跑去,只见一条野狗叼走了其中的一只耳朵。我捡起地上的那个放在兜里,拼命地去追野狗。当我从野狗的嘴里气喘吁吁地抢下那只耳朵,回到家中的时候,我惊呆了。我看见杨大光赤身裸体地……
我妈听见了我的脚步声,连忙把杨大光推到地上,急火火地穿上衣服,看着我说,宝坠,去买点酒回来。我眼睛看着我妈,我的目光是憎恨的。我没有去买酒,我呜呜地哭着,跑出了家门。在路上,我遇到了大权,也就是你小说里写的那个跟你讲述“割耳朵”的那个人。他把我拉到一个胡同里,跟我说了我爸朱河死了,而且被埋在轧钢厂俱乐部的旁边。你小说里,他说他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他在撒谎还是你有意隐瞒。但这些都不重要。我跑到了轧钢厂俱乐部旁边的树下,我一下子就找到了埋着我爸朱河的地方,我用手抠着,手都抠出了血。我要把我爸朱河挖出来。就在我疯狂地挖着时候,大权在身后拉着我说,人都死了,你挖他干什么?我说,我爸没死。没死。大权看着我说,宝坠,别挖了,你们家现在斗不过杨大光的。我坐在地上呜呜地哭着。后来,我把那两只耳朵埋在了我爸朱河坟墓的旁边。我一个人坐在我爸朱河坟墓的旁边,天黑了,夜深了,我觉得肚子叽哩咕噜地叫起来。我饿了。我吞咽着唾沫。我在那里睡着了,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直到我妈找到我。我扑在我妈的怀里说,这就是我爸朱河的坟。我妈也哭了。我妈怎么来的呢?也是大权偷偷告诉我妈的。我妈对我说,宝坠,为了你,妈也没有办法,为了你就是让妈去死也行,可是,现在你还小,妈还不能死……你要听话,听妈妈的话。我回到家后,才知道,杨大光喝醉了,妈妈才跑出来找我的。
第二天,杨大光醒了。我妈叫我喊杨大光“爸爸,”,我咬着嘴唇就是不喊。我妈生气地打了我,还让我跪下。我妈说,宝坠,你要是叫妈死的话,你就不喊。我妈看着我。我哭着,声音颤抖着,对着杨大光喊了声“爸爸”。杨大光哈哈地笑着说,好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儿子了,你们娘俩跟我,我一定叫你们吃香的喝辣的。我看见我妈的脸上堆着难看的笑。从那以后,杨大光天天带着我去抓人,然后批斗那些人,还去烧那些教堂。我不愿意跟他去,可他逼着我去,要不就打我,也打我妈。在烧教堂的时候,我带着一个人逃走了,把他藏到了我家的地下室。最危险的地方可能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个道理当时我不懂,现在想想就是这么回事。有一天,杨大光领着我在镇上的馆子里吃饭,他喝了很多酒,天黑,我们往家走,到铁路桥上的时候,他站在桥上撒尿……你能想到,我狠狠地把他推到了桥下面。我竟然一点都没害怕。我绕道跑到桥下面,只见他脑浆子都摔出来了。你可能不会相信,一个那么小的孩子竟然能干出那样的事,但是,我干了。我杀了一个人。我回到家,我妈问我杨大光呢?我说,不知道。后来人们发现了杨大光的尸体,可是,我和我妈都没有去管。据说是他的亲属给收的尸。我妈好像感觉到了什么,但我妈没有问我。令人想不到的是,一个造反派的头头死了,竟然无声无息。镇上也没有什么动静。甚至很多人认为,是另一个造反派的头头干的。
我承认我有罪,可是罪不在我……
其他的事情不说了,我妈生了一场大病,死了。临死前,她拉着我的手,把我托付给了牧师。
就这么回事。
顺便说一下,下个月,我可能会国内办一个画展,画展的名字就叫《时代的孤儿》,希望你能来参加。
我开玩笑说,你不怕我报案吗?
他在电话的那端笑了笑说,你没有证据,你的小说来自你的虚构,我的讲话也可能完全来自我个人的虚构。因为每个人的骨子里都隐藏着为正义杀人的欲望。不是吗?还有,我想,任何一个有血性的读者看到你虚构的杨大光的形象,都可能会挺身而出,杀了他。只是,我是第一个站出来的读者,而你是真正的杀人凶手。你起码在这个小说里杀了四个人。
他在电话那端狂笑着。
他的声音让我脊梁一阵发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