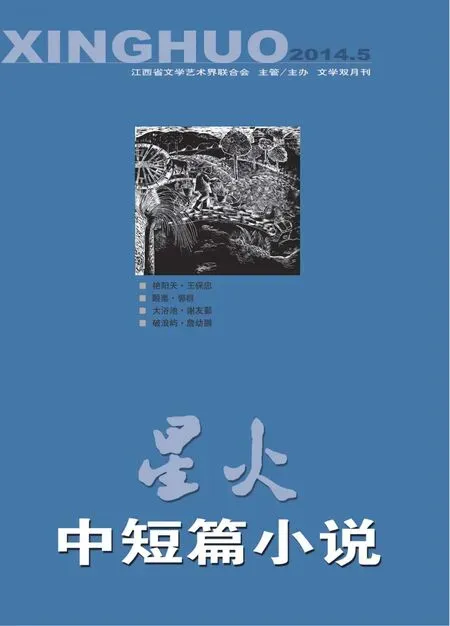如 莲
□ 莫大可
我到了某个季节就不能出行,因为我患有严重的花粉过敏症。春天里,我必须躲避植物孢子看不见的疯狂“攻击”。为什么把花粉过敏又叫做“枯草热”,我所受的罪全是那些发育壮硕的植物带来的,种子把我的身体当成了“乐土”。
后来,K就用一顶破草帽为我制了一个类似于头篷的玩意,帽檐用发黄的蚊帐缝制成遮挡。样子真难看,我虽然一下子接受不了,但戴着那玩意还是让我有些许神秘感。我告诉K,蚊帐不会是从老情人家里扯下来的吧。K不理我,我继续骚扰他:这个玩意真别扭,吐口唾沫还要把那布片样的玩意揭开来,像撒尿,先解裤子,再掏家伙。我又说,看我,是不是像个古代的侠客呢?
K没有搭理我,他背着一个硕大的摄影包,包里鼓鼓囊囊的,K每次出门都这样,步履匆忙,不过有时他会回头叮嘱我一些事情,比如修片的要求,比如帅哥(我们养的一只猫)的粮草又没了,比如电费别忘记交,都是些烂事情,他是担心我在那幕帘后会睡着。
K又整理了一遍沉甸甸的背囊,今天有三档婚礼要他去拍摄,做我们这一行的叫“行摄”,犹如独狼,徘徊在大小影楼和摄影工场之间,肉条也好,排骨也好,都不能嫌弃,要活下去,就不能挑肥拣瘦。K走了,像条大船颠簸在春天的翠色里。
一到春天,我就“瘫痪”了。
春天可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旺季,人们扎堆结婚,以最密集的形式迅速寻找配偶,完成繁衍过程里的重要一章。当“枯草热”来袭的时候,我就只能在“运河五号”的工作室里修片,喂猫。“运河五号”是一排紧邻运河的老厂房,解放前曾是某实业家的后花园,同时又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纺织厂。当曾经的熙熙攘攘退出历史的舞台后,河流却依然忠实地守护着那些残存的记忆。现在,工厂最前面的一排位置被开发成了店铺,靠后一些的车间被改造成了独立的工作室,租给艺术家,摄影师,类似于Live house的小酒吧,我和K租住的就是最里面的一间工作室。我们不对外挂牌,不大的房间里贴满了海报,摄影作品,其中有一副是我们最为满意的,经过PS后的巨大相片上站满了结婚的新人,那都是我们服务过的对象,差不多有三百多对吧,数字不惊人,但阵势惊人。我和K站在新人们的中间,让三百对新人变成了我们的陪衬。我们的许多生意是靠这张“嫁接”过的图片获得的,大有人体活广告的创意,K和我都很满意。
我带着K为我制作的那顶独特的头蓬准备开始工作,可能是我太过投入的缘故,我根本没有感觉到有人站在门外注视着屋里的一切。那天,徐娜盯着那张巨大的相片看得发了呆。起初徐娜以为是一张电影海报,她站在门外,被一大片雪白吸引住了,婚纱,头花,那个漂亮呵,新人们摆出优雅的姿势,露出幸福的微笑。她完全沉浸在相片的氛围里了。徐娜被感染了,也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白天的“运河五号”很安静,少有人溜达到此。我们的邻居是位画家。画家头发稀疏,是美院的老师,我叫他老赵。老赵显然是个闲人,可能退休了,也可能在哪里挂了个闲职。整个冬季,老赵都在他的工作室门前忙于造园,把自己弄得像个泥瓦匠,除此之外,就是我这个“瘫痪”在春季的摄影师。
我真的没想到一个陌生人会站在门外。陌生人吓了我一跳,不是老赵,老赵进来一般都不打招呼。我不知道陌生人在门外站了多久,她好像沉迷在我身后的相片里,今天也没有约好的客户来取片,我等待陌生人说话,但我等来的依然是沉默。于是,我忍不住先咳嗽了一声。
要么是我的咳嗽声吓着了徐娜,要么是我的模样太过于诡异,反正徐娜是被吓着了。她全然没注意到一个戴着武侠片里才有“行头”的人躲在暗处向她咳嗽,
我没有揭开头篷,继续躲在暗处看着徐娜。徐娜的胸脯不停地起伏着,让我想起运河里风浪席卷过的泊岸。
不好意思,没有打搅到到你吧。她的话着实让我大出意外。我有心撩开幕帘想仔细看看门外的陌生人,但是我不能,那些花粉会飞进我的眼睛,它们太细小了,它们会停留在我的眼帘,像潮湿热带雨林里疯长的苔藓。我摇了摇头。
你的样子好怪哦,这里的人都很怪,刚才一个老头还拿着烂泥巴在堆一个石墩呢。我知道她说的是正在造园的老赵。我点了点头。
“啊,原来它躲在这里啊。”这次我被徐娜的一声惊呼给吓着了。
白猫从花架上跃落到地面,温顺地匍匐在我的脚边。徐娜指着白猫说,我以为是我们家的那只呢,搞错了搞错了,我们家的“咪咪”没这么大。徐娜蹲下身来看着白猫。
我特别讨厌小猫小狗。猫是K要养的,因为我们租住的房子里经常出现老鼠,有只猫会好许多。老厂房以前还出“大仙”,就是黄鼠狼。咪咪,你叫啥名字呀。徐娜用一根树杈逗玩着白猫。透过纱帘,我看清了徐娜的脸,鹅蛋型的脸庞,眼睛特别大,不过有着很深的黑眼圈,小嘴鼓鼓的,像赌气的样子,还蛮可爱。
她站起身来说,店里的“小不点”跑掉了,找了好久哦,也不知道被哪只流氓猫给拐跑掉了。她靠近我,一股强烈的中药味袭来。
她用的形容词挺特别的——流氓猫。
你这人好奇怪哦,不说话,戴着个头篷,要是在夜里一定被你吓死。徐娜甩了甩头,我知道你们是照相的,改天也帮我照一个,打个折吧。我叫徐娜,在“台风”上班。
我戴着头篷,如果再披个黑斗篷就更像侠客了。那天我挺懊悔,没有把头篷摘下来,更没有告诉徐娜,我是一个技术不错的摄影师。我知道“台风”,那是一家新开的音乐酒吧,有着很强的文艺调调。我没去过“台风”,老赵和他的学生经常去,老赵说,当下没有什么东西能值得他玩味了,追求的精神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就无意义了。
老赵现在一会儿和稀泥,一会儿敲砖削瓦,乐趣多多,这个老赵真是玩得高深莫测了。我挺羡慕老赵的。老赵是艺术家,艺术家不上班最大的典型人物是赵佶。所以我极其羡慕艺术家,可以不上班,可以筑园雅集,他们比文学家都长寿,也都是环保主义者。
我问老赵,老赵,“台风”里美女多吗?
老赵说,多,多到像天上星星。
文艺青年加美女,那隐藏着的种种艳遇!但我不可能像老赵那样高调,我就是个摄影师,更关心行业的淡季和旺季,电脑里大堆积压的片子,我的合伙人K先生正如独狼穿行在城市森林,我明白为什么K的眼神总是那么冷峻,我们只是和那个巨大的派对毫无关系的局外人。墙上的挂历被K用狼毫圈满了大大小小的标记,那是出工的记号。K心情好的时候会用那支狼毫题壁,K的书法不错,笔墨酣畅,不过气势全被潮湿斑驳的墙壁吞没了。
看着满墙的墨团K说,一个大型的展会在南方召开,某家实力超群的企业邀他全程摄影。K没有继续说下去,从摄影包里掏出相机,手法熟练地退出内存卡。K要远行,我摘下K为我制作的头篷看着他。多年的合作使我们达成了一种默契,K点点头,凝视着手里的狼毫说,要是觉着闷,可以出去走走。
我点点头,我说我不会走得太远。我曾经有过一次在路上差点被花粉夺取性命的经历,所以我说我不会走得太远。春天,变成了紧闭我的季节。
我依然带着头篷在工作室修片,老赵忙于他的筑园工程,我们互不相扰,日子过得倒也清闲。那天,徐娜先是站在老赵的工作室前看老赵和稀泥,她一语不发,看得津津有味。等老赵歇下来的时候她问老赵,老师,隔壁那个带帽子的人真是奇怪哦。老赵说,你觉着他哪里奇怪了,他不是很正常嘛。
徐娜有些腼腆地继续说,那他总带着怪怪的头篷干啥?
老赵说,怕见人,见光死。
这么邪门啊,他的脸是不是有缺陷。徐娜用手比划着,是被烧伤了还是有其他原因?
老赵把一块硕大的磐石架在石墩子上,他望着徐娜说,没啥,就是花粉过敏。徐娜这次没有站在门前看那张相片,她撅着嘴“咪咪”地叫唤了一阵,她在找那只白猫。白猫听到了,像闪电一样躲进了房间的深处。这家伙这么怕生,徐娜说。
“小不点”找到了吗?我在问她一直寻找的另一只白猫。
没有,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徐娜失望地摇摇头。
我说,找到那只流氓猫就好了。
徐娜咯咯地笑着答道,我们老板伤心死了,那只猫是她的命根子。我说,你还这么开心,猫没了你还这么开心?徐娜说,我不能把我的不开心表露给你看啊,人要活得开心一些,不是吗?
我被她的话问住了。我发现K为我制作的那层幕帘有了个小小的破洞,徐娜的目光正试图穿过那个破洞。你能把头篷摘了吗?真是难看死了。
我摇摇头。虽然我很想摘下那丑陋的遮挡。
徐娜站在那张相片前看了很长时间,她指着我和K说,哪一个是你?
我说,个子矮一点的是我。我长的是矮了点,但不有碍观瞻。
你会摄影,一定很厉害吧?看着相片里那些一对对新人,徐娜露出艳羡的神色。要是有那样一张婚纱照该有多棒啊。我露出怀疑的神色,虽然她看不见。她才多大啊,顶多二十,冒顶二十二,一定被Live house里的那些文艺青年给 “毒化”了。那些女子都到了老到嫁不出去的年龄了,叼着烟,喝着酒,说着醉话,只有老赵说,装都装不像。又有几个人能达到老赵那样的境界呢。老赵说,我是老了,只能附庸风雅了。我相信老赵的话。
当徐娜提出要拍婚纱照的一刻,我一点也不惊讶。
我对陌生的徐娜一点也不了解,就像我不了解春天一样。我变得与世隔绝,自从K离开后只有白猫陪伴我,白猫傻乎乎地扑弄着老赵刚刚栽种的花球,老赵筑造的微缩版园林也有了雏形,绿水、枇杷、芭蕉叶、湖石假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老赵欢喜的不得了,大有在此隐世的念想。老赵于是开园迎客。
我一定成了百老汇《歌剧魅影》里的剧院幽灵,丑陋到了不敢见人的地步。老赵的第一位客人,一位行为艺术家在见过我后击掌直呼“大好”。我不明就里,试问好在何处。行为艺术家答道,在这装逼的世界只有你最会装。我哈哈大笑,老赵也哈哈大笑。然后,行为艺术家提出要收购我的这顶头篷作为他装置艺术里的道具。我没答应,因为他要把K精心制作的这顶头篷放在一口棺材上。行为艺术家曾经也是老师,是老赵的朋友,老赵说,他啊,可爱到迂腐,迂腐到可爱,以独善其身的清高安抚失落的心。
管他娘的,我继续修片。
应诺替徐娜拍婚纱照是在一个下雨的午后,我的手指开始厌倦了点击鼠标,有按快门的冲动。K打来电话,依然是叮嘱修片,喂猫,夹杂着一两句南方那个城市不为人知的气候和景色。我挂断电话,看到徐娜湿淋淋的站在工作室门口凝望着我。我说,你进来说话,外面下雨。她没有答话,呜呜地哭出声来。我问她,你是怎么啦,进来说话吧。我给她搬来一个椅子。
徐娜坐下就泣不成声了。“小不点”找到了,找到了……
原来雨水灌进了紧邻河道的一条排污沟,“小不点”随着泛滥的春水一起飘向大河。我说原来不是流氓猫呵,这座园里到底有没有流氓猫。
有,还不止一只。徐娜开始破涕为笑。
我用雀巢咖啡招待了徐娜。徐娜说,下午不忙,雨天客人更少,所以有闲过来。我对她的到来表示欢迎,也从她的话语里了解到徐娜的家在外地,她上班的“台风”是徐娜的表姐经营的。
我说,表姐一定照顾你吧。
徐娜说,很照顾啊,我表姐还没结婚呢,她比我大11岁,她不想找男人,也不想要小孩子。
我说,你呢?
徐娜露出羞涩的笑,她嘴角有些许黄色的茸毛,让我想起花粉和孢子。徐娜提出要拍婚纱照,她的语气就像小孩闹着玩。我问她新郎呢?她说拍着玩玩呗,不要很多场景的,就在这里拍,她指了一下老赵的园子。
有谁把拍婚纱照当成玩玩的呢。没有。现在有了,是徐娜。我帮她打了个对折,徐娜说,不请化妆师,让她表姐帮着化妆。我估算了一下,也就百来块,没赚头,不过这次春拍可以安慰我寂寞已久的手指,现在徐娜变成我的客户了。
在老赵的竭力邀请下我去了“台风”。老赵的意思是,不去白不去,是他学生请客。夜晚的一排店铺灯火通明,在运河的涛声下竟让人有恍惚之感。工作室离“台风”并不远,但我从未感觉到今晚特有的那种宁谧之感。找定座位落坐,店不是很大,但氛围一流,适合文艺青年和文化人,“台风”开在运河边,就是做老赵这样的客户生意,合对的很。
老赵是这里的常客,很多人和他打招呼。要了酒水茶点,几个人边吃边聊。老赵和他学生的话题多是当下的时事热点,也有人把话题扯到想为某某局长送一件礼品,看中了某画家的画作,想请老师在价码上去圆个场。老赵点个头,说今年下半年打算开个人画展,到时都来凑个热闹吧。
学生们连声附和,说,要得,要得,老师的画展一定要办得最上档次。
老赵是画家,善画奔马,老赵画的马形神兼备,如果不是园太小,老赵或许会养上一匹。老赵是我们几个人的焦点,自然引得老板来招呼。老板也就是徐娜的表姐,长得真是很一般,没有妖娆的风姿,不知道为什么能搞出这样有特色的酒吧,背后一定有高人,三十好几都不结婚。
打过招呼表姐走了。我在找徐娜,徐娜呢。找了半天没找到,这店里也就两个服务生,我拉过一个问,徐娜呢?
服务生说,徐娜在医院挂水呢。
徐娜生病啦?我追着问。
服务生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你不知道啊,徐娜每周都要去定期治疗的啊。
定期治疗?她得的是啥病啊。
——白血病。
小时候看过山口百惠的《血疑》,幸子得的就是绝症白血病,大岛茂的女儿需要IH阴性血才能延续生命,我印象深刻。现在徐娜得的就是那种看不好的绝症,我伤心了,但不欲绝。没理由,我们才认识几天,没理由,她还没死,何况她只是我的一个客户而已。
K在电话里唠叨的依旧是琐事,他告诉我夜晚的城市充斥着不解的暧昧,他把他们全部装进了相机,等着回来和我细说。我掐着指头计算春天的尽头,白猫安静地睡在我脚下,老赵的园林接近收工阶段,他的访客每天不断增多,有诗人,作家,画家,也有旅行家。他们在园子里谈天说地,兴致勃然。我想问老赵,想借他的园一用,为徐娜拍上几张照片。
自从上次行为艺术家有意收购我的头篷后我开始刻意避开他们,我不想成为他们议论的对象,要么他们真是没见过世面。我问老赵,老赵,改天借你园子一角拍几张照片可否。老赵说,可以啊,有啥借不借的。
老赵正和一位作家在说话,作家姓李。李作家的眼光显然抵不上行为艺术家,他说,老赵啊,你们这里怎么会有养蜂人呢。你难道还要在这小园里养一群蜜蜂不成。
老赵说,有趣吧,你还真猜不出来。
李作家提出要戴上一戴我的头篷,体验一下那种隔着幕帘的于世恍惚。我回绝了李作家的体验要求。
李作家微微打量着我,一会儿说,这里在拍戏?一会说,没搞展览会啊。李作家的答案层出不穷,末了索性转移了话题,说起一位画家画里的乳房情结。我觉得老赵的这些客人都不真实,和他的学生比起来差远了。借园成功,我又接着给影楼打了个电话。影楼等于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借了两套婚纱,说定了送过来的日子。我又掐算了一下日期,觉得春天真的快到尽头了。
再次看到徐娜,她又瘦了,黑眼圈变得更大了。她还是那么活跃,我们好像成为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
徐娜说,蒙面人(她起的外号),告诉你吧,我表姐谈恋爱了。她喜滋滋的模样不像说假话。
我说,你表姐老到那样还有人要。
我表姐没打扮呵,打扮起来还是蛮有味道的。你见过我表姐?
没有。我掩饰住自己的慌张,那次我摘掉了面具,以正常的面目出现,没有人会认识我。我说,你要多注意休息,少吃辛辣的食物,平日里小心不要弄出伤口……
连我自己都觉得罗嗦起来,徐娜的脸在纱帘后开始晕散开来,我居然不争气的让眼眶潮湿了起来。我怎么就轻易地动了情了呢。
徐娜低着头,手里拿着K常用来题壁的狼毫逗玩着白猫。你都知道啦,是表姐,还是小张。一定是小张,回去割她的舌头。狼毫顺着白猫光滑的皮毛撸动,那小东西很享受地闭上眼睛。
她嘴角的茸毛让我想她是多么年轻,上次我们说起死亡的话题还是“小不点”,徐娜很忧伤。我想她急着拍婚纱照就是为了迎接日后的死亡吧。现在,她很淡定地告诉我她得的就是白血病。
是啊,是啊,我就是得了那倒霉的白血病。也许,我很快就会死去。徐娜掏出手机给我看,你看,这么小的年纪就得了这毛病,头发都做得掉光了。那是她和一位小病友的合影。她说,我不想做化疗,表姐帮我配中药。
徐娜握着白猫的爪子说,猫咪,我过几天来看你,到时候你就做我的伴郎吧。我说,你特别喜欢猫吧。她说,是啊,特别喜欢猫的沉静。我关掉了电脑,我的电脑里有无数新人拥抱的画面,屏保也是拥抱,文件夹里也是拥抱,内存条里也挤满了拥抱,我只能关掉电源。我有脱下头篷的冲动,抱一抱这个喜欢猫的女孩子。
老赵微缩版的园林完工了。我真佩服老赵的那双手,既能搬得山石,也能绘出万马奔腾的场面。老赵在磐石上沏好茶,和他聊天的是位旅行家。
旅行家很年轻,去过很多国家,也常带点国外的小纪念品给老赵。这次旅行家带给老赵的是一把干枯的莲蓬。干瘦的莲蓬让老赵看得入了迷,那失去水分的丝丝经脉让老赵抚摸了良久。干瘪的莲蓬发出夏季荷塘特有的清香,老赵眯着眼睛说,上品,上品,值得把玩啊。
旅行家告诉老赵,他按照玄奘当年出使的路线一路走下去。行至印度,旅行家被异域的风光吸引住了,公路旁植满了印度榕、芒果树、棕榈,猴子四处打闹,旅行家看到公路旁荷塘里盛开的荷花,他从车上下来,凝视着那一洼洼的翠叶粉荷,他畅畅快快地在荷塘里沐浴,采集了大把的莲蓬,他透过落满夕阳的水面仿佛看见了佛的化身。
老赵,你相信吗,我正准备上岸,一辆大卡车把我的越野车给顶了个底朝天。
旅行家在回忆里嘘了口气,大有勘尽了生与死的了悟。旅行家说,活着就不要太执著了,生死上天所定,太过执著反而是痛苦了。
我觉得这个年轻的旅行家不简单,他不像行为艺术家,用某种愤世嫉俗来痛击世界的虚伪,也不像作家,用太多的假设叩击本已脆弱的心灵。旅行家沉默不语,只顾喝茶抽烟,然后,起身走人。
和徐娜约好的时间已过了三天,她依然没有出现。板凳上的婚纱已经有了薄薄的一层灰,电脑里的片子都已经修的差不多了,我的脑子里又塞进去了无数的脸,长的,圆的,瘦的,胖的,K已经安排好了回来的日程,在结束完南方的工作后他要去看望一个旧友,我一直说那是他的老情人,每年去看望几次,完成所谓的交合和调情。K说等他回来为我换一顶新的头篷。
夜晚,春天的夜晚适合谈情说爱,表姐正和一位学者模样的客人在谈情说爱,不谈情说爱真是浪费掉了。我独自坐在“台风”,表姐已经记不起我了。期间有文艺老男人和小资女邀我玩杀人游戏。我礼貌地回绝了,真是对不起,我说我在等人。
我拉住小张的手,把小张吓了一跳。我说我没神经病,我就问下徐娜去哪里了?
小张说,住院了。她很是厌烦地甩开了我的手。
我说她怎么样了,到底怎么样了。我又情不自禁地拉住了小张的手。我说,她会死吗?
……无聊。
我发现小张是个美女,她一定以为我在借这个话题骚扰她。没有办法,我只能去找徐娜的表姐。不知道怎样开口,我尽量表现得自然一些。我说徐娜呢?表姐抬头看我,笑着问,你是娜娜的朋友?我直奔主题,徐娜又住院了?表姐点点头,她没有必要隐瞒什么,表姐说,她的血小板减少到只有3万了。表姐忧伤地低下头,学者模样的男人趁势握住了表姐的手。
晚上,刮起了大风。接着下起了狂暴的雨。
开灯,我看见白猫瑟缩在一角。风大雨大,也许这阵狂风暴雨后就跨入了夏季。我一直等待夏天,我有许多人生计划,去看望年迈的父亲母亲,用攒的钱买个新的镜头,或许会谈场恋爱,也可能会去旅行,我等待这样的季节。
第二天,我看到了老赵的园子。一夜的风雨让老赵精心筑造的园子变得面目全非。老赵说,想不到,想不到。我以为老赵在为那些残花败柳叹息。老赵说,这半夜风雨,也让贼有机可趁——老赵用来摆茶的磐石不见了。那是老赵的学生花了大价钱从民宅淘来的。
老赵又准备开工了,他画了一张更为“宏伟”的图纸,精准地标注出每样设施,他的园子扩大了,大有侵入到我们工作室的架势。老赵说,变一家人了。
植物的种子随着季风的到来明显减少了,K不再给我打电话了,他像一颗种子飘得远远的,我知道他一定和他的老情人在耳鬓厮磨。我想,徐娜也许死掉了。我没有勇气去“台风”打听。我甚至迂腐地想,他们一定会出殡,如果出殡就知道了。
影楼不断的来电话催还婚纱,我编造了无数次的谎言,说假话都不用预演了。值得庆祝的是我摘掉了头蓬,那块发黄的蚊帐变得肮脏不堪,它为我遮挡了一个季节的风尘。我抱着白猫,看着老赵的园子,我看到徐娜站在园子里,徐娜正站在园子里对着我笑。
我差点说,你没死啊。我太激动了。
徐娜又瘦了,她的脸颊骨无情的突出,眼窝深陷,嘴唇苍白,唯一不变的是嘴角边细微的茸毛。她的脸是精心打扮过的,干净,没有多余的东西。我依然用雀巢咖啡招待这个季节里我唯一的客户。徐娜抱着白猫,用狼毫细心地梳理着白猫的胡须。
猫咪,猫咪,姐姐要拍结婚照了,说好做我伴郎的呀。
我的脸有些虚肿,徐娜说,你的脸好胖啊。
“胖。”我咯咯地笑着说,那是虚肿。
她依然叫我蒙面人,蒙面人,照片就交给我表姐吧。表姐“五一”结婚,我都说好请你们去照相呢,打个折呵……
我说你不来拿片了,还是等你自己来拿片吧。
她咬着苍白的嘴唇,牙印深深地陷进去,我注意到她的眉帘上抹着淡淡的一层眼影,粉色的,像塘里的花荷,我感到了夏季的延伸。最后还是挑了老赵园子里的一角,那天老赵不在,忙得我汗水淋漓,我的表现像个新手。徐娜坐在一张大红的贵妃椅上,她穿着红色的婚纱,像一团落到地上的火。
笑一笑,笑得灿烂点。她笑起来,喜悦如莲。
阳光并不刺眼,我从取景器里看到了模糊潮湿的一片,我无力地按下快门,“咔嚓”,清脆之声越过春天的晴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