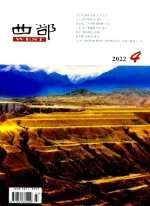随笔二题
(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著
朱景冬译
千年安魂曲
我们这些拉丁美洲的孩子,讲拉丁语的欧洲国家的孩子,我想还有讲法语的非洲地区的孩子,通过马莱特和艾萨克先生的绿皮小书学习了世界史,他们把历史经过的时代很清楚地划分为中世纪、近代和现在。中世纪始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基督教巩固时期。近代始于发现美洲和康士坦丁失陷之间的选择时期。现在,毫无疑问,始于1789年法国革命。
这是为西方写的一部西方的历史,但是在日期和事件的目录后面有其对更重要的时间和空间的描绘。中世纪那种由上到下以信仰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其活力来自精神力量和世俗力量之间的政治紧张状态。从这种紧张状态——拜占庭世界和俄罗斯世界不存在这种紧张状态——中,最终诞生了民主。文艺复兴运动结束了封建主义的分裂局面,看到了在商贸野心的推动下和宗教战争的破坏下民族和国家的诞生。对非欧洲国家的征服,使这些国家进入了世界史,但条件是,它们必须沦为殖民地——就是说,它们必须“文明化”,就是说,不加引号地受剥削——这是凭借神圣的法律建立的君主专制制度。这种制度最终被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所摧毁,这个阶级自由解放的呐喊便是法国和美国的革命。最后是现代,它被描绘为一个物质大发展的十九世纪。在二十世纪开始时,它断言进步、自由和幸福是同义词:现代的梦想,孔多塞乐观主义的胜利。
这样,千年的图解就有了一个大空间:被西方殖民化的整个世界。不过,只是一个时期,就是作为确切的人类发展尺度的西方历史的时期:休谟、赫德尔、洛克的时期。毫无疑问,但丁、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描写的,巴赫、莫扎特和贝多芬歌唱的,布鲁内莱斯基、菲舍尔·冯·埃拉希和克里斯托弗·雷恩建筑的,伦勃朗、贝拉斯克斯和戈亚描绘的,托马斯·德·阿奎诺、斯宾诺萨和帕斯卡尔思考的,贝尔尼尼、米圭尔·安杰尔和罗丹雕塑的,狄更斯、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描述的,歌德、莱奥帕尔迪和波德莱尔用诗表现的,艾森斯坦、韦尔斯和布纽埃尔搬上银幕的,克普勒、伽利略和牛顿解释的一千年,不仅为西方带来了荣誉,也为全人类带来了荣誉。
“怎样才能成为波斯人呢?”在一个把大多数不是白人和欧洲人的人类留在黑暗中——尽管有维科——的光明世纪,孟德斯鸠曾嘲讽地自问。对亚洲和拉丁美洲受排斥国家的历史存在进行的征服或再征服是过去一千年的基本事实之一。其结果是,不是只有一种历史,而是有许多种历史;不是只有一种文化,而是有许多种文化。
怀着这种意识到达千年末,是这一千年的胜利之一。
但是,结束的岁月会留下人对人施加暴力的骨肉相残的烙印。霍布斯的“人对人像狼一样”的观点玷污了这个千年科学与艺术的伟大成就。从天主教和新教的法庭到维辛斯基法庭和麦卡锡法庭都不可容忍。其间,一部暴力的历史描述了在征服美洲,三十年战争,对欧洲的阿拉伯人和犹太少数民族的迫害和驱赶,欧洲对黑非洲、印度和中国的殖民侵略,以及依靠强制劳动力、儿童劳动、种族奴役和排斥女性而进行的经济扩张中不断加深的痛苦。
人使人遭受痛苦的能力在我们自己这个垂死的世纪达到了顶点。在整个历史上从没有如此残酷地死过这么多人:在两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殖民战争——在阿尔及尔、越南、刚果、罗得西亚、中美洲发生的——死亡数百万人,还有希特勒下令对犹太人、天主教徒、共产党人、吉普赛人、奴隶和同性恋者进行灭绝的大批遇难者;由美国历届政府扶植和庇护的拉丁美洲军事独裁政权进行的迫害规模虽小,但是受害者遭受的痛苦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减轻。
这样清点死亡人数的异乎寻常之处是,历史上这个科学技术最进步的千年,也恰恰是历史上政治和道德最落后的千年。无论阿蒂拉、尼禄还是托克马达,都不如希姆莱或皮诺切特残暴。在这个千年结束时,它的悲剧是:它虽然拥有确保人类幸福的一切措施,但是由于我们用最坏的措施对待灾难而把那些良好的措施废弃了。弗莱明、索尔克、克里克、沃森、波林、居里夫人,世纪末的一切伟大的科学家似乎应该永远和致命的、但是不需要的侩子手和不必要也没有任何理由杀死数百万人的历史罪人的幽灵共处。
古老悲剧的暴力作为人类可歌可泣的斗争的一部分表现出来:我们是不幸的,因为我们不完美。二十世纪的专制制度把悲剧变成了罪犯:这便是当代历史的悲惨罪行。丑恶政客们拒绝给历史以认识自己拯救自己的机会。古拉格集中营、奥斯威辛集中营或阿根廷监狱的受害者被剥夺了悲惨的再认识而变成了暴力的数字,第九个、第九千个或第九百万个……受害者。世纪末的一些大作家——特别是弗朗茨·卡夫卡和威廉·福克纳——的深刻意义在于把悲惨的尊严归还给了罪恶历史的受害者们。
罪恶的或悲惨的历史告诉我们,当十年前冷战结束的时候,历史也结束了。巴尔干半岛和车臣、阿尔及利亚和下撒哈拉愈演愈烈的暴力,加上已成为现代城市生活的常规而例外的暴力,应该提醒我们反对在1999年12月最后一天或2000年1月1日举行过分的庆祝活动。无论是人类的显贵还是仆人,都懂得日历。在光辉的岁月里,我们将创造通讯工具、艺术、惊人的医学成就,我们将深入到无始无终的无限宇宙中我们尚不了解的空间。我们将创造友谊和爱情。但是,在昏暗的夜晚,三分之一的人类将饿死,地球上一半的孩子会被拒之校门外,占人类半数的妇女将被关上肉体自由的大门,人类将继续掠夺大自然,仿佛我们不可一世的狂怒达到了不要空气、不要水、不要森林、不要生存下去的权利的程度。
在这一千年,历史不再是单一的历史——像西方的历史那样——它并入了许多历史和许多文化。
在这一千年,科学、物质和技术上取得的非凡成就并没有克服道德和政治可怕的落后状态。
现在开始的这一千年会好些吗?
亚伯·克萨达的箭
有一首博特罗唱道:“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相识的时刻开始。”
博特罗是一种热带地区的、调子忧伤的浪漫主义爱情歌曲,也是关于爱情的一种报道形式,在意大利叫做“一见钟情”,在墨西哥叫做“一箭中的”。
一对男女相遇便永远相爱,谁也离不开谁,无论道德规范还是物质上的障碍都无关紧要,不管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的距离都没关系,因为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相识的时刻已经开始。
这本书叫《缪斯的猎手》,它汇集了我的朋友亚伯·克萨达的绘画,是一本描绘爱情的书。在书中,亚伯天天出门去狩猎,怀着射箭的疯狂热情猎取他所爱的一切东西。
瞄准爱情射箭的克萨达先是对女人们(特别是贵妇们)满怀感情,随后又因看到她们那么孤独而感到痛苦不安,于是就为她们每个人找了伴侣,就像即将登上方舟永远去度蜜月的诺亚那样。
但是此人不是诺亚,而是亚伯。他在路上受到该隐罪恶的监视。世界上有带武器的人,军人,但也有平民百姓,他们都不太喜欢成双成对谈情说爱的人。
于是亚伯宣布他喜爱游戏,并把关于游戏的画像交给情人们,让她们把它交给当局,当局就像吸血鬼一样根本不加理睬。
他还声明他热爱火车、轮船、飞机、出租汽车和飞船,让恋人们永远拥有方舟,以便一起逃走,被打散时好相聚,并把卑劣的该隐甩在后面。
作为这个爱情狩猎队的猎手和向导,亚伯·克萨达拥有完美的伪装:他赤身裸体狩猎,以免身上的衣服弄出动静而惊动猎物,特别是缪斯。
猎手克萨达用他父亲亚当的衣服伪装自己。我们都一样一丝不挂。
但是,如果我们认出亚伯,那是因为他在做梦,尽管他赤身露体,一支游行队伍白天黑夜每时每刻都从他眼前经过。即使闭着眼睛,他也看得见,并要我们和他一起观看他们爱的东西。于是他又动心喜爱女人了。
妻妾和圣母,变化无常和虔诚,令人不安地混杂在一起。她们坐在沙发上,好像在邀请我们到她们面前去,她们靠在沙发上,好像对我们说:已经没有你的位置,她们独占着豹皮椅子和俄罗斯浴缸,就这样提醒我们这些男人:如果你是我所生,或者你为我死去,我才能给你留个空位置。
“我怎么会是你所生,怎么又会为你死?”亚伯问女人们。
那些女人,有时称为母亲夏娃,有时称为恋人维纳斯,有时称为寓言作家斯切雷萨达。她们对他说:“这很简单,只要你和我一起生,和我一起死,我们永远在一起。你在中间做的,是你的事情。”
所谓“你的事情”,是指世界。亚伯·克萨达一次又一次在世界上旅行观察它,对它了如指掌,和它一起娱乐。那些女人始终注视着他,总是在旅行结束时等着他,这样问他:
“你为我带来了什么,孩子,回头的浪子?在你进行的伟大旅行中,你拯救了什么?你从贪婪和忌妒、野心和懒惰、遗忘和冷漠以及该隐的狂怒中夺回了什么?”
回头的浪子的回答取决于他回到哪个女人面前。
如果他回到恋人维纳斯面前,他的回答就是:“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相识的那个时刻开始。”在这种情况下,亚伯将带着不多的东西从游猎中归来,为的是避免麻烦,避免交付太多的行李费,同时也为了使渴望的幽会更快地到来。他带回的东西有几包斗牛牌雪茄烟,一对帝国的神蛋和一个屏风。在去想象的、刚果色的非洲中心猎捕缪斯之前,可以在屏风后愉快地脱去衣服。
但是在维纳斯的眼睛里,在她那像某些蛇的舌头那样又长又分叉,时而狭窄、凶险,时而被泪水映得晶亮的目光里,有一副忧郁的神情,她对画家说:
“世界先于我们存在,知道这事我们感到高兴;但是世界将经历灾难而幸存,知道此事我们又感到忧伤。”
可怜的艺术家只能这样回答残忍的缪斯说,先于我们的东西是记忆,后于我们的东西将是渴望,但是只有站在现在这个时刻才能回忆过去,或想象未来,而现在就意味着置身现在。
被猎获的猎手克萨达很清楚地知道,这种存在的中介是女人,是她们的抚爱、她们的宠爱、她们的吻,有时还有她们的残忍,最坏的情况是她们的遗忘。这一切告诉我们:
“开始,你是刚出生;最后,你又是刚死去。”
于是,回头的浪子便躲进了第二个女人夏娃母亲的怀抱。她对他说:
“我们的生命在我们出生前就存在了。”
这句话,艺术家也明白。当然对,有一种传统,有一部历史嘛……任何东西都有其源泉,什么也不会凭空产生。
因此就产生了和艺术家时而通过笑容时而通过叹息,但总是通过那种恰恰把他变成一个艺术家的非凡精神传授的一切东西联系在一起的感觉。
亚当的儿子亚伯收集了世界上的果实,拿去献给了他母亲夏娃。这种礼物,可能就像河里的一块画着一位预言家的面孔的卵石那么可笑;就像一头黑色斗牛那么令人生厌;就像一座空荡荡的体育场那么凄凉;就像一头孤单的奶牛那么忠厚;就像中央公园的一条僻静的道路那么危险,但是夏娃对这些东西缺乏兴趣。她有一只咬过的苹果,不想拥有别的东西。夏娃回避任何财富,但是夏娃记得过去的体验。她感谢那些美丽的玫瑰,但是她不要任何礼物。
“你什么也别给我,亚伯儿子。你还是把一切讲给我听吧。告诉我,你经历过什么时代?”
回头的浪子,缪斯的射猎者,爱神亚伯明白这个问题,便又开始了他的旅行,不过,这一次是在记忆里。他对最初叫夏娃的女人说:
“我经历的时代,大家都戴着草帽;大家都相信飞艇;那时匈牙利拥有一艘战舰,尤卡坦却仍然没有潜水艇;那时火车常常晚点,因为它们为等待我的每个朋友上车而误了时间;那时胡安·索里亚诺和胡安二十三世教皇是同一个人;那时戴面具的斗士沙多受到妻子的疼爱,但是她一见他不戴面具就离开了他;那时我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
“你看我把自己画成什么样儿了,母亲,我已不像一个墨西哥北方人:身材魁伟,先前是黄发如今是白发,有点秃顶,面带微笑,目光敏锐;而成了你们这个模样不同的儿子:这是我想象出来的,眼睛近视,胡子很长,头发像豪猪毛。”
“你还喜欢我吗,母亲?你还经常拥抱我吗,妻子?我死去的那一天你会把我的眼睛合上吗,知识分子圈里的维纳斯?你会给我的坟墓献花吗,有一点点缺陷的尤卡坦姑娘?不管怎样,不管我变化多大,你还爱我吗?”亚伯对夏娃说,他发现两个人都发生了变化。
因为对缪斯窃窃私语的女人是许多姑娘。
原来的夏娃不可避免地开始像即将死去的维纳斯了。
但是在这两个女人中间还有一位纸牌上的女王——他想象的寓言作家斯切雷萨达,不讲故事的故事作家。这是她说的话:“我们只是在我们想开始想象的时候才开始生活。”
还是她,正是在夏娃和维纳斯之间的斯切雷萨达使现在的克萨达有了那副更吸引人的外表,他那股现代的古老香味,他那种有点过时的装饰,他那种怀念火车和齐白林式飞艇的情结,他那双无声电影明星的耳朵,但是还有他那种不死的、刚刚爱上躺在沙发上的女人们,欢呼拳击台上的冠军,搭乘下一班驶向灯塔的轮船,下一趟驶向魔山的火车,在交叉小径的花园里迷失方向的老汽车,出去寻找流逝的年华的缓慢的飞艇的炽烈愿望……
作为一个时代——有时是那个时代的富足,有时是那个时代的贫乏——的写照,亚伯·克萨达的绘画最终既是对没有女人、没有夫妻、没有空气的空荡荡的空间的回忆,也是对那种空间的驱邪;在那种空间里,死亡抢在生命的前面,在时间之前到来。是亚伯同该隐的斗争。
当我们在亚伯的那副最凄凉的画上看到位于终点的垒球运动员,利马莱斯垒球队的最后一名队员时,我们的笑容顿时凝结在了口唇上,他的目光那么忧伤和绝望,他甚至都不想举起戴手套的手去接那只也许永远不会飞来的球。
就在亚伯的这幅画的中央,画面就像一枚决定命运的硬币。不过,抛起来的命运,硬币的正面或反面,不把他的美妙作品包含的这一切可能性告诉我们吗?——
从在世界上存在以来的一切记忆和渴望。
意外事件的幽默,偶然的命运,用讥笑破坏肃穆气氛、赶走懒惰并用爱情和友谊、男神和女神来代替的失败之举。
冒险和旅行,肉体上的危险和精神上的危险。
一包雪茄烟,一张摆好的桌子,一匹备好鞍的骏马;准备起锚的费利尼的船,马上就要关门的爱德华·霍伯的酒吧,等待狂欢节的基里科的广场,被公共市场挤掉的卢梭海关。
我们用来对冷漠和死亡说“否”的千百种方式。
对权力说这句话的笑声、歌声和梦幻:“你需要我,因为不存在凌驾于任何东西之上的权力,你更需要我,而不是我更需要你,你应该承认我的自由……”
对可爱的人说这句话的爱情之箭:“什么也阻止不了我,我一定要飞到你身上……”
与此同时,决定命运的垒球队员、缪斯的猎手,站在伟大的非洲国家中央,带着刚果人的面色,等待落在嘴上的一句话而不是落在手上的一只球。
亚伯·克萨达对我们保证说,他不会抛弃他的小兄弟,他将对他许下诺言,他的话也许像写在从前的手抄新闻小册子和更古老的阿兹台克手抄书上一样,通过一朵云传到那个孤独的人儿的嘴上去,好让那个只身站在我们硬在大地上创造的那一大片空地上的人儿听到他的话。认出对他说话的热情的艺术家后,他抬起头来对他说:
“克萨达先生,我太自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