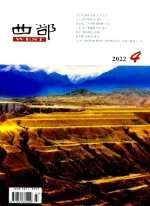博尔赫斯怎样成为他自己
高尚
使一个人成为他自己的那些要素——时间、地点、相关人物和事件……从他命运的最终结局来看,都是缺一不可的。缺少其中任何一种,这人便不会成为他自己,而会是另外一个什么人。这些要素以其奇妙的序列存在于绵邈的时空之中,似乎是专门为某个人而准备,并早在他到来之前就已在那里等待着他了。它们犹如一颗颗钉子,最终把属于一个人的命运牢牢钉在了他的身体上。如同十字架和受难梦见了耶稣,失明梦见了荷马和弥尔顿,一些先事而来的要素则梦见了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时间、相关人物和事件:为命运奠基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生于1899年。如果换个姿势审视这一事实,则完全可以认为,博尔赫斯与其说是个人物,还不如说他更像是1899年的一个期待而已。假设他早到或晚到这个世界一步,那么他后来所经历的一系列人和事,在这个充满偶然的世界里就会变得难以预料了。例如,他十五岁那年的欧洲之行直接催化了他的文学生涯,而如果他晚出生一年,那么他的欧洲之行显然就变得虚幻了,因为就在那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假如没有1914年的欧洲之行,也就很难有1919年的西班牙之行了。没有这次西班牙之行,他便很难得到西班牙当时声名鼎鼎的大师拉斐尔·坎西诺斯的发现和栽培(他的第一首诗歌就是在西班牙发表的),就完全可能和西班牙的极端主义失之交臂,或仅仅是道听途说而已。而错过这两件事,就很难想象博尔赫斯最先对文学的参与和创作亲历会从哪个码头上启航,又如何最终到达自己的目的地……1899年必然充满着期待,而这些期待之中的一个,必然是博尔赫斯。
同样,假如博尔赫斯的父亲,豪尔赫·吉列莫·博尔赫斯碰巧没有和那位名叫莱昂诺尔·阿塞韦多的“十九世纪的绝色佳人”相遇相合,那么他所携带的家族眼病基因便不会遗传给博尔赫斯,失明的命运也就会落在一个别的什么人头上。而没有失明,博尔赫斯在被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时,对这一职位而言会显得多么异己(他的几位前任均患失明症),并且又怎么可能赢得他那暗含玄机的盲人的命运(在由这一命运的秉承者所形成的序列里就站立着永恒的荷马和伟大的弥尔顿)?
我反复地说:我失去的仅仅是
事物毫无意义的外表。
这句慰藉的话来自弥尔顿,那么高尚,
……
如果我能看见我的脸,
我就知道,在这个难得的傍晚我是谁
(《盲人》)
如此动人的吟诵,只能出自一位盲人的心上。这真可谓是博尔赫斯那无可争辩的命运的一个绝笔。
1899年这一时间,豪尔赫和莱昂诺尔这两个人物,对于博尔赫斯的命运而言他们是那么富有深意,以致怎样深入理解都不为过。他们都先于他而存在,又都将其影响贯穿于他的整个文学生涯之中,成为他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文学和失明,使他要比常人更快捷地接近以荷马为先驱的盲人的命运和伟业,也足够形成他那关于命运的精妙玄学:在无涯的人间,文学和失明终究要找见那个人,让他成为这一命运的承接者。博尔赫斯曾怀着深入探讨的心情,在《天赋之诗》这首诗中对此表达出自己的感知:
某种事物,肯定不能名之以
命运这个词,安排了这一切
另一个人在另外的迷朦之夜里
也曾领受了这数不清的书籍与黑暗
只是承接这一命运需要诸多因素,其中包括诞生和时间,而博尔赫斯这样表达了他对时间的感受和理解,在他逐渐接近命运主体之时:
时间是构成我的物质。时间是载我消逝的河流,而我就是这河流;时间是毁灭我的老虎,而我就是这老虎;时间是吞噬我的火焰,而我就是这火焰……
(《关于时间的新辩驳》)
是的,他本身便是自己的全部时间,既是这时间的全部主体,也是这时间的所有喻体;这时间不多也不少,刚够用来构筑他全部的个人命运。
布宜诺斯艾利斯:梦的走廊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什么?是“气候宜人的地方”,是船长和水手们的天堂,是世界最南端的城市,是阿根廷的首都。
但最主要的,它还是博尔赫斯的诞生地。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样也是先博尔赫斯而在的,他所不能选择的命运的一种:它是等待他降生的接生婆,是他学步行走的地面,他的书房,他的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公学,他的沉默内向的少年时光,也是临终之际被他遗弃的一块陆地。它就像等待着船只到来的码头那样,早在他之前多少个世纪就已在那儿等待着他。博尔赫斯终于来了。然而他也像船,虽停泊很久,最后还是开走了。由于博尔赫斯之死,它才第一次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他不得不降生于此(因为他无法选择),但绝不死亡于此(自主的决定)。在这里他搁下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东西:诞生、行走、吃住、文学、爱情、屈辱以及迟到的名声……然后他到日内瓦辞世大撒把。布宜诺斯艾利斯因此成为博尔赫斯最绝对意义上的诞生地,他在此获得了真正的永生,没有死亡。
无论博尔赫斯本人是否愿意承认,这一切都足以表明这座城市对他而言意味深长。
但对博尔赫斯来说,这一切更像是弥漫在诞生地上空的轻烟。比这更深远,也更能表现他存在的,则是梦幻,构成他的文学的所有梦幻。准确地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他的梦的走廊,这是作为他的诞生地的深刻含义之一。
正如其他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那样,博尔赫斯把他的第一本诗集——1923年自费印出,仅仅印刷了三百本——献给了这座城市,取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这是他作为诗人献给诞生地的第一份郑重礼物,或者说,是诞生地给他注入的第一股力量。在这一力量的推动下,此后,布宜诺斯艾利斯就宛如星辰一般,在他所有作品中不时洒下自己奇异的光辉。
然而这颗星辰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光辉并不是直接散发在博尔赫斯的作品中,而是完全经过博尔赫斯的心灵折射。换句话说,作为作家的诞生地,它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已然不是它本来所呈现于大众面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博尔赫斯的作品中,只能看到有关这座城市的蛛丝马迹,却见不到它日常现实的模样。
也许正是因为这类原因,在一些中国当代写作者和评论者那里,有一种关于博尔赫斯的写作“不及物”的批评。但也许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及不及“物”,而在于对这一“物”的理解上。这类批评者所言之“物”,通常是指大众眼耳所能见闻、所能感受到的日常现实生活,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应该而且当然是由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所构成,而且他们表示只对这类事物表示信任,并认为只有这类事物才是真实的;而对发生在内心精神世界的诸多现实和事件,则由于它们不能在现实维度里被度量、被眼耳所见闻,而被视为“非物”,因而有意怀疑其真实价值,有意从一种自诩的平民或大众立场的写作中对其进行贬斥和排除。公允地说,采取平民或大众立场的写作本身或许无可非议,但那顶多也只是一种个人写作取向而已。若因此而贬损来自精神世界的“形而上学”,一则显得浅薄,再则也太过矫情,更毋庸说在认识论上这纯粹是一种倒退和“返祖”,因为即使是日日可见可感的日常现实也未必真实可信、值得信赖。博尔赫斯大约是可以解决这一认识的,从他的创作本身看,他无非是在一个层面上不及“此”物,而在另一层面上及“彼”物、及人罢了,他作品中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正是如此。
对博尔赫斯而言,诞生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他创作中的位置,更像是一种诱发因素,有时又体现为素材和题材的意义。它更像是一座可供作家使用和取舍的材料库,那里的街区、陋巷、院落和年代久远的某座建筑,犹如一件件材料——不明自身价值的蒙昧的材料,被作家顺手拈来,然后再赋予它们以某种灵性和价值,使它们重获新生。它有一副梦的脸庞,所体现的不是它的过去和现在的已然性,而是面朝未来的种种或然性。这种或然性通过对它的现实的形而上的抽象来获得,这便是博尔赫斯有别于他的阿根廷同侪们的地方。在这里,读者看不到博尔赫斯对诞生之地的感念、讴歌甚至批判,唯能看见的,是他的形而上学之梦。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为例,他在题为《拂晓》的诗中宣布:
我又一次感到了那出自叔本华
与贝克莱的惊人猜测,
它宣称世界
是一个心灵的活动,
灵魂的大梦一场,
没有根据没有目的也没有容量。
人口众多的繁华之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诗人那里成为灵魂的大梦一场。而当他在其中寻找自己的屋舍时,却发现它也是在白色的天光中惊愕而冰冷,一切均不再是它所显现的那样,而是裸露出冰冷陌生的梦的形态,成为梦魇之邦。在另一首题为《陌生的街》的诗中,这种梦魇表现得更为具体:
每一间房舍都是一架烛台
芸芸众生在烛台上燃烧着孤单的火焰……
1969年,当博尔赫斯的这本诗集再版时,前面增加了一篇作者的序言。诗人比较了自己的今昔之异:“那个时期,我追求的是日落、郊区和不幸;而现在则是早晨、闹市和宁静。”这表明作者不仅以诞生地为梦之走廊,而且从不静卧在某一固定的点上做梦。
值得注意的是,博尔赫斯不仅通过诗歌,同样还以小说形式穷尽他的梦廊。他的《玫瑰色街角的汉子》等短篇,便是他诗歌中“郊区”的延续,其中那些拼刀子、斗殴、打架的汉子们,都十分完整地保留了只有在某种梦中才会有的形态,而作者则竭力要让梦跟真实一样可信,让读者信以为真。很多相同的例子都表明这一点:博尔赫斯用自己的身体去喂养形形色色的梦,然后以梦为基石,建设起一个纯属他个人的家乡。但奇怪的是,那些与他素昧平生、各居世界一隅的他的阅读者们,竟能够毫无障碍地在此安身立命。
这或许就是来自诞生地的启示:一个作家,只有当他以一种个人方式超越了故土,当他在写作中放弃了感恩、赞颂这些情感,他才有可能成为那个不同于众的自己。某种意义上,博尔赫斯不是降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是降生在形而上学的冥思和梦想之中。这也许是出于天性,也许是因为阅历。形而上之梦才是他真正的诞生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只有一个做梦的博尔赫斯,而很少有一个生活过的博尔赫斯。梦即他的生活。
读书意味着什么?
博尔赫斯的传记作者、美国人詹姆斯·伍德尔在《博尔赫斯:书镜中人》一书的结尾部分写道:
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用于阅读、做白日梦、写作——任何作家希望
做到的也许正是这一点……
阅读和感受阅读是博尔赫斯的第一技能和主要天赋,他长于幻想的个性以及文学修养均由此得来。他个人也曾坦言读书是他生活的主要经历,比爱情更重要:“我总是先读书,然后才接触物质世界。”在使博尔赫斯最终成为他自己的那些要素中,事先等待被他翻开和事后仍纷纷找到他的那些书籍,那其中或梦或醒的各色灵魂,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仿佛都是构成博尔赫斯其人的专门成分,都要迫不及待地回到他那里,以便为二十世纪的人类文学塑造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人始于一场艳遇一场姻缘,读书则成为仅次于诞生的第一要素。
读书使博尔赫斯成为形而上学的、富于幻想的,继而又将这二者工具化、材料化的作家。
他作品中这样的例子已遍及字里行间,毋须再举。他的创作中鲜有以描写众生可见的社会日常现实为动机的作品,则可以反证这一点。幻想和形而上学本可使博尔赫斯在这一类型的作家行列里名列前茅;而同时又将这两个方面从根本上化为素材,使之兼为形式依据加以运用,这一突破则使他成为这方面的大师。他由此充实了文学大师的这一含义:可以也敢于将苦苦求索的东西对象化,并在敬畏之中取消其严肃性、神圣性。这在博尔赫斯的创作中表现为一种为他所独有的实验精神,一种先见之明和勇气。在被他所阅读的书籍作者中,下列几位应该被我们牢牢记住:切斯特顿、斯蒂文森、吉卜林、德·昆西、贝克莱、休谟、叔本华、惠特曼。也许还包括中国老庄。而叔本华的那些对世界的并非宿命论的解释,不妨视世界为一种卓越的精神创造的假定,则给他的读书经历以令人倾羡的高度。这个高度不在关于世界的阐述中显示其价值,而在博尔赫斯的创造中尽现其功。
阅读对一个作家的成长而言,其影响神秘而复杂。就博尔赫斯而言亦如此。但他还是通过其作品留下了一些可见之物。从他创作的素材运用来看,便可发现那些材料的来源穿越了日常现实和形而上学、历史真实与虚构、过去与未来、梦与非梦等对立的范畴。作者在这些空间自由穿梭,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无对立的、平等的广泛联系,一视同仁地对待它们。因此,他也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他同代乃至后代在某一层面上苦心经营的作家。他那大量的、大范围的阅读所修成的正果之一,便是他成为“作家们的作家”;通过阅读,他对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不同遗产进行了个人的探究和假想,使之成为他创作的着眼点和入手处,他最终还使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获得了公认的“世界性”。这或许也可解释为他通过博览群书而赢得了众多的精神祖国,成为少有的、在精神上没有唯一祖国的作家。对博尔赫斯来说,从其人到其作品,读书不仅也是生活之一种,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高于生活的生活。
祖国:文学的历险之地
在一个人不能不接受,并且注定要深受其影响的各种要素中,祖国便是其中一个。祖国轻而易举地选择了形形色色的人们,但一个人却不能轻易地选择祖国。祖国之于个人基本上是别无选择的,是一个人必须无条件接受的现实之一种。博尔赫斯生逢其时的阿根廷似乎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作好了各种准备,为博尔赫斯而作好了准备。
作者前期对考虑机床电能的柔性作业车间调度开展了优化分析[11],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刀具、切削液等辅助资源能耗分摊到车间作业过程中,并考虑工件流转过程产生的搬运能耗,研究面向广义能耗的柔性作业车间调度优化模型。首先引入车间广义能耗的概念,对柔性作业车间调度直接电能和间接能耗进行分析,然后建立了以广义能耗和完工时间为优化目标的柔性作业车间调度优化模型,并基于多目标模拟退火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得到最优调度方案。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以至于也可以说那简直不成其为“准备”。但实际上却比任何准备更充分、更彻底,对博尔赫斯而言,再没有比这些准备更适宜的了,因为只有阿根廷才给了他如此特别的生态。首先,博尔赫斯始终认为自己在文化方面接受英国和东方的影响要比其他国度——例如美洲各国——的更多。他探讨过阿根廷的作家与传统,并且在一定意义上他本人也表现为是这一传统的承接者。但那只是他的文学中为数不多的一部分,远不是全部。我们说博尔赫斯在文学—文化精神上没有唯一的祖国,其意义也正在于此。他成为他自己完全凭借一种多元的力量,是一种综合的结果,而阿根廷并不可能单方面为他提供这一切条件,任何一个文化—文学意义上的国度都不可能提供。然而从反论中也许恰恰可以得出这一结论:正因为阿根廷—博尔赫斯的祖国—之于他的这一现实状况,所以才为他的国际化创造(准备)了更为充分的条件。既然祖国在文化—文学方面给他的是一种如此特别的境遇、一些后来可称其为机会的种种可能性,那么在别的方面可能更为充分。
这便是第二点: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立图书馆馆员、写作者、市场鸡兔检查员、非官方性质的文学讲演者、现政权不可调和的批评者、著名作家、国立图书馆馆长……这些都是博尔赫斯的祖国所为他准备和安排的,或者说是祖国之于他的具体表征。但此中另有深意。博尔赫斯作为一位成功的作家——这是他最重要的身份——则更多地具有墙内开花墙外红的况味,因为他并非是在自己的祖国,而是在国外率先获得了声誉。这使他在祖国的命运富有戏剧性,颇具传奇色彩,但更令人感到此中潜伏着某种危险。勘探博尔赫斯的这一命运,从底部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因果政治,而不是文化或文学。这令人难堪,更令人不悦。他在祖国的生存,很多时候来自政治的影响显然要比来自文学的更加突出,虽然事实上也完全可以认为这是由文学这一根源所引起的。若非文学,谁又能保证博尔赫斯不会是现政权积极的合作者呢?这类例子在他同时代的同行们那里并不鲜见。
1946年,胡安·庇隆执政,市立图书馆前程看好的助理博尔赫斯由于在反对庇隆的宣言上签字,被降职为市场鸡兔检查员。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那些无知的鸡兔们有福了,如果它们有知,恐怕会成为全世界最自豪、最骄傲的家禽了,因为它们将要接受一位世界级文豪的检查,若不是此人一怒之下辞去了贵干的话。詹姆斯·伍德尔在《博尔赫斯:书镜中人》一书的序言中对此作了这样评价:
博尔赫斯作品的法译本正在流传之时,庇隆则正在给他的国家造成
很大的损害——说得精确些,从1946年到1955年——损害的影响持续
到博尔赫斯去世。阿根廷成了庸俗透顶的地方。
作为阿根廷文学、文化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博尔赫斯到死同他国家的历届政府不和(尽管他公开宣布的保守主义思想使他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穷凶极恶的阿根廷政权有同流合污之嫌,而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的阿根廷,是一个充满压迫、拷打与失踪者的尸体的年代;尽管八十年代初他曾郑重宣布了自己的反政府声明,而他的政敌宁肯对这一切避而不谈)。1955年,当他开始失明,并被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时,他曾在《我的生活》(或译《自传性随笔》)中表示自己十分激动,但那并不表达实际上的和解,否则,他便不会在1984年的一个访谈中如此表达自己的感受:
我来自一个令人悲伤的国度。
在此之前,在他被革职为市场鸡兔检查员之时,他也曾如此描述自己的处境:“在阿根廷不能以梦幻的词语思维,而只能以噩梦的词语思维。”这便是博尔赫斯和他的祖国。这个祖国由不同的历史时期赋予了它不同的内涵,但对博尔赫斯而言则成为大同小异的事实——他一直未能完全予以接受的事实。当他感到来日无多,在生命的最后时日,他选择去遥远的日内瓦谢世。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他对在那里度过的美好时光的最后追寻,同时还可以理解为这是关于“悲伤”的注释和对噩梦的最后逃离。
如此,在博尔赫斯那里,祖国的含义便显示出其特殊性。从两者关系的最终结果来判断,伤害会是双重的:不仅是博尔赫斯,也许还包括他的祖国。祖国之于博尔赫斯,重要的是它最终成为他的文学历险之地,一种他必须经由的现实。然而若非如此,他又从何赢得他那特殊的个人命运?正如王子不经历九十九种险遇便不能得到公主的爱情那样。关于这一点,如果在更为内在的方面加以考察,作为一位国际文化名人的祖国,阿根廷也许不必对此感到难以释怀,因为在一个题为《文学只不过是游戏》的谈话中,博尔赫斯如是陈述了他关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见解:
我是怀着下述信念长大成人的:这就是个人为贵而社稷次之。我不能欣赏那种认为国家比个人更重要的理论。
这种见解不仅已昭示出博尔赫斯与他的祖国阿根廷之间的基本关系,而且也远远超越了这一关系。他所言说的显然是无时空界限的概念,陈述的是对人这一主体的最大尊重以及对自由与独立意志的渴望,并非仅仅针对阿根廷而言。他的这一见解并非是随意发表的即兴之说,而是确有其思想的一致性。在一本由艾斯特万·佩科维奇所编、1980年出版于马德里活字出版社的名为《博尔赫斯言谈录》的书中,同样也收有他这样的言论:“我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我也不积极从政。也许我是个平静的、默默无闻的无政府主义者。我在家里梦想政府的消失。我不信国界和国家这个危险的神话。我知道,财富的分配令人烦恼的差异是存在的,我希望这种差异能够消失。但愿有朝一日会出现一个没有国界、没有不公正的世界。”这既是他对个人与国家关系见解的补充,也是对“社稷次之”这一看法的原因的揭示和阐释。
然而富有意味的是,在1999年博尔赫斯百年诞辰之际,阿根廷将此年宣布为“博尔赫斯年”,总统还下令铸造了一套带博尔赫斯头像的金、银、铜币,其中铜币达一百万枚。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已特辟有用博尔赫斯名字命名的大街,阿根廷国立图书馆也在十分显要的位置特辟了“博尔赫斯厅”……这一切或许是在历时半个世纪之后,阿根廷对五十多年前“庸俗透顶”的彻底纠正,是博尔赫斯辞世十多年后在祖国赢得的新的、他本人始所未必能够料及的命运,是被他所充分体悟的充满遗忘与重复的历史中新出现的一页,甚至是令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可能会对自己关于个人与国家关系宏论产生怀疑的事实。但也许这更源于他自身的光辉。
“被读”形成的博尔赫斯
任何作家及其所创造的文本,其可能的各种意义、价值和功能,都是在被他者阅读后才得以形成或实现的,这便是被读,它是一种使作家及其文本产生开放性、多重性、多义性甚至歧义性的阅读过程。使博尔赫斯成为他自己的最基本、最必不可少然而又由于它最普通因此最易被人们所忽视的显著因素,那便是他的被读。一方面几乎所有写作中都深嵌着对被读的深沉期待;另一方面,只有被读才能真正证明文本与写作者。换言之,只有被读才是形成一个写作者的第一明证,严格地说,甚至连“博尔赫斯怎样成为他自己”这句话本身也是被读出来的。这种被读的功用对博尔赫斯而言也毫不例外。这也正如吉卜林、切斯特顿等作家经过他的“被读”后更显其重要性那样。从未“被读”的作家事实上就如同从未出现过一样。因此,在各种各样的命运和际遇中,“被读”是极其重要的一种,等待着或好或坏的作家。这也包括博尔赫斯。
和博尔赫斯隔着千年时光的荷马,经过他的“被读”,便在他所在之处再度复活了,并发出耀眼的光辉,像照亮了其他人一样将他照亮。现在他也在自己的后读者那里存活下来,继续着他往日隐约可见的生活,直到他所谓的终极遗忘发生。如果没有被读,他也便从未存在。而关于这一点,他的读者、研究者和传记作者们几乎视而不见,人们差不多忘记了正是由于被自己阅读,一个叫做博尔赫斯的人才渐渐形成,然后卓然于世。他在吐谷曼大街上的历史(或时间)重影,已经暗示着他将被读的命运,或者说已成为他被读的隐喻。1899年,他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吐谷曼大街的一所住宅里,这所住宅当时的门牌编号为840号。1930年以后,由于城市改建吐谷曼大街840号已不在原处。但当来自四面八方的景仰者纷纷前往吐谷曼大街840号缅怀博尔赫斯诞生之所的往昔时,他们实际上只是遇见了一个和他诞生之所相同的编号而已(真正的840号实际上处在现在的830号位置上),在这里已经很难捕捉到这位大师呱呱坠地的任何气息了,那所他诞生其间的又矮又小、毫无气魄的住宅已不复存在。如今在他的诞生地上出现的是一家珠宝钟表店……
吐谷曼大街事实上已经不是一条,而是两条、三条……甚至更多条不同的吐谷曼大街了。它已布满了历史——时间的重影。时间是这里无处不在的读者。吐谷曼大街840号经过它的阅读,已不断增值。从前的840号如今躲在安静的珠宝和滴答作响的钟表(均和时间有关)后面隐居着,并不显现自身;如今的840号只不过是它的名不副实的影子和替身。这些重影只有在时间——被博尔赫斯所反驳、所取缔、所重组的时间——的眼里,才能被显示出来,但对人间读者而言则是难以企及、恍若隔世的梦。
吐谷曼大街由于在时间那里“被读”,至今仍经久不衰,直至最终的消亡到来。这种情形远远地早于博尔赫斯而存在,现在则是博尔赫斯本人。一切将要“被读”的事物其命运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是一条街道,还是一个人。博尔赫斯究竟从何时开始被读,被何人所读,在被读中每个读者到底调动了怎样的天性、阅历及怎样的知识储备,这大概是个难以确定又因人而异的问题,但从他所获得的被读结果来看,至少令他个人颇为满意。这完全和他早期对自己认为比较上乘的读者群的选择密切相关。从他自印第一本诗集开始,他就意识到这一点。他的《永恒的历史》一书在出版当年虽仅仅卖出三十七本,但在这一意识的参与下,他对一本一次能售出两千本的书的被读效果公开表示质疑。优质上乘的读者总是少数,他对这“少数”的渴望要比对两千名群众读者的强烈得多,因为在他看来,这“少数”人具有比多数群众大得多的复活与唤醒能力。他们可以让真正优秀的作家活力无限、永葆青春。在这少数人中,不少人本身即为作家,博尔赫斯本人也正是由此而成为“作家们的作家”,而这一被读结果所带来的影响,在他身后益显得深广。
观察博尔赫斯被读的历史,可以看出关于他是“作家们的作家”的这一称誉实际上也包含一些多重因素,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一样。在博尔赫斯的被读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引导性的环节——即作家本人对他人阅读的一种预设性引导,这首先来自他对自我及其创作的“自读”。他一边强调了自己对文学的专注、领悟和深入,并逐渐确定了自己的文学尺度,例如在对主题与方法的新发现、对材料的运用等方面;一边又从自身生存的境遇中,抽取可以用来注释其创作的观念、态度和事件等,用以加强自己作品的被读效果,以期得到自己所希望的某种确认。他的传记作者和研究者之一埃·罗·莫内加尔便是接受他这种引导的读者之一。在莫内加尔的博尔赫斯传中,其人其作品放射着神秘、玄奥、优美的光辉,投射出作者对他完全的、几乎无保留的敬重、赞赏与肯定,在这种肯定中诞生了一个被神圣化了的至高无上的博尔赫斯。然而在博尔赫斯的另一个传记作者和资深研究者詹姆斯·伍德尔那里,博尔赫斯则被描述成一个具有鲜明的优点与同样鲜明的缺陷的人。伍德尔显然属于那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博尔赫斯读者,他在很大程度上并未接受博尔赫斯预设的引导,虽然他对博尔赫斯的文学创作给予了适度评价,但为了接近另一个博尔赫斯,却竭力去探究博尔赫斯私人生活中鲜为人知的某些方面,以期达到对博尔赫斯的生活与文学的另类解说。
但无论是莫内加尔,还是伍德尔,他们更像是博尔赫斯在被读中的两个极端的例子。而在各国那些关注风格与流派的评论家那里,有人或以他曾编辑幻想文学丛书为由,或以其作品的风格特点为依据,视博尔赫斯为“幻想文学”大师;而注重文学流派研究的评论家,则根据拉美文坛的状况及他在拉美文坛的地位,视他为“魔幻现实主义之父”。虽然博尔赫斯本人曾多次表明:自己并不真的是什么“幻想文学”作家,也与魔幻现实主义无关。他认为自己和某一现实的文学流派并没有什么直接瓜葛,而且事实上他既不相信什么流派、也反对“文学流派”这一提法。尽管如此,他仍还是无法左右这类被读,时至今日,关于他是“幻想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或“魔幻现实主义之父”的说法仍不绝于世。
由此可见,博尔赫斯在被读中获得的是一种货真价实的多重性和多义性,或者说,“被读”形成了一个多重、多义的博尔赫斯。这正如他本人曾在批评了惠特曼的某些传记作者之后,发现了不止一个惠特曼一样。如今他在被读中也已成为无数个博尔赫斯。他的命运也即惠特曼在他本人那儿所获得的命运,世界上不再可能传诵一个仅仅是“诗意的”或“优雅而神秘的”博尔赫斯,此外还将有一些“世俗的”、“烦恼而通俗的”博尔赫斯。他甚至也面临着被消解于绝对理性的深奥的可能性之中的惊险:他在被读中几乎是神,同时又兼而为人。总之,他已形成于被读的神秘与无限定之中、也即人性之中。他所获得的这种开放性、多重性、多义性甚至歧义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的生命力之所在,这种生命力来自他个人生活与写作中那些突出、鲜明的部分,或许还有经他个人强调了的某些方面。被读是如此浅近,又如此深远,博尔赫斯的全部都将被移进这种多重观察之中,使他不再是一个单面人。在此间,他既有创造、收获,又有等待、丧失;既非凡又普通;一边诞生、一边衰亡,继而再生,如此循环往复。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他在《循环的夜》一诗中充满疑虑与感伤的吟诵:
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在下一个循环中归来,
就像循环小数那样重新反复;
但我知道一个毕达哥拉斯式的黑暗轮回,
一夜一夜地把我留在世界的一个什么地方。
通过被读,那个1899年诞生、1986年谢世的人,已是另外一个渐行渐远的人,就如同他在与科塔萨尔的谈话中所描述的情形一样:“不是我,而是另一个叫博尔赫斯的人……”
但他同时又确如循环小数那样,穿过晦黯的毕达哥拉斯式的轮回,进入了新一轮的存在之中。在这一存在的深处,《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神曲》、《浮士德》以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那些神情已经平静的作者们早已纷纷落座。尽管那里已经落满了时间的积尘,但却是为世代作家们所渴望的难以企及的命运。博尔赫斯曾胆怯地谈论它,如今他自己也来到了这一存在的门前。他用那双失明的眼睛朝里面一遍遍张望,脸上带有真实和梦幻的多重表情。事实上这是一个由被读造成的、不断撩拨着人的探求欲望的奇迹,博尔赫斯本人早已从他的血缘、他的祖国、他的雄心、他的政见、他的爱以及与他相关的众多事物中脱身而出。他已不在这些事物之中。他已到达比这一切更宽泛、更辽阔的事物中间。除了他所为之而感到无数疼痛、无法释怀,最终了然彻悟的遗忘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可以与之对抗。
一个人如果能够管理和运用好自身的这三种能力:阅读(了解他人),幻想(内心神奇),创造(无中生有),那么他至少可能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和名声,还有可能给世人留下一笔可资享用的遗产,尤其是一个作家。但这还需要天赋。这也就是博尔赫斯——那位作家们的作家——留给我们这些俗人的一部分遗产,它使我们在尽情享用之时血液沸腾,像寂静的雪片在血管里纷纷落下。也许博尔赫斯深谙此道,因而他曾如此开导那些打算创作巨著的人:
中世纪给我们留下了哥特式的建筑,也给我们留下了仙女的故事和对什么问题都争论不休的经院哲学。中世纪特别给我们留下了《神曲》。这本书我们继续阅读,继续赞叹不已。这本书的生命比我们长,而且长得多。它通过一代代的读者,变得更丰富。
在此,他通过谈论《神曲》,已经把自己的渴望、把自己被读的可能命运以及怎样最终成为自己的预想等相关要素,全都坦陈给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