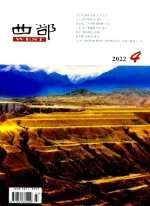公平:暴力革命与暴力美学——《让子弹飞》叙事逻辑的悖谬
焦勇勤
耀眼的阳光下,骏马奔驰而过,流动的树林,快速滑行的火车,简练娴熟的蒙太奇,以及铿锵有力的音乐,共同组成一幅灿烂明亮、流畅如诗的影像。姜文用极具浪漫主义风格的片头,开启了一个极具英雄主义色彩的叙事。
《让子弹飞》讲述了一个公平的故事,曾经是革命者的张牧之,在经历革命失败后上山为寇,变身为土匪张麻子。张麻子一次意外劫持了一个卖官上任的县长马邦德,在“上任就有钱”的突转之下,张麻子为挣钱冒充县长上任鹅城,逃亡未成的马邦德化身师爷为其将官场潜规则一一道来,在跪着挣钱还是站着挣钱的选择中,张麻子选择了站着挣钱,于是与鹅城恶霸黄四郎产生直接冲突。在经过痛打武举人、鸿门宴、劫持替身、麻匪火并、出城剿匪、智杀替身等一系列斗智斗勇的对抗后,假土匪、真恶霸终于被铲除,影片的主题——公平似乎由此而被建立。就这样,一个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实现公平的经典英雄故事,在幽默、滑稽、轻松的全新语境下被重述,并以6.7亿元的票房开创了中国电影的新时代。
《让子弹飞》的确是一部好看的商业大片,同时,它也具有饱满的艺术性。这种艺术性不仅体现在其浪漫主义的风格上,还体现在它内蕴丰富的主题上。
影片主题涉及的方面很多,革命与启蒙,暴力与公平,英雄与狂欢,这些主题不仅与我们当下的现实关联,而且也与中国近现代史对接,形成一个意义关联、环形回绕的互文本。
应该说,这是中国当代影视界难得的一部思想性较强的影片。但同时由于导演对公平概念的误读,导致影片的叙事逻辑存在着巨大的悖谬。
一、从革命出发的暴力
片名《让子弹飞》似乎预示了它的暴力内涵,而影片最后“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的口号,显示其将暴力推至极端的努力。
对姜文来说,现实就是不公平,就是暴力。在一个只有暴力、没有公平可言的世界,面对暴力,面对不公平,姜文选择的是以暴制暴式的革命。土匪英雄张麻子射出了一串子弹,射向恶霸黄四郎,最终得以实现的形式是子弹、枪炮、炸药和抢劫。因此,暴力成为该片的叙事起点。
暴力是一种权力。对此,罗素在其《权力论》中区分了三种权力:传统的、革命的和强暴的权力,并把“不以传统或同意为基础的权力称为暴力”。费孝通也意识到这种权力的存在,他指出社会中存在着四种权力: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权力和时势权力,其中,横暴权力就是暴力权力。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权力也似乎一直与暴力相伴而生,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中就主张通过暴力维持权力的权威性。
既然暴力是一种权力,它就具有权力的属性,即:它要么合法,要么不合法。合法的暴力权力可以转化为权威,从而得以持续,比如国家机器就是用合法的暴力来维持自己统治的。不合法的权力不能产生权威,因此不可持续,它只会激起更强烈的反抗,比如法西斯主义。
权力的合法不合法实际上来源于人们对这种权力的认同,而并非都来自于暴力,很多时候即便人们不采用暴力,同样也可以产生某种权力。比如,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并未使用暴力,但同样拥有某种权力,这种权力就是对皇权专制权力的制约。《论语·宪问》中提到:“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由此可以看出,儒家知识分子因其站在百姓一边,从而拥有某种权力,这种权力是通过掌握知识话语来实现对国君/皇帝/君主权力的制约,而与暴力无关。
但是,在《让子弹飞》中,姜文选择的是以暴力权力来实现其权威,并认其为合法,因为他认为张麻子的暴力权力来源于革命,而革命权力只要与大众利益联系起来,似乎就具有了合法性。对此,索雷尔在其《论暴力》中指出:“作为阶级斗争的一种纯粹和简单的表达的无产阶级暴力,也必然是美好和高尚的事物;它是为文明的永恒利益服务的;或许,它不是获取暂时物质利益的最佳手段,但是,它能把世界从野蛮主义里拯救出来。”因此,作为革命的权力和革命的暴力似乎就达成了某种同盟,革命与暴力成为一个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正如1960年4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所指出的:所谓革命,就意味着被压迫阶级使用革命的暴力。
影片中,按照张麻子自己的叙述,他是蔡锷的手枪队长,而蔡锷是辛亥革命的主力,因此,张麻子在影片中显然是以革命者的身份出现的,而当他面对恶霸黄四郎对百姓的肆意欺凌和横征暴敛时,他选择站在弱势群体一方,选择以暴力的形式来对抗,当他最终选择要铲除恶霸的时候,他选择的仍然是革命的方式,因此,他的暴力权力实际上是革命权力的一种转换。
但是,革命的权力就一定是合法的吗?
二、指向公平的革命
革命既是一种权力,又是一种权利。当人们面对专制、独裁、暴政的时候,人们当然有权利进行革命。但当它一旦实施,不管是从精神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实际上它已经演变为一场运动和一个过程。
正如傅勒在《思考法国大革命》中所言:“人们所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那个被收进档案、打上日期并美化为一道曙光的事件,不过是先前社会政治演变的加剧罢了。这个事件摧毁的并不是贵族,而是社会上的贵族原则,从而取消了社会对抗中央国家的合法性。”按照这种说法,革命并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而不过是一场运动或一个过程的一环罢了,是对现有霸权的反抗、对立与争夺,无论它使用暴力还是非暴力,这场运动或过程的基本内涵是颠覆现有秩序,重建新的秩序。如果它不以新秩序为目的,这样的革命就只能是一个政治事件,一个未完成的革命,有时甚至不能称其为革命。
阿伦特说:“对革命现象的描述,暴力不如变迁来的充分,只有发生了新开端意义上的变迁,并且暴力被用来构建一种全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缔造一个全新的政治体,从压迫中解放以构建自由为起码目标,那才称得上是革命。”(《论革命》)金观涛在分析“革”与“命”的汉字本意也认同这种观点,他说:“革与命两个字的联用,表达某种秩序或天命的周期性变化,其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接近西方revolution的原意,即天体周期性运动或事物周而复始变更。”(见《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因此,革命作为一场运动或一个过程,必然与重建或新建某种秩序联系在一起,而秩序的背后则一定有某种理性精神作为支撑。
理性包含两个层面:知的理性与行的理性,即康德所谓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理性表现在认识领域就是对人、自然与社会的认知,表现在实践层面则是对秩序的确认,即对权力分配关系的肯定。理性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基础。
理性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古典理性、现代理性与后现代理性。古典理性知的层面就是对天地人关系的一种认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权力来源、分配的认定。
对中国来说,从五行说到天人合一说,关于天地人三位一体关系的知识在殷周时代基本定型,这种定位也为权力的确定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王国维在其《殷周制度论》中指出:殷周时代最重要的变化体现在立子立嫡之制、庙数之制和同姓不婚之制三种基本制度的确立。这一系列制度的背后就是权力定于一尊和有序传承的大一统式皇权型专制理性,这种理性经由孔子、孟子、董仲舒、韩愈、朱熹等人的叙述,成为古代中国的基本意识形态。
对西方来说,从毕达哥拉斯学派“万物都是数”到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以神秘主义数学、几何学和天文学为基础的古代科学原则被确立,这种认识论经由柏拉图的神创宇宙论和亚里斯多德对“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的实证主义研究,发展成为政治权威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城邦式贵族专制理性,然后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和罗马帝国的兴盛,发展成为大一统式君主专制理性。
其后,基督教兴起,上帝创造万物成为人们对世界的基本认识,上帝的唯一性被贯穿到世俗社会,教会的权力因此被确立,教皇的专制统治取代君主的专制统治。尽管神学理性取代古希腊的世俗理性,但从整体层面来看,神学理性不过是古典理性的一种变形罢了。
现代理性是对古典理性的颠覆和反动,它源自于文艺复兴时期对人和科学的热爱,经由对经验世界和自然科学的肯定,从而确立了现代科学的基本原则,并因此扩展到对社会系统关系的重新解释,从而彻底改变了对原有权力来源、分配的界定。从马基雅维利对君权的鼓吹和霍布斯对国家权力的实证分析,到卢梭《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等一系列启蒙思想的传播,私有产权、主权在民、社会契约、民主、平等、自由、法制等一系列公民权利得到普遍认同,原有的权力结构被改变,新的社会秩序被建立,并因此而形成了西方现代制度保证和法律保障等一整套权力运作与制约机制,现代理性因而被确立。
现代理性自然有其不足之处,比如个人主义、唯科学主义、唯理性主义、国族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父权制、强权政治等缺陷,由此产生了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等对非理性主义的探索与崇拜和对现代理性的反动。但藉由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和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等,发展出当代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利奥塔多元叙事模式理性、福柯“在实践的考古学和谱系学中质询的哲学态度”理性,以及大卫·格里芬生态理性等为主要方向的一系列后现代理性。
后现代理性显然更加承认不同群体、不同种族、不同表达方式、不同种类等的权力,是一种更加承认多元权力、多元价值的理性。可以说,现代理性确立的基本思想和原则并没有被改变,只是得到了继承、发展和超越。
在《让子弹飞》中,姜文把革命指向公平,因此,公平成为其反对既有秩序、构建未来秩序的指针。影片中既有的秩序来源于两个方面:
首先是黄四郎所代表的秩序,按照影片叙事,黄四郎是以恶霸身份出现的,他是鹅城几大家族之一,属于豪绅或士绅阶层。对此阶层,费孝通在《中国士绅》中曾加以研究,指出其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到过承上启下维护稳定的功能,“在中国传统权力体系中存在两个层次:上层有中央政府,下层有以士绅阶层作为管事的自治团体……保持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联系的重要性,意味着士绅需要在当地组织中拥有决策和管事的地位”。而在电影中,姜文提供给我们一个不同于费孝通的另一种叙事,即黄四郎僭越了中央政权,自己用暴力来实现专制统治,为鹅城赋予了一个不公平的恐怖秩序。
然后是张麻子所代表的秩序,张麻子尽管是以冒牌县长的身份出场的,但他的权力至少对老百姓来说仍然属于中央政权的代表,属于古典理性的一种。而当他面对豪绅权力威胁的时候,他通过选择暴力革命来推翻黄四郎的恐怖统治,是要重新给予鹅城秩序,这个秩序就是公平。
那么姜文所说的公平究竟属于那个层面的理性呢?
三、回归暴力的公平
《让子弹飞》中有关公平的叙事有两个段落:卖凉粉的在躲避冤鼓的过程中,不小心撞到了武举人,武举人对卖凉粉的施加残酷的暴力;六子吃了一碗粉,而卖凉粉的说他吃了两碗粉,六子为证明清白只得剖腹自杀。两个冲突,两个不公平,不公平在影片中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公平,《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从此中国人的心里种下了公平两个字,但是公平究竟是什么,似乎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
公平,按照罗尔斯的理解就是正义。正义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道德层面的和政治层面的。道德层面的正义或公平,指的是某种行为符合当时人们的共识,比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规定的“正义就在于人人都做自己的工作而不要作一个多管闲事的人:当商人、辅助者和为国者各做自己的工作而不干涉别的阶级的工作时,整个城邦就是正义的。”这种公平实质上是专制制度下的“财产权,而与平等毫无关系。”
政治层面的公平或正义则“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是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罗尔斯:《正义论》)它涉及的是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合理分配。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家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公民权利制约、对抗政府权力的主张,即对政府权力的控制与分权,并因此而发展出了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为此,罗尔斯还提出了正义原则的两个标准:“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从这两个原则出发,政治公平或正义实际上指的是一种公民权利意识和政治分权主张,具体来说,它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1、政治行政系统:合法权力的分配(和结构力量);2、经济系统:经济权力的分配(和结构力量);3、社会文化系统:私人可获得的、可任意支配的报酬与权力的分配。(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
在此基础上,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将不公平界定为对人的某种权利的“剥夺”,既包括对政治权利的剥夺,又包括对经济权利的剥夺,为此,他引入社会选择理论来解决不公平。尽管他也意识到“自由悖论”原理,即在坚持帕累托效率的同时(假定无限制域),满足自由的最低限度要求是不可能的,但他提出应该运用信息扩展原则来加以统计,即“对那些构成社会中穷困群体的个人的各自剥夺的资料有必要归总,从而为总贫困做出信息丰富而有用的测度”,并因此而做出社会应有的选择。
由此看来,现代意义上的公平实质上是一种政治结构的公平,是建立在公民权利的确认和对政府权力的控制与分权基础上对政治权力的合理分配。它绝不是简单地通过权力转换或通过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来实现的,更不是非理性的权力狂欢,它必须通过较为完善的社会制度和合理有效的法律制度来加以保障。
在《让子弹飞》中,不公平显然表现为卖凉粉的与武举人的冲突和六子与卖凉粉的冲突方面。影片首先刻意突出了武举人对卖凉粉的暴行,以及卖凉粉的谎言效果,并通过痛打武举人,还卖凉粉的以公平,从而喊出了“公平”这个影片的关键词。其后,在六子与卖凉粉的冲突中,导演将不公平冲突演绎到极致,一碗还是两碗粉的矛盾,看似是谁在说谎的问题,而实际上是说话者背后由谁来掌握话语霸权的问题,体现的是政治权力的无所限制问题,是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双重缺失的问题。公民权利缺失的根源是专制制度的存在,政府权力缺失的根源则可以归结为豪绅权力凌驾于政府权力之上,从而形成了豪绅(黄四郎)权力的单一话语模式与单一叙事结构。因此,透过影片我们可以看出,即便政府从豪绅手里把权力夺过来,如果不能保证公民权利并对政府权力进行控制和分权,那不过是一种古典理性的重建,是一个专制政权的复辟罢了。
显然,影片中的革命既不是复辟,又不是构建现代理性或后现代理性。它实际上是一种非理性革命,即它只是颠覆而不重建,因此,它只能是从一种暴力权力向另一种暴力权力的过渡。
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在影片土匪对恶霸的斗争叙事中清楚地看出。最初这场斗争似乎都是按着革命的理性过程向前发展的,从火并到智取,从单打独斗到发动群众,这些似乎都显示着革命权力运用的理性一面。但随着杀死恶霸替身这一关键情节的逆转,革命从公平转向不公平,革命权力的合法性被颠覆,革命目的的合理性也被颠覆。恶霸替身尽管有恶霸的外在特征,但实际上也仍然是一个受害者,代表着老百姓的另一面,是革命权力合法性的规定者,也是革命目的的检验者。如果他的被杀不是出于自愿,那就只能是被滥杀,是革命的反面。
影片中随着张麻子对恶霸替身的有意屠杀,替身成为革命权力的牺牲品,革命也因此成为暴力的牺牲品,这种通过牺牲革命权力合法性的形式来实现革命成功的革命过程,使得暴力权力替代革命权力,革命权力又回归到暴力权力,暴力成为其自身,并被美化,成为暴力美学的化身。这种暴力权力的滥用,尽管表面上与恶霸权力的滥用不一样,但性质却是相同的。因此,这就造成一种悖谬,革命与暴力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如果没有理性的限制,则必然会走向其反面,这种革命不再是革命,而只是暴力权力的独语。阿伦特在《论革命》中指出:“革命展现出它的全貌,具备了一种确定形态,革命开始摄人心魄,与滥用权力、暴行和剥夺自由这一切促使人们造反的东西划清了界限”。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让子弹飞》中的革命没有将自己与造反划清界限。
正因如此,影片开端革命者对公众进行革命启蒙的公平秩序,最终演变成另一个不公平秩序的开端,这种悲剧我们显然并不陌生。“中国当代革命观念的核心是斗争哲学和革命人生观,它以取消一切差别为终极关怀。事实上,正是斗争哲学泛滥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暴露了中国式革命新道德和做无产阶级“圣人”的不可欲,才导致中国当代革命乌托邦观念的解体。”(金观涛:《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福柯曾经指出的“研究权力的策略、网络、机制和所有这些决策赖以实施并迫使其得到实施的手段”就显得尤为必要了。从这点上来说,影片虽然是一个艺术作品,但其中也有其自身的叙事逻辑,也因此体现了某种权力机制建构的无意识。《让子弹飞》中姜文从公平出发,最终却建构了一个与其所反对的暴力权力结构相同的暴力权力结构。
《让子弹飞》实质上是一个二元论的暴力权力结构叙事,正如姜文自己在影片中说的,就是土匪碰见了恶霸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显然他说出了实话。《让子弹飞》尽管打着启蒙和革命的旗帜,但最终却沦落为以暴制暴的非理性对抗,尽管有对抗,但不客气地说这种对抗与公平无关。
综上所述,《让子弹飞》尽管涉及到诸多具有现实和历史意义的重大主题,但因其所宣扬的非理性暴力美学本质,最终使影片演变成为一个二元暴力权力论的叙事,一个貌似合法合理实则既不合法又不合理的叙事,一个无关公平又混淆革命的叙事,一个巴赫金所谓的狂欢化暴力美学叙事,一个打着启蒙运动的幌子进行的反现代主义叙事。这种叙事曾经作为我们现代化进程的主旋律,曾经在文革叙事中发展到极致,也曾经一度淡出我们的视野,而今它又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