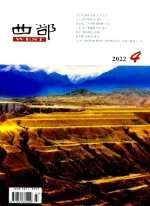西域文化的诗性智慧及其现代意义
张春梅
我们知道,维柯有关“诗性智慧”的论述是站在史学与哲学联系基础上的,更注重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他在《新科学》中指出,原始人的诗性智慧最能与诗性联通,想象力最为发达,“原始人在他们的粗鲁无知中却只凭一种完全肉体方面的想象力,而且因为这种想象力完全是肉体方面的,他们就以惊人的崇高气魄去创造,这种崇高气魄伟大到使那些用想象来创造的本人也感到非常惶惑。”这种诗性智慧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各种有关西域的典籍中频频出现,也常成为民族叙事的重点。其影响的广度与强度在当下语境中不仅没有削弱,反倒决定着人们对西域的想象性言说。当我们提及“西域文化”时,扑面而来的是久远的历史文化传统,即便是现今在诸种场合展现的民俗以及各种形式的歌舞表演,也都是以与现实生活构成距离和反差的生产生活方式为想象的基点。从一定层面上说,这是对一种地域与民族的浅层认知,阻隔了对真实社会状况的读解,但换个角度看,则说明这种表达在民族性的阐释上的深刻根由。本文对“现代背景下的诗性智慧”的读解即意在此,从现有的诸种元素反观诗性文化的原始表现,并将之置于现实语境中,来考察其接受与言说特性。
诗性智慧之原始表现
对于西域文化,这种“诗性智慧”与草原游牧文化和绿洲农耕文化构成最基本的互为表达关系。游牧文化彰显出的力度、强度、强烈的主体性,以及具体生活中对自由、骏马、猎鹰、荣誉的高度重视,都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游牧传统获得了对话的可能。这当中还应有暴力行为的盛行,包括战争的频发。而农耕文化对水土和花草的重视,则彰显着多元历史的铸造功能。
在现有的著作中,有不少介绍西域历史上存在的不同生产生活方式。《史记·大宛列传》载:“乌孙多马,其富人至四五千匹”;《旧唐书》说:“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显然,羊、牛的多寡直接关系到生存。《汉书·西域传》则描述这样一种生活状况:“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以上这些记载呈现的是在西域早期存在的生活方式——游牧。游牧民族从根本上说是骑马民族,马既是迁徙、游牧时的坐骑,又是征战的战骑。月氏、匈奴、乌孙、突厥、蒙古等征战几乎全是骑兵。这说明在西域地区自古以来就有着游牧生活,相应地产生了影响至今的草原文明,直到现在,牧民定居问题依然是这个地区的一大社会问题。广阔的西域还有悠久的绿洲农耕文化,佘太山在《西域通史》中说:“南疆适合农业的经济形态早在距今三千年前的早期铁骑时代已开始形成了。”不同的生产文化类型产生了不同的仪式和神话。对于西域绿洲农耕民族来说,土地是生命之源,其土神观念以及仪式常与土地有关,土被视为洁净的母神。《大唐西域记》记载于阗人的建国传说有这样的描述:“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状如乳,神童吸吮,遂至成立。……地乳所育,因为国号。”这种地形与人体的相似联系,在维柯看来就是一种诗性智慧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切语种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的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用人的感觉和情欲的隐喻来形成的”。这是诗性智慧的表现形式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他类,《周书·突厥传》记载:“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隋书·北狄传》则言:“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也。”以上记载都说明突厥始祖以狼作为自己的图腾。张岩在他的《图腾制与原始文明》一书中也说:“在属于同一部落图腾下的所有男人和妇人都深信自己系源自于相同的祖先并且具有共同的血缘,他们之间由于一种共同的义务和对图腾的共同信仰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与维柯所说的“最初的诗人们给事物命名,就必须用最具体的感性意象,这种感性意象就是替换和转喻”有内在的一致性。在当代民族文学叙事当中,要想找到惯用的描述和比喻非常容易。狼皮或者狼头装饰在西域许多地方都可见到。在西域文化的典型之一游牧文化中(实际上我们关于西北民族的想象大多与草原和游牧连在一起),常常看到人们将植物、动物乃至天地等自然万物和自然现象神化和人格化,“万物有灵观构成了处在人类最低阶段的部落的特点,它由此不断地上升,在传播过程中发生深刻的变化,但自始至终保持一种完整的连续性进入于高度的现代文化之中”。维柯把这种原始人对自己生存世界的想象能力称为诗性智慧的开始,“诗性的智慧,这种异教世界的最初的智慧,一开始就要用的玄学就不是现在学者们所用的那种理性的抽象的玄学,而是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像这些原始人所用的。这些原始人没有推理的能力,却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这种玄学就是他们的诗,诗就是他们生而就有的一种功能(因为他们生而就有这些感官和想象力);他们生来就对各种原因无知。无知是惊奇之母,使一切事物对于一无所知的人们都是新奇的。……他们还按照自己的观念,使自己感到惊奇的事物各有一种实体存在,正像儿童们把无生命的东西拿在手里跟它们游戏交谈,仿佛它们就是些活人”。
这种原始诗性智慧在特定的生存状况下生成,随着历史的演进就有了不同的表达,有些融化为日常生活的无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发生着作用。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综合叙事的过程,一个不断注入强调因子的过程。在诗性表达中凸显出的一个特征是,“新疆各民族传统的思维中以象征思维特别发达。这是一种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它虽产生于原始社会的野性思维,但在进入文明社会后并没有弱化,反而强化了”。(见仲高《西域艺术通论》具体来说,生态地理环境这一本为审美中的自然因素却成为审美意象的决定点。在绿洲农耕民族那里,以自然为审美客体的描写非常突出,其中“花”出现的频率最多,而以玫瑰花为最。这在现今的维吾尔人家也时常见到,几乎每个拥有宅院的家庭都有花丛围绕。花成为许多美好事物的象征,尤其是爱情。很多姑娘也以花为名,所以你总会听到这样那样的“古丽”。而在草原游牧民族中,马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而鹰、高山、青松、草原、蓝天、山羊、猎犬等也是常出现的象征群落。在当代哈萨克族作家笔下,这种描绘几成文本无意识,可以说处处可见。的确,对于我们所观照的西域文化来讲,体现出“人类的最初创建者都致力于感性主题,他们用这种主题把个体或物种的可以说是具体到特征、属性或关系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它们的诗性的类”。(见维柯《新科学》)
除了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中所显现的诗性智慧,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西域文化自古至今都不是单一的存在。在一些研究文章中,我们常看到这样的表述:“西域艺术文化尽管有东西方文化助动力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讲是内部诸民族文化互动的结果”;“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文化,基本上是希腊化的阿拉米亚文化和伊朗文化。这种文化是肥沃的新月地区古代闪族文化逻辑的继续。这种古代文化是亚述人、巴比伦人、腓尼基人、阿拉米亚人和希伯来人所创始和发展起来的”;“草原地区游牧民族同绿洲地区农业居民的关系,在古代中亚历史上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些都阐明一个事实:我们所面对的西域文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化系统,而是融合了多重文化元素的多元整体。这提供了一种比较文化的视角,将西域文化与多种文化联系起来综合考量。比如游牧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就可连及英雄史诗以及后来的骑士文化,我们可以在个性鲜明、粗野、好战、马啸西风、重诺、嗜肉、好酒等等方面发现其中的相似。如果说西方人性格的形成离不开中世纪的骑士文化传统,那么,或许,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秉承西域文化传统的西部群落性格与遥远的过去紧密相连。这是我们至今能在多领域发现原生态的重要原因。而且,需要强调,这种性格是多重质料熔铸的结果。
诗性智慧之现代影像
在《美的生成新论》一文中,新疆著名文化学者孟驰北先生开章明目:“从现在起,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保存的局面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会逐渐淡化。”对于“淡化”一说,我表示赞同。边疆地区原以游牧为主导生活方式的群体业已大部转为住居的生活方式,相应地,原有的与游牧有关的审美方式、人与自然的关联方式都难以维系旧貌。然而,“淡化”并不意味着“消亡”,也不意味着不存在,其踪迹(trace)就像宗教一样在蛛丝马迹之中静静地展示自身。这种情况就需要我们对当下的审美状况作出区分,大众文化的审美指向并不就是大众的,而对于大众文化的评价也并不就能一语说清其存在与发展的样貌,日常生活、影视文化、文学,这些都是表现审美状况的重要领域,这些领域的表述是否相同?倘其不同表述所构成的是杂糅的审美形态,那么,传统的审美方式于其中发挥着怎样的功能?或者,是什么在暗中主导着现在的审美走向?这些问题一时很难说得清楚,但却是思考当代审美观念的重要地点,对此我们可以生活中的诸种表现为田野做初步的分析,以期达到反思的目的。
当代中国生活方式在社会语境发生巨大变化的状况下的确与前大为不同,但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却不容忽视,那就是在不同领域审美观有所不同。这和文化形态有关。具体来说,主流的政治文化携带着强有力的道德建设力度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借助着大众文化的宣传强势日益在社会及个人生活的各个部分展开。如此一来,在日常生活日益审美化的同时,文学话语与各种媒体话语分别以各自方式表达自身,其中有交叉,也有自性,而且,在这种多元复杂的话语系统之中,由于物质及文化形态变动而引起的纠结、矛盾心理也是一种审美所必须面对的现实。
在对大众文化的反思中,我们不能忘记前面提出的疑虑,即传统文化在所生成方式不再的情况下以何种样态表达自身。媒体与电子信息的超级穿透能力并没有漏掉偏远的地域。这里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迁。而新疆的多民族特性、多种经济方式混杂的社会状况使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充满混杂局面。这就牵涉到如何表达群体意识、民族意识及个人意识等问题。当我们将视线停留在各个民族身上、不分男女的牛仔裤时,一种跨越界限的信息糅合着时尚、休闲、现代等意味扑面而来。这种趋同的日常审美形式同时伴随着有所区别的群体选择:如对花色繁多的喜爱,厚底高跟鞋持续走俏,备受欢迎的皮革制品,卷发的长盛不衰。其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三五成群着同色同样服饰出行。这与大众文化大肆宣传的个性、时髦实有出入,而个性与时髦之间的矛盾亦显而易见。还必须指明,这种现象在本人新疆生活的生涯中始终存在,对此可能并不能简单以大众文化的类型化效应予以解释。虽然这些有选择的符号在各民族中的受欢迎尺度缺少确凿的具体的数字,但其流行程度或者普遍程度在你步入街头的偶一回首之间却以一种常态出现。这种现象带来的启示是,传统美学中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踪迹随着不同生活方式的交叉表现出共在趋势,而非断裂式的呈现。
这种属于民族或者地域的诗性智慧常常转化为现实生活中艺术表现的对象,从而与实际生活拉开了距离。在西域广博大地上徜徉神思的人们,其想象几乎没有不在民族视域与传统生活方式之中流连的。纵观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书写,从伤痕、改革到反思,接下来的寻根与先锋,及至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学走了一条从主体书写到文学性追求的道路,但最终还是落脚到日常生活。中间曾引起广泛关注和影响的寻根文学看似在具体、琐碎的寻常生活中寻找被视为虚化的精神,“混沌模糊的意念”,被认为是一种“自我解构”。但必须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随着各种样式文学的轮番出台,一种对传统精神力量的借重趋势日显突出。寻根文学以畅想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为前奏,而又以“文化寻根”作为自己寻求心理平衡的支点,“诗意叙事、散文化结构、怀旧的语态也为寻根小说先布设了文体特征”。这种“寻根”意识与“民族”构成了二位一体关系,民族性的书写成为主要对象,在中西、不同生产方式摩擦与对话之中,这一关系很容易受到欢迎。新疆多民族文学回归传统、弘扬传统以及苦难叙事的明显意向,以及单边叙事方式均可与流行于八十年代的寻根联系起来,同时反映出物质与生产领域的变动在文学领域的别样思考,凸显出诸如不适、矛盾、拒绝、向往等多重复杂心态。这显然也是当代审美观的一种,对于传统的力量也绝非“淡化”可以说得清的。大众文化对美的符号的利用与宣传,和文学作品的话语传导似为不同路数,哪种更真实、更贴近生活实际与心理实际,都很难说。或者,这就是今日生活之现实,审美也在这不同方式之间进行着不同的诠释和表达。哈萨克族著名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的作品《走动的石人》至今读来仍然觉得富含着多重文化意义。这一“石人”跨越千年与一个现代哈萨克人梦中赫然相遇,由此特殊境遇引出传统与现代、科学理性与信仰、城市与乡村、文化认同与差异、价值与判断、动与静等多元存在。作者指出:“显然这位主人公迷失了对于这位石人的文化认同和敬畏,出现了价值判断的断裂,所以引发了他的轻率、他的惶恐、他的痛苦、他的迷惘,由此牵引出一系列的故事。而这一点,似乎也是许多现代人共同的感知和心路旅程。传统文化似乎与我们渐行渐远,甚或变得隔膜起来,而新的文化积淀尚没有夯实,还在形成中,有时还显得相当脆弱。但是,犹如那座跨河而建的桥梁,虽被洪水冲毁,我们依然要致力于去构建它,因为生活需要它。”
传统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在西部甚至被强调。尽管外部语境已经发生而且仍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但在这种情况下的原始诗性智慧却获得了凸显自身的张力空间,并在实际上成为打造民族性的有效手段。歌舞剧《阿嘎加依》在2010年的新疆可谓赚足风头和眼球。这出剧以哈萨克族生活的主要地域阿勒泰为叙事场景,选择哈萨克人的文化习俗和历史传统作为叙事对象,而所有情节均以一个人的生存历程为限,其象征意味和展示意味相当明显。但不可否认,该剧明朗、热烈而又不失温情的镜头将观者带入了一个纯粹的哈萨克人世界,那里有孩子出生时的“斯劳”(相当于洗礼),属于草原文化的一些细节在此已然展现。下一个镜头是孩子在被清水洗遍全身之后的遍涂羊油,这是对孩子健壮成长的美好寄望,显然带着强烈的草原民族的特征。接下来的学步礼则似乎冲破了民族的界限,而进入礼仪文化的序列。人类的艰难历史在一个孩子跌跌撞撞的行进之中开始。孩子渐渐长大成人,一些关键的草原元素开始出现,白色骏马、绿油油的草原、帅气的小伙、娇羞而不失洒脱的姑娘、草原上的婚礼等等。但最能触动人历史神经的,莫过于草原石人、马蹄声和强壮的黑熊的身影。石人在诉说着这个民族漫长的历史,马蹄阵阵催醒着观看者的前世神经,黑熊则呼唤着曾强有力的游牧民族的粗壮与豪气。这一切似乎都已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一种观影中的存在,尤其对于越来越多的进入城市的草原民族来说。尽管如此,却不能不承认这种叙事方式成功营造了民族的一体氛围,大大激发了在场的哈萨克人的民族自豪感,也令农耕民族沉淀已久的活性心理元素在观看中萌醒、跳动。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原生态的各种文化表现获得高度重视。2010年青歌赛上,新疆荣获亚军,其成功全凭原始意味十足的原生态唱法,其中的“刀郎木卡姆”和“玛纳斯”组合当居头功。对于普通听众,很难用简单的话语来评价这类唱法的“好坏”“优劣”,但其中洋溢着的强烈的生命力量和投入的热度,恐怕每个在场的听者都会感受到。作家赵光鸣在2009年的“南疆系列·帕米尔远山的雪”中描述了民间游吟歌者“阿希克”的大地歌唱,流浪的歌者用他的执着挚情打动了所有在场的听者。那是一种来自广场的演唱。来自民间。同样是一种原生态的歌唱。对于这种原生态的多方位展现,不能不说是原始的、民族内心深处的记忆在现代并未逝去,而以潜在方式存于民间、长于民间。这是一种来自久远过去的诗性智慧的现代影像。
当立足现代回视传统
如果说诗性智慧成为一个民族观照自身的主要着眼点,这里我们尤其强调的是西域文化的界域,在全球化语境甚至后殖民的话语中,这些内容又自然成为抵制被同化、被征服的历史因由和形式支撑。民族美学叙事回望传统成为现实身份的一种有效表达。这种叙事中,不同民族的叙事具有不同的特征。对于本民族以外的他民族(需强调,这里的“民族”实际上是同样的“中华民族”所包括的各族群。对新疆而言,这种族群观念可能更加复杂),拥有实在距离的观看视角决定了审美观照的内涵与外延。就现实情况看,这种观看包括旅游者的眼光和同一地域生活着的他者的眼光。尽管如此,在表达上这二者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欣赏的、向往的情感与小心翼翼的表达是其共同特征。这样的叙事呈现出的大多是唯美的画面和异域风情之美。就目前类似的书写而言,是不足以表征民族或者更高层次的民俗审美的重点的。为什么这样说?一则因为这种表述将所视对象锁定为不变的形象,一则带着过多的主观想象成分,二者都远离了生活的实际,自然不能呈现真实的状况。而更关键的一个理由在于,尽管描述民族生活的话语良多,却并没有改变说者与被说者之间的距离意识,深层认知自然也就无从谈起。或者,从现有的艺术想象的持久不变已经能够说明这种书写背后的对浅表呈现的满足。这就为深层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提出了要求。
以上论述是针对他民族叙事来说的,那么,在本民族自叙中的文化又有怎样的表现呢?《心山》是维吾尔族作家巴格拉西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体现出浓烈的寻觅主题,仿如奥德修斯历尽艰辛回归家园和忒勒马科斯寻父的精神母题。“心山”具有类似的象征意味,它是埋葬着“漂亮母亲”和拜格库勒拜格的坟墓,是夏库尔村人的精神“圣地”。换句话说,“心山”就是传统,就是夏库尔村人的精神归宿。整个故事就是以这种精神征召为主体力量,牵引着来自城市和乡村不同界域的三个孩子走上了寻觅之旅。尽管这一寻觅的过程就像浮士德的最终死亡一样,生命的失去为这次冒险做出了标识,但孩子们身上所彰显的“向往”、“崇敬”力量,却唤起了整个夏库尔村人的“古老”意识,文末全村人向着“心山”的行进就是对“寻觅”、“皈依”的最好注脚。这是就作品的主题来说的。作品中的一些细节则叙说着这个民族的深层心理。老奶奶对“风沙”的恐惧,“担心灾难会从那边突然袭来,失去她的果园、房子、她的孙子,圈里的牛羊、鸡窝里的鸡以及整个夏库尔”,“她担心会有天灾人祸”。当就此现象问及作者巴格拉西,他说:“我发现我们维吾尔族人的生活本身就很神秘,外表上来看不大能看得出来。就比如现在都二十一世纪了吧,我们的人呢还是照样相信风代表什么、水代表什么,树、颜色代表什么。……这是萨满教的一些东西,可见萨满教的东西我们还在沿用,像用石头算命啊。”老奶奶对“雨水”倾盆而至的恐怖与维吾尔族对“水”的敬畏是连为一体的。维柯在对“lustrum”一词的追溯中指出:“文化从水开始,人先感觉到水的需要,然后才感到火的需要,在结婚和剥夺教权的祭礼中水都先于火。这就是在献祭礼之前必行沐浴(或洗手)礼这个各民族古今流行的一种习俗的起源。”的确,这种习俗在今天的许多民族中都可以见到,如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都有“洗手礼”。巴格拉西也说:“我们维吾尔族对河水是非常尊重的,一下雨也会感到害怕,《心山》中那个奶奶对水有一种恐惧,把水看的太神了。”除了这种萨满教的细节外,作品中还有维吾尔人生活智慧的一些片段,典型如“恰克恰克”,这是一种民间的笑话,闪现的是这个民族对幽默的体会和日常表现。作品中有个小孩的名字叫“吐来克皮特”,“皮特”是“虱子”的意思,牛虱子。这种在人的名字后面加上某种绰号的做法是典型的恰克恰克表述。目前对伊犁的恰克恰克研究已经开始。最后,不能不提,整部作品中强烈的回归传统的意识以及对现实社会尤其城市生活的不满,总的来说,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文中不止一次提到城市,却见不到一丝欣喜:“城里人很少思考有关自己、生存、家园以及先辈的事情,是的,根本就不想!难道不是吗?”“那座城市和牢笼式的楼房,好斗而不知足、奸诈而吝啬的城里人,在他眼里变得十分丑陋。他们好像都是些用塑料做成的有生命的假人。”类似的反复叙述为全文营造了一种声讨现实人生的话语指示功能。
在《心山》的题记中有这样两句话,可以看作是对文本主旨的一种注解:父亲说:“孩子,你要像捍卫自己的信仰一样,捍卫父辈开垦的土地和山川。”母亲说:“孩子,你要时常惦念你的列祖列宗,不要让他们的亡灵感到孤独,否则会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两者体现的都是对传统的认知强度和热度。所以如此,是因为当传统遭遇现实、现实与传统纠葛重重时,一个越来越鲜明的问题开始产生,如何维护自身特性?《心山》以古老传统抨击现代性的主张是较为突出的一种民族性表达。这在目前所见的民族文学叙事中是屡见不鲜的,其内涵与所谓的“西方中心论”、“失语”相辅相成。这说明,对传统的理解是个不断迫近现实的过程。现实变动速度越快,这种情绪就越明显而且变得敏感。“变”在现代性的意义上,是一个不断向前的运动,单纯以“不变”或“回归”来应对来自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动恐怕只是一种软弱和暂时的做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体验方式、审美方式就不具有现实意义。对于每个社会中的个人来说,我们都生活在被无数传统包围的现实之中,无时无刻不受历史记忆的影响。“切断历史”的做法既是不可行也是不可能的。在这种状况下,所要考虑并付之行动的可能就是如何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建立起互利互动的局面,以改善现实的生活状况。
就目前的民族文化研究来说,尤其针对西域文化,单纯强调某民族如何如何的做法显然也是不全面的。当我们提及西域文化,实际展示的是一个融合、变动、吸纳、综合的过程。进一步说,民族美学研究趋向于地域美学研究实属必要。这方面,王治来先生强调“伊斯兰化”和“突厥化”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不是这块地域自古以来固有的特征,正是说明这样一个问题。王治来在他的《中亚通史》中说:“中亚地区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有着自石器时代起以至现代的悠久历史,但也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多民族、多宗教和多种文化并存。”“中亚”的地域意义远远超过某些有意扩大一种特征的做法。我们对中亚尤其具体到中国西部时,也要把握这一点,站在地域的角度来看其互动交流,对话是主流,而国家认同是第一位的共同认知。
现实生活中诗性智慧渐渐成为被改写被观看的对象,站在现实的、发展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必然。然而在这种“看”与“被看”之间,却很容易忽视两种存在的现实。一是贬弃现实,以传统作为所有行为的旨归和判断标准,这样做,很容易滑向危险的狭隘民族主义深渊。一是具有现代性的时空意识,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现实,而无视传统中的智慧的、诗性的内涵,如简单地认为游牧文化是一种过时的被淘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而忽略这种文化当中蓬勃的生气和人本价值,如此,则会流于肤浅和盲目自信。两种看法,实则都是主体发展不健全的结果,是一种不自信。用席勒的话来说,就是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矛盾冲突的结果,而需要用一种游戏冲动来连接二者。对于西域文化研究,这种游戏冲动是具有审美内涵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即以集体无意识形式存在的诗性智慧。即便是以展示的方式强调这种智慧的意义和价值,也好过无视其存在的做法。只是,我们需要做的,是在诗性智慧与现代性之间找到一个可以搭建的桥梁,而非两厢看不顺眼或偏向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