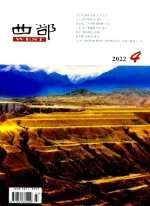短篇小说二题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朱景冬译
爱之后的必然死亡
当参议员奥内西莫·桑切斯遇到他生命中的女人时,他的一生还剩下六个月零十一天。他是在“总督玫瑰园”认识她的。那是一个梦幻般的小村镇,夜间它是光彩船的秘密船坞,大白天则像荒漠中的一段最没用的弯道。它面对一片单调乏味、没有航线的大海,离什么地方都很远。谁也不会怀疑那里居住着一个能够改变任何人的命运的人。甚至连它的名字也像是一种讽刺,因为村镇里那朵唯一的玫瑰也被参议员奥内西莫·桑切斯在认识劳拉·法里纳的那天下午弄走了。
那是每四年举行一次的竞选运动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宣传站。喜剧团的行李车大清早就到了。随后到来的是运送印第安人的几辆大卡车。他们是为了充实公共集会的人数而从其他村镇雇用来的。快到十一点的时候,在音乐和爆竹声中,部长级的、草莓饮料色的汽车和随行人员的吉普车到了。参议员奥内西莫·桑切斯在凉爽的汽车里心情平静,感觉不到天气的变化。但是车门一开,一股炽热的气流不禁使他颤抖了一下。他那件天然丝的衬衫很快就湿透了。他觉得自己一下子老了许多岁,并且比任何时候都感到孤独。在实际生命中,他最近刚满四十二岁,在戈丁加(德国城市)获得冶金工程师的荣衔;他酷爱读书,但是没读几本译得糟糕的拉丁经典作家的著作。他和一位光彩照人的德国女人结了婚,婚后生了五个儿子。家中的每个成员都很幸福。在所有成员中,他本是最幸福的一个,但是在三个月前他被告知,到下一个圣诞节,他将永远离开人间。
直到群众游行的准备工作结束以后,参议员先生才在为他预备的专用寓所里独自休息了一个钟头。在躺下之前,他把一朵路经荒漠活下来的鲜玫瑰插在喝的水中,午饭吃的是随身带来的规定吃的粮食,为的是避免每天总要等着他去吃的油炸山羊肉。饭后他提前吃了几粒镇痛药丸,这样,他首先感到的将是轻松,而不是疼痛了。最后他打开距离吊床很近的电扇,光着屁股在玫瑰色的半明不暗的光线下躺了十五分钟,竭力保持头脑的平静,免得打盹时想到自己的死亡。除了大夫以外,谁也不知道他的死期已经判定。他已决定独自忍受他的秘密,既然生命不会有任何转机。这不是因为他专横,而是因为他感到难为情。
当下午三点他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他觉得完全控制了自己的意志。他心情平静,衣着干净,下穿一条粗麻布长裤,上着一件花衬衫,由于吃了镇痛丸而精神愉快。然而死神的困扰要比他想象的严重得多,因为当他走上讲台时总觉得受到那些争夺跟他握手的运气的人的奇怪蔑视。他不像以前那样对一群群赤脚的印第安人表示同情。他们几乎忍受不了荒芜的小广场那些炭火似的小石子。他挥了挥手,几乎愤怒地止住了众人的掌声,开始讲话。他脸上没有表情,两眼注视着散发着热气的大海。他那缓慢而深沉的声音像平静的水,但是他事先背下来的、屡次中断的演讲并不是为了讲真话,而是为了反对马科·奥雷利奥德的方法论第四卷中的一个宿命论观点。
“我们在这里集会是为了打倒天命。”参议员反对他的一切信念,说,“我们不再是祖国的弃婴,不是上帝在干渴和恶劣气候王国里的孤儿和我们自己土地上的流亡者。我们将成为另外一种人,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将是伟大的、幸福的。”
这是他的竞选团的陈规陋俗。在他讲话的时候,他的助手们向空中撒出了几只小纸鸟。那些假动物像活的一样,在木头讲台上空飞舞,向海上飞去。与此同时,另一些助手从行李车上搬下来几棵作道具的树,树叶是用毡做的。他们把树栽在了人群背后的硝土地上。最后,他们搭起了一堵纸板墙和几间红砖、玻璃窗的假房子,用它们遮住了现实生活中的破棚屋。
参议员延长了讲话,引用了两段拉丁文,为的是给喜剧团更多的时间。他答应提供下雨的机器,饲养专供食用的动物的活动养殖场和幸福油。这种油能使石头地里长蔬菜,能在窗子上悬挂三色堇。当看到他的想象的世界已经完成时,他用手指着它说: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生活将是这样的,”他叫道,“看吧,我们的生活将是这样的。”
众人转身去看,一艘纸做的远洋轮船正从房子后面驶过,它比那座假城市的最高的房子还高。只有参议员本人注意到,由于装了拆,拆了装,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结果用纸板搭的村镇已被恶劣的气候腐蚀坏,几乎跟“总督玫瑰园”一样破败、凄凉和尘土飞扬。
十二年以来,内尔松·法里纳第一次没有去问候参议员。他躺在吊床上,在断断续续的午睡中听到了参议员的讲话。吊床安在一幢房子的凉爽阴凉里。房子用没有刨的木板盖成,盖房子的这位药剂师曾用同样的一双手肢解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他逃出了卡宴(法属圭亚那首府)的监狱,在帕拉马里博遇到一个美丽的、不敬神明的黑女人,一起搭乘一艘装运无辜的赤鹌鹑的轮船来到“总督玫瑰园”。他们生了一个女儿。没过多久,妻子死去。她的命运与他的前妻不同:他的前妻的碎尸被他埋在自己的菜园里当了肥料,她的尸首则被完整地埋在了当地的公墓里,并且用了她的荷兰人的名字。女儿继承了她的肤色和身材,继承了父亲的一双易受惊吓的黄眼睛。父亲有理由认为,他所生养的女儿是世界上最美丽的。
自从在第一次竞选运动中认识参议员奥内西莫·桑切斯后,内尔松·法里纳就请求他帮助办一张假身份证,好应付司法机关。待人和蔼但态度坚决的参议员拒绝了他的要求。几年来,内尔松·法里纳一直坚持着,一有机会就用不同的方式重申他的要求,但是得到的回答依然如故。所以这一次他躺在吊床上没有去,命中注定要活活烂在海盗们的那个炎热的巢穴里。当传来最后的掌声时,他伸长脑袋,从围墙的木桩上看见了喜剧团的背面:楼房的支柱、树木的支架和在暗中推动远洋船前进的魔术师。他不禁愤怒地骂起来。
“狗屎!”他叫道,“纯粹是政治骗子。”
跟往常一样,讲完话后,参议员照例在音乐和鞭炮声中到村子的街上走一走,村民们把他围起来,向他述说自己的苦难。参议员耐心地听他们讲述,总能找到一种方式,既能安慰所有的人,又不向他们许诺难办的事。一位妇女高高地站在房上,身边围着六个年幼的孩子,她在人群的喧闹声和鞭炮的爆炸声中好不容易让参议员听到了她的要求。
“我们要求不多,参议员。”她说,“我只要一头驴,用它从阿奥卡多水井往家里驮水。”
参议员看到了那六个瘦骨伶仃的孩子。
“你男人干什么去了?”他问。
“去阿鲁瓦岛上碰运气去了。”女人风趣地回答,“他碰到的是一个牙齿上镶钻石的外乡女人。”
她的回答引起了一阵哈哈大笑。
“好吧,”参议员决定说,“你会得到一头驴的。”
过了一会儿,他的一名助手就给这个妇女牵来一头驮东西的驴。驴背上用永久性的笔迹写着一句竞选的口号,让人们不要忘记这是参议员送的礼物。
在街上进行的短程察访中,参议员又做了一些别的小姿态,此外他还给一个病人喂了一口饭。那个病人特地让人把床抬到门口,好看看参议员从门前经过的情景。在最后一个街角上,他从围墙的木桩孔里看见内尔松·法里纳躺在吊床上,显得精神不振,郁郁不乐,但他还是冷淡地问候了他:
“你好吗?”
内尔松·法里纳在吊床上翻了个身,泪水浸湿了他那琥珀色的眼睛。
“我很好,你知道。”他说。
听见问候声后,他女儿出现在院子里。她穿着一件平常的瓜希拉旧晨衣,头上系着彩结,脸上涂着防晒霜。然而,尽管她的仪表显得挺邋遢,但还是可以说,世界上没有比她更俊俏的了。看到她后,参议员全身都酥软了。
“我的妈!”他惊叹一声,“这才是上帝的创造!”
当天晚上,内尔松·法里纳便叫女儿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去见参议员。
在参议员的寓所门口,两个背步枪的警卫热得打瞌睡。他们让她坐在门厅里唯一的椅子上等候。
此时此刻,参议员还在隔壁房间里和“总督玫瑰园”的头脑们聚会。他把头头们召集来,是向他们透露他在讲话中避而未谈的真情。这些人和那些在荒凉地区所有的村镇参加会议的人如此相像,参议员本人竟觉得每天晚上召集的都是一样的会议。他的衬衫湿透了,老是想用电扇吹出的炭火似的热风把衬衣吹干。在闷热的房间里,那台电扇像只大黄蜂一样嗡嗡直叫。
“当然,我们不会把纸糊的鸟儿当饭吃。”他说,“你们和我都知道,到这个山羊拉屎的地方有树木和花草的那一天,井水里有鲱鱼而不是蛔虫的那一天,你们和我在此地就没有什么事可做了。我说得对吗?”
没有人吭声。说话的时候,参议员从日历上扯下一张石印彩色画,用手叠了一只蝴蝶。然后把蝴蝶抛在电扇吹出的风中,蝴蝶便在房间里飞舞起来,最后从半开的门缝里飞了出去。参议员控制着想到死亡的复杂心情,继续讲着。
“所以,”他说,“你们知道的情况我就不重复了。总之,我的重新当选对你们的好处比对我的还大,因为我在这里仅仅闻到了臭水和印第安人汗水的味道,相反,你们得这样生活下去。”
劳拉·法里纳看见纸蝴蝶飞了出来。只有她一个人看见,因为门口的警卫已经抱着枪靠在长靠背椅上睡着了。石印彩色画做的大蝴蝶盘旋了几圈后完全展开了,撞在墙上黏住了。劳拉·法里纳想用手指甲揭下来。这时,一个警卫被隔壁房间的掌声惊醒,发现了她的徒劳的意图。
“揭不下来。”他迷迷瞪瞪地说,“它是画在墙上的。”
当开会的人们走出来时,劳拉·法里纳又回到椅子上坐下了。参议员站在房间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把手。直到门厅的人走完后,他才发现了劳拉·法里纳。
“你在这儿干什么?”
“是我父亲叫我来的。”她说。
参议员明白了。他望了望昏昏欲睡的警卫,又打量了一下劳拉·法里纳:她那迷人的姿色使他忘却了疼痛,于是他决定把自己交给死神。
“进来吧。”他说。
劳拉·法里纳站在房间门口不禁惊呆了:数不清的钞票飘动在空中,像蝴蝶在飞舞。但是参议员关闭了电扇,没有风吹,钞票逐渐落在了房内的东西上。
“你瞧,”他微微一笑,“连臭狗屎都会飞。”
劳拉·法里纳像小学生坐在课桌前那样坐下了。她的肌肤平滑而丰满,肤色和密度都像原油,头发像不满三岁的小母马鬃,一双大眼睛比灯光还亮。参议员顺着她的目光看去,最后看见了被硝石弄脏的玫瑰。
“这是一朵玫瑰。”他说。
“是的。”她说,有点不知所措,“我在里奥阿恰见过。”
参议员坐在行军床上,一边谈论玫瑰,一边解衬衫扣子。在左肋部——他猜想,心脏准在这边的胸腔里——有一个海盗文身,画着一颗被箭射中的心脏,他把汗湿的衬衫扔在地上,让劳拉·法里纳帮助他脱皮靴。
她面对行军床跪下。参议员继续若有所思地打量着她。一面解鞋带一面想:这次两个人相遇,倒霉的可能是谁呢?
“你还是个娃娃。”他说。
“别这么说,”她说,“到四月我就满十九岁了。”
参议员对此很感兴趣。
“哪一天?”
“十一日。”她回答。
参议员觉得更妙了。“我们都是白羊座。”他说。然后又微笑着加了一句:
“这是孤独的标志。”
劳拉·法里纳没有注意他的话,因为她不知道把靴子放在哪里。参议员也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劳拉·法里纳,因为他还不习惯这种突然到来的爱情。此外他也很清楚,这种爱情是侮辱性的产物。只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他才用双腿夹住劳拉·法里纳,搂着她的腰,背朝下躺在了床上。这时他才知道,她只穿着一件外衣,里头完全光着,因为她的肉体散发出一股野生动物才有的说不清的香气。但是由于身上的冰凉的汗水,他觉得心里发抖,皮肉发颤。
“没有人喜欢我们。”他叹了口气。
劳拉·法里纳想说什么话,但房间里的空气只够她呼吸的。他让她躺在身边,关了灯,房间里顿时一片昏暗。劳拉·法里纳觉得自己的命运非常可怜。参议员慢慢地抚摸着她,轻轻地去摸她的下身。跟他的愿望相反,他碰到的竟然是一个铁家伙。
“这是什么东西?”
“一把锁。”她说。
“真荒唐!”参议员狂怒地吼道,然后明知故问,“钥匙在哪里?”
劳拉·法里纳松了口气。
“在我爸爸手里。”她回答,“他叫我告诉你,让你派一个心腹去取钥匙,让心腹带一份为他解决身份问题的保证书。”
参议员心情不禁一阵紧张。“卑鄙的法国佬,”他气愤地咕哝道。然后闭上眼睛,使心情平静下来。他觉得黑暗中只有他自己。“要记住,”他想起来了,“或者是你,或者是其他某个人,将在很短的时期内死去,不久后你们连名字也不存在了。”
他等待那些冷汗消失。
“告诉我一件事,”他问,“关于我,你听见人们讨论什么了?”
“照实说吗?”
“照实说。”
“好吧,”劳拉·法里纳大胆地说,“都说你比别的参议员坏,因为你跟他们不一样。”
参议员不动声色,闭着双眼沉默了很久。当他再睁开眼的时候,仿佛从他最隐秘的天性转回来似的。
“真是见鬼!”他做出了决定,“告诉你那个该死的父亲,他的事我一定为他办。”
“你要是愿意,我自己去要钥匙。”劳拉·法里纳说。
参议员阻止了她。
“把钥匙的事忘掉吧。”他说,“跟我睡一会儿。一个人孤单的时候,有个人在身边是愉快的。”
于是,她两眼注视着玫瑰,让他躺在自己的肩上。参议员搂着她的腰肢,把脸藏在她这只野生动物的腋下,害怕到了极点。六个月零十一天后,他肯定也是这样搂着她死去的。他死前,由于他和劳拉·法里纳的丑事无人不知,他自暴自弃,遭人唾弃。当他想到舍下她死去,还恼怒地哭了一场。
八月的鬼怪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到达了阿雷索。我们花了两个来小时才找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它是委内瑞拉作家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在托斯卡纳原野上那个田园诗般的河曲处购买的。那是在八月初的一个星期天,天气炎热,行人嘈杂,在满是游客的街上,很难找到什么人打听情况。在经过多次徒劳的尝试后,我们又回到汽车上,沿着一条没有路标的意大利柏油小路离开了城市。一个年迈的放鹅妇人正确地指给我们那座城堡在哪里。在告别之前,她问我们是否要在那里过夜,我们像预料到的那样回答她说,我们只是去吃午饭。
“这样好些,”她说,“因为那幢房子里闹鬼。”
我和妻子不相信中午会有鬼怪,便对她的轻信报以嘲笑。但是我的两个儿子,一个九岁,一个七岁,想到能够有机会见到现形的鬼怪却感到很幸运。
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不仅是优秀的作家,而且是慷慨的东道主和美食家,他准备好了永远难忘的午餐,正在等我们。由于我们姗姗来迟,我们没来得及参观城堡的内部就入席用餐了。但是从外表看,它的样子并不可怕,只要从我们进午餐的花儿盛开的花坛那儿看到城堡全貌,任何不安都会烟消云散。很难相信,在那座房舍建在高处的、勉强容纳九千人的小山上,会涌现出那么多有着永久的才智的人。然而,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却以其加勒比人的幽默对我们说,那些人中没有一个是阿雷索最杰出的。
“最伟大的人物,”他断言,“是卢多维科。”
就是这样称呼,没有姓氏:卢多维科,伟大的艺术家与军事家,他建造了那座为他带来不幸的城堡。整个吃午饭的时间米格尔都对我们谈论他。他对我们讲述了他的巨大权力、不幸福的爱情和他的可怕死亡。他对我们讲述了在一个精神失常的时刻他为什么把她的情妇杀死在他们刚刚做爱的床上,后来又唆使他的凶恶的警犬用尖牙利齿把他自己撕碎。他十分严肃地对我们肯定说,从半夜开始,卢多维科的鬼魂就会在黑暗的宅内游荡,要为他遭受的爱情的煎熬寻求平静。
实际上,城堡既高大又阴暗。不过,在大白天,酒足饭饱,心情高兴,米格尔的故事像他讲的那许多事件一样只可能是为使朋友们开心而讲的一个笑话。午饭后我们毫无惊讶地参观了八十二个房间,它们经历过一代代主人所做的各种各样的改变。米格尔把底层楼进行了彻底的修理,请人装修了一间铺着大理石地板的现代卧室,安装了蒸汽浴和物质文化设施,还开辟了我们用午餐的那块鲜花怒放的花坛。二层楼是几百年间最常使用的,那一溜房间却毫无特色,不同时代的家具听天由命地丢在那里。不过在最高的一层,仍保留着一个原封不动的房间,在那里时间忘记了流逝。
那是一个神奇的时刻。那里摆着一张床,床帏用金线绣成,用金银绸带编织的奇异床罩由于被杀死的情妇的干燥血液而依然硬如纸板。壁炉里的灰烬已经冰冷,最后一块木柴变成了石头,衣柜里的武器装满了火药,沉思的骑士的油彩画像镶在金框里,是由在那个时代没能幸运活下来的佛罗伦萨某位大师画的。不过,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新鲜的草莓香味,它居然不可思议地滞留在卧室的空间里。
夏季的白天在托斯卡纳漫长而缓慢,地平线在原地一直停留到晚上九点。我们参观完城堡时已经十点多。但是米格尔坚持要带我们去圣方济会教堂看皮耶罗·德拉·弗兰切斯卡的壁画,然后我们在广场的葡萄架下喝了杯咖啡,进行了愉快的交谈。我们回来取行李时,发现晚餐已经做好,我们只好留下来用晚餐。
我们进晚餐时,在只有一颗星的锦葵色天空下,一些孩子在厨房里点上几个火把,跑到黑暗的楼上去探险。我们在餐桌上听到了他们那种野马般奔跑爬楼梯的声音,门扇的呻吟声和在黑暗的房间里呼唤卢多维科的快乐叫喊声。我们留下来过夜的坏主意就是他们想出来的,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高兴地支持他们的提议。我们没有正当理由对他们说不同意。
和我的担心恰恰相反,我们睡得很好:我和我妻子睡在底层一个房间里,我的几个儿子睡在隔壁房间。他们两个的思想都是现代的,毫无鬼怪的概念。我一边设法入睡一边数着客厅里的钟表打让人失眠的十二下,同时想起了那个放鹅妇人的可怕警告。不过,我们实在是太累了,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直到天亮。醒来时已经七点多,灿烂的阳光透过窗口的爬藤植物照射进来。在我身边,我妻子正在清白无辜的人们的平静海面上航行。“真蠢,”我对自己说,“如今仍然有人相信鬼怪存在。”直到这时新摘的草莓的香味才使我颤抖了一下。我看到壁炉里的灰烬已经冰凉,最后一块木柴变成了石头,三个世纪以前的愁容骑士的画像从金框上望着我们。原来我们不是睡在前一天夜里睡的底层的房间里,而是睡在卢多维科的卧室里:飞檐和窗帘挂满灰尘,床单浸透了他那可恶的床上的依然热乎乎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