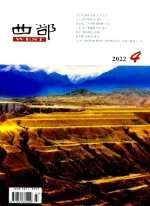巴西逍遥游
胡续冬
初到萨尔瓦多
几年前的一个夏夜,我乘坐VARIG航空公司一班登机秩序混乱到了极点的红眼航班飞到了传说中的好景之都、距巴西利亚一千五百公里远的萨尔瓦多。
大概很多中国人听到萨尔瓦多的时候都会以为是中美洲的那个弹丸小国,那显然不是我去的这个萨尔瓦多。我所去的萨尔瓦多虽然名字和那个弹丸小国一模一样,但它却是巴西巴依亚州的首府,一座在巴西人见人爱的东北部沿海城市。外国人心目中巴西的象征地是里约热内卢,其实只有巴西本国人才知道,萨尔瓦多才是真正的巴西精神的源头。1501年,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加初次登陆此地。1763年以前,这里一直是葡萄牙在南美殖民地的首都。萨尔瓦多历史上曾经是南美黑人奴隶贸易的中心,因此,几个世纪以来,整个巴依亚州,尤其是萨尔瓦多市的文化受黑人影响极大。萨尔瓦多是著名的桑巴舞的真正发源地,除此之外,它也是巴西重要民族音乐形式的发源地,黑人武术卡普埃拉的发源地,巴西狂欢节的发源地,民族佳肴豆饭的发源地,城市暴力的发源地,以及巴西人民懒惰、热情、不守时、拖拖拉拉等“民族性格”的发源地。
凌晨三点多到达萨尔瓦多国际机场之后,一辆事先电话预订好的出租车带着我们穿过了几乎长达三公里的竹林大道,在丘陵中迂回了一番之后,终于开到了惊涛拍岸的海边。萨尔瓦多不愧是一座不夜城,即使到了凌晨,滨海大道依然华灯灿烂,几座十八世纪的古灯塔依然面朝大西洋放射出刺目的强光,临海山坡上结构混乱的贫民窟依然灯光万点。
我下榻在电话预订的一家华人客栈。这家客栈虽然距离本市最秀丽可人的巴哈海滩仅二百米远,可以从窗口瞥见一角海水,但是不知何故,有着优良卫生传统的华人居然经营出这么肮脏的一家客栈:狭小的客房潮湿阴暗得如同军统特务把持的渣滓洞囚室,床单上毛球横生,枕头上散发出一股人类泌尿系统分泌物的气味。最要命的是,年久失修的拉窗根本无法拉上,凌晨的潮声此起彼伏,残酷地粉碎了我的睡意。我决定,明天一早就去投奔巴西人民经营的客栈。
萨尔瓦多的巴哈区
由于不堪忍受华人客栈的肮脏,我一大早起床就开始在巴哈街区寻找新的落脚点。巴哈区不愧是LonelyPlanet重点推荐的驻足地,清新秀丽的小街上到处都是造型各异的葡式家庭小客栈。我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最中意的一家:“海洋之星”。这家客栈为蓝白双色搭配,阳光下极其鲜亮,房间内洁白无暇,葡式拉窗正对一街的本地佳丽。这是一家地地道道的家庭客栈,主人米盖尔和法比娅娜的厨房,客人可以随意使用,完全可以去海边的市场买回海鲜然后自己在主人的厨房中大摇大摆地烹制,非常之DIY,让我想起西班牙电影《露西娅和性》里那家海岛客栈。
萨尔瓦多的形状是一个标准的“V”字形,“V”字的西侧是一个名叫万圣湾的内海,东侧是碧波万顷的大西洋,巴哈区正好位于“V”字的尖嘴上,独揽三面海景,实为绝佳之地。“海洋之星”客栈距离万圣湾和大西洋均只有百米之遥,随时可以从客栈散步到位于万圣湾和大西洋岬角处的巴哈灯塔。巴哈灯塔是一座十八世纪的古建筑,建在一座古堡上,古堡现在是一座殖民时期海军战绩博物馆,但灯塔依然行使着它亘古不变的引航职能。巴哈区有两个海滩可以供游客戏水:位于大西洋一侧的巴哈湾是冲浪、潜水的好地方,但由于岩石较多,不可游泳;位于万圣湾一侧的巴哈旧港风平浪静、水清沙净,是本地人游泳的上好去处。我去巴哈旧港游泳的那天适逢好天气,沙滩上挤满了本地黑人和世界各地的游客。和里约美女如蟹的海滩不同的是,巴哈的海滩上几乎不见美女,倒是有很多本城无所事事的青年在集体练习黑人武术卡普埃拉,沙滩上遍布漆黑到底的肌肉男在倒立、翻跟头、腾空入浪。在巴哈旧港的沙滩上一定要注意防范一群本地狡黠小儿的“偷袭”,他们往往趁你不注意朝你的脚上猛浇凉水强行为你洗脚,然后向你索要洗脚费。
萨尔瓦多的焖海鲜驰名南美,尤其是红焖海鱼,其鲜辣之味堪与川菜媲美。在巴哈区,有一家红焖海鱼做得极棒的餐厅,名字叫“螃蟹”,这个莫名其妙的名字一开始让我以为是一个螃蟹市场。这个吃鱼的“螃蟹”餐厅还有更无厘头的一面,餐厅里所有的店小二一律穿着上面印有巨大的“店小二”字样的制服。当然,其无厘头的程度显然不及“海洋之星”客栈里一条狗的名字,这条一脸苦相、随时悬吊着口水的沙皮狗明明是条公狗,但却有着一个响亮的名字——“母狗”。
萨尔瓦多的教堂
从巴哈坐公车不到半小时,就可以到达萨尔瓦多老城的中心——证道广场。萨尔瓦多的老城大致可以分为高城和低城两部分。高城位于海边的山丘上,是十六世纪以来巴西东北部的天主教文化中心,集中了数十座富丽堂皇的古教堂和大片的殖民时期贵族居所、博物馆。低城在海边,历史上是贫民的聚居点,现在依然密布着范围巨大的贫民窟,混乱的古旧民房与装饰简陋的大厦交错,颇似广州、深圳的城中村。
高城绝对是一个让人不忍离去也很难顺利地离去的古建筑的迷宫。走在十六世纪的石板路上,一座座建筑风格各异的宏伟教堂完全像是在给人上欧洲建筑艺术史的课程:时而是仿古罗马的巴西利卡风格(巴依亚大天主堂),时而是巴洛克风格(圣多明哥教堂),时而又是洛可可混合葡式庭院风格(圣恩教堂)。在这些密集的教堂中,最豪华的当属圣弗朗西斯科大教堂。这座建于十七世纪早期的大教堂无视当时信徒的贫困,居然拥有两个纯金的尖顶和一个重达八十公斤的纯银枝形吊灯,用于内部装饰的蓝色瓷砖也全是从葡萄牙运来。由于天主教在十七世纪将盛行于萨尔瓦多的巴西黑人宗教坎东布雷教宣布为邪教,并对其黑人信徒加以迫害,修建圣弗朗西斯科的黑奴们心中怀着极大的怨愤,因而他们在教堂的装饰上动了很多小手脚:一些小天使的脸看上去更像黑人小孩,另一些小天使则悬垂着巨大的阴茎,还有一些圣女浮雕被雕成了孕妇模样。圣弗朗西斯科大教堂是专供修士和贵族阶层做礼拜用的,平民和黑人在里面仅被允许站在角落里。为了让更多的平民也沐浴天主的荣耀,教会又在圣弗朗西斯科大教堂的一侧修建了圣弗朗西斯科第三等级教堂,专供平民参拜。随着十八世纪末葡萄牙在巴西殖民地的首都由萨尔瓦多迁往里约,萨尔瓦多高城的宗教中心曾经一度衰落,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历史并不是很长的圣弗朗西斯科第三等级教堂居然被埋在了地下,直到1930年一个电线工人在铺线的时候再次发现了它。第三等级教堂重见天日之后,人们不得不为当时教会所掌握的财富叹服:即使是这样一座供草根阶层使用的教堂,里面的内壁居然也饰有大量金片。
萨尔瓦多的贝鲁利诺和低城
当我从萨尔瓦多高城的教堂区走出来的时候,海雾迷蒙的天空开始飘起了细雨,而此时,我也恰好走到了高城的贝鲁利诺街区,一个古民居的露天博物馆。贝鲁利诺在葡萄牙语里的意思是“刑场”,在殖民时代,这里是威震拉丁美洲的黑奴刑场和黑奴贩卖中心。很难想象,在距离圣恩浩荡的圣弗朗西斯科大教堂仅数步之遥的地方居然是巴西黑人们血海深仇的源头。巴西是南美洲最后一个废除农奴制的国家,直到1835年,拉美的其他地方已经扬起了自由平等之旗,在巴西,肆意给黑人用私刑、蹂躏黑人女奴还都是合法的行为。在今天的贝鲁利诺,依然可以见到用来捆绑黑奴加以鞭笞的石柱,而在黑奴拍卖场的遗址上,依然可以见到立柱上标注的拍卖底价:一头产奶的牛等于五个黑人男奴,一个黑人男奴则等于五个黑人女奴。
从高城坐上一个造型古怪的电梯,就可以来到亘古不变的贫民窟低城。低城的海滨立着一个奇异的雕塑,也是萨尔瓦多的标志性雕塑之一:两个以奇妙的角度嵌合在一起的黑人屁股,据说象征了萨尔瓦多的丰饶。屁股雕塑旁边就是著名的摩代罗市场,这个混乱得无以复加的大自由市场是贩卖萨尔瓦多各类手工艺品的中心,全世界的游客都是从这里把具有萨尔瓦多特色的巴依亚服饰、卡普埃拉乐器、盛装黑人雕塑、吊床等物什带回国的。除此之外,市场上还有很多身着巴依亚镂空白裙的黑人大妈在摆摊出售萨尔瓦多风味的甜辣油炸小点心,有一款加有虾肉、红辣椒酱的小炸饼颇似我国的肉夹馍,另一款椰蓉做的炸糕则酷似我老家四川的糍粑。
在摩代罗市场,我老是被人当成日本人,无数小贩围着我大叫“啊立嘎多”,我被弄得无比郁闷,就拉着朋友到马路对面的街心小花园清静清静。这时,原本寂静无人的四周慢慢聚拢了几个无所事事的黑哥们,而对面,一个卖点心的黑人大妈则不停地朝我挥手让我过去。当我不知所措地走到大妈那里才知道,原来我周围聚拢的是一帮经常在摩代罗市场周围行凶的劫匪,由于我和朋友孤零零地坐在那边,如果我们晚过来几分钟,绝对已经被打劫一空。直到这时我才想起早上刚刚看的LonelyPlanet里面的一句话:“高城由于旅游警察密集绝对安全,而低城,尤其是摩代罗市场周围,则遍布小偷和劫匪,千万不可落单。不过,总会有好心人帮助你。”一时间,我对LonelyPlanet提供信息之准确佩服得五体投地。
去富尔奇海滩看海龟
富尔奇海滩(意为“猛滩”)北距萨尔瓦多市区八十公里,是萨尔瓦多最迷人的海滩,足足有十一公里长,银白色的沙滩被十一万棵椰子树环绕,完全是猪样小朋友麦兜的梦想之境。我去富尔奇海滩的头一天萨尔瓦多还大雨倾盆,出发的时候却已是天光大好。老天有眼,我也和麦兜小朋友一样,早车去晚车返,开开心心地在“盗版马尔代夫”过了一天。
富尔奇海滩最著名的其实不是美景,而是海龟。巴西东北部海岸线生活着全球数目最庞大的野生海龟群,但是,由于吃海龟蛋、取海龟壳等恶劣行径屡禁不止,野生海龟的数量在逐年下降,为此,巴西环境保护总署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在东北沿海实施“海龟计划”,有组织、无功利地保护野生海龟,营造海龟与人之间亲密、和谐的关系。富尔奇海滩就是推行“海龟计划”的一个重点区域,该计划在以富尔奇海滩为核心的五十公里长的海滩上每年保护着五百五十个海龟巢穴。我这次去富尔奇海滩的季节不对,没有赶上头年9月到次年3月的海龟产卵期,看不到母海龟埋蛋孵化、小海龟摇摇摆摆爬向大海的奇景,只能在“海龟计划”的核心陈列区看到一些供游客了解海龟生活习性的示范龟,不过,这数十只身长十厘米到一百五十厘米不等的大小海龟已经足以满足我观察海龟探头的爱好了。在富尔奇海滩观看海龟的世界各国游客都对这些憨态可掬的龟哥们表示出了极大的友善,唯独有一个白领模样的来自南中国广州或深圳一带的女游客,为了和海龟头频频合影,居然用小树枝抽打海龟,引起了在场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也令同是中国人的我深感羞愧。
我在富尔奇海滩遇上了一件神奇的事情。当我和朋友在椰林碧水之间尽享南美阳光、在沙滩上和招潮蟹玩捉迷藏游戏的时候,一条不知谁家的大黄狗来到我们身边,死活都不愿离开我们。这条来历不明的神犬趴在我们身上撒娇,抢我们的椰子水喝,还残忍地扒开了我做的沙雕裸女的胸部,简直是“富尔奇一霸”。我们正不知怎样甩掉这只小霸王的时候,一伙本地小混混从我们身后走过,趁我们不注意,试图顺手牵走我们放在沙滩上的东西。这时,只见“富尔奇一霸”狂吠了数声,扑在小混混们身上大力撕咬,吓得他们丢下我们的东西落荒而逃。为了奖励这只神犬,我使出刨坑神技抓了一只狡猾的招潮蟹给它吃,没曾想神犬不但没有吃到这顿美味,反倒被小螃蟹夹得痛哭不已。
萨尔瓦多的依达帕里卡岛
据说到萨尔瓦多不去周围的海岛会是一生的遗憾,于是,我就来到了位于低城北部的一个小偷云集、抢劫案频繁发生的险恶渡口,登上了一艘状如UFO的快艇在海浪中疾速穿梭。快艇上的气氛有些诡异,我身后一个黑社会模样的人在用一个板砖手机给岛上通话:“有两个日本人要上岛,但是有一个好像会说葡语。”我意识到这是在说我和我的朋友,顿时觉得有些紧张。二十分钟后,快艇到达了依达帕里卡岛。还好,没有任何黑社会上前迎候,倒是碰上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出租汽车司机,带着我们在环岛公路上溜达。
依达帕里卡岛位于萨尔瓦多以西的万圣湾,是萨尔瓦多附近海域面积最大的岛,有若干个古色古香的小镇(其中一个小镇依达帕里卡镇有萨尔瓦多最古老的教堂),居住着一万八千个安享岛上丰厚的果蔬和畜牧资源的巴依亚黑人。环岛公路风光奇好,周围不见人影,只有白牛漫步,鹦鹉啁啾。
我们在一个名叫“一路平安”的海滩村庄下了车,到沙滩上晒了半天的太阳。岛上的海滩比萨尔瓦多城中海浪最小的巴哈海滩还要风平浪静,确实是在海中畅游的好地方,可惜,“一路平安”的海滩不是纯沙质海滩,虽然岸上看上去黄沙灿灿,可一入海水就会发现脚底其实是滩涂地。有滩涂地的海滩海水自然不会特别干净,因此,我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沿滩拾贝上。小村毕竟是小村,没有过多的游客前来游览,岸上的海螺、海贝、海星散落一地也没什么人来拣。我以坚韧的Discovery精神顶着烈日研究了形状不一的海螺里寄居蟹的生活习性,颇有心得。
午后,海滩上的农家海鲜店为我们端上了本地最负盛名的菜肴:红焖龙虾。岛上出产的龙虾个大壳薄,仅仅一个龙虾就对我们的胃发起了极限挑战。饱餐之后我再也无力研究寄居蟹,一个电话叫来了老实司机,快艇急驰回到了萨尔瓦多市内呼呼大睡。
神秘的坎东布雷之夜
在萨尔瓦多城中,有一个去处名唤Casa Branca,和那个众所周知的“卡萨布兰卡”很相似,相当于英语里的“WhiteHouse”。但这里可不是傻人辈出的米国白宫,而是萨尔瓦多非—巴融合宗教马孔巴教举行宗教仪式坎东布雷的中心,也是南美最古老的德黑诺(坎东布雷仪式的圣殿)。
当葡萄牙殖民者把大批黑人奴隶从西非优鲁巴部落贩运到巴西的时候,奴隶们除了给这片丰腴的土地带来了艰辛的劳动,还带来了崇尚万神与信徒在梦幻状态中进行交流,包含了极大的巫术成分的伏都教。伏都教登录美洲之后,与基督教的一些教义相结合,形成了巴西黑人特有的马孔巴教,而马孔巴教在其老巢萨尔瓦多最有名的仪式就是现在已对游人开放的坎东布雷仪式。数百年来,欧洲殖民者强行在南美推广基督教并采取各种措施试图消灭巴西黑人自己的宗教,但其结果只不过是使得基督教里的神灵、圣徒和来自西非的优鲁巴部落的诸神产生了对号入座关系。马孔巴教及其仪式被认为是研究南美文化融合现象的最为重要的标本之一。
在萨尔瓦多的最后一夜,我来到了Casa Branca,参加了一次云山雾罩的坎东布雷仪式。在仪式上,一群本地黑人妇女身着白色镂空长裙,唱着优鲁巴语的圣歌曼妙地起舞,男人们则奋力敲打复杂、强劲的非洲鼓点。女人们所跳的舞蹈有着典型的西非舞姿,手势极为丰富,随着鼓点的变化不时变换着摆臀、挪步的节奏。坎东布雷仪式上女人完全是主导者,男人只是一个敲鼓的工具。随着鼓点越来越诡异,一些跳舞的女人开始进入催眠状态,不停地颤动、翻腾,也就是说,按照马孔巴教的理论,她们已经在和各种神灵自由地交流。最后,一般会有一个人浑身披挂着最高神灵奥克萨拉的行头出场,宣告本次仪式在人与神的和谐沟通中结束。
坎东布雷仪式虽然允许游客参观,但绝对不许拍照,也不允许游客去搀扶催眠状态下的信徒。我虽然对仪式所包含的具体教义不甚了了,但还是深深地被仪式中神奇的音乐所吸引。据说,在坎东布雷仪式上,也有一些游客因为对鼓点声过度着迷,最后和信徒们一样进入了催眠状态。
金路古镇巴拉奇
2004年8月,旅居在巴西利亚的我陪国内来玩的朋友再度飞往里约,不过,这次一下飞机并没有在里约市内逗留,而是马不停蹄地直奔电影《中央车站》里那个混乱无比、劫匪如云的中央车站,在那里坐车前往一个传说中的天堂——古镇巴拉奇。
巴拉奇位于大里约州的西南角,和圣保罗州交界,从里约出发要在里约—桑托斯公路上颠簸四个多小时才能到达。这四个小时的路程绝对不会让人疲乏,因为公路一直从西向东在山海之间延伸,南侧是碧波万顷、银滩不绝、小岛星罗棋布的大西洋,北侧是高耸入云、悬崖与瀑布交错的群山,二百五十四公里一路好景不绝,实在是巴西自助游的一个必选项目。巴西的长途汽车上一般都有厕所,但不幸的是,由于山路崎岖,车身从来没有停止剧烈的摇晃,很多在晃动状态下有大小便心理障碍的人将会在坐立不稳的厕所里无功而返。
到达山崖下、海滩边的巴拉奇的时候,一路的好景达到了极致。巴拉奇是一个殖民建筑的露天博物馆,在阳光之下,一幢幢墙壁洁白、门窗鲜艳的葡式建筑相互映衬,红、黄、蓝、绿互攀互嵌,形成了一个魔方一般五彩斑斓的整体,远远地看去,整个古镇比单独的一个亭台楼阁更像是一件精心雕饰打磨的艺术品。比起我曾经去过的巴西高原上的古镇比利纳波利斯,巴拉奇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传奇风韵:背后的高山山岚弥漫,面前的海湾霞雾变幻,城中古堡、教堂、民居和椰林树影耳鬓厮磨,城边大群的信天翁在银沙、彩船、白帆之间飞翔,好一个地老天荒自得其乐的温柔乡!
巴拉奇原是圭亚那印第安人的地盘,十七世纪在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州发现了黄金之后,巴拉奇一带成了从里约到那里的黄金之路上的一个必经之处。万恶的葡萄牙殖民者把无辜的圭亚那印第安人赶进了暗无天日的深山,并把巴拉奇修建成了一个富甲天下的金路重镇。时至今日,城中几处辉煌的教堂仍能依稀见到巴拉奇当年的富庶。据史书记载,1711年驻扎巴拉奇的弗朗西斯科上校从巴拉奇出发去解救被法国军队包围的里约,他的舰队足足带了一千箱蔗糖、两百头牛和六十一万个金币。1720年代,随着另一条更加便捷的金道开始启用,巴拉奇迅速地衰落了下去。如今,巴拉奇完全是一个自助游的圣地,葡式民居几乎全部变成了葡式家庭旅馆,古老的街道上遍布来自欧洲和阿根廷的背包旅行客,如果独身来到巴拉奇旅行的话,据说在这个醉生梦死、恍若隔世的地方,背包客之间的一夜情发生率几乎高达百分之九十。
“五姐妹客栈”
在古镇巴拉奇,我们按照著名的LP(Lonely Planet)的指引,住在了一家乖巧别致但却有个奇特的东方庭院的“五姐妹客栈”里。按照LP的介绍,这个客栈是由温柔可人的哈盖尔大姐和她的四个妹妹苦心经营的,有着令人浮想联翩的家庭气氛,尤其令我想起武侠片中常见的“相思女子客栈”之类的名称。住进去了之后我发现,因LP而变得全球闻名的哈盖尔大姐果然温柔体贴,客栈的氛围倒也是淫逸迷幻,不过她的四个妹妹长得实在是“浮想联翩”的终结者。
“五姐妹客栈”和巴拉奇小镇上其他五十多家家庭旅馆一样,俨然是“全球一家亲”的架势,院子里充斥着英、西、意、德数种语言和性感的法国狐臭,坐在阅览室里喝咖啡的人们几乎每人手持一本不同语言版本的LP在筹划消磨时光的最佳方案。我不得不在这里表扬一下我国人民至今还没有引进的LP,自从我的朋友从巴黎国际机场给我买了一本LP带来之后,传说中的LP给我带来了无以复加的便捷。像巴拉奇这种巴掌大的小镇,LP居然给出了带有街道名称的详细地图,并且还列有街道的各种异名,其对小旅馆、小餐馆等资讯细节的介绍也详细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在巴拉奇的一些LP上榜上有名的廉价小餐馆里,我随时可以看见手持LP的各色人等鱼贯而入,颇像特务接头。
在萨尔瓦多老城的时候,我本以为自己对殖民风格的建筑已经产生审美疲劳了,但是巴拉奇小镇上的老民居还是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审美神经。巴拉奇的民居比我以前见过的殖民建筑群保存得更加完好,色彩搭配也更加绚烂。更加神奇的是,巴拉奇本来就在海边,但城中却有一条穿街过巷的古运河,该运河在城中最有沧桑感的马特里斯教堂广场前面入海,把小镇活生生弄成了一个南美威尼斯。
由于旅游开发比较成功,巴拉奇的很多古街成了商业街,街上全是清一色的特色小店,兜售本地艺术家的艺术品和香蕉干、甘蔗酒等本地特产,但比起我国的大理、丽江、阳朔等地,巴拉奇的旅游小店内部装修品味更加高古醇厚,很有遭人唾弃的“知识分子趣味”。巴拉奇人民的“知识分子趣味”的确比较浓郁,小小一个居民不过三千的小镇,居然有一个和我国万圣书园一样庞大而故作雅趣的书店,书店中的沙龙会所也比万圣书园的所谓“醒客咖啡厅”更加有所谓的“格调”。我去的那天在书店的沙龙里正好有一个关于本地印第安文化的多媒体艺术展,无数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在里面悠闲地社交,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门外,被葡萄牙人几百年前从巴拉奇赶到山上去、至今还在那里艰辛生活的印第安人却在沿街摆摊、乞讨,晚上则衣不蔽体地睡在街上。
在巴拉奇出海
来到巴拉奇的第二天一早,我和朋友在“五姐妹客栈”享用美味的葡式早餐,并和隔壁的一个英国独行妹交流巴西背包游经验,这时,院子里突然走进来一个膀大腰圆的肌肉男,问我要不要出海,说是已有两个法国妹妹订了他的船出海,我和我的朋友同去的话可以少付一点船资。在巴拉奇出海也是巴西背包游的一个经典项目,我正有去传说中的“巴西蓬莱”溜达溜达的企图,但鉴于该肌肉男相貌实在太凶悍,同时亦有强行拉客的嫌疑,我怀疑是歹人,不敢贸然答应。毕竟,来之前有很多人告诉过我南部海滩的很多船夫都有洗劫游客将之弃置荒岛的恶名。肌肉男看出了我的顾虑,赶紧用德语口音浓重的英语告诉我他其实是一个瑞士人,因为喜欢这个天堂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娶妻生子生活了十多年。“五姐妹客栈”的主人哈盖尔大姐也告诉我此肌肉男是本地十大杰出移民兼十大杰出船夫,绝对值得信任。于是,我和朋友就愉快地上了这个名叫克里斯托弗的肌肉瑞士男的非贼船。
巴拉奇的码头彩船密集,除了游船,还有很多本地一大早出海打渔归来的渔船,码头上充斥着鳗鱼、金枪鱼、龙虾和章鱼,看着实为眼馋。开船之后回望水边的巴拉奇古城,但见离海滩最近的多雷斯教堂倒映在洁净的海水中,仿佛虚构之境。
巴拉奇一带的地形非常复杂,周围有一百六十多个岛屿,岛上植被茂盛,野生动物资源极为丰富,加上地处内海大岛湾,风平浪静,水波不兴,是出海游岛、潜水、深入动物世界的上好去处。十六世纪初大航海家亚美利哥航行到今天巴拉奇一带海湾的时候望岛兴叹,在航海日志中写道:“哦,上帝啊,如果这世上有天堂的话,它一定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到如今,这种毗邻天堂的感觉仍然存在。克里斯托弗的船很舒适,有一个铺着防潮垫的顶层,可以趴在上面晒太阳,不但视野极为开阔,还会有信天翁的翅膀从身上掠过。我和朋友本想占据顶层,但与我们同船出海的两个极其美艳的法国妹居然是一对同性恋,她们一开船就甜甜蜜蜜地趴到了船顶上厮磨,我们只好郁闷地在待在底层,被口水佬一样的克里斯托弗抓住聊天。
游荡在巴西蓬莱
克里斯托弗不愧是十大杰出船夫,熟悉方圆数百里海域的每个犄角旮旯。他带我们去一些船迹罕至的水域喂鱼,只要捏着饼干把手伸入水中,就会有成百上千模样花哨的海鱼在你的手心里顶来顶去。他还带我们去了一个据说他平均每周能看见两次野生海豚起舞的水域,不过当天运气不好,没有看见一只海豚,倒是看见一群飞鱼嗖嗖掠过海面。
巴拉奇周边海域的确像是传说中的蓬莱,千米一大岛、百米一小岛,由于地形、土石构造和面积的差异,每个岛的植被大有不同。有的岛上全是典型的热带常绿阔叶林,有的则是一堆光秃秃的怪石,上面神奇地长满了仙人掌。克里斯托弗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原始森林保存完好的岛屿,要我们上去试着穿越一下本地人在林中踩出的小径,体验热带雨林风貌。我们和那对法国女同性恋情侣走在巨树参天的林中小路上的时候,四面群猴乱啼、鹦鹉惊飞,女同性恋之男方本来一直走在前面,当密林中传来类似巨蟒滑动的声音时,“他”开始害怕起来,停下来冷冷地对我说:“你是男人,应该走前面。”我和朋友都注意到“他”说“男人”二字的时候饱含仇恨和不甘。
巴拉奇的几乎全部海岛都是私有的,很多海岛上都有造型雅致的私宅,有的“岛主”在岛上辟有咖啡馆、酒吧和餐厅,供游人消遣时光。有一个海岛上建有本地监狱,在蓝天碧水绿树银沙的映衬下,该监狱居然像个疗养院一样诱人,据说,因为地处距离其他岛屿都很遥远的一个小孤岛,该监狱的越狱率为零。克里斯托弗带我们去了一个很邪门的小岛,岛上松萝挂树,芦荟丛生,浅浅的海滩清澈至极,一间小巧可人的酒吧在沙滩边上向偶尔到来的游人敞开,里面备有若干酒水,但是居然没有一个人,只有一只小黑犬看护着这个袖珍天堂。游人消费完了酒水,按照酒单上列的价格把钱留在狗窝旁边的一个小篮子里就可以了。岛主放心地把岛上的财务大权全部交给了小黑犬。据说,在酒吧里开了酒水如果不放钱进小篮子的话,小黑犬会凶相毕露,阻拦赖账者登船离开。克里斯托弗说该岛主手中有十个岛屿,这个岛是最小的,因此懒得上来打理,每周上来一次送货并到小黑犬处取钱即可。
我们和克里斯托弗在海上整整厮混了一天,到最后我们发现不仅“巴西蓬莱”无比诱人,就连克里斯托弗自己也具有诱人的传奇性。这个唐僧一样的家伙不停跟我们絮叨他的身世。此人出生于瑞士的一个人口只有五百人的小镇,巴拉奇是他一生中定居过的最大的“城市”。他由于不习惯人情淡漠的瑞士小镇,中学没毕业就出来闯荡世界,足迹遍布东欧、东南亚、澳洲、加勒比,最后选择了巴拉奇定居了下来,和一个山上的印第安女子生了一个标准的印第安小酋长造型的儿子。他已经完全不能习惯欧洲的生活,前些年回瑞士探亲的时候,在火车上按照巴西小镇人民的习惯朝陌生的人们问好致意,却被家乡的人们当做神经病冷眼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