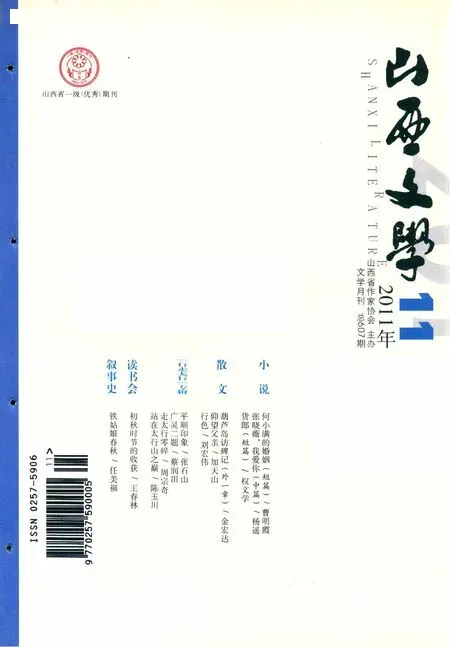哈金笔记
薛 荣

《自由生活》:除了梦想,还是梦想
选择简洁朴实的文笔,我认为不是因为哈金放弃了母语,斗胆用英语写小说造成的。长期对英美文学的攻读让他用洋腔洋调玩点词藻技巧肯定不在话下。有记者问过他,哈金强调了自己是在波士顿大学教写作的,言下之意是,能教的写作,无非是一些写作技巧而已。玩技巧谁不会呀,但哈金心里有一个“太阳”和两座“大山”。“太阳”是由美国文学传统延伸出来的“伟大的中国小说”这个概念;两座“大山”分别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
我有个画家老友,你逼他写个千把字的画论,他捏着圆珠笔,满脸赤紫,眼光不时地朝窗户看,死了的心都有了,就是整不出几个句子,但你让他与评论家灯下对谈,毕加索八大山人雷诺阿,线条色彩黄金分割点,弄一本厚厚的访谈录也不过七个工作日。哈金的“文学宣言”都是面对媒体的话筒随口一说,但我还是相信此乃一个杰出小说家发自肺腑的内心感言。为了让中国的同行和读者信服,哈金强调不光是他本人,许多当红的美国小说家现在都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的作品上下功夫,对流行的博尔赫斯、昆德拉和杜拉斯之流,他指出他们不过是独辟蹊径,开垦出一块属于自己的文学自留地而已。真正的敬仰和皈依,应该是文学这棵大树粗壮的主干而非纷繁的枝叶,由此哈金给出关于伟大的中国小说的定义:“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正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
看如今的世道,这真像一个关于中国小说的神话,不过哈金即使不这样说,他也面朝着如此灿烂的“太阳”一步一个脚印地跋踄着,长篇小说《自由生活》就是他打造的一座厚重的里程碑。作者从小说主人公武男自己终结了政治学博士学业,转而从进餐馆打杂开始,承担起了一个移民美国的三口之家的生活重担。故事的进程覆盖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但没有直面重大历史事件,而是在柴米油盐之间夯实了小说的基础。一切都是为了在异国他乡生存,几乎所有为生存而做出的努力都是形而下的,令人身心疲惫,但武男终究是个有梦想的男人。他的梦想成双:一为对初恋女友蓓娜的思念,二是对写作的向往,用武男的话说,写作于他,是“做点有钱人做不到的事”。工作的劳累曾长久地压迫着他,与文坛的若即若离也使他讨教无门,内怯三分,以至自我怀疑。他曾严厉地责问过自己:“你一定要过文学生活才能写出文学作品吗?”在生活和写作之间,武男挣扎着;在妻子萍萍和恋人蓓娜之间,武男痛苦着;在遥远的中国和正生活着的美国之间,武男悲愤着,感叹“要是我们能从血里把故国挤出去就好了”;在汉语和英语之间,武男的笔管内充满了畏惧。无论是《中国可以说不》的海外华人讨论会,还是友人元宝的山间画室,哈金最多采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了观念的冲突和人情世故。作为美国朋友,珍妮特和戴夫的善良纯真令人动容。华人社团的活跃分子,年轻的爱国者洪梅一直和武男彼此误解与对立着,闹得最僵时,为了一只给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送绿豆汤弄丢了的钢精锅,武男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了她,但为了救治珍妮特和戴夫从国内领养的孩子海丽,洪梅的政治热情一下子焕发出人性的光彩,帮助患白血病的海丽找到了良药。在小说中,洪梅虽说是个次要角色,她身上单纯的爱国主义思想确实与武男的怀疑主义态度格格不入,最终她还是得到了武男的敬重。由于极为生活化的结构布局,小说中诸多的情节曲折与勾连非常自然,甚至当武男写诗遇到困难时,用中奖得来的飞机票回中国去看蓓娜,他的意图是:“他并不打算与她重续旧情;他只需要看到她那张脸、听到她的声音,来重新点燃他的热情,好使他能写出诗来。为了自己的艺术,他需要看到一个理想女性的身影,就像一个画家使用一个模特儿。”从政治学博士生到一个真正诗人的路途是何其遥远啊,武男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学位,到中餐馆的厨房里打杂,他历尽艰辛,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餐馆和别墅,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他自由了,但“要是你不知道怎么利用自由,那么自由就是没有意义的”。
为了自由的意义,一个中国男人从歌颂相濡以沫的老婆入手,用英语写出了哀婉的诗章。
哈金曾经坦言,他在动笔写一个大作品之前,总会选定一部或几部经典,作为标杆和参照。当初为了写作长篇小说《疯狂》,他把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看了四遍,但写《自由生活》时,哈金选定哪些作品作参照我没看到相关的说法。也许已不用多说了。同样的对革命的祖国命运的思考,同样的是男主人公对分行写作的喜爱,同样是结尾附录了诗歌,还有武男夫妇对电影《日瓦戈医生》的推崇,我猜测哈金是用这一部三十三万字的小说在向帕斯捷尔奈克的《日瓦戈医生》致敬,同时他要致敬的还有他的家人,他把《自由生活》题献给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因为“不可能不把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经历和人物放进去,这是肯定的,但绝对不是自传”。
《好兵》:方寸之间有天地
短篇小说集《好兵》是哈金写作的分水岭。自此之后,作为出版过三部诗集的诗人哈金隐入内心,而小说家哈金神情憨憨地步入前台,初次亮相,手中就有了一个美国笔会海明威奖。这对于用英文写小说的哈金不啻是个巨大的鼓励。要知道,为了是用中文还是用英文写作,哈金曾长久地纠结过,犹豫过,这在长篇小说《自由生活》里都有过笔涉自我的心理剖析:“用英文进行创作,在新大陆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做一个除了服从自己的意愿之外不屈从于任何别的东西的真正独立的人,是要披荆斩棘的,实际上,他害怕这些障碍。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在想方设法地逃避搏斗。这些年来,他把全部精力和热情都投入经营餐馆,付清了买房贷款,然而,摆脱债务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他再也没理由不写作、不去做真正该做的事了……他是个逃兵!他为此而对自己感到厌恶!”
十二个短篇故事,哈金写了三年,之后书稿在诸多出版社之间流浪,退稿的借口看似都挺专业的,有的说没有市场,有的强调它的文学气息太浓了,甚至太诗意了些。最终,一家现在倒闭了的小型出版社接受了这本书。在寻求出版的几年里,哈金肯定也有过做一个“逃兵”的想法,这种感觉太刻骨铭心了,多年后,他把自己这一时期的内心挣扎借用到了开餐馆的业余诗人武男身上。实事求是地说,写小说的哈金是个“好兵”而非“逃兵”,短篇小说集《好兵》的出版和得奖显示了美国文坛良好的氛围与评介机制。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为大众所熟知:前苏联和美帝国主义这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等是第二世界;中国和众多贫穷落后的亚非拉国家是第三世界,在这之中,红色中国是当之无愧的“带头大哥”。《好兵》所写的,就发生在两个世界对抗的中国东北“反帝、反殖、反霸”最前线的事情。这是独具慧眼的选择。难怪美国笔会海明威奖的评委们都肯定说“哈金开阔了美国文学的新领域”。和哈金差不多岁数的国内军旅作家,像李存葆、朱苏进等的作品,那完全是两个向度上的、不一样的风景。
去国经年的哈金是美国作家,他写的英文小说翻过来之后读上去却不像是翻译小说,而似大陆文坛上的“久经期待”之作。前几年,研讨会访谈录流行卡佛,大家说来说去,但真正的影响没有体现到短篇小说的写作上来。更早的时候,有个老翻译家叫戴骢译的《骑兵军》影响很大,它行文的风格、刻画的力度和冲击力令人惊叹,我们都检讨说,温吞水似的扯淡好没意思,啰里啰唆讲故事也太没劲了,我们也要搞点“铁与血”的生命之歌,但搞来搞去,个个都搞回到自己的老路上,扑腾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出人意料的是,哈金的《好兵》和巴别尔的《骑兵军》却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好兵》的台湾版序言里,哈金坦陈他读了《骑兵军》之后,“我觉得自己可以写一本类似的书”。这样的感觉源自于他不满十四岁就在东北边境开始的军队生活。在中苏肯定要打一场大战的心理阴影下,少年哈金对在军营里的成长过程刻骨铭心。《好兵》“这本书讲的是集体的故事,是军人和老百姓们的喜怒哀乐,跟我个人的自我无关。故事里的事件和人物基本上都是真人真事,只不过出现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被我捏到一起,改名换姓,东接西连,构成各种各样的人物和情节。”素材是现成的,但怎么写却历经了从巴别尔到契诃夫的过程。在短篇小说《报告》和《字据》这两个巴别尔风格的作品之后,哈金在写作中体会到了巴别尔的极端性与局限性,仍旧在伟大的俄罗斯小说传统的范围内,他自然地转向了契诃夫,阅读契诃夫的体会让哈金的写作更为开阔和自由。
虽然有些短篇小说的基本构架有着小小说的简陋,但哈金还是有能力通过多层次的人物矛盾来增强小说的厚重感。典型的是军事主官和教导员指导员之间的勾心斗角,笔墨虽少,但烘托的效果不弱。老调的“军民鱼水情”哈金是唱了又唱,其中有豪爽的朴大爷,办了两次的寿宴富有喜剧色彩,而全民军事化之下的民兵连长龙头的遭遇却是一场悲剧,正可谓有狂热的地方就有疯子,有阴谋的地方就有牺牲品。《空恋》是一个带传奇色彩的故事,几个报务员通过深夜的战备电报往来,展开了一场似有若无的三角恋爱,但一切在监听之中,结果只是一场人性的“搭错车”。有关军营里的性压抑在本书中演绎出了《晚了》和《好兵》这两个故事,前者以玩笑打赌惹出的情事,男女双方最后冲破层层阻力,成就了一段逃亡的姻缘;后者的主人公军事标兵刘福,实在管不住自己的老二,在经历了暗娼小白妖和一头据说不会怀孕的母骡之后,背着一麻袋旧报纸叛国投敌,最终死于战友的枪下。《苏联俘虏》中的警卫战士在搜寻逃跑的俘虏莱夫时,极度的疲劳让契诃夫的笔法之下,漫溢出了几百字的意识流,意趣生动,堪称意外。小说集里没有正面写女兵,较为遗憾,好在有女里女气的小白脸《季小姐》,热闹了整个新兵连。



在哈金笔下,解放军基层的军官有些还是蛮小肚鸡肠的,你弄我我弄你地搞个不停,但老红军就不一样。离休干部刘宝明虽然职位不高,每天不过是在大门口跟别人下下象棋,但请他来讲《党课》,老人还是在谎言满天飞的年代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出了真话,这堂党课是失败了,但老红军铁骨铮铮的形象却树立了起来。在《辞海》中,师后勤部梁部长是又一个老红军,因是半文盲,以至于不认识作战命令上的“撤退”这两个字而牺牲了一百二十多个战友的生命和全团一半的机关枪,自己也身负重伤。特殊的经历让他即使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也对借助一部家传的《辞海》勤奋苦学的战士周文倍加喜爱。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当复员在即,由于受到向周文索要《辞海》而不得的指导员的打压,周文无法入党,最后关头,还是在梁部长的干预下,事情得到了圆满解决。临别时,梁部长送给他的忘年交英雄牌钢笔留念,周文无以回报,急中生智把自己珍爱的《辞海》送给梁部长作为纪念。初读之下,我无法不为哈金写出这样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品而感到意外,但细细一想,却又觉得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纵观哈金在《好兵》之后的作品,我认为其文学的情怀、思想的价值,均在于他的开阔和包容而非单纯的非黑即白式的对立与排斥。他自己对这个短篇极为看重,其英文小说集就是以之命名的,整个短篇小说在矛盾中展开性格,在性格中见识人性,层层递进,成功地刻画了“文革”时期一个头脑清醒、富有正义感的老红军形象,重新点燃了读者心中的红色情怀。
这样的短篇小说拿到国内来,得鲁迅文学奖那是众望所归的,但哈金是美国的什么什么院士,又拿了那么超多的大奖,我为我脑海里产生这样富有中国特色的念头感到不好意思。
《等待》:是个小经典,算不上大作品
记忆中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常有惊人之举。我读的最早的黄书,撇开手抄的《少女之心》不算,像模像样的第一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读他们出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书当时就禁掉了;之后到了新世纪,在本地秀州书局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子里,一堆随地堆放的新书中有一本湖南文艺版的长篇小说《等待》,封面做得俗气,译者和作者名字相近,有自己译自己的嫌疑,所以我拿起来没翻几下就放下了。此书后来落入一诗人手中,通读之后又结合网上资讯,诗人每逮住个写小说的,都拿此书作教材教导一番,本人不幸也罗列其中,狼狈之极,只能去图书馆借阅补课。
读后掩卷,不得不承认,这一次湖南文艺出版社又是剑出偏锋,让人刮目相看。此书极不一般,它是从美国翻译过来的,但根本不像当代美国小说;它写的是“文革”时期的陈年往事,但不同于任何所谓的“伤痕文学”代表作,也不似新时期“新写实”小说。它表述语句的简约与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有得一比,但时不时出现的七弯八扭的翻译腔又提醒读者,它终究是面向英语读者的异域之作。也可能是为了在英语读者中凸现它的东方色彩,哈金让小说主人公孔林的乡下妻子淑玉有一双“小脚”,这确实是过度虚构了,没法不承认是这个长篇小说最显眼的败笔。哈金在和黄灿然的访谈中,也被问到这个问题,但他强调了淑玉这个人物的塑造是有原型的,是一个父母辈的熟人,从而回避了问题。
但这样的美中不足,无法消磨《等待》的经典地位,虽然用哈金的话说它只是个“小经典”,而且还是横向比较意义上的说法。小说序的部分是一场孔林和淑玉离婚的预演,带出了他和老姑娘吴曼娜的情事,这种状况身处在非婚姻关系男女只能在院内散步和夫妻分居满十八年才可以单方面离婚的军医院里,众多的纠结和纷争皆在暗无声息中进行。吴曼娜是处女这一点不假,但她的感情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电台台长董迈激起了她的欢心,也伤了她的心。中苏交恶与“文革”背景,让木基市的这座军医院成了一座“白色监狱”,很多的医护人员在封闭单一的环境里得了缺爱少欲的慢性病,长期夫妻分居的孔林是个病人,失恋后的吴曼娜也是个病人,她的恋爱“空仓期”在几次借书和一次长途拉练中有了一位新人:有妇之夫孔林,而后就如许三观一次次卖血一样,夹杂在两个女人中间的孔林一次次的试图离婚,都于失败而告终。既然前途无望,在第二部分中,年岁不饶人的护士长吴曼娜与孔林丧偶的表弟相了亲,又经组织介绍,成了离婚了的军区魏副政委的候补妻子,最终却落选了。在这其中,孔林扮演的角色是很让人叹息的,他的软弱和市侩气在此表露无遗,甚至也让人怀疑他与吴曼娜的爱情。恶魔杨庚的出现可以看做是上天的惩罚,其中强奸的叙写和第三部分吴曼娜生产时叫骂的语言是最为强劲有力的,但虚无和绝望已经弥漫开来,孔林的耳边出现了一个声音,在与之对话的过程中,孔林对吴曼娜、对爱情、对自我已经彻底幻灭了,更为可笑的是,又一场等待竟然在淑玉心中升起,她希望等到得了绝症的吴曼娜死后,她和前夫能破镜重圆。长篇小说《等待》分成四个部分,随着事件的推进与人物的丰满,后一部分总比前一部分来得精彩,特别是最后几个章节,等待了十八年的孔林历经磨难,他内心敞亮却空无所有。得失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了。他只想麻木地度过一个安宁的老年。
作为经典中的主人公总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的,虽然哈金指出,“我写《等待》是让人们更深刻地了解自己,而不是了解中国。”但是你只要真正读懂了哈金笔下的孔林,读懂了中国男人,那你肯定是个“中国通”了。尹丽川认为,“孔林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失败的折中主义者和随波逐流的人。他的失败感甚至与生俱来的。他具有反思性,又缺乏理论和行动。对于旧道德,他反对却不反抗,对于新社会和新价值观,他一边怀疑一边顺从。他的怀疑不伴随行动,即使行动也是被动。”反对却不反抗——此丫头的话说得非常到位,我不补充了。不得不承认,哈金在小说人物的把握上是有一套的,不光是孔林,像淑玉这个人物形象,其实是可以拿她来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作比较的。关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对政治家是这样,对于出身农村的军医孔林也是如此。孔林从乡村出来,想过上一种真正的城市生活,虽说这种生活不过是在军医院里做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却不得不承受来自自我和社会的双重扭曲。
孔林毕竟是有妇之夫,他的等待要么是离婚成功,要么原地踏步,但吴曼娜不同了,她是单身的老姑娘,容貌中上,根红苗正,在这十八年中,她在这头,小脚老太太淑玉在另一头,仿佛是一场拔河比赛,两个女人争夺着孔林。但是,吴曼娜有的是撒手离去的机会,比如两次的相亲,但林林总总的原因,让吴曼娜“咬定青山不放松”,强制的外在规定变成了自觉的内心束缚,相爱成了习惯,离婚也成了一个仪式,只不过孔林给自己涂上一些责任的幻觉。其实和淑玉的小脚一样,孔林和吴曼娜这对恋人对性的克制,是这部长篇小说的又一个不可思议之处,或者叫过度虚构之处。想想王小波的《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的骚驴王二,小说年代几乎是同时的孔林真像个穿着军便装的唐僧,而吴曼娜就婚后的表现应该是很饥渴的一个女人,但哈金让他们俩黄昏时分在医院里散散步就糊弄过去了,这真是哈金式的套路,我在保留意见的同时,也纳闷为什么小说的可读性不由此而降低呢?原因想来是小说家在写实上的功力、局部的精雕细凿与合理的人物互动,让小说以静水深流式的展开而接近生活本来的面目。
年年、月月、日日,这等待的十八年天天都在上演着一出悲剧,但是在这悲剧里,一切都是缓慢的,慢吞吞的,清新可人的姑娘成了在厨房里砸锅摔碗的泼妇,不知不觉中,甜蜜的爱情变质为苦涩的幻影,中苏之间的仗不打了,魏副政委因“四人帮”而落马,孔林的女儿也长大了……其间多少事情横生枝节,缠缠绕绕,让记忆化作空白,身体成了一具空壳……这悲剧因为过于缓慢的展开而不像是一出悲剧,仅仅沉淀为读者心头的一片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