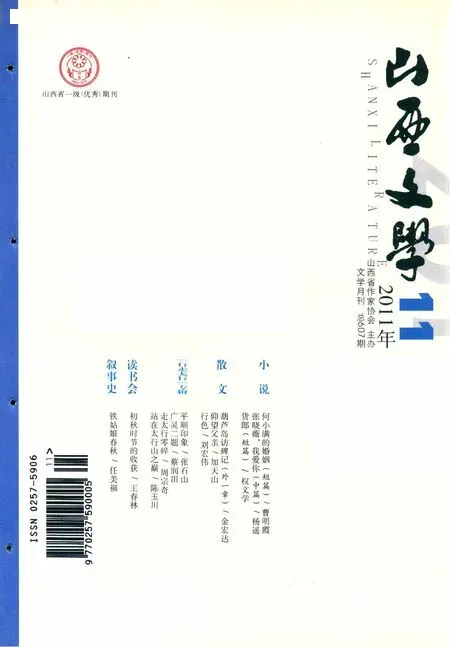铁姑娘春秋
任美福
不由自主地,又溜到太原南宫边那个古物旧书市场。倒不为收藏什么古董,而是去买回一些旧日的记忆。不经意地,发现一个上世纪60年代的旧硬皮笔记本让我惊呆了:插页里一幅油画,画的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女青年在台上讲演,头上戴着当年的“火车头”棉帽(像雷锋那样),别着鲜红的五角星帽徽,帽檐下掖着两条短辫子,上衣是洗得发白的军装——那个年代的女孩们最喜欢把绿军装洗得发白,就要那个朴素的风采,腰间扎一条皮带。红扑扑的脸庞,是那种劳动铸就的健康美,洋溢着蓬勃的朝气,放射着激情燃烧的青春光芒……这幅画太像我姐姐当年做铁姑娘事迹报告的神态了!那个年代的铁姑娘们,就是这样的青春风采!这幅画捕捉了那个年代特有的美的瞬间,我凝视着她,勾起了重重叠叠的回忆,当年铁姑娘们的非凡往事铺天盖地涌来。
1
新中国诞生的第二年,一个不起眼的300多口人的小山村,出现了一个奇妙的巧合:一年里全村没生男孩却生了18个女孩。抗日战争时这个村子归属昔西县政府,是八路军的根据地。许是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刚结束,又分了田地,人们无比幸福的缘故吧,这18个女孩生得个个美貌灵秀。更巧的是,女孩们的名字大多有个巧字,同名竟有好几个。喊叫时,还得依出生月先后在名字前加个大和小区分。当时全村里青壮年男子太少,下地劳动尽是些上了岁数的老人。后来的铁姑娘事迹报告对当时的情景是这样描述的:“宋家沟,真稀罕,光养女的不生男,闺女们,忙做饭,养种地,靠老汉。”这一现状加上传统观念作祟,父母本无心供女孩念书,到了1963年,这批刚14虚岁的女孩一起从小学辍学下地挣工分去了。
从这一天起,一个小乡村便开始演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铁姑娘”活剧。18个女孩,竟在14岁至17岁的年纪,生动得远近闻名又大喜大悲。
那时我还很小。我是以少年的眼睛所见和片断的记忆串联起她们那段春秋岁月的。
每天黎明,雄鸡刚叫,正在被窝里的我,总是被姐姐起早的声响惊醒。她五更起来总要洗涮一顿才去上地,晚上收工回来又总是洗呀洗的。父亲总是不耐烦地唠叨:下地就又土了,老洗什么?姐姐不听,天天如此,洗个没完。从冬到夏,姐姐不缺一天勤。她们那一茬女孩都要强,谁也不甘落后。后来,她们就成了村里的生力军。打坝、造地、下种、锄田、收秋、打场……干的活又快又精干,老少都赞扬她们。很快,“铁姑娘队”的名称就叫开了。
最壮观的是她们的集合行动。秋收时,割莜麦是个要样儿的活,她们干得比男人们还好。担庄稼嵌担子是个技术,就是把捆好的莜麦捆子,用尖担一头一捆扎进去担回村,必须扎孔平衡,否则半路就撒了包了。她们心灵手巧,每个人的莜麦担子都嵌得重心适当,妥妥帖帖。到晚上收工时,她们一排溜担起担子,从远山梁上往村里走。山上的路多是羊肠小路,只容一人过,她们这个小分队把肩上的庄稼担子一溜斜成一个角度,既能顺路而行,又能依小路山势排成独特的队列,齐刷刷地像舞蹈造型一样。姐姐是她们的领队,到该换肩时,姐在前面一声“嗨!”18条庄稼担子,36个刷溜溜甩动的庄稼捆就齐刷刷旋转,调了位置换了肩,那场景真是比舞蹈学院舞台上的编排都美。每天晚上姑娘们担庄稼走回村里时,大人小孩都出来观看,但见:她们脚下清一色的黑布鞋白袜子,走得铿锵潇洒,一顺溜的庄稼担子像打了线一样齐整,一飘一飘甩动。她们全都梳着两个短辫子,随着担禾的甩动一翘一翘地跳跃,那时节,天然的动感韵律,可是美极了呢!
她们又是女民兵班。稍有农闲,就要训练。有时,我们下了课,正遇她们操练。她们才都15岁,一排溜站起队来,一般般高的个子,拿着小木枪报数。有趣的是,她们的眉毛都是浓浓的类型,一样的弯曲,一排溜望过去,眉毛和眼睛像是老师在黑板上划了一排排圆括号,无表情也都像是在笑呢。民兵指导员是男的,比她们岁数大一倍,十分严厉,命令她们匍匐前进,她们就不顾街上的泥土瓦块全部卧倒,掖着木枪,在哨声的命令下,像去炸敌人碉堡一样爬行。哨吹一下,她们变一个姿势往前挪动一下,一直前进百米方止,把衣服扣子都磨掉了,全身都是灰土。
接近年关的腊月里,她们就又成了农村剧团的演员了。她们排的戏,抵不上县里剧团,但有时个别情节和表演却出奇的好,超过了剧团。排戏是很耗气的事,姑娘们故意调皮捣蛋,气得那个教戏的把“汽灯”“保险灯”都扔了(那时农村没通电)。到了演出时,忘了台词,就胡编乱说,有一次竟把土语骂出口,让文武场笑翻不能伴奏。演古戏时把现代话说进剧中,台下笑成一堆,农村唱戏最有趣也就在这儿。
轮到开群众大会,姑娘们就成为会前最活跃的风景。她们合唱一首又一首的歌,那些歌都激情高昂又深情悠扬,如《李双双》、《我们是刘胡兰的民兵班》、《焦裕禄,我们的好书记》等。特别是那首《大寨铁姑娘》,朝气蓬勃,斗志昂扬,节奏明快,旋律优美,那才是无与伦比的铿锵玫瑰。姐姐还把一支抗战时歌唱八路军在昔阳沾尚龙门口打了胜仗的歌谣《打马坊》几十段都搜集齐,率领姑娘们唱,一时成为开会前的必唱歌。一开大会,就有人喊:铁姑娘队!唱《打马坊》吧!姑娘们就齐声唱起来:“清早上起来俺心发愁,日本鬼叫俺备牲口,粮食集上等听着呀,收了良民往马坊走……”
到了1966年,红色浪潮开始了。每次会前都要集体背诵毛主席的老三篇。铁姑娘们集体背老三篇是全村人最爱看的“演出”了。只见我姐姐挑一句头,姑娘们就哗哗背起来。不知是什么导演给排练的风格?她们一样样的声调,抑、扬、顿、挫,停顿、起伏,是那么整齐有力,洁白的贝齿整齐地开合,圆圆的脑袋以一个节律颤动,短辫子一齐甩,胸脯齐整整一起一伏,比音乐指挥家指挥下的合唱队都翘楚。全县文艺汇演时,她们戴上女兵帽,穿上军装,表演舞蹈《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红五星、红领章、短辫子,舒展挺拔的动作,健美奔放的英姿,那风韵真是空前绝后了!呵呵,那样的青春风采是特有的时代艺术奇观哪,她们比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金玲传》中的青年们都鲜活灿烂许多呢。
2
劳动的大熔炉是严酷的。铁姑娘队的经历不只是欢笑、活跃、朝气、激情,更多的是难以想象的艰苦。
到了学大寨的高潮年份,上地担饭便是天长日久的事。说铁姑娘们十冬腊月在地头吃冰碴饭是有点夸张,但从春到冬一日两担饭在地头吃是真的。
忙碌的春播季节,遍地是耕牛。远远望去,在那一小队一小队的下种作业链中,点缀着一点红的或绿的或黄的鲜艳的彩点,那是她们,春天来到了,换衣的季节才展现她们的女儿装。她们在下种,男劳力不足时,也要挎粪施底肥。
夏天,一茬庄稼要三遍锄苗,一次间苗,一次培土,一次末锄,劳动强度十分大。到暑伏天,毒毒的日头把她们都晒得黑黝黝的,玉米叶子把她们的脸和臂都划出细细的血痕,汗水一渍,疼痛难忍。但大片大片的庄稼地都让她们像梳妆似的梳过了……到了中午,男人们都在地头睡去了,而她们,只要挨着河流,必定一条河内都是她们洗衣服的声音。
收秋的季节,更是她们大显身手的时候。男人们干多少,她们一样也干多少。劳动是艰苦的,也是欢快的,更有丰收的喜悦。在收割的田地里,一天到晚是她们欢快的笑声和嬉闹,有说不完的笑话趣事。
这里的严寒来得特别快。一年的无霜期只有120天,山高天寒,地广人稀,产量低下,付出多,收获少,世世代代农人们用成吨的汗水去向土里要食要穿。但也就是这片贫瘠的土地,却也地灵人杰,有名的清漳河的发源地之一便是这个村前的小溪,昔阳县的最高点西老庙也在这儿。生在这块不富饶的土地上,甘甜的泉水和粗糙的小米养育出一群水灵灵的姑娘,只是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不允许她们安享女儿青春。苦岁月里,她们没有来得及去品尝爱情的曼妙浪漫,便冲到了奋斗的风口浪尖上。深秋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人们脸上像刮皮一样生疼。夹杂着从漫山遍野无植被裸露的土地上卷起的沙尘,每日收工回来的她们,头上包着的头巾全是尘土。
那几年,收完秋,姑娘们就被派到八沟九梁上刨树坑,准备播油松籽。顶着呼啸尖厉的风沙,姑娘们穿得圆滚滚的,头上包着纱巾,戴着大口罩,只剩下一对秀美的大眼睛出发了。到山上一字溜排开,三米一坑,漫山遍沟把树坑刨得密密麻麻。
到了中午,唯一的食物是一个干粮袋中的玉茭面窝头。有的人家为了改善口感,窝头中加进酸菜或南瓜丝,有的做成发糕,但总归还是玉茭面。她们架起干柴,点燃篝火,把干粮放在火边烤得金黄……清漳河一道川的沟沟梁梁,一望无际的油松林,就是那个年代的人们用镢头刨出来的。
收工时,没什么往家拿的,姑娘们无一例外地把红的、橘黄的,大珠的、小珠的各种品种的沙棘灌枝担得满满的,看那一溜烟行走的队列像搬回来一片山林一样。农人们不叫沙棘枝,叫它黑圪针,嫩时吃“醋溜溜”,枯死了砍柴烧。她们把沙棘枝堆到各家房顶上,让霜打雪压一冬天就不涩了,又甜又酸味道美极了。那就是那时农村孩子们的水果,没人知道它曾是成吉思汗大帝的圣果,谁也想不到今日它会上到高级酒店的餐桌上。
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冰天雪地,冻土三尺,学大寨搞农田水利建设,硬是要把冻地揭开,把山石崩裂造地垒坝。青年团、铁姑娘队的力量是多么伟大呵,他们硬是用血肉之躯开山取石,在滴水成冰的冬天筑起拦河大坝。都才16岁的铁姑娘们,和男人们一样扛石头,用铁绳抬石料,用钢钎凿炮眼!她们从口罩里冲出的呵气,冲到眉毛上,头发梢,把眉毛刘海儿都冻成冰溜子,姑娘们全是冰挂的白眉毛,白刘海儿。
就这样的恶劣天气,险恶环境,也没见一个姑娘哭鼻子的。反而是,每当集体统一歇气时,所有的姑娘无一例外地拿出钩针,灵巧的双手上下左右翻花,勾织出袜子、围巾、帽子。她们把供销社的白线手套买来,拆掉,绕成线球,就开了“编织工厂”。她们织出的袜子图案竟有三维立体感,漂亮极了。
那个时代的姑娘们精神是完美的,因为她们有理想信念,因为她们激情燃烧。她们纯洁、纯真、单纯、清纯,纯得很呢。推广细毛羊改良,铁姑娘队向传统观念挑战,一个姑娘家自告奋勇担当起配种任务,根本不理睬别人的笑话调侃,一年工夫就把任务完成了。姑娘们都担任着记工员,她们公正无私。记得有一次一个老太婆胡搅蛮缠,非说姐姐给她少记了半天工,姐姐却记得清清楚楚老太婆那天没出工,就是不给人家通融。
铁姑娘们的事迹很快被下乡干部报告到公社党委又转到县委,安排秀才班子给写报告材料。姐姐是领头的,让她去做报告。先是全公社讲,后来到了县里七一广场大会讲,要求不许看材料要背下来。公社书记和大队书记陪姐姐到了县里。姐姐没有见过那么大场面,到县城的当夜不敢睡觉,半夜又偷偷爬起来背材料。第二天,几千人的大会开始了。不知哪个公社的选手上了台后,腿打战,手发抖,双唇青紫,吓得浑身哆嗦,一字也没讲就下台了。轮到姐姐上场了,开始她讲得滔滔不绝,赢得了一阵阵的掌声。忽然,她瞅见了台下坐着的公社书记和村书记,这两人怕她紧张,就一直不敢抬头看她。谁想,就在姐姐瞅见他俩的一刹那,他俩抬头了,六目相对的一刻,姐姐的脑袋“轰”地一下变成了空白,所有背下的讲稿全忘光了,一句也想不起来了。她的脸通红,这可是给姐妹们丢脸,给家乡父老丢脸,给书记丢脸呀!怎么办?讲台上有一只暖瓶,一只茶缸,姐姐不慌不忙,倒了一缸热水,喝起水来了!台下几千人静静的,就看着她喝水,她把一茶缸的水就那样一口一口喝完。台下的群众说,这孩子讲得太累了,看渴成啥了?他们哪知姐姐心里的紧张!喝完了也想起来了,姐姐又口若悬河,一泻千里把报告做完,在哗哗的掌声中走下台。两个书记问她:你真是渴成那样了?她笑说:“哪是呀,我给忘了!”真险哪。
全县的有线广播播出了大会的实况,每一位报告者的录音全部播出。姑娘们集中在喇叭匣下面,听她们的领队向全县报告。不久,姐姐又去了榆次,参加晋中地委组织的全地区更大规模的报告会。哎呀,闹大了,闹大了!全乡都在议论,不简单呀,一伙女娃娃们!
没几天,姐姐归来。姐妹们一窝蜂拥进我家,把她像英雄一样推来搡去。笑声,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像炸了锅一样,快要掀掉屋顶了。姐妹们看她带回些啥?一看,哇!一大包油印的铅印的材料,有半麻袋那么多。在她们眼里,姐姐见了世面了,不仅到了城里,还到了更大的地方榆次了!姐姐拿出照片给她们看,她是机灵的,合影时一下子窜到大寨村的郭凤莲旁边,和郭凤莲紧挨着照了相,姐妹们又是一阵欢呼。
3
铁姑娘队的春秋是短暂的。然而就那短暂的岁月,却并不是只有欢乐和喜悦,悲剧的种子早就播下了。
还是1965年的一天深夜,人们睡得正熟,突然尖利的哨声一阵紧似一阵,民兵连在紧急集合了。姐姐不顾一切,匆匆忙忙穿起衣服就冲出门去……一家人都惊醒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过了好久,姐姐回来了,却呜呜大哭起来。父母吓坏了,好不容易才问清楚,是民兵连在演习,命令姑娘们去山沟里搜寻“美蒋空降特务”。那几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民兵练兵抓得很紧。姑娘们跑进黑洞洞的山沟中,又惊又怕,拿着个小木枪乱吱哇,没有把“特务”抓住。男民兵扮的“特务”在她们搜寻中跑了。民兵指导员狠狠批了她们。父母亲说,这不都是假的嘛,干吗半夜三更还哭鼻子抹眼泪的,劝了一顿,睡了。小山庄又恢复了安静。
但那几年,却不知为何,半夜三更里,常听见姐姐在被窝里偷偷啜泣,不知是什么伤心事。
1966年,红色浪潮来了,铁姑娘队也走向了辉煌的顶峰。就在这节骨眼上,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铁姑娘队里的一名队员怀孕了。
单纯的女孩不敢跟父母说,不敢给队员们说,也束手无策,只是事后偷偷告诉我姐。劳动时她拼命担大担子想通过重压把那个孽胎压下来,大雨时,她跑进雨中让暴雨狠狠地淋,希望受凉堕了胎……可是那孽种稳固得很,看着看着肚子隆了起来。她再不敢出门,直到后来,到县医院才把孩子生下来。在农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一时间,消息像旋风一样传遍十里八乡,几乎家喻户晓。
究竟是怎么回事?事情很快真相大白,就是那个民兵指导员制造的罪孽。他利用女孩们的纯洁无知,利用手中掌握着管教民兵的权力,干下不光彩的勾当。
事情的发生是戏剧性的。1964年罗瑞卿组织大比武,民兵们经常操练,投弹打靶是硬功夫,光木枪瞄不行,要实弹射击才见真效。那时候,大寨村的郭凤莲,神枪手远近闻名,传说酒瓶上面放上鸡蛋,打掉鸡蛋留下瓶子,姑娘们羡慕得不得了。但实弹是有代价的,一发子弹要消耗一毛钱,那时一个劳动日才一元钱。几次射击,耗资不小,收效却甚微,铁姑娘们被训得抬不起头来,哭成泪人。她们文化低,不懂三点一线射击要领,又怕浪费了子弹,从瞄准到击发的时间特长。规定每人三发子弹,打完报靶。姑娘们趴到射击堆上,瞄呀瞄,瞄准又虚了,虚了再瞄,没有十分钟射不出一发弹。谁也不知道,子弹飞过去的那一头发生了什么事。
报靶的是那个民兵指导员。他和那一名女队员两人藏在靶牌旁的一个水磨房里,等三枪响过之后,跑出来报靶。就在这三枪的三次瞄准间隙时间里,他又是威逼,又是以“进步”利诱,让纯洁不更事的女孩不知所措,没了主意。
她才16岁,多么需要一个知心人的疏导关怀,可是,没有,四处都是白眼和讥讽。她顶不住四面八方的议论和压力,羞于见人,父母又怕她想不开,把她死死关在屋里,从此不敢出门,在家待了整整两年,直至出嫁。可怜父母心,左不是,右不是,听任唾沫星子淹死人。我清楚地记得那父亲的苦楚状。那一天,老父亲在干和泥的活儿,他狠命地甩着泥,火辣辣的太阳光下,照得那黑膛膛的脸明晃晃的,因为他的脸上淌着汪汪的汗水。乍一看,像是淋了大雨一样。年少的我细心了一下,分明看见了他脸上长一道短一道的汗水中搅和着长一道短一道的泪水。我呆呆看着他,他是无声的,两眼却急速地哗哗淌着泪。唉,农人们就是这样一种感情:他们在辛苦、无奈的生活中是宽容、包容、豁达、达观的,多么大的委屈也都能咽得下。当他们实在咽不下时,女人们会去坟头或河边大哭死去的亲人,向缥缈在另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里的灵魂哭诉。男人们就这样,狠命地干活时偷偷地把痛苦的眼泪淌出来再咽回去。可怜他,无颜面对全乡村的各种各样的目光和议论,又实在不能再责怪承担着巨大精神重压的女儿,她还小啊。况且,他对给女儿造成如此伤害的那个人又能怎样呢?
姑娘们压抑许久的怒火终于爆发了。正遇夺权的风暴,她们联合起来奋起反击,控诉那个指导员对她们的压制、迫害和侮辱。在群众大会上造了他的反,让他威风扫地了。
然而,好景不长。风言风语,世俗观念,迅速像过堂风一样以想象不到的速度蔓延开来,铁姑娘队的名声受到了污损,把纯洁不更事的女孩们压垮了。
她们伤了心。“文化大革命”第二年,她们才17周岁,便纷纷到外村找对象。她们好像已经累垮了,更要命的是精神也垮了。18周岁一到,便一溜烟远嫁他乡,嫁到更偏僻更小的山庄庄去了。她们希望到一个安宁的不太苦累的地方去生活……姐姐出嫁那天,用一个网兜提了一个脸盆,里面放着香皂、雪花膏、牙刷、牙膏,正中放着《毛泽东选集》四卷。姐夫学校的30多个老师每人出了二毛钱买了一个玻璃镜框,算是结婚的贺礼。
自那以后,村里后来几茬的女孩子们再没有活跃起铁姑娘的风采,也没有了那个组织。一代代嫁出去嫁进来,生生不息,平平凡凡。今年回乡祭祖,与姐姐谈及铁姑娘往事,她仍能把18个队员的姓名、性格特征、嫁到的地方说出来。没有人为她们的事讴歌过,我由此萌发了写此文的念头。我不由得联想到当今村里的青年男女,生活这么好,却没有了丝毫当年的精神状态。看今日女孩们的装扮,花红柳绿,却远没有当年铁姑娘不爱红妆爱武装的风采美。姐姐她们当年是清纯的、鲜活的、动人的,虽然,那个时代没有让她们表现“花输双颊柳输腰”的美,但她们的飒爽英姿却是胜过典雅赛绝风骚超越妩媚的!铁姑娘的两根短辫子比当下女孩子们烫的“方便面”、“狮子狗”不知美了多少倍!铁姑娘们的浓眉大眼自然大方,又岂是当今的文眉画眼圈忸怩作态能比得了的?她们的容貌美是劳动锤炼的,太阳施敷的,美在旺盛的青春活力!她们更美的是内心世界,那个年代的理想,多少年回忆起来也是难忘的无悔的青春。
最可气的一件事!一群小伙子们无事干,在城里干起赌博来,那小子输了20万元。为了还上赌资,竟然回村偷偷将一沟的油松砍光卖掉了!没人举报,亦没人管。我听说后,专门进沟看过,满沟的油松砍得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桩在呜咽。这片林是铁姑娘们造的,是没有立碑的铁姑娘林,那是铁姑娘的青春留念,是她们留在娘家唯一的青春岁月铭记啊。一件记载着不平凡年代青春少女们光荣历史的作品,就这样被一个无赖毁掉了。巨大的失落,深深的遗憾,无比的愤怒,使我久久不能平静,坐在被砍掉的油松树桩上,不愿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