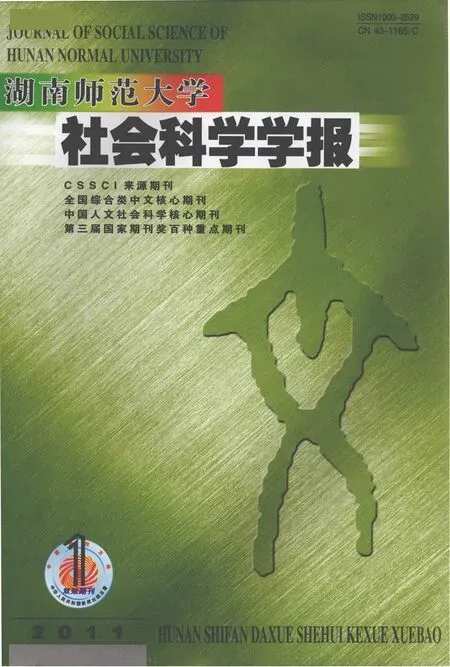刑事诉讼统一证明标准论纲
——兼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层次论者商榷
张元鹏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刑事诉讼统一证明标准论纲
——兼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层次论者商榷
张元鹏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多数学者提出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应当按照不同的诉讼阶段设立不同的证明标准,这种观点不妥。一些法治发达国家的确是按照不同的诉讼阶段设立不同的证明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也要跟在他国身后亦步亦趋。就现阶段而言,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刑事诉讼构造和司法生态环境,认识论不能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层次论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并且不同办案主体深受探究案件事实的能力、程序分流机制设置、侦办案件的压力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应坚持不同诉讼阶段统一的证明标准,这更利于防止错误追诉、防止错判、防止更大量的案件进入审判从而带来的案件发回重审。
证明标准;诉讼阶段;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
一、问题的发端
刑事证明标准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负担证明责任的主体利用证据对争议事实或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近年来许多受人尊敬的学者提出了刑事证明标准的多元性和体系化的思路,他们主张根据不同种类的案件、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对不同的证明主体和证明对象设置不同的证明标准,应当说,这些观点是富有创造性的,且其中的大部分观点笔者也赞成,但他们所主张的根据不同诉讼阶段设立不同的证明标准之观点则值得商榷(除立案的证明标准外)。他们提出的刑事证明标准的阶段性理论依据在于:第一,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其直接任务、诉讼主体及采取的诉讼行为皆有不同,这些因素要求对不同阶段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1]。第二,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证明过程即为一个认识过程。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也必须遵循认识论的一般原理,渐进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逐步达到定案所要求的标准。因此,在我国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应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1]。由于上述观点要求按照不同诉讼阶段制定由低到高的多层次的证明标准,因此本文将其观点称作证明标准的层次论。层次论者的观点单纯从认识理论的角度来说并没有错,但把这种原理运用到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并作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逐步提高的认识依据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它似乎把不同阶段混同为一个阶段,把不同主体的认识过程当做同一主体认识过程来理解了。按照此说法,在侦查阶段对事实证据认识差一些没关系,按照认识论的原理,到检察机关那里认识就会提高,到审判那儿就更高了,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阶段是由不同的人、不同的职能部门进行的,而不是同一群人或同一个部门在不同时间的活动,“一个案件经过法律的不同阶段——控告、逮捕、起诉或审理,案件参与人中的分层可能会变化。”[2](P17-18)而且侦查机关侦查结束后它的工作就基本结束了,不会参与审查或审判来逐步提高它的认识能力,加之审判人员的认识能力并不一定就比侦查人员的强,因此,“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也必须遵循认识论的一般原理,逐步地、渐进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逐步达到定案所要求的标准”[1]之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二、域外的阶段性证明标准探究
提出阶段性证明标准(也即层次性证明标准)的学者大多受到了西方法制理念和司法实践的影响,在此,我们有必要去了解域外关于阶段性证明标准的理论状态与实践情况。
1.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证明标准
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一般实行检警一体化,检察官有权在侦查中指挥警察,如在深受大陆法系影响的我国台湾地区,检察机关设有专门的部门和场所,以便举行由检察官主持、警方和辩方参加的听证活动。引人注目的是,在听证的众多重要事项中,连案卷制作与否的决定权都要由检察官行使,然后警察才有权制作,这表明警察侦查的结果就体现着检察官的要求。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审前也没有侦查和审查起诉的明确划分,因此,其与我国大陆警检分立下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之证明标准的审查不具有可比性。具有可比性的是英美法系国家警察侦查终结移送检察官起诉的证明标准。在英美法系国家,这一阶段证明标准没有硬性的要求,如在美国,检察官与警察的关系是一种微妙和重要的互相依赖关系。成功的控诉依靠警察出色的工作。对于普通的街道犯罪,如夜盗、殴打、抢劫和破坏公共秩序罪,警察是刑事诉讼程序的守门员,案件不会诉至法院,除非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并将犯罪嫌疑人交付给检察官。检察官也对警察产生影响,检察官如何对待警察和检察官如何处理案件将影响警察将来如何完成工作。当检察官拒绝签署指控时,警察会推测什么地方出了错,他们可能假设出错的是检察官的“软心肠”或腐败。然而,警察常常承认他们逮捕所需的证据不及检察官获得有罪判决所需的证据标准高。如果警察希望他们的逮捕能获得有罪判决,那他们就会竭力提供给检察官适当的证据。检察官不被要求对每个案件都提起指控,许多检察官事务所对审查的1/3或更多的案件都不起诉。指控决定实际上不受控制和事实上不受审查的状况是几年来人们一直关心的事情[3](P66-67)。根据以上相关文献的介绍,大体可以推断英美法系国家侦查终结的案件证明标准不会高于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但由于警察不希望案件被检察官驳回,就会尽力收集证据提高证明标准,因此,可以认为此时的证明标准会在事实上接近定罪所需要的标准。
2.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提起公诉通常是指公诉机关(一般由检察官代表)以政府或人民的名义向法院指控特定的被告人犯有特定的犯罪,请求法院依法审理后正式确认指控成立、并对被告人判处刑罚的诉讼行为[4]。提起公诉的决定意味着国家针对特定公民的刑事追究程序的开始,被告人可能被剥夺自由、财产乃至生命。因此,只有证据达到起诉所需的证明标准,检察官才能起诉。如果检察官明知证据不足,仍然要决定起诉,这不是“滥用裁量权”的行为,而是“职务违法行为”。被告人经法院宣判无罪或裁定驳回起诉后,可以反过来控告检察官恶意追诉,以侵权行为或滥用职权罪追究其法律责任,并且可以要求国家赔偿。无论是在诉讼理论上,还是在各国的诉讼实务中,要求只有在达到法定的证据标准时才能决定提起公诉,是确保公诉权得到正确行使的最重要条件[4]。在英国,检察官提起公诉时要进行证据审查和公共利益审查,其中,证据审查是提起公诉的基础。英国《1994年皇家检察官守则》第5条要求“检察官必须确信对每个被告人提出的每一项指控都有足够的证据提供现实的定罪预期”(realistic prospect of conviction)。所谓“现实的定罪预期”是一项客观标准,而不完全是检察官的主观猜测,它是指陪审团或治安法官组成的法庭,在主审法官或书记官根据法律规定很可能给被告人定罪,如果根据现有证据没有这种现实可能性,并且警察也说不再有其它证据或者没有可能再找到其它证据,就不应当就某个罪名提起公诉。在美国证据法上,依证明所需的确定性程度划分,证明标准由高到低共有以下几个层次:(1)绝对的确定性——任何法律目的均不作此要求;(2)排除合理怀疑——刑事案件中为有罪认定所必需;(3)明晰且有说服力的证明——适用于某些民事案件以及某些管辖法院对死刑案件中保释请求的驳回;(4)优势证明——适用于多数民事案件以及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肯定性抗辩;(5)可成立的理由——适用于逮捕令状的签发、无证逮捕、搜查及扣留、控诉书和起诉书的发布、缓刑及假释的撤销,以及对公民逮捕的执行;(6)合理相信——适用于“阻截和搜身”;(7)有合理怀疑——无罪释放被告人的充足理由;(8)怀疑适用于调查的开始;(9)没有信息不能采取任何措施[5](P301)。在美国,如果可能性根据(可成立的理由)不存在,那么检察官除了不起诉外别无选择。检察官也须考虑宣告有罪的可能性、宣告有罪要求证据超出合理怀疑。被害人的愿望可能在决定中占很大分量,但这只是检察官必须衡量的众多因素之一。如果美国的地方检察官基于被害人的告发拒绝签发控告,那么被害人就几乎不能追究他人的刑事责任。如果地方检察官拒绝签发指控,州总检察长有权签发指控,但这项权力很少行使[3](P66-67)。总之,检察官必须确保证据能提供一幅令人信服和完整的画面,以支持指控的有罪判决[3](P68)。在德国,其刑诉法典第152条第2款规定,须“在有足够的事实根据时,检察院具有对所有的可予以追究的犯罪行为做出行动的义务”。在检察院起诉之后,则由对案件审判享有管辖权的法院裁判是否开始审判程序或暂时停止程序。此时,根据该法典第203条规定,须“认为被诉人有足够的犯罪行为嫌疑”,方可裁定开始审判程序[1]。法国法要求检察官有明显理由认为发生了犯罪且嫌疑人实施了这一犯罪行为。但由于法国有大陆法上的经典预审制度,检察官在提起公诉时,可以不明确地指明被告人而申请预审法官启动预审程序,查明应当被指控的具体被告人[4]。日本没有明确规定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理论界对此长期存在争论,一般采用有犯罪嫌疑作为标准。实务中一般认为“被嫌疑事实,根据确实的证据,有相当大的把握可能作出有罪判决时,才可以认为是有犯罪嫌疑”[5](P301)。
综上所述,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审查起诉都要求一定的证明标准,只有证据达到这一标准后,检察官才能决定起诉,否则就是追诉权的滥用。另一方面,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普遍比法院定罪的证明标准低,还达不到内心确信或排除合理怀疑的高度,但事实上,侦查控诉机关出于成功追诉的欲望,也常常最大限度地去接近定罪标准。因此,可以初步肯定,在以上各国代表的法治较为发达的国家中,确实存在证明标准的多层次设立的立法标准。但这是否意味着我国也要(除了立案标准外)设立按阶段划分的多层次证明标准吗?
三、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层次论的回应
关于立案阶段的证据标准应当不同于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提起公诉和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学术界没有争议,作者也同意。这里所要探讨的是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是不是一定要低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对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构造、司法体制和司法环境没有发生显著改变之前,应坚持统一的证明标准,理由如下。
1.认识论不能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层次论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
证明并不等于认识活动。一般而言,典型的认识活动只存在于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而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行政审判一样,则主要蕴含着一种证明活动。对于控诉方而言,认识活动已经完成,有关的结论和论题已经产生和明确[6](P201)。在侦查阶段,如果侦查人员对案件的人和事还有疑惑,还没有形成内心确信,他就敢于移送审查起诉,检察人员就冒然提起公诉,而寄希望于沿着认识论的一般规律,在庭审阶段查明事实真相,这无论在理念上和还是在事实上都存在很大问题。
第一,这种观念想当然地认为法官是事实真相的发现者,他的发现能力是超凡的,法官的慧眼能够通过庭审发现侦查人员不能发现的案件事实,能够作出符合事实真相的判断,因此,前两个阶段的证明标准要比法官作出裁判的证明标准低。实际上,就事实的发现能力看,法官也是普通的司法人员,其事实的发现和推理能力可能还远远赶不上侦查人员,法官的长处在于中立、公正且没有偏私,他只能根据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判断,在法官基本上不再拥有刑事庭外调查权的情况下,法官已经失去了如中世纪法官那样的依靠特权来发现事实真相的能力。第二,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往往能亲历罪案现场,有时候甚至是目睹犯罪的一些过程,他们对犯罪过程及所遗留下来的证据有着最接近事实的鲜明印象,因此,他们所还原的案件事实也最接近所发生过的案件事实,其证明标准所能够达到的程度也更高。而其后检察官和法官所得到的证据都是由侦查人员提取和固定的,从时间上来看,控诉、审判主体所还原的案件事实已经和所发生过的案件事实“渐行渐远”,即使他们发现了疑点,由于许多证据已经无法再次提取、罪案现场已经破坏等原因,发现事实的难度也随之提高。因此,事实上的案件证明标准可能随着诉讼进程的推进反而降低了,之所以还要推进诉讼进程,最主要的不是发现案件真实这一实体目标,而是法院充满权威的审判宣告。第三,在庭审中,控方的证据和控诉理由在事实和证据等方面受到辩方的强烈对抗,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专门认识案情的侦查活动不同,法庭控诉主要是控、辩双方证明给权威裁判者看的诉讼活动。因此,在法庭上,法官从未经历过案件事实,他们接触的是由侦察控诉机关和辩方提供的证据,而在我国现实司法环境中,辩方的取证能力极其有限,因此,法官更多的是依赖于控诉方的证据并通过理性思维去还原案件事实真相,而辩方即使是提供了证据也会起到抵消控方证据证明力的作用,因此法官所还原的案件事实真相并不一定就比侦察控诉机关所还原的案件事实证明标准高,近期报道的重大冤假错案就是最好的例证。第四,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逐步推行,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出台《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后,任何通过严重侵犯被追诉人宪法权利的非法取证行为所获得的证据都有可能被排除,在我国目前证据生成机制还很不成熟,侦查取证行为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的情况下,庭审中一旦被告人翻供,起诉可能即告失败,导致整个诉讼程序“无功而终”,为了保证一定的犯罪追诉率,大量控诉成功的案件实际难以超越审前阶段的证明标准。司法实践证明,定罪裁判所需要的实际证明标准常常大大低于“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6](P211)。第五,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发现一条规律,那就是案件从侦查开始直到审判结束,就侦查、控诉和审判三个行使国家公权力的主体所采集的证据看,证据从整体上“如同穿越时空的粒子”出现了逐步衰减的状态,在侦察阶段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最原始、数量最多,而经过检查机关的筛选可能排除了一些不合法的证据(未必不真实),审判阶段中,由于辩方的指摘和法官的合法性审查,证据会进一步“衰减”,证明案件真实性的难度进一步提高。如果按照证明标准层次论者的说法,审前证明标准低于定罪标准,那么,证据从审前到达审判后,案件证据水平不是提高,反而降低了,又由于在证明标准的尺度选择上,我们关注的重点是裁判正当性的最下限,而非诉讼证明可能达致的最高水平[7](P204),因此,如果审前证明标准低于定罪标准,那么案件又如何从侦查开始通过完整诉讼程序,特别是审判程序的“证据衰减”过程达到定罪标准的呢?审前较低的证明标准会导致一种极为尴尬的后果就是低于定罪标准的案件都无法最终经过审判程序定罪。果真如此的话,为什么对低于定罪标准的案件还要提起国家追诉呢?所以,证明标准层次论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会陷入极大的困境。在刑事诉讼的运行过程中,认识论显然不足以为层次论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
2.中国特有的刑事诉讼构造
中国刑事诉讼的构造与西方刑事诉讼构造不完全相同,并且有自身的文化底蕴和制度环境,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刑事诉讼的证据标准理论套用在中国刑事诉讼中。法治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审判中心主义”和无罪推定原则,推行司法审查和令状主义,警察的侦查活动受到来自国家权力和诉权的监控,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严格限制羁押的适用,同时,案件从警察机关移送检察机关以及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期间,侦查活动继续进行,加之提出指控的时间距离逮捕的时间很短,要求公诉证据标准低于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是有一定道理的。而我国的刑事诉讼实行理论上的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刑事程序带有明显的“流水作业”的性质,三机关在各自负责的诉讼阶段都必须依法最大限度地查明事实真相,然后根据法律规定认定特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每一个专门机关在其所负责的诉讼阶段必须从事实上和法律上保证对案件作出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结论,不允许把自己应当完成的任务推到下一阶段,特别是在事实和证据上,要求三机关反复审查、验证,最终确保有罪的人受到应有的处罚、无罪的人不受追究[4]。更加严重的是,由于庭审方式的改革,法官不能够在庭前阅卷,不能轻易的进行庭外调查,且庭审期限较短,造成法院探求事实的能力明显下降。此外,我国实际上实行的是侦查中心主义,因此,如果案件在进入庭审之前大幅降低证明标准的话,案件的真实性恐怕难以保证。即使在德国,对诉讼结果起决定作用的所有实质性证据都是靠侦查程序收集的,而在侦查程序中犯的错误是根本不能在公开审理阶段得到顺利修正的,其结果便是,对被告人的赌注完全被下在了侦查阶段而非公开审理阶段。因此,公开审理早已不是刑事程序真正的判断中枢了,他无非指望着花了费用走个过场对侦查程序中产生的结果再加渲染而已,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和顶点阶段。因此,必须对侦查终结的刑事案件予以严格的筛选,坚持较高的证明标准,尽力避免将证据不足的案件提交审判,从而保障无辜者免受错判的风险[7](P266)。
3.公检法三机关探究案件事实的能力不同
我国侦查检查机关拥有超凡的探寻案件事实的能力,往往比人民法院更具有获得事实真相的优势,这是因为法律所赋予了它们特定的职权和地位,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其本身就具有天然的便利条件。侦查机关可以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讯问,羁押犯罪嫌疑人成为常态,看守所在侦查机关的控制之下,律师没有在场权,较长时间的询问和封闭的场所使犯罪嫌疑人难以抵挡侦查机关的强大压力,往往做出有罪供述,长时间的羁押确保了办案机关获取证据的能力,拘留的羁押期限可以延长至37日,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可以因所谓重大复杂的案件延长至7个月,因精神病而鉴定的期限可以不计入审限,就检察机关而言,审查起诉时面对的是一个已经经过侦查机关彻底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还有补充侦查或退回补充侦查的权力,并可以依法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人的意见。侦查、起诉机关收集的证据,可以当然地进入法庭审理程序,就连证人在侦查、起诉过程中提供过的证词,也可以询问笔录的形式直接作为控诉证据使用。而辩护律师收集、调查证据的权利极为有限,庭审中形式上的“对抗”并没有改变辩护力量极为微弱的现实。而法官很难在庭审过程中通过辩方获取证明案件事实的重大信息。实践中控方证据在庭审中才被发现不足以定罪的往往是因为侦查取证工作本身就存在严重缺陷,或者审查起诉工作不细致,并不是因为法定的公诉证据标准不可能达到。相比之下,法院的案件事实发现能力就捉襟见肘了,因此,没有理由要求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高于移送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4.我国与域外国家和地区的程序分流机制不同
就人权保障和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而言,不同诉讼阶段的证明标准当然是越高越好,但在大部分西方国家,由于人权保障、犯罪率上升、司法资源紧张等等原因,导致案件进入审判程序之前其证明标准低于定罪标准,同时进入庭审后无罪的判决率较高,直接影响了刑事诉讼程序的犯罪追诉价值和诉讼效率价值的实现,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他们发展出了较为发达的不同的案件审理程序。在美国,有众所周知的辩诉交易制度,使得大部分案件,特别是控方证据不足的案件在审前就得到犯罪嫌疑人的认罪,从而使90%的案件得以从普通审理程序中分流。在德国有处刑令程序,在犯罪嫌疑人认罪的情况下,一定范围的轻罪案件可以不经过正式庭审而得到法庭的判决。这样,提高了诉讼效率,同时,由于这种分流机制使得认罪者能够获得较轻的刑罚,人权保障和犯罪追诉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皆得以实现。我国的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这两种程序的选择权在法院而不是当事人,这样就剥夺了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如此一来,如果大量的证明标准较低的案件一旦进入庭审,其结果不外乎一是有罪,一是无罪,有罪分为证据确凿的有罪和证据不足或没有证据的冤案,无罪的结果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侵犯了无辜者的自由和权利,冤案那更是对人权和正义的亵渎,因为缺乏正当程序保障的审理将极有可能产生有罪判决,这样人权保障和诉讼效率以及追诉犯罪的功能将面临严重挑战。
5.我国与域外国家和地区侦办案件的现实压力不同
在我国侦查控诉机关面临着极大的追诉犯罪的压力。首先,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犯罪率明显升高,许多犯罪黑数无法统计,而侦查人员的侦破能力直接影响着其自身利益,因此,侦查人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办案压力。其次,被害人给侦查控诉机关的压力各国都存在,但中国尤甚,特别是中国存在的独特的信访制度,使得被害人有一种潜在的权利,如果侦查控诉机关不追诉,还可通过上访解决问题。同时,有些被害人常常到侦查控诉机关闹事,只要你不追诉,我就不走,有时甚至形成被迫追诉的案件。第三,新闻媒体的压力。新闻媒体事实上已经成为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后的“第四种权力”,有些案件,还未经过法院审判就被新闻媒体“定了罪”,焉有不追诉之理?笔者正在密切关注河北大学的李启铭开车撞死女学生的案件,那句“我爹是李刚”的网络名言已经家喻户晓,新闻媒体和网络的炒作到底会对李启铭的审判带来什么还有待观察。此外,社会法制生活中还存在很多干扰侦查控诉机关追诉活动的现象,产生了种种的不当压力。侦查控诉机关面对这些压力,有些能够克服,有些只能顺从,一旦决定追诉,往往在事实上降低了案件的证明标准。
四、现阶段坚持不同诉讼阶段统一证明标准的意义
鉴于上述我们国家特有的诉讼模式和司法实践的现实状况,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我国的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坚持统一的证明标准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具体如下:
1.防止错误追诉
第一,侦查机关追诉倾向明显,难以监控。我国警检关系是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而实际上的“侦查中心主义”使得公安机关拥有较大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其往往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就开始庆功了,此时如果规定较低的证明标准,则在实际运作中就会促使公安机关为了尽快结束侦查并建议提起公诉而匆忙地给案件定性,从而降低证明标准并将案件“囫囵吞枣”地移送给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而且实践中警检关系是相互配合的,每天与警察打交道,一些检察官开始视警察而并非视公众为他们的当事人。一些检察官不愿批评警察的工作,哪怕只是暗示。这些检察官经常有很好的理由害怕警察会怨恨检察官而做出不指控的决定,并担心以后他们不合作。检察官不愿意弄僵与警察的关系可能导致检察官为了使警察满意而指控不应指控的案件。不幸的是,警察放任草率的工作或过分地提起指控不应指控不能促进公正[3](P64-65)。这种情况不仅在我国有,在美国等法制较发达的国家也普遍存在。即使在法国这样传统上实行警检一体化的国家,检察官真正实现对侦查的监控也是困难重重。因此,在他国存在的现象,恐怕在中国也不能幸免。所以,对侦察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规定较高的证明标准是制约侦查机关滥用刑事追诉权的坚强屏障。第二,我国的公诉权由检察机关独立启动、专门行使,不受任何司法审查。在域外法治国家,检察官提起公诉并不一定能导致审判。大多数法院都有对检察官提起诉讼案件的实体审查权。英美法系国家治安法院对检察官起诉案件实行预审,而法国除了可以直接传讯或立即出庭的案件外,由预审法官决定案件是否交付审判,重罪案件还必须经过二次预审。他们的检察官享有的仅仅是请求审判的权利,而法院真正拥有是否将案件交付审判的决定权。而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弱化了开庭前的实体审查,检察机关已经在实质意义上成为了案件是否交付审判的决定者。对于检察机关依法作出的起诉决定,法院几乎必定开庭审理,被告人必须接受法院审判,在开庭审判以前没有任何救济的机会。要求检察机关决定起诉时掌握较高的证据标准,有利于避免滥用公诉权,保证起诉案件的质量。在这方面,法国检察官严格掌握公诉证据标准的经验值得借鉴。同时,中国的检察机关在现实条件下还不能完全独立行使检察权,办案中经常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的情况下,规定较高的公诉证据标准也有利于检察机关抵制外来干涉,从而防止错误追诉。
2.防止错判
第一,我国辩护律师不享有庭前调查取证权,1996年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律师更加难以得到控方的证据,无法在庭审前进行有效的防御准备,证人普遍不出庭,使得我国刑事案件的庭审过程中不能进行充分的质证,庭审本身应当具有的核实证据、查明事实的功能并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法庭审判在很大程度上是走过场的。第二,“虽然自审判方式改革以来,人们对法院依职权包揽调查取证和收集证据的做法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对于是否保留法院调查取证的权限以及调查取证范围,依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主张应当完全取消,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当保留但应予完善或改进。”[8](P387)而1996年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法院从此就没有权力在开庭审理以前进行庭外证据调查,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也只有在对庭审中提交的证据有疑问时才能依法进行有限的庭外查证活动。法院定案所依据的证据大体就是检察机关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提供的证据以及庭后移送的证据。在法庭上,审判人员只能通过双方提供的证据和双方的辩解来做出判断,他们不能亲历第一现场,很难弄清楚证据的来源和双方辩解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他们真可谓是蒙眼的“神”,是一个很可能被假证和谎言所欺骗的“神”。第三,在控辩式庭审模式下,法官对犯罪事实的认识主要是借助检察官的控诉活动进行的。在法庭审理中,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是通过控辩双方的说服活动进行的。由于辩方只负责根据法律和事实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辩护主张,能否有效地揭露犯罪只能仰赖于检察官的控诉活动。也就是说,公诉人可否准确地认识并解释证据的证明价值及各证据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握定罪标准,能否正确并合乎经验和逻辑地论证案件,直接决定着法庭对案件事实认识的方向和结论。因此,为了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检察官理所当然应当承担比当事人更多的职责上的责任[7](P268),严格把握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第四,中国特有的司法体制也使得法院无法真正做到独立裁判。对于重大的证据不足的案件,特别是有政法委出面协调的或社会舆论压力较大的案件,法院基本都会做出有罪宣告。“错案追究制”的推行,国家赔偿的制裁更使得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困难重重。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的有罪判决率很高,在有些地区,法官甚至认为案件经过了侦查和起诉环节还可能出现无罪判决吗?有些地区已经有了一定时间的全部有罪判决的记录。审判人员的这种权力“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所指出的,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被滥用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注意和道德界线的诱惑。‘人们可以把它比作附在权力上的一种咒语——它是不可抵挡的’。”[9](P376)美国学者波斯纳认为如果检察官不进行甄别,而是对任何被指控的人都提出起诉的话,无辜者被判有罪的比例也许就很大,因为陪审团只需要合乎情理地肯定被告有罪就可以判定他有罪[10](P274)。而在我国这样一种只要起诉就几乎意味着有罪判决的司法体制之下,如果不将侦查终结移送起诉和提起公诉的决定提出较高的证明标准,将会导致冤假错案泛滥成灾。
3.防止更大量的案件流入审判程序
理论上讲,如果侦查终结移送起诉和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降低,可能使本来不应该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却符合了较低的证明标准,从而顺利进入到审判程序之中,这样可能导致一种直接的后果就是更大量的案件进入到审判程序,从而增加了司法成本和工作量,这又会引发一系列其他不利的后果。首先,浪费司法资源,减低了审判的正确率。我国司法资源紧张,案件的增加无疑会增加审判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司法人员可能经常为繁多的案件而忙的不亦乐乎,很少有时间去思考、去学习,结果提起诉讼的案件大部分由于缺乏证据事实而中途终结或宣告无罪,做了许多前期的无用功。而且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在紧张的时间内应对因证明标准降低而增加的案件的做法,表面看来其在时间上提高了个别案件的效率,但这种效率是以浪费司法资源和降低判决的准确率为代价的,同时,案件也需要时间的考验,冤案错案大部分与匆忙结案有关。其次,我国司法审判中的顽疾之一就是案件的发回重审,特别是多次发回、久拖不决危害尤甚,许多学者对此作了分析和论证,找出许多引起发回重审的原因,但他们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诱因既是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量。理论上讲,案件量是发回重审的上游问题或入口问题,如果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量较低,那么被发回的数量同样会低,反之则高。如果降低证明标准,那么,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量就会增加,这些增加的案件由于本身的证明标准较低,使得法官裁判的难度增加,被发回重审的几率会比通过证明标准较高而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更高,因而会引发更加严重的发回重审现象。发回重审不仅损害了司法的权威,而且印证了西方的那句名言:“迟到的正义为非正义。”因此,坚持案件侦查终结移送起诉和提起公诉案件的证明标准同判决的证明标准相同,可以减少进入审判程序之案件量,提高司法效率,一定程度上减少发回重审的现象。
[1]汪海燕,张小玲.论刑事证明标准及层次性[J].中国法学,2001,(5):125-131.
[2][美]唐纳德·J·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唐 越,苏 力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3]樊崇义.域外检查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4]孙长永.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及其司法审查比较研究[J].中国法学,2001,(4):119-136.
[5]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6]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7]吴宏耀,魏晓娜.诉讼证明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8]王利民.司法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9]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0][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 力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Abstract:Most scholars bring up different standards of proof in different stages in Law of Criminal Procedure.I do not think so.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set up different standards of proof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tages,but this does not mean it adapt to our country.As far as the present period is concerned,our country has its own criminal procedural structure and judi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Epistemology can not provide adequate theoretical supports for the theory of gradation of standards of proof in the criminal procedure.For different case staff,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some factors,such as the ability of case recognition,the system of procedure distributaries,the pressure from crime investigation,we should continue unified standard of proof in different stages of litigation.It will prevent some cases from being prosecuted or sentenced wrongly and will prevent many cases from coming in justice to cause some cases being remanded for retrial.
Keywords:standard of proof;stage of litigation;deporting for checkup prosecution;prosecute
(责任编校:文 泉)
On Theory of Unified Standards of Proof in Criminal Procedure Law---Talking About the Theory of Gradation of Standard of Proof
ZHANG Yuan-peng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Beijing 100038,China)
DF73
A
1000-2529(2011)01-0042-05
2010-08-23
河北省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刑事司法程序研究”(200902155)
张元鹏(1973-),男,河北廊坊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研究生,北华航天工业学院文法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