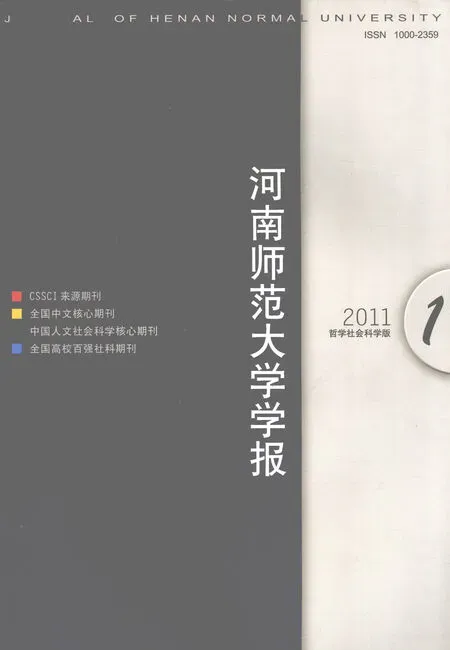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之证明
葛 同 山
(扬州大学 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之证明
葛 同 山
(扬州大学 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认定多是依靠作为“受害人”的控方收集的言辞性证据。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证明,控方证人和警察需要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较低,对证据的认识不同于司法机关。辩护人妨害作证的判断应该以律师执业标准为准绳,律师向被告人披露相关证据不构成妨害作证。
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警察出庭作证;证人出庭作证;律师的真实义务
现有理论对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刑法领域。仅从刑法的角度研究辩护人妨害作证罪,即便取消《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妨害作证罪,律师的很多正当辩护行为也会依据《刑法》第307条规定的妨害作证罪被追究刑事责任。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虽规定在实体法上,但该罪的设定、认定离不开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地位的科学界定。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中,追诉机关、控方证人和作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有利害关系。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证明和其他主体妨害作证罪的证明存在重大的不同。因此,从刑事诉讼法的角度研究该罪的证明可以弥补实体法研究的不足。
一、控方证人出庭作证
《刑法》第306条包括三个罪名: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毁灭证据、伪造证据行为较为明显,且有一定的客观性较强的证据加以证明,因而实践中较容易认定;律师涉嫌毁灭证据、伪造证据犯罪的也为数很少。“绝大多数律师被定罪,都是因为妨害作证,具体地说,是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1]。律师对有关证人的威胁、引诱行为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的主要形式,决定了该罪中主要的控方证据,表现形式都是主观性很强的言辞性证据。实践中,公诉方指控辩护律师涉嫌妨害作证罪主要靠的是证人证言。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直接证据,多是那些在律师先前代理的案件中受律师“威胁”“引诱”,尤其是受律师“引诱”的证人。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中的控方证人,尤其是那些曾受律师“威胁”“引诱”的控方证人,如果律师犯罪成立,其本身就涉嫌犯罪。因此,这些关键的控方证人和辩护律师具有一定的利害冲突,他们通过作证,把自己伪证罪的罪责推卸给律师或者希望借此减免自己伪证罪的刑事责任。由于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也是证据的来源,所以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委托人也会作为控方证人指控辩护律师。在委托人罪责较重的犯罪中,举报律师妨碍作证罪甚至成为委托人立功减刑、保全性命的救命稻草。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中控方证人更加容易丧失证言的客观性、真实性。控方证人出庭接受被告人的质证,是克服律师妨害作证罪中控方证人证言主观性较强弊端的程序保障。
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控辩双方的质证,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可司法实践中,“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大行其道,证人出庭率很低。所谓“案卷笔录中心主义”,指的就是以公诉方提供的书面笔录作为主要的控方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全国法院一审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不到10%,二审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不到5%[2]。“案卷笔录中心主义”说到底就是侦查中心主义。“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剥夺了辩护方的质证权。其他案件中,由于证人和被告人无具体的利害冲突,追诉机关虽然职能上和辩护方对立,但毕竟不是“受害人”,以笔录代替证人证言尚有些微的客观合理性基础。证言笔录从一定意义上讲已经不是原始证人提供的证言,它演变成了笔录制作者提供的证言。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中由“受害人”制作的证言笔录,其客观性、真实性根本没任何保障。证人出庭作证是保障被告人对质权的需要。对质权是发现诉讼真实的一个重要的程序装置。“对质条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确保证据的可靠性,而所谓的可靠性,指的是程序上的而非实体上的保证。要确保证据的可靠性,必须以特定的方式进行评定,而这一方式就是通过交叉询问的严峻方式进行测试”[3]。控方证人出庭且接受辩护方实质性的质证,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才能得到保障。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中,侦控方和被告人存在利害冲突,再以本质上为传闻证据的证言笔录代替证人出庭,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根本无法保证,同时也丧失了基本的程序公正。
实践中,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审理,控方证人同样极少出庭。李庄案中,一审中辩护方竭力申请包括龚刚模在内的控方证人出庭,可被一审法院拒绝。为保障程序公正,兼之李庄案的社会影响,二审中龚刚模等控方证人出庭接受了辩护方的质证。死刑案件由于关涉被告人的生死,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了有限的证人出庭制度。辩护人妨害作证罪,控方证人和被告人有直接利害冲突,证言主观性强,必须出庭接受辩护方的充分质证。辩护人妨害作证罪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理论界一直对其诟病有加,批评公诉机关假借该罪对辩护律师加以职业报复。律师作为一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律师刑事责任的追究对一国法治的影响巨大;律师作为专门维护他人权利的专业人事,在自身涉嫌职业犯罪的诉讼程序中能否维护自己的权利,对于判断一个国家刑事诉讼程序是否具备基本的程序公正具有标志性的价值。在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短期内难以取消的情况下,为彰显程序正义,作为权宜之计,最高司法机关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律师妨害作证罪中控方证人出庭作证。
二、警察出庭作证
警察出庭作证是西方法治发达国家普遍的司法实践。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相应制度。相反,《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曾经担任过本案证人的侦查人员应当回避。基于对侦查人员身份和证人身份彼此矛盾的强调,《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等于间接地排除了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8条、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43条隐约地规定了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但是这些规定不完整,同时部门司法解释的形式也难以得到侦查机关的尊重。“警察不出庭作证对律师的辩护活动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主要表现就是无法对控方的非法证据提出有效辩论或者质疑”[4]。在律师妨害作证罪中,警察不出庭作证直接剥夺了作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就控方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的质证权。
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自身的特点决定了警察出庭作证的必要性。刑事诉讼结构决定了追诉机关和辩护律师职业上的对立冲突。律师的成功辩护是公诉方实现胜诉的职业利益的一个巨大的障碍;在实行错案追究制的情况下,辩护律师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公诉方实现职业利益的一个“绊脚石”。如果说辩护律师出于职业利益的考虑有作伪证的嫌疑,同样不能排除追诉方为达到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定罪的目的而作伪证的动机和可能;在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中,作为“受害人”,侦查、公诉机关作伪证的可能性更大。从认识论上看,警察制作的各种书面证据如勘验笔录、询问笔录以及在对其他证据的保全与固定中,多少会加入制作人的主观偏见。在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中,这种可能性更大。鉴于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中控方证据主要是那些在律师先前所代理案件中,受辩护律师“威胁”“引诱”提供“虚假证言”的证人提供的证言,警察是否对这些证人进行了“威胁”“引诱”,是否违法地收集了相关证据,是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中警察出庭作证所要审查的核心。警察出庭作证,与提供各种书面证据相比,最大的功能在于接受辩护方以及法官的询问,在公平、公开又相对自治的环境中,在控辩双方的多轮对质交锋中,检验警察所搜集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中警察出庭作证,就其所收集的证明辩护律师妨害作证罪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接受作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的质证,是排除追诉方为达到给辩护律师定罪的目的而作伪证、非法收集证据的需要,是消除追诉机关对律师的职业报复嫌疑,实现程序公正的需要。
任何人都不能充当自己案件的法官是一条自然正义原则。在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中,追诉方和辩护律师在律师在以前所代理的案件中有利益冲突;在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中,追诉方和作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利益直接对立。追诉方所收集的证据不接受被告人的质证直接为人民法院采证,违背了任何人不得充当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基本原则。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一直被理论界、律师界视为公诉方对辩护律师进行职业报复的利刃,“从1996年到2003年全国一共有300名辩护律师因为辩护导致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90%以上被无罪释放,真正被定罪的不到5%”[5]。这说明刑事诉讼实践中确实存在追诉方对辩护律师进行的职业报复。警察出庭作证具有消除追诉方利用妨害作证罪对辩护律师进行职业报复的嫌疑的客观效果。
要求警察出庭作证是刑事诉讼控辩平等原则的要求。警察不出庭,辩护方在法庭调查中质证的权利也就被剥夺了,刑事诉讼中控辩平等也随之遭到破坏,从而也动摇了司法公正的基础。鉴于律师在一国司法制度中的特殊地位,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中警察出庭作证,切实保障作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的质证权,对于彰显刑事诉讼的控辩平等具有特殊的价值。如果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中作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的质证权尚不能得到保障,普通案件中被告人的质证权就更加难以实现。警察出庭作证是实现控辩平等的需要。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中警察出庭作证具有示范作用。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中警察出庭作证完全可以作为克服刑事诉讼实践中“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突破口,作为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改革的一个切入点。
三、辩护人妨害作证的判断应以律师的执业标准为据
刑事诉讼结构的基础是控诉、辩护、审判三方职能的分立。辩护律师的职能是专门维护受刑事追究者的合法权益,对受刑事追究者负有党派式的忠诚义务。党派式的忠诚义务,要求律师积极辩护,运用一切合法手段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作为一个职业整体,可以说辩护律师负有维护公平正义、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职责。但是对于进入具体诉讼的律师个体而言,不应该要求其承载过多的公共职责。和侦查、控诉、审判机关相比,辩护律师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介入刑事诉讼,无需像公权力机关那样在证据的收集判断上负有客观真实义务。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具有单一性。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决定了其对证据的判断不同于侦查、控诉、审判机关,标准相对较低。
辩护律师较低的真实义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具有片面性。“从辩护人的地位、任务来看,辩护人不像检察官那样承担完全的真实义务(客观义务)。在维护嫌疑人、被告人的正当利益上不产生矛盾的限度内,负担真实责任。换句话说,辩护人以维护嫌疑人、被告人的正当利益为任务,在这个限度内为发现真实而协助”[6]。辩护律师只注重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对不利于被告人的事实可以置之不理。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具有权利的属性。辩护律师不得收集、提交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案件事实,辩护律师有权利消极地不予以披露;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案件事实,辩护律师有权利加以证明;在自己举证能力有限时,有权利申请警察、检察官、法官运用国家权力加以收集。不得积极地揭露不利于被告人的案件事实以及积极地收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是辩护律师对被告人的义务;对司法机关而言,是辩护律师的权利。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具有消极性。刑事诉讼中公诉方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人具有无罪推定权、反对自证其罪权、沉默权等权利。辩护律师承继了被告人对控方追诉活动的消极抵抗权。法律对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要求,也多是要求辩护律师消极地“不作为”,律师不得伪造、毁灭、隐匿证据,不得教唆他人伪造证据,不得向法庭提交明知是虚假的证据。辩护律师没有积极地揭露案件真实的义务。
律师的真实义务低于侦查、公诉、审判人员,甚至还要低于普通民众。普通民众知道案件事实有如实作证的义务,但是针对辩护律师基于职业上的原因知悉的不利于受刑事追究者的案件事实,法律赋予其职业上的保密特权。辩护律师真实义务低,在收集判断证据时对相关证据真实性的注意标准就相应较低。因此不能因为律师所提交的证据与客观事实有所出入,甚至与公诉方认定的事实有所出入,就启动追究律师妨害作证罪的司法程序。基于对辩护律师诉讼职能和真实义务的科学界定,各个国家律师协会对辩护律师收集、判断证据的辩护行为设定了行业标准。美国律师协会制定的《美国律师职业行为标准规则》规定,律师不得故意向法庭提交虚假证据,但是只要有“合理理由认为”相关证据并非伪证,他就可以合法、正当地向法庭提交,无需考虑相关证据本质上是否真实。辩护律师对于自己仅仅怀疑而不是明知是虚假的证人证言,提交给法庭通常不被认为违反职业规范。被告人有反对自我作证的权利,同时也享有自我作证的权利。对于被告人本人提交的言词性证据,辩护律师注意程度更低。为了保障被告人自我作证的宪法性权利,“应允许刑事辩护律师提交被告方自己的证言,而无需考虑它是真是假”[7]。可见,在美国律师实务界和理论界,辩护律师可以放任被告人本人“证言”的虚假,将其提交给法庭。对于被告人的“说谎”行为,允许辩护律师对其保持默许态度。这一点和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在辩护律师会见了嫌疑人、被告人之后,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若发生变化即追究辩护律师的妨害作证罪的做法大相径庭。律师职业规范对辩护律师收集、判断证据设定了相对较低的执业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一种事实探知绝对化的倾向。诉讼职能和侦查、控诉、审判机关迥异的辩护律师也承担着几乎和司法机关同样高的真实义务。具体就律师妨害作证罪而言,《刑法》第306条规定辩护律师“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构成律师妨害作证罪。威胁、引诱作为描述性用语,很容易和律师正当的辩护行为相混淆,如将辩护律师“提示”“协助”当事人收集有利于己方的证据认为是“引诱”当事人伪造证据,将辩护律师对证人的“诱导式的询问”认为是“引诱”证人作伪证,等等。“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即构成律师妨害作证罪,界限模糊,条件要求极低。在《刑法》第306条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短期内难以取消的情况下,应该先取消“威胁”“引诱”这两个罪状;同时从严把握律师妨害作证罪的构成,对于律师不妥当的取证举证行为优先适用纪律制裁,不宜轻易入罪。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认定应该以律师执业标准为判断准绳。如此,方和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增加当事人主义成分、强化辩护的精神相一致。
四、辩护律师向被告人披露相关证据不构成妨害作证
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公诉方往往将辩护律师向被告人披露自己收集的证据作为指控妨害作证罪的证据之一。在李庄案中,控诉方将李庄向龚刚模宣读同案犯樊奇杭的供述作为证成妨害作证罪的证据之一;在张耀喜涉嫌妨害作证罪案中,辩护律师将自己收集到的李洪涛的证人证言告诉被告人,这一行为也被公诉方作为控诉证据[8]。辩护律师将自己履行辩护职责中收集到的证据向被告人披露被视为妨害作证,其根本原因在于过分地强调了辩护律师对司法机关的保密义务。为了防止被告人利用辩护律师提供的案情,干扰、妨害侦查、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辩护律师不得向被告人透露履行职责中得到的相关证据。此处对辩护律师保密义务的强调,和对辩护律师过高的真实义务的强调异曲同工,其落脚点都在于保护发现真实的司法利益。如何认识辩护律师向被告人披露案情的行为,涉及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定位。
辩护律师基于受被告人的委托参加诉讼,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是其职责;辩护律师享有被告人所不享有的职权,因此辩护律师不仅仅是被告人的代理人,在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过程中也承担有一定的公共职责。“对于辩护人来说,背离了与委托人的依赖关系,完全不可能期待它的其他的公共职能,只有忠实地捍卫委托人的利益,才能实现对辩护人所期待的公共性职能”[9]。如是界定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则不能近乎绝对地禁止辩护律师向被告人披露案情。很多国家允许辩护律师向被告人披露案情。《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律师可以将其取得的预审案卷材料的副本复制给其顾客[10]。在德国,辩护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将所收集的证据向被告人披露,德国学术界认为“辩护人得将并且也必须将其从卷宗中所得之数据,或用口语传达,或用卷宗影印本之方式告知被告,使其得知诉讼程序之发展及助其有效地进行辩护”[11]。向被告人披露案情是辩护律师的职权,辩护律师原则上可以将自己履行辩护职责时知悉的案情披露给被告人;仅“对于那些一旦被追诉人知悉可能会影响其他案件侦查、妨碍证人作证、干扰被害人如实陈述或者可能对证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进行打击报复的信息材料……辩护律师不得披露给被追诉人”[12]。由此可见,辩护律师向被告人有限地披露案情是正当的辩护行为。
将辩护律师向被告人披露在履行职责中收集到的证据视为妨害作证行为,侵犯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刑事诉讼中辩护权的主体是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是辩护权的一个主要方面。禁止律师向被告人披露案情,过于强调辩护律师相对于被告人的独立性,绝对地禁止辩护律师向被告人披露案情侵犯了被告人的辩护权。鉴于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作用,很多国家宪法将获得律师帮助权作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加以规定,国际人权公约中强调的也是被告人的获得律师帮助权。从获得律师帮助权的角度来看,被告人有权利要求辩护律师向其披露案情,尤其是律师在履行职责中收集到的证据;向被告人披露案情是辩护律师对被告人的义务,同时也是辩护律师的职权,司法机关不得无故干预。禁止辩护律师向被告人披露案情,将辩护律师向被告人披露相关证据视为妨害作证,同样是过于强调辩护律师对司法机关的真实义务,而忽视了辩护律师首先是被告人的辅助人这一根本角色。
将辩护律师向被告人披露证据视为妨害作证是对律师保密义务的误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38条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但是,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该条关于律师保密义务的规定出发点是错误的,内部结构是混乱的。律师的保密义务,理应是辩护律师对委托人的保密义务,保密的对象是辩护律师在履行辩护职责时知悉的不利于被告人的案情。检视该条规定,律师保密的对象却是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当事人的隐私。刑事诉讼实践中,追诉机关据此可以将相关案情解读为“国家秘密”,禁止辩护律师向被告人披露。从该条的“但书”条款看,律师的保密义务应是履行职责时知悉的不利于被告人的案情。纵观国外关于律师保密义务的规定,多是规定律师不得泄露在履行职责时知悉的不利于委托人的案情。但是委托人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只有将保密义务界定为不利于被告人的案情,方和“但书”的内容逻辑上吻合。将辩护律师的保密义务回归其本原,回归为辩护律师不得泄露履行辩护职责中知悉的不利于委托人的案情,则保密义务就是辩护律师对抗追诉机关的利器。律师的保密义务,其权利主体是委托人。辩护律师向被告人披露相关证据谈不上妨害作证。
[1]陈兴良.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之引诱行为的研究——从张耀喜案切入[J].政法论坛,2004(5).
[2]毛立军.全国政协在青海专题调研证人出庭率低症结何在[N].人民政协报,2007-07-31.
[3]Ohio v.Roberts,448U.S.56(1980).
[4]王超.关于我国警察出庭作证问题的分析[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5).
[5]陈瑞华.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若干问题[J].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6).
[6]日本司法研修所.刑事辩护实务[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58.
[7]皮特·莫瑞.出庭律师的道德[G]//江礼华,扬诚.美国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8.
[8]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刑二庭.刑事审判参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7-11.
[9]村冈启一.辩护人的作用及律师伦理[J].尹琳,译.外国法评译,1998(2).
[10]罗结珍.法国刑事诉讼法典[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112.
[11]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M].吴丽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71.
[12]韩旭.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及其家属证据知悉权研究[J].现代法学,2009(5).
[责任编辑孙景峰]
OntheProofofDefenderImpairingTestification
GE Tong-shan
(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9,China)
The proof of defender impairing testification is mainly based on the oral evidences gathered by the prosecutor as victim.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 witness and the police should attend the court as witness. The defender’s faithful obligation is low relatively compaired with the judicial organs. The attorney’s professional practice should be the judge standard of defender impairing testification. Disclosure of evidences gathered by the defender to the prosecuted shouldn’t be considered to be impairing testification.
defender impairing testification;police serving as witness;appearing in court as a witness;attorney’s faithful obligation
DF713
A
1000-2359(2011)01-0087-05
葛同山(1969—),男,河南西平人,扬州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研究。
2010-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