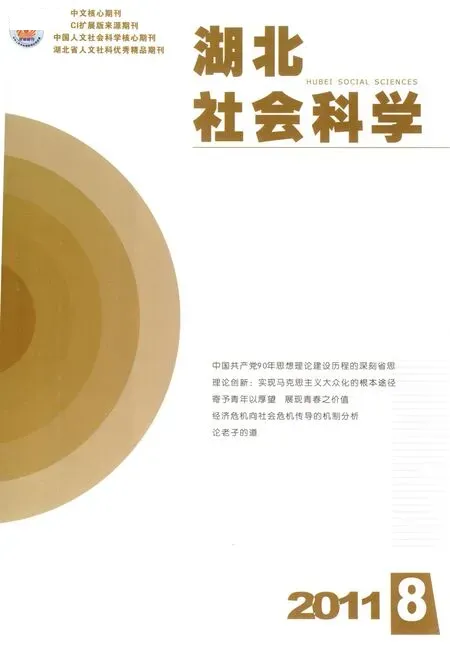鲁迅小说的散文精神
——论鲁迅小说中的一种文体越界现象
余新明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303)
鲁迅小说的散文精神
——论鲁迅小说中的一种文体越界现象
余新明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303)
尽管小说与散文都有各自的文体规定性,但在鲁迅小说中存在非常明显的由小说文体向散文文体进行“越界”的现象,体现出一种鲜明的散文精神。向散文越界于鲁迅来说是一种非常“自觉”的行为,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从西方小说那里得到启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身上深厚的中国古典散文积累。具体来说,鲁迅小说在“情真”、“意丰”、“言杂”三个方面表现出向散文回归与交融的趋势,它们带来了鲁迅小说突出的抒情性、复调性和丰富性等特征。其结果,就是产生了现代新型短篇小说——散文化小说。
鲁迅小说;文体越界;情真;意丰;言杂;散文化小说
我们在阅读鲁迅小说时,总感觉鲁迅小说和我们一般认为的小说有些不同,甚至感觉到有些不像小说。它们有的结构松散,有的没有完整的故事而只有一个个的场面,有的笼罩于浓浓的情绪之中,相较于小说,它们似乎更接近于散文。美国学者李欧梵在研究鲁迅的小说创作时就认为:“1922年所写的五篇:《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读来像散文而不像小说,当然最后一篇《社戏》作为抒情散文是绝妙的。”[1](p52)不仅这几篇,大多数鲁迅小说都有这种散文化倾向。鲁迅似乎也注意到了他的小说与一般所谓小说的不同,在《呐喊·自序》中他称自己的小说为“小说模样的文章”,到30年代的《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在谈起当初写的小说时还是以“小说模样的东西”来称指。“小说模样”就暗含着“非小说”的因素,即鲁迅小说作品中有非常明显的小说文体向其他文体的“越界”现象,比如说对散文、诗歌、戏剧的某些文体特征的吸收和使用。在谈到文学的类型时,美国学者韦勒克和沃伦说:“优秀的作家在一定程度上遵守已有的类型,而在一定程度上又扩张它。”[2](p279)鲁迅是一位天才作家,他正是这样一位文类的“扩张者”。因篇幅所限,本文仅限于讨论鲁迅小说向散文进行“越界”的文体现象。
一
小说和散文是现在学术界公认的关于文类划分四分法中的两种,相对于另两种(诗歌和戏剧)来说,它们更为接近——在文本表现上它们都是无韵的散行体文章。散文这一概念,在其历史的发展中存在着广义与狭义之分,其广义的散文(Prose)是与韵文相对称的一个概念,一切非韵文的文章(包括小说、话剧、论文、后来的狭义散文等)都包含在内。而狭义的散文,则出现于我国新文学初创期的五四时期,五四新文学家在西方近代文学观念的影响下,获得了一个“纯文学散文”(大体相对于西方的Essay)的概念,并与小说、诗歌、戏剧构成完整的纯文学体系。尽管狭义散文的范畴较广义散文已大大缩小,但相较于小说、诗歌、戏剧来说,它所包含的文章类型依然众多,这导致了(狭义)散文的概念与内涵仍然难以确定。
孙绍振先生在为方遒先生著的 《散文学综论》所写的《序》中说:“散文理论是世界性的贫困。”在这篇《序》中,他还转引了南帆先生对散文理论的不确定性的阐释:
诗的理论或者叙事学精益求精,蔚为大观。相反,散文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文类理论,散文的游移不定致使它的文类理论始终处于一鳞半爪之中。……诗学之中没有散文的位置。散文的文体旨在颠覆文类的权威,溢出规则管辖,撤除种种模式,保持个人话语的充分自由。[3](p1)
在这段引文中,南帆先生不仅道出了散文理论“贫困”的现状,更指出了散文这一文体的“颠覆”性特征,即一种突破限制、追求自由的精神,我谓之为“散文精神”。在这一精神的拨动下,散文文体的本质特征的确很难概括,参考一些代表性著作,[4]可以看出散文这一文体的基本特征:1.抒情性,是一种重在抒情的文体;2.真实性,追求事件、情感的真实;3.自由性,在选材、表达方式和语言运用比较自由。
作为文类之母的散文,天然地具有与其他文类进行交融和互渗的能力。郭风先生说:“在一定条件和文学气候影响下,散文从本体内部产生了小说(在我国,例如唐代传奇),并最终使小说成为文学领域内一个最大的家族,这是散文文学本体的一次最大的分化或分离。……但是,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亦即诗歌与从散文中分离出来的小说,向散文归化的情况,回流的情况,于是,出现了自由诗、散文化的诗、散文化的小说,等等。”[5]但在中国古代,在小说兴盛起来后,由于人们过于强调“文各有体”,严守门户之见,加之以对小说的轻视——认为小说乃“丛残小语”(汉·桓谭《新论》)、“匪为玩好”(汉·张衡《西京赋》),不过是一种消遣娱乐的材料,远不能与承担“载道”功能的文章相比——因此,这种小说向散文回归的倾向只是一种自为的存在,远非自觉的行为,因此,中国古典小说也未能在文体特征上大面积地吸收散文的特征,只是恪守自己的领地玩些翻新的小游戏。而把这种“自为”状态变为“自觉”行为的,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鲁迅,因为他在西方小说那里得到了启发。
鲁迅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谈到自己当初写小说的准备时,这样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这些百来篇外国作品主要是东欧一些弱小民族的短篇小说,鲁迅1909年在日本时还曾与周作人热心地翻译了一些,编成《域外小说集》两册,1921年又重出了合订本。在合订本《域外小说集序》中,鲁迅谈到了这些小说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区别:“《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两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这些短篇小说,像鲁迅所译的《四日》、《谩》和《默》,都是些人生的断片,不重情节的完整性,却把重心放在人物内心的情感体验和心理活动上,“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黯澹的烟霭里〉译者附记》)。对于这些迥异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西方小说,在《域外小说集》的“略例”中,周氏兄弟却以一个颇为中国化的文类名称——“小品”来指称(“集中所录,以近世小品为多”)。这对于一向谨严的周氏兄弟来说,显然不是轻率的断语,更可信的解释是他们在西方现代短篇小说和中国古代的“小品”之间发现了很多类似的地方,因为他们都非常熟悉中国古代散文。在他们看来,西方现代短篇小说与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长篇章回小说)差异很大,却很接近于某些中国古代散文。这一发现给予他们的启示是:可以按照中国古代散文的做法来写小说。因为他们对中国古代散文的驾轻就熟,他们很容易做到这一点。西方文学的启示,与中国文学传统的结合,就促成了中国现代小说新的审美风尚的诞生——向散文的回归与交融。
鲁迅小说到底在哪些方面表现出向散文回归与交融的趋势?我认为,可以概括为“情真”、“意丰”、“言杂”三个方面。
二
首先,我们来看鲁迅小说的“情真”特征。
所谓“情真”,是指鲁迅小说具有强烈的主体介入精神。对于小说里的故事、人物,叙述者、隐含作者和作家本人,都不是持超然物外、冷眼旁观的态度,而是把自己全身心投进去,并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或显直或婉转地表露出种种真切的情感态度:激愤、哀伤、悔恨、同情、留恋、希望、嘲弄……对于文艺创作,鲁迅曾这样说过:“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里面。”(《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显然,鲁迅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是贯彻了这一主张的。巴人在谈到鲁迅的作品时这样评价:“鲁迅先生的作品,差不多没有一篇不从憎与爱中迸裂出来。”[6](p103)萧红在谈到自己对鲁迅小说的认识时,也很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鲁迅小说的调子是低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而鲁迅却自觉地和他们一起受罪。”[7]李长之先生则干脆说:“鲁迅彻头彻尾是在情绪里。”[8](p137)对别人评价他小说的看法——“极富于同情人和热烈的情绪”,“对旧势力之一一加以讽笑,是‘含’了‘泪’”——鲁迅也持赞同的态度。
与中国古典小说偏好全知全能的视角不同,鲁迅小说偏好第一人称,在《呐喊》《彷徨》的25篇作品中,有13篇(《狂人日记》、《孔乙己》、《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故乡》、《阿Q 正传》、《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采用了第一人称,其中《狂人日记》和《伤逝》干脆就用了日记(手记)体。在这些第一人称作品中,“我”要么是故事的见证人,要么亲身参与故事,因为“我”多是一个情感世界丰富、思想敏感的现代知识分子,因此外在世界的人和事都进入了“我”的内心,并且因“我”思想、情感的观照,这些外在的人和事都笼罩上“我”的情感色彩。在鲁迅的大部分第一人称小说中,因“我”的思想、情感的介入,小说的重心不再是外在的故事和人,而是弥漫小说各处的“我”情感、思绪。
鲁迅小说的情感之真可以从他创作小说的初衷中找到答案。在《呐喊·自序》中,他说他从事文艺运动的目的是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他说他信奉的是“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因此,鲁迅在创作小说伊始,就站在了一个与被视为“闲书”、“不算文学”的中国传统小说绝然不同的位置上。在此种创作心理的驱使下,他当然不能采取与中国传统小说“列位看官”、“且听下回分解”等类似的超然态度,他必须显示出对笔下人、事的强烈的情感、思想判断,并以此来影响读者的精神(灵魂)世界。从创作的题材来说,《呐喊》《彷徨》中的两大题材——农民和知识分子,都是鲁迅非常熟悉的,鲁迅对他们充满感情。鲁迅曾说:“创作总归于爱。”他“亲近”“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的中国农民,一提笔,“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境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对于阿Q、祥林嫂、爱姑这样的农民,他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又充满深情与关爱。在谈到《阿Q正传》这篇小说时,周作人说作者“想撞到阿Q,将注意力集中于他,却反将他扶了起来了”,阿Q反倒是未庄“唯一可爱的人物,比别人还要正直些”。[9](p233)对于知识分子,鲁迅就更为熟悉:同他一样的启蒙知识分子,他和他们走过同样的道路,有类似的情感经历;像《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这样不学无术、道德败坏的知识分子,鲁迅也见过,了解他们。对于前者,他是无限的理解与同情,又哀伤他们的命运;对于后者,他是怒不可遏地进行无情的讽刺与攻击,要揭出他们的本性来。
鲁迅小说的“情真”特征,形成了鲁迅小说在文本表现上突出的抒情色彩,抒情的场景、段落、文字,在鲁迅小说中随处可见。这大量的抒情成分,势必冲淡作为小说文体所要求的叙事性,结果就是叙事的完整性、连续性的被破坏,导致一种新的带浓郁抒情色彩的散文化小说的出现。这种新的审美创造,使鲁迅小说成为别出心裁的、让人惊异的杰作。李长之先生由衷地赞叹说:“鲁迅的笔是抒情的,大凡他抒情的文章特别好。
三
我们再来看鲁迅小说的“意丰”特征。
所谓“意丰”,是指鲁迅小说在思想、内容上的丰富性,并在丰富性基础上因其内部的不统一而呈现出来的某种驳杂性。鲁迅是个思想深刻而复杂的文学家,观察人生、社会的全面、深入,加上他思想意识内部的矛盾和张力,使他在创作他的小说时,思想不是向某一点收束、集中,而是向外进行多角度的发散性投射。当这些角度彼此距离甚远、甚至相互矛盾而至难以统一时,就出现了“众声喧哗”的“复调”现象。严家炎先生的论文《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就非常精辟地指出鲁迅小说具有“复调”特征:“鲁迅小说里常常回响着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声音。而且这两种不同的声音,并非来自两个不同的对立着的人物(如果是这样,那就不稀奇了,因为小说人物总有各自不同的性格和行动的逻辑),竟是包含在作品的基调或总体倾向之中的。”细读鲁迅小说,这种总体倾向上的复调的确是鲁迅绝大部分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狂人日记》里狂人的日记,既是一个迫害狂的“疯言疯语”,也是一个启蒙战士的“惊天发现”,两种价值判断既对立又统一,这是这篇小说第一个层面的复调;文言小序中狂人向正统的封建统治秩序的回归,与白话文日记里狂人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的彻底否定和批判,则构成了这篇小说更高层次上的复调。《伤逝》里男性主人公的诉说,一方面可以看作他的真诚而痛苦的忏悔,另一方面,从他剖析自己的心路历程中可以看出他也是在做一种减轻灵魂负疚感的自我辩解、自我开脱,真诚忏悔与自我辩解是矛盾而分裂的。《补天》一面歌颂女娲的创造精神,一面又写到了创造的荒诞——创造出来的人类并没有使这个世界更美好,反倒增加了战乱、争吵与破坏;鲁迅还借女娲两腿之间的古衣冠的小丈夫,来对当时攻击汪静之的《蕙的风》的“伪道学”们进行反击,——这三方面是彼此不从属、各自相对独立的关系,在一定的意义上它们分裂了文本,造成思想倾向上的复调性。《理水》既赞颂禹的埋头苦干精神,也批判文化山上学者们空发议论、不学无术的丑态,还揭露了“大员”们的官僚主义作风,并借卫兵不让禹太太进去——“要端风俗而正人心,男女有别”——来抨击那些封建主义的道学家们腐朽的男权中心意识,因此,《理水》简直就是一曲四面出击的多声部大合唱。对于鲁迅小说的这种复调性,钱理群先生进一步解释说:“他的作品总是同时有多种声音,在那里互相争吵着,互相消解、颠覆着,互相补充着,这就形成了鲁迅小说的复调性。所以在鲁迅小说里,找不到许多作家所追求的和谐,而是充满各种对立的因素的缠绕,扭结,并且呈现出一种撕裂的关系。”
与鲁迅小说总体倾向上的复调特征密切相关的是,在鲁迅小说中出现了“复故事”的叙述技巧。所谓复故事叙述,是指在同一篇鲁迅小说中出现的叙述多个故事的现象。这些不同的故事,表达的思想、情感往往各异其趣,构成了鲁迅小说故事层面的复调。之所以能够断之以“多个”故事而不是“一个”故事,是因为这些故事之间并不是一种因果逻辑关系,因而并没有组合成更大层面的情节而成为某一个故事的一部分,它们之间往往是一种相对独立、彼此平行并列的关系。而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中国古典短篇小说,小的故事之间往往结成一个个因果逻辑关系,形成情节,然后组合成更大层面的故事,你推我拥,把故事推向前进。因为它们必须彼此依靠才能显出自己的作用和意义,因此这些小故事一般不具有独立性,因此也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故事”,而只能是某一“情节”的一部分。在大多数鲁迅的小说中,有一个松散的时间框架,但一般没有十分严密的因果逻辑关系,因而小说的组成多为事件的拼合。《孔乙己》里既写了“我”(咸亨酒店里的小伙计)在酒店里的遭遇,也写了孔乙己的故事,而且关于孔乙己的故事不止一个——被酒客嘲笑,教“我”识字,给孩子吃茴香豆,打折腿后还来喝酒,这些故事间也并不存在因果逻辑关系。《阿Q正传》里写到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阿Q被闲人们打,阿Q赌钱被抢,阿Q与王胡比捉虱子,阿Q挨假洋鬼子的哭丧棒,阿Q欺负小尼姑,阿Q恋爱的悲剧,阿Q的革命,……这些故事,虽然都发生在阿Q身上,但也没有形成因果逻辑,它们只是时间的藤蔓上结出来的一个个的“瓜果”,各有自己的色泽与芳香。
鲁迅这样来建构他的小说,是与他关注人的精神世界这一创作主旨密切相关的:只要有助于展现人的灵魂世界,一个零散的场景,一个小片段,一些小的生活细节,这些一鳞半爪就够了,何必要那些曲折起伏、上钩下连、冲突激烈的情节呢?这些平行、并列的故事,因为没有因果逻辑的组织,所以在表达的意思上也不是向某一点集中,而是呈现为相对独立的发散状态,各自有属于自己的意义。
所以,无论是总体倾向还是故事层面的复调,它们都增强了小说意蕴的丰富性,并在丰富的基础上呈现为一种颇具张力的驳杂性,反过来,则削弱了小说整体上的集中性和统一性,使小说文本无论是意蕴还是结构,都显出一种散文式的“形散”特征。
四
最后,我们来谈谈鲁迅小说的“言杂”。
鲁迅小说的“言杂”特征,是指鲁迅小说广泛使用了一些非小说文体的表达方式,如非叙事性的景物描写、抒情和议论。小说应该以叙述(叙事)为主,但这些非叙事成分在小说中大量存在时,无疑小说的叙事性就遭到了削弱。鲁迅小说的抒情在前面谈鲁迅小说的“情真”特征时已经有所涉及,这里就重点谈谈鲁迅小说里的议论与景物描写。
对于小说要叙事的文体特征,鲁迅是有充分的认识的,因此他很反感小说里有过多的议论。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中,他批评《官场现形记》“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至过甚其辞,以合时人之嗜好”的缺点,对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他则评曰“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实际上都是批评它们议论过多过滥的弊病。在为叶永臻的小说《小小十年》做的“小引”中,他指出其缺点也在于“说理之处过于多”,因此他“在校读时删节了一点”(《三闲集·叶永臻作〈小小十年〉小引》)。尽管鲁迅对小说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但由于他利用小说进行启蒙的迫切要求,他在小说创作中还是大量地使用了议论。他曾说:“不过大约心里原也藏着一点不平,因此动起笔来,每不免露些愤言激语,近于鼓动青年的样子。”(《三闲集·通信》)例如,《狂人日记》中大段大段的都是狂人对“吃人”现象的激烈的抨击,《阿Q正传》第一章“序”中对国粹派的嘲笑和讥刺,第四章“恋爱的悲剧”中关于“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及“女人是害人的东西”的议论,《端午节》中方玄绰对“索薪”、“亲领”的大段牢骚性议论,《兔和猫》中对造物主“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的责备性议论,《头发的故事》甚至全篇都是N先生的激愤的议论……这些议论文字,从小说故事的发展来说,它们不起什么作用,把它们从小说中拿掉,对故事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如此一来,小说的思想意蕴会因此而淡薄,小说的辛辣性、启蒙性和战斗性,也会逊色不少。对于在小说中使用议论,鲁迅从不讳言,“就是我的小说,也是论文;我不过采用短篇小说的体裁罢了”。[10](p190)
鲁迅小说中的景物描写,虽少而精,也为人称道: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 《故乡》
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晴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 《在酒楼上》
这些景物描写,与议论、抒情的文字一起,再加以鲁迅精炼、老到的叙述,就构成了鲁迅小说极为自由、灵活的表达方式,这与散文天马行空的自由表达是一脉相通的。而鲁迅是一个追求用笔自由的作家,从小说创作一开始,他就没有把小说当作纯粹的小说来写,他的小说只是作为启蒙的号角而出现的,所以他说:“……体裁似乎不关重要。……倘作者如此而牺牲了抒写的自由,即使极小部分,也无异于削足适履。”(《三闲集·怎么写》)
鲁迅小说的“情真”形成了鲁迅小说的抒情性,鲁迅小说的“意丰”、“言杂”形成了鲁迅小说的“散”,而且“情真”、“意丰”和“言杂”都在一定程度是削弱了叙事性,——这都表现出向散文靠拢的明显趋势,是一种大胆而有意义的向散文文体的“越界”。其结果,就是产生了现代新型短篇小说——散文化小说,它具有完全不同于中国古典小说的美学品格,是鲁迅对中国文学发展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不同于中国古代小说的娱乐功能,中国古代散文承担着严肃的“文以载道”任务,而到了现代,这一任务转移到了小说上,鲁迅的“利用他(小说)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是否意味着鲁迅小说接受了小说形式之外的另一种散文精神?
但是,鲁迅小说毕竟是小说,它的虚构性与散文的真实性还是把它们与散文区别开来;同时,它们超出一般散文的叙事性(尽管被削弱),还是显出了自己内在的文体规定性,这是我们讨论鲁迅小说的散文精神时要把握的前提。
[1][美]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2][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修订版)[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3]方遒.散文学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4]佘树森.散文创作艺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5]郭风.散文琐论[J].人民文学(函授版),1988,(5).
[6]巴人.鲁迅的创作方法[A].孙郁,等.吃人与礼教——论鲁迅(一)[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7]萧红.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座谈会记录[J].七月,1938,(15).
[8]李长之.鲁迅批判[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9]周作人.关于《阿Q正传》[A].周建人.年少沧桑——兄弟忆鲁迅(一)[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0]冯雪峰.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A].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C].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
I210.97
A
1003-8477(2011)08-0119-04
余新明(1973—),男,文学博士,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
责任编辑 邓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