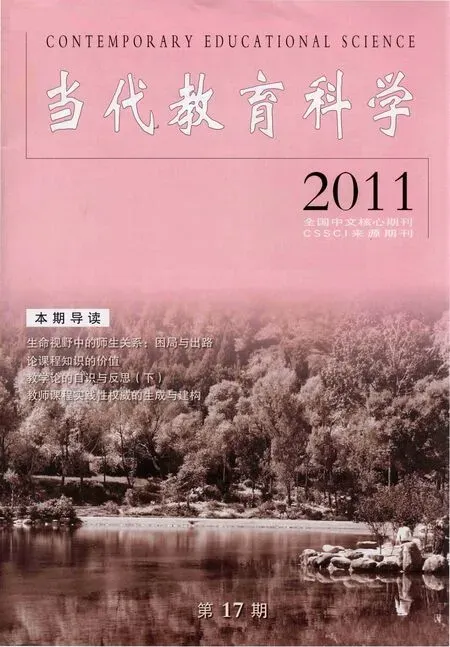植入实践的课程理论研究
——基于我国课程理论研究发展历程的考察
● 张茂坤
植入实践的课程理论研究
——基于我国课程理论研究发展历程的考察
● 张茂坤
植入实践的课程理论研究遵循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以实践问题为研究对象,以教师的教育生活为研究重点,通过实践的方式方法,引导教师关注并重构个体教育哲学。植入实践的课程理论研究范式将理论研究的品性立足于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课程理论研究“模仿”、“思辨”、“依附”的特点,从而实现对实践的引导和指导作用。
课程理论;课程实践;实践品格;理论自觉
课程改革必须“理论先行”,从而为课程实施者提供多种思维方式与角度。然而我国的课程理论研究一向注重对课程领域中基本理论、基本概念的探讨,在某种意义上淡化了对实践问题的研究。表现在实践过程中,许多课程研究工作者在对诸多具体课程问题的解决上常常是就课程而论课程,没有把课程问题置于广阔的社会与学校教育教学实践情境中加以深入的探索,提供的解决方案深奥、玄虚(甚至其本身就无任何实际价值),令实践者无法领悟或有效践行。最终,实践依旧在低层次上运作和重复,理论则成为了空洞的符号和没有生命力的装饰品。脱离实践的理论研究与脱离理论指导的实践正如康德所言:“没有理论的具体研究是盲目的,而没有具体研究的理论是空洞的”,[1]最终,两者的脱离造成了两败俱伤。回顾我国课程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我国课程理论体系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与课程实践的联系是如此之薄弱,在引进国外理论、研究课程基本理论、为政治政策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与课程实践的联系却渐行渐远。
经济学家利用博弈模型比较独立研发和合作研发的市场绩效,从而揭示企业从事合作研发的条件和内在机理。他们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比较:企业的研发投资量、产品市场势力、利润和社会福利。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技术溢出(technology spillover)是减少企业研发投入的主要原因,而合作研发可以克服这一缺陷。1998年之前的早期研究模型抽象,假设条件苛刻。而之后的近期模型放松了假定条件同时拓展了研究对象,研究朝着更为具体和细致的方向发展,也更具应用性。
一、我国课程理论研究发展历程的回顾
追溯课程发展史,尽管古代的课程思想源远流长,但是课程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从教育研究中相对独立出来是20世纪初的事情,我国的课程研究的历史则更短。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教育理论方面主要是借鉴苏联的教育理论体系和概念范畴,只有教学论,而没有课程理论,课程只是作为教学论研究的一部分而存在。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课程研究才受到我国教育界的重视,逐渐迈出了课程研究的步伐。考查改革开放以来的课程理论研究历程,我们大体上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一)课程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
这一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的课程研究是作为教学研究的一个亚领域进行的,由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三部分组成,总体上受到教学理论方法与问题的制约。处于一线的教师对课程的敏感度极低,在他们的头脑中,课程就是课程表上安排的具体科目。因而,课程在理论体系的建设中没有自觉提炼出自己的学科范畴及核心理论命题。这一阶段主要从事的研究工作是翻译、评介国外的课程思想和理论。如美国学者布赖恩·霍而姆斯的课程改革思想和麦克唐纳的课程论被最早翻译过来,之后日本学者尾崎政二、英国课程论专家丹尼斯劳顿等的课程理论被相继介绍过来。在直接翻译、介绍国外课程思想和理论的同时,我国学者还具体探讨了布鲁纳的学科结构课程论思想,并评述了美国课程论的主要流派。同时还有学者全面考察了西方课程发展的历史与课程改革。[2]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对国外课程理论与实践经验的评介,在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的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课程研究的兴趣。并且随着课程实践的全面恢复与起步,课程理论研究也走向了初步探索与反思的道路。但是,这一阶段还基本处于研究的自发阶段,在理论上依附于国外,学科身份上从属于教学领域,课程研究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二)课程理论研究的探索阶段
这一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末)的课程理论研究已不满足于对国外课程理论与课程实践的简单介绍,而是在借鉴国外课程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围绕着我国的课程的一些基本领域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与实践。课程理论工作者开始自觉的探索课程理论、积极介入课程实践中。例如对课程结构调整的关注、对综合课程与潜在课程的研究、对课程编制原理的初步探讨、对课程实践领域进行的大规模教学实验等。相对于前一阶段,我国学者初步确立并提出了有理论支持的学科命题,拓展了研究范围,涉及了课程研究的主要领域,并就一些基本的课程理论范畴作了初步的界说和阐发,建立了课程论的学科意识。但就总体来看,这一阶段仍然处于课程研究的摸索中,还未形成课程研究的独立品性。
(三)课程理论研究的应用阶段
几人不再吭声,递个眼色,努了努嘴,跟着往前走。——王爷今天气性大着呢,惹不得!逛庙会的那念头还是待明天再说吧。
(2)辛镇地区高压盐水层发育主要受沉积、断裂和构造位置的控制。沉积储层分布范围明确,断裂体系促进了油水运移,构造位置决定了油水分界。深大断裂附近的沙四上亚段储层地层水矿化度高,压力大,高压盐水层主要分布在构造部位。
二、我国课程理论研究的特点分析
课程理论研究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在指导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为什么会遭受质疑?课程理论研究的“根”究竟在哪里?这也许是我们课程理论研究者首先应该反思的问题。。这么多年来的研究,除了“模仿”、“思辨”、“依附”,我们似乎缺少了应有的“创新”、“实证”与“独立”,而这些良好的研究品质又是源于何者?我们应站在哪里?坚守何种立场?朝哪个方向前进?讨论何种话语?我们的研究才不至于成为无谓的徒劳呢?历史的发展与事物发展的本性启示我们,理论的根源在于实践,理论生成于实践,理论与实践都有着本然统一的联系:其一,理论来自实践,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没有实践,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二,理论是人类教育经验的总结、概括与升华,是历代教育实践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晶。总之,理论从根本上说来自实践,所以理论不仅是理论性的,而且还是实践性的,它应“保有实践的充盈、丰富和生动”。[7]课程理论研究的品性应当立足实践,无论是理性层次的课程理论研究还是操作层次的课程理论研究,都应是由实践而生、进而升华的过程,实践是一切真知的来源。我国课程理论也唯有立足于自己的实践,才能使得我国的课程理论研究能够真正挺起腰板,实现“直立行走”。
(一)模仿多于创新
本次选择我院接诊治疗的58例鼻出血患者,分为参照组与对照组,所有患者均符合顽固性鼻出血诊断标准,排除存在鼻内肿瘤、精神病史、血液疾病的患者。参照组患者中最大年龄69岁,最小年龄20岁,平均年龄(36.5±1.3)岁;其中女性15例,男性14例;实验组患者中最大年龄68岁,最小年龄20岁,平均年龄(35.5±1.3)岁;其中女性14例,男性15例;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中未出现差异,P>0.05,不存在统计学意义,可比。
从我国课程理论体系建设的过程来看,我们的课程理论的话语系统、学科结构、研究内容、课程的基本理论,根源上是源自于西方的。无论是课程理论研究初期的大量引进与借鉴还是当前的课程研究与创生,我国的课程理论研究深深地打上了模仿的烙印。当然,模仿并没有错,相反,引进与借鉴的目的与诉求便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它是我国课程理论体系建基的一个必经阶段。但是如果仅仅局限于模仿而不创新的话,那将无益于我国课程理论自身的发展,更不利于课程实践的发展。翻阅一下课程改革启动时期的学术论文、论著,我们便能够看到,这些所谓的理论成果对我国教育实践所做的描述、证明、提升越来越少,而更多的是用外来的理论来诠释中国的实践,用既定的课程理论程式来框定实践的发展方向,课程理论研究话语的依附性、学科思维方式的贫困与方法论的缺乏成为当前课程理论研究的客观存在。每一种理论都有其产生、存在的时代性、地域性、选择性、实践性和文化自觉性,而以引进或借鉴为主体的课程理论研究必定有别于我国实际的课程实践情境,必定产生水土不服的症状。因此,我国的课程理论研究应指向我国的课程实践场景、场域,与本土的课程实践相结合,解决实践领域中的课程问题,体现出课程理论研究的主体精神、实践品质,唯有如此,才能与西方研究者处于平等的位置上实现对话。
(二)思辨强于实证
在众多有关教育研究方法的书籍中,人们所谈到的方法主要是量化和质化的方法,它们是西方主流的理论研究方法。但在我国,思辨性研究却强于实证。就思辨性的课程理论研究而言,它并不直接通过系统的研究方法从现实实践中获取信息,而是通过经验总结或者概念推演来完成研究工作,强调概念层面的分析和理论体系的推演,注重课程价值与规范的澄清,[3]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的探讨上,如课程论的性质、学科地位、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等,研究方式讲究书斋式或者坐而论道式,研究成果具有精神引领的价值,对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思想、教育精神、教育信仰、教育理念和教育思维产生重大的影响。“没有精神和信仰的教育必定是庸俗的教育”,[4]由此足以看出思辨性研究在整个研究范式中的重要价值。但是,思辨过于强势对我国的课程实践而言却并不是什么好事,思辨强于实证,对具体问题研究较少,问题意识淡薄,导致思辨出来的课程思想的理论生成力和实践效度都很弱,无法有效指导实践。我们必须意识到,思辨性的课程理论研究模式只是课程理论研究的一种范式而已,相对于我国的课程实践,我们更应当将课程理论研究放在如何将课程理论有效的指导实践的方向上来。如果思辨只是意味着崇高,却没有实用性做支撑的话,那么由思辨而形成的理论必定是空洞无物的。
(三)依附胜于独立
“模仿性”的理论不关乎现实,对实践缺乏有效指导;“思辨性”的理论过于悬置,无法直接应用于实践;“依附性”的理论服务于政策,将实践画地为牢。无论是“模仿”、“思辨”,还是“依附”,课程理论的研究似乎都没有找到自己发展的源泉到底源自于哪里。真正的理论研究到底是怎样的?真正的课程理论如何对实践产生作用?我们认为:只有植入实践的课程理论,关注个体生存意义与价值的课程理念才能真正的走进教师的视野,融入到教师的教育生活中来。“植入”,意味着“扎根”,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教育实践这块广袤的土壤中播种、生根、发芽以至结果。因此,解决“模仿”、“思辨”、“依附”的课程理论研究的品性,必须回归到理论研究的源头,让理论及其研究回归实践、走进实践、关注实践、服务实践,让实践在反思和变革中吸收理论、应用理论、生成理论、创新理论,使两者形成良性循环和互相促进的机制,从而既促进理论的升华又促进实践的深化。“植入实践的课程理论研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质性研究或者广泛意义上的实证研究,而是有具体指向、具体内容、具体方法以及具体目标的一种理论研究范式,它对促进课程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有效的服务于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发展路径。
三、课程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植入实践的课程理论研究
由于我国教育研究,特别是近年来课程研究传统的延续,即课程研究的政策范式的导向,使得我国课程理论的研究带有非理性主义的政治解释学的色彩。政策注解式的课程研究思维方式在课程理论研究领域大有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课程研究的轴心选择和定位仍然受到政策条文的影响,相当多的理论文章以对政策的阐述代替了严谨的理论研究,忽视了研究本身的目的指向性与应有的学术价值。为政策进行官方解说成为课程理论研究者的价值所在,为课程理论研究附加行政化取向成为课程理论研究者的倾向。课程理论研究的独立性让位于权力,研究性让位于官本位,这种思想的泛滥导致了目前教育研究 “泡沫”现象,独立的与思想性的东西太少,而形式主义与浮躁的现象相当严重,功利主义侵蚀了思想的生产。学痞、学官、学奴、学霸等伪研究者[5]混迹于课程理论研究领域的现象并不鲜见。课程理论研究目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是否具有对现实教育问题的解释能力,是否能导引教育实践的不断完善,这是教育研究存在的价值所在。”[6]如果课程理论者不是基于此而是基于彼的话,也就抛弃了自我以及自我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课程理论发展基本趋于稳定、成熟,课程研究已经具有独立学科的身份、独立的研究理论空间与实践指向。课程研究者不断更新课程与教学的研究观念,大胆改革现行的课程结构和内容,加大了对课程研究的投入,课程理论研究全方位展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动为这一时期课程研究成果的应用提供了用武之地,同时也为反思我国的课程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这场声势浩大的课程改革以90年代末的素质教育大讨论为前奏,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和《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颁布为标志,在经过两年多的局部试验和强大的舆论攻势之后,终于以承载全新教育理念的角色走上了历史的前台。课程理论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不可小觑,使人们对课程的认识更加的深入人心,但留给我们更多的是反思。有人批评课程理论界的主导舆论基本上是源于西方后现代课程理论,根本不适应中国课程改革的发展,无法承重中国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也有人认为书斋式的课程理论研究演绎的是一种学术作秀的伪理论,对课程的实践的指导意义微乎其微;另有学者也提出了理论研究的“去行政化”倾向……这些问题充分反映了当下我国课程理论研究过程中的种种矛盾、不适与纠结,当然也为当前课程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生长点。
(一)研究对象:一切问题应从“根”上来研究
从课程理论发展初期到现在,我国的课程理论研究已经走过了近40年的历程。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动与结束是对我国课程理论研究的一次实践历练,它不仅映射了近十年来我国课程理论研究的发展水平,更是将整个课程理论研究历程作为一个整体而加以重新认识,从课程理论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课程理论研究的三个特点:
(二)研究内容:以研究教师的教育生活为重点
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讲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课程理论工作者与教师的关系,课程理论者要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彰显其存在的价值,首先要实现自我身份的“祛魅”:深入实践,理解实践,尊重实践及其自身的逻辑性和规律性,而不是“用逻辑的实践代替实践的逻辑”(布迪厄语)。教育实践的主导者是教师的教育生活,生活是需要“过”的,教师“过”教育生活的过程即是教师发展样态的真实写照,也是课程在实践中的表现形态。教育生活由一个个活生生的教育情景链接而成,教育情景的产生、发展、结束不仅体现了教师行为的全过程,而且也是课程授受的全过程。因此,课程专家要在实践中研究课程的真知,必须以教师的教育生活为重点内容,从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发现课程发展的轨迹、问题与方向,并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起的课程理论研究成果才能真正的、有效的服务于实践。
(三)研究方法:探索植入实践的课程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
近几年,随着人们对课程理论界的质疑,课程专家也开始反思理论的研究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在对“自上而下”的课程理论建构路径批判的基础上,已经开始着力构建一种“自下而上”的建构通道:即通过对教师教学实践的观察和描述来分析影响课程教学的因素,或者是与教师进行深度的访谈进行个案研究,或者是大学的教育理论者和中小学校结对实施“专家引领”下的课程变革等。这些实践方法对于促进我国课程理论的实效性以及课程理论本身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下的质性研究、实证研究、叙事研究、扎根理论等都为课程理论的实践化提供了良好的方法。我们在此应积极的去实践这些方法,从而为我国课程理论的建设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一线资料,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理论的建构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研究目的:引导教师关注并重构个体的教育哲学
教师作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他们对课程有着更为直接的理解,他们对课程理想、课程精神、课程价值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与认识,这些见解与认识在其长期的课程实践中逐步汇集成为教师的教育思想,并成为随时随地影响着教师课程实践的教育哲学。课程理论在推广的过程中遭遇阻隔的原因也在于此,它虽然关注了课程实践,但却忽视了思想的巨大力量。正如帕斯卡尔曾言,人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可是,这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因此,课程理论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向人们证明理论的“合理性”、“正确性”、“学术性”,更重要的在于能够指导人们的实践并使实践工作者能够积极主动地走进理论,学习理论,“读懂”理论,用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把理论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形成自觉的理性方式和批判意识,努力使实践成为理论的一种实践观照。[8]引导教师审视既有的教育哲学,就是要求课程理论研究者要引导教师反思其课程教学,通过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换,构建符合变革时代品质要求的课程观,以推进课程改革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诉求。课程理论唯有激发教师内心理论的需求,对其课程教学生活及教学行为背后所支撑的教学观予以批判反思,结合自身的教学理解寻求课程教学的改进与创新,才能把课程理论的学习由外在的要求转化为自我发展的内部动力,课程理论研究也才因此而落到实处。
植入实践的课程理论研究不是抛弃、否定原有的课程理论研究的成果,而是注重源头发展,继承创新。如果前一阶段的引进、借鉴,我们称之为“博采众长”的话,那么这一阶段的实践历练就是“厚积薄发”,最终实现的将是课程理论研究的“大放异彩”:彰显主体性的课程理论研究意识,构建系统的课程理论研究结构,呈现鲜明的课程理论研究生命,树立卓越的课程理论研究品质,从而建立起独具我国特色的课程理论大厦。
[1]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孟,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4.
[2]李定仁,徐继存.教学论研究二十年(1979-1999)[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48.
[3]李黔蜀,于泽元.论思辨性课程研究意涵与基本方法[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9,(6).
[4][8]余文森.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层级和关系[J].中国教育学刊,2010,(9).
[5][6]任永泽.福柯的考古学方法对教育研究的启示[J].教育导刊,2010,(11).
[7]宁虹,胡萨.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本然统一[J].教育研究,2006,(5).
张茂坤/山东临沂大学费县校区校长助理,办公室主任,副教授
(责任编辑:孙宽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