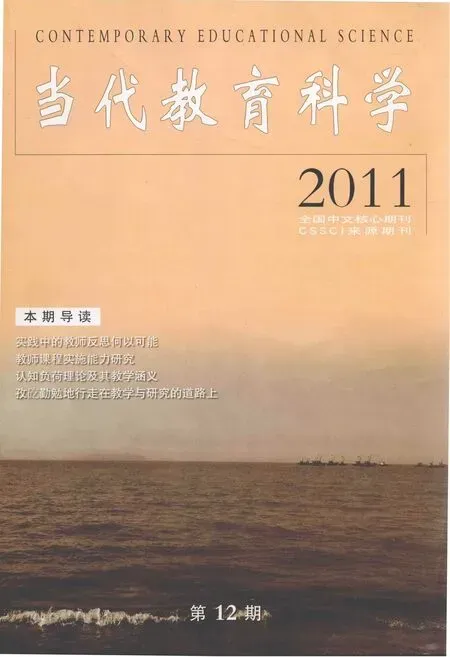论课程研究的后现代品性
● 李志超 靳玉乐
论课程研究的后现代品性
● 李志超 靳玉乐
课程研究领域正在经历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即从单一的学科主导性研究范式发展到多元的科际包容性研究范式。它规避了“课程是什么”的概念泛化所造成的课程定位无根性、课程发展无效性。在将富含逻辑的科学性、涵泳想象的故事性、充满体验的游戏性有机结合的过程中,重新赋予课程以鲜活的生命力,彰显其内在的后现代品性。
课程研究;科学性;故事性;游戏性
课程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胶着于“课程是什么”之类众说纷纭的话题。而是在从单一的学科主导性研究范式向多元的科际包容性研究范式的发展过程中达成了共识,开创了融科学性、故事性和游戏性于一体的课程研究新时期。
一、作为科学的课程研究
科学性是课程研究的基本规范。课程研究不是扩散的随意性组织,而是有计划的专业性活动。课程研究的科学性希冀于超脱空玄的纯粹哲学理路和浮庸的日常生活脉络,在对其内在基本逻辑体系和组织框架的认识日趋成熟的基础上成为时代的精神。时代的使命感和社会的责任感赋予课程研究在科学性表征中显现出形而上的理性价值追求和形而下的恰切逻辑范畴。形而上的理性价值追求,意指课程研究依托于批判性思维,在否定中肯定,在质疑中推理,从而不断发现新问题,形成新认识。从基于“社会”和“共同经验”的要素主义与永恒主义课程到定位“个人”和“兴趣”的进步主义课程,从倡导知识结构的学科结构主义课程到知识“去中心”化的后现代主义课程,无不体现着课程研究的价值取向由“理想”向“现实”中变迁。形而下的恰切逻辑范畴则明确了不同课程研究范式的基本准则和内容体系。即,实质性现象—指目标、学科内容、材料等课程的基本范畴,探究他们的实质和价值;政治—社会现象—关注课程发展的政治和社会过程;技术—专业现象—着重探讨那些使课程得以改良、配置和取代的个人和团体过程。[1]言而总之,科学性作为课程研究深化的动力机制,不仅夯实了课程研究的规范性基石,而且使课程研究在对自身实然性把握的基础上揭开了应然性面纱。
真理再往前一步往往会成为谬误。课程研究严格恪守“摇镜扫描”技术,努力使图像和屏幕相符应的同时,成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科学认知范式。早在16世纪,巴黎大学的拉莫斯在《知识地图》中就提出课程体系是一个连续而完整的线性统一体,教学应秩序化地逐级进行。20世纪40年代末,泰勒提出了以目标为中心的课程原理。这是经过学校办学宗旨和学习理论加以筛选形成的。在他看来,“行为”和“内容”是型塑课程目标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但在现代实证主义科学范畴下,他的课程目标难以摆脱技术理性的支配,体验化“内容”成为规约化“行为”的牺牲品。凡此种种,课程理论在研制中以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样态依托于社会实践而存在,并没有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这一“反理论”、“反历史”的课程开发“处方”,追求永恒不变的“唯科学主义”真理观,信奉物质资料再生产的技术理性策略,全然无视“价值关涉”的实践活动。课程研究成为一种规约化的模式体制。
“科学的使命是发现‘真正’的本质及其‘真正的’运作方式。”[2]后现代课程研究所攻击的是拥有特权、唯我独尊的“科学”概念下所产生的科学沙文主义,所摒弃的是超验的、固定化一的、唯我独尊的科学方法。[3]后现代课程研究的合理发展依傍于富含理性逻辑的科学方法,洞识隐藏于现象深处的问题并将其连根拔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透过字面行文,从拥挤的文本中寻找曾经失察过的话语,在“视界的流变”中推动“问题域的转换”。置身于有待关心爱护的课程大花园中,我们要保持科学作为逻辑缜密的研究方法的锐利性,采用整体性和关系性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在批判性的价值观引领下,通过对课程研究纵向式的深度演绎和横向式的广度探讨,达成其内在品性适度和完整的平衡。“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课程研究得以青春永驻,同样需要“科学共同体”的建构。“科学共同体是产生知识的单位,它是一个给定专业的从业者们,由他们的教育和训练中的共同要素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了解彼此的工作,其特点是他们在专业方面的思想交流时比较充分的,他们在专业方面的判断也是比较一致的。”[4]课程研究中,无论是科技取向课程范式还是人文取向课程范式,其内部成员都是在充分的思想交流和稳定的研究热情中,逐步形成共同的心理积淀、共同的理论假设和共同的研究方向。来自“科学共同体”的公认信念使课程研究能够以其特定的理论体系和逻辑起点为基础,进而建构的概念、原理、法则都能“持之有故,言之有理”。
二、作为故事的课程研究
故事性使“濒临死亡的边缘”课程研究在丰富的想象力中得以复活。“以往的课程灵魂必须被摆渡到永不回归的彼岸安息,而在此岸的我们,则需要获取新的灵魂。这并不是说我们想要摆脱任何控制,而是说我们想要另一种新的、更有活力的精神来控制我们。”[5]这需要我们在生活的“搏动”①、情境的际遇中发现课程之真,体验情感和理性共融所带来的课程之美。故事性的课程研究所追求的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而不掺杂人为因素。丰富的情感使得课程不再是由冰冷的知识建模所构成,而是热情洋溢的生命个体对知识的领悟与抉择。抽象意义的知识通过栩栩如生的故事性讲述得以表现,在情感的软着陆中实现了内在扩充。这是课程在人文关怀下寻找其所失落的精神世界,是课程从技术理性的高空中回归充满人性的生活世界。正因为生活世界是人在实践活动中获得教育的世界,是人之自我建构的世界;所以课程在实践、交往、理解和感悟的生活世界中充满了情趣,彰显了个性,从而得以升华。
理想和现实之间往往总会有所偏差,把握不好,则会误入歧途,步入极端。故事性的课程研究之所以饶有趣味,在于其内含着丰富的艺术性。可以说,没有艺术性的支撑,这一娓娓道来的故事难免会有些许晦涩。艺术需要技能技巧,但却不等于艺术就是技能技巧。课堂中赶时尚、走时髦,往往导致表演课、示范课走过场,轰轰烈烈过后,教师和学生仍然是其中的局外人。这种过分地对“艺术”的追求,无异于对课堂打了一剂强胰岛素,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儿童的学识品性虽表面看起来得到了充分补给,其实质却是内在心理品质疏松脆弱的畸形发展。启迪心智、发人深省的雅艺术成为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俗艺术。故事性的课程研究中,回归生活世界的呼唤不绝于耳,可是回归什么样的生活世界却并没有交代清楚,给人一种似是而非、模弄两可的感觉。简单地认为回归生活世界就是悬置知识,回归生活世界就是实体现象的自在表征,那只会从“玄思”的哲学滑向“空洞”的生活。一味地将课程知识和生活世界相剥离,其实质是在课程研究中追求“主客二分”的认知方式,不但不利于课程走向实践,反而会使课程僵化。
故事性的课程研究是启迪学生心灵的艺术的活动。它不是一种单维度的技术指向,而是多向度的思维方式在实践中的路径。它首先考虑的是情境因素。情境常常发挥着“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潜在作用。学生正是在课堂事件的耳濡目染中受到启发,从而产生对知识的热爱。言而总之,我们所体验到的热情和愉悦无不是在内在心灵与教育情境的相互作用中所生成的。其次,它根据学生的心理发展需求和知识的基本逻辑,通过在二者之间合理架构,引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在激励学生的自信心中调控学生的学习状态。不同的学生其内在的心理发展水平不同,对知识结构的认识和理解也不尽相同。课程的内在故事性不是千篇一律的一致性,它通过对学生因材施教,使不同的学生得以充分理解其内在的真谛。
三、作为游戏的课程研究
游戏性是课程研究的存在方式。游戏并不是“玩耍嬉戏”的流俗化理解,“游戏是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这种活动或消遣是在某一固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其规则是游戏者自由接受的,但又有绝对的约束力;它以自身为目的并又伴有一种紧张、愉快的情感,以及对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认识”。[6]显而易见,游戏是游戏者之间互相尊重事先制定的准则,在经历活动的过程中,所表露出的情感体验。“游戏的真正主体并不是游戏者,而是游戏本身。”[7]这是“自我”在游戏过程中达到了“忘我”而充分沉溺于其中的自我表现,是生命体的人诗意地生活在世界中所感受到内心精神体验。这种精神指向人的智慧,追求生命的激情;指向生活的想象,赋予人在交往过程中拥有一种家园感的亲情关系;指向自我的自主投入,反对外界的强制压迫。一言以蔽之,游戏性的课程研究充分尊重了人的自然发展规则。学生的发展并不仅仅依赖于知识、技能等正规教育的社会文化力量,更重要的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等非正规教育的社会文化力量熏陶。将课程作为一种游戏来理解,使其突破了传统知识认识论的限制,将“成物”的“知识人”提升为“成人”的“游戏人”。参与者不是孤立地将课堂和教学当作客体对象加以认识和把握,而是能够根据其中的具体情境相应地作出调整,实现其与参与者之间的融合,参与者对知识的获取实现了以自身的生命、生活、生长、生成为契机的意义感悟。将课程作为一种游戏来研究,由情入景、以景激情,不仅使学生的智力在自我更新中获得了发展,而且学生在体验的关怀下培养了自己的道德情操和审美修养,从而解决了学生自身的分裂问题,构建了启智立信,知、情、意和谐共生的完人。
现实的操作往往会扭曲美好的愿景,制度化的教学对学生发展的过度重视,使“寓乐于景”的游戏失去了其鲜活的品性。军队式的训育体制使内在自我在越来越受管制的生命中失去价值感,在追问存在者的呼唤中忘记了存在者本身。从夸美纽斯的班级授课制到赫尔巴特的教育科学化,从斯金纳的程序式教学到布鲁姆的教学目标分类学,无不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抽空了学生具体生活中的意义。追求效率至上的课堂教学因高度技术化、程序化因素的渗透犹如一档“麦当劳”快餐,过分注重于应用性的提高,忽视了原创性和多样性的发挥。游戏不再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为了休息之故”而产生的活动,虚无化的精神品性致使课程开拓出的是封闭而抽象的逻辑路径,学校窒息于僵死而无活力的观点以及孤立而无生命的情愫。当然,如果没有一定秩序化教学的约束,游戏在课堂中则等同于纵欲。游戏人怎么想就怎么做,个人之私欲的不断膨胀遮盖了公众情怀的价值。这不仅不利于学生学习自我效能的提升,也不利于教师专业化的发展。
真正的教育是“人之成人”的教育。游戏性的向往焕发了课堂的生命活力,使课程研究从“祛魅”中“返魅”。游戏性的课程迫切需要把教师和学生从知识的权威中解放出来,通过“心理的现实感”和“欣赏感”对课程进行“自我意识概念化”,在课程从“跑道”向“跑道上跑”的转变过程中寻求自我的灵性—智慧、顿悟、直觉、想象。游戏的课程不是教师和部分优秀学生的游戏,而是课堂活动中所有参与者所共同拥有的一个活动。课堂中游戏性意义的升华,得以在师生、生生之间平等、民主的“我—你”会话的实现。每个参与者在都享有话语权力的同时,也在彼此交流中不断倾诉自我,倾听他人。“会话是一个逐渐形成理解的过程。因此,在真诚会话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向他人开放,真诚地认为对方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并且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对方以及他所说的一切。”[8]也就是说,每个人作为游戏的积极参与者,都是站在自我本位的立场上不断用他者的思维理解他人,进行转化性创造,使自我体验的课程得到恰切发展。它打破了“我—他”的压迫关系所造成的跷跷板现象,使游戏作为一种不间断的活动得以持续下去。
注释:
①注释:“搏动”在此指在经验中心跳动的心脏,是一种鲜活性的表征,它取代的是正处于我们认识论中心的充斥着言辞抽象的冰冷而贫瘠的世界。具体详见:[美]小威廉姆 E.多尔,[澳]诺尔·高夫.课程愿景[M].张文军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218.
[1]江山野等.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课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61.
[2]周作宇.没有科学,何来主义?——为教育研究中的“科学主义”辩护[Jl.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4):19.
[3]王治河.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增补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35.
[4]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20.
[5][美]小威廉姆 E.多尔,[澳]诺尔·高夫.课程愿景[M].张文军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31-32.
[6][荷兰]约翰·胡伊青加.人,游戏者[M].成穷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35.
[7][8]Gadamer,H-G.Truth and Method[M].New York:Continuum,1993.107-112,385.
李志超/西南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靳玉乐/西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责任编辑:张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