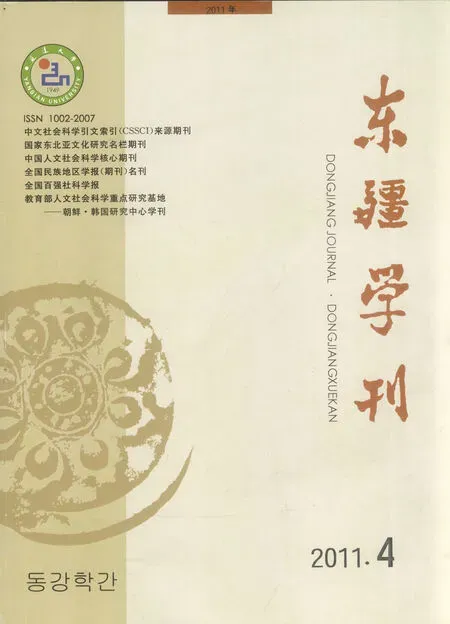隐性与显性:犯罪嫌疑人确认的两个阶段
尹茂国
隐性与显性:犯罪嫌疑人确认的两个阶段
尹茂国
犯罪嫌疑人是一种角色主体,对其确认可以分为隐性与显性两个阶段。立案、采取强制措施、第一次讯问及通缉等诉讼行为是犯罪嫌疑人由隐性转为显性的主要方式。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由于隐性与显性两个阶段的界定模糊,从而导致侦查权的膨胀、犯罪嫌疑人非正常隐性化及诉讼权利失衡等问题的存在。因此,对犯罪嫌疑人隐性与显性的明确界分,将有助于实现对侦查权的法律规制及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隐性与显性;犯罪嫌疑人;权力规制;权利保障
一、确认犯罪嫌疑人的两个阶段
犯罪嫌疑人并非源于自然,而是在特定情境下,在具体的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由于在立法中所享有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不同,从而导致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不同,并成为具有独特利益追求的一种角色主体。
(一)隐性阶段
隐性阶段主要是指从侦查机构确认某一社会个体为犯罪嫌疑人,到向犯罪嫌疑人或社会公开之前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
第一,已经确认了犯罪嫌疑人。这个阶段是处于由犯罪嫌疑对象上升为犯罪嫌疑人之后的阶段。从总体上而言,犯罪嫌疑人也是犯罪嫌疑对象之一,只不过犯罪嫌疑对象处于不确定、不具体状态,而犯罪嫌疑人则是侦查机构根据所掌握的事实和证据,在排除非犯罪可能性的基础上,将侦查对象具体在某个或几个具体的社会主体身上,并围绕该主体展开专门调查工作或采取有关的强制措施。因此,犯罪嫌疑人是已经被确认、被具体化的犯罪嫌疑对象。
第二,尚处于不公开状态。尽管在隐性阶段,犯罪嫌疑人已经得到确认,但侦查机构尚没有对社会及犯罪嫌疑人公开,因此,此时的犯罪嫌疑人只是侦查机构视角中的犯罪嫌疑人,社会及犯罪嫌疑人则处于不知情状态。这里的“公开”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侦查机构没有向犯罪嫌疑人或社会公众公开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二是侦查机构没有向具有司法审查职责的司法机构公开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第三,权利保障处于消极状态。隐性状态并不表明侦查活动的停止,只不过是说,一方面,侦查活动处于不公开状态,还没有对社会与犯罪嫌疑人公开;另一方面,侦查活动没有涉及公开损减犯罪嫌疑人权利的问题,犯罪嫌疑人没有权利保障的必要性或无法采取权利保障的措施。在这个阶段,以积极方式来对抗权力侵害的诉讼权利没有存在或行使的空间。如果侦查机关采取了损减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侦查活动,而犯罪嫌疑人仍处于不知情状态,那么就构成了侦查权力的滥用。
(二)显性阶段
显性是指侦查机构通过一定方式,使犯罪嫌疑人这一角色处于公开状态。这种公开状态并不必然地表现为对整个社会的公开,而是表现为由侦查人员内心确认的犯罪嫌疑人转为向其他社会主体公开的犯罪嫌疑人。这种公开既可以表现为直接向犯罪嫌疑人的公开,也可以表现为向被害人及负责司法审查的司法机构的公开。
1.由隐性到显性的必要性
侦查机构向社会及犯罪嫌疑人公开这一身份,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
第一,制止犯罪的需要。有些犯罪尚处于进行当中,需要侦查机构首先采取强制措施加以制止,以维护社会秩序,防止犯罪后果进一步扩大。
第二,调查取证的需要。通过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以防止其逃避侦查或对证据的破坏。另外,讯问犯罪嫌疑人也是调查取证的重要方式之一,无论犯罪嫌疑人是采取积极辩护的方式,还是采取保持沉默的方式,这都是对所涉及犯罪的一种反应,对于进一步的调查取证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缉拿犯罪嫌疑人的需要。对于在逃犯罪嫌疑人,当需要依靠社会力量来缉拿犯罪嫌疑人时,则存在向社会公布犯罪嫌疑人身份的必要性。
第四,诉讼公正的需要。如果刑事诉讼是在秘密中进行,最后只是告知犯罪嫌疑人一个结果的话,那么这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讲是不公平的。犯罪嫌疑人不只是处于被动的接受角色,还可以进行积极的参与。犯罪嫌疑人可以通过法定诉讼权利的行使,来捍卫自身的实体权益。
2.由隐性到显性的方式
关于犯罪嫌疑人的确定问题,有学者认为确定犯罪嫌疑人身份是从第一次讯问开始,第一次讯问使得被讯问人开始享有法律赋予的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并认为以采取强制措施来认定犯罪嫌疑人是不正确的,应该是确定犯罪嫌疑人在前,采取强制措施在后。况且,有些案件并不采取强制措施,不能认为不存在犯罪嫌疑人。[1]笔者认为,无论是采取强制措施,还是第一次讯问,都是建立在犯罪嫌疑人已经被确认的基础上,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确定,则采取强制措施和讯问等问题都无从谈起。而第一次讯问及采取强制措施,均是犯罪嫌疑人由隐性到显性的方式之一,二者之间并不是一种排斥关系。另外需要澄清的是,犯罪嫌疑人的确定与犯罪嫌疑人行使诉讼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没有利益及利益冲突,也就没有权利,没有权利也就无所谓权利保障。在犯罪嫌疑人处于隐性状态时期,政府与犯罪嫌疑人没有正面接触,不存在从犯罪嫌疑人身上直接获取利益的情况,因此,犯罪嫌疑人也无所谓运用权利来抗衡政府、制约政府以维护权益的问题,此时,犯罪嫌疑人不具有行使诉讼权利的机会。犯罪嫌疑人由隐性转为显性,主要通过这样一些诉讼行为体现出来:
第一,立案。以立案作为犯罪嫌疑人已被确定的表现之一,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世界各国关于立案的规定并不一致。“综观世界各国有关诉讼立法,除前苏联、东欧和蒙古等国家与我国一样,将提起刑事诉讼即立案作为独立的诉讼阶段在其刑事诉讼法典中加以明确规定以外,法国、美国、英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的刑事诉讼文法都不将立案视为独立的诉讼阶段。”[2](213)就犯罪嫌疑人的确定而言,立案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侦查机构只是确定有犯罪事实发生,但并不确定犯罪嫌疑人;这种情况下的立案并不能起到确定犯罪嫌疑人的作用。如公安机关接到报案,称有人被杀,经核实后认定为他杀,犯罪事实发生,即可立案侦查,至于犯罪嫌疑人的确定则有待于进一步调查。二是犯罪嫌疑人已确定并向社会公开的立案。这往往发生在举报或侦查机关通过一案牵扯出他案的情况中。
第二,采取强制措施。强制措施种类很多,如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搜查、扣押、冻结等等。对社会主体采取强制措施,就是犯罪嫌疑人由隐性到显性的过程。因为强制措施涉及到犯罪嫌疑人权利损减的问题,必须要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抗争的能力,以防止政府滥用职权,不合理地侵害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诉讼权利则是犯罪嫌疑人对抗侦查机构,以维护自身实体性权利的有效手段。
第三,第一次讯问。在侦查阶段,讯问的对象只能是犯罪嫌疑人,这是侦查机构与犯罪嫌疑人正面交锋的关键环节,因而也是权利需要保障的重要领域,其中以第一次讯问尤为重要。它既是侦查机构向犯罪嫌疑人所进行的一种“宣战”,以公开的态度表明已将被讯问人纳入犯罪嫌疑人的范围之内,同时也是犯罪嫌疑人获取对抗权利的开始。犯罪嫌疑人既可以通过消极防守的途径,也可以采用积极抗争的方式来维护其合法权益;既可以依靠自身力量来予以抗争,也可以借助外力来实现有效抗辩。
第四,通缉。通缉既是查获犯罪嫌疑人的一种手段,也是向社会公开犯罪嫌疑人身份的一种方式。一旦被通缉,犯罪嫌疑人将处于可以被随时缉拿的状态,因而也应该拥有随时为自己申辩的权利等。
二、隐性与显性界定不清所导致的问题
对犯罪嫌疑人与嫌疑对象、犯罪嫌疑人隐性与显性的研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理论性的探究,更是出于权利保障的实践需要。尤其是在立法尚不健全、没有将所有可能涉及个体权利损减的强制措施都纳入法律调整范围之内的社会,这种划分更具有现实意义。我国在犯罪嫌疑人的界定方面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一)嫌疑对象犯罪嫌疑人化对待
例如我国《警察法》第9条规定的警察盘问权,就具有嫌疑对象嫌疑人化的倾向。其一,“盘问”的模糊定位。从性质上看,盘问应当是一种询问,而不应当是讯问,但盘问后,警察却可以根据盘问情况,决定进一步采取拘留或其他强制措施,因此,结果上又起到了讯问的效果。其二,证明标准低下。现场盘问只是要求有嫌疑即可,而带至公安机关继续盘问,也只需要“(1)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2)有现场作案嫌疑的;(3)有作案嫌疑身份不明的;(4)携带的物品有可能是赃物的”。在缺乏中立第三者审查的情况下,是否存在嫌疑也只是警察自身的一种判断而已,带有较大的伸缩性。其三,可以限制人身自由。留置时间最长可达48小时,而且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不存在来自司法审查机构的审查。这种嫌疑对象嫌疑人化处理的方式,极易造成警察权的膨胀和个体权利的损减。
(二)隐性犯罪嫌疑人显性化对待
侦查机构的主要职责就是调查犯罪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这也是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利益所在。一般而言,以懈怠职权的方式来放弃利益追求,无异于否定自我的存在价值,这是任何权力行使主体都不愿意采取的一种方式。在职责要求无可回避的情况下,选择以最便捷的方式来实现利益追求,便会成为侦查机构的首选。在特定社会条件的限制下,当损减权利成为获取利益的一种捷径时,便会出现把嫌疑对象嫌疑人化对待、隐性犯罪嫌疑人显性化处理的现象。以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秘密侦查行为为例,秘密侦查行为直接涉及到个体的隐私权保护问题,因此,也是各国刑诉立法重点调整的内容之一。如美国立法就要求除特殊情况下,搜查必须要得到法官的批准,否则就构成违法。但侦查人员以普通社会个体的自然感知能力和方式,在普通民众所能够涉猎的领域所进行的观察,不被视为是一种搜查;侦查人员从普通飞行器和正常航线内所能观察到的视角进行观察,不被视为是一种搜查等等。[3](64~65)这实际上就是要求,隐性犯罪嫌疑人必须以隐性化的手段来对待,不允许以显性化的方式来对待隐性犯罪嫌疑人。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由于缺乏关于秘密侦查行为的具体规定,从而使得该行为成为侦查机构视情形自行决定的事项。如侦查机关可以在不经中立第三者审查的情况下,自行决定秘密窃听隐性犯罪嫌疑人的电话、查阅隐性犯罪嫌疑人的信件等等,这些侦查行为均已对犯罪嫌疑人的隐私权构成了侵害,但犯罪嫌疑人尚处于不知情状态,无法对自我的权利进行有效救济。而事实上,隐私权是重要的宪法权利,也是不能被任意克减的权利之一。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与实践中的做法,实际上是将隐性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显性化处理,但在性质上却又界定为隐性犯罪嫌疑人,属于隐性犯罪嫌疑人被非正常的显性化。这不仅为侦查权的肆意制造了温床,而且也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造成了困难。
(三)犯罪嫌疑人显性化的手段欠缺正当性
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将犯罪嫌疑人显性化,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的理念问题,并进而涉及到对显性化手段和方式的正当性评价。以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为例,我国在犯罪嫌疑人显性化的方式和手段方面,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使犯罪嫌疑人显性化的主体欠缺中立性。我国刑事诉讼中,除了逮捕这一强制措施以外,拘留、搜查、扣押等强制措施均可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逮捕虽然由检察机关审批,但检察机关从性质上而言,与侦查机关同属于控诉机构,并非与控诉利益无涉的中立者,因而难以保证犯罪嫌疑人显性化过程中的公正性。
第二,犯罪嫌疑人显性化的情形欠缺规范性。以搜查为例,主要表现在搜查理由和无证搜查两个方面。一是搜查理由的随意性。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09条的规定,只要侦查人员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就可以自行作出搜查决定,以目的的正当性掩盖了对搜查理由的合理性审查。二是无证搜查情形的不规范性。刑诉法第111条:“进行搜查,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在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遇有紧急情况,不另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但并没有规定在执行逮捕和拘留的时候,遇有哪些紧急情况可以无证搜查,也没有规定搜查的范围和界限,更没有规定在非执行逮捕和拘留的时候,是否可以无证搜查,从而使得无证搜查情形不具有规范性。而其他多数国家对此均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如美国对无证搜查情形就作出了较为详细的列举,规定了附带于逮捕后的无证搜查(Search Incident to Arrest)、对汽车的无证搜查(A utomobile Search)①这里对汽车的无证搜查,并非指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进行,只是在特定情况下才可以采取。一般包括以下三种情形:一是实施逮捕时由被逮捕人实际控制的区域;二是在紧急情况下;三是根据警察部门的规定,需要对被扣押车辆进行物品登记的。参见Ronald J.Bacigal:Criminal law and Procedure:An Introduction,WEST LEGAL STUD IES,2002:201.、经同意后的无证搜查(Consent Search)、紧急情况下的无证搜查(Search Under Exigent Circum stances)等等,并对每种情况的适用条件作出了严格规定。
(四)显性阶段权力与权利的配置失衡
侦查机构一旦以某种方式公开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就意味着一种对抗的开始。侦查机构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对抗不是一种纯粹力量的比较,而是在法律规则指引下的一种理性抗争。在正当程序原则之下,这种对抗应当是一种平等对抗,而平等与否的关键在于权利与权力的平衡程度。就我国显性犯罪嫌疑人而言,权利与权力处于失衡状态,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基本诉讼权利的缺失。我国侦查阶段中,无罪推定权的不完全确立、不自证其罪权的缺失等等,客观上造成了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构之间的失衡对抗状态。其二,手段性权利的匮乏。基本诉讼权利的设立仅仅是平等对抗的前提,能否实现的关键在于手段性权利的到位状况。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这是犯罪嫌疑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而围绕该权利的实现所设置的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可以视为是手段性权利。由于立法中缺乏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的规定,而司法实践中,律师的会见权又备受阻滞,从而使得获得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这一目的性权利难以得到实现。其三,程序性救济权利的缺位。犯罪嫌疑人由隐性到显性的过程,往往就是犯罪嫌疑人权利损减的过程,如因被采取强制措施而转为显性就是一个实例。强制措施总是意味着一定权利的损减,对于非法实施的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应当具有救济的途径。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的问题,不在于没有规定具体的程序性救济措施,而在于缺乏由中立第三者进行司法审查的制度。由于犯罪嫌疑人不具有启动程序性裁判的诉权,从而使得对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审查,仅仅限于决定机构的自我审查,或者由担负着控诉职能的检察机关进行审查,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机制,难以保障程序公正的实现。
三、界定隐性与显性阶段的意义
(一)有利于实现对侦查权的规制
权力具有扩张的一面,“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和道德界线的诱惑”。[4](376)侦查权是一种积极权力,即侦查人员必须通过积极的方式来履行自己的职责要求。而侦查人员所负有的调查犯罪事实、收集证据、缉拿犯罪嫌疑人的职责任务,也决定了侦查权是最具有进攻性的权力,是最易于与犯罪嫌疑人权利发生冲突的权力。当权力界限不明确或缺乏制约力量时,侦查权主体就会利用自身力量上的强大,直接以损减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职责任务。这要求当主体处于嫌疑对象或隐性犯罪嫌疑人阶段时,则要求侦查机构不得以损减公民名誉权、人身权、自由、隐私权及财产权的方式,来实现其职责任务。而当主体已经客观上处于显性犯罪嫌疑人阶段时,则不允许侦查机构仍然以隐性的方式来对待犯罪嫌疑人。从手段上看,侦查机构已经采取了损减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侦查措施,该措施足以使隐性犯罪嫌疑人转为显性犯罪嫌疑人。但从结果上看,该措施并未产生隐性犯罪嫌疑人显性化的结果,从而客观上造成犯罪嫌疑人权利已处于被损减状态,而除侦查机构外,包括犯罪嫌疑人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体却处于并不知情的非正常状态。如我国侦查机关所采取的秘密监听、秘密搜查、对信件的秘密监控等等,都属于此类情况,客观上造成犯罪嫌疑人处于权利已被损减但却无权予以对抗的状态。因此,对隐性与显性犯罪嫌疑人的界定,有助于实现对侦查权的制约和控制。
(二)有助于完善权利的保障机制
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主要涉及两大部分:实体权利与诉讼权利。实体性权利主要通过消极和积极两种方式来实现。所谓消极方式是指权利主体不需要以积极方式来追求权利的实现,而只是要求权利相对方恪守义务,不实施权利侵害行为,即可实现对权利的保障,这类权利往往表现为一种对世权。积极方式则表现为权利主体以积极的作为方式来追求权利的实现与保障。刑事诉讼权利根据权利指向不同,可以分为实体性诉讼权利及救济性诉讼权利。实体性诉讼权利直接指向实体性权利,如刑事诉讼中的辩护权及不被非法搜查、逮捕等权利,均以人身权、自由及隐私权等为指向,构成刑事诉讼权利体系的核心内容。救济性诉讼权利则以实体性诉讼权利为指向,如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诉权当属此类。当犯罪嫌疑人处于隐性阶段或者社会个体处于隐性之前的阶段时,表现为权利主体以消极方式来实现权利的保障。即权利主体不以积极作为方式来维护权利,而是要求刑事诉讼权力主体不得以损减权利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职责需要。当犯罪嫌疑人处于显性状态时,则要求一方面赋予犯罪嫌疑人实体性诉讼权利,以保障其实体权利免于非法侵害;另一方面需要设置有效的权利救济手段,以保障其实体性诉讼权利的实现。通过对犯罪嫌疑人隐性与显性的界分,来确定在不同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重点和方式,从而有利于实现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三)促使刑事诉讼程序更具合理性和正当性
从根本上讲,刑事诉讼的发展过程实际就是在保障最基本人权的基础上,以多大权利代价来实现追诉犯罪、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没有最基本人权保障的秩序是缺乏道德性的、低层次的秩序;而秩序无法保证基础上的人权保障,也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因此,在基本人权得到保障的基础上,以最小的权利代价来实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标,这是最为理想的选择。对犯罪嫌疑人隐性与显性阶段的界分,不仅仅要求当犯罪嫌疑人需要显性化的时候,侦查人员只是向犯罪嫌疑人或社会作出宣告,而是对通过何种方式进行显性化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尤其是需要以损减犯罪嫌疑人权利方式来进行显性化的时候,则不仅要求一个与争议利益无涉的中立者来行使最终的决定权,而且还要赋予犯罪嫌疑人行之有效的救济权利,来实现对侦查权的制约和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在刑事诉讼基本目标得以实现的基础上,通过不断降低权利代价的程序设计,无疑更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
[1]刘梅湘:《犯罪嫌疑人的确认》,《法学研究》,2003年第2期。
[2]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
[3]Jerold H.Israel,Wayne R.Lafave:Criminal Procedure-Constitutional Limitations,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91.
[4][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D915.12
A
1002-2007(2011)04-0062-05
2011-01-26
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批准号:07SFB2025。
尹茂国,男,延边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延吉133002)
[责任编辑 全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