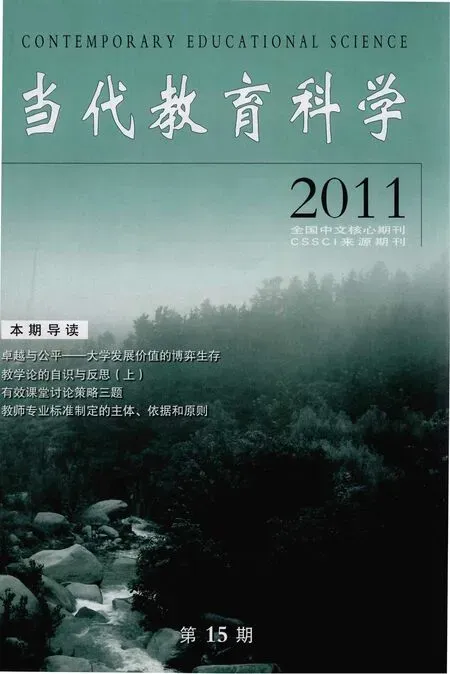课程公共性的价值诉求与理想境域
● 赵丽丽 周 博
课程公共性的价值诉求与理想境域
● 赵丽丽 周 博
课程公共性是一个我们必须严肃面对、细细揣摩并尽可能透彻阐释、挖掘其真义的研究领域。课程公共性具有公开性、实在性与共同性等特点。课程公共性并不能凭空产生,而是需要“课程公众”的积极参与与建设。公众需借助于对课程的理性的讨论,扩展课程的“公共空间”;基于课程实践的反思向度,重审课程的“公共交往”;呼吁政府公共角色归位,强化教育部门的“公共责任”;超越课程公共论述本身,培育兼济天下的教育“公共情怀”,才能实现课程公共性的价值诉求,进而达至课程公共性的理想境域。
课程公共性;公共空间;公共交往;公共责任;公共情怀
对公共性的追寻和公共知识与智慧的渐次生长,成了我们时代的一种突出的文化(精神)现象,集中地表明了我们这个时代人文学术思想的显著而深刻的特征。[1]在我们这个时代,公共性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不必深思、不需熟虑,就能随时遭遇生活中的各种公共性问题,教育领域当然也不例外。课程作为教育的下属概念,理应具有公共性的属性,但这一点却经常被忽略,因为太关注于教育的公共性,而忽略了它的子系统的公共性研究。作为教育公共性的延伸概念,课程公共性一方面表达了课程作为公共领域事物的事实存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课程公共性已成为教育公共性的下位概念,它既是对公共性在教育领域的具体说明和应用,也是教育在特定领域对公共性的反映。
一、课程公共性的基本特征
“公共”一词一般来说有两种渊源:一是起源于古希腊词汇“pubes or maturity”,强调个人能够超出自身的利益去理解并考虑他人的利益,同时意味着具备公共精神和意识是一个人成熟并可以参加公共事务的标志;二是起源于古希腊词汇“koinon”,英语词汇“common”就起源于这个词,意为人与人之间在工作交往中相互照顾和关心的一种状态。[2]汉娜·阿伦特在对上述古希腊人的公共生活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对公共性概念做了较为深刻而又全面的阐释。她认为,“公共性”一词是一个复数概念,它应当包含公开性、实在性与共同性等三个特征,而这三个方面也就成为我们剖析课程公共性的基本价值维度。
(一)公开性
公开性,它首先意味着“在公共领域中展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为人所见、所闻,具有可能最广泛的公共性”[3]。课程的公开性表现在课程的方方面面,例如课程目标的确立依据、课程内容的选择、课程实施的具体步骤以及课程评价的制定过程等,都以一种公开的姿态呈现在公众面前,接受公众对课程的批评、建议或者意见。特别是课程政策的制定,更应当将课程信息公布于众,唯有公开课程信息,才能满足公众对课程的了解,才能实现课程政策的有效运行。其实,从课程制定者本身利益来说,其并不愿意公开课程相关具体内容,保密能够为其提供更多自由裁量的便利。但是,随着公开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以及公众意识的增强,课程已开始由封闭走向公开,这为公众评价政府行为提供了基本的信息支持,人们可以自由发表言论,提出自己对课程的认识与理解,并由此而形成公众舆论来影响政府决策;同时也保障了个人权利,通过公众舆论而形成的课程形态更符合大众的利益,更能反应多数人的课程意愿。
(二)实在性
公共性还意味着“实在性”。阿伦特认为:公共世界是一个所有人共同的聚会场所,每个出场的人在里面有不同的位置,每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和听,这就是公共生活的意义。私人生活则与之不同,它只提供固定的位置和视角。她认为,过一种完全私人的生活,首先意味着被剥夺了对一种真正的人的生活来说本质重要的东西,也即被剥夺了从被他人看到和听到中产生的 “实在性”。私生活的贫乏在于他人的缺席;就此而言,私人无法显现,如同他不存在一样,他做任何事情都不对别人产生影响。[4]而公共生活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确保人的“实在性”,人们在公共场域中能够获得对“自我”在场的现实体验。这种实在性表现在课程上,则是人们在以课程为议题而形成的公共空间中,就课程问题而表达自己的想法、思想,由此来体现自我的一种“实在性”或者彰显自我的存在价值。课程公开仅仅是一种状态,如果仅为公开,而被置之不理的话,这与课程将自己密封于自我禁锢的格子里,过着一种无人问津的“私生活”无异。公众对课程的所听、所闻、所言、所问汇聚成课程的公共领域,以至呈现出课程的公共性。
(三)共同性
公共性的最后一层含义是“共同性”。诚如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霍尔所言:“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可能真是用一种独有的和个人的方法理解和解释世界。但是,我们能够交往是因为我们共享很大程度上相同的概念图并因此用差不多相像的方法理解和解释世界……由于我们以大致相似的方法解释世界,我们能够建立一种可分享的诸意义的文化,并因而构造一个我们共同居住其中的社会世界。”[5]这种共同性反映到课程上,则是指课程应寻求公众的参与。课程不是公众机械、被动接受的以定论方式而出现的知识,而是众多主体对其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等诸多问题进行讨论而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唯有当课程成为公众“共同”的追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主体才能以更加合理和开放的心态与观念展开对话协商,充分表达自己的理想、价值和态度,倾听他者的表达与叙述,从而实现有效的改造课程。
二、课程公共性的消解
公共性是课程的应然属性,然而现实的课程公共性建设却受到教育系统内外因素的影响,课程公共属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具体表现如下:
(一)课程开发过程的相对封闭性
我国的课程形态呈现在公众面前的一般是成文的、系统的课程体系。学校只是负责课程授受的任务,至于课程目标是怎样确定的,课程内容为什么要如此选择,课程实施的具体方案为什么这样制定,课程评价采用了什么样理论基础,对于一线的教师而言都是“一问三不知”的,更不用说家长、学生了。课程开发的主导权在国家、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课程专家提供课程意见,课程开发呈现封闭式模式。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课程开发模式,虽然在课程设计的规范、课程开发技术、课程先进教育理念的应用等方面体现出较高的课程设计水准,但学术理性的课程设计取向并不利于教师的课程实施。虽然政府主导的课程开发也是从“公共的善”出发,但其封闭性的开发模式却抹杀了课程的公共性,课程开发丧失了其应有的协商、对话等特征,进而,其行为也就失去了公共性特征。
(二)课程私人领域发育的不成熟
私人领域的充分发育和成熟是公共领域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是说,只有在私人的权益、立场、声音得到充分保护、尊重、弘扬的基础上,公共领域才可能真正形成,公共性才得以真正实现。[6]在我国,课程公共性的实现要经历一个漫长的积累阶段,因为我国的课程私人领域的发育极为不成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我国自成立以来一直实行的是大一统的课程设计模式,而三级课程管理方式的出现也只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事情,课程的“国家专属”使得公众失去了对其了解、认识的机会,因为不了解、不熟悉,所以公众对其也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也就无法形成公共舆论,也就无法影响课程政策。人们只关注于实践状态的课程实施是否实现,是否落实到位,而对于课程的上位认识却少之又少。
(三)市场经济因素对课程的渗透作用
市场经济倡导效率优先、功能至上、完全竞争等理念,这些因素也在源源不断的渗透到课程领域中来。精英教育的课程设计、应试教育的课程实施都体现了市场因素对课程的影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考定乾坤等思想的出现就是这种市场因素向课程渗透的最好例证。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课程的教学不再是着眼于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不再是关照学生的学习兴趣,而是功利取向、效率取向,它破坏了人们对于教育“教书育人”的期望,造成了教师厌教、学生厌学的局面,家长对教育的不满由此加重。课程所追求的“公共的善”的根本旨趣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拷问。
三、课程公共性的价值诉求与理想境域
课程公共性并不能凭空产生,而是需要“课程公众”的积极参与与建设。
(一)借助于对课程问题的理性讨论,扩展课程的“公共空间”
课程公共性的发展是基于一定空间的,我们将这个空间称之为课程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是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批判空间。[7]当然,它不仅仅以批判与开放为特征,更重要的是它在理性讨论的框架内实现自由、民主、正义的精神。当课程人对同一课程事件开始发言讨论或是关心同一个课程现象的发展时,就创造了一个公共空间,这个空间基本上是无形的,但是它却是使你我他产生关联的媒介。我们关心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世界”,虽然这并不代表我们对这件事或这个世界要有相同的判断。而如果“课程人”之间不屑与相反意见者进行沟通,采取极不宽容、极不友善的态度,这会使理性讨论的空间压缩殆尽,公共空间也就无从谈起,进而,课程也就封锁于每个人的意识之中,也就形成不了成熟自洽的课程公共性。
(二)基于实践的反思向度,重审课程的“公共交往”
以往的公共性主要集中在公共舆论及讨论等话语层面,而实践层面的公共性则容易被人忽视。不可否认的是,公众舆论与讨论等话语层面的公共空间十分重要,但它们却无法承担起全部的公共性责任。因此,我们必须同时注重实践与理论两个不同层面的公共性。[8]同理,课程要建立本领域的公共性特征,也应当在注重理论思维方式的同时,更应该回归到实践认识论的方向上来。因为所有的课程问题都产生于实践,所有的课程决策、课程理论、课程实施最终都要在实践中获得检验,无论是课程行政人员的课程政策、课程工作者的课程理论,还是教师的课程实施,最终的集结点都是实践。课程公共性是追求“公共的善”的目标,因此,它应以解决课程实践中的诸多课程问题为目标,只有这样,它才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这就要求课程行政人员、课程专家、课程实施者应当基于实践的反思向度,将政治生活中的民主理念与制度引入到课程实践中来,不屈从于外界市场、制度、权力法则或非知识因素的控制,以独立的姿态参与平等的对话,每个人有兴趣去了解别人的意图、想法或主张,每一个参与者都能以秉承善意或想要帮助对方完成论辩为基本目的,反对形形色色的学术霸权、学术专政,在不同理论交锋中追求课程的公共性,追求课程的真。
(三)呼吁政府公共角色归位,强化教育部门的“公共责任”
我国对公共性的认识处于褊狭的公私二元对立之中,注重形式上的公(公有、国办、共管等),却忽视了实质意义上的公(公平、多元、共享)![9]这也就为市场因素的入侵提供了可趁之机,导致了课程非公共化的离心力量的加剧。课程公共性的建设就是要呼吁政府的公共角色的归位,强调政府对课程建设的适度干预,这种干预不是掌控,而是在课程与公共性之间铺设一排排石子,让人们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强求在鸿沟的两岸跳来跳去。具体而言,就是要以公共服务为理念,使课程政策的决策与执行、课程权利的配置与监督、课程资源的分配与运用体现出公平和公益的原则,以实现每一位学生全面、自由、自在的发展。
(四)超越课程公共论述本身,培育兼济天下的教育“公共情怀”
作为课程人,我们不能仅仅囿于课程领域的理论研究、课程实践活动,不仅应有为求知而求知的理性探索精神,不只是立足于课程的立场来研究教育,我们还应关乎于专业工作之外,还必须深切地关怀教育的现实,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应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志向。唯有如此博大的胸怀与孜孜不倦的教育情怀,才能使我们超越个人的私利之上而共谋公共利益,培育一种兼济天下的“公共情怀”,当其延伸至教育领域之中时,我们对公共性的理解与认识不仅获得了更广阔、更深刻的涵义,更能够在对教育的追求中敞开自我,不断地质疑、追问,再质疑,再追问。时刻把心灵的触角伸向人间社会的冷暖,不忘记自己作为普通个体的良知与社会一员的责任。 ”[10]
[1][7]袁祖社.“公共性”的价值信念及其文化理想[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01).
[2]郭湛等.哲学视域中的公共性及其当代诠释[J].齐鲁学刊,2005,(01).
[3][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M].竺乾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0.
[4]Hypatia.公与私(评论《人的境况》)[EB/OL].http://book.douban.com/review/4834437/,2011-03-14.
[5][英]斯图亚特·霍尔.表征[M].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8.
[6][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252.
[8][日]今田高俊.拓展新的公共性空间[J].朱伟钰,译.社会科学,2007,(12).
[9]康永久.公立学校的公共性问题[J].学术研究,2005,(09).
[10]刘铁芳.守望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35.
赵丽丽/河北经贸大学信息技术学院,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理论 周 博/河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
(责任编辑:孙宽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