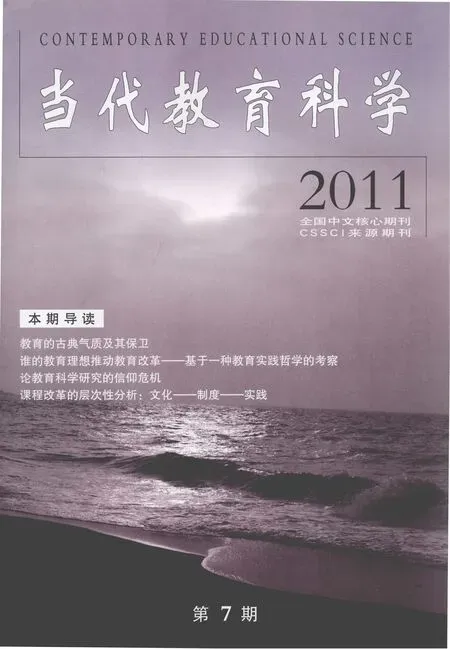课程改革的层次性分析:文化—制度—实践*
● 黄东民 王 静 赵继忠
课程改革的层次性分析:文化—制度—实践*
● 黄东民 王 静 赵继忠
课程改革具有层次性,每个层次分属到不同的权重。其中,文化改革是核心,制度改革是保障,实践改革是关键。要实现课程改革的预期效果,应秉持对传统文化“守成”与“创新”和对多元文化“兼容”与“发展”的文化观,提倡从协商取向的权力关系中衍生而来的扁平式管理方式,尊崇实践主体的意愿从而实现改革的超越性变异。
课程改革;课程文化;课程制度;课程实践
在“改革”浪潮的推动下,我国课程改革已经走过了九年的历程,回首改革之路,虽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但结果却也并不如人意:课程改革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应为”而却又“难为”或“不为”的尴尬境地。反复追溯实践到理论、理论到实践的反思路径并不能给我们提供新的改革思路。课程应从长计议,反躬自省,从改革本身寻求出路。课程改革要实现预期目标,既不能奉行合而不分的混沌式改革方式,也不能容忍分而不合的断裂式改革格局,而是要将课程改革视为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坚持其整体性,又要对其进行层次性分析,只有认清层次之轻重,识别层次之缓急,才能真正走出课程改革的困窘之地。
一、课程改革的层次性分析框架
梁启超在反思中国近代社会改革历程时,曾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把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分为器技——制度——文化三个递进式演变的阶段[1],并认为最重要的阶段是最内层的文化觉悟。借鉴梁公的社会改革历程的划分,将宏观领域中的社会改革缩影至微观领域中的课程改革,我们不难发现,其实,课程改革也必然包括三个阶段,它们分别是课程实践——课程制度——课程文化。其中,课程文化是课程改革最内核的因素,课程制度是课程文化有序传承与理性选择的结果;而课程实践则是课程文化与课程制度的具体执行环节。因此,课程改革应遵循课程文化——课程制度——课程实践的改革路径,而不是相反的改革思路。
(一)课程文化
文化之于课程,就是课程的根,变枝叶而不变根本,到最后终究是徒劳。美国著名人类文化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文化模式》中认为,人之本性,是由文化,即习俗塑造的,而不是生物学遗传的天性。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使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2]。课程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它起源于文化传承的需要,而后与文化联姻,形成了不同于社会系统内其他文化类型(例如政治文化、宗教文化、家族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的文化——课程文化,它体现了课程的社会性与守成性。课程的社会性即是指课程改革是个社会问题而非技术问题那么简单,课程并不仅仅是教育“份内”的事情,它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公共话题;课程的守成性则是强调了文化对课程根深蒂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课程价值取向的坚守: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柱是儒家学说,因而对课程文化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课程目标上,注重“贤人”、“君子”的培养,道德教育居首;在课程内容上,偏重人伦与社交而忽视科学;在课程实施上,注重内省而忽视外求等。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形成的课程文化既有特殊性也有同质性,既有先进性也有保守性,深刻影响着课程改革的思维与方向。
(二)课程制度
课程制度在课程发展中起着衔接的作用,当然,这种衔接并不是被动衔接,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它不仅承袭文化,指导实践,最重要的是,它还会根据当今社会的发展实际作出相应关照。在课程制度的制定、实施过程中,文化作为一种影响因素被隐蔽起来,或者有时候我们会找寻不到文化的影子,但制度对实践却有着统领的作用,指导、规定实践。课程制度是指课程领域中课程政策、课程管理体制等共同构建的制度体系,是国家根据课程发展的需要,对课程领域中关键问题的执行提供办事规程与行为准则的体系。课程制度在课程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曾如课程专家阿普尔所强调的:“当我们阅读可称为这个国家的话语(课程)时,我们应该强调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史蒂芬·博尔和理查德·鲍所强调的政策文本和政策语境。”[3]。理解了一个国家的课程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就能够理清这个国家课程发展的走向或者改革的方向。
(三)课程实践
课程实践,不难理解,主要是指课程在实践领域中的发展形态。当课程付诸于实践时,它也就具备了实践的形态。以实践的方式体现课程文化,以实践的方法贯彻课程制度,课程实践是文化与理念的物化阶段,也是课程发展的最终端。实践是课程文化、课程制度得以体现与实现的最关键环节。我们课程改革多年来反复追溯理论到实践,实践到理论的哲学命题,从实践中寻找改革的出路,从实践中获得理论的提升,从实践中追寻制度的合理性,这些都充分的证明了实践在整个课程改革中的重要性。
二、课程层次性改革的阻力因素分析
理清课程改革的层次有利于寻找系统的结症。每一个层次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存在,也就造成了多个层次所构成的系统的问题。只有对各个层次中的阻力因素进行分析,才能为问题解决奠定基础。
(一)课程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置若罔闻”与对舶来文化的“浅尝辄止”
在课程改革过程中,我们遭遇到两种文化观的对峙与撞击,一是传统文化,一是舶来文化,两种文化较量的结果是舶来文化占据了上风,而传统文化被弃之一隅。对传统文化的“置若罔闻”是基于这样的逻辑:传统文化模式以政教合一的政治核心论为基点,以学而优则仕的教育功能论为途径,以人上人的人才价值观为指导,集专制主义、等级观念、大一统思想、官本位思想于一体的文化体系之于现代中国,阻力大于动力,糟粕多于精华,因此,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的态度应是“放弃”。放弃的同时要有新的文化来滋养,因此舶来文化成为课程改革的“香饽饽”。课程改革也就进入了“转换”与“重建”的热潮,受到诸如建构主义、多元智能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化思想的冲击。传统文化在与多元文化的交流、交锋中失去了定力与责任,而多元文化在与传统文化的交融、交往中失去了原色与内涵,结果就造成了课程改革中文化取向的缺失与混乱,使得我国课程改革失去了根基。
(二)课程制度:垂直权力关系衍生而出的线性执行方式依旧循规而行
我国的课程制度在新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受制于文化因素的影响,大一统、官本位的思想在课程制度的建设过程中仍然保留着强劲的势头。虽然我国课程政策较之以往更加宽松,课程管理也开始实施三级课程开发制度,但是,不同层面的“课程人”之间还是一种垂直的、管理取向的权力关系。在这种权力关系下,课程行政领导和专家学者被认为拥有较高专业资质和广阔视野,适合担任改革规划者;而学校与老师则缺乏相应专业资质,视野有限,只能充当改革执行者。双方各负其责:行政领导提供课程改革的通知和行动计划,学者专家负责提供课程材料与解读,学校和老师遵循决策指示和专业指导进行改革[4]。虽然学校有开发校本课程、进行校本教研的权力赋予,但是这种权力的有限性、有效性却值得商榷。不同层面的课程人在课程改革中并没有达到一种扁平的、协商取向的权力关系,独特的执政文化与身份赋予使课程专家及课程行政领导具有了专业权威,而这种专业权威的外挂性而非内生性导致了教师话语权的失落,从而影响了课程实践的实效性。
(三)课程实践:改革中的虚假认同导致了改革的衰退性变异
课程改革固然离不开设计良好的课程,但更重要在于课程实施者基于自身所处独特情境对课程的理解及课程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效改革之过程绝非可以预设的,而是在预设中孕育着生成。由于课程制定者本身没有很好的做好“文化研修”,对课程实施的大环境缺乏一定的了解,虽对课程实施具有高瞻远瞩的前瞻性,但是却无法控制实施者本身所具有的思维惯性,结果造成了改革的衰退性变异。只以课程规划者和设计者的价值、信念为圭臬,而不承认课程实施者之文化价值、信念的存在及其合法性,只是一味的要求其放弃所持有的根深蒂固的深层社会文化价值和教育信念,其结果只能是课程领导者的一厢情愿。
三、课程改革的应然路径
课程改革有效性的实现是基于文化、制度、实践三者之间的平衡,只触动其中一方是无法实现课程改革的预期效果的,理想的状态应是采取整体推进,系统把握的原则,将课程层次中的问题各个击破,才能实现课程改革的跨越式发展。
(一)课程文化:秉持对传统文化“守成”与“创新”和对多元文化“兼容”与“发展”的课程文化观
一个文化复古主义者,不仅会强烈要求“原汁原味”地传承本族文化,还会疾呼“尊孔读经”、“设立国教”;一位全盘西化论者,则也绝不至于拒斥传承这么简单,还会高喊“打倒孔家店”、“不读中国书”;[5]而一个负责的课程改革家绝不会采取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也不会将自己的文化根基扎根于他者的文化土壤中,而是在守成本土文化、兼容国际视野中实现文化创新,为课程改革提供正确的文化价值取向。
文化传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语境”,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社会遗传基因的复制和再生。在人类四大文明古国之中,只有中华民族的文明没有间断,因而其文化也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的教育文化更是渊源悠长,形成了独特而稳定的特征并影响深远。“人为地毁坏某种文化并不能消灭它而只会造成混乱和衰退,人为强行某种文化并不能弘扬它,而往往造成反抗和动乱,个人改宗可以在一生的成长过程中完成,民族的改宗只能在民族的历史演化中发生,越是已经成熟或古老的民族,改宗的可能性越小,因此,我们对待文化的明智态度应该是文化守成。”[6]文化守成并不排斥多元文化,传统文化与多元文化不是对立,而是相得益彰。传统文化在守成的同时应以包容、开放的心态迎接外来文化的到来。课程改革更是如此,我们应排斥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即不能盲目排斥西方文化,更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夜郎自大,而是应在对传统文化精神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借助他者文化以完成我国课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自我完善。
(二)课程制度:提倡从协商取向的权力关系中衍生而来的扁平式管理方式
课程文化在课程改革中属于上位概念,而课程实施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则属于下位概念,如何将文化与实施有效的结合并将改革顺利贯穿于课程发展的始终则是由课程制度来决定与规范的,课程制度在课程改革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注意,在这里,课程制度是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既不是上传下达,也不是横空出世,而是有所继承、有所发展、有所启迪。课程制度来源于课程文化(当然并不仅仅来源于此),却又会根据实施状况而构建着现实文化。课程制度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课程人发挥着自己的特长与专业智能:课程专家在课程制度制定与实施中引领文化方向,课程行政领导把握课程制度的制定与实行,学校与教师将课程实践中的情境性、实践性、实效性的知识融入到课程制度的制定与修订中来。课程制度制定与实施的过程既传承、发展了文化,又关注、亲历了实践,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向交流通道,不同层面的课程人在协商、合作的过程中建立起了扁平式的权力关系,有效地保证了课程制度的合理性与正确性。
(三)课程实践:尊崇实践主体的意愿从而实现课程改革的超越性变异
课程的实践命运掌握在教师与学生的手中,尽管有课程专家、课程管理者对课程实施的具体问题、具体事项的指导,但是作为法定知识的课程内容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进入课堂教学的实际并被学生内化为其文化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关键还是在于教师与学生。因此,对这些个人意义的分析理解是实施计划的前提条件,要做到课程实施的超越性变异,必须充分考虑“文化—个人”的视角。教师与学生等个人因素是实施课程改革的重要变量,在课程实施环节中处于改革的核心位置。因此,作为课程改革者而言,课程改革理论只有在深切关怀师生自身的课程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得到他们真正的认同;同时要营造一种改革性的文化环境,使其愿意去改革、享受改革所带来的确定性与喜悦性,从而消除师生的虚假认同,实现课程实践的超越性变异。
[1]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A].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C].长沙:岳麓书社,1985.7.
[2]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王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1.
[3]Apple, Michael W.texts and contexts:The state and gender in educational policy[J].Curriculum inquiry,1994,24.
[4][7]刘宇.从内容到过程——“后实施时代”课程变革及其研究的走向[J].教育发展研究,2009,(18).
[5]容中逵.论当前我国教育传统文化传承践行之文化观基础[J].当代教育科学,2008,(1).
[6]唐逸.文化守成与制度更新[J].哲学研究;2005,(2).
本文系河北省科技厅“河北省高职院校女大学生人力资源开发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4572218D。
黄东民/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 王 静 赵继忠/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管理
(责任编辑:孙宽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