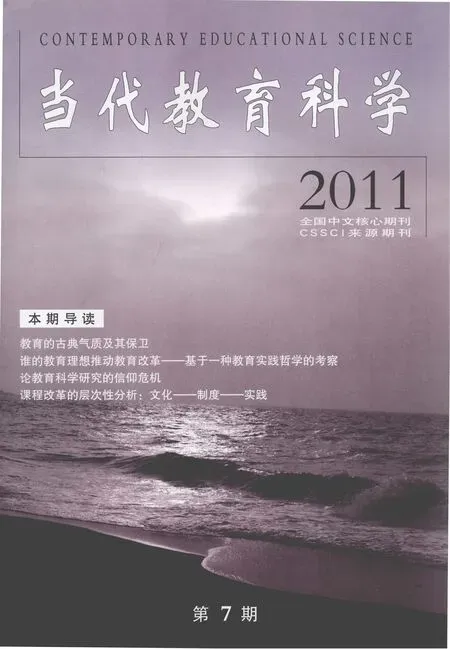谁的教育理想推动教育改革*
——基于一种教育实践哲学的考察
●王 东
谁的教育理想推动教育改革*
——基于一种教育实践哲学的考察
●王 东
教育理想的主体是多元的,教育理想实践主体的多元性使教育理想具有内容、边界和层次的差别与多样性。教育理想只有走向公共教育哲学,通过公共性反思形成重叠共识才能影响教育政策,并推动教育政策机制的完善,从而最终成为教育实践的真正推动力。
教育理想;主体;教育实践;公共教育哲学
教育理想是教育实践的思想来源之一,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动力。如果说教育理想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它一定基于一种教育实践哲学——来源于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将影响和干预教育实践。因此,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具有实践和历史价值的教育理想是谁的教育理想?换言之,谁的教育理想更有可能转化为实践哲学下的行动指南,推动教育的变革?只有理清了教育理想的主体及其性质,教育理想的历史价值和实践价值才能得以澄清,教育理想才可能成为教育发展的真实动力,而不仅仅是一种理念的虚妄。
一
所谓教育理想,指的是人们所期望的教育发展的理想状态或境界。教育理想既可以理解为对教育诸要素的一种要求和设计,也可以理解为教育作为公共事业整体被期望具备的价值、功能和特点。教育理想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是对教育现实反思的结果。教育理想是社会主体给予教育现实的理性的实质性批判,是其对教育现实诸多问题的反思性生成。人们对教育理想内涵的理解并不具有一致性,差异源于教育理想主体的多元化和权威教育理想主体的虚拟化。
教育理想指向于教育发展的未来预期,但基于现实反思的教育理想并不停留于教育形态的整体型构,个体的人才是教育理想关涉的中心。在论及什么是教育时,雅斯贝尔斯强调:“教育正是借助于个人的存在将个体带入全体之中。”[1]因而,教育理想不可避免地要表达对个人的关注,也就是对人之处境的期望,从而通过个人价值的实现来实现教育的社会价值。这种教育对个人的关注是由教育与人的关系这一基本特质决定的。从教育理想的表述中可以折射出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普遍个人处境的现状与主张。个人与社会的两极总是教育期望的基本支点,而在深层次上,对个人价值的态度与取向决定了教育理想主张与表达的主要特征。在可预期的社会生活中,作为一种思想动力,教育理想引领着教育实践,为教育实践赋予了理想主义的光芒。但诚如有学者所言,教育理想可能是人道主义的,也可能是功利主义的。[2]教育理想的价值取向和形成动机在社会发生学意义上具有天然的多样性,因而教育理想相应地具有内容、边界和层次的差别与多样性。教育理想不像教育目的那样是一个确定的、普遍使用的规范概念,因此,对教育理想这一语词的使用更多是思想意味的以及实践性的,而非纯粹学术意义上的。
教育理想的价值在于从观念上建立了关于“什么是好的教育”的认识。尽管教育理想的最终落脚点是教育实践,但教育理想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教育实践,却是一个复杂而又不确定的问题。教育理想是作为文化信念被广泛传播,还是在不断的主张、呼吁和争执之中走向教育政策,干预教育实践,既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也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教育实践的历史告诉我们,教育理想的基本意义还是在于“清思”,即解决对“好教育”的认识问题。但这个似乎由教育思想家们承担的工作事实上并不简单如此,社会性教育理想的形成以及对教育实践的引领其实是一个社会融合和社会选择的过程。教育理想通常难以成为教育实践的直接推动力。
二
教育理想之所以不能成为教育实践的直接推动力,原因在于教育理想内在矛盾的存在为我们带来了认识与实践的双重困境。教育理想的内在矛盾即因教育理想主体的多元化而产生的内容与性质的矛盾。教育理想是一种模糊的表述,因为其主体被隐匿了。教育理想主体的宏大视角来自于国家和主流社会,微观视角则来自于特定社会阶层以及个人和个人背后的群体。教育史所留下的关于教育理想的陈述主要来自于人类的文化精英即教育思想家们,他们的言论可能反映了特定时代对教育最富远见和洞察力的看法,并具有更为久远的历史价值。而在现实生活中,则由公众人物和学术精英通过公共媒介反复表达。这里体现的是基于社会实践史的话语权以及话语的力量。问题是,他们的代表性够吗?他们代表谁?如果仅仅是代表自己,以及一种思想的内部传递,其教育理想的实践价值何在?
就教育史的考察而言,国家意愿、文化精英、市民社会是教育理想主体的主要来源。国家意愿亦即国家意志,是国家权力的主观表达。国家意愿对教育理想的主张一定要从满足国家的需要开始,所以是高度政治化的。国家意愿下的教育理想关注的不是教育本身,不是受教育的人,而是教育作为工具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国家利益的需要。国家权力既是非人格化的,又在具体的政治生活中通过活生生的人,表现出强烈的人格特点,从而反映特定阶层的利益与意愿,乃至于政治人物的个人情怀。就公共教育的本质而言,教育理想的演进无法摆脱国家意愿的桎梏。尤其在教育理想作用于教育实践这一环节,国家意愿因为掌握着教育权力具有无可比拟的先天优势。
文化精英是人类文化的探索者和记录者,是可陈述的教育史的话语人。教育思想家们留下大量的关于理想教育的陈述,这些陈述不仅影响着当代也影响着未来。文化精英对教育理想的主张依托的是文化的张力和人类文明的力量,因而是超越现实的政治经济需求的,以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最高目标。文化精英更深地立足于人性和人的价值,因而其教育理想具有更广泛的普适性和文化性。同时,文化精英的权威地位极大的保证了其观点与思想的广泛传播与社会认同,以文化再植的方式实现对教育实践的普遍影响,这种影响既是广泛的、深刻的,又是间接的、缓慢的。但文化精英的言论非常容易泡沫化,必须经历学术的磨砺与洗礼,经历实践和历史的检验,才可能转化为实践性知识而流传,进而成为教育实践的推动力。
市民社会是一个大致的表述方式,适合当代,不适合历史,在此以市民社会作为普通社会成员总体的指称。市民社会的教育理想来自于家庭对下一代的成长期望,他们寄托于教育,渴望改变或维持自身代际相传的命运。在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中避免不利处境是市民社会教育理想的基本动力。因此,获得良好的公共教育,寻求优质的教育资源与公平的教育机会,才会成为现代社会的热点议题。市民社会的教育理想具有最普遍的广泛性和现实性。既可以鲜活地呈现于一个家庭,又可展示出社会的整体风貌,并进而影响公共教育政策;某种意义上,也可能成为文化和专业精英的思想来源。
在现当代,教师群体作为专业教育群体尤为引人关注。教师的教育理想作为教师内在素养的核心内容,对教育实践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教师的教育理想既蕴含着其基于职业需要而产生的对教育发展的应然期望,也背负着他们职业生活所积累的感慨、困惑与渴求,甚至也夹杂着行业利益的考量。教师群体的教育理想有着复杂的成分,主要指向所处的工作环境、工作角色以及工作任务本身,而较少涉及教育事业的整体。
作为教育核心要素的受教育者,是教育理想所关涉的当事人和教育活动的中心。他们是否是教育理想的拥有者?在教育发展进程中,尊重儿童青少年的权利与地位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教育伦理,那么,他们的感受、需要和主张是不是理应得到国家、社会与学校的极大尊重,而具有可以合法表达的教育理想?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复杂的原因来源于受教育者的身份。作为未成年人,尽管他们拥有表达教育理想的天然合法性,但他们的主张能力是有局限的。他们的教育理想往往通过表达赋权的方式由家长、社会和学术界代为表达,从而在公共意义上成为间接的教育理想主体。
教育理想主体的多元性使得关于理想教育和教育期望的陈述变得不确定起来。我们谈论教育理想,一定指向于立足于教育现实的教育实践的努力,进而展露的是关于教育发展与变革的期望与主张。显然,这里包容了多样性的声音。当然,多样性的声音并不意味着没有一致的“重叠的共识”,但身份和立场的不同必将导致教育理想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如何通过公共教育的选择机制化解,并形成积极的教育改革的推动力?这就形成了本文所说的教育理想的困境。教育理想的困境实质是教育实践的困境,是选择的困境和权力的困境,而不仅仅是认知的困境。教育理想主体的多元化使得一个看似完美的陈述与主张,由于缺乏与之对应的实践主体和实践空间,而不具备实践中的生机与活力。这是教育理论研究者乃至于所谓的教育思想家通常所面对的尴尬。而问题是,无论是政府、市民社会,还是教师群体,其对教育理想的展望都和对利益的谋求相连,并因此丧失了批判的能力与资质。对教育现实的批判与教育理想的主张由与利益无涉的文化精英和教育思想家表达,无论是在立场上还是在深刻程度上显然更为合适。只是思想的力量经过实践的释放到底能发生怎样的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却是非常不确定的,也是难以人为设计与控制的,何况思想本身也常常存在问题。
三
教育理想的困境提示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教育理想如何可能?这不是一个理论生成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这里,“可能”有两层含义:其一,教育理想如何达至“重叠共识”,形成可信的主流价值和共同知识;其二,教育理想如何走进实践,成为真实的教育改革的推动力。
对教育理想的最终价值而言,如果不能建立实践的道路,那么关于教育理想的讨论就是苍白的。这就要求教育理想实现基于教育实践哲学的转换,最终走向公共教育政策,目标是公共教育的改善。在这一过程或机制中,国家的声音、政府的声音、公众的声音、专家的声音、教师的声音、学生的声音以及独具魅力的个人的声音,一定会汇集而形成教育理想的 “和声”。但在最终的教育决策和教育实践中,到底是谁的教育理想发挥了作用则很难辨析。多重的试误机制、博弈机制和传播机制,会使教育理想的形成、传播与认同,在经过反复的磨砺之后既可能形成 “重叠共识”,也可能保持在多维的冲突与分裂状态。这意味着教育理想的最终道路必然通向公共教育哲学。亦即通过论题的公共化完成关于教育理想的讨论、传播和共识的达成。所谓公共教育哲学,原指一种不同于个人教育哲学、专业教育哲学的教育哲学研究形态,是一种对“大众教育意识、教育生活和教育政策进行的批判性分析”,[3]具有平等、开放和对话的特征。我们这里将其引申为对教育生活的公共性反思、对话和辩驳,而不仅仅是专业人员的研究范式和话语风格。公共教育哲学是实践意义上的关于教育的公共论坛,其话语主体的多元性和论题的开放性为教育理想的充分表达提供了可能。教育理想走向公共教育哲学的意义在于通过广泛讨论与意见表达,形成有价值的、可行的、并被普遍接受的“重叠共识”。至此,教育理想才会走出文本和学者的书斋,而可能成为真正的教育实践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但就教育的实践史而言,由教育理想到教育实践并不是简单直接的生成过程。教育理想往往是文化的产物,要传递的主要是关于教育价值的判断。它是实践的,但不是操作的,很难作为客观要素直接进入公共政策和教育改革的视域。对教育理想的陈述通常不是公共行政语言,它是非常个人化的、对教育期望的表达。任何对教育美好前景的描述,在公共政策的话语里都并不非常可靠。教育理想更多的还是存在于个人的思想活动中,或寄居于民间意见之内,从而间接地作用于教育实践。从教育理想到教育实践,需要一个操作性的制度化生成,才可能解决教育理想如何可能的终极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改善公共政策的决策机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而这有赖于广泛的民主和成熟的民主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使教育理想的重叠共识成为可能,而当重叠共识在公共教育哲学意义上已然建立,教育理想对教育实践的推动作用则表现为对教育政策的影响。重叠共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教育政策?教育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尊重了重叠共识的价值与意愿?这些核心问题关涉的就是教育政策产生的方式,亦即是谁和用什么样的方式与程序制定并实施教育决策。“谁的教育理想”在根本上就是对教育政策内隐价值的追问和质疑,以及对教育政策模式与程序的更广泛的期待。
鉴于此,我们倡导一种基于教育实践哲学的教育理想观,亦即走向公共教育哲学的教育理想观。其意义在于给个人化的教育理想提供“意见的场所”,以形成思想的交汇和可能的教育实践的推动力。在现代社会,“意见的场所”所维系的不仅仅是关于教育的主张,也维系着观点交汇的方式和效果,以及教育理想与教育实践之间互动关系的特点。开放、对话、尊重和平等,这是公共教育哲学视角下的教育理想观所倚重的言说道路,并作为言说方式界定和限定了教育理想与教育实践之间的张力。在内容上,走向公共教育哲学的教育理想观将追寻教育理想的人道主义特质和民主价值,即将人的发展、人的尊严与人的价值与社会正义作为核心,以此为前提建构优质教育的应有意蕴。人道主义的教育理想和民主社会有着内在的关联,强调公民对教育的期望和期望的表达建立在民主、自由、公平和正义的社会基础之上。公民拥有教育理想的表达权和主张权,而国家、政府及其代言人退到幕后。这是现代民主社会教育理想的应有生态。
[1][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54.
[2]薛晓阳.教育的超越本质及自由教育的理想[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96-101.
[3]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69.
*本文系辽宁省“十一五”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背景下教师资源配置机制研究”(课题编号:JG10DA009)的阶段性成果。
王 东/鞍山师范学院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责任编辑:刘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