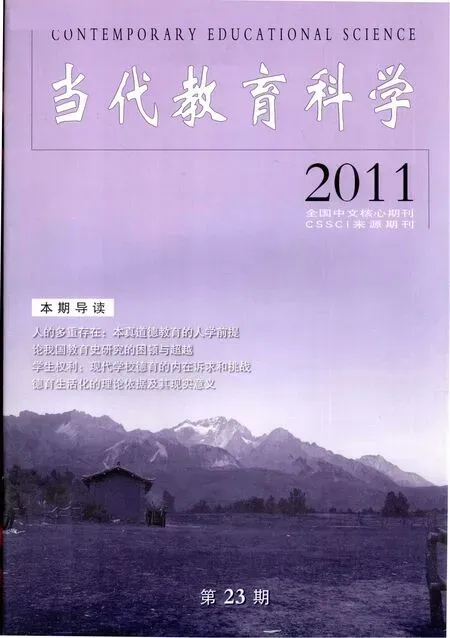论我国教育史研究的困顿与超越
●李江刘茜
论我国教育史研究的困顿与超越
●李江刘茜
中国教育史研究历经百年发展,成果丰硕。然而,回眸近代我国教育史研究,不难发现其发展是在研究意识、研究思维、研究模式以及研究价值观等方面的困顿中艰难前行的过程。这种困顿在现实教育改革的映照下,表现的尤为突出。时代要求我国教育史研究应在国际化大环境中展开针对性研究,强化问题意识、进行专题化研究,审思分期模式、创新研究思维,打破研究的“中心论”倾向从而推动我国教育史研究的多元化发展。
教育史;教育史研究;研究思维
基于西方史学理论的新史学观,引起了史学研究的革命性进步。20世纪上半叶,摆脱了中国传统教育研究模式的中国教育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它在理论基础、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尝试着创新。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学者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开始从传统的“学说型”解释视角向“学理型”的知识体系和理论阐释方向努力,并最终完成了其学科构建。也就是说,从最初的学习美日到全面移植苏联,再到今天的全球视野的艰难历程可以看出,我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之路就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渐进过程。百余年的研究成果颇丰,学科的研究价值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学科的研究对象得以明晰确认。但我们也应看到,教育史研究繁荣的背后亦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并认真面对,以利于我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的健康发展。
一、我国教育史研究的困顿
(一)“只褒不贬”的教育史研究意识
我国教育史界先后出现几种表现形式不尽相同的教育史观,如进化论教育史观、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吻合的教育史观、教育获得现代性过程的教育史观,它们本质上都是一种进步教育史观。[1]社会的车轮滚滚向前,社会的构成要素也是不断丰富的。我们不是否定发展的前进性,只是我们所有的教育史研究都是在这样一种前进型思维指导下开展,就难免不把我国的教育发展历程看作由低级向高级、由不成熟向逐步成熟发展的历史,从而忽略社会发展中都无法避免的停滞不前、甚至后退现象。例如对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完善的研究、对教育目的和教育作用的确认和改进的研究、对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的研究、对学校的发展的研究等,都倾向于“显示它们逐步递进和不断朝着科学化方向演化的过程,凸显教育制度和教育基本理论发展至今的主要轮廓。”[2]其主要目的不过是“为了论证现有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的合理性。”[3]这样的研究倾向,无疑是抹灭了一定历史时期内不同群体、不同个人对教育相关问题认识的不一致性;无疑是把本来应该是多元交叉的教育史简单化成了直线的和单一的。这本身就违背了教育史研究的真正内涵,其成果也只能是历史的一种错误解读。
再者,无论哪个时代,其教育主流背后都有复杂的教育观点共同存在。只不过是由于种种原因,其中的一种被政府和民众所接受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而已。“只褒不贬”的教育史研究意识是一种对历史充满赞扬歌颂式的乐观主义观点。在这种研究意识支配下,我国的教育好像一直都风平浪静,而取得的进步与成果似乎也都是合乎情理、水到渠成。这样一来,我们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一些“共通共用”的结果,而不是能引起争鸣的真知灼见。人们被固有的模式所限制,而少了对差异的研究或是突破现有模式束缚的努力,获得的成果当然也只能是对已有结论的重复。
(二)“多横少纵”的教育史研究思维
以时间为中心的教育史研究记录了历史发展过程中重大的教育事件和教育人物,其目的在于勾勒教育发展的整体轮廓,展现整个教育发展史。目前的多数教育通史、国别教育史等都是这样的模式。这样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我们理清教育发展的脉络,但却丧失了历史本身的生动性。也许在初期的教育史研究中,这样的思维尚能满足理论和实践的需要,那么随着今天社会发展速度的提升,这种仅限于整理历史事件的研究已经无法响应现实的纵深要求了。现实需要历史给予的帮助关键在于“如何做”,而不仅仅是“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一来,我们也许没有必要对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教育事件做全局性的整理,更多的是要求我们把研究的视角更细微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揭示教育事件发生与发展的动力。
更进一步来讲,历史发展的每个重要关头总是存在着多种发展方向,而历史呈现给我们的只能是一种。我们应该清楚“在追溯前因后果时,常得要在某些关键点上存有事情可能朝向另一不同方向演变的考虑,才能有较周全的解释”[4]。而在以时间为主线的编年体研究思维下,这样“可能”的历史却无法呈现出来。所以,与其对历史做宏观叙事式的研究,不如对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关键事件做可能性分析;与其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归纳整理,不如对历史做尝试性“导演”。
(三)“简单划分”式的教育史研究模式
从宏观层次看来,“古代——近代——现代”的教育史分期方法一直为我国的教育史研究者们所遵从。这种研究思路是移植于西方的研究模式。但是从社会发展本质上来讲,历史发展本身并没有固定的可遵循的模式,并且各国的教育背景不同,教育政策不同,教育目的也不相同,所以不能采取“千篇一律”的分期方法。具体到我国的教育史研究分期,必须改变过去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分期方式。
从微观层次看来,多数的教育史学著作都以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二元划分的方式展开。在这样的研究模式下诞生的研究成果只能是“伟大人物的教育思想史”,而忽视了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关系。我们知道,“教育的发展不等于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简单相加,两者也不是截然对立、互不交叉的领域。”[5]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交叉融合的背后既需要一系列的教育理论为基础,更离不开相关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知识支撑。
(四)“中心固定”的教育史研究价值观
审视我国现阶段的外国教育史研究,更多的是在讨论欧美国家,而缺乏对非洲教育、中东教育、印度教育以及南美教育的研究。反观国内教育史研究,大多是将汉族教育作为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中心,而较少关注各少数民族的教育传统、理念、实践等;一直都重视儒家发展历史的教育问题,而对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历史的教育问题却研究的不够;研究的重点基本局限于官办教育的历史问题,而常常忽视对民办、商办以及合办教育的研究。由此可见,未来的教育史研究应当“将研究的视线逐步向下移动和对外扩散,实现教育史研究从精英向民众、从高层向基层、从中心向边缘、从高雅向世俗的过渡”[6]。
二、我国教育史研究在路径澄明中超越自我
面对我国教育史研究存在的问题,新世纪的研究应结合当代社会发展趋势,摆脱传统的束缚,清醒地认识到学科自身存在的弊端;应当参照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教育改革,关注历史科学的发展与研究动态,构建我国教育史研究的新体系。具体来讲,教育史研究应该注重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转换。
(一)紧扣时代脉搏,在国际化背景下展开针对性研究
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事物的相互关联中蕴含着历史发展的既定规律,这些规律是我们揭示过去发展的依据,更是我们预知未来发展的依据。错综复杂的历史中,存在着多样化、个性化的发展个体。也就是说,历史是多维的,立体的。生活在其中的我们应该看到,每一事件都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与整个社会紧密相连的。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说:“我试图把人类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换言之,即从世界性的角度去看待它。”[7]对教育史研究而言,首先,应当从人类教育史发展的整体出发,打破中外对立的局面,突破国别界限,把我国教育史研究放入世界教育史的视野中综合考察;其次,在研究过程中,不能用停滞的目光看待教育事件的产生、发展与消亡,而要用动态的眼光去研究,因为任何一种教育都不会永葆青春,也没有一种教育能够永恒不变。当然,在研究展开过程中,我们还要客观对待外国教育家对我国教育史研究的成果与结论。在承认他们可以给予我们不同思维、不同视角的新成果的同时,也要看清其所处研究立场的不同等内在研究缺陷——他们只能从其自身的利益出发,选择性地对我国的教育问题进行思考、总结,并提出结论。所以,不能一味地翻译、引用这些成果,而是应该学习其研究方法、尝试其研究视角、借鉴其研究思维,认真参加教育实践,解读群众的教育呼声,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二)强化问题意识,突破惯用的编年体式教育史研究范式
上面我们已经论述,编年体教育史研究范式有助于勾勒教育发展的整体轮廓,展现整个教育发展史。但是,它在理清教育发展脉络的同时却迷失了教育史研究自身追求的客观性,常常使教育史研究变成为教育历史事件的堆砌,从而丧失了教育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年鉴学派提出的问题史研究以其独特的视角颠覆了传统叙述史的研究范式,为历史研究注入强劲的活力。问题史研究就是将现实的教育问题作为教育史研究的起点,突出其研究主题,找出矛盾冲突的根源并提出解决策略,从而为现实的教育改革提供参考性意见或建议。
美国著名的教育史学家布鲁柏克 (John S.Brubacher)在其著作《教育问题史》中拟出了与教育相关的十七个主题,并进行了系统研究。在研究中,布鲁柏克初步展现了教育问题史的特点:根据教育现状将教育体系细化为不同的研究主题,然后从主题入手,展开纵向研究,逐渐深化。这样的研究融通古今,带领读者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激发了读者对教育史研究的兴趣。同时,由于相关的研究都是基于现实实际问题展开的,有利于改变教育史研究流于形式,脱离现实的局面。
(三)改变传统研究模式,创新教育史研究思维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提倡打破“古代——中古——近代”的固定思维模式。他站在史学研究的最高端告诉我们,研究人员不能固守千年不变的教育史分期方法。千百年来,教育与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教育史研究人员在分期问题上形成了固定的模式。然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也各有特色。具体到我国的教育史研究现状,我们尚未走出原始社会教育、奴隶社会教育、封建社会教育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教育的分期传统。固化的分期思维模式牵制了我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或按教育问题分类,或按思潮流派归纳,或按朝代分期,或按经济水平展开,按这样的思路来研究我国的教育史,才有可能追溯历史真相,在真正揭示教育事件发生、发展、消亡的同时,给现代教育改革以启示。
(四)打破“中心论”,改变中心固定的教育史研究价值取向
在文化形态史观看来,不能只将一种文化作为中心,而应该打破“中心论”,倡导多元化。这也是我国教育史研究的基本发展方向和趋势。首先,开阔研究视野,增加对非洲教育、中东教育、印度以及南美教育的关注。虽然目前来说,欧美教育较为发达,但并不能代表以后会永远发达。况且研究并借鉴更多国家的教育发展经验,对于幅员辽阔的我国来讲,也会为因地制宜地开展教育改革提供理论或现实依据。其次,加大对国内各少数民族教育经验、教育传统的研究,挖掘有代表性的教育家和学校。从政策和资金给予外部保障的同时,培养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的专业人员,丰富科研队伍的结构及层次。第三,关注非主流文化的教育观以及教育实践活动,拓宽研究领域。在重视儒家教育的同时,研究道教、佛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的教育历程;在重视官办教育的同时,加大对民办教育、商办教育以及合办教育的研究;在研究现存史料的基础上,重视来自非官方记录甚至口述的教育资源。研究重心向非主流文化的转移是我国教育史研究走出当前研究领域过于狭小的基本路径之一。对于此,英国当代著名教育史专家理查德·奥尔德里奇(Richard Aldrich)这样说:“教育史是更普及的、大众教育领域的课程。”[8]他把教育史研究和教学的宗旨定位为要适合大众的需要,成为普及的内容。所以,我国教育史研究应当在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研究领域等多层面进行多元化尝试,将研究的视线更多地投向少为关注或从不曾被关注的下层民众教育中去。
[1]张斌贤.教育历史:本性迷失的过程——对教育法杖的“另类”观察[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2).
[2][3][5]梁淑红,杨汉麟.我国教育史学科研究范式的反思与转化[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1).
[4]于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169.
[6]周洪宇,申国昌.新世纪中国教育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9).
[7][英]汤因比.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0.
[8][俄]卡特林娅·萨里莫娃,[美]欧文·V.约翰宁迈耶.方晓东等译.当代教育史研究与教学的主要趋势[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121.
李 江/西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刘 茜/西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