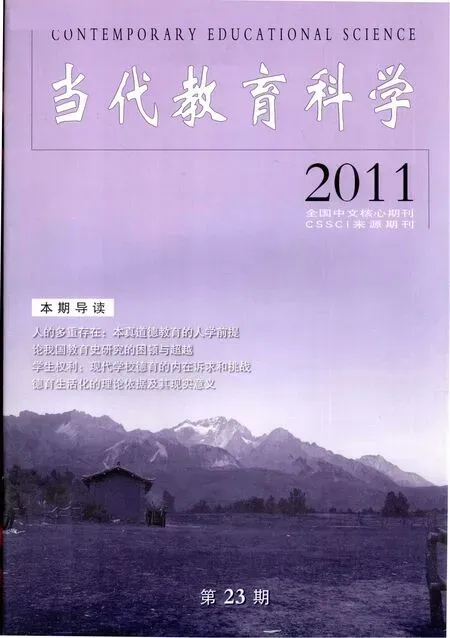人的多重存在:本真道德教育的人学前提
● 刘丙元
人的多重存在:本真道德教育的人学前提
● 刘丙元
道德教育建基于何种人学前提,不仅关系到道德教育自身存在及其运动方式能否得到合理性论证,亦关系到道德教育能否关照人的真实生活。以片面的人学理论为前提,道德教育也就不能负载道德的真实。本真的道德教育应以人的多重存在为其人学前提。只有道德教育以完全不带偏见的态度承认人的多重存在这一事实,并以其为教育逻辑展开的人学前提,其对道德的解释才会贴近真实生活。
人性;道德;道德教育
毋庸置疑,道德为人而存在,而道德教育即在于促进人性的完满,然而,现实中的道德教育能否实现其本真使命,乃在于其能否正确地理解道德,而对道德的理解又最终要回到人性的问题上。因此,道德教育建基于何种人学前提,不仅关系到道德教育自身存在及其运动方式能否得到合理性论证,对道德及其生活意义具有切实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亦关系到道德教育能否关照人的真实生活,引领人走向真正的和谐与美好。易言之,道德教育的“能够”取决于其是否具有本真的“应当”。当代道德教育因其偏颇的人学定位,以致脱离生活、功利化等诸症难消,而丧失教化的内在权威力量。
一、人性的割裂:道德教育无以自证的根源
有学者指出,“如果道德教育没有一种科学的哲学本体论的定位,道德教育就不能促进人性朝向一个理想的状态,道德范畴和道德律令也就不能从关于人性的真理命题中推演出来,或求助于人的本质性的特征而被说明为‘正当’或‘应当’。”[1]如果这一命题成立的话,那么,任何具有说服力的道德教育都须有一个科学的人学前提,由此前提出发,道德教育才能完成自我之真理性的合理性论证,从而获得真实的权威的教化力量。然而,综观现代道德教育之人学基础的理论发展历史脉向,却因对人性的割裂而使道德教育陷于无以自证的境地。
对于人性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不同的道德哲学对此有不同的诠释。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人之理性与感性存在的争论,而在中国哲学史上则有所谓的理欲之辩。对于西方伦理思想传统及其线索,人们一般认为其主要分为理性主义伦理学和感性主义伦理学两大基本路线。[2]理性主义伦理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对伦理学绝对形而上学知识基础的先验假设和对整体主义道德原则的理想追求。在理性主义看来,理性思考是形成德性的不二法门,而德性也必是摒弃一切感性、情感、经验的纯理性的。与理性主义伦理学不同,西方传统的经验主义伦理学则主张从人的感觉经验中寻找人类的道德起源、内容和标准(据此,西方一些学者又把经验主义伦理学分为快乐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等流派)。因此,经验主义伦理学传统往往坚持从个人道德经验出发,坚持以个体主义或利己主义为基本道德原则。不难看出,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这两个基本的伦理理论传统,其基本的前提是将人性割裂为理性存在和感性存在两个对立的状态而各执一端,并分别从各自的人性本体论前提出发推演出理念伦理或经验伦理。不同的人性前提导致不同的道德生活方式假定,它们所诉诸的道德动力因此也相去甚远。理性主义认为道德行为的动力来自于一般原则,来自于主体的理念世界,而与主体的所处境遇、经验无关,并且主体也必须抛开自己的境遇、经验而践履道德原则,否则其行为就没有道德价值。因此,理性主义通过人的理性认识使道德规范获得确定性和普遍适用性。经验主义则将道德行为的动力交付于个人的行为结果、情感和心理因素,而理性只是用来“功利结果计算”,即休谟强调的所谓“理性是情感的奴隶”。如此,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那里,就有了两种不同的“道德人”,一种是由道德法则统治意志、为义务而义务的道德人,一种是由自己私利出发,根据自己的情感、需要进行选择的道德人。
事实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都把人性片面化了,它们忽视了人的存在中的一般与特殊、整体与个体的辩证统一,忽视了伦理中的理念与境遇的辩证统一。理性主义把人只看成理性存在,极易导致不顾具体情景和对象的区别和差异而抽象地运用一般原则,由此承载道德价值的人格与德性只能是放弃自己个体存在的为义务而义务的人格与德性。包尔生认为德性是一种自然的素质,它包含着人的情感、冲动,甚至“冲动构成了德性的恒久的基础”,“它们不能像许多道德学家们设想的那样由理性思考来代替。”因此,“一个像斯宾诺莎所说的哲人那样的,不是由冲动而仅仅是由理性规定着一切行动的存在物是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康德的那种仅仅由道德法则统治着意志,没有冲动和倾向的尽本分的人也是不存在的。这样一个存在物不会是人,而只能是一个幽灵。”[3]与此相反,经验主义执着于人的经验性的个别存在,坚持道德的个人主义立场,则不可避免地使人们陷入各自的私利而忘却或偏离普遍的原则,或者放弃对道德规范普遍性的追求。在经验主义看来,由于道德的基础和标准在个人那里,道德的意义或价值便是相对的,不可公度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就不能对某种人格是善还是恶进行判定,而只能根据有限公度的不确定的规则进行行为的判定,善与恶必须也只能根据外在的规则来判定,由此规则在个人主义道德中获得了中心地位,而德性则被否定或边缘化了。因此,西方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伦理传统尽管作为相互对应的理论流派对人的道德存在进行了符合各自本身逻辑的论证,但其将人性截然割裂,使人要么超然于世俗,做一个无私无欲的 “幽灵”,要么基于私欲而将善恶交于外物,做一个只会靠外在规则来指导行为的“快乐人”。前者拿一个幻想世界的人格来要求现实中的人,后者则从现实的个人私利出发,否定了德性对人类的善和美好生活的承担。毋庸置疑,道德及其教育无论以以上哪种人性作为人的本质存在来建立自己的本体论根据,都难以获得真理性与合理性的辩护。
对人性进行割裂而使道德教育失于真实的人性本体依据,这样的哲学论争在中国哲学史上,则表现为理欲之辩。《礼记·乐记》就已提出了理与欲之分,至宋明时期理欲分野达到极端,致使理欲之间出现典型的紧张与对峙。尽管至明清之际,哲学家开始更多地从相容、互动的角度理解理欲之间的关系,但是总体而言,理欲二分对立的伦理思想传统构成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道德实践的基本脉向。我们说,理作为超验的规范,即如朱熹所言的“所当然之则”,它以普遍的形式,规定了道德主体应当承担的一般义务,而欲则首先与生活世界中的存在相联系,并涉及广义的情、意等。以合乎理为人性之本质规定,亦即以理为道德行为的推动力,“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否定和排除生活世界中的具体存在成为道德行为动力的可能。其对道德人格的诉求与西方理性主义伦理脉路相近,其结果亦是将人与其现实生活世界割裂开来。因此,灭人欲的道德及其教育往往导致的是扭曲的人格,虚伪的道德实践。其实,在明清时期,就有哲学家对理欲对立这一人性的道德定位进行了批评,主张理欲之间的相互结合以指导道德生活和道德实践。如王夫之就曾指出:“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离欲而别有理,其唯释氏为然,盖厌弃物则而废人之大伦矣。”[4]也就是说,理欲分离使人远离现实的生活世界,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道德关系和道德实践;理欲分离的道德只能使我们遁入佛门。戴震批评无条件抑制人欲对人的生活的弊端时,指出:“然使其无此欲,则于天下之人生道穷促,亦将漠然视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无是情也。”[5]在戴震看来,灭人欲不仅使人丧失生活热情,更断送了生命追求和人生的活力。
综上,无论是西方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伦理学还是中国传统的“天理人欲”之伦理说,其在道德基础上的分歧反映的也是其在人性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分歧使其相互攻讦,同时又使之产生一种可笑的共生关系:它们都利用对方的威胁来为自己的压制辩护。这种状态还以其他的形式在其他层面上表现出来,如道德上的禁欲与纵欲、传统与现代、相对与绝对、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等等的二分割裂与论争。这种论争使道德失去了终极一致的目的,无论是为了义务还是为了“快乐”或“幸福”,道德实际上都是被作为了工具;道德沦为工具,承载道德价值的人也必然同样沦为工具。其实争论人是一种理性存在还是感性存在、天理存在还是欲望存在,都否定了一点:人具有规定其真正目的的本质。毋庸置疑,有什么样的伦理学就会有什么样的道德教育,因为任何的道德教育都是建基于特定的人性与道德的理解。当道德教育建立在一种偏颇的道德人性理论之上时,其也就失去了其实现自身之真理性的合理性辩护的可能。事实上,无论是西方还是我国,割裂人性的伦理传统至今仍在支配着现实的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成为当代道德教育无以自证进而难以获得令人信服的权威力量的根源。以片面的人学理论为前提,道德教育也就不能负载道德的真实,由此,道德教育脱离生活、陷于功利化等自然亦在所难免。
二、人的多重存在:本真道德教育的人学前提
其实,人的存在即如人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如果我们仍承认道德教育是为了人的生活,那么就不应将人的生活片面化、平面化,因为人的生活意义即在于其丰富多样性,而生活是什么样,人就是什么样,由此道德教育就必须承认人的存在的非片面化、平面化这一真实状况。只有当道德教育关照人的真实存在,其对道德的解释才会贴近真实生活,从受教育者角度来讲,“那道德及其教育”才令人信服并值得信奉。因而,本真的道德教育应以人的多重存在为其人学前提。
法国当代哲学家埃德加·莫兰在概括既有的人性研究的问题时指出,已有人性研究不能揭示人的本质,其缺陷在于研究范式的片面化。他认为与漫长的数万年人类发展史和已逾2500年的哲学史相比较而言,关于人的科学的历史甚可忽略不计。[6]在他看来,既有的人性理论对人的理解是封闭的、片段的和简化的,它把人同自然和他的自然本性割裂开来,把自然与文化割裂开来,把人简化为“工匠”和“智者”。这种封闭的、简化的理论范式将人的概念变成了岛屿似的概念,[7]即或立足于个体或依托于社会,或只强调自然本性或仅持守社会倾向,而在理论形态上则归属于生物学主义、社会学主义或者人类学主义等片面化的范式。理论研究范式的狭隘性撕裂了人的完整性,最终无以科学地解释人的实存、应存与能存之间的逻辑辩证关系,更无从解决人之个体、社会与类存在的统一性问题。其实所谓研究范式的迷失之关键在于那些理论不是从整体性上把握人,或者其思考的出发点就不是整体意义上的人的观念。事实上,人的存在是具体的、现实的,兼具感性与理性、生物性与社会性等多重特征,且这种多重存在构成了人的整体,只不过从类的角度讲,人具有自由自觉的本性,正是这种自由自觉性使人保持了自身之多重存在的整体与和谐。可以说,人的多重存在是人天生的存在方式,而这种多重存在也是源于人自然的生活形态本身。即使是仅从人的精神存在角度来说,也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的,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结构说及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等心理学研究已经揭示了这一点。马克思讲,生活怎样人就怎样,多彩的生活表现了人的多重性,其实生活之丰富多彩亦源于人之存在的多重性。单一的人必定导致单一的生活,而单一本就不是生活的全部和本性,如此,单一也本就不是人的全部和本性。所以,多重存在才是人的现实和真实存在。在人的不同发展阶段,或人处于不同的生活境遇中,总是呈现出不同的心理倾向性,或生物学的,或社会学的,亦或人类学的,多种倾向性的失衡易使人自身的健康发展受到毁损,如此才有了人的社会实践以发展人的自由自觉性。社会实践体现了人对自己的多重存在的自由自觉地整合。由于社会实践的要求是基于人的多重存在的现实,所以它才有明确的目的性,而实践本身体现着人自身的自由自觉性,所以人的存在是一种目的性存在。
道德本质上是人存在的一种方式,道德的本体论承诺及其价值根据的考察,不应离开这一基本事实。因此,追寻道德的本源不能仅仅指向超验领域,或者仅仅指向感性形态。人首先是一种具体的多重存在,既呈现出感性的形态也有理性与精神的规定;既是一个个的个体又展开为类和社会的结构。略去其感性、生命之维,人便只是抽象的存在;漠视其社会的、理性的规定,则难将人与其他存在区别开来。作为人的存在的方式,道德的价值并非外在或超然于人自身的存在,道德生活即体现着人的自由自觉的有目的的实践方式——使人从自己的多重存在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扬弃自身。因道德生活,人从而由事实所是走向可能所是。
麦金太尔指出,道德构架是一个必需具备三个要素的结构:未经教化的人性,实现其目的而可能所是的人,以及使他能够从前一状态过渡到后一状态的道德训诫。而伦理学的全部意义也就在于使人能够从他目前的状态过渡到其真正的目的。但是,把人性截然分为要么理性要么非理性的做法,实际上拒斥了目的论的人性观,或者否认了道德的人性目的。尤其是在现代这个道德相对主义的时代[8],更是从根本上消除了“实现其目的而可能所是的人”这一概念。人的多重存在的观念被消除,任何的目的概念也就被放弃,其结果是使道德构架只残存下两个关系模糊的要素:一个是某种特定的道德内容即丧失了其目的论语境的道德命令;一个是某种有关未经教化的人性本身的观点。麦金太尔进一步指出,既然道德命令是为了校正、提升和教化人性,那么这些道德命令显然无法从有关人的本性的片面陈述中被推演出来,也不可能以其他方式通过诉诸其特性来证明其合理性。因为以这种方式所理解的道德命令很可能会遭到以这种方式所理解的人性的驳斥。[9]因此,执于片面的人性假设而不是以目的论的多重存在的人性为本体论根据,道德及其教育就无法建立自己的真实的合理性基础,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有效批判,由此也就失去权威。道德的追求以人的存在为本体,善的本源即在人自身,善即在于对人的存在价值的肯定,人格与德性所体现的首先就是对完美存在的追求和确证。因此,人格与德性的真正意义应当从人自身的存在中去追寻:正是实现存在的多方面的潜能和内在价值,构成了德性的真实内容。德性与人格实现的是“to do(做什么)”与“to be(成就什么)”的统一。道德不以人的真实存在为本体,也就难以使做什么与成就什么达到相互统一。道德存在集中地体现了人的本质所在,它不是现成存在,而是人的动态的生存性存在。所以道德展现的是人的生存意义,是人对自己的不断澄明和成就。以道德称义人,才会使人获得自身存在的运动方式,即“做人”才是一个自由自觉的历史的运动过程,亦即是人的真正的生存过程。因此,道德关照的是人之实存、应存与能存的统一,而非片面;道德存在体现的是人之个体、社会、类存在的统一,而非片面。道德因人的多重存在而存在。道德存在就是人对自身多重存在中之最本质人性的确证与表现,亦即道德就在于成就人,就是对自身多重存在的不断扬弃。[10]也就是说,道德体现着人的实践的自由自觉性。
正因为人是具体的多重存在,才需要道德来实现自身的自由自觉地扬弃,由此也才需要道德教育来发展人的自由自觉性,来指导人的自我扬弃的道德实践。道德教育体现着人的自觉意志,也使人产生自觉意志。故而道德教育不是为限制人而教育,不是为伦理规范而教育。道德教育存在的根本目的不为别的,就是使人获得“人”的称义。所以,它就是教人正视自己的多重存在,并发展自己的自由自觉性而不断扬弃自身,自觉为人,实现人之整体的可能存在;就是实现道德与人的本质存在的本体统一。人性扬弃是道德教育的使命,也是它的最终归属。正是以人的多重存在为前提,道德教育才会由人的真实生活出发,对道德的解释更符合人性,更符合社会生活的现实存在,道德及其教育的真实意义才会得到合理性辩护。
基于人的多重存在,道德教育发展人的自由自觉意志以善其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在道德上受过教育的人”就要变成单一存在的人。道德对人性的扬弃乃在于使人形成善善、恶恶的特定的人格或德性,而非使人祛除存在的多重性,是要使人性的内在结构趋于和谐而主动利于美好生活的生成与延续,而非要强制人作出牺牲被迫迎合特定的规则及精神要求。本真的道德教育就是忠实于道德的本真意义,并通过发展受教育者的心智,使其理解并信奉道德的这种意义,进而自由自觉地整合自己的人性结构,能够使自己的行为及内在品性更有利于自身、社会及类的生存和发展。正因为道德教育发展人的道德自由自觉,才使人对价值的主动追求成为可能,使人性的更加丰富和不断超越成为可能,所以,道德教育最终促使人的自我扬弃而致人的多重实存变得更为和谐与完美。
西塞罗曾断言:“事实上,如果找到指南,没有任何民族的任何人不能获得美德。”[11]但是,我们说,只有道德教育以完全不带偏见的态度承认人的多重存在这一事实,并以其为教育逻辑展开的人学前提,其所寻觅的指南才会有现实意义,所构想的完美道德人才会反映道德的真实,所赞赏的美德才值得我们向往。由此道德及其教育才会令人信奉。毕竟,以真实的人性为前提才会有真实的道德教育,真实的道德教育才会展示道德及其教育的真诚,而只有真诚最能赢得信任。
[1]戴木才.时代性“道德裂变”及其道德哲学拯救[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2]章海山.西方伦理思想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绪言部分.
[3][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何怀宏,廖申白译.伦理学体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405.
[4]读四书大全说(卷八)[A].船山全书(第六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1,911.
[5]戴震集·孟子字义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73.
[6][7][法]埃德加·莫兰.陈一壮译.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173.
[8][美]L.J.宾克莱.马元德等译.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6.
[9][美]A.麦金泰尔.龚群译.德性之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69-71.
[10]刘丙元.人性的扬弃:道德教育存在的本真意义[J].山东师大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1).
[11][古罗马]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57.
刘丙元/山东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
(责任编辑:刘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