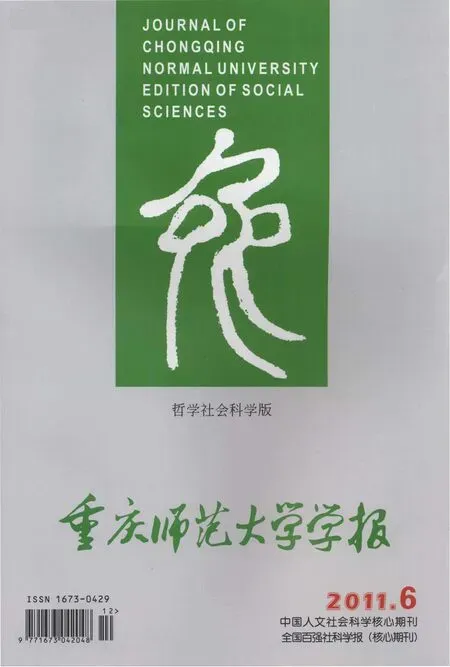李商隐的经学背景考论
谢建忠
(重庆三峡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万州 404000)
李商隐的经学背景考论
谢建忠
(重庆三峡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万州 404000)
李商隐创作的一翼深深植根于经学的土壤之中。其家庭的经学教育传统、青少年时代的经学教育和仕进道路上的经学考试,都显示出他具有良好的经学背景。
经学;家庭传统;经学教育;科举仕进
唐文宗时代是一个重经学的时代。唐文宗喜好经学,郑覃以经学的精深淹博而位至宰相,刊刻了开成石经供天下士子参照学习,经学之盛,蔚然成风。这种风气渗透入教育、科举、仕途、文化、文学等诸多方面,影响制约了这个时代诸如李商隐等许多文人的人生行为和思想观念。
李商隐的家庭有良好的经学教育传统。曾祖父李某,字叔洪“年十九,一举中进士第”[1](859)。进士除诗赋策考试外,还需通经,即考“帖经”,如《通典》载开元“二十五年二月,制:‘……其进士停小经,准明经帖大经十帖,取通四以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策,考通与及第……(天宝)十一载……进士所试一大经及《尔雅》,帖既通而后试文试赋各一篇,文通而后试策,凡五条。三试皆通者为第。’”[2](356-357)按照程序,进士考必须先考“帖经”,开、天后且多是“帖大经”,考试通过后才能参加后面的考试。这种帖经考试相当于用经典的原文来填空,主要考记诵的能力,对浩繁的经学经典的记诵如果达不到滚瓜烂熟的程度,是不可能通过考试的,也没有参加后面一系列考试的资格。由此可见,李商隐曾祖父所受的经学教育的功底是很深的。
李商隐祖父李俌,曾为邢州录事参军。《请卢尚书撰曾祖妣志文状》载“夫人既孀,教邢州君以经业得禄”[1](860),一般认为“当是以明经登第而得官”[3](13)。明经科考试则是以《五经正义》等经典的经疏作为考试内容,有针对经文的“帖经”,还有针对经义、疏义的所谓“口义”或者“墨义”考试,难度不小。例如权德舆作考官时的《明经策问七道》中的《毛诗第五道》:“问:风化天下,形于咏歌,辨理代之音,厚人伦之道。邶、鄘褊小,尚列于篇;楚、宋奥区,岂无其什?变风雅者,起于何代?动天地者,本自何诗?南陔白华,亡其辞而不获,谷风黄鸟,同其目而不刊,举毛、郑之异同,辨齐鲁之传授。墙面而立,既非其徒,解颐之言,斯有所望。”[4](4940-4941)无论是题量或者其难易度,都很有分量[5](31-38)。此例说明,一是明经举的“明经策问”依注疏进行命题、答卷,这与史书所载“(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6](71)的教育科举政令吻合;二是明经举考生必须把经典及其注疏背诵、理解得滚瓜烂熟,否则,帖经和策问这两道门坎是迈不过去的。李商隐所说的邢州君“以经业得禄”这五个字后面,不知道其祖父李俌在“经业”上面所花的功夫有多深,鉴于李俌相关资料的限制,所业之经的情况付之阙如。
李商隐有个堂叔李某,“年十八,能通《五经》”[1](855),不幸其父病倒,遂放弃在国子监太学的学业返回家乡,其父死后,庐于冢侧,遂誓终身不从禄仕,师友皆诱劝他参加时选,都遭到其坚决拒绝。李某潜心经学,“益通《五经》,咸著别疏,遗略章句,总会指归。韬光不耀,即成莫出,粗以训诸子弟,不令传于族姻,故时人莫得而知也。”[1](856)所谓“别疏”,当是与《五经正义》有别之注疏,从这一点看,李某钻研经学是较深的,可能有一些自己研习《五经》的心得,而且李某还用来训教子弟,不传族姻,颇有点类似家传“宝典”意味。尽管我们无从判断李某的“《五经》别疏”在经学注疏上有什么特别的贡献,然而却可以判断他“别疏”《五经》是很有气魄的,也是花了极大的精力的。综上看来,李商隐的曾祖父、祖父、堂叔等人所从事的经业,营造了这个家庭的经学教育氛围,形成了家庭经学教育的传统。从所存资料看,李商隐的裴氏姊“生禀至性,幼挺柔范,潜心经史”[1](863)。李商隐决心抚养其堂叔李某的遗孤:“瑊等既幽明无累,年志渐成,则当授以《诗》《书》,谕其婚宦,使烝尝有奉,名教无亏。灵其鉴此微诚,助夫至愿。”[1](338)这些资料也表明,经学教育是这个大家庭的传统,经学教育代代相传,即所谓的《诗》《书》传家,也是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李商隐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接受经学教育就不可避免了。
李商隐早年的经学教育是从五岁开始的。他在《上崔华州书》中自述说:“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诵经书,七年弄笔砚。”[1](441)五岁读经书,不可能是“五经”或“六经”全读,一定是挑选比较适合儿童识字教育、诵记教育的一两本经典开始学习教育。根据唐人早期经学教育的一般情况,我们可以推测李商隐开始学习的大致是哪几部经典。《册府元龟》记载“房玄龄幼而聪敏,五岁能诵《毛诗》”[7](9211),可见房玄龄的经学教育发蒙是从《毛诗》开始的。王维《裴仆射济州遗爱碑并序》记载裴耀卿:“八岁神童举,试《毛诗》《尚书》《论语》及第”[8](761),既然是八岁神童举及第,那么诵读《毛诗》、《尚书》、《论语》当从四、五岁起就开始了。《新唐书》记载了李白“十岁通《诗》、《书》”[9](5762),可见李白早期的经学教育是《毛诗》《尚书》。《旧唐书》记载了韦温“七岁时,日念《毛诗》一卷。年十一岁,应两经举登第”[6](4377),可见韦温的早期经学教育是从《毛诗》入手的。白居易早年的经学教育也是如此:“诸子尚幼,未就师学,夫人亲执《诗》《书》,昼夜教导。”[10](2838)综上大致可以说,唐人早期经学教育大多是从《毛诗》、《尚书》等开始的,再结合李商隐《祭处士房叔父文》里决心承担起其堂叔儿子瑊等的早期经学教育“当授以《诗》《书》”来看,我们推测李商隐“五年诵经书”有可能是指开始诵读《毛诗》、《尚书》。这两部经书在李商隐的记忆里是很深刻的,多次在他的诗文里出现,如《为怀州刺史举人自代状》:“本以《诗》《书》,绰有机断”;《赠送前刘五经映三十四韵》:“《诗》《书》资破冢”;《为安平公谢除兖海观察使表》:“古为《诗》《书》俎豆之乡,今兼鱼盐兵革之地。”
《毛诗》《尚书》并称,既是当时社会的共识和习惯,也是李商隐的认知,这种认知与其早年所受经学教育有关。
李商隐早年直接受到其堂叔李某的经学教育。他回忆说:“商隐与仲弟义叟、再从弟宣岳等,亲授经典,生徒之中,叨称达者,引进之德,胡宁忘诸?”[1](858)“某爰在童蒙,最承教诱,违决虽久,音旨长存。”[1](336)从回忆中可以看到,李商隐与仲弟、再从弟等人是由其堂叔李某教授《五经》的。如前所述,堂叔李某治经学的功夫下得深,著有《五经》“别疏”,他用自己的特别见解,来引导学生通经致用,教授之功让学生不可忘怀,而少年时代的李商隐受其教益最为深刻,学到的经学知识和理论深深扎在了自己的脑海里,永远也不会忘记。
李商隐小时候还下功夫阅读了其他经学著作,《与陶进士书》记载:“始仆小时,得刘氏《六说》读之”,牢牢诵记,领会其中的大义,而且还“盖尝于《春秋》法度,圣人纲纪,久羡怀藏,不敢贱薄,连缀比次,手书口咏,非惟求以为己而已,亦祈以为后来随行者之所师禀”[1](442),学习经学的虔诚态度行为于此可见。所谓刘氏《六说》即指经学著作,刘氏指刘知几的儿子刘迅,右补阙,撰《六说》五卷,《新唐书》载:“迅续《诗》、《书》、《春秋》、《礼》、《乐》五说。”[9](4525)《国史补》卷上还记载了其内容:“刘迅著《六说》以探圣人之旨,唯说《易》不成,行于代者五篇而已,识者伏其精峻。”大意是刘迅阐发《诗》、《书》、《春秋》、《礼》、《乐》,十分精到,观点鲜明有力,通经学的人都很佩服。李商隐小时候读刘迅的经学著作“连缀比次,手书口咏”,体会到“《春秋》法度,圣人纲纪,久羡怀藏,不敢贱薄”,从中可见李商隐接受经学教育时用力之勤、敬仰之诚和所受影响之深。
早年的经学教育为李商隐的科举仕进奠下了扎实的基础。李商隐大和七年参加了科举考试。大和七年有制:“其进士举,宜先试帖经,并略问大义,取经义精通者;次试议、论各一道,文理高者,便与及第。所试诗赋并停。”礼部曾奏具体方法:“伏请帖大经各十帖,通五通六为及格;所问大义,便于习大经内,准格明经例问十条,仍对众试口义。伏惟新制,进士略问大义,缘初釐革。今且以通三通四为格,明年以后,并依明经例。其所试议、论,请各限五百字以上成。敕旨依奏。”[7](7684、7683)这说明大和七年的进士考试包含了帖经、口义、议论等环节,帖经、口义无疑是考经学知识和通经能力。大历初,归崇敬的奏疏里明确指出“大经”即《礼记》、《左氏春秋》这两部经典[9](5037),那么大和七年李商隐参加进士考试无疑是针对《礼记》、《左氏春秋》进行了“帖大经”各十条、“众试口义”各十条。帖经必须答对《礼记》五条、《左氏春秋》六条,方可及格,众试口义必须答对《礼记》三条、《左氏春秋》四条,方可及格,然后再试议、论,这些考试通过后,方才进入录取环节。从《上崔华州书》看,李商隐是通过了所有考试环节的,最后在录取环节被知贡举贾餗刷掉了,其原因是“为故贾相国所憎……居五年间,未曾衣袖文章,谒人求知”[1](441)。原因很清楚,就是李商隐不愿意“学人行卷”(《与陶进士书》),故未被知贡举贾餗所录取。大和七年录取二十五人,根据《通典》记载“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2](357),可以推定,进入录取环节的考生一定是少数。这少数考生在“帖大经”、“众试口义”、“试议、论”三个环节的考试中一定是及格者,或者说是通经的佼佼者。由此可以断定,李商隐经学教育的功底一定很厚,通经的程度不可谓不高。
李商隐开成二年考中进士,一般认为,李商隐自述的令狐綯向高锴的举荐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不错,但我们认为,如果没有李商隐自己经学教育的深厚功力和诗、赋的才华,他不可能在考试过程中进入录取环节,进入不到这个环节,谁的举荐也起不到作用。因为大唐律明文规定:“知而听行,亦从贡举以下知非其人,或试不及第,考校、课试知其不实,或选官乖状。各与同罪,谓各与初试者同罪。”[11](1127)所以即使有令狐綯的举荐,如果李商隐的帖经、问义、诗赋、试策等环节有一个环节未通过,那么礼部伺郎知贡举高锴也不敢网开一面的。李商隐能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其一端当得力于他深厚的经学教育背景。
还有必要指出,开成三年李商隐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时,其考试内容包括天地灾变、人事兴废、皇王之文、圣贤之文以及草木虫鱼等[1](443),这些内容与《诗》、《书》《礼》《易》《春秋》及其经学阐释有很紧密的联系,所以博学宏辞科考试主要转向了通经致用能力的测试,李商隐能够通过考试(虽然最后录取时被人刷掉了),其经学知识的深厚和通经致用的能力,应当是无容置疑的。再者,李商隐受到考官周墀慧眼识玉,也有一定原因。周墀,长庆二年擢进士第,大和中郑覃奏周墀等校定开成石经的九经文字[6](4491),其经学功力的深厚可见一斑。周墀能够在博学宏辞科考中相中李商隐,这也可旁证李商隐的经学功力非同一般。
李商隐开成四年、会昌二年两以书判拔萃为秘书省校书郎,书判拔萃是吏部考试,“试判三条,谓之拔萃”,判文考试也跟经学有关,《通典》载判文拔萃考试的要求是:“採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2](361)李商隐考试的判文无存,但我们可从白居易当年所作的判文中窥其端倪。如:“得甲去妻后妻犯罪请用子荫赎罪甲怒不许三姓好合,义有时绝,三年生育,恩不可遗。凤虽阻于和鸣,乌岂忘于反哺?旋观怨偶,遽抵明刑。王吉去妻,断絃未续;孔氏出母,疏网将加。诚鞠育之可恩,何患难之不救?况不安尔室,尽孝犹慰母心;薄送我畿,赎罪宁辞子荫?纵下山之有怒,曷陟屺之无情?想《芣苢》之歌,且闻乐有其子,念《葛藟》之义,岂不忍庇于根?难抑其辞,请敦不匮。”[10](3561)白居易的判文不背人情,合于唐律,又引《毛诗》经义,经史之义洽切,被评论家称之为“真老吏判案”的精彩判文。这样的判文不仅要求经学的功底,而且还要求通经致用的能力。李商隐能够在“书判拔萃”考试中胜出,不能不说是具备了深厚的经学功底和较高的通经致用能力。
正是由于李商隐具有良好的经学教育背景,经学知识和通经致用的能力都达到堪为人师的地步,所以大中五年他被选任为国子太学博士。正如他自己在《樊南乙集序》所说:“选为博士,在国子太学,主事讲经,申诵古道,教太学生为文章”[1](441),太学博士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从事经学教育,而太学的经学教育与科举的经学考试又是紧密对口的。《唐会要》里对博士的工作有详细记载:“诸博士、助教皆分经教授学者,每授一经,必令终讲,所讲未终,不得改业。诸博士、助教皆计当年讲授多少,以为考课等级。应补当司诸学生等,按《学令》云:诸生先读经文通熟,然后授文讲义。每旬放一日休假,前一日,博士考试。其试读,每千言,内试一帖,帖三言;讲义者,每二千言内问大义一条,总试三条,通二为及第。”[12](1373)太学博士这个岗位,择人标准很高,“须取有德望学识人充”[12](1370)。李商隐能被选任为太学博士,足证其经学造诣已经达到了相当深的程度。
综上可见,经学背景在李商隐的文化背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其经学背景除了给他提供人生入仕态度的精神力量和他诗文的经史典故之外,还在他的文学创作中起着积极正面的影响作用,如其创作中的“怨刺”、“比兴”等诗学精神就主要源于《毛诗》及其经学阐释。
[1] 李商隐.樊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 杜祐.通典[M].中华书局,1996.
[3] 刘学锴.李商隐传论[M].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
[4] 董诰.全唐文[M].中华书局,1987.
[5] 谢建忠.《毛诗》及其经学阐释对唐诗的影响研究[M].巴蜀书社,2007.
[6] 刘昫.旧唐书[M].中华书局,1986.
[7] 王钦若.册府元龟[M].中华书局,2003.
[8] 陈铁民.王维集校注[M].中华书局,2005.
[9] 欧阳修.新唐书[M].中华书局,1986.
[10]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1] 徐松.登科记考[M].中华书局,1984.
[12] 王溥.唐会要[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Research on the Background of Li Shangyin's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Xie Jianzhong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ollege,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Chongqing,Wanzhou 404000,China.)
Li Shangyin’s creation deeply rooted into the soil of the study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His family tradition,the education in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his youngsters and the official classics exams all shows that he has a good background of Confucian classics.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family tradition;education in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ransformation
I206.2
A
1673-0429(2011)06-0078-04
2011-09-10
谢建忠(1950—),男,四川广安人,文学博士,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