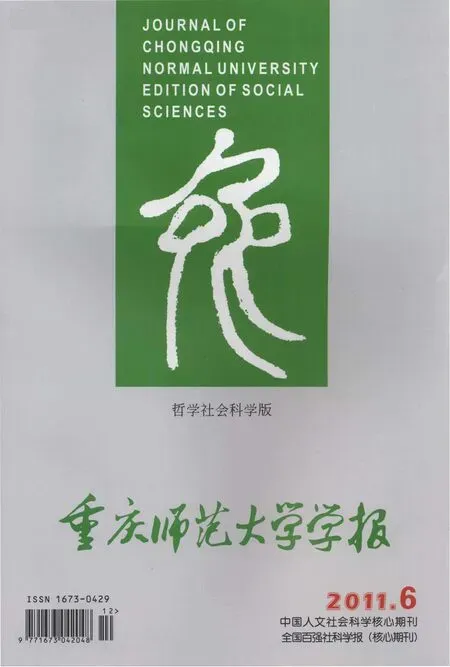向死而生:论王小波小说的生死观
张川平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语言文学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51)
向死而生:论王小波小说的生死观
张川平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语言文学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51)
王小波小说中的“死亡叙事”在主体建构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以对死亡景观和死刑想象独特的文学呈现、贯穿其间的爱欲与死欲的纠结、对死亡的凝视和深描、对死后世界的想象等,建立起以主体建构为目标和目的的死亡叙事,“向死而生”的生死观成为其小说文本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支点。
王小波;死亡叙事;向死而生;主体建构;爱欲与死欲
就王小波的文学作品而言,死亡不仅意味着生物个体的终结,也与主体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死法”是“活法”的镜像或折射。王小波正是在此意义上,建立起以主体建构为目标和目的的死亡叙事,“向死而生”是其人生和叙事的一大重点。
“向死而生”是存在主义生死观的重要内核,海德格尔这样阐述其具体内涵,“生向着死。躲避死,也依然是沉沦着向死而在。存在同死亡连在一起;生存之领悟始于懂得死亡。死亡张满了生命的帆,存在的领悟就是从这张力领悟到存在的。……死亡是每个人自己的无可替代的可能性。所以,领悟着死来为存在作筹划,就是从根本处来筹划各种可能性了。”[1](408-409)王小波笔下人物“死亡”的“可能性”和自由空间暗示了“生存”维度的相应侧面,因此,直面“死”便意味着反思“生”。
一、死亡景观与死刑想象
在《三十而立》中,我们看到一种颇具震惊效应的死亡景观。看护老姚,使王二置身于急诊室死亡气息的包围和压抑之中。他触目所及是丑陋的垂死的病体,如地狱般令人毛骨悚然,声音恐怖,气味难闻,灵魂逃离,尊严丧失,亲情残缺,人性漠然……生命在通往死亡的最后一站挣扎得如此痛苦和孤独,旁观者不由自主对死亡产生一系列狰狞、惨酷的联想。作者这样写道:“这是险恶的夜,夜空紧张得像鼓面,夜气森森,我不禁毛发直立。在这种夜里,人不能不想到死,想到永恒。死的气氛逼人,就如无穷的黑暗要把人吞噬。”[2](113~114)
在王二因死亡而触发的身心感应中,我们看到了海德格尔所言的带来“本真生存”的“畏”。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写道:“畏剥夺了此在沉沦着从世上事物以及公众讲法方面来领会自身的可能性,畏把此在抛回此在所为而畏者去,即抛回此在的本真的能在世那儿去。畏使此在个别化为其最本己的在世的存在。”[1](92)“畏”令此在摆脱对死亡的“闪避”而“先行到死”、“直面死亡”,“因此也就从烦忙于世务混迹于众人的羁绊中解放出来。怕死使此在裹足不前,而畏却在死亡的空无面前敞开了生存的一切可能性,任此在自由地纵身其间”。[1](97)我们在《三十而立》的“急诊室”(对病人而言,其更确切的名称是“待死室”)看到了“畏”和“怕死”两种截然不同的针对死亡的态度。
面对死亡的威压,儒家伦理和革命伦理——即血缘亲情、同志友爱——暴露出其冷漠、虚伪、无力、失范的一面,对死亡本身的恐惧和对他人之死的爱莫能助成为他们放弃情感抚慰的借口。孔子有言:“未知生,焉知死?”中国文化形成了关注“生”漠视“死”的传统和特点,“死”只被视为人降生之时即已注定的肉体毁灭的必然,从根本上缺乏终极关怀、哲学思考、宗教导引,只规定了诸如“丧葬”、“守孝”等“礼”的仪轨,更多着眼于“身”而忽视了“心”的死亡困境。这与海德格尔“未知死焉知生”的“向死而生”的存在主义生死观相比,侧重点截然相反,也造成了瞬间亲情逃离、(一生仰赖的)“母胎”脱落从而搁置病体、流放灵魂的死亡危机,也即,源于“怕死”的自私、漠然以及对死亡本身的“滑开”和“闪避”。那个因家中女人“害怕死人”而把患了绝症已入膏肓的姥姥拉到这环境恶劣的急诊室等死的年轻人,根本无视姥姥的义愤和无声的抗议,只关心哪儿能买到令其“眼睛一亮”的重九牌香烟。在单位为抓贼摔断腿的老姚无人愿意看护,只能躺在一堆垂死者中间忍受病痛折磨,恐惧使他抓住王二这平时的怀疑和防范对象充作依附稻草。肉体的溃败、生命的消散凝聚并放大了人生所有的“忧”、“烦”、“畏”,子孙、同事的麻木无情,使他们在未死之时便觉悟到已被“关系”的“母胎”抛弃,像一只无依无助的羔羊,孤独地被拖到刹那间将告结束的生死临界点,但他们此刻心理的空间印象却似“果壳中的宇宙”至微至大,其精神煎熬不啻“一日长于百年”的炼狱体验。
这种任人摆布、提前被当作尸体处置的死亡景象强烈刺激了王二,他以梦境的形式预见了自己的死亡步骤——一种常态的程式化的操作过程。护士按规程打理尸体,着装,化妆,掩饰容颜的衰老迹象,抹去疾病的摧残烙印,消泯痛苦挣扎的刻痕,使之呈现一种等级化的死亡待遇营造出的平均化的体面和安详。“事实上,我要做个正经人,无非是挣死后塞入直肠的那块棉花。”这是礼遇有加的丧葬和悼念仪式给王二的最大教益,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活着的时候无法被削平的峥嵘头角、非凡个性,经此一番死亡“打理”便轻而易举被捕获和修整了,死亡遂成为使其生不从死亦从的陷阱。
对此,王二以自己的想象预先拒绝、背叛了程式化的死亡。那是一种“血淋淋的光荣”——“当他们把我拖上断头台时,那些我选中的刽子手——面目娟秀的女孩,身穿紧绷绷的黑皮衣裙,就一齐向我拥来,献上花环和香吻。她们仔仔细细把我捆在断头桩上,绕着台子走来走去,用钢刀棍儿把皮带上挂的牛耳尖刀一把把钢得飞快,只等炮声一响,她们走上前来,随着媚眼送上尖刀,我就在万众欢呼声中直升天国。”[2](114)由此可见,王二的选择不是被“无常”赶入窒息的境地,无声无息地寂灭,而是无畏地主动承受死刑,伴着异性的爱与美,享受死亡,挑战死亡,在死亡的血气蒸腾中使生命力以最绚烂的形式释放和喷发。这种主动赴死、以生驭死的姿态并没有道义伦常的寄托,所谓“舍生取义”的“义利之辨”和“鸿毛”、“泰山”的“轻重之辨”于王二而言淡若浮云,他的死刑想象是对生存之悲的反抗和超越。死法的选择体现了王二特有的“贵生”观念,那就是变被动承受为主动取弃、变盲目麻木为清醒警悟——哪怕是清醒地品味身心痛楚、直面死亡的泰山压顶,在生死大限之内高扬个人主体性,实现生命的尊严。
二、爱欲与死欲的纠结
在王小波的死刑想象中,我们看到类似福柯的“求死意志”以及死亡降临时那种“巨大的欢欣”。这酷似虐恋剧目的死亡模拟表演和死程的反复和延宕,频繁出现在王小波笔下的人物身上。如鱼玄机的主动“自首”、公开受死(《寻找无双》);红拂费尽周折申请自杀指标且不能一绞而毙,而要在生死的夹缝中忍受无尽的折磨,最终她是否死去仍是一个谜(《红拂夜奔》);女刺客被砍头的情景呈现为一种回环复沓式的改写,其间贯穿着浓郁的品味死亡、享受死亡的愉悦、兴奋和凄美的调子(《万寿寺》)。
王小波处理死亡情节的态度和角度偏向于对生命的一种形而上的凝视和深思,死亡想象常常是一种痛苦冲动的“极限体验”。藉死亡的排练、预演,作家及其虚构人物“第一次认识自己”,实现了一系列心理体验的转换,即“把罪行变成喜悦、把痛苦变成快乐、把折磨变成销魂,以及(这最不可思议)把死的愿望变成压倒一切且不可言状的爱的情感……并体验一种神秘的狂喜”[3](12)。所以,直面死亡、思考死亡,获得一种身体和心理的尖锐新异的高峰体验,在王小波构建个体自我的过程中是至为重要和必要的环节,是其发明自我、改变自我、超越自我、向死而生的题中应有之义。
弗洛伊德指出:“人有两种冲动,一种针对生命,多少有点等同于性欲的里比多;另一种是死亡本能,其目的就是要毁坏生命。”[4](123)而且,两种本能常常混杂在一起,“或者针对自我,或者针对自我之外的对象”,这样的纠结在王小波的小说文本中颇为常见。不仅《三十而立》中的死刑想象把痛感与快感、死亡与性联系起来,在《似水流年》、《我的阴阳两界》等“王二系列小说”的主人公身上,一再呈现生死爱欲纠结渗透的主题和情节。最具典型性的是《似水流年》中王二与小转铃置身于“文革”禁欲时代近于被遗忘的角落、一个废墟般破败的建筑中,在青春期涨潮式欲望的驱使下,几乎每晚上演以死刑想象作为“性唤起”和达到“性高潮”手段的性爱狂欢。小说这样写到:“干之前,我编了个小故事,说到我将被砍头。窗外正给我搭断头台,刽子手在门外磨刀,我脖子上已被画上了红线,脑后的头发已经剃光了。人们把小转铃叫来,给她一个筐,让她在里面垫上干草:‘别把脸磕坏了,这可是你的未婚夫!’准备接我的脑袋。”[2](170-171)小转铃的性欲伴随着因恋人即将赴死的恐惧喷薄而出,她被各种“新死法”——如“绞死”、“开膛挖心”——刺激得性欲勃发,命悬一线的危境是他们把握自我和爱欲的所在,死亡想象使每一次彼此的给予和接受在死刑的重压下变得诡秘、郑重、歇斯底里、刻骨铭心。小转铃痛哭着用身体承接、抓住极致的幸福,爱欲与死欲在此合二为一。
与之类似,红线对女刺客的死刑想象也弥漫着一种同性之间灵肉难分的爱欲,而《似水流年》中的线条,本是一个对任何人与事都持“无所谓”和无所畏惧态度的顽劣女孩,但其生命中遭遇的两次生存危机或曰死亡危机皆与“性”有关。第一次表现为初次看到男孩粗大性器的心理震撼,使她一度“关闭”了所有的智力活动,沉沦于自我与他者、女性与男性的相较相斥的巨大晕眩中不能自拔,由异性性器官引发的阉割和匮乏的焦虑,甚至使她产生了无以为生的迷乱和既渴望死亡又惧怕死亡的迷狂。她第二次与死亡面对是初次性交时的身体迷茫和心理无助,身心经历了类死式“血肉模糊”的初创后,她开始步入随时获得“欲仙欲死”的性体验的成熟人生。她的死亡危机由“性”引起、印证、强化,也通过“性”得以最终克服。爱欲与死欲的隐喻式表达及其置换,标志着线条的个体自觉与自我确立,也即,在爱与死彼此抵达、纠缠而形成的三角区域和愈收愈紧的夹缝中,自由经营的自我在与异性的交流和托付中处于一种被安全呈现和贮存的佳境。
王小波笔下种种感染了“死亡本能”的性爱或者说以性爱来呈现的死亡,以其有悖传统、不同凡俗的方式,使人性中“最自由奔放、最随心所欲、最不受拘束的力量”呈锐不可挡之势奔腾涌现。因之,死亡不再是终结,而是生命的涅槃,是撬动生之板结禁锢的锐利武器,是向着自由境界的开启和重生。
三、对死亡的凝视与深描
对于死亡,王小波的思考和艺术表现是多角度和多向度的。他除了“利用”死亡想象和死亡叙事宣示个体主体性的合理、合法及其不可侵犯,并藉之宣泄对生存之“非存在”境遇的不满和反抗之外,还揭示了死亡以一种无法预知和拒绝的偶然,突降并强行终结个体生存的样态。死亡瞬间的爆发制造了无数残酷和惨烈场面的凌驾力量与个体的盲目和渺小之间,呈现视觉和心理上畸轻畸重的失衡局面,死亡带来了生存真空,生命的定格和停滞,激活了对生命和生存本体意义上的形而上思考。这一思考主要由死亡的目击者和旁观者完成,其表达方式则诉诸于对“死程”和“死相”的慢镜头式的还原回放、显微镜式的细节放大、万花筒式的情节碎片拼贴等。这颇似格尔兹所发挥的名之为“深描”的人类学方法。它以“微观描述”的方式来阐释观察和研究对象的文化意义,“是从以极其扩展的方式摸透极端细小的事情这一角度出发,最后达到那种更为广泛的解释和更为抽象的分析”[5](287)。它的一个最为显明和重要的作用在于使长期以来位居主流的“宏大叙事”、宏观概述、“巨型概念”等获得一种浸润着叙事者独特个性的“可感知的实在性”。对于“死亡”这个“巨型概念”,我们向来不乏各个学科、各种角度的本体论、现象学的大而化之的辨析、界定,但无论何种概念都无法涵盖、穷尽类似人体毛细血管的细节究诘。
“深描”的表现方式是“第三者”——既非凶手又非受害者——在猝不及防的震惊效应下对“死亡”的长久“凝视”和反复回味。作家既展示了(非正常)“死亡”降临个体时常常被宏观话语忽略的潜藏在“瞬间”和“皱褶”之类细微时空中的秘密,又藉这种展示使“死亡”凝结为旁观者生命中一个无法克化和剔除的“硬核”,对其情感和精神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死亡”记忆的人生折射成为“向死而生”理念的具象诠释,种种被动的、无意义的“死亡”不再是灌注着作家诗意赞叹、体现着个体自由意志的“行为艺术”,而是质疑和反思的对象。我们看到《革命时期的爱情》写到文革武斗中被一杆大枪刺穿胸膛的人作“胡旋之舞”的垂死表演,作者将他的“死态”与“电流下的蜻蜓”并置:“随着电压与交直流的不同,那些蜻蜓垂死抽搐的方式也不同,有的越电越直,有的越电越弯,有的努力扑翅,有的一动不动,总而言之,千奇百怪。”[2](251)死者——无论人还是动物——不仅无法逃避死的命运安排,而且就连具体的死法都是无法选择的,它的更可悲之处在于“没被电到的蜻蜓都对正在死去的蜻蜓漠然视之”。
王小波以王二为媒介选择并深入挖掘了这一与“死亡本能”和“求死意志”等作为自由标志的死截然不同的死,这是被历史纪录抹消、被历史天平忽略不计的死亡,但却是既抽象又具体的“人”的死亡和“人”的历史,思者因之对“生”之懵懂、被动、盲目产生了“如梦方醒”的彻悟感,被动的“死”通过自觉的个体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并改写了“生”。
四、被剥夺的自杀权和死亡解释权
死亡的被动性,或曰权力对死亡的管理,除了表现为诸如“拿起笔作刀枪”、贺先生、刘先生等这样的“不得不死”之外,还表现为以“自杀指标”的分派作为控制形式的“求死不得”。这是对自我控制死期和死法等权力的剥夺,其意图不关对生命的政治态度和挽留之情,甚至不针对和拒绝“死亡”本身,而是将矛头指向欲死之人,通过对死亡动机和死亡效应的控制而将死亡变为束缚求死者的绳索。
在《红拂夜奔》中,红拂的殉夫愿望一经启动,便陷入了官僚体制及其运作机制的泥淖。手续繁杂至极,必须经过填表申报、等待名额、确定自杀方式等程序框限和执行者的仪式苛求的折磨,速度之慢,效率之低,对她的“求死意志”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官方为了获取贵妇“殉夫”的恰到好处的意识形态寓意,达到最佳社会效益和示范效应,对红拂的自杀实施了至为细致的分段包干和包装处理,使“自杀”这一本来是个体的自主选择的行为,呈现致命的受控状态,死亡在体制面前的无力和委顿尽显无遗。具体而言,红拂的“自杀”已经变为当权者假手“专家”“魏大娘”实施“演礼”程序的最佳借助对象。这一程序先行将红拂的意愿、意志排除在外,而以一系列有条不紊、一丝不苟的“计划”循序展开:“工部要行文到岭南,要当地砍一棵上等的楠木,来给红拂做棺材;国子监要把红拂写入明年魏征丞相的国情咨文内本年度社会风气继续好转一节;国史馆要把她修入正史;中书省要给她拟定谥号等等,这些都和她没有了关系。”[6](323)官方对红拂之死的重视体现在种种豪奢、尊贵的待遇上,但豪奢包裹死之“尸”,尊贵冠以身后“名”,于红拂本人无关。红拂既是御封的“节烈夫人”,也是“钦赐殉夫人犯一名”,在高台上展览漫长而“庄严”的极尽肉体折磨和人格羞辱的死程,享受这份没有人权的“光荣”。个体的主体意识和自由意志,在她发出“自杀”请求时即已死掉,完全被忽略不计了。“她只管等到一个良辰吉日死掉就可。而且这一点也和她没有什么关系:不到那个日子,她想死都死不了,到了那个日子,她想活也活不成了。这就是说,虽然红拂暂时还是活着的,但是我们已经可以把她当作一件事了。”[6](323)红拂因其死志完全被异己力量操纵,成为权欲和物欲围猎开发的“资源”,官方要的是带有务虚色彩的社会效益,必欲按照自己的周密安排置之于死地,红拂的女儿要的是实惠的经济效益,必欲拯救其生命以便将其身体剩余的商业价值在欢场中充分开掘出来。不仅红拂的自杀与自我意愿脱钩,有关她的生死较量也与主体完全分裂。求死意志一经公开,红拂便陷落于生死皆不由己的沉沦之旅。
红拂的“求死不得”相较于李靖的“激情之死”(一向以老迈昏聩混世的李卫公死于“马上风”)。自然是更噬心的悲剧,其可悲之处在于作为主体自决的最后获取机会也被剥夺和接管了。归根到底,“自杀”的自由可视为主体自由的终极体现,它涉及的是“自我及其身体、精神与意志的归属问题”。只有主权归属自我而非归属“他者”(无论这一“他者”是国家还是社会或某一党派、团体),自杀权才能被界定为基本人权。它曾经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化转型过程的一个重要现象”,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知识女性的自杀就曾经是引发公众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的社会现象。只有享有自杀权的主体,才有可能像福柯一样发展一种“自杀的艺术”。那是开掘主体、抵达主体可能性之极限临界点的充满冒险挑战和创造乐趣的活动,沉浸于自杀的单纯与快乐中的主体为自杀所作的准备与红拂的“死亡程序”大异其趣。“装饰它,安排所有的细节,找到各种要素,想像它,听取关于它的忠告,使之成为一项没有旁观者的具体工作,一项只为自己,只为那生命最短暂的一瞬间而存在的工作。”[7](64)福柯所主张的完全个人化、私人化、主体独自选择和承担的直面死亡、碰触死亡的自杀探索,在红拂那里变异为“他杀”表演。可见,在王小波笔下,死亡兼有积极和消极的形态,有主动赴死和被动受死之别,所以,惨烈的死刑可以撑起主体精神的骨架,受控的自杀却是最彻底的剥夺和放弃。
这种“死亡”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启悟和警示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王小波将人生视为一个在日益趋近中学习死亡、准备死亡的过程,他不断给虚构人物制造与死亡狭路相逢的机会,并使死亡记忆成为情感翻腾、思想反刍的一个挥之不去的触媒和焦点。对死亡谜团的探究折射出生存的荒诞,死法成为活法的镜像。个体跨越生死的最大的宿命之悲在于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被设置、被建构、被阐释,包括死后的身与名。《未来世界》中两位知识分子遭遇的非人的身体肢解和语言暴力可资佐证。“我的舅舅”是位患有心脏病的作家,正在等待第二次心脏手术时因电梯事故致死——“被压扁了”、“变得肢体残缺”。“我”作为历史学家在为之作传时,首先在“导向”和“史实”之间面临“陈述”的两难。为了符合“导向”的刚性原则(它也是修史者的生存原则),“我”改写了“舅舅”的死法,为他安排了“痔疮”、“前列腺癌”等与那个时代施之于“不受信任的人”的惩罚机制相关的疾病和死因。另一位怀疑主义哲学家因以“怀疑”为业而遭怀疑,被“安置”到屠宰厂存身,落入全自动的流水作业线被肢解,一只手与猪蹄一起流入超市。关于他的死因有三种推测:“其一,不小心掉进去的;其二,自己跳进去的;最后,被猪赶进去的。”[8](123)两人的意外之死(其直接原因是技术时代的机械故障)呈现出的惨怖与狰狞昭示了死亡本身及其寓意的威力和辐射力,有着强烈的物化、非人、反生命的特征。死亡摧毁的不仅是一堆血肉的生物活性,更可怕的是经由对死因的再次施暴,使对活人的设置和掌控得以延伸和加强。这与尸体的处理和化妆一样,通过话语对死亡的重行肢解、拼装、诠释,权力抹消肉体的同时捕获死亡。
围绕着生死,围绕着个体自我的自主和自由诉求,王小波的文学探索呈现出诸多层面的丰富和复杂。他不仅捍卫人的生命和生存权,而且捍卫死亡的自由和死亡的解释权。“自杀指标”、对尸体的“凝视”和“深描”、死亡叙事的造假与求真,等等,显示了王小波在跨越生死、无限拓展的主体争夺和保卫的战场上和战斗中的智慧凝结和意志执守。这种争夺呈现为环环相扣、循环往复的链状连接,具体表现为,“我”对“舅舅”死因的“求真”叙事因触犯“导向”原则,导致“我”身受其惩、难以为生,生死构成一种多米诺骨牌式的因果效应。这种一触即发、不可遏止的坍塌带来的致命威胁直接指向个体自我的建构和生存。
五、生殖在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双重匮乏和空置
相对于对死亡的关注和表现,生殖在王小波的小说中被大大弱化和空置了。虽然涉性叙事频繁出现,几乎弥漫在他的每篇小说,但这些性活动无一例外排斥生殖,且常常涉及男性的性无能和心理畸化的性压抑。如《白银时代》中呈现“越来越简约”趋势、最后“连热都不热”的“夫妻生活”,《未来世界》中被安置人员面临“比”掉的恐惧,《2015》中“舅舅”到碱场改造后得了“阳痿”病,《红拂夜奔》中虬髯客用打草鞋的怪诞行为来转移和压抑对红拂的爱欲与性欲,等等,不一而足。男性性功能的衰颓固然造成了生殖障碍,但作家并不以此为忤,他意在说明衰颓的起因——生命受控状态——对个体戕害之深。它一直切入最私密的领域,使个体生命在空间舒展、时间延续上全方位受阻。
此外,小说还有多处对精液的无用和无害化处理的描写。如《黄金时代》中王二和陈清扬避居的深山草房周围扔弃了很多避孕套,这也是他们“作案”的物证。小说写到王二射精入土的细节,二人曾先后有生育的愿望,但终未达成一致。《三十而立》中许由受无聊和好奇的驱使,在显微镜下观察自己的精液,惊叹之余并没有产生一种男性的自信,反而滋生了挥之不去的孤独、迷茫、自怜之感。这一有着强烈恶作剧色彩的细节,拒绝、阻断了生殖意义上量的繁衍,蕴含着对主体不确立、不独立状态的焦灼和隐忧。在《2010》中“老大哥”召集的party过后,用过的避孕套竟然装了半垃圾车。这些被隔离和废弃的“精液”一方面喻示了被约束和管制的男性生命力,一方面也表明作家对性欲之“快乐原则”的强调和谨守,非生殖目的的“性”更接近个人和两性的较为原始和单纯的本能欲求,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关系和生殖伦理的剥离。王小波通过排除生殖的性活动和性描写,并非对生物学意义上人类繁衍的拒斥,而是拒绝承担巩固、延续、复制这种压抑、扼杀个体主体性的伦理关系之“质料”的任务,也即,在王小波看来,被排挤、过滤掉主体自觉和自由的个体繁衍是毫无价值的,作为“历史中间物”的觉醒者主动切断这一生物链条的盲目延伸,是一种富有理性和责任感的选择。社会学家视性快感与生殖目的的分离为“最具革命意义”的两个分离之一,对“生殖秩序”的反叛和“伟大的拒绝”,也是现代性观念的重要标志,所以,“精液”所昭示的对“快乐原则”和“生殖原则”的取弃,不仅反映了关于“性”的价值判断的差异,更与个体的自觉、自主、自由息息相关。
真正的“人”的诞生,在王小波的笔下,是一个长于个体人生甚至长于群体历史的漫长而艰难的过程,随时面临着胎死腹中和夭折的危险。王小波在《三十而立》的结尾有一段十分精彩深刻的比喻,大街上的“滚滚人流”使王二突发奇想——“眼前这世界真是一个授精的场所”,在世界这个巨大无比的“子宫”里,追求“名利”,挣一块死后塞入直肠的棉花,就是一枚精子或受精卵的短暂生命途程的全部意义。它们被迷惑、受诱惑,走入歧途,手段异化为目的,活力销蚀,终于夭折于生命诞生之前。每个人从母体的子宫到世界这一子宫,无非是生物学意义的精子向社会学意义的精子的转化而已,是“母胎”的转移,始终没有长成一个独立健全的生命的机会,遑论“三十而立”。王二的挣扎、挣脱正是生命诞生时充满痛楚、血污且潜伏着危险、孕育着希望的激动人心的场景再现。他要自己剪断与“母胎”相连的脐带,自己塞好那块棉花,从生到死,“自己料理自己的事,是多么大的幸福!”这才是“三十而立”的真义所在。显然,在王二那里,“生”的艰难甚于“死”的尴尬和恐惧。
从宏观的角度而言,挣脱“历史的脐带”是更为艰巨的任务。在《万寿寺》中,王小波形象地将最高统治者发威后萎靡的生殖器喻为“历史的脐带”,治乱循环的历史以及置身于两极震荡、颠簸中的百姓,类似于柔弱被动的女性,无不受专制强权这一“母胎”及其“脐带”的掌控和拖曳,而斩断那条极为柔韧致密的“脐带”必然要倚赖新生儿的自我觉醒、求生欲望和求生能力。《三十而立》中早产儿王二的艰辛存活展示了生物学意义上生命的强旺和顽韧,而王小波小说的主人公们都喻示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生命永不放弃的自我拯救。
六、逆转传统的死后世界的想象
与忍受酷刑的“活死人”式的“生”相反,王小波在其早期作品《绿毛水怪》中虚构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死后”世界。它借助了阴阳两隔的恋人彼此思念、召唤、走近的情节模式,但并非重复《倩女离魂》和《牡丹亭》之类经出生入死、起死回生而终得圆满的爱情喜剧。
陈辉对妖妖(杨素瑶)刻骨铭心的思恋归根结底是对曾经共同拥有的“思维的乐趣”和“生活的乐趣”的无尽怀想,那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深刻契合,是“情之所寄”、“魂之所衷”的幸福所在。作者的用意和用力处不止于此,妖妖“有一次在海边游泳,游到深海就没回来”,这种非正常死亡与其说是一次事故,无如说是以死亡为手段对生命意义的探求,它是生命的敞开而非终结。
与人世间无序、无奈的漂泊、分离相比,“死”并没有成为使二人永相睽隔的“锁”,反而是打开奇趣美丽新世界的“钥匙”。王小波由之展开的“水怪”世界,如同一面镜子,映出了陈辉和妖妖的学校和插队生活的枯燥乏味、被动单调,也是王二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人生的显影。它奇瑰多姿、辽阔无比,充满了探索的乐趣:“海里世界大得很呢。它有无数的高山峻岭,平原大川,辽阔得不可想象!还有太平洋的珊瑚礁,真是一座重重叠叠的宝石山!我可以告诉你,海是一个美妙的地方,一切都笼罩着一层蓝色的宝石光!我们可以像飞快的鱼雷一样穿过鱼群,像你早上穿过一群蝴蝶一样。傍晚的时候我们就乘风飞起,看看月光照临的环形湖。我们也常常深入陆地,美国的五大淡水湖我们去过,刚果河,亚马逊河我们差一点游到了源头。半夜时分,我们飞到威尼斯的铅房顶上。我们看见过海底喷发的火山,地中海神秘的废墟。海底有无数的沉船是我们的宝库……”[9](33)这里用了一连串惊叹号,作者和笔下人物的感叹和赞叹溢于言表。
海底是一个没有“区隔”和“栅栏”的自由世界,是一个可供畅游和高飞的无限空间,“水怪”们的体力和智力得以充分培育和施展。他们有设在山洞的实验室,有“相当规模”的工业和城市,有岩洞音乐厅,“在海底,象征派艺术正在流行”……这个充满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世界,灵动、轻逸、飞扬,速度奇快、动感十足,敞开了无限可能,孕育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妖妖化为水怪,投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境界,正是脱其“形”得其“神”,以“死”喻“生”,“死”而重“生”,化解了“母胎”式人生不能承受之“重”,流溢着“纵浪大化”的自得、畅快和甘美。这种生死转换的写法貌似科幻小说、童话和神话,然而小说主人公于短暂的阴阳相通之后的永相睽隔揭示了“死后”之超脱无非“生者”的南柯一梦,解构了前者的玄妙和浪漫。王小波的目的既非证实亦非证伪,他意在说明“死”是“生”的正向延伸(妖妖变“水怪”合情合理、势所必然)和反向虚构(“水怪”世界和人间的不同),陈辉的生不如死并非仅为爱情,更因爱情和生命所寄托的物质和人文环境只能臆造却无法移植。跨越生死的是“人”的写法和活法的巨大差异。
余英时先生有一篇题为《中国古代死后世界观的演变》的文章,讨论的是“在佛教传到中国以前,中国人关于死后的世界究竟持有什么样的观念?”这一“非常有趣同时又十分困难的问题”。当然,他是从历史典籍出发梳理这一演变并力图说明演变的原因的,此处拿来与妖妖的死后世界作比,似乎有以大套小、异质相较、极不合榫之嫌,但“一个民族原始的死后世界观往往反映了它的文化特色,并且对它的个别成员以后的思想和行为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并非浮泛显豁的事实),作一番比较也是非常有趣而必要的。
这里的比较主要以文学作品所折射出的观念为考察对象。中国的文学作品对死后世界的虚构自然受到当时主流观念和作者个人所持观念、所欲宣扬的观念的决定性影响,对于死后灵肉、魂魄等的路向、归属、分流,有宗教信仰者自然尊奉教义所述,如佛教、基督教等都有明确谛示,无宗教信仰者则不脱历史形成的“共识”的框限,“共识”是相对而言,不同的阶层对之有不尽相同的想象,且非毫无变化,因此情况很是复杂。根据余英时的考察,“‘仙’的观念从《庄子·逍遥游》、《楚辞·远游》到司马相如《大人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都指一种‘绝世离俗’的生活”,因此,死后成仙即从“此世”过渡到“彼世”,但是,“自从秦皇、汉武求仙以来,‘出世型’的‘仙’便逐渐为一种‘入世型’的观念所取代,因为这些帝王贵族们一方面企求不死,而另一方面又不肯舍弃人世的享受”。[10](9)借“出世”成仙永葆“在世”的一切实惠,这种现世特权藉想象在死后的延续,导致天上世界成为“神仙的世界”,魂与魄两分——“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魂”显然比“魄”更受珍视,于是有“上达天廷(泰山)”和“下赴黄泉(蒿里)”两个景象和待遇截然不同的死后世界,这与宗教上“天堂”“地狱”的死后世界两分法很相似。
正统文学作品延续对当权者歌功颂德的传统,顺应其心念所系,将他们死后的生活想象为“长生”和“极乐”的终极幸福模式。一般人物根据道德考量和“果报”思想被安置在“飞升”和“堕落”的两个空间,是对其在人间行善的“补偿”和作恶的“惩罚”。在民间文学中,则有许多下层小人物死后遂愿(包括有情人终成眷属、升官发财、名节完满、恩怨得报等十分“现实”的愿望)的浪漫叙事,这是一种强烈的无以泄导只能发抒为梦幻式想象的心理代偿形式。
这些粗略归纳的死后世界观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生死两个世界之间的联系不但没有剪断,反而印证和加强了此世超稳定的秩序建构和文化结构,所不同者,只是人间的等级变化为死后的神仙和鬼怪符号,具体填补符号者以拔高和贬低的方法、补偿和惩罚的机制实现了人间地位角色的永久固化和翻转。因此,“死”是连接阴阳两界的中介和桥梁而非将之隔断的沟壑,死后和方生是具有同样的世界观和组织方式的一个世界。20世纪勃兴的新文学则据科学唯物世界观,否定死后世界之存在,完全可以绕开“死”的界限径直进入类似“桃花源”或“理想国”的乌托邦叙事。“死”是一种反抗和斗争的终极造型,肉体消隐而精神永存,抛开痛苦而永葆欢乐,摆脱人间炼狱而驻留自由王国,呈现一种神圣高蹈的凝固状态。
王小波写到了很多“死”的场景及其漫长、曲折、残酷、滑稽的过程,但死后世界的想象唯此一次。他塑造了很多“活死人”的形象,而只借妖妖的水怪世界写出了“死人活”的非人间却更人性化的景观。作者没有把“绿毛水怪”安排进神仙的天堂或鬼魂的地狱,而是有别于天与地的大海,并称他们为“绿种人”。他们的死后地位和生活方式与惩罚、补偿无关,海底世界不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人间万象的复制,他们的神奇能力不是为了助其实现报恩和报仇的生前夙愿,而是实现更大神奇——完美自我——的手段,亦不同于与生俱来的神仙的法术和鬼怪的招术,而拥有不断自我拓展、自求变化的可能,所以,作者特别写到“绿种人”的实验室,而不去突出某种类似神仙符咒或法器自具非凡神力的高科技产品。海底的时空是无限敞开的,它不是人间世经过权力过滤、筛选和道德审判后的最终收束,而是另一种人生、别一重洞天,是潜藏着无限可能的未完成状态以及供其穷尽可能的生存环境。这里强调的是艺术和美、奇趣和智慧,尤其是对这些理想生活元素的自由追求。
这个死后世界是王小波在很多小说中描绘的“无智”、“无趣”、“无性(爱)”现实的反面叙事,虽出于文笔尚显稚嫩的早年,但已标示出其理想的高度和与众不同的个性及文学气质。
综上所述,王小波的小说在叙事比重和分布上貌似重“死”轻“生”,实际上,无论现实中的生不如死,还是死后世界的舒展自由,其叙事重心皆围绕着并落实在个体生命和生存的焦点上,个体存在的自主性和合法性是王小波所认同的“生”与“立”的基本标志和真正意义。王小波的全部生死叙事都证明了此种寓意上的“生”之匮乏和“立”之艰难,“向死而生”则成为主体建构的哲学支点和文学叙事的重要维度。
[1] 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M].三联书店,1995.
[2] 王小波.黄金时代[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 李银河.福柯与性——解读《性史》[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4] 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5] [美]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6] 王小波.青铜时代[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7] [美]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 王小波.白银时代[M].花城出版社,1997.
[9] 王小波.黑铁时代[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0]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To Death:The Death Narrative of Wang Xiaobo’Fiction
Zhang Chuanping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e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Hebei,Shijiazhuang 050051,China)
“Death Narrative”of Wang Xiaobo’novel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main part construction.He showed the landscape of death and the death penalty,the tanglement between the desire for love and death,the deep description of death,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world after death,etc.Thus he established the death narrative based on the main part construction.“To Death”became an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supporting point of his novels.
Wang Xiaobo;death narrative;to death;the main part construction;the desire for love and death
I206.7
A
1673-0429(2011)06-0005-08
收稿日期:2011-09-29
张川平(1970—),女,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本文是2011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重点课题“文艺精品创作生产机制研究”(编号: 201102033)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