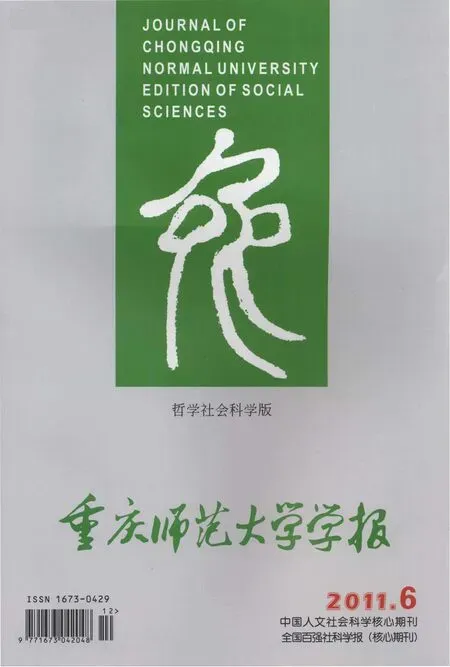再论1930年代“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
欧孟宏
(湖南理工学院 文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6)
再论1930年代“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
欧孟宏
(湖南理工学院 文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6)
1933—1935年,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软”、“硬”电影之争。这次论争在左翼电影批评家与软性电影论者之间展开,涉及到电影艺术的本质、内容与形式、艺术性与倾向性、批评的基准等问题,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双方政治立场、文学与艺术观念以及电影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场论争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左翼电影理论与批评、软性电影理论与批评、左翼文艺理论及新感觉派的文艺观都提供了有力的参照和依据。
“软”、“硬”电影之争;软性电影观;电影理论与批评
1933—1935年,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一场引人注目的电影之争,这次论争主要是在左翼电影批评家罗浮(夏衍)、唐纳、尘无、鲁思等人与强调电影的艺术形式和娱乐功能的刘呐鸥、黄嘉谟、穆时英、江兼霞等人之间展开的。它是左翼文艺家与“自由人”、“第三种人”之间的论争在电影领域里的延伸。这场电影论争最初是因为刘呐鸥在其创办的《现代电影》杂志上发表《中国电影描写的深度问题》、《关于作者的态度》等文章之后而引发的。而“软性电影论”的正式提出,是稍后黄嘉谟在《现代电影》上发表的《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一文。他在文中认为“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事实上,尽管刘呐鸥、黄嘉谟、穆时英、江兼霞等人都攻击过左翼电影,但他们攻击的程度与所采用的基准皆有所不同,比如刘呐鸥以艺术价值为基准,而黄嘉谟则以娱乐价值为准绳。而在左翼电影批评人士的回击中,上述这些人的观点被冠以“纯艺术论”、“纯粹电影题材论”、“美的观照态度论”和“冰淇淋论”而统称为“软性电影论”。
一、对软性电影观的重新检视
为了更为准确地把握这场所谓的“软”、“硬”电影之争,笔者将这场论争中软性电影论者的主要观点重新进行了一番检视。
早在1932年7月1日至10月8日,刘呐鸥就在《电影周报》第2、3、6、7、8、9、10、15期上发表了《影片艺术论》一文,其主要观点如下:(一)关于电影的本质。刘呐鸥认为:“影片艺术是以表现一切人间的生活形式和内容而诉诸人们的感情为目的,但其描写手段却单用一只开麦拉和一个收音机。”“影戏是动作的艺术,影戏的内容应该盛入动作表现的形式里。”由此可以看出,刘呐鸥将视觉表现视为电影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特质。(二)从上面的电影本质观出发,刘呐鸥认为“织接”是电影艺术的生命。刘呐鸥所说的“织接”不单指具体的剪接工作,还包括整个影片的蒙太奇思维和总体构想。(三)对苏联“电影眼睛”学派和欧洲先锋电影运动从艺术角度加以述评,指出其优点与不足,强调应当正确运用电影特性来创造电影美。(四)文学是电影的一个重要艺术元素。刘呐鸥认为,字幕和文学的叙事方法对于丰富电影的画面内容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他同时也指出电影和文学毕竟是不同的两种艺术,其表现形式和方法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在银幕上一味搬用文学要素,显然是有害的。
从《影片艺术论》一文来看,在苏联蒙太奇学派和欧洲先锋电影的影响下,刘呐鸥对电影的认识主要是从电影所特有的物质手段出发来论述电影的表现手法和形式特征,进而证明电影是一门独特的艺术。这表明刘呐鸥的电影理论从一开始就将电影的艺术性摆在首位,这与西方早期电影理论颇为相似。
在《中国电影描写的深度问题》(载1933年4月6日《现代电影》第1卷第3期)一文中,刘呐鸥开门见山地指出:“在一个艺术作品里,它的‘怎么样地描写着’的问题常常是比它的‘描写着什么’的问题更重要的。”[1](158)他批评国产电影最大的毛病是内容偏重主义,而不把丰富的内容纯用电影的手法描绘出来给人看。刘呐鸥认为影艺是沿着由兴味而艺术、由艺术而技巧的途径而走的,视觉要素的具象化是一部影片形式上的最后决定者。在此文中,刘呐鸥认为暴露片当然可以做,因为它是题材中的又一方面,但他反对那些技巧不完熟、描写不够的暴露片,将其视为畸形儿。在《论取材——我们需要纯粹电影作者》、《关于作者的态度》、《电影节奏简论》、《开麦拉机构——位置角度机能论》(分别载于《现代电影》第4期、第5期、第6期、第7期)等文章中,刘呐鸥进一步强调一切作者艺术家一定要以“美的观照态度”“处理材料,整理事实而完成他的创作”。在《电影的形式美的探求》(载《万象》第1期)中,刘呐鸥更是明白无误地指出:“在一般艺术上形式,即表现方法,却比主题,即内容更重要。”“一部影片的艺术上成功与否,却与意识形态少有关系。”
概括起来讲,刘呐鸥的基本观点就是将技巧的运用与形式的创造视为电影创作的根本,他认为发展国产电影的关键,不在于主题内容的改造和革新,而在于形式技巧的完善和提高。
黄嘉谟在《电影之色素与毒素》(载1933年10月1日《现代电影》第1卷第5期)一文中批评国产电影现状时说:“好好的银幕,无端给这么多主义盘踞着,大家互相占取宣传的方地,把那些单纯的为求肉体娱乐精神慰安的无辜观众,像填鸭一般地,当他们张开口望着银幕时,便出人不意的把‘主义’灌输下去。”他要求抛弃一切含有宣传作用的素料,重新恢复第八艺术的纯真的表现,让每个人用他的技巧自由地去发展。
在《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载1933年12月1日《现代电影》第1卷第6期)一文中,黄嘉谟首先就明确指出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它本来是软片制成的。接下来,他批评中国电影却由软片变成了硬片,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左倾意识在作怪。黄嘉谟还认为革命口号题材的影片因为其干燥而生硬的说教使得观众进电影院的兴趣大减。黄嘉谟进而提出:“电影是软片,所以应该是软性的。”
在《软性电影与说教电影》(载1934年6月28日7月2—4日《晨报》“每日电影”)一文中,黄嘉谟认为说教派主张应在电影里散布主义的宣传,这无论如何是断送国产影片的一种方法。他还认为,如果抹杀电影应有的娱乐性,便会失去观众,完全失去电影的效用。在批判左翼电影理论之后,黄嘉谟指出中国影业惟有走上纯影艺而接触到现实生活的“正路”,才有开始繁荣的一日。
从黄嘉谟的这几篇文章来看,他尽管也与刘呐鸥一样坚持“纯影艺”的艺术主张,但他更侧重于强调电影的娱乐价值。
江兼霞在《关于影评人》(载1934年12月20日《现代演剧》第1期)一文中认为,电影如果离开了电影艺术,纵使能达到教育的使命,那也不过是枯涩的教材、拙劣的幻灯影片而已。以此作为依据,他说:“影片制造,电影批评,必须先从它的艺术的成就、技术问题入手,内容是其次的。”[2]
1935年,穆时英针对左翼影评人提出的电影批评的基准问题发表了《电影批评底基础问题》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穆时英批判了鲁思的庸俗社会学电影本质观以及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机械论。穆时英认为,要解决电影批评的基础问题,首先必须明确艺术的一般本质和电影的特性。为此,他指出:“艺术是人格对于客观存在的现实底情绪的认识,把这认识表现并传达出来,以求引起其他人格对于同一的客观存在的现实获得同一的情绪认识底手段。”“电影借助胶片、演员、摄影师、导演及脚本所共同构成的画面以表现作者的情绪。”接下来,穆时英探讨了电影作品的内容、倾向性与形式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它们是三位一体的统一物,互相决定,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在上述基础上,穆时英进而指出电影作品的倾向性与艺术性、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四者之间也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艺术价值并不是电影作品的全部价值。最后,穆时英才提出了电影作品的评价基准应该为:电影作品是具有二重价值的,产生于它的倾向性的社会价值和艺术性的艺术价值。影评人不能机械地拿它的社会价值,也不能单纯地拿它的艺术价值来做评价基准,而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看,才能决定其评价。[3]
从《电影批评底基础问题》这篇文章来看,穆时英并不是刘呐鸥和江兼霞那样的艺术至上主义者,他是从情感方面来揭示艺术的本质进而触及到电影的特性的。他对左翼电影理论的电影艺术本质论、内容与形式统一的一元论并没有全盘否定,而只是揭示左翼影评人在电影理论方面所犯的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唯物论错误。事实上这对于纠正左翼电影理论的某些偏颇是非常有益的。但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文化环境下,穆时英的这一很有见地的文章并没有引起左翼电影理论人士的深刻反省,反而使得左翼影评人士与他之间的论战进一步升级。先是有鲁思还击穆时英的长达万余言的《论电影批评底基准问题》,之后有尘无的《论穆时英的电影批评底基础》以及史枚(唐纳)的《答客问——关于电影批评的基准问题及其他》等文章,均对穆时英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为了应对左翼影评人的责难,穆时英又写下了一篇长达4万字的理论文章《电影艺术防御战——斥掮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招牌者》,该文从1935年8月11日至9月10日在上海《晨报》连载。从这篇文章来看,由于穆时英对康德、尼采、叔本华等西方哲学家以及马克思、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等人的哲学观和文艺思想都有所涉猎,因此他不仅能够指出左翼影评人在哲学观和文艺思想上的庸俗社会学与机械唯物论的缺陷,也能为自己的观点找到理论依据。穆时英在这篇长文中批判和论述了九个问题,其观点大致如下:(1)伪现实主义的本体。穆时英认为,左翼影评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历史行程一致论、艺术反映客观现实论、客观反映的正确程度决定艺术价值论都是伪现实主义,因为他们只强调了辩证唯物论里边的机械论倾向,只抓住了“存在决定思维”这个原则,而忽略了其余重要的、详细的规定。(2)思维与存在。穆时英认为,一切思维导源于存在,这是存在决定思维这个公式的第一义。他批判左翼影评人只知机械地套用“存在决定思维”这一名言,而没有真正理解它。(3)主观与客观中间的距离。穆时英认为,在思维中存在着的现实与在客观中存在着的现实是不能不有着若干距离的差异的,现实认识是一个无限的过程。(4)文化的意义。穆时英认为左翼电影论者只知道解释艺术和一般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基础,而完全忽略了文化的积极的方面。(5)艺术的本质。穆时英认为,就一般意义来看,艺术是反映主观的工具,而不是表现现实的工具。(6)艺术的思想与情绪。穆时英认为艺术是人格对于客观存在的情绪的感应,此感应的表现与传达,以求引起其他人格对于同一的客观存在引起同一的情绪感应的手段。(7)艺术的终极的使命。穆时英认为,一切艺术都是生存斗争的反映与鼓吹。(8)内容与形式。穆时英明确表示他并不否定内容决定形式这一定律,他只是批判左翼电影论者曲解了内容决定形式这一定律。穆时英借用安海姆的电影理论论述了电影中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在此,穆时英重申了他在《电影批评底基础问题》一文中确立的电影批评基准。(9)批评底路。穆时英认为电影艺术作品的批评与电影艺术作品的创造同样是理论的实践的最基本的一部分,其重要性绝不在作品创造之下。
对于穆时英的这篇重要理论文章,无论是鲁思后来在《影评忆旧》中回忆“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还是程季华所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对‘软性电影’分子的斗争”这一章节中均未提及,即便到目前为止的诸多关于“软硬之争”的学术论文中,也很少有人提及穆时英的这篇文章。其实,穆时英的《电影批评底基础问题》、《电影艺术防御战——斥掮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招牌者》这两篇文章对于我们理解“软硬之争”的性质与双方的理论缺陷有着重要意义。如果说刘呐鸥、黄嘉谟、江兼霞等艺术至上主义者在电影本质观和批评观上与左翼电影理论发生根本对立的话,穆时英的电影理论则更多的是对左翼电影理论的一些偏颇加以矫正。事实求是的说,尽管穆时英的电影理论也存在缺陷,但他以其深厚的哲学根底和文学艺术修为作为基础,对电影的认识比左翼影评人显然更为深刻。
二、“软”、“硬”电影之争的几个焦点问题辨析
从现有文献来看,“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双方争论的几个焦点问题如下。
1.电影艺术的本质
对艺术本质的认识历来是艺术理论中的一个最基本最关键的问题。而电影既带有文化产品的商业性,同时又是一门艺术,因此不论是左翼影评人士还是软性电影论者,均无法绕开电影艺术的本质这一核心问题。正因为这样,电影艺术的本质问题首先成为了他们双方论战的焦点。在《清算软性电影论》一文中,唐纳充分认识到了电影首先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具有商业性,同时它也是一种艺术。唐纳接下来谈到了艺术的本质。他说:“艺术是社会的现象。社会的基础物质的经济结构,经济——阶级——阶级心理——艺术,这就是艺术的一元论的概念。”[4]尘无也认为,艺术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它是借着形象而思维的。[5]同样地,鲁思对电影之本质的认识也没有跳出上述两者的窠臼。他说:“影艺是社会现象的一种,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即社会人类的意识形态的反映;更本质地说,它是某一种方式,反映客观存在的现实。”[6]在《论电影批评底基准问题》一文中,鲁思又对艺术的本质作出了如下概括:“艺术是由直接的存在底形象反映客观现实,它绝不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直接的现象)上,这是不可能的。它必得阐明事物底规律性与必然性,由个别的现象来说明普遍的现象,由部分的东西来解释整个的东西,这是艺术的特质和任务。”[7]事实上,鲁思对影艺本质的认识与他对艺术本质的认识并无什么不同。总的说来,左翼影评人是在艺术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上来认识电影的本质的。
软性论者的电影本质观中,刘呐鸥是从电影艺术的特性来理解电影的本质的。他认为:第一,动作是电影艺术成立的第一要素,富于暗示性,最能使它的意义给人明白;第二,电影是科学(光化学、工学)和艺术结婚的混血儿。[8]黄嘉谟则将娱乐性视为电影的本质,他直言不讳地说:“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而穆时英是从情感方面来探讨艺术的本质的,他说:“艺术是人格对于客观存在的现实底情绪的认识,把这认识表现并传达出来,以求引起其他人格对于同一的客观存在的现实获得同一的情绪认识底手段。”“这样的艺术底本质,当然也是电影作品底本质;它和别种艺术底不同,只是工具的不同,文学作品借文字,绘画借颜料,雕刻借石膏,音乐借音符和乐器,电影则借胶片、演员、摄影师、导演及脚本所共同构成的画面以表现作者的情绪。”[9]比较起来,软性论者中的刘呐鸥、穆时英等人的电影本质观显然比左翼影评人更有说服力,因为他们的电影本质观更能反映出电影艺术的某些重要特性。而左翼影评人尽管能够准确地揭示出电影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但将之作为电影的本质则显得机械而形而上学。更为欠缺的是,他们将艺术的本质与电影的本质混为一谈,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2.内容与形式
刘呐鸥在《中国电影描写的深度问题》中指责国产电影最大的毛病是“内容偏重主义”:“内容重,描写过浅,于是形式便全部被压倒了。全体现出catalogue(目录)式,好像只许翻翻目录,给你想象他内容的丰富,而不把丰富的内容纯用电影的手法描绘出来给人看”,“可是在技巧未完熟之前的内容过多症却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他是头重体轻的畸形儿”。江兼霞则认为影片制造、电影批评,必须先从它的艺术的成就、技术问题入手,内容是其次的。他指责中国电影每一张新片开映,总有“意识正确”的影评人在检查它的成绩:内容是否空虚,意识是否模糊等等。黄嘉谟批评那些革命口号题材的影片表面上看来都是革命性的,前进的,奋斗的,耸听而又夸大的,但其内质却空虚和贫血,勉强而浅薄。相比之下,穆时英对左翼影评人的内容与形式统一的一元论并未加以全盘否定,而只是批判他们在这一问题上所犯的简单机械唯物论错误。
为了反击软性电影论者的批评,左翼影评人异口同声地坚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一元论。唐纳在《清算软性电影论》一文中指出:“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只在理论的探讨的方便上才被分割,实际上这是不可分离的。”但唐纳同时申明他绝不反对新内容要求新形式的创造。然而,他片面而武断地认为:“软性论者所谓形式的创造,绝不是和新内容适合的形式。从他们的根本反对新内容,更可以知道他们所谓创造形式,实际上就是使观众不去积极支持新生电影而已。”事实上,软性论者并没有简单地全盘否定新内容,即便是特别推崇形式美感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刘呐鸥,也认为暴露片当然可以做,因为它是题材中的又一方面,他只是反对那些技巧不完熟、描写不够的暴露片,将其视为畸形儿。至于唐纳认为软性论者所谓创造形式是为了使观众不去积极支持新生电影就更是毫无根据的猜测了。罗浮(夏衍)在《“告诉你吧”——所谓软性电影的正体》一文中认为,在艺术史上,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始终是内容占优位性的。他说:“史上不知道有多少的作家,在形式上极不完整,极端粗犷,有时甚至于文字的通顺都不能做到,可是只因为在他们的心灵有了强烈的内容,而博得了不朽的声誉。”尘无在《清算刘呐鸥的理论》一文中说:“‘形式是内容决定的’!怎样的内容一定会要怎样的形式来表现;怎样的形式是只合表现怎样的内容。”鲁思在《驳斥江兼霞的〈关于影评人〉》一文中说:“形式与内容构成不可分的统一,对立的统一;形式是内容的范畴,内容是决定形式的。”当然,他同时也承认当时的新的电影批评也有着缺点,就是影评人把内容的检讨看得太重,比较地忽略了电影的技巧。因此,鲁思说:“新的电影批评,不该忽略那些欧美电影的技巧,因为新生的电影是要继承这已发展了的优秀的技巧,而更加彻底地把新的内容统一起来。”[6]
左翼影评人坚持电影的内容与形式的一元论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界长久以来一直坚持内容决定形式,内容与形式应该相互统一在一起的观点。这种观点的来源主要是受到了苏俄的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列夫派”、“岗位派”以及日本藏原惟人新写实主义等左翼文艺理论的影响。
不容否认,软性电影论者在对待电影的内容与形式方面的确存在着拔高形式的意义而贬低内容作用的倾向,尤其是刘呐鸥的所谓“美的观照”、“视觉要素的具象化”等理论更是完全离开内容而孤立地谈形式。事实上,软性电影论者的形式主义倾向也有其特定的中外文艺思潮背景。比如刘呐鸥、穆时英是当时上海新感觉派的主将,他们深受日本新感觉派和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想的影响。日本新感觉派作家池谷信三郎说:“艺术上最重要的首先是形式,其次是感想,再次是思想。”[10](92)川端康成曾说:“没有新表现,就没有新文艺。”[10](92)在这些文艺观的影响下,刘呐鸥和穆时英重视电影艺术的形式美乃是一种必然。而与此同时,欧洲大陆的先锋电影运动以及爱因汉姆等人的电影理论对刘呐鸥等人艺术至上的电影观的形成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刘呐鸥、黄嘉谟等人创办的《现代电影》本身就是以介绍中外电影的知识动态和理论为宗旨,对世界各主要电影大国的创作情况都比较了解。因此,软性电影论者重视电影的艺术形式可以说是紧跟了世界电影发展的大趋势,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问题在于,软性电影论者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国难当头和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时刻,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软性电影论者这种忽视对社会现实的揭露而重在追求艺术形式的唯美主义倾向显得不合时宜。尤其是黄嘉谟等人对电影娱乐功能的大力鼓吹明显地有悖于时代精神。这必然会引起左翼影评人士的不满和愤慨,因此,双方的论战将不可避免。
3.艺术性与倾向性
左翼影评人对作品内容的高度重视使他们必然将作品的倾向性摆在首位,而艺术性则为其次;加上当时的左翼电影理论界人士将电影视为一种宣传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工具,因此,左翼影评人特别强调电影的阶级性,重视作家的世界观。唐纳认为,根本没有不带倾向性的艺术家,根本没有纯客观的“美的观照态度”,每个艺术家都有派别。[11]尘无认为,世界上没有没有主观的客观作品,艺术价值和政治价值是辨证统一的。[5]鲁思亦认为,“艺术性”与“倾向性”两者根本就不应该割裂开来。[6]当然,话也说回来,左翼电影批评尽管以电影的意识形态批评为重点,但也并未完全忽视电影的艺术技巧批评。
左翼影评人士对作品倾向性的强调遭到了软性电影论者不同程度的批判。黄嘉谟指责中国电影界“主义学说,样样搜罗。放着纯正的艺术不理,而去采用什么主义,什么化,什么派”[12]。他在《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一文中认为,目前中国影片之所以由软片变成硬片完全是左倾的“意识论”在作怪。[13]黄嘉谟并不否认“电影也是最普遍的教育和宣传的利器”,但他同时也说:“但并不能说每部影片都是教育和宣传的利器。都要负‘说教’‘填鸭’的责任。”“至于反帝反封建,当然是一般影界从业员的热切愿望,但是我们主张应该量力而为。电影从业员所做的反帝反封建的步骤,决不能比政治力和社会运动力更加进步。”[14]江兼霞则非常明确地说:“要使中国电影进入与外片抗争的地位,必须丢开了所谓‘意识’的圈套,而在编剧、导演、表演上,竭力去作电影之艺术上的各方面的研究,然后才可以走入正轨。同时,影评人假如是真心的效忠于中国电影的话,也该着重影片之艺术的批判,而不必只是空谈意识。”[15]相比之下,穆时英在作品的艺术性和倾向性之间的关系上论述得更为具体也更为深刻(见前文所述)。
从双方的观点来看,左翼影评对作品倾向性的强调对于促使当时的中国电影从武侠神怪片与家庭伦理片的狭小圈子里摆脱出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批所谓“现实的题材”与“前进的意识”的反帝反封建影片出现在银幕上,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电影的走向。但左翼影评人这种过于注重“意识”而忽视“技巧”的倾向使得他们常常先入为主地以阶级观念或民族意识来作为衡量一部影片价值高低的首要标准,遮蔽了一些思想意识不左倾而艺术价值较高的电影作品。更为严重的是,为了迎合左翼影评人的“意识”要求,不少影片出现了在银幕上“闹意识”的情况。它们要么人为地制造阶级对立情节,要么在银幕上喊空洞的革命口号,要么在影片结尾加一个光明的尾巴,从而影响了作品内容的合理与完整,艺术性当然也就不同程度地打了折扣。其实,即便是左翼影评人,他们对于“意识”的理解也各有千秋,其中大部分人在谈“意识”时显得空泛而充满说教意味,并不能正确指导电影创作,当然也很难真正使观众受到启示。
在广大农村出现灾荒与破产、城市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小市民生活贫困、民族危机日益紧迫等社会现实面前,软性论者却在电影的倾向性与艺术性之间更重视后者,这使他们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一些左翼影评人说他们“是和败北主义、亲敌主义相一致的”,“是文化侵略的清道夫”。事实上,在对待艺术性与倾向性的问题上,除了黄嘉谟和江兼霞态度偏激地全盘否定国产影片的左倾意识而主张电影的娱乐性与艺术性之外,刘呐鸥和穆时英并未否定作品的倾向性。穆时英的小说集《南北集》就带有明显的普罗文学倾向,而刘呐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对城市中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予以了揭露和批判,对无产阶级新生力量进行了暗示。他们在电影上之所以更加强调艺术性,是因为他们是以艺术家的立场来看待电影的。如果说刘呐鸥的电影理论完全是探讨电影的艺术形式而忽略其倾向性的话,穆时英则以深厚的哲学和文艺理论为基础,详细探讨了电影作品的内容、倾向性与形式三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他说:“内容既然是和客观现实对立并适应的,通过了人类意识底情绪认识的主观现实,它自始就不得不包含倾向性。”“倾向性是作品内容必然地包含了的元素,然而倾向性却不是内容本身。”“形式愈能表现内容,愈能加强倾向性,作品底组织机能便愈发展,它底艺术性便愈丰富,它底艺术价值便愈高。”[9]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穆时英完全承认一切艺术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倾向性,这与左翼电影理论并无分歧,他所批判的是那种只片面追求影片内容的思想倾向性而不讲究影片的艺术形式创造的意识形态电影批评,将其称为“伪现实主义”。
4.批评的基准问题
关于批评的基准问题,软性论者谈得比较少。江兼霞认为:“影片制造,电影批评,必须先从它的艺术的成就、技术问题入手,内容是其次的。”“影评人如果是真心的效忠于中国电影的话,也该着重于影片之艺术的批判,而不必只是空谈意识。”[15]穆时英则在《电影批评底基础问题》一文中专门谈到了“电影作品底评价基准”这一问题。穆时英认为:“电影作品是具有二重价值的,产生于它底倾向性的社会价值和产生于它底艺术性的艺术价值。影评人不能机械地拿它底社会价值,也不能单纯地拿它底艺术价值来做它底评价基准。而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看,才能决定其评价。”[3]从江兼霞和穆时英的观点来看,他们对于电影批评的基准显然有些差异。江兼霞认为电影批评应以艺术与技巧为重点,而穆时英认为电影批评应该立足于挖掘作品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两者不可偏废。由此观之,穆时英的电影批评基准更为合理。
与软性论者相比,左翼影评人对电影批评的基准尽管论述得比较多,但立场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唐纳在《清算软性电影论》一文中说:“科学的电影批评应该是看作品的是不是表现客观社会的真实。”“作品是不是表现客观现实的真实,是和作家的世界观分不开的。”[4]这样一来,唐纳很自然地就把意识形态批评作为了电影批评的基准。罗浮(夏衍)在《“告诉你吧”——所谓软性电影的正体》中指出文化——艺术批评者的批评基准应该是“‘作品是否在进步的立场反映着社会的真实’,而决不在作品的外貌是否华奢与完整”[16]。尘无在《清算刘呐鸥的理论》一文中指出:“一个作品的艺术价值的判定,是在他反映现实的客观的真实性的程度,而所谓真实性,就是这一个社会中的主导的必然的内在。”[5]鲁思在《论电影批评底基准问题》一文中也明确说道:“影艺作品的价值,在于这作品反映客观现实,正确到了怎样的程度,才是决定影艺作品底唯一的客观价值。所以电影批评底基准问题的原则,是电影艺术地表现社会的真实。”[4]从夏衍、尘无、鲁思等人对电影批评基准的论述来看,他们与唐纳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以意识形态作为电影批评的主要基准,有的人甚至认为作品艺术价值的高低也是由它反映客观现实的程度决定的。
三、对“软”、“硬”电影之争的批判与反思
“软”、“硬”电影的这场论争,是由于双方在政治立场、文学与艺术观念以及电影观念等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左翼影评人很多都是左联作家,有的人还是中共党员,他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来看待国产电影的,自然要求电影作为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因此,他们将作品的倾向性和教育性作为衡量一部作品价值高低的标准。同时,像唐纳、鲁思、王尘无等左翼影评人士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主要是以从苏联和日本借鉴过来的左翼文艺理论作为依据来展开电影批评的,他们自身缺乏深厚的艺术素养,因而在电影批评中不免出现重思想性而轻艺术性的弊病。
而软性电影论者大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上层社会人士,他们对现实社会的看法显然不可能与左翼人士一致。而像他们中的刘呐鸥和穆时英,是当时海派中一个重要文学流派——新感觉派的主将,二人在描绘上海都市景观上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因此,软性论者的政治立场和艺术观念决定了他们的电影观显然会以艺术性作为基点。
本来,双方的众多差异导致他们的电影观念产生分歧是很正常的,如果双方能够以宽容的态度容纳对方,就不致于在论争中出现断章取义、故意曲解甚至于加以人身攻击的状况。问题在于,左翼影评人采用宗派主义的方式,试图以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夺取电影批评的话语领导权,使电影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目标服务。因此,他们势必难以容忍软性电影论者在理论观点上对自己加以非难和指责。而软性论者作为现代上海大众文化的代言人,他们一直是将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品和娱乐工具来看待的,很多国产电影的左倾观念和电影评论界的重意识而轻艺术的主流使得他们不得不起来表示不满。于是,双方借助一些报刊杂志在电影话语权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左翼以工农大众的代言人自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为武器,试图将国产电影的创作方向和批评标准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软性论者的电影主张与上海现代大都会的商业消费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对于电影的艺术性或者娱乐性的强调,完全是为了追求个体的生命自由。在当时的上海,文化消费的主体毕竟还是以现代新市民阶层为主,小资产阶级、商人和作为社会中间阶层的市民职员群体(包括律师、工程师、会计师、教师、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构成了电影消费的主体。这些人需要在下班之后进电影院松弛自己紧张的神经。因而,软性电影理论的出现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社会基础。但是,历史的错位,主要是一个时代性问题。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软性论者主张电影躲进艺术的象牙之塔,或者借助电影来获得快感而置民族危机与社会矛盾于不顾的论调,显然有悖于时代的要求,他们既与国民政府当局倡导的新生活教育运动的精神相违背,又与激进的左翼革命思想背道而驰,因而最终只能处于话语的边缘,失去了他们本来应有的位置。
就意义来看,不论这场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的最终结果如何,软性电影理论对左翼电影批评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偏颇与缺陷进行了有力的匡正和补救,他们的电影理论与批评更接近了电影的本质。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特定的左倾政治环境和左翼影评人士的急功近利,软性论者的这些颇有价值的观点并没有被左翼影评人士所接受。而左翼影评人士通过这场电影论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左翼电影批评存在的合法性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但不容置疑的是,左翼影评人士在一些重大的艺术(当然包括电影在内)理论问题上存在着机械化、简单化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左翼影评人士在与软性论者论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宗派主义和上纲上线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的不良倾向,给建国后的电影批评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意识形态的独白性原则”(即“一元论的原则”)具有如下弊端:它强化等级制,企图压制一切非权威力量。它扼杀创造潜力、窒息蓬勃的生机,它导致单一性、片面性、简单化、僵化。它是培育教条主义的温床。[17](482)
总的看来,这次软硬电影之争不仅使中国电影界对于电影的一些重大问题有了非常明确的认识,而且双方争论的问题已经超越了电影的范畴而扩展到了艺术领域,甚至于包括哲学的一般性认识问题。双方在论战中发挥得非常出色,精彩论述层出不穷,不仅使自身的电影理论素养得到稳步提高,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电影理论的整体水平,形成了中国电影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一句话,这场长达三年的电影论争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左翼电影理论与批评、软性电影理论与批评、左翼文艺理论及新感觉派的文艺观都提供了有力的参照和依据。
[1] 丁亚平.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C].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2] 江兼霞.关于影评人[J].现代演剧,第1期(1934年12月20日).
[3] 穆时英.电影批评底基础问题[N].晨报·每日电影,1935年2月7日—3月3日.
[4] 唐纳.清算软性电影论[N].晨报·每日电影,1934年6月15日—27日.
[5] 尘无.清算刘呐鸥的理论[N].晨报·每日电影,1934年8月21日.
[6] 鲁思.驳斥江兼霞的《关于影评人》[J].现代演剧,第1期(1934年12月20日).
[7] 鲁思.论电影批评底基准问题[N].民报·影谭,1935年3月1日—9日.
[8] 刘呐鸥.中国电影描写的深度问题[J].现代电影,第1卷第3期(1933年4月6日).
[9] 穆时英.电影批评底基础问题[N].晨报·每日电影,1935年2月7日—3月3日.
[10] 黄献文.对三十年代“软性电影论争”的重新检视[J].电影艺术,2002,(3).
[11] 唐纳.清算软性电影论[N].晨报·每日电影,1934年6月15日—27日。
[12] 嘉谟.电影之色素与毒素[J].现代电影,第1卷第5期(1933年10月1日).
[13] 黄嘉谟.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J].现代电影,第1卷第6期(1933年12月1日).
[14] 嘉谟.软性电影与说教电影[N].晨报·每日电影,1934年6月28日,7月2—4日.
[15] 江兼霞.关于影评人[J].现代演剧,第1期(1934年12月20日).
[16] 罗浮.“告诉你吧”——所谓软性电影的正体[N].大晚报·火炬,1934年6月21日.
[17]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The Dispute Between“Soft Film”and“Hard Film”in the 1930s
Ou Menghong
(College of Arts,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nan,Yueyang414006,China)
in the 1930s,there was a noticeable dispute between“soft”and“hard”film in the filmdom.
This dispute was between“the Left”film critics and the“soft film”critics,touched the nature of film arts,content and form,artistry and tendentiousness,and the criterion of criticism,etc.This dispute offered powerful reference for us to totally understand“the Left”films’theory and criticism,“soft film”theory and criticism,“the Left”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and the new sensation concept.
the dispute between“soft film”and“hard film”;the views of“soft film”;theory and criticism of films
J9
A
1673-0429(2011)06-0013-08
2011-10-20
欧孟宏(1976—),男,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戏剧影视文学。
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932—1937年中国左翼电影研究”(项目批准号: 10YJC76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