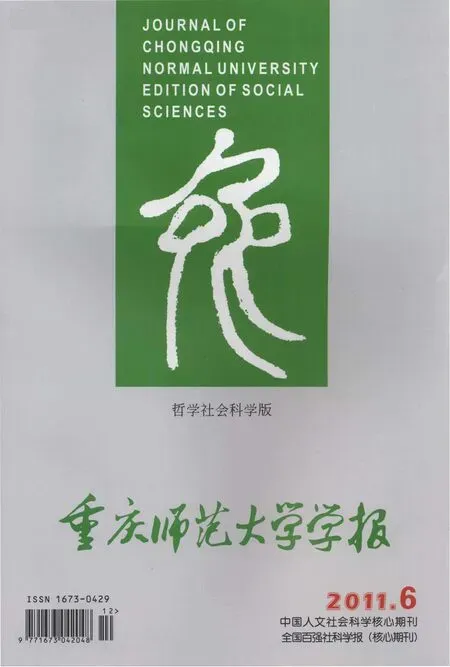《新华日报》的文艺专刊《星期文艺》
王学振
(重庆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重庆 400047)
《新华日报》的文艺专刊《星期文艺》
王学振
(重庆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重庆 400047)
《星期文艺》是《新华日报》创办初期设立的第一个文艺专刊,由胡风编辑,因稿源缺乏,问世不久就停刊了。《星期文艺》注重评论,它存续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经初步形成了《新华日报》文艺副刊注重战斗性、批判性的特色。由于胡风在文坛的重要影响以及“七月派”作家的有力支撑,《星期文艺》也得以刊载了一批生活实感与战斗激情紧密融合的优秀创作,形成了抗战初期文艺园地的一道靓丽风景。
《新华日报》;文艺专刊;《星期文艺》;胡风
《新华日报》十分重视文艺,除了在综合性副刊《团结》、《新华副刊》刊载大量文艺作品、文艺理论与批评文章,关注文坛动向外,还曾经先后出版《星期文艺》、《文艺之页》、《戏剧研究》、《时代音乐》、《木刻阵线》等文艺专刊。虽然《星期文艺》存续的时间不长,但它毕竟是《新华日报》的第一个文艺专刊,并且是在抗战初期文艺报刊纷纷停刊的情况下,由新华日报社聘请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胡风亲自编辑的,因此无论是就研究《新华日报》本身和以胡风为首领的“七月派”还是就认识抗战初期的文艺状况而言,《星期文艺》都是有其一定的价值的。
一
《星期文艺》是《新华日报》创办初期设立的第一个文艺专刊,由胡风编辑,因稿源缺乏,问世不久就停刊了。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一张大型日报。为了扩大影响,《新华日报》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力求丰富多样的,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创办于汉口的当日,其副刊《团结》就问世了(所谓“《团结》创办于1938年1月18日”[1](1)的说法是不确切的)。刊载于第一期的《开场白》对《团结》作出了这样的定位:“促进团结,拥护抗战是它的主要目的,下面几点便是它的具体内容:一、报告并讨论救亡工作的经验;二、介绍抗战中的实际知识;三、批判各种错误言论,揭发汉奸托匪破坏团结的阴谋;四、回答读者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此外还要选抄革命导师,爱国领袖的嘉言警语;也刊载些文艺作品,随笔杂感。长短杂出,庄谐俱备。”[2]可见《团结》是一种“采纳各色各样的文章而成”[2]的综合性副刊,文艺在其中所占的份额并不是特别大。为了“能够有一点关于培养情绪,提高意志的食粮,能够注意一下关于培养情绪,提高意志的工作”,以形象的思维“补助论理(理论)的思维底不足或枯燥”,[3]新华日报社决定加强副刊中的文艺成分,在刊行《团结》的同时,出版一种文艺专刊。这种文艺专刊每逢星期天出版,所以命名为《星期文艺》。
虽然《星期文艺》自始至终都署名为“星期文艺社编”,实际上却是由胡风一人编辑的。王德宽、蔡清富、马蹄疾、熊飞宇等学者都认为《星期文艺》是由胡风主编的,却又无一例外地没有说明理由,比如马蹄疾的《胡风传》附录二《胡风著、译、编书目》就是这样简单记载的:“1938年1月,应华岗之请,担任刚在武汉创刊的《新华日报》副刊《星期文艺》主编。”[4](326)对于这种看法,本文并无大的异议,只是想补充几条证据,以消除读者对这种看法依据何在的疑惑。首先是胡风的回忆和日记。《星期文艺》创办初期,担任总编辑的是刚刚从山东国民党监狱出狱来到武汉的华岗(华西园)。胡风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求学时曾加入共青团,华岗是该时期胡风在共青团组织的领导人,对胡风比较了解。据胡风“抗战回忆录”之一《在武汉》回忆,胡风从上海来到武汉后,华岗曾经约请他为《新华日报》编辑《星期文艺》。[5]胡风日记对此也多有记载。1939年1月3日:“……到新华日报馆。西园说是副刊每周出文艺材料一次,要我担任。”1938年1月7日:“……下午过江找西园。还是每周得出一次文艺专刊。”1938年1月9日:“……出饭馆后同乃超到《新华日报》,与西园商量副刊事,大概是等适夷来负责,我每周编一天文艺。”1938年1月14日:“……下午过江付《星期文艺》的稿子,知道适夷已来,等他不着,约在明天见。”1938年1月15日:“……过江到报馆,付齐《星期文艺》稿。与适夷、西园谈甚久。”[6]其次是丁玲的两封信。丁玲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时,三个与其未曾谋面的女同志征予、寒曦、沸沁曾经通过《七月》杂志转给她一封信。1938年1月15日,丁玲在山西省洪洞县万安镇给三人写了复信。次日,丁玲又致信胡风:“我并不是不想写一点报告之类的东西给你,天理良心,来看过我的人就会原谅我的。过几天能设法抽出一点时间,也许可以写一篇关于我们最危险的一夜,几乎全团消灭的事(按:后来写成《冀村之夜》),但这预约也不知哪天得实现。……寄上这篇通讯稿(按:指复征子、寒曦、沸沁信),你看看能使用否,或者介绍到别的地方去。”后来丁玲致胡风的这封信以《从临汾寄到武汉》为题,发表在1938年2月1日的《七月》第8期上;丁玲复征子、寒曦、沸沁的信则以《答三个未见面的女同志》为题,发表在1938年2月6日《新华日报·星期文艺》第3期上。[7](135)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胡风与《星期文艺》的紧密联系。其三是《星期文艺》的作者群。《星期文艺》的作者,主要有茅盾、艾青、丁玲、适夷、冯乃超、罗荪、东平、柏山、曹白、奚如、李辉英、慧琳、马耳、罗苡、黎嘉、符真、黄明等人。这些作者中,除罗苡、黎嘉、符真几人生平不可考外,大多与胡风有着一定的关系:其中茅盾、丁玲、楼适夷、冯乃超等人是胡风“左联”时期的战友;丘东平、彭柏山、曹白等人是“七月派”的中坚;艾青与胡风的关系也较为密切,两人的艺术观念比较接近,胡风曾发表《吹芦笛的诗人》高度评价艾青,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向太阳》等诗歌名篇都是在胡风主编的《七月》问世的,正因为此,有的学者将艾青归入七月诗派[8](5),有的学者虽然没有明确将艾青视为七月诗派成员,却也认为七月诗派是在胡风的理论和艾青的创作共同影响下形成的[9](321)。可以想象,如果不是由胡风来编辑,《星期文艺》是不可能拥有同时包括艾青、丘东平、彭柏山、曹白等人在内的这样一支作者队伍的。
《星期文艺》自1938年1月16日创刊,至1938年2月20日终刊,总共只刊行了五期(按照新华日报社每逢星期日出版一期文艺专刊的规划,1938年1月23日应该推出《星期文艺》第二期,但实际上是迟至一周后才刊出;胡风回忆说总共只刊行了四期[5],当属记忆之误)。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星期文艺》的停刊呢?从《星期文艺》第二期就未能按时出版的情况看来,应该是稿源存在问题。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稿源问题的产生既是当时的大环境造成的,也与《新华日报》的具体经营状况等有关。首先,《星期文艺》创办时,全面抗战开始不久,时局十分动荡,一般作家虽有以身报国的热情,却缺乏对战争的深刻体验和对生活的深思熟虑,也缺乏必要的物质保障和安定的写作环境,因此当时问世的大多是一些比较浮躁的急就章,真正的优秀之作是很少见的。其次,《新华日报》创办之初,经营状况还不是十分理想,报纸发行量不是很大而免费赠阅的很多,广告少而且大多不收费,这样报社的经费运行必然比较困难。这一点也影响到《星期文艺》的生存。1938年1月30日《星期文艺》第二期的一则征稿启事中有这样一条:“来稿发表后,如作者声明需要报酬,当酌送薄酬。”[10]由此看来《星期文艺》虽然没有根本废除稿费制度,但至少有部分作品是不付稿酬的,进一步推测,即便是支付稿酬,绝对也不会很优厚。这恐怕也是《星期文艺》稿源问题加剧最后导致停刊的一个原因。
二
《星期文艺》存续的时间不长,却以其很有分量的文艺评论,初步形成了《新华日报》文艺副刊注重战斗性、批判性的特色。从这一点来讲,《星期文艺》虽然停刊了,其精神和特色却被《新华日报》其后的文艺副刊继承和延续下来。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充当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喉舌。因此即使是其副刊,也必然带有一定的战斗性和批判性,文艺性、娱乐性不是它的主要追求。按照总编辑华岗的设想,《星期文艺》应该发挥对文艺方向的引领作用,因此它不是发表一般性的文艺作品,而是要“注重文艺评论,特别是批评文艺上的不良倾向”[5]。胡风在受命之时,并不完全认同《星期文艺》的这种编辑出版方针:“这个用意虽然好(按:指批评文艺上的不良倾向),但做起来有很大困难。抗战刚起,一般作者读者感情激动,很难深思熟虑地写文章。现在当务之急是引导他们用力多写点文章,由编辑慎重地选择发表,现在还很少经得起当作倾向评论的作品,性急地做反而不利于创作的发展。尤其是,在党报上发表这样的文章,会使作者产生顾忌,暂时间对《团结》的方针不利。再一个困难是,还很少人能写出这种不带副作用的评论来。”[5]尽管如此,胡风还是勉力贯彻了报社的这一意图。在《星期文艺》第一期的《致读者》中,胡风写道:“文艺上的具体问题(在这里当然不想展开系统的文艺理论或全面的文艺运动问题),例如应该指明的倾向或应该注释的论点,可以短警地提出意见,应该介绍或警告的文艺作品,也可以短警地提出批判,至于短小的诗歌,报告,速写,通讯等,也未始不能从一个小的视角反映出民族战争大潮里的人生面相来。”[3]由此看来胡风虽然没有计划将《星期文艺》办成一个十足的评论性文艺副刊,却也是将文艺评论放在《星期文艺》的首要位置的。
《星期文艺》每期只有五千多字,却不惜篇幅,先后发表了《作家与生活》、《人体写生的实验》、《关于大众文艺》、《诗人,你们往哪里去?》等文艺评论文章。
冯乃超的《作家与生活》(第二期)鼓励作家正确处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积极投入抗战。文章首先分析了战争对文学的影响,认为一方面“战区的扩大,文艺购买力的减退,印刷成本的高涨”的确造成了文化市场的萎缩,“对于滋生在以国库补助和商业后援基础上的‘纯文学’,给以无情的打击”,另一方面作家如果能够积极投入抗战,从事“适合文艺作家的社会职务”,就可以“更深刻的去认识现实——整个民族抗战期中国民生活的一切相貌”,“这个事实,毫无疑问地丰富我们文艺的题材,加强文艺主题的积极性”,因此“商业的文学关系的衰落,不是中国文艺发展的障碍,相反的,它自身的衰落可以减少中国文艺的发展的障碍”。然后以罗曼·罗兰“成为诗人并不妨碍同时成为一个技术家。我个人相信,所有的作家除了他们的文艺工作以外,有其他的事情与职务,不能仅仅从事于文学。……我认为特殊地成为诗人简直是罪恶”和鲁迅“不仅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的名言勉励作家“改变写作的旧习惯”,真心实意地投入救亡运动中,合理解决“要写作没有生活保障”和“有了生活保障,没有写作时间”的问题。[11]
罗荪的《人体写生的实验》(第三期)从重庆《新民报》关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从警察局妇女救济所雇用健美女性充任模特儿,实验人体写生的一则报道生发开去,批判了脱离抗战的纯艺术倾向。文章用文艺性笔调对念念不忘“高贵的氛围气”的“艺术大师们”进行了辛辣嘲讽:“把镜头透过新闻纸吧:在温暖如春的教室里,我们的艺术大师和他的门弟子,披长着发,胸前装饰着一大朵黑花结,左手拿着颜料盘,右手拿着画笔,在几十双眼睛集中的地方吧,那里就应该是刚刚从妇女救济所里被认为健美合格的女性了,她裸体着,而且要配合这温暖如春的意境,她不应该想起她是怎样来到救济所的,即使是被敌人的枪炮,或别的一些残酷势力送入救济所来。因此,她像一个Venus,笑着,不许有丝毫忧虑地笑着。她,骄傲地被数十枝画笔描摩着,是一个春的姿态吧!我们的艺术大师满意地笑了,他们是存在在‘高贵的氛围气’里面,他们忘掉了怎样从南京到重庆来的。”文章还以中国妇女遭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血迹斑然”警醒广大文艺工作者“用笔,用刀做工具,用广大的真实的世界做模特儿”去进行“更为真实”的“人体写生的实验”。[12]
茅盾的《关于大众文艺》(第四期)从赵景深创作的鼓词《八百好汉死守闸北》的缺陷说起,批评了当时“旧瓶装新酒”的抗战文艺作品普遍存在的问题。茅盾认为民间文艺具有“故事的逐步展开,秩序井然”、“主角和配角的分明,并且以故事系于人物,即以人物为骨而以故事的发展为肉”、“抒情和叙事错综溶合,抒情之中有叙事,叙事之中有抒情”等“基本要素”,正因为具有了这些“基本要素”,民间文艺才能真正深入民间,因此利用旧形式“应该不是活剥了形式过来,而是连它特有的技巧也学习之,变化之,且更精练之,而成为我的技巧”,“应该把民间文艺中最好的体制连血带肉吞下去,经过消化,然后自铸新词”。茅盾指出,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由民间文艺研究专家和演奏专家(艺员)精诚合作,“科学的研究民间文艺,洞见它的构成的要素与技巧的特长”。[13]
黎嘉的《诗人,你们往哪里去?》(第五期)批判了“少壮诗人派”对未来派的仿效。1938年1月,鸥外鸥、柳木下、黄鲁、欧罗巴、胡明树、杨起等诗人在广州创办《诗群众》杂志,发表《少壮诗人宣言》,发起了“学习未来派”的运动(有人认为“中国既没有类似于‘未来主义宣言’的理论主张,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未来主义作家,更没有群体意义上的未来主义创作”[14],是与史实不符的)。宣言宣称“高度发达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主义的社会所创造了而给今日我们的诗人所发掘出来的美的焦点:那是大都会与机械的美了。前者是都会主义,后者是机械主义,但各反映于今日的艺术之中”,注目于“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奏着爵士乐的舞榭,……摩天楼……立体战争……战舰,海上飞机场,坦克车……有声电影,性恐慌……”等所谓“今代的生活”。黎嘉对“少壮诗人”的宣言和《用刷铜膏刷你们的名字》、《囚徒之歌》、《革命的广告员》等代表性诗作进行解读,质疑“今天的中国是不是可能产生未来派,是需要怎样的未来派”,断言“未来派在意大利本是反动的,在俄国却是革命的”,“少壮诗人派所谓的‘学习未来派’,只不过是模仿着未来派的皮毛,而成了‘摩登的形式主义者’。他们并没有玛耶珂夫斯基的对于革命的热情,而只在创造着怪式怪样的东西”。他特别强调:“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着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自卫战争,这战争是伟大的,也是艰苦的。我们全国同胞——连诗人也在内——都应当奋勇参加这战争,尽全力坚持这战争,诗人们的诗篇,也必须是帮助这神圣的战争的。这种帮助抗战的诗篇,必须是坚实的,具体的,朴实的。”“今天,中国的诗人们只有一条路可走,这条路是与全国民众一起的。”[15]
在今天看来,《星期文艺》的这些文艺评论文章,有的比较中肯得体,比如茅盾的《关于大众文艺》对《八百好汉死守闸北》的评价就比较辩证、客观,对抗战初期通俗文艺运动存在问题的揭示也很到位。但也有的文章略显简单、急躁,比如罗荪将中央大学师生用裸体模特进行人体写生实验与日本侵略者奸淫、屠杀中国妇女的兽行相提并论。黎嘉对“少壮诗人派”的批判也有商榷的余地。未来派是19世纪之初发源于意大利的一个艺术流派,标榜反传统,崇拜机械文明,歌颂运动、力量和速度,在艺术形式上多有创新。正如黎嘉所言,未来派在俄国是革命的,学习未来派也并无不可。就思想内容而言,鸥外鸥的《用刷铜膏刷你们的名字》以替租界外国资本家住宅刷门牌的中国工人口吻,痛斥各国资本家是“流氓”、“匪痞”、“恶棍”,是“一群贪婪可憎的苍蝇满伏在中国”,欧罗巴的《囚徒之歌》抒写牢狱的苦闷,表达了对“在我们意象的原野响着角笛了,呼啸着号召我们了”的“红旗的布尔塞维克同志”的想往,黄鲁的《革命的广告员》讴歌“摇响了革命的铜铃,无数的群众跟着,喧闹地暴动地,驱走在地球的街道上”的革命动员者,似乎都是倾向于进步,倾向于革命的。就艺术形式而言,“少壮诗人派”进行了学习未来派的积极尝试,鸥外鸥正是继续了这种尝试,后来才写出了在抗战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那首名篇《被开垦的处女地》。就这两点看来,“少壮诗人派”的创作并不存在大的问题,也许是《少壮诗人宣言》对运动、力量、速度的过分宣扬招致了误解,招致了批判。但是,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看,这些批判又是可以理解的,从总体上讲也有利于抗战文艺的健康发展。在国破家亡之际,文艺的政治化、大众化是必需的,血与火的现实不允许艺术家追求象牙塔里的“纯艺术”,也不允许艺术家去制造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
正如胡风在编辑《星期文艺》之前就意识到的,《星期文艺》注重文艺评论,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其稿源的困难,胡风回忆说,他“找不到评倾向的文章”,“自己也不能轻率地写”,只有建议将《星期文艺》停办了。[5]《星期文艺》虽然持续的时间很短,但它所开创的这种战斗性、批判性传统却在后来得到了继承。时过境迁,制约文艺专刊的稿源问题不复存在,《新华日报》对抗战文艺的引导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
在重点推出文艺评论的同时,《星期文艺》也刊载了一些篇幅短小的文艺创作。这些创作有的也难免战争初期的稚嫩,但由于胡风在文坛的重要影响以及“七月派”作家的有力支撑,《星期文艺》还是发表了不少生活实感与战斗激情融合得比较好的优秀之作,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可以称得上抗战初期文艺园地的一道靓丽风景。
这批优秀之作大多出自“七月派”作家(当然也不完全局限于“七月派”作家)笔下,集中在抒情性的诗歌和纪实性的报告两种文体。
《星期文艺》发表的诗作并不多,只有艾青的《我们要战争——直到我们自由了》(一期)和柏山的《除夕——并致M.》(二期)两首,但这两首都堪称成功之作。艾青的《我们要战争——直到我们自由了》很好地传达了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顽强决心、坚定信念,只看标题就使人产生一种血脉膨张的感觉。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对战争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不是简单地诅咒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而是呼吁中国人民通过这场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去缔造一个全新的中国:“不要悲哀——/让战争带去古老的中国/让炮火轰毁朽腐的中国//让古老的中国/穿上寿衣/让古老的中国/躺进棺材/让古老的中国/埋到地底去//让我们流着眼泪/送去古老的中国/朽腐的中国//送去那/高利贷的/包身工的/学徒的/童养媳的/一切写了卖身契的奴隶的中国//……我们要战争呵——//让我们射击那/闯进我们国土来的盗匪/射击那/枪杀我们/奸淫我们/毁灭我们的日本军队/射击那/日本帝国主义的/无耻的/污秽的皇冠/射击那/带给四万万五千万人以无止境的悲苦的/太阳旗/——侵略的标志//高举我们血染的旗帜/在我们所到的地方/用战争的火焰/轰毁那/束缚我们的枷锁/囚禁我们的牢监/抽打我们的皮鞭/和戮杀我们的敌人//我们要战争呵/——直到我们自由了。”[16]柏山的《除夕——并致M.》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通篇却没有撕心裂肺的空洞号叫,而是选取前后两个除夕的不同场景,通过貌似冷静的对比将侵略者的罪行自然而然地暴露无遗:“在乡下,除夕的晚上:/火炉里燃着通红的柴火,/灶神前点着明亮的油灯,/小孩们穿起花花绿绿的衣裳,/准备迎接新年的财神。/整年忧伤着的母亲,/那时也释下生活的愁苦的重担,/强颜欢笑地对着我说:/‘孩子,祝你明年幸运!’//……到今天,又是一个除夕的晚上:/屋子里,没有通红的柴火,/屋子里,没有明亮的油灯;/但屋外边满布着:飞机、大炮、与敌人。/屋子里,更没有著新衣裳的孩子们,/屋子里,更没有强颜欢笑的母亲,/但有一个她——M君,神色仓惶地跑来,/对我报告了七个朋友的不幸。”诗篇融入了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显得深沉含蓄。比如写诗人自己的苦难历程:“人间的树木,一年一年地冒着风雨长成,/我也和树木一样,自己养育着自己的生命。”再如写M离去后诗人的感情变化:“我的心、如同深深的枯井/欢快与悲愁/在其中,都不能激起一点滴的回声。/她去后!/屋子里,有如古庙一般的冷静,/墙上的画像也满露着一脸的愁纹。/我躺在藤椅上——她刚才躺过的地方,想:/在路上,她是否会发生意外的事情呢?/最后我明白了:这是用不着去计算的啊,/走过她前面的,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17]
报告是“七月派”作家擅长的一种文体,也是胡风在抗战初期大力倡导的。胡风所说的“报告”,包括报告文学、速写、通讯、慰劳记、访问记甚至报告诗、报告据(活报)等等。鉴于战争初期作家难以写出反映战争的鸿篇巨制,胡风特别推崇报告这种文体。在编辑《星期文艺》之前不久的1937年,胡风还曾专门写作了一篇论文《论战争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对报告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阐述。在胡风看来,正是借助于报告这种文学样式,“我们民族底伟大的史诗底序章”,“才没有完全被空间、时间、以及特殊条件所淹没,所埋葬”,“在伟大而苦难的大时代里面,我们的作家在获取着这个战斗的形式”。[18](17-18)《星期文艺》发表的很大一部分创作,包括符真的《大沽口外》、黄明的《打老婆过日子的人》、慧琳的《郭沫若先生访问记》(以上一期)、东平的《两个青年的吵架》、曹白的《魔火下的上海》(以上二期)、丁玲的《答三个未见面的女同志》(三期,丁玲在前引1938年1月16日致胡风信称其为“通讯稿”)、李辉英的《开封的一夜》(五期)都可以归入报告这一文体。这些作品用朴实而真切的笔触,记载了抗战初期方方面面的生活,其中东平以自己和作家陈辛人的生活经历为基础[5],叙写知识分子怎样克服自身思想缺陷走上抗战的正确道路,曹白依据自己的耳闻目睹,揭露了日寇占领上海后犯下的滔天罪行,丁玲述说自己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经历和感受,勉励年轻人克服斗争中的困难,李辉英表现开封在战争中的紧张空气,记录搜捕韩复榘余党的过程,都是当时的不可多得之作,即便是在今天也仍然不失其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
[1] 黄桂花.《新华日报》之《团结》初步研究[D].重庆师范大学,2009.
[2] 开场白[N].新华日报·团结,1938-01-11.
[3] 致读者[N].新华日报·星期文艺,1938-01-16.
[4] 马蹄疾.胡风传[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5] 胡风.在武汉——抗战回忆录之一[J].新文学史料,1985,(2).
[6] 晓风.书信和日记见证了楼适夷和胡风夫妇的深厚友谊[J].新文学史料,2011,(2).
[7]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年谱长编1904—1986(上卷)[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8] 周燕芬.执守·反拨·超越——七月派史论[D].华中师范大学,2002.
[9] 程光炜等.中国现代文学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0] 征稿[N].新华日报·星期文艺,1938-01-30.
[11] 冯乃超.作家与生活[N].新华日报·星期文艺,1938-01-30.
[12] 罗荪.人体写生的实验[N].新华日报·星期文艺,1938-02-06.
[13] 茅盾.关于大众文艺[N].新华日报·星期文艺,1938-02-13.
[14] 李鑫,宋德发.未来主义文学在中国[J].世界文学评论,2006,(2).
[15] 黎嘉.诗人,你们往哪里去?[N].新华日报·星期文艺,1938-02-20.
[16] 艾青.我们要战争——直到我们自由了[N].新华日报·星期文艺,1938-01-16.
[17] 柏山.除夕——并致M.[N].新华日报·星期文艺,1938-01-30.
[18] 胡风.论战争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A].胡风.胡风评论集(中)[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Xinhua Daily’Art Special Issue-Week of Literature and Art
Wang Xuezhe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7,China)
Week of Literature and Art was the first art special issue which was found by the Xinhua Daily in its initial stage.Hufeng was the editor,but because of the shortage of manuscripts,Week of Literature and Art stopped publication soon after its coming out.It paid attention to comment,though it didn’t stay for a long time,it initially formed the features of militancy and criticalness which was emphasized by the Newspaper supplement of Xinhua Daily.Due to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Hufeng in the literary circles and the writers’powerful support of“July Groups”,Week of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ed lots of excellent creative works and formed its unique features in the early days of Sino-Japanese War.
Xinhua Daily;art special issue;Week of Literature and Art;Hufeng
I206.6
A
1673-0429(2011)06-0026-06
收稿日期:2011-10-31
王学振(1969—),男,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副研究员,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批准号:07JC51017);重庆市社科规划一般项目(项目批准号:2010YBRW72);重庆师范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1XWB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