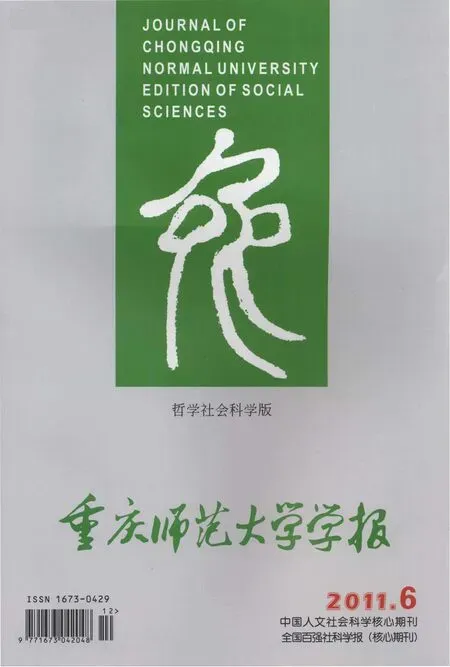自由“实在性”确立的起点:理性存在——重释先验哲学视角下的自由问题
肖福平
(贵州财经学院 外国语学院,贵阳 550004)
自由“实在性”确立的起点:理性存在
——重释先验哲学视角下的自由问题
肖福平
(贵州财经学院 外国语学院,贵阳 550004)
自由理念的“实在性”就康德先验哲学的理性存在而言是自明的,它既不能单独由理念的纯粹形式加以确定,也不能单独由经验对象加以确定;在理性存在的条件下,自由理念的“实在性”地位不仅是先验的,也是实践的,实践的地位带来自由意志决定的自然过程的存在;自由与自然的对立或统一因为回到理性的过程而成为必然,理性存在的事实所确立的既是关于自然世界的实在性,又是关于自由理念的“实在性”。
理性;理念;实在性;实践理性
在先验哲学中,康德必须关注理性地位的确立,只有这样的“确立”才会开启建立自身理论体系的新路;面对传统哲学的“理性”观,他传承了关于“理性”存在的本体论,即“理性”被视为一种超验的、绝对的和原初的能力存在,一种赋予宇宙万物以秩序的“逻各斯”;同时,对于“理性”存在的问题,他另辟新径,并认为理性的存在应该属于自由的世界,应该同自然的对象存在区分开来,或者说,自由世界的“实在性”不能等同于“是什么”的确立,因为它没有体现自身属性的任何谓词;不管传统习惯如何武断地进行判定,其结果都要回到它“不是什么”的路上。因此,理性存在的自由问题一旦在普通理性里被思考,它就会面临要么是虚幻的产物、要么是认知对象的结果。那么,理性的自由“实在性”应如何解决呢?既然理性存在的自由地位无法单独在自由的世界或单独在自然的对象上得以确立,那就必须抛弃先验与经验的对立,必须寻回两者的联系,在决定与被决定者的必然联系上进行思考。
康德认为,理性作为先验的存在,它应该是某种独立于现象的纯粹形式存在。但他又认为,理性应该是实践的理性,它总要将世界的呈现打上自己的烙印,是理性规定了世界。于是,理性的实践特性第一次突破传统哲学的理性观,将理性的原初能力真正地带到自然的世界之中。可以说,自然是关于对象的实在,理性是关于对象本质的实在,即自由的“实在”。当然,不论是自然的实在,还是理性自由的“实在”,都必然奠基于自然与自由的理性的统一。而且,作为理性的自由总是决定的环节,因为只有理性的统一才能具备洞见自由“实在”的契机。在康德将实践的特性赋予理性存在之后,理性存在的自由才取得了自身决定地位的真正实现。只有在这样的过程里,理性才体现为一种绝对的实践能力,自由才体现出一种积极的自我决定性,即“人所具有‘从他自己决定自己’的‘能力’”[1](15),并通过该能力的实现将自由的意志贯彻到现象世界的存在之中。在康德看来,自由意志就是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就是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人的意志,因此,在我们如此小心地探寻自由与自然的统一、探寻自由理念的“实在性”与经验对象的联系时,我们面对了问题的起点:人的存在过程不仅是有条件的和经验的,而且是绝对的和自由的。于是,在思考理性自由的“实在性”问题上,理性存在前提应该作为一个关键,并同人的存在事实联系起来。
一、理性理念的存在状况和自由理念的先验性说明
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自由是一种先验的理念,产生这样的理念在于人类理性的存在要求。也就是说,自由的理念只有在理性存在者那里才是可能的,它是理性追求绝对统摄性原则并回到绝对自发性上的必然结果,因为这样的原则在感性经验中是无法达到的,感性世界所呈现的只是现象琐碎和杂多。作为理性的统摄原则是所有自然条件系列的条件,是涉及自然存在物的绝对整体性问题,但这样的问题在普通理性那里常常被看成可以经验的对象加以判定,从而陷入“二律背反”的困境。在康德的先验哲学里,感性和知性的认识对象分别是现象和概念,或者说,人们在实际的认识活动里只可认识现象的世界,不能认识理念世界的图景或理性的自由之在;而理性作为人类最高的认识能力,它所要求的就是超越现象的条件系列去追求自由理念的所在。康德认为,在人类去认识自由之理念时,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人们不可能从自由理念那里获得什么材料来构建或认识理念本身(在智性的自由世界之内,没有这样的材料可寻),人们所拥有的一切不过是知性能力中的范畴和概念,是已经被给与的现成的自然对象。于是,人们便容易在一种不经意的状态里把理念的对象当成经验的对象来认识。其结果就是使人们将自由的理念当成具有可经验性的知性范畴,把本体论思维中的、凭借纯粹概念的逻辑结果当成可经验的外在对象,将合乎理性要求的主观必然性当成自然的客观必然性,由此产生关于自由理念的“先验幻想”。当然,这里的“幻想”只是基于康德知识对象的称谓。康德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错误就是如此,它混淆了理念形式同现象的划分,将理念世界的存在视为可经验的对象加以认识,从而产生了关于“宇宙理念”的“二律背反”问题。不过,这样的“背反论”除了指明知性概念被误用所产生的“幻想”之外,一点也不代表自由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对立,因为我们一旦清楚了“背反论”的原因,理性与知性能力、本质与现象之分也就可得到清楚的界定,自由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也会由于对非自我之物的认识转向对真实自我的考察而获得解决。于是,作为自然对象在被经验时,决定性环节就回到了人的“此在”,回到了世界之内的产生性中心,即人的中心。
当然,在理念自由与自然对象存在的关系说明中,康德对自由理念的阐明应该同他在《实践理性批判》里作为道德律的自由阐明有所区分。在这里,自由理念的“实在”(actual existence)并不是康德的证明所在,而且,作为一种实在的证明单单在理念的世界里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康德对先验自由的说明在《纯粹理性批判》里“并不是要去证明自由的现实性存在”[2](170)。先验自由自始自终就不曾越出自己的领地,而只是保持了一种理性理念的地位,它总是作为“去经验”的纯粹之在。如果我们要将这样的理念看成一种存在,那也是一种具有绝对性和普遍性的存在,一种“去到根上”[1](14)(going to the root)的、原初性的、绝对自我(absolute self)的存在。它在世界之内,但又无法被确立为任何经验的可能性对象。如果理性的理念存在被看成具有经验意义的自然物的实际存在,先验自由便不再是对应于现象世界的智性对象,或者说,这种自由本身便是某种可经验的对象了。其结果不但造成纯粹理念具有经验的内容,而且使先验自由本身不再具有绝对普遍的必然性。这样的先验对象就在“自然存在”那里被还原为经验的对象,世界之内的存在就会成为具有同一性的物的堆积。但这样的结果在康德那里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此外,在我们讨论自由的积极作用时,除了将自然的因果系列联系到一个无条件的自由原因之外,并没有在认知方面提供关于这种连接的任何有效性,除非我们能够认识到“真实的自我”不仅在于自身,而且在于非真实的现存之物;在认知的尺度上,理念的世界和现象的世界还是截然不同地被区分;在关于理性世界的先验演绎或判断中,其作为主词的纯粹概念变成了理性的理念,其谓词也是没有任何经验直观内容的先验所指,因此,其“实在性”问题的解决在经验或知识对象的意义上是难以实现的。康德说:“我所说的自由在宇宙论的理解中就是自行开始一个状态的能力,所以它的原因性并不是按照自然规律又从属于另外一个按照时间来规定它的原因。”[3](433)同时,“我们关于这个主体就会完全正确地说,它自行开始了它在感官世界中的结果,而不是这个行动在它里面开始了自身。”[3](438)康德把主体所具有的这种特征称之为先验的自由(海德格尔对此有不同的观点,认为自由比人更原始,“人只是自由的可能性”[1](93)存在)。很明显,康德的先验自由是理性主体的行为原因的先验性存在,它同主体的行为的原则规定联系起来,就自然转到了自由与道德律的关系上去了。因此,当我们把康德的先验自由限制在宇宙理念的范围内时,目的是将自由的理念与康德的纯粹理性部分对应起来,并将作为道德律要求的理性同实践的理性对应起来。其实,两个部分的内容都处于康德先验自由理念的关联之中。
不论是对于我们行为的绝对原因本身,还是对于行为结果的现象系列,我们自然意识到了作为最高能力的理性存在及其作用问题。然而,在经验的意义上,我们除了收获理性原则下的结果以外,没有收获任何关于行为或选择原因的先验根据的知识。因此,关于自由理念的先验说明并不是建立在认知对象上来进行的,它可以被描述成对表象产生之最遥远的根基的一种假设性判断,其结果在纯粹思辨理性方面只有作为理念的存在(对于康德的先验哲学思想来说,这当然是一种先验的存在,一种并非因为感性的随意性而产生的“实在性”存在),或者说,“理性至少有与现象相关的原因性”[3](443)。这里的原因性就是自由的原因性,两者是同一的,“如果理性有与现象相关的原因性,那么,理性就是这样的一种能力,结果的经验性的序列的感性条件才首先开始了”[3](448)。
二、自由理念的回归及其“实在性”的可能
依据康德的认识论,我们能够经历一种人类知识获得的历程,获得一种关于先验主体与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认识,并将这样的“获得”推进到其可能性根据上去。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可认知的经验领域,永远不越出那一范围,理性悖论的问题又何从谈起呢?对于理性存在者的本质要求而言,任何这样的限制企图都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永远无法满足理性,它在问题的答案上把我们越带越远,让我们永远在问题的彻底解决上达不到满足。”[4](140)由此看来,理性主体的存在之旅必然要发生在没有路标的本体界,通过脱离自然限制而朝向自由之旅,在“有关自由或自然界的必然性的宇宙学的一切问题上,谁能满足于经验知识呢?”[4](140)但是,我们又不得不面临一个难题:作为实践主体的存在能够突破知识的界限而回归本体界,从而享有自由;这种自由除了纯粹性、精神性和超越性之外,是否还有某种“实在性”或“实存性”呢?也就是说,自由的理念是否可能具体化为知性对象般的存在,并作为实践哲学的经验对象而存在呢?涉及这一问题也就涉及到了认识论的对象与实践论之自由的结合问题。在这一问题上,自由和自然地位的确立及联系从未获得统一的认可,关于这一问题的纷争,是“说不尽”的问题,颇似康德自己所面对的传统的形而上学如何成为科学的情形。从康德知识论的角度看,自由在认识论中是一个达不到的彼岸理念,认识的主体只有在对现象世界的注意和关照过程里,也就是在思考认识外在世界的行为中,才能借助经验对象来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才能通过某种智性直观面见理性存在的自由。当然,我们无法知晓这样的“智性过程”。如果用一个比喻的说法,从认识对象开始的旅程就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离家”,一种由于关注外在对象而遗忘自我的暂时性状态;在前面关于理性的分析里,我们知道,这种“离家”起始于可经验的、具有可直观对象的现象世界,终止于对自我的回归和对理性自由的必然期盼;作为人的自由主体性只有在其自然的主体性退去之后才得以显现,康德的先验理念的存在才由此取得说明的契机。
康德说:“我们的理性,像生了自己真爱的孩子一样,生了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的产生,同世界上任何其他东西一样,不应该看成是偶然,而应该看成是为了重大的目的而明智地组织出来的一个原始萌芽。”[4](140)作为知识层面的形而上学对我们没有意义,但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这一目标和“重大目的”是同一的,它主要体现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建立上,体现在自由、灵魂、上帝等一系列道德理念的设定上。道德理念或道德形而上学的对象不是在现存之物里展开的直观对象,而是内在于理性存在者的必然本质。“假如我们还能够对人的主体有另外一种眼光(但这种眼光当然并没有赋予我们,我们所有的不是它而是理性概念),亦即一种智性的直观,那么我们也许就会最终发觉,就永远只能涉及道德律的东西而言,种种现象的这个完整链条都取决于作为自在之物本身的主体的自发性,关于这个自发性的规定是根本不可能给出任何自然解释的。”[5](136)不管智性直观怎样存在,但就理性理念与人的“此在”过程的必然联系来看,却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当然,理念存在的“实在”发生在本体界,是“作为自在之物本身的主体”的“实在性”。这样的“实在性”之域虽然没有自然因果的连接和应用,但拥有绝对的自发性能力,合乎自由的原因性规律。一旦理性理念因为理性的实践行为而实现其自身的形式规定,并将自由的原因性同道德律联系起来,“离家”的人便在真正意义上拥有了一个道德主体的源头:只有在自由之在的源头,我们才能目睹道德主体本身的意义;同时,自由作为道德主体的源头也第一次为理性理念的“实在性”出路提供了新的路径,将“实在性”与理性存在的实践必然联系了起来。如果自由的理念在人们追求宇宙绝对整体性时还是一种超越的发现,那么,在人们经历了从本体界到现象世界的返回时,“超越的发现”原来就是“自我”的存在必然。“超越的发现”如此深刻地带来对自由理念的意识和拥有,以至于在理性主体内消解自由的任何企图都变得无路可走。从作为道德主体的道德律或自由到具体的道德行为准则和规范,“自由的概念,一旦其实在性通过实践理性的一条无可置疑的规律而被证明了,它现在就构成了纯粹理性的、甚至思辩理性的体系的整个大厦的拱顶石。”[5](136)
可以说,理性世界的自由綻出主要体现在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对“自我”的回归,是人的道德行为里所体现的对理念自由的关顾。在此意义上,自由通过人的意志在实际行动中得到确立。在上文的分析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作为自发性源头的自由,由它的原因性存在自发地导致了自然系列的如此呈现,而且也看到了理念自由对一切系列乃至现象界的行为对象产生影响。康德说:“理性的这些理念现实地证明了它们在作为现象的人的行动方面的原因性,这些行动之所以发生,不是由于它们被经验性的原因所决定……而是它们被理性的根据(即自由)所规定。”[3](444)自由是实践理性的直接现实。
三、理性的实践特性和自由理念的“实在性”转换
在我们借助康德的视角对其先验哲学所涉及的理性、理念和存在的不同品格进行梳理之后,人的“此在”成为主客观二分产生的根本原因,自由与自然的原因性在人的行为里发生作用并统一于理性的存在就会变得确定无疑。
如果我们把现象事件当作物自体,把时空当作物自体的存在形式,那么这种作为物自体的存在便必然处在受条件限制者的因果系列的连接当中,自由就永远没有了立足之地;相反,如果把现象和物自体归属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将经验对象的存在只是作为我们直观条件下的表象的存在,那物自体就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作为现象根据的一种存在,并由现象的“实在”(经验对象如此呈现是基于我们作为主体性的存在)回到其产生根据:自我的“实在”。在确定了这样的不同“实在”之后,我们便有了一种不同于自然原因性的原因性:一种智性的原因性。康德认为,对于这样一种智性原因性的作用,其决定的结果虽然可以在现象系列中存在,但其本身以及其自发作用过程却在我们的经验之外。当然,“经验之外”不能离开理性存在的事实,或者说,不同原因性对于同一结果作用不能缺少理性存在这一“自明”的前提。基于如此的“前提”,经验对象的出现意义就不仅仅是对象存在的标明,更是对智性原因性存在即自由理念之“实在”的标明。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理性存在的“前提”应该成为自由理念“实在性”问题探讨的首要条件,正是在这一前提条件下,“实在性”问题上的实践理性之路、纯粹意志之路以及道德命令的现实化之路才得以可能。康德认为,人作为一种理性的存在必然是一个二元的统一体,它在理性存在的基础之上将两个系列的和谐必然地完成;或者说,人的行动既服从经验的法则又服从自由的法则,人的“此在”与世界的如此实现成为必然。于是,康德在其理论理性里完成了对自由“实在”及其与自然进程之相容性的说明(尽管它在“是什么”的定义上不能言说)。康德认为,关于自由“实在”的证明问题是自己的理论哲学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只有这样,他的实践哲学才可以从自由本身的证明上解脱开来,从而转到实践理性的自由上去。“像这样把自由观念看作是有理性东西依之而行动的基础就足够了,没有必要从理论角度来证明。如若我们不来做这种证明,那么那些约束一个真正自由东西的规律,也就同样适用于只能按照自己对自由观念而行动的东西了。”[6](88)
康德认为,理性存在的实践行为是理性的必然要求,并与一种来自理性理念(自由)的“实在性”规定根据相联系,这种理念“实在”的规定以“应该”的方式来影响感性世界的行为事件,因此,在感性世界的因果规律作用之外,这种理性理念的规定性或来自自由世界的作用在这里应该予以承认。尽管自由的理念在纯粹理性里还是处于一种消极的态势,但它在理性存在的本质要求下必然通过理性存在者的行为体现自身的“实在性”。所以,理性本身的“实在”以及理性存在者的行动事实就意味着先验自由向实践自由的必然转变,并在新的领域确立自由理念规定性的“实在性”地位。
[1] Heidegger,Martin.The Essence of Human Freedom[M].trans.Ted Sadler,London:MPG Books Ltd,2002.
[2] Kant,Immanuel.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M].trans.J.M.D.Meiklejoh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80.
[3]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
[4]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78.
[5]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1998.
[6]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7] Kant,Immanuel.Foundation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M],trans.Lewis White Beck,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Chengcheng Books Ltd.,1999.
The Precondition of Establishing“Reality”of Freedom:the Exist of Reason
Xiao Fupi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iyang550004,China)
In Kantian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the actuality of reason or idea is self-evident,and it can not be determined by the idea itself alone,nor determined by natural object alone.The being of reason is not only transcendental,but practical;the practical reason determines phenomenal objects through the will of freedom,and the process of rational being makes the opposition and the unity between freedom and nature necessary,and it establishes the actuality of both nature and reason.
reason;idea;reality;practical reason
B504
A
1673-0429(2011)06-0032-05
2011-10-04
肖福平(1962—),男,重庆璧山人,贵州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哲学的理性主义、语言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