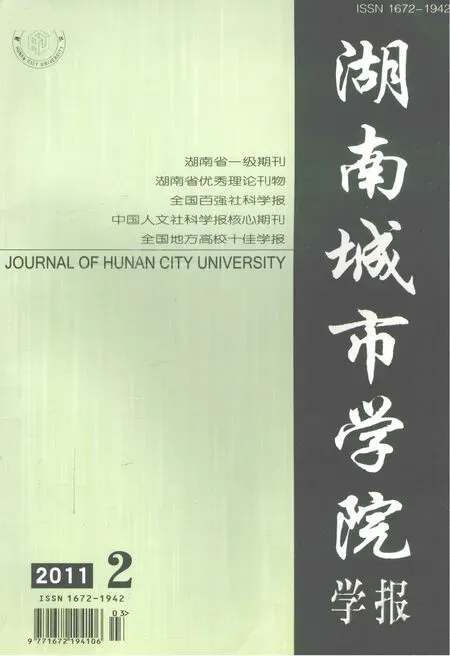李泽厚的本体论批判
张文初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长沙 410081)
李泽厚的本体论批判
张文初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长沙 410081)
近20年来李泽厚思想探索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批判传统的本体论。李泽厚批判的主要是理性本体、欲望本体、圣爱本体、语言本体、“Being本体”。李泽厚的批判是从他自己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出发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坚持以制造和使用工具为基本内容的人类物质实践活动的本体性,以此反对传统本体论的精神本体性;坚持从人的现实生存的完整性上肯定人和人的生命,以此对抗传统本体论对人性的单面认定;坚持人的历史性生存的多样性、流变性、当下性,以此颠覆传统本体的单一性、恒定性、彼岸性。
李泽厚;本体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
一
对理性本体、欲望本体、圣爱本体、语言本体、“Being本体”等历史上多种具有重大影响的本体论观念展开批判是李泽厚近20年思想探索的一个重要方面。理性本体在历史上有中、西两种形式。西方视之为本体的理性主要是认知性的、工具性的。认知理性在哲学上发端于笛卡尔的“我思”、中经启蒙主义的激扬,到康德的纯粹理性达到巅峰。20世纪西方反理性主义思潮盛行,但与此同时,科学理性、分析理性、高科技理性这些属于认知理性、工具理性范畴的理性观念理性思潮仍然具有主宰西方人现实生活的力量。中国历史上视为本体的理性主要是伦理道德型的,其重心是以社会性规范约束个体的心理、行为。“思无邪”,“仁者安人,知者利人”(《论语·里仁》)、“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程颐《遗书》卷24):这里的“思”、“仁”、“道心天理”就是中国传统理性的内容。孔孟的“仁”、“义”奠定了传统中国道德理性的基础。宋明的“理”论、“心”论,现代新儒家如牟宗山等倡导的心体、性体则把道德理性推向了本体论的层面,被视为人性和人生的本体。对于中西两种内容有别的理性本体,李泽厚的总体观点是:承认理性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但反对把理性作为本体。谈到工具理性时,李泽厚说:“工具理性有用处,但是它不是本体”,[1]158“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分析哲学把人变成机器,像机器的部件、齿轮、螺丝钉,人就是robot,这太可怕了”。[1]158在讨论宋明理学和新儒学的道德本体论观念时,李泽厚说:宋明理学和新儒学的“主题是‘心性论’,基本范畴是理、气、心、性、天理人欲、道心人心等”;其优点是“极大地高扬了人的伦理本体”,其缺陷则是使“个人臣伏在内心律令的束缚统制下,忽视了人的自然”。[2]30这种“忽视”同样意味着道德不能作为本体。
欲望本体在历史上有多种表现形式。依李泽厚的观念,中国近代的自然人性论,西方“对肉体及心灵作所谓‘极度体验’(limit experience)的病态追求”,[1]99现代哲学盲目崇拜的反理性情绪、尼采式的毁灭论、海德格尔存在论中蕴含的“原始物质冲力”,[3]88后现代生活的物欲横流等等,都属于或者说都包含了欲望本体的观念。李泽厚清醒地意识到欲望本体的现实泛滥:“随着百年来传统礼教崩溃和传统心理的急剧转换,以及革命道德重建的失败,……性欲和兽性作为生存意志的核心、作为个体存在价值甚至归宿的感受、体验在当代文化中已大有呈露。”[3]123欲望之所以不能成为本体,欲望本体论之所以不能成立,在李泽厚看来,道理很清楚:第一,它不符合人性的实际;第二,它对人来说是一种灾难。所谓“不符合人性的实际”就是说人从来就不是欲望性、动物性的存在者。即使像卫慧小说中描写的“讲究穿着、奢侈度日、疯狂作爱”,极力张扬欲望的后现代青年,也仍然会“以人生理想、生活价值等等肯定着、许诺着和装饰着”自己的“生命和生存,使自己的有限性和主客观时间都具有或可无限延伸的‘内容’和‘意义’”[3]89这就是说,在人和人的生命生活中,总有一些超越欲望的东西在。所谓“是灾难”,就是说如果任凭欲望泛滥、任凭人身上的兽性发作,结果会是个体和群体自身的伤害和毁灭。李泽厚不欣赏尼采,原因就是他认为尼采的强力意志、酒神精神重视的只是人身上的生理性力量,尼采哲学是“毁灭”哲学。李泽厚也强调指出,海德格尔的“原始物质冲力”类似尼采的强力意志,同样可能导致法西斯式的后果。
对圣爱本体的否定在历史上主要是针对以西方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哲学,在当代中国学术语境中则主要是针对以刘小枫为代表的“圣灵叙事”。李泽厚承认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缺少圣爱本体所开启的差异性、独特性、悲剧性、深刻性,但他“不同意”说“西方传统的”“高远、深远一定优越于中国”。李泽厚认为,圣爱不能成为本体,是因为“由于缺少足够的平面展开,即人情世事的温暖支援,人只与上帝有内在关系反而容易陷入绝对隔离和怪异孤独的境地。”[3]124《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针对刘小枫所说的“纯粹地紧紧拽住耶稣基督的手,从这双被现世铁钉钉得伤痕累累的手上,接过生命的充实实质和上帝的爱的无量丰富,……承担起我自身全部人性的歉然情感”,李泽厚以揶揄和冷峻并含的笔调写道:“在或可煽起浓烈感情的华美文辞中,这个‘上帝的爱’‘基督救恩’‘生命的充实实质’和‘全部人性的歉然情感’其实是非常抽象和空洞的”,“纯粹地紧紧拽住耶稣基督的手”的手“恐怕只能是一只黑猩猩的手”。[1]105
20世纪是语言学的世纪。李泽厚重视语言,而且特别重视汉语的文字。他认为:“汉字是世界文化的大奇迹,它以不动的静默,‘象天下之积’,神圣地凝冻、保存、传递从而扩展着生命:‘人活着’的各种经验和准则。”[1]169他承认在这种“保存、扩展人的生命”的意义上,汉字的特征似乎更突出地显证了现代语言哲学“语言说人”的语言本体论观念。但是,李泽厚坚决反对视语言为本体的哲学。他认定:语言不是人的根本,语言不能代替人本身,“21世纪要恢复人的意义和尊严,就应当在理论上批判语言的绝对理念。”[4]119在2008年撰写的《关于“美育代宗教”的杂谈答问》中,李泽厚从人生活动与宗教经验相结合的层面对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之家”的著名论断作了别出心裁的解读。海德格尔的论断通常被理解成语言本体论的经典性说明,认为它的意思就是说人生活于语言之中,语言是人生的本体。李泽厚反对这样的理解。他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的“语言”有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公共语言。“人的语言把人的动作、创造、道路、生活和生存保留起来,传给后代。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或者可以说是存在之家”。[4]206第二个层面是超公共语言的“神”。“满载经验、记忆的历史性的语言,却又常常不能成为个体感情—信仰所追求、依托的对象。人们所追求依托的恰恰是超越这个有限的人类经验、记忆、历史的某种‘永恒’、‘绝对’、‘无限’的‘实在’、‘存在’、‘本体’、‘神’,认为那才是人所居住的归宿和家园,‘语言是存在之家’在这里便是超越公共语言的‘语言’,即神。”[4]206以两个层面的区分为基础,李泽厚认定,两个层面所显示出来的语言重要性或“家园性”均不等于说语言最终是人的家园或人生的本体。第一层面的公共语言因其有保存、传递人类经验的作用看上去如同“家园”,但最终真正作为家园的还是人的活动、道路、创造本身,而不是保存和传递这种活动、创造的语言载体。第二层面的“语言”虽然具有承载个体情感—信仰的作用,但它本身实际上已经不是语言,而是神,是具有神秘性的人类经验或超经验的宇宙神秘。李泽厚把这种宇宙神秘叫作“天言”。在李泽厚的观念中,“天言”的哲学概念性内容是“宇宙自然的物质性协同共在”,不是人格化的上帝、天主及其指令。
对作为本体的Being的批判针对的是海德格尔的哲学,目的在于消化和超越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海德格尔区别Being与存在者,以此构建他的基本本体论,并对现代人的生存作本体论的解读。李泽厚从人类生存本体论的层面解读海德格尔的Being。与断然否定理性、圣爱、欲望、语言的本体性不同,李泽厚并不否定Being相对于人的生存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他说他要做的是用情本体填充海德格尔的Being。这就是说,他并不反对视Being为本体,他要反对的只是海德格尔对Being的生存论解读。在李泽厚看来,海德格尔的Being空洞,没有内容,是一个深渊;因其空洞,Being具有把人引向机械性、动物性的危险。他认为西方学者发现的第三帝国的士兵带着《存在与时间》奔赴战场的事实正好说明了Being的深渊性与危险性。李泽厚认定Being空洞性的基本依据是海德格尔对人的生存所作的“本真本己性”和“非本真非本己性”的区分。“Being通由Dasein而敞开、现出,Dasein是意识到那死的无定的必然而‘烦’、‘畏’。除去了一切‘非本真’‘非本己’(即世俗的,亦即being-in-the-world,活在世上)之后,‘本真本己’与上帝的会面,便成了一个空洞深渊。”[3]87在李泽厚看来,‘非本真’‘非本己’不能除去,人只能生活在‘非本真’‘非本己’之中;要“让‘本真本己’与‘非本真本己’妥协并存,而且还合二为一”,[3]89在“平平凡凡琐琐碎碎的日常生活中”,寻找“道路、真理和生命”,[3]126让“Dasein 和我的有限性”“安息在这情感本体的积淀里”。[3]126
李泽厚对历史上诸种本体的否定关联着他对传统的本体概念本身所作的超越性拯救。李泽厚说:“在海德格尔和德里达之后,去重建某种以‘理’、‘性’或‘心’为本体的形而上学,已相当困难。另一方面,自然人性论导致的则是现代生活的物欲横流。因之唯一可走的,似乎是既执着感性又超越感性的‘情感本体论’的‘后现代’之路”[1]180李泽厚这段话虽是对历史上“诸种本体”的否定,但同时也包含对传统的“本体概念”本身的否定。传统的“本体”指的是最终的实体、最终的可以安置人生和世界的存在者。就生存论的领域而言,传统的本体内含四种特性。第一,可依托性,人可以将自我的生命生存依托于其上。第二,超越性。传统本体的超越至少有两种形式。一是对现象的超越。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物自体都是这样的本体,它们都与现象相对,都否定现象。二是对存在者和非本真生存的超越。海德格尔的Being和本真生存就是此种概念。第三,实体性,本体自身是一实体。第四,恒定与单一。在传统观念看来,本体是不变的一,与多相对,与流变相对。变动不居、纷繁多样的现象不可能是本体,因为它的流变性多样性使它不具备可依托性:人们不可能将自我的生命生存依托于本身变动不居、纷繁多样的东西之上。可以用来作为生命依托的东西自身一定是恒定的、单一而明确的实体。传统的这种本体论观念在现代社会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在自我生存的领域中,人们痛苦地看到,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恒定不变的,一切皆流,什么都会消失,用时下“潮人”情有独钟的网络语言来说,“神马都是浮云”,所谓永恒单一的实体是虚构的神话。由此,在现代社会,保持和重构本体概念就必须放弃“永恒单一的实体”观念。李泽厚说:“所谓‘本体’不是Kant所说与现象界相区别的noumenon,而只是‘本根’、‘根本’、‘最后实在’的意思。”[1]55这就是说,在今日的哲学中,本体的观念可以保留的只有“可依托性”这一层内涵,至于“超越性”、“实体性”、“单一恒定性”等等规定都必须放弃。
二
李泽厚的本体论批判是从他自己的本体论观念出发的。李泽厚的本体论叫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本体论可以是关于宇宙整体的研究,如宇宙本体的建构;也可以是关于社会现象、自然现象某一方面的研究,如所谓社会本体、自然本体。李泽厚的本体论是人类学的。“人类学”一词在李泽厚的本体论哲学中意味着“将哲学本体论人类学化”,即:以对人的关注和研究作为哲学的基本命题。李泽厚自认他的这一思路是康德哲学的延续与发展。《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第六版说:“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曾提出‘我能知道什么’等三大问题,本章前面已讲。晚年,康德在这三问之后,又添加一问,即:‘人是什么?’康德说,‘第一问由形而上学回答,第二问由道德回答,第三问由宗教回答,第四问由人类学回答。归根到底,所有这些都可看做是人类学,因为前三问都与最后一问有关。’”[5]347李泽厚要做的是康德想做而又没来得及做,或者说受其自身哲学体系的限制而不可能做的工作。“所谓关注和研究人”,在李泽厚的思想中可以从否定和肯定两个层面理解。从否定层面说,它指的是不把与人无关的宇宙自然作为哲学的基本主题。李泽厚的哲学关注自然、关注宇宙,但这种关注是在人类学的视野上进行的,是从与人生有关的角度上来展开的,他反对撇开人的宇宙本体论、自然本体论。从肯定层面言,“关注人”指的是把人的整体性存在作为哲学主题。李泽厚认为,从人的整体存在出发,哲学有一个出发点和具体展开的三大问题。一个出发点是:人活着,或者说,“我意识我活着”。三大问题是:人会如何活下去?人生意义何在?人活得怎样?三大问题分别归属于认识论、伦理学、美学三大领域。人类学的出发点和三大问题又包含着人的起源和归宿两个不同维度。这两个维度体现为人的两种形态和两个本体。“起源”属于整体,即人类,关于人类的形态研究形成的本体是工具——实践本体。“归宿”指个体,关于个体的形态研究形成的本体是情本体。李泽厚认同“人群有起源日,个体没有”这样的哲学观念。人是以“类”的形式共同进化成“人”的,不是以“个体”的方式成为“人”的。人在最初只有作为类的意识,没有作为个体的意识。人的个体意识是在很晚的历史阶段出现的。这就是关于人的“起源”的基本观念。人的归宿与起源不同,所谓“归宿就是起源”、“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流行说法不是对人命运的真实描绘。人的归宿是个体的生成。个体意识的不断强化,个体作为不可取代的个体性的存在,是人性发展的走向。人类的起源、人的类意识的形成,一般人性能力的发展,依靠的是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群体性实践。“工具”因此成为“本体”。个体的人生活在“情”中,既生活在心理性的“情感”之中,也生活在现实性的“情况”、“情境”之中。这种生活于情中的观点,就是李泽厚的情本体论。“人生无常,能常在常住在心灵的,正是那可珍惜的真情‘片刻’”,“只有它能证明你曾经真正活过。”[1]191在俗世尘缘、强颜欢笑、忧伤焦虑中,努力把握、流连和留住这生命的存在,“这就是生命的故园情意,同时也就是儒家的‘立命’”。[1]192由此,李泽厚把情作为个体生命的归宿,作为生命的本体。
“人”是历史上所有哲学都不会忽视的主题。李泽厚的人类学重视从人的历史性出发关注和研究人。李泽厚将自己的哲学命名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甚至简化为“历史本体论”。在李泽厚的观念中,“历史”一词甚至比“人类学”更重要。一方面历史是人的历史,谈历史即意味着谈人,历史包含了人;另一方面,人只能是历史性的存在,“历史”是对人的深层次规定。当然,李泽厚的研究是哲学研究,“历史本体论”眼中的历史因此不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李泽厚的历史意识吸收了黑格尔、福柯历史哲学的思想成分。李泽厚说相对于《批判哲学的批判》从马克思回到康德、即从人类生存的总体回到个体和个体心理的思路,他后期哲学重视的是从海德格尔回到黑格尔,即从心理上回到历史、回到关系。“历史”在李泽厚的思想中蕴含两个方面的规定。第一,它首先是指人类现实物质实践的过程。在此一意义上,历史同精神史、心理史有别,同黑格尔的历史不同,而且侧重于指与现在、未来相区别的“过去”。人类的物质实践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活动,其具体内容就是制造和使用工具。人是靠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历史实践而成为人的,个体的人性能力(包括纯粹理性和道德理性)和人性情感都是以制造使用工具为基本内容的历史实践的产物,是在历史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本体”在这一层面上就体现为“工具本体”。以历史为本体,即是以工具为本体。李泽厚著名的“三句教”“历史建理性、经验变先验、心理成本体”因此首先是对工具本体的断定。第二,“历史”指的是具体真实的人类生存活动本身。在此意义上,历史同一般性理论规定有别,同脱离人生真实的想象、信念不同;它包括过去,也包括现在、未来。情本体侧重于从此一维度提出。“历史本体”在“情本体”的层面上意味着人只能生活于具体历史性的生活情感和生活情境之中。三句教中“心理成本体”的“成”一方面是说,具体物质性的工具实践“生成”了人性心理、人性情感,使人的心理情感具有了本体意义;另一方面也是说,因为历史本身即是人生活的真谛所在、归宿所在,因此,人的心理情感和现实活动本身即“成为”了人生的本体。
三
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在多种层面上构成了对包括理性、欲望、圣爱、语言等传统本体的否定。首先,工具本体的物质实践性同理性、圣爱、语言等非物质、非实践的本体对立。西方的纯粹理性,中国的道德理性,发端于神学传统的圣爱,都不是物质实践性的存在,都属于精神、意识的范畴。精神的东西不能成为本体,因为它们本身是衍生物,不是最终的实在。李泽厚虽不认同传统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不承认人头脑中的意识一定来自于客观世界,但李泽厚坚持心脑一元论的观念。心脑一元论“认为任何心理都是脑的产物,包括种种神秘的宗教经验,没有脱离人脑的意识、心灵、灵魂、精神、鬼神以及上帝。”[4]207离开人的大脑,不可能有意识、精神、灵魂。而人的大脑神经是在物质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由此,理性和圣爱都需要在肯定物质实践第一性的前提下来理解、定位,不能把它们作为本体。语言本身具有物质性。但语言的物质性(语音)只是语言的物质外壳,不是语言最核心的东西。语言是符号,其核心是它的意指功能。语言意指功能的形成,一方面依赖人类生活世界的开辟,另一方面依赖人自身语言能力的形成,而“被依赖”的两者都来自于人类的物质性实践。
其次,历史本体论的完整人性观拒绝传统本体对人性的单面性认同。历史本体论以人的整体和个体的统一、感性和理性的统一、自然和必然的统一、责任和幸福的统一等多种矛盾面的一体化来肯定人的生活和生命。在李泽厚看来,传统的本体虽也重视人,但它们对人的肯定都陷入了单面性之中。纯粹理性和道德理性的对立、圣爱和理性和欲望的对立、欲望和理性和圣爱的对立、理性和欲望和圣爱的对立,在各自确认自身合理性的同时,意味着相互间取消对方存在的合理性。正是因为承认竞争的各方就其本身语境而言都是合理的,李泽厚的历史本体论因此强调“不可舍弃”原则。欲望、理性、圣爱都是人生命的内容,都不可缺少。抛弃欲望、抛弃感性生命的圣爱不是人的爱,只能是想象中的神灵的爱。抛弃理性和圣爱的欲望不是人的欲望,只能是动物的欲望。抛弃欲望和圣爱的理性,不管它是认知的、还是道德的,同样也不是人的理性,只能是机器的理性。对于人的生命的完整性的强调,对于人性每一方面都不可缺少的坚持是李泽厚历史本体论的基本特征。
历史本体的多样性、流变性、当下性证伪了传统本体的单一性、恒定性、“彼岸”性。传统的本体以对于单一、恒定、彼岸的确认为目标。传统本体的确立本身就旨在克服当下现象的多样性变化性。前述传统本体的的四特性已对此加以揭示。历史,无论是物质性的实践,还是情感、情况都是具体多样的、不断变化的、当下呈现的。历史的多样性流变性既源于决定历史进程的主体的复杂性,也源于历史活动的开展所依据的历史条件的特殊性,还源于参与历史活动的个体的主体性。历史不是单一个体的事业,而是由许许多多的人们共同演绎的过程。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决定历史的进程。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虽然在推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作用的发挥本身也是由众多参与者决定的。在现代社会,个人权能型、个人魅力型的领袖人物的作用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展开日益减弱,历史的共同参与性、共同决定性极大凸显。历史因此更加具有多样性、流变性。每一个人、每一群体都成长和活动于特定的历史时刻,每一历史事变都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虽然有时候表现出明显的重复性、具有规律性,李泽厚的历史本体论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坚持历史的规律性,但李泽厚的规律性、重复性从来不否定历史条件和历史事变的独特性。一方面,李泽厚认为,不可否认的历史规律只应该在“宏观”的层面上理解,“所谓‘宏观’,是指至少以千百年为单位作计算的人类的时间过程”,[3]26具体而细小的历史事件比如某某政治家的被暗杀等,就不能从“规律性”上解释。另一方面,李泽厚非常重视偶然性。他强调:“不能把总体过程当成是机械决定论的必然,必须极大地注意偶然性、多样的可能性和选择性。”[1]27他说:“人性、情感、偶然,是我所企望的哲学的命运主题,它将诗意地展开于21世纪。”[1]248李泽厚把偶然性看成是个体主体性在历史层面的表现。“个体主体性的凸出,从历史角度看,就是偶然性的增大。”[1]134其具体内容就是“个体的命运愈益由自己而不是由外在的权威、环境、条件、力量、意识……所决定”;同时,“人对自己的现实和未来的焦虑、关心、无把握也愈益增大”,“命运感加重”。[1]135历史当下性对于传统本体“彼岸”性的证伪既意味着取消传统的空间压倒时间的生存观念,也意味着取消传统的或凸显过去、或凸显未来的时间观念。传统的空间压倒时间的生存观同传统的时间观一致。其共同规定是空悬一个与时间的流变性相对的、或存在于时间之外、或存在于未来、或存在于过去的彼岸性的世界,认为人生的意义就是去追求那个与当下生存相对立的彼岸世界。现代生存放弃此种彼岸性的追求,坚持生存是一历史性的过程;生存不是未来的某种目标,也不是过去的某个事实,生存就是当下的活动。李泽厚虽然没有直接就历史的当下性展开详尽的论述,但其历史本体论对历史当下性的肯定是明确的。他说:“超越的本体即在此当下的心境中、情爱中,‘生命力’中,也即在爱情、故园情、人际温暖、家的追求中。”[1]242这里的“当下”虽然也与福柯等后现代哲学家高扬的“当下”不同,但它同样是与超时间的空间、超当下的过去或未来相对的,是拥有具体多样性的现实人生本身。而肯定和追求此一当下、具体、多样的现实人生就正是李泽厚建构历史本体论、颠覆传统本体论的哲学目的所在。
[1] 李泽厚. 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5.
[2] 李泽厚. 己卯五说[M].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9.
[3] 李泽厚. 历史本体论[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4] 刘再复. 李泽厚美学概论·附录[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9.
[5] 李泽厚. 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7.
Li Zehou's Critique of Traditional Views of Ontology
ZHANG Wen-ch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Li Zehou's main thought in the past of 20 years is the critique of traditional views of ontology. What Li Zehou criticizes includes reason ontology, desire ontology, worship ontology, language ontology, and Being. Li Zehou submits his critique on his thought of History Ontology of Anthropology, that recognizes human material practice, negates traditional spirit substance; recognizes the totality of human existence, negates one-sided view of humanity; and recognizes diversity, alterity, and immediacy of human existence, negates unity, eternity, and other fields of traditional views of ontology.
Li Zehou; ontology; the history ontology of anthropology
B 016
A
1672–1942(2011)02–0029–06
(责任编校:彭 萍)
2010-12-10
张文初(1954-),男,湖南长沙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西方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