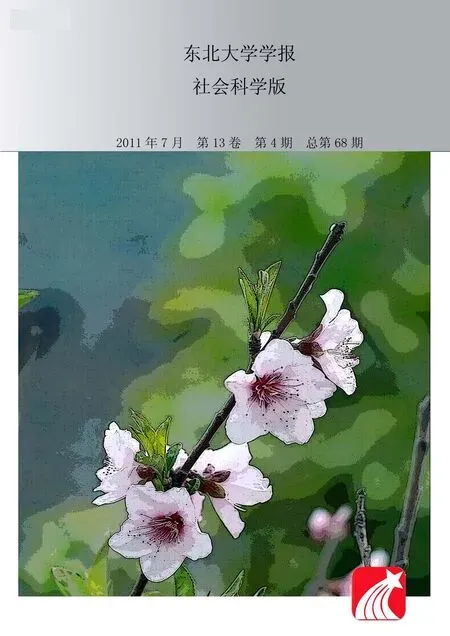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罗沙·科德菲尔德
冯 溢,颜晓川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 110819)
《押沙龙,押沙龙!》[1](Absalom,Absalom!)[2]是美国南方作家福克纳创作的一部文学巨作,许多美国评论家、文学史家都认为这是福克纳作品中最重要,也是最复杂、深奥,最具史诗色彩的一部。福克纳曾对一位朋友说,这是有史以来美国人所写的最好的小说。可见作家对该书的期待。这本小说被称为解释性的小说,体现了福氏多角度叙事手法的最高境界,故事由四位叙事人罗沙小姐、康普生先生、昆丁和施里夫讲述。多重叙事构建出了南方萨德本家族在大约半个世纪的兴衰史。白人穷小子萨德本依靠不名誉的手段起家,在杰斐逊小镇造房娶妻,构筑他的梦想。萨德本在婚外有一个混血儿子邦,邦为了得到父亲承认,接近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亨利,并成为了妹妹朱迪思的未婚夫。亨利为了家族杀死了邦,然后逃走了。小姨罗沙多年后发现了藏身在大宅之中的亨利,导致萨德本的混血女儿克莱蒂放火烧宅,象征着萨德本梦想和旧文化的大宅随之毁灭。表面看来,该书主要涉及到南方由来已久的种族问题。但是,细细推敲琢磨,我们不难发现书中一个重要主题,即南方女性对南方父权制的挑战。Deborah Clarke提出,在福克纳最强有力的作品《押沙龙,押沙龙!》中,福克纳直面展现了南方社会中女性对白人父权制的挑战[3]。南方淑女罗沙小姐就是这样一位女性人物的代表。她性情乖戾,言行颠倒,时而是个孱弱无力的老处女,时而又像个强壮有力的男人,是个多重矛盾体。事实上,罗沙言行的颠倒和性格的古怪一方面是女性在父权制度下被压迫、被扭曲的写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一位身处社会弱势群体的女性对父权制社会的反抗和挑战。
兴起于20世纪初的女性主义对建立在理性和功利传统之上的科学观进行了不断地批判、反思和构想,不同流派的女性主义通过不同的方法、视角和框架结构解释了女性之所以受压迫的原因,并提供了消灭这一社会现象的种种解决办法[4]。女性主义理论为我们解析南方父权社会下的女性罗沙小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本文主要基于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Luce Irugaray的女性主义理论,通过对罗沙小姐的叙事、爱情观、婚姻观和下乡之举的分析,探讨罗沙小姐的女性主义意识,解读其颠倒的言行和古怪的性格的真正原因。
一、 母女纽带和颠倒的言说
罗沙小姐的母亲死在产床上,母女的纽带在她出生时就断裂了。丧母事件给罗沙留下了严重的创伤,使她对母亲的死永远不能忘怀。罗沙的父亲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一生中唯一关心的就是他在乡邻间享有的名声,他对女儿没有付出父爱。在等级森严、气氛沉重的父权家庭中,童年时期的罗沙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和父亲的关爱,缺少儿童应有的欢乐和玩伴。罗沙说她“不知什么是爱,甚至父母的爱”[1]139。罗沙自幼由她的姑姑、一个老处女带大,这位姑姑就像她的母亲和父亲一样。姑姑没有教给她什么本领,她只学会在一扇扇封闭的门外偷听大人的事情,并通过大人复杂和愚蠢行为来揣摩种种人类的行为。罗沙表现得早熟,这种早熟体现在对父亲以及父亲所代表的父权制的憎恨,她“对父亲带进这幢房子的任何、一切事物深深地不赞成”[1]53。这种精神禁锢、情感干涸的生活使得罗沙发育不良,矮小单薄,似乎没有经历过青春期就进入了成年期。于是,罗沙渴望着母亲的爱,她总是不自觉地感到自己仿佛还隐藏在母体那原始的寂静里,童年的时光是在母体中度过的,似乎没有出生过。Luce Iruguray认为,母亲与女儿的纽带在父权文化中被割断,所以女性谱系是缺失的。谋杀母亲以维系男性秩序,这是西方文明的基础。女儿必须离开母亲才能进入欲望秩序和父亲法律,……女儿必须忘记童年和母亲[5]。然而,罗沙并没有走进父权社会为女性预设的道路,她与身处的父权社会势不两立。她把自己活着看做是对尘世上男性至上原则的控诉,而且是“可以引申的控诉”[1]52。
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是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她们是“他者”、“客体”,处于被剥削、被支配的地位,永远是沉默的,没有发言权。罗沙小姐却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了昆丁。这说明罗沙不仅打破了女性的沉默,有言说的欲望,而且还要让自己的故事被南方占主导地位的男性知晓,同时希望能够通过昆丁把这个故事带到北方。Luce Irugaray 认为,女性要想获得主体性,就一定要挑战和打破男性话语,而在初始阶段,女性只能通过模仿才能摧毁这种话语机制,这是历史为女性制定的路径。女性对自我角色被男性设定和认定的状况的直接挑战便是须要像(男性)主体一样地言说[6]227。罗沙的叙事是沉默的女性模仿男性话语的模型,显示了女性对白人父权社会男性意识的模仿和挑战。
罗沙所居住的这座南方小镇是一个封闭、传统的父权社会的缩影。在小镇的社会环境里,女性被划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部分”,每个女性只能朝单一的方向发展,即“成为女士、妇人、娘们”。这三种女人是“黄花闺女”、“娼妓”和“黑奴小妮子”的代名词。这种对女性角色的设定使得女性只能在预设好的轨道中扮演她们的社会角色,女性不仅身心受到压抑和禁锢,还沦为男性股掌的玩物,成为父权制的牺牲品。罗沙小姐在叙事中充满了对小镇居民舆论的模仿。小镇居民们想到萨德本时,首先想到的是“冷酷无情”,“是恐惧而不是尊敬”[1]36。萨德本和埃伦的婚礼受到小镇人的唾弃和反对。罗沙在叙事中带着毫不宽恕的心态,反复地数落着萨德本这个恶魔、这个邪恶的化身:“他不是个绅士,……娶埃伦甚至娶上一万个埃伦也无法使他变为绅士”。她认为,萨德本是 “穷凶极恶的无赖和魔鬼”[1]10, 有着“杀人恶魔的脸”和“太黑暗了以致都说不出口”的背景[1]11。此外,罗沙还十分看重南方传统社会的家族荣誉。埃伦和萨德本的婚礼遭到镇上人的公开攻击,婚礼上有人向萨德本扔去了垃圾,这不仅使家族中所有人尊严丢尽,对家族中尚未出嫁的罗沙小姐更是奇耻大辱。后来,萨德本的儿子相互残杀,这又一次加重了科德菲尔德家族的耻辱,让她们全家蒙羞。萨德本给罗沙家族带来了厄运和诅咒,罗沙甚至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她的父亲或是祖父作了孽。南方社会对家族荣誉感的信奉由来已久。Bertram Wyatt-Brown提出,不同种族的南方人保持着一种共有的、存在于现代化之前的对个人和家庭的荣誉观,南北战争前,在南方人的活动和人际关系中,荣誉观以一种惊人的、错综复杂的方式影响着人的行为、态度和价值观[7]。罗沙小姐对南方父权社会意识和传统文化的模仿可见一斑。
此外,罗沙小姐的叙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叙事人的叙事。康普生先生、昆丁和施里夫的叙事中不断地出现“按科德菲尔德小姐的说法”,“照罗沙小姐所说”的话,这是对罗沙叙述的引用和重复。“康普生先生、昆丁和施里夫他们的叙事都表达了白人父权制的文化信仰。”[8]176在某种程度上,这说明了罗沙小姐的叙事的确反映出白人父权制的文化信仰。Minrose Gwin提出,作为叙事人,罗沙说出了南方社会的文化,同时有时候也成为了文化的代表,其原因在于她的叙事是“被压抑的歇斯底里的父权制叙事”,是女性在父权制体系之下发展出来的症候[8]152。难怪当我们读到罗沙的叙事时,会发现其叙事的特点是古怪别扭、怒气冲天、喋喋不休,是自言自语的独白。罗沙对父权制社会意识和文化信仰的模仿,一方面说明了女性没有主体声音,只能模仿男性的文化和意识,处于弱势、沉默的被支配地位;另一方面又说明罗沙打破了女性的沉默,展现了女性对主体社会文化信仰的模仿,这种女性对男性声音的模仿在男权社会中形成了一种“阳物秩序内的颠倒”,一种理性秩序内的“嬉戏的穿越”[6]228。这种“穿越”是女性在男性话语中的穿越,是一种颠倒的话语,是女性在理性社会中制造出的非理性。
二、 紫藤的爱与独身的选择
罗沙代表女性欲望的回归不仅表现在对父权文化意识的模仿上,还体现在她的女性意识和对欲望的表述。她在男性叙事与女性叙事之间的转化是通过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穿越来完成的。
Minrose Gwin提出,罗沙表达了女性的欲望,其叙事中的“紫藤的夏天”标志着其女性欲望的回归,她的叙述贯穿在意识与无意识的空间之中[8]152。小说第五部分主要是罗沙的内心独白,其中很大程度上是意识流描写。罗沙小姐谈到了她的梦和对爱情的渴望,并且把自己的短暂而旺盛的女性情愫隐喻成美国南方生命力旺盛、无处不在的紫藤。“以前有过(他们也不可能告诉你这一点)一个紫藤的夏天。……这春夏属于每个呼吸在尘世的女性。”[1]136罗沙感受到紫藤旺盛蓬勃的生存状态,感叹这样花团锦簇的春夏也应属于她这样身份卑微的淑女。她像一株小病苗,尽管没有青翠的叶子和艳丽的花簇,但她仍然有生存之根和爱的渴望。在这春夏中,罗沙感受到对爱的渴望,编织了美好的梦想。罗沙的少女情怀不仅体现在她对爱的渴望,还体现在她用诗歌歌颂南北战争中的骑兵英雄,还有她对邦的单恋。在连见都没有见过邦的情况下,罗沙就暗恋他,而邦那时已经是朱迪思的未婚夫。在花园里,罗沙尾随着邦和朱迪思这对恋人,走在花园小径上,心中猜想着哪条印痕是邦留下的脚印,想象着这紫藤花和玫瑰曾听到过何等的誓言。这充满灌木、藤蔓和玫瑰花的园子成了罗沙的“避难所”,在这里她陶醉在美好的梦中,虽然这爱情仅仅是单恋,是不可能获得的爱,但是对于一个感情受禁锢的女子却是何等的美好和甜蜜。但是,罗沙在叙事中反复否认着对邦的爱,因为这种爱是一种“母爱”,达到了“爱的顶点”。罗沙说如果她对邦的感情是爱,那么“也是母亲们的爱”[1]142。在父权制社会中,罗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作为母性文化的化身,她对邦的爱只能是以一种母亲对孩子的爱来体现。她在没有见到邦时就爱上他,对朱迪思没产生嫉妒,得知邦要结婚就立刻为朱迪思赶制嫁衣,这些都说明了罗沙对于邦的爱是一种近乎母爱的感情。Irugaray指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性别身份“被删除,而不是被保留”,罗沙对邦的爱表明了在父权社会里,女性情感受到压抑、扭曲,女性的爱情无法正常地体现,两性关系无法自然地发展的问题实质。
罗沙对婚姻的选择也在很大程度上显现了罗沙的女性意识和生存状态。罗沙同意嫁给她的姐夫萨德本,因为她并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这是南方社会为罗沙预设的道路。在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南方“大多数年轻人都已经死去”,“活下来的男人不是太老便是结过婚的或是疲倦了,活得太累不想谈情说爱了”;萨德本是罗沙在这种情况下最佳也是唯一的选择[1]164。从叙事中,我们看到罗沙又一次成为了南方文化的代表,同时也言说了女性悲惨的命运。在萨德本提出侮辱性的试婚请求的那个下午,罗沙感到五雷轰顶,怒不可遏,于是她搬出了萨德本大宅,从此选择了和这个男权社会抗衡,禁锢了自己43年。禁锢自己而选择不婚,成为老处女,这是罗沙对于男权主义者萨德本的控诉,同时也是对南方父权制社会的抗争。在康普生先生看来,罗沙视自己为“一个惩罚工具:倘若不是强大得能与那人(萨德本)抗衡的积极工具,也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象征”[1]53。在父权社会里,淑女们接受严格教育,以期婚嫁后,能够作为“夫君的皇冠”、一个大家族的掌管者、一个显赫家庭的女主人而生活下去[9]3。罗沙选择不婚显然走到了父权社会的反面,无疑老处女的身份在当时是一个消极的象征。在罗沙所处的20世纪里,评价女性的社会地位主要根据她的家庭背景和婚姻关系[9]48。罗沙打破了婚姻的惯例,而选择了独身,这无疑使自己的社会地位更加卑微低下,而且还遭到南方小镇居民的不满和唾弃。美国淑女很大程度上是对英国淑女文化传承的产物。“20世纪前十年,英国淑女呈多种特点:……她们中有的把独身当作保持尊严的标志。”[10]穷困的罗沙无依无靠,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她没有同意未婚夫的请求,却依靠无名氏留在门口的很少的一点食物维持生活,这是一个弱小女子与父权制抗衡的勇气之举。维护尊严的代价是沉重的,于是罗沙被蹂躏得如同鬼魂一样。在坟墓一般的晦暗、阴沉沉的屋子里,43年来百叶窗一直是紧闭的,屋里隐藏了悠悠岁月的全部叹息。罗沙穿着43年来一成不变的一袭黑衣,令人望而生畏,一张模糊不清的脸带着一种无奈和呆呆的怒气。
不仅在外貌上罗沙被扭曲,在性别特点上,罗沙在两性间游移不定,体现出雌雄同体的特点。“双性同体,又为雌雄同体,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一种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特点的人,这种人在古希腊神话和宗教里并不罕见。”[11]罗沙觉得自己“活得不像一个女人、一个少女”,倒更像一个男人,是“雌雄同序的提倡者”[1]139。Rchard Godden指出,罗沙是具有颠覆性的,这样说是因为罗沙游移于男性和女性之间[12]。罗沙表面看起来不定的性别其实是其不定的社会性别的反映。“在英文中,sex指生理性别,gender指社会性别。生理性别指男女在生理上的差别,社会性别指社会对男女的社会角色、行为、道德、自我意识的构建和不同期望。社会性别身份与环境、女性在社会上的位置、阶级和种族有密切关系。”[13]女性主义者认为,社会性别是文化的构建,女性在一种文化强制下变成了一个女人 ,而并非生来就是女人,女性可以根据自己的社会位置主动构建自己的社会性别,并付诸实施。在父权社会中,绝大多数女人选择了顺从女性的性别刻板模式,而罗沙却选择与父权社会抗衡,她有时动作和言语就像男性,这正是她父性社会性别的体现;有时又表现出母性的爱与情怀,但这只能是在无意识或潜意识中才能达成。如果我们认识到,在父权社会的环境中,罗沙无法保持主体的统一性,她在主动地构建自我的社会性别时,时而采取模仿男权主流社会的声音,时而又流露出女性的情愫,她的社会性别无法达到统一而被扭曲、被异化,那么,她的性别身份的不定性就不难理解了。从某种意义上讲,罗沙不仅颠覆了男权社会中的叙事,而且也颠覆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扮演的社会性别身份。
罗沙小姐的下乡之举是其男性性格特点的体现,是女性主义反抗意识付诸行动的高潮。罗沙叙事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要昆丁陪她一起去萨德本大宅看个究竟,因为她直觉地感到有人偷偷地住在那里已有四年。在小说的结尾我们才发现了这个真正的目的。的确,罗沙本可以不再考虑任何与萨德本家族有关的事情而平静安宁地度过她的余生,但是因为邦被亨利枪杀,罗沙久久不能安宁。50年后,凭着女性的直觉和她性格中的倔强、坚持,罗沙鼓起勇气,在昆丁的陪同下,重新回到了萨德本的大宅,并发现了隐匿其中的已病入膏肓的亨利。罗沙凭借直觉采取行动,这是女性特点的体现,而她的下乡之举更大程度上是其男性性别特点的体现。尽管罗沙当时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但是在她瘦小孱弱的身躯里,竟然有着“一种猛烈、无法消解、爆炸性的力量”。她把前来阻止她上楼的克莱蒂一拳打倒在地,那动作“只有男人才会有”。在看到大宅被烧后,罗沙还想冲进大宅,她与副保安官无声地挣扎和格斗[1]357。这些都体现了罗沙的男性社会性别特点。更加重要的是,罗沙的下乡之举导致萨德本大宅被毁,小镇的平静被打破,这是女性在男权制社会中所制造的颠覆性的破坏。萨德本的混血女儿克莱蒂看到载着副保安官、医护人员和罗沙小姐的急救车,以为这就是来押亨利去镇上的黑囚车,因为他曾枪杀了邦。由于不希望亨利被绳之以法,于是克莱蒂便纵火烧毁了大宅。这座象征萨德本梦想和男权主义的大宅像是“怪物似的火绒般干燥的烂空壳”,烟雾“透过挡雨板扭曲的裂隙往外渗透”,“仿佛房子是金属丝纱网编的,里面充满了吼叫”[1]362。在父权制的体系中,罗沙用“父亲法律”打破了父权制社会的平静和安宁,她模仿男性,在父权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体系内部形成了一种颠倒。她一出生就打破了一个父权家庭的平静,又通过下乡打破了父权制南方小镇的平静。施里夫说罗沙“最后拒绝做一个鬼”,这可以理解为罗沙拒绝女性被边缘化、被压抑的社会角色,从禁锢中走出来。而昆丁说此后的小镇“平静永不再来。平静永不再来。永不再来。永不再来”[1]361。到这里,罗沙女性主义意识和其巨大的颠覆性被彰显无遗。在1909年,大宅被烧毁。1910年,罗沙小姐与世长辞。康普生先生在写给儿子昆丁的信中提起了罗沙小姐的葬礼。葬礼那天天气好极了,“虽然很冷,他们为了挖墓穴不得不用铁锹把土刨开”,康普生先生观察到了一个细节,“在较深处的一个土块里我看到有一条红毛毛虫,在土块扔上来时显然还是活的,虽然到下午它又冻僵了”[1]365。或许,这条毛毛虫就是作家福克纳为罗沙死后设计的化身:鲜红的颜色和不畏严寒象征着罗沙的精神,而毛毛虫这一令人不悦的昆虫和被冻僵了的事实是罗沙在父权社会被扭曲和折磨的写照。
三、 结 语
在很大程度上,《押沙龙,押沙龙!》这本小说呈现了深受压迫的女性挑战南方父权社会的主题。罗沙对男性话语和文化的模仿,她的紫藤般旺盛的母性情怀和欲望,她的不婚,以及她的下乡之举,都是一个身处弱势的女性对父权制社会的反抗和挑战。我们不仅看到罗沙坚忍不拔、不畏强暴,与世俗和父权制抗衡的精神和行动,也读到了罗沙为她的抗争所付出的代价:被蹂躏得个性扭曲,面目可怖。通过罗沙,我们仿佛看到在父权制的压制下,美国南方女性积极地构建自我的社会性别,与不公的父权制社会抗争,听到了她们青春的怒吼和女性意识的声音。在历史的长河中,越来越多的美国南方女性已经走出了父权制控制的阴霾,实现了女性的独立和平等,南方淑女们也已经成为了历史,而福克纳小说中所刻画的南方淑女展现了女性当时的生存境遇和对父权的勇敢抗争,艺术地再现了这段被排除在历史书写之外的女性抗争史,同时也使这段女性的历史不朽于世。
参考文献:
[1] 威廉·福克纳. 押沙龙,押沙龙![M]. 李文俊,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2] Faulkner W. Absalom,Absalom![M]. New York: Viking, 1986.
[3] Clarke D. Fantastic Women and Notmothers inAbsalom,Absalom![M]∥Bloom H. William Faulkner Bloom's Major Novelists. Broomall: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0: 71.
[4] 董美珍. 女性主义科学观探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3.
[5] 朱迪斯· 巴特勒.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70.
[6] 露丝·伊丽格瑞. 话语的权力与女性的从属[M]∥汪民安. 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7] McMillen G S. Women in the Old South[M]∥Boles B J. A Companion to the American South.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217.
[8] Gwin M. The Silence of Rosa Coldfield Hobson[M]∥Hobson F. Absalom a Case Boo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9] 王恩铭. 20世纪美国妇女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10] 张光明,侍中. 淑女的历史[M].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7:195.
[11] 柏棣.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205.
[12] Godden R. Fiction of Lab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91.
[13] 苏红军,柏棣. 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