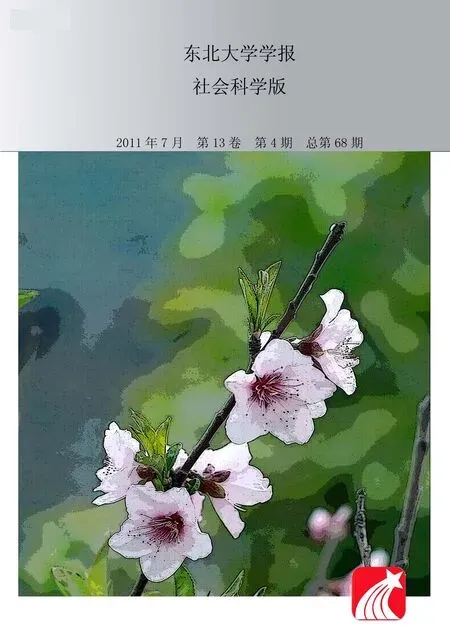阿伦特“根本的恶”的困境及其政治哲学意义
王 义,罗玲玲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辽宁沈阳 110819)
肆虐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屠杀与种族灭绝事件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对于德裔女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来说,对这场历史事件进行一种全新的认识,关涉到人类的命运。
一、透过极权主义理解人性邪恶的理性困境
对于阿伦特来说,极权主义之种族灭绝政策使其不能再沿用功利主义进行理解。“死尸工厂和遗弃人的洞穴的危险性在于,如今人口到处在增长,无家可归的现象也到处在增长,如果我们继续根据功利主义来思考世界,那么,人民群众依然会变成多余者。”[1]573汉娜·阿伦特提到的功利主义是近代西方广义上的人性观,以此为基础,建构了西方近代的社会科学。按照功利主义人性观看来,且不谈及人的本质是否是道德的,至少在现实本性上体现为功利,它以外在的质料为目的,服从于自己的生存或存在需要。由于功利,人可能将其他人当做工具,但是不可将自己当做工具来使用,根据形式逻辑的矛盾律来表达就是“人不可能毁灭自己”,也就是说,功利性是人的自然本性。根据功利性建构起来的人类社会,必然以功利性为其基本自然规律。而死亡集中营等现象表明,极权主义想要通过全面恐怖的方式建立起一种妄图毁灭人性自然需要的实验方式。“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不是改变外部世界,或者社会的革命性演变,而是改变人性。集中营是实验室,在集中营里试验改变人性和羞耻心,所以集中营不光是囚徒们的事情,也不光是根据严格的‘科学标准’来管理他们的人的事情;它关系到所有的人。”[1]572
通过对极权主义历史进行的意识形态考察,汉娜·阿伦特提出其邪恶动机超越自然功利,它作为一种具有自身目的性的存在,表达出来就是“人是多余的”。该种意识形态,以完美的人类为意向,功利性或者说现实的人类成为被摧毁、被改造的基本对象,摧毁的手段就是以秘密警察为制度保证的全面恐怖,全面恐怖则体现为集中营式的灭绝政策。“彻底的恶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在这种制度中,一切人和其他人一样是多余的。操纵这个制度的人相信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是多余的,极权主义的杀人者最为危险,因为他们连自己是死是活都不在乎,不关心自己是否生活过、是否出生过。”[1]573由于阿伦特发现该种意识形态的违反矛盾律之处,因此就能推论出一种不包含有任何善意的“根本的”恶意了。“有一些罪行是人们既不能惩罚,又不可宽恕的。当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时,它就变成不能惩罚的、不可饶恕的绝对罪恶,不再能被理解,也不再能由自我利益、贪婪、渴望、怨怼、权力欲望、怯懦等罪恶动机来解释。”[1]572
汉娜·阿伦特提到她遭遇到“根本的恶”时候的理解上的难题,不过就是意味着,如果我们根据功利主义背后的矛盾律来理解极权主义现象的话,我们永远不能通达极权主义的内在本质,她将这种理解上的困境比喻为加在现代人身上的重担。“我们实际上不必借助任何事物,就可以理解一种用十分有力的现实来和我们对抗、打破我们所知的一切标准的现象。”[1]573也就是说,阿伦特此时认为必须冲破传统的理性,进入到一种超出人类理解限度之外的理解方式,极权主义乃至恶才可以被认知。同时,对极权主义进行理性的探究,也就是在动机的探究中,赋予了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以超乎人类理解限度的理性根据,它才能超越人类的功利动机。如此一来,阿伦特的“根本的恶”概念就与哲学理性主义的传统道德观乃至康德于“根本的恶”中提到的“绝对的恶意”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
二、 理性的二重维度:真理与道德
“我们的哲学传统从来就不相信一种‘根本的恶’,在基督教神学那里,即使魔鬼也是天使出身,康德至少怀疑这种恶的存在,即使他立即用理性化的概念将之解释成‘反常的恶意’,但是也可用可理解的动机来解释。”[1]572由于西方的理性主义秉持的矛盾律,一个人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功利目标的前提下,将其他人乃至自己当做工具加以利用,也就是说罪恶起源于“自我利益”、“贪婪”、“渴望”、“怨怼”、“权力欲望”、“怯懦”等罪恶动机,本质上是人的 “自爱”。
理性主义的内在逻辑是:其天赋对象即本体的自在自为。自在意味着本体是一个尚未展现自身的、理念上的同一者,可以被理性认知,由于同一而完满,是一切理性认识最终要符合的朝向者,蕴涵着一切现实的乃至潜在的展现,这是理性的认识维度赋予其对象的理念完满性即真理;同时,自在者自为,自为就是自在者的展现自身,是对自身的回复,即由理念上的同一上升到现实的自身统一,所有展现出来的现象都是自在的完满性的表现,是一种完善,是对真理的明证,正是因为此种展现,本体才作为证明了自身的同一者,这是理性的证明维度赋予其对象的道德实践意义。由于本体的自身统一及其独立性,与杂多现象的对立就必然成为题中之义,本体至真且至善,杂多的现象相对于理念的完满性,存有欠缺,从而是相对意义上的恶,同时由于杂多现象又是对真理展开的符合乃至证明,也是相对意义上的善。
所以,对于哲学传统来说,杂多现象不存在“绝对的恶”、“根本的恶”,同时也不存在“绝对的善”、“根本的善”,而关键是,现象总是自在者的自为展现,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现象都是自然而然的,那么,恶又从何而来?这就引申出康德“根本的恶”概念提出的立意所在,即,任何含有违背理性先天规定的主观根据,都可以称做是“根本的恶”,“它虽然也可能是与生具有的,但却不可以被想象为与生具有的,而是也能够被设想为赢得的(如果它是善的),或者是由人自己招致的(如果它是恶的),……所以,这种恶必须存在于准则背离道德法则的可能性的主观根据中,而且如果可以把这种倾向设想为普遍地属于人的(因而被设想为属于人的族类的特性),那么,这种恶就将被称做人的一种趋恶的自然倾向”[2]21。
对于康德来说,既然秉持着理性的真理维度与道德维度之间的内在统一这种哲学的传统态度,作为根据的根据必然是至善者,从而迫使作为恶的规定性根据的根据不能具有实在性,而只能是一种潜藏于人性之中的主观根据,既不能是感性的实在,也不可能是理性的实在。换言之,它只能是人类的自爱。“为了说明人身上的道德上的恶的根据,感性所包含的东西太少了;因为它通过取消有可能从自由中产生的动机,而把人变成了一种纯粹动物性的东西。与此相反,摆脱了道德法则的,仿佛是恶意的理性(一种绝对恶的意志)所包含的东西又太多了,因为这样一来,与法则本身的冲突就会被提高为动机(因为倘若没有任何动机,人性就不能被规定),并且主体也会被变成为一种魔鬼般的存在物。”[2]21
至此,就能发现阿伦特提出“根本的恶”概念并不是康德所说的“根本的恶”,而是康德所否定的“绝对的恶意”。康德所理解的“魔鬼般的存在物”,在阿伦特那里,通过极权主义运动的现实冲击,成为了摆在现代人面前的现实性与挑战,导致了人类理性对于“根本的恶”的认知困惑。
三、理性遭遇恶的困境:“绝对的恶意”是否可能?
理解阿伦特放弃“根本的恶”概念的关键,在于理性遭遇恶的认知挫败,或者说,是“根本的恶”概念本身就必然要面临着如康德所言化解不了的逻辑困境,才导致了对于道德之恶的认知的放弃。对于这种极端的罪恶动机,康德没有进行深究,那是因为他固守着理性同一律的自我循环,赋予历史现象以不同程度上的合理性,回避了理解极端事件的现实本质的特殊性问题;而阿伦特执拗地坚持极权主义及其罪恶动机的实在性,强调其恶的“根本”而又自觉无法化解这种冲击带来的困惑,随后提出了“平庸的恶”概念,遭遇到各种不解与敌视,却无法澄清“平庸的恶”概念的革命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两人都没有深入认识到:理性自身设置的道德陷阱,是“根本的恶”无法穿透极权主义的迷雾的障碍。
首先,由于坚持极权主义的超越功利性的恶意及其难以通过矛盾律、同一律来理解的根据,赋予了恶以实在的规定性乃至客观的根据。继而这种根据就冲破了建构在至善者的客观实在性与道德之间的统一关系,冲破了作为最终尺度即作为统一者的统一性,划出一个人类理性尚没有涉足的,但是终究是可以被认知的“根本的恶”的实在维度,而同时阿伦特保留了对之继续进行理性探究、动机探究的可能,这样就无形中赋予了那个作为“根本的恶”的根据以一种统一性。也就是说,只要理性赋予了事物以根据的时候,就必然同时赋予其统一性,而这个统一性作为“根本的恶”的根据乃至尺度,其本身却回复了自身,成为一种超越了被相对地评价为善和恶的自在自为者。如此一来,原先作为评价一切的至善者由于受到“根本的恶”的冲击而与“根本的恶”一道成为相对的善,而又产生了作为自在自为者的终极价值尺度。最终,理性经过一番对于恶的根据的无穷探究,最终的结果不过是对于自己的两个维度不断统一的无限循环而已。
正如康德所说,与法则本身的冲突被提高为动机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会违背自身”,矛盾律、同一律作为形式逻辑不可能失效,阿伦特于极权主义现象中发现的违背自身的逻辑不过是预设了作恶者以理性的能力,进而产生了“根本的恶”概念的循环困境。所以,既赋予了“根本的恶”以迥异于至善的实在性,又保留了对其进行理性探究的可能,最终的困境必然是阿伦特转向对于作恶者理性动机的理性探究的放弃,是“平庸的恶”概念得以产生并具有重大意义的最关键原因。
四、关于阿伦特“根本的恶”的转折及误解
美国学者Bernstein认为,在阿伦特提出“根本的恶”概念的时候,她对于康德“根本的恶”概念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于恶的理性化的放弃,进而进入到一种关于恶的认知的盲区。“请注意,尽管阿伦特提到了康德,但她宣称,为了理解那一‘以其不可抗拒的实在性面对我们并打碎我们所知的一切标准之现象’,我们实际上无所求助。”[3]有的学者认为,阿伦特对康德“根本的恶”观点的理性化恶的批评实际上没有切中康德提出“根本的恶”的所指,他们认为康德提出“根本的恶”本质上是要建立人在邪恶发生的时候不可避免的道德责任。“Arendt的解释太过强调恶的非理性或者反理性,以至于忽略人即使活在一个邪恶的集权暴力的统治之下,发生邪恶的过程中,个人仍然有不能逃避的责任问题。”[4]
在阿伦特“根本的恶”与康德“根本的恶”概念的比较理解中,诸多学者都注意挖掘康德“根本的恶”概念中的道德自由问题乃至其自身转化问题,进而证明人在罪恶面前涉及的不可避免的道德责任能力,也就是说,阿伦特没有涉及到道德与罪恶的责任问题,直接否定了人类的道德承担问题,也就同时否定了道德存在的可能。然而,先不说康德的“根本的恶”概念中的自由根据仅仅是能够“被设想为”普遍地属于人的,而现在关键的问题是,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出现冲击着、瓦解着这种主观的根据,极权主义的理性逻辑超越西方哲学传统理性主义的逻辑规律。也就是说,康德所说的“自爱”即主观根据,在阿伦特看来奠基于理性主义道德运思的传统之中,它更为主要的是确证人类的道德能力问题,而极权主义的出现却冲击着这种传统,此时,我们必须“无所求助”,才能理解这突如其来的历史怪物。
而关于阿伦特为何放弃“根本的恶”,转而提出“平庸的恶”,尚存在争论,国内流行的见解大体是,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实质的改变,这两者不过是两种恶,或者说,“根本的恶”是潜藏的作恶倾向,另有极端的恶体现为希特勒代表的法西斯纳粹体制之恶,而“平庸的恶”不过是体制之下逐渐被剥除了道德能力的“平庸性”表现而已。如涂文娟所言:“根本的恶”的根本特征表现为破坏了人类发展和进步的概念,致力于把人变成多余的人的事业,以及消灭了人的法律人格、道德人格以及作为个体的人,是极权主义专制下道德崩溃的一个根本的理论上的原因,体现为诸如以希特勒为代表的“元首之恶”即一种“大恶”;而阿伦特于之后提到的“平庸的恶”的特征体现为无思想和肤浅性,是一个重要的合谋者。涂文娟进而认为:“根本的恶源于人性的某种东西,只要有人和人类社会,就一定存在这种根本之恶,无论有没有邪恶的领袖,它都潜在地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因为如果人性本身没有根本的恶,人就不会被魔鬼所诱惑。”[5]
刘英认为:“阿伦特指出的这两种‘恶’实质上是从社会与个体两方面揭露了现代社会极权制度下人性的丧失状况。”[6]如果将“根本的恶”理解为阿伦特所说的极端性,“根本的恶”的确体现为体制上的异化,与“平庸的恶”相互构成,但是,这就等于简化了阿伦特“根本的恶”与康德“根本的恶”概念之间,乃至与整个哲学传统之间的转承关系。忽视了“根本的恶”是理性在遭遇极权主义之恶时候的整合乃至困境,“平庸的恶”是对理性探究、动机探究的根本放弃,转向哲学诠释、哲学与政治关系反思,即走向具有阿伦特特色的政治哲学之路。
五、阿伦特对哲学与政治关系的反思
本文只是想在此处指出隐含于“根本的恶”概念中的理性困境,借此梳理阿伦特关于恶的思考的前后转折的关键所在。理性内在的二重维度,真理与道德,尽管经过阿伦特的“根本的恶”概念显露出缺陷,但也就是仅此而已罢了,相反,就像理性赋予真理以至善属性一样,由于阿伦特执著地赋予恶以实在性,就在同时依然秉持着哲学的传统,尚未超越出去。
所以,只有放弃对艾希曼动机的深究,放弃那个深藏于人性深处的不可告人的恶意,阿伦特才会走出理性自设的困境。“我的看法改变了,已不是主张‘根本的恶’的观点了。……恶绝不是根本的东西,只是一种单纯的极端的东西,并不具有恶魔那种很深的维度,这就是我真正的观点。‘恶’正犹如覆盖在毒菇表面霉菌那样繁衍,常会使整个世界毁灭。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思考要达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何况,涉及恶的瞬间,因为那里什么也没有,带来思考的挫折感,这就是恶的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7]166
放弃了价值属性(在这里为恶)的赋予,而代之以生活背景个人言行的描述,一个真实的犯罪者就呈现出来了,极权主义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恶的“平庸性”也展现了出来。“既不阴险奸刁,也不凶横而且也不是像理查德三世那样决心‘摆出一种恶人的相道来’。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它任何的动机。这种热心的程度本身也绝不是犯罪。……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于愚蠢,却又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就仅这一点滑稽,如果还去作任何努力尝试希望能知道艾希曼有恶魔一般的要因,那是不可能成功的。……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性恐怕能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表现出巨大能量的事实正是我们在耶路撒冷学到的教训。”[7]54-55也就是对理性化的邪恶动机探究的放弃,代表公民麻木精神状态的“无思想”概念才呈现出来,作为阿伦特后期对政治现象与哲学关系、对哲学本身的诠释的启动概念。
总之,在“根本的恶”阶段,由极权主义的极端到“根本的恶”的价值规定性,被阿伦特默认为一种关于价值属性的认知行为,无形中赋予了恶以实在性;同时,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由于秉持着对象的统一性,必然在认知中赋予对象以价值属性。然而归根结底,道德上的善和恶,都需要一个尺度来评价,也就是说,绝对尺度的道德属性是被预设的,而善和恶是被相对地评价的,至于那个尺度自身,由于自在自为而被理性识做是至善者。换言之,哲学传统的理性主义不可冲破,阿伦特转向了对哲学本身的反思与诠释,才看得分明,它只不过是一种意义或价值的赋予行为,在其背后,是人类总体如何生存于历史中,如何在历史中发现意义的现实问题或者说是人类之间的政治交流问题。
阿伦特在最后一部代表作《精神生活》三大卷本之中,提出哲学与政治的亲缘乃至对于政治生活的遗忘。苏格拉底对于真理的追寻,始终是在与公民的对话之间展开的,而苏格拉底之死,使柏拉图产生了对公共判断力的极大偏见,对于柏拉图来说,首先真理成为一种纯粹内在的思考,另外,政治生活也成了一种等级关系的统治。作为恢复哲学与政治的亲缘关系的努力,阿伦特发挥了康德的“判断力”概念,“它使我愉悦或者不悦,作为一种感觉这似乎完全是私人的,也是不可传达的,但实际上这种感觉植根于共通的感觉,因此一旦通过反思的转换就可以传达,而反思考虑到其他所有的人及他们的感觉……。换句话说,一个人在判断时,他是作为共同体的一员在判断的”[8]。
由于经过“根本的恶”阶段的理性困境,阿伦特政治哲学思想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反思到了哲学理性的意义赋予行为,是作为一种对待历史进程的旁观——诠释行为,并通过将哲学思考的这种纯粹性引入人类公共生活中,来恢复政治生活的公正性。
参考文献:
[1] 汉娜·阿伦特. 极权主义的起源[M]. 林骧华,译. 北京:三联书店, 2008.
[2] 康德. 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M]. 李秋零,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3] 理查德·J.伯恩斯坦. 对根本恶的反思:阿伦特与康德[EB/OL]. (2005-04-10)[2010-08-30]. http∥www.cnphenomenology.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841.
[4] 陈瑶华. 康德论“根本恶”[J]. 东吴政治学报, 2006(23):62.
[5] 涂文娟. 政治及其公共性:阿伦特政治伦理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163.
[6] 刘英. 汉娜·阿伦特关于“恶”的理论[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9,62(3):319-325.
[7] 汉娜·阿伦特.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8] Arendt H. Lectures i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