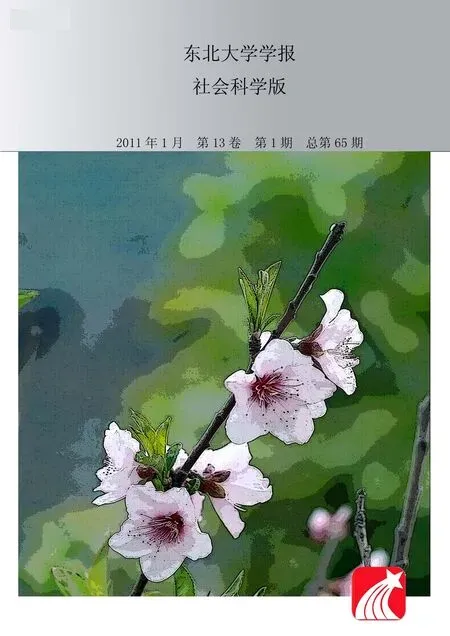论两种技术哲学融合的可能进路
易显飞
(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湖南长沙 410114)
技术哲学有工程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二元对立”的区分,这种区分深深地根植于哲学上的基础主义。基础主义的哲学传统以追究哲学牢固的基础为目的并以精神与物质的二分为其前提预设,然后,在此假设上进行自身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研究。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因袭了这种二元分立的基础主义传统,因此,二者相应地凸显了各自的理论优势与缺陷。笔者主张,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在研究内容上,加强对技术创新的本体论哲学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采纳“经验转向”与现象学的视角为主要认识维度;在研究主体方面,注重对技术哲学研究者进行“两种文化”的教育。以此作为促进两种技术哲学融合的一种尝试。
一、 技术哲学中的两种传统理论倾向及其缺失
基于技术哲学历史演变的考察,卡尔·米切姆认为技术哲学有两个流派:工程的技术哲学和人文的技术哲学。他认为工程的技术哲学始于为技术辩护即分析技术本身的本质,其致力于发现人类事物中到处体现出来的自然,试图用技术来解释非人世界和人类世界,并且用技术作为依据和范式来追问和评判其他事物,借以加深或拓展技术意识。反之,人文的技术哲学则力图追寻技术的意义,即其同艺术、文学、伦理、政治及宗教的关系。具有代表性的是其考察技术如何可能(或者不可能)适应或者应用,并用非技术准则来评价、追问和反思技术[1]。总的说来,第一种传统比较倾向于为技术辩护,第二种则主要对技术持批判态度。
从本体论意义看,工程的技术哲学凸显了技术的自主性,将其理解为主体或动因,只关心纯粹的技术之“是”和何以为“是”,增强或扩展了技术的意识,甚至将技术高度发挥成一种理性,支配和驾驭现代人的生活,忽略了人、技术与生活世界本真的生态关系。例如,R.舍普认为:“只有在技术的历史中找到技术的根源和原因,才会更好地理解技术”[2]。卡尔·米切姆认为:“技术哲学是像一对孪生子那样孕育的,甚至在子宫中就有相当程度的竞争。”[3]而人文的技术哲学把技术理解为对象,它从道德之“善”与艺术之“美”的角度来批判技术,关注人的历史境遇,强调人类的自由与解放,在解释学意义上描述技术,而忽略了对技术过程具体的认识。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工程的技术哲学在认识内容上忽略了非技术的要素,只强调技术的主体性。它的研究局限在技术系统里面,而没有充分关注技术系统之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人文等非技术系统。其认识范围与认识过程较为孤立和片面。而人文的技术哲学在认识内容上强调教育、宗教、社会、哲学等传统技术系统之外的因素,并运用非技术的知识来批判和反思技术。两者的认识路线呈现对立与互补的特点:工程的技术哲学是从技术出发向其他领域扩散,是一条从内到外的认识路线;而人文的技术哲学是从外到内的认识路线,它利用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理论来反思技术本身。总体看来,两条认识路线都具有自身的优势与片面性,须要走互相融通之路。
从价值论方面来看,工程的技术哲学展现了技术巨大的功能及技术发明的重要性,并把技术发明活动当成类似于艺术创作的享受性体验,甚至认为技术能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与人文危机等。而人文的技术哲学更加关注技术的后果并对技术的负价值进行反思与批判。它认为技术并不能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所有困境以及人类对这些问题的解决须要借助非技术的力量。总之,工程的技术哲学主要强调技术的正价值,而人文的技术哲学更多地关注技术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在其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理论基础上体现出了各自的特点与不足。二者各自偏执,工程的技术哲学传统走向技术自我;人文的技术哲学则走向非技术。如何使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走向融合,以促进技术哲学持续、合理地发展呢?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
二、 技术创新哲学研究:从研究内容上促进两种技术哲学融合
从研究内容来看,工程主义的技术哲学与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之所以对立,在于两者的研究对象都走了“偏锋”。前者只是以技术发明为主要研究对象,较少考察技术所处的整个社会大环境;后者从社会维度审视技术,较多地蕴涵技术悲观主义情结,对技术实践的内在反而缺乏体悟。由于技术创新从其一般理解的意义上讲是始于技术构思终于技术的商业化运用全过程,这样,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可以把工程主义与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关注重心包容在内,从而实现两者的融合。
技术创新本质是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是对技术发明的“扬弃”,也是技术的存在方式。发明家的技术成果,只有通过技术创新阶段,才能形成技术的最终结果并被应用于消费者。技术创新是技术存在意义的展现,技术创新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对技术的领悟。我们正是通过对技术创新的每一个阶段的具体把握,才能领会技术的本质。技术创新过程是一个时空阶段,而技术则是无数这样阶段过程的综合[4]。技术创新是一个展现过程,通过它我们构建了周围的世界,展现了我们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矛盾的方式。而从哲学的视角对技术创新进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融合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内容的现实途径。不少学者都呼吁要加强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陈昌曙从学科建设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和现实的社会实践的需要三个方面论证了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重要性[5]。有学者甚至认为,如果技术哲学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那么在这样的定位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就成为了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和核心[6]。
其实,工程技术哲学与人文技术哲学的研究内容都体现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技术创新本身是一个主客融合的过程,在这个技术的展现过程中,技术共同体与其相关的环境因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技术创新在对技术的扬弃中可以使工程技术哲学的技术理性更加鲜活,并打开与展示“技术黑箱”;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实践是一个开放系统,它的每一阶段与环节都负载着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它本身与社会、文化、政治、习俗等因素紧密融合,而这正是人文技术哲学的落脚点。
技术创新一方面体现了工程技术哲学的技术本体,另一方面又包含了人文技术哲学的“非技术”因素,技术创新是工程技术哲学与人文技术哲学内容的二重化。工程的技术哲学在对技术的研究中固然要把技术升华为具有主体性的理性本体,但是不能脱离技术的存在场所——技术创新。而人文的技术哲学在反思技术时要深入理解技术的内在意义。技术创新这个“二重化”的身份在展现技术的过程中把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融合起来。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7]马克思强调实践对于思维的根本意义,两者分离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而技术创新实践正“重合”了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的实践内容,因此,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的内容分歧须要通过技术创新这座桥梁来融会贯通。
三、 “经验转向”与现象学:从方法上促进两种技术哲学融合
从研究方法来看,工程主义技术哲学只强调技术理性,从技术这个基础出发向其他领域扩散,是一条从内到外的研究路线;而人文主义技术哲学运用人文、社会以及哲学思想等知识来批判和反思技术,是一条从外到内的研究路线。两种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各有所长,但各自也存在缺失。笔者主张,借鉴“经验研究”与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可以从方法上促进两种技术哲学融合。
所谓“经验研究”,是指一条与人文的技术哲学相对立,但又不全采纳工程的技术哲学理论的技术探究之路。其实,早在1995年,美国技术哲学家皮特就曾关注“技术哲学研究中的经验转向”问题,他认为技术哲学家们由研究抽象的形而上的技术对人类的影响转向研究形而下的技术是如何从物质和观念上来影响人们的生活的[8]19-21。
我国的陈凡教授也认为,技术哲学家要反思技术,就必须去打开这个黑匣子,使他们的分析基于对工程实践的内在洞察和从经验上对技术的充分描述。技术哲学研究中的这种经验转向,一方面表明工程技术哲学研究范式中将技术看成是抽象的,并忽视技术本身的缺陷,因而逐渐受到技术哲学家的普遍关注。另一方面,主张“经验转向”的技术哲学家们强调,人文的技术哲学也应该更多地关注于应用工程科学和研究技术的经验科学,而应较少地关注与现实联系不充分的、抽象的神话和臆想,人文的技术哲学应基于现代技术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经验式的充分描述之上来反思技术,要打开技术“黑箱”[9]。现代技术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且是高度复杂化的和差异化的现象。要认识到现代技术的这个特点,只有通过从整体水平上的分析转换到局部层面上的分析才可能,技术的丰富性只有通过对现代技术进行放大镜式的观察才能显现出来[8]28。从人文技术哲学来看,它越来越注重对技术系统的内部结构和运行过程方面进行规范性、描述性和批判性的研究,不是把技术当做一个单一的整体来进行分析,而是开始关注技术的设计、生产、改造、创新等微观机制,从而能在此基础上探讨各种类型技术系统的人文社会意义。
工程主义技术哲学是从技术理解人和技术,而人文主义技术哲学是从人来理解技术,思想路线的互逆性导致两者的对立,笔者尝试从现象学的角度出发,按照“朝向事物本身”的价值要领,找到一个能够克服两者对立的新维度,重新理解技术。现象学的方法主要源自胡塞尔的“第一哲学”。自20世纪初胡塞尔创立现象学以来,现象学为当代欧陆哲学提供了一个较严格的方法论工具。该方法主要的特点在于对“理性”这一概念重新加以审视和解读,认为传统的理性概念实质上是一种对理性本身的误读与背离,其结果造成科学的危机。相应地,将现象学方法用于技术哲学研究,应当首先是一种态度或“范式”的转变,“整个现象学的态度和属于这一态度的悬置本质上注定了首先要达到一种个人的完全转变,从一开始就可以与一种信仰的改变相比”[10]。海德格尔开创了运用现象学进行技术哲学研究的先河。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不仅是手段,其本质是一种展现方式,居于“座架”之中,座架意味着对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置着人[11]。“座架”支配着一切,人的本质被它要求着、挑战着。海德格尔赋予了技术各种意向,而不是单纯的工具和行为。后继者伊德沿着梅洛-庞蒂对知觉分析的路径,认为不存在纯粹的技术本身,技术是一种关系性存在,技术的基础和核心就在于技术与人和世界的相关性,他的技术哲学是一种“人—技术”关系的现象学。
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从本体论意义上通过胡塞尔对理性的重新定义、海德格尔独特的“诗”与“思”而达到一个自在自为的世界,一个“在”的世界,而不是进入一个“是”的世界。只有在这个本真的存在世界里,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才能融合起来回归到真理与精神的家园,人类才能真正“诗意的栖居”。运用现象学方法就不能离开意向性,而技术本身就具有意向性,这也是技术与现象学可以交融的因素之一。而从伊德的观点看,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可以从技术与其相关因素的关系来融通,以这个关系理论为基础来建构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融会贯通的平台。陈凡教授也认为,现象学追问技术的本质,使技术既向自身敞开,同时也向人与社会敞开,这是对工程主义和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分裂困境的一种解决[12]。当然,两者之间如何采用现象学范式进行具体融合,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有必要指出的是,“经验转向”与现象学不是割裂的两种方法,恰恰相反,两者是交互耦合的。技术哲学研究中的“经验转向”要求现象学的技术哲学应注重对具体技术的规范性和描述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各技术系统的人文社会意义;反过来,“朝向事物本身”的现象学对技术的研究由抽象的形而上学层面转向描述层面,为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转向”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四、 “两种文化”的教育:从研究主体上促进两种技术哲学融合
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C.P.斯诺指出:科技与人文正被割裂为两种文化,科技和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分化为两个言语不通、社会关怀和价值判断迥异的群体,这必然会妨碍社会进步和发展。当前,两种文化的分裂非但没有缓解,反有愈演愈烈之势。科学文化以物为尺度,推崇工具理性,追求真;而人文文化以人为中心,推崇价值理性,追求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区别主要表现在文化客体的不同。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的对立,就是“两种文化”对立在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技术哲学不管是走向“两种文化”的哪一极都会有理论方面的缺失。而代表这两极的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的研究主体可以通过“两种文化”的教育来促进其融合。
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的分野因袭了“两种文化”的分野。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从自身的文化基础出发走向各自的道路。工程的技术哲学以技术为研究核心,强调技术的工具理性,最终走向以物为中心的科学技术的本体。其传统高扬技术的理性,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并革命性地改善了人们在衣食住行、医疗保健等方面的状况,然而技术的日臻完善会导致一个问题:过去人们主要意识到他们不能做的东西以及自身的局限,在定下方案后,需要很多精力去解决这个方案中的技术问题。现在已经掌握了实现任何具体思想的技术手段的一般方法,人们似乎丧失了提出任何目标的能力。正如奥特加所指出的,技术专家正体现了工程主义技术哲学的人文的缺失。他们深陷于技术的泥潭而失去了人类社会理想与信念的指向。另一方面,人文的技术哲学则强调“非物”的思想意识及生态环境等因素,并运用它来反思与批判技术。人类面临的价值迷失等也与技术的发展脱离不了干系,人文的技术哲学正是建立在这种人类社会面临的现实基础之上对技术进行的反思。“(人文的)技术哲学家必须开始就他们的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工程师对话,而为了这一点他们必须学会工程师的语言。”[13]技术之思也应具有规范性,杜尔宾说过,技术哲学要说明的是一个好的技术社会该是像什么样子[14]。
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的分立还涉及到两类研究主体的“知识完备性(intellectual integrity)问题”。皮特认为,人文的技术哲学家对技术一味地批判,而不是通过开发各种手段,以使我们所拥有的技术知识和对技术的理解与我们对世界是如何彼此联系在一起的看法结合起来。他认为这样对技术哲学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15]。他主张技术哲学工作者“必须以哲学家而不是意识形态学家的身份把注意力集中于事物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15],以正视目前出现的“知识完备性问题”,努力做到技术哲学团体与其他研究团体的交流和讨论上的融合。
有学者认为,之所以会有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的区分,就在于两类研究主体存在明显的区分[16],工程的技术哲学的反思主体多是技术专家或工程师,如提出“工厂主哲学”的化学工程师安德鲁·尤尔、德国技术发明家恩斯特·卡普、俄国工程师恩格迈尔、德国化学工程师埃伯哈德·席梅尔和X射线治疗技术的发明者德索尔等等;人文的技术哲学的反思主体多是人文学者,尤以哲学家为多,如芒福德、奥特加、海德格尔和埃吕尔等[17]。要使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的研究主体不至于成为“单面人”,“两种文化”的教育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要大力推进对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研究主体“两种文化”融合的教育。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研究主体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上的合二为一是实现两种技术哲学融合的保证。从技术哲学对技术实践的指导作用来看,要实现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的“二位一体”技术实践的价值目标,关键还是取决于人,即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研究主体本身应该同时兼具“两种文化”。要做到这一点,还是要从教育入手,使我们的教育真正转向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加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实行“文理兼容”的教育[18]。缺乏(自然)科学技术的教育仅仅是培养信仰而没有充分的知识支撑,缺乏人文精神的教育仅仅是传授知识而没有理想信念的指引,因此,二者取长补短才是工程技术哲学与人文技术哲学的融合之道。
参考文献:
[1] Mitcham C. 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62-63.
[2] 舍普 R. 技术帝国[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3-4.
[3] 卡尔·米切姆. 技术哲学概论[M]. 殷登祥,曹南燕,译.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10.
[4] 易显飞,张扬. 技术哲学应首先关注技术创新的哲学问题[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21(1):18-20.
[5] 夏保华,陈昌曙. 简论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1,17(8):18-19.
[6] 夏保华. 技术创新哲学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37.
[7]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55.
[8] Achterhuis H. America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M]. Blooming: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9] 盛国荣. 西方技术哲学研究中的路径及其演变[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8,30(5):38-43.
[10] Husserl E.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137.
[11] 海德格尔. 技术的追问[M]∥海德格尔选集. 孙周兴,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6:924-954.
[12] 陈凡,傅畅梅. 现象学技术哲学:从本体走向经验[J]. 哲学研究, 2008(11):102-108.
[13] Kroes P. The Empirical Turn in the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M]. Amsterdam: Elsevier, 2000:8.
[14] Durbin P T. SPT at the End of a Quarter Century: What Have We Accomplished Techno[J]. Techne, 2000,23(2):35.
[15] Pitt J C. O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Past and Future[J]. Techne, Society for Philosophy & Technology, 1995,1:1-2.
[16] 刘大椿. 关于技术哲学的两个传统[J]. 教学与研究, 2007(1):33-37.
[17] 张同乐,邵艳梅. 关于两种技术哲学的困境之思[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25(1):13-16.
[18] 杨怀中. 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研究[M]. 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4: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