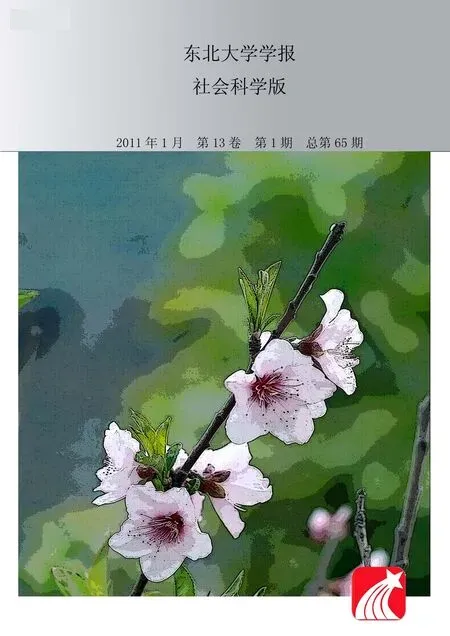科技风险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特征
米 丹
(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上海 200237)
21世纪初的全球金融危机*指2007—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2007年始于美国,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失控而演变为世界金融危机。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思,而作为成就了现代金融领域的“金融工程”仍然是被完全排除在任何异议之外。就在人们痴迷于各种高科技所带来的物质财富激增的时候,科学技术另一种潜在的威胁也正在孕育并发展着。这种威胁同样表现在金融工程技术中,是现代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新的科技风险形态。这种科技风险经历了数次历史演变,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具备了当代的形态特征。
一、 科技风险的内涵及历史演变
1. 科技风险的内涵
科技风险与科技价值及其实现密切相关。 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出发, 科技价值就是指现实的人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科学技术的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 科技价值包括科技的固有价值和科技的社会价值, 前者指由科技本身固有的属性所体现出来的价值, 后者则指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过程中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意义。 科技价值只有通过价值实现才能由潜价值转化为显价值, 使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各种需要得到实际的满足。
科技风险是伴随科技价值实现的过程而产生的,是指科学技术在应用过程中所可能引发的危害或损害。科技风险是科技价值在实现过程即被消费、被享受中,科学技术对人或社会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来源于科学技术内在的不确定性。
首先, 科学知识本身具有不确定性。 进入20世纪, 由牛顿经典力学构造的完全确定的世界图景开始动摇。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 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彻底打破了拉普拉斯决定论的自然图景, 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日益表现出非线性和不确定性的一面。 在科学哲学领域,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否证式科学发展观打破了传统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理论发展的确证性原则, 深入揭示了科学知识的相对真理性的一面, “消除错误导致我们的知识即客观意义上的知识的客观发展, 导致客观逼真性的增长, 它使得逼近(绝对的)真理成为可能”[1]。
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早就包含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之中,科学知识的条件性和相对真理性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坚持的科学观。“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2]“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3]“我们的知识对于客观的、绝对的真理的接近的界限是历史地有条件的,可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之逐渐接近于它是无条件的。”[4]只不过,科学知识的这种相对性长期以来都被人们忽视了,在物质财富面前,“知识在谬误中前进”被迫退到了幕后,这种忽视是产生当代科技风险的重要原因。
其次,科学知识中社会因素的渗透进一步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在20世纪中后期逐渐形成了以汉森(N.R.Hanson)、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和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等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从而使科学成为一种发展知识的方法论框架或理论范式,并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库恩的“范式”(paradigm)理论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所谓范式,是指从事同一个特殊领域研究的学者所持有的共同信念、传统、理性和方法。范式决定了科学家的世界观、价值观、信念体系、思维方式等等,同时科学知识的意义和标准也由范式给定,是历史的和相对的。以库恩的历史主义解释为契机,在20世纪末,涌现出了一股由社会学家掀起的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和解释的思潮。默顿(Robert K. Merton)的科学社会学阐明了科技活动不仅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社会诸因素的强烈影响,而且在内部也是社会化的存在。之后,以“爱丁堡学派”(Edinburgh School)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则将科学知识完全纳入了社会的范围。
从逻辑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再到科学知识社会学表现了科学知识由确定性向不确定性、由绝对真理性向非理性的转换过程。这一过程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局限性,但是他们提出的科学中的非理性因素对于打破知识的盲目信仰是有积极意义的。非理性因素在科学中确实存在,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人的认识水平的有限性,同时也揭示了科学知识中真理性和相对真理性、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辩证统一。
2. 科技风险的历史演变
关于科技可能引发危害这一点,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了。早在1750年,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论艺术和科学》一文中就曾论证,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将导致道德败坏,最终必将无益于社会的进步。每个时代的科技风险都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在现代科技革命以前,这种形式更多地存在于贤哲们独特的思想中,并非明晰的现实形态。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在当代,科技风险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普遍。各种高新技术发展的风险问题空前涌现出来,包括生态风险、基因技术风险、网络风险、核生化技术风险、纳米技术风险、航天技术与太空风险等等。20世纪中期以来,关于科技风险的讨论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是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的争论主要是科学技术专家关于核能控制和评估中的风险研究,相对而言,普通公众对科技风险的讨论比较微弱。风险的应用领域则主要限于经济的范围,风险评估也基本限于概率、数学函数或模型等可计算的范围之内。由此看出,此时的风险定义带有明显的经济学色彩。
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一个转向,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批评者和新技术的反对者开始主导风险问题的争论,公众开始质疑高科技的后果带来的负效应,“风险”问题越来越超出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概率计算范围,逐渐向公众化、社会化和政治化转移,不断引起新旧价值观的冲突与变化。风险研究也开始关注个人心理学的因素,个人的感知、偏好、背景、信念等更多主观性的东西被融入风险研究中。“这些因素证实了对风险的直觉理解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能化约为概率和后果的乘积。”[5]
20世纪80年代之后,人们对风险问题展开了全方位的讨论。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件成为风险问题研究的转折点,此后,风险问题突破了核能的狭隘领域而扩展到生物技术、科技伦理、全球生态问题等多种领域,风险分析也广泛涉及到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理论等各社会科学领域,同时,各种协会组织及广泛的社会成员也加入到风险研究与讨论中来。风险问题带来的全球冲击使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并开始对现有的社会制度造成冲击。正是在这一阶段,“风险”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二、 当代科技风险的特征
当代科技风险是随着20世纪中期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而产生的,科技所带来的巨大威胁正在成为整个世界的焦点。当代科技风险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当代科技风险具有“不可感知性”和“知识依赖性”双重特征
在工业社会早期,工业发展带给人们的景象是:弥漫在伦敦空气中的煤烟,下水道恶臭的有毒水汽,德国工业中心的上空长期的灰黄色的烟幕等等。这些危险明显地刺激着人们的眼睛和鼻子。而当代科技风险则逃离了人们的感知能力,以放射性、基因变异、空气和水中看不到的毒素等无法明显感知的形式存在。对它们的“感知”则“只出现在物理和化学的方程式中(比如食物中的毒素或核威胁)”[6]20,并依赖于科学知识的界定。“人们关注的焦点正越来越集中在那些受害者既看不见也无法感知的危险之上;……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危险都需要科学的‘感受器’——理论、实验和测量工具——为的是使它最后变成可见和可解释的危险。”[6]26“不可感知性”不等于风险并不存在,而是说明它的表现形式较之以前更加隐蔽、模糊和不确定。除非发生了实际的核泄漏并造成了影响或者出现了禽流感的感染病例,否则,人们并不明确地知道正在应用的一些技术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影响的范围是多大、有多大的可能性造成严重后果。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们只能在方程式和统计数据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但对于现代风险而言,其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
这种“不可感知性”和“知识依赖性”表明了当代科技风险具有现实的和建构的双重属性。风险的本质不在于它正在发生,而在于它可能会发生,因此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既存的外在之物去观察它,在这个意义上,必然是建构的。但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建构风险,相反,风险正是在建构过程中被逐步揭示的,必须结合那些保证其存在的技术敏感性和技术诀窍[7]。风险的客观可能性的存在是前提,在此基础上,风险在媒体、科学或法律等知识媒介中被转变、夸大或削减。
2. 当代科技风险具有“人为的不确定性”
当代科技风险主要来源于人类自己的决策,即“人造风险”,更确切地说来源于现代科技的发展。首先,来源于技术化环境的风险。前现代的灾难一般都是外部对人类的打击,因此都可以归之于自然的神秘力量。但随着科技的发展,自然便逐渐退化为人类控制与利用的对象。然而,技术的成功却带来了新的风险形式,生态危机、全球环境变化、各种新的变异病毒(禽流感、SARS、疯牛病、甲型H1N1流感等等)开始向人类科技挑战。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则早已超越了纯粹的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向人类自身提出了挑战和质疑。人工智能对于人类自身的潜在威胁成为世界的焦点。2010年5月20日,美国科学家宣布“完全由人造基因控制的单细胞细菌”研制成功,这意味着世界首例人造生命的诞生,由此它被命名为“人造儿”。生物技术正在颠覆“进化”的概念,同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对于人的价值、伦理和意义的冲击。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现代科技本身似乎也无法为此给出任何确定的预防机制或解决措施。现代的“生态威胁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知识的结果,是通过工业主义对物质世界的影响而得以建构起来的”[8]。
其次,是制度化风险的发展。制度化风险的发展同现代科技与制度的结合密切相关。典型的例子就是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的一系列经济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提供了风险的激励机制(如投资市场、股票市场和金融市场),同时各种制度为人类的安全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但这种制度潜藏的无法控制的因素又带来了新的风险,即制度性风险。
当代风险的决策性质使得风险超越了外部而成为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而这种决策“是由整体组织机构和政治团体做出的”[9]68。技术—经济的发展,科技成果的应用,现代的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等一起为工业风险负责,同时也意味着当代科技风险固定责任人的缺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则称之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这种制度化风险的一种表现。金融工程技术这一知识体系包括了金融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学等。在投资银行满怀信心地利用精湛的金融工程技术的同时,却忽视了当代科技风险已远远超越了科技自身,它是一种社会问题并涉及多方利益主体。金融工程技术增加了金融交易的环节,所带来的一种社会负效应就是疯狂的投机,由此又加剧了金融衍生品的"滥用"和房地产的泡沫。这种社会负效应是排除在金融工程技术的知识体系和评估体系之外的。传统风险评估局限在封闭的依据共同契约的科技专业人员共同体中,排除了共同体之外的任何因素的渗入与参与。但是,在当代的科技风险面前,这种封闭的以范式为基础的科学实践不再适用。当代科技风险处理的问题涉及到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不仅要求科学内部评估的有效性,而且涉及到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领域,同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领域具有影响。金融工程技术所隐藏的另一种风险来源于其方法论,金融工程的方法是数学建模、数值计算等工程技术方法,而当代科技风险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不可计算性”。
3. 当代科技风险具有“不可计算性”的特征
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个人保险和公共保险,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交通保险等等。以这种方式,传统工业社会发展出了一套应对风险的预防和赔偿的标准规则体系,这些体系靠事故统计学的帮助使不可计算的事件变得可计算,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人们的安全意识。“可计算性”风险的基础是统计学及概率计算。这要求预先有一些经验的统计数据作为推算的基础,同时,造成损害的因果关系在一定时期内要保持稳定。这种方法一般用于物质性损害,同时排除了技术损害中人为因素及社会因素的影响。例如,对来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统计、对某一复杂技术系统出现故障的风险评估等等。
然而,核能的、化学的、基因的、生态的大灾难摧毁了以科学和法律制度建立起来的风险计算的逻辑基础。科技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并逃离了人们的感知范围和可预测范围,它不仅涉及某一物质性危害的结果,而且可能包含多种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灾难,而原因则可能来源于多种途径。正如贝克所说,所谓可计算和可选择的安全不包括核灾难,也不包括气候变迁及其后果,亦不包括亚洲经济崩溃,不包括低概率但高效果的未来技术的各种形式的风险。事实上,大多数引起争论的技术,比如遗传工程,是没有个人保险的。全球性的灾难后果使金钱补偿机制失效了;预防式的事后安置因致命灾难情况下可想象的最坏情形而被排除,对于结构进行检测的安全概念失效了;“事故”成为一种有始无终的事件,在时间上无休止地蔓延,从而正常的标准、测量的程序以及计算的基础均被破坏了[9]72。
三、 当代科技风险的表现形式
科技带来的新的风险形式主要表现为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核技术、新材料及新能源等在社会应用中所具有的潜在威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危险更多了,毕竟相对于前现代时期,我们有了更多的安全措施和医疗保健,只是今天的“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低,但后果的严重性是以前任何时期所没有的,是一种低概率、高危害的风险。
1. 当代科技风险扩展为广泛的社会风险
现代科技风险的产生和增长是一个体制化的社会过程,科技活动受到三种体制化因素的影响,即学科的功利价值取向、研究对资金的依赖和研究者的法定义务。这三种因素通常是一致的和相互加强的,且都相应加强了技术社会化的趋势,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带来了社会风险[10]。
在这种情况下,科技风险的社会负面影响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来。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查理斯·培罗所说,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却掩盖了社会潜在的巨大风险,被认为是“社会发展决定因素和根本动力”的现代科学技术正在成为当代最大的社会风险源[11]。科技风险不仅带来了生态的破坏,而且还直接影响到了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的多个方面。信息技术与经济的结合发展使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就将波及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运行;核武器的发展则直接导致了国家间基于政治目的的战争烽火;在社会领域,生物技术挑战了几千年来形成的伦理规范;在文化领域,科技风险已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而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风险文化。在风险面前,人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渗透着科技的因素,科技已经和人类社会融为一体,科技风险因此从根本上说就是社会风险。
2. 当代科技风险呈现出全球化趋势
现代科技风险都不再仅仅限于某一个时间段或某一个特定的区域,而是经常形成一种没有时间限制的带有全球性损害的灾难。核武器可以在瞬间毁灭整个地球;放射性物质的泄漏在不知不觉中导致人体器官的衰竭,并且其影响可以延续至数代以后。1984—1985年最早发现于英国的疯牛病危机,不到20年工夫就扩散到了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几十个国家。2003年,美国的疯牛病使美国国内与牛肉产业相关的畜牧、生产、销售、餐饮等各个行业都受到冲击,经济连锁反应很快从美国国内扩展到外贸领域,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经济损失上百亿美元[12]。而2007年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短短数月就从美国金融业蔓延到实体经济,进而引发了百年罕见的全球金融危机。科技风险全球化的规模和速度随着科技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也逐渐呈现加速趋势。
科技风险的全球性特征与科学技术纵向的日益分化以及横向的高度综合密切相关,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科学(Big Science)系统更是加强了科学技术的全球化进程。在大科学的时代里,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或团体能够控制整个科技项目的发展,同样,科技风险也不可能只在某一特定的区域爆发,它往往给各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带来无法预测的后果。另外,当前科学技术已经渗入到了经济、政治、军事等社会的各个领域,而大科学的出现也将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科技的全球化势必带来风险的全球化。正如贝克所指出的:在这个疆域消失的科技全球化时代,风险也就必然全球化了。因此,科技全球性的世界已然形成全球风险世界[13]。
全球风险为世界各国带来了新的国际不平等,如危险的工业已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低工资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越贫困的国家承受的风险可能性越大等等。但最终,当代科技风险是全球性的,风险的制造者和从中受益者也终将承受风险带来的不良后果。在科技迅速发展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今天,科技风险也必将成为制约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不容忽视的力量,因此,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全面的反思。
参考文献:
[1] 波普尔. 客观知识[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135.
[2]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561.
[3] 恩格斯. 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26.
[4] 列宁.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M]. 曹葆华,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128.
[5] Allen F W. Towards a Holistic Appreciation of Risk: The Challenge for Communicators and Policymakers[J].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s, 1987,12(3/4):138-143.
[6]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 何博强,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4.
[7] 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约斯特·房·龙. 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M]. 赵延东,马缨,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5:3.
[8]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96.
[9] 乌尔里希·贝克. 世界风险社会[M]. 吴英姿,孙淑敏,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0] 赵万里. 科学技术与社会风险[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1998,15(3):53.
[11] Perrow C. Accidents in High-risk System[J]. Technology Studies, 1994(1):23.
[12] Zhang Qingpu, Hu Yunquan. The Systematic Research on Enterprise Knowledge Management[J]. Journal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2,9(4):354-358.
[13] 薛晓源. 前沿问题前沿思考:当代西方学术前沿问题追踪与探询[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