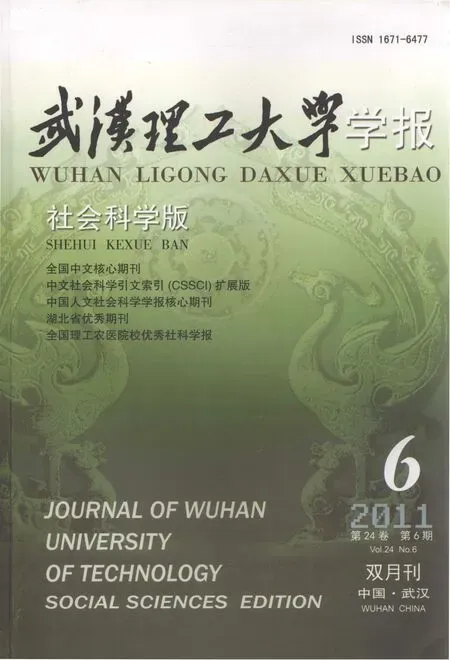知识产权侵权获益赔偿的立法模式的选择*——以现行法为分析对象
孙良国
(吉林大学 法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知识产权侵权获益赔偿的立法模式的选择*
——以现行法为分析对象
孙良国
(吉林大学 法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均明确规定了侵权获益赔偿。通说认为,获益赔偿只是损害赔偿的一种计算方式。实质上获益赔偿与补偿性的损害赔偿理念不同,其还有效保护权利、剥夺不当得利、威慑未来侵权行为等功能而非仅仅是填补损害,具有独立地位。就获益赔偿,我国知识产权法有补充式和选择式两种立法模式,前一模式认为获益赔偿是损害赔偿的替代性计算方式,后一模式赋予受害人可选择主张损害赔偿或获益赔偿。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大都以选择式立法模式为主。选择式立法模式在权利保护和行为威慑上具有明显优势而且毋庸采取推定的立法技术,应为我国知识产权立法较为科学和理想的立法模式。
损害赔偿;获益赔偿;立法模式;知识产权侵权
我国《著作权法》第49条、《专利法》第65条、《商标法》第56条都明确规定,知识产权一旦受到侵害,权利人有权向侵害人主张因侵权行为而获得的利益。笔者将此“以获益为基础的赔偿”称为“获益赔偿”。但是我们也看到,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同样为知识产权,同样为无形权利,但法律对获益赔偿的立法模式却不同,目前并没有立法材料或学者对此作出解释。笔者试图对此进行解释和批判。分析的起点是获益赔偿的性质和功能。同时笔者也将概括我国现行法所确立获益赔偿的两种立法模式和它们的观念基础,并进而分析它们的优劣,从而为选择更为理想的立法模式提出建议。
一、获益赔偿的性质——以通说和对通说的质疑为中心
(一)获益赔偿性质界定的通说
损害赔偿是以权利人为中心的,赔偿的标的只能是“损害”,而且是“权利人”的损害。为什么知识产权法允许权利人主张赔偿的标的是加害人的获益呢?目前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获益赔偿是损害赔偿的一个计算方式[1]。汤宗舜先生直言:“赔偿损失,顾名思义,是损失多少赔偿多少,也就是西方国家实行的填平补齐原则,因为这是民事制裁,不含有惩罚性质。”[2]另一种认为,知识产权具有无形性,其一旦受到侵害,损害不容易证明,而有时侵害人的获益是比较明确的,这是获益赔偿即具客观性。上述两种解释非我国独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通说也大多将获益赔偿作为损害赔偿的一种计算方式,主要表现为获益赔偿都规定在损害赔偿计算的条款中。但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获益赔偿是否真是损害赔偿的一种计算方式?对该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损害赔偿本质的理解。
一般认为,私法仅涉及矫正正义,不涉及分配正义[3]60-69。按照私法的“矫正正义观”,只有权利人的权利才能与权利人的赔偿请求权结合起来,权利经由加害人的侵权行为而变为损害,因此损害与赔偿是唯一体现矫正正义的链接。此理念被称为“补偿性的损害赔偿观念”[4],也称为“填平”理念。这默示了两点:
第一,私法或者侵权法不具有任何惩罚性。惩罚性不是私法的目标,而是公法的任务。《欧洲侵权法原则》第1.101条及其注释也明确认为,受害人只有权主张损害赔偿,侵权损害赔偿只具有补偿性,不具有惩罚性[5],因此惩罚性赔偿在欧洲并不具有普适性。只要权利所受到的损害得以填平,侵权法即可退出舞台,不再发挥作用。
第二,侵权法所体现的“矫正正义”自身将权利与损害相等同。权利的完整性与权利的消极形态即损害相关,其直接体现的是具体个案中权利对于权利人的消极价值。法律不应当考虑到积极的价值,即权利人不能基于被告因侵权行为而获得的利益提出赔偿,两者没有相关性[3]120-151。
(二)获益赔偿性质通说的质疑
获益赔偿与损害赔偿的补偿性理念并不一致。换言之,损害赔偿的理念并不能解释获益赔偿的正当性及存在,因为:
第一,损害赔偿是以权利人为出发点,而获益赔偿则是以加害人或侵权人为出发点的。两者具有显而易见的根本差异;
第二,损害赔偿着力于对权利人损害的补偿,而获益赔偿则着力于对加害人的利益剥夺。两者的基点正好相反;
第三,简单地将“获益赔偿”作为损害赔偿的一种计算方式,或者为了预防如上的冲突而将“获益”“拟制”为“损害”,并进而使获益赔偿纳入在损害赔偿的框架内[6],值得商榷。前一做法已经逾越了损害赔偿的语义意旨,超越了补偿性概念的界限;后一做法虽然意识到获益赔偿与损害赔偿并不相同从而经由拟制而将“获益赔偿”转化为“损害赔偿”,但这却可能淹没“获益赔偿”的性质和功能,不利于司法适用;
第四,单纯因为知识产权为无形权利,权利人的权利一旦被侵害,其损害难以证明作为获益赔偿的权宜之计,也并不合适。这是因为:一是该理由很难有正当性,其并没有说明获益赔偿的理论基础;二是根据损害赔偿的规则,损害难以证明或者没有损害时,应由权利人自己承受该负担或者法律只赋予名义损害赔偿,此时赋予获益赔偿似乎也不合乎其理念;三是在很多情况下,有形财产权受到侵害而损害难以证明也大量存在,但到目前为止,法律并没有赋予有形财产权被侵害时的获益赔偿,法律对无形财产权如此情有独钟好像并不符合“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的法治理念。
综上,知识产权侵权获益赔偿不能在补偿性“损害赔偿”的框架内得到适当解释。因此,在现行法的框架内只能被视为一个“例外”,但我们应当认真对待“例外”[7]。
(三)获益赔偿的性质及其解释
事实上,获益赔偿与损害赔偿不同,其具有独立的价值。获益赔偿的正当性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权利的完善保障。权利不仅仅表现为消极形态的损害,也表现为积极形态的获益。既有的矫正正义观只是将损害与权利相等同,有失偏颇。因为,无论是财产权(包括有形财产权和无形财产权)还是具有财产内容的人身权,权利的内容自身包含了权利人可以使用其来获得利益的能力。这是一个不容否认且应当受到尊重的客观现实。据日常经验,我们也可感受到,单纯的损害赔偿并不总能使权利人得到满足,为什么加害人可以从其侵犯权利中获得利益,而自己却仅仅因为损害不容易得到证明,法律却剥夺权利人利用其知识产权而获得利益的权利呢?因此,获益依然是权利的获益品行的衍生品。所以,获益赔偿较能够实现权利的完善保障[8]328。
第二,直接体现剥夺不当获利和行为威慑功能。任何人不能从自己的不当行为中获利,是一个古老的格言。美国版权法明确承认此点,美国众议院有关1976年版权法的报告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判给损害赔偿是补偿版权所有人因侵权而受到的损失,赋予利润所得是防止侵权人因违法行为而不当获利……”[9]。禁止不当行为是从侵权人角度出发的,其不应以权利人的损害为先决条件。权利人应当有权获得权利的所有衍生物。获益赔偿必然还具有防止不当得利,使侵权人无利可得。
在美国,对获益赔偿也有不同理解,“根据衡平原则,15U.S.C.A第1117条赋予商标所有人主张从被告商标侵权利润中获得赔偿的权利。法院对获益赔偿表达了不同观点。一些法院认为获益赔偿仅仅是一种赔偿商标持有人丧失的或转换的销售额。其他法院认为获益赔偿不是对商标持有人丧失的或转换的销售额的赔偿,而是作为一种被告不当得利的校正以及对未来行为的威慑”[10]。我国也有学者如此认为:“无过错的侵权人……如果从侵权行为中获得了利润,仍然应当承担将利润返还给著作权人的责任。否则无过错的侵权人就会从侵权行为中牟取利益,却使得受到损失的著作权人得不到任何补充,这人就会从侵权行为中牟取利益,却使得受到损失的著作权人得不到任何补偿,这是与民法的公平原则和著作权法的利益平衡理念相违背的。”[11]
知识产权侵权救济具有多元性,而绝对不仅仅是填补损害。“侵犯专利权救济的一个目标是为过去的侵权行为作出赔偿。设计用来完成该目标的救济就是金钱损害赔偿和利息。另外一个救济目标是阻止未来侵权。设计用来完成该目标的是禁令、惩罚性赔偿与律师费。”[12]128
因此,知识产权侵权中获益赔偿既能实现完善的权利保护,又能够剥夺不当利益,威慑未来侵权行为,具有独特的公平性。能够实现公平的赔偿方式自然毋庸“退居幕后”而理应“走向前台”。获益赔偿具有独立的地位,其性质就是获益赔偿。获益赔偿的这一定性对获益赔偿的立法模式选择和评判具有决定性意义。下面笔者将论述我国知识产权法中获益赔偿的两种立法模式及它们的优劣势。
二、补充式的立法模式
(一)补充式立法模式的含义
补充式立法模式是指,获益赔偿只是损害赔偿的替补,只有权利人无法证明损害或者损害难以确定时,法律才赋予权利人基于加害人获益的赔偿。如果权利人能够证明损害或者损害可确定的,其只能主张损害赔偿,获益赔偿并无适用空间。同时,该模式还意味着,如果权利人主张获益赔偿,而加害人能够证明实际损害或者损害确定时,加害人应可有权提出抗辩以否定权利人的获益赔偿。体现此立法模式的是著作权法和商标法的相关规定。《著作权法》第49条第1款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专利法》第65条第1款亦是这一思路。
当然,该模式也并非我国独有。在日本专利法中,如果侵权人的利润超过专利拥有人的实施专利的能力,如果侵权人证明由于其比专利拥有人更佳的管理和销售能力获得了更多的利润,或者如果他证明,由于其他市场上的其他竞争产品的有效性,专利产品的需求会转向其他除了侵权产品的其他相竞争的产品,本段(即获益赔偿——笔者注)就不适用[12]118。
(二)补充式立法模式的根据
《著作权》、《专利法》选择该立法模式不是偶然的,其真正的理论根据是传统的损害赔偿理念。无损害即无赔偿,损害是赔偿的界限,这是损害赔偿的应有之义。即使加害人利用该权利获得了超越损害的利益,权利人对该种利益并无法律上的请求权。但损害不能或不易证明时,如果恪守损害赔偿的理念,权利人则无实际的赔偿请求权,这是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结果,因为它挑战了法律所能容忍的正义底线。如有时有些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害无法计算或者难以计算,但的确存在加害人获益的情况。这是获益赔偿存在的客观基础。
(三)补充式立法模式的变种
《欧盟知识产权执法指令》第13条1(a)款要求成员国的司法机关在计算损害赔偿金数额时,应考虑所有适当的因素,如对权利受侵害一方造成的负面经济影响,包括利润损失,以及侵权者获得的利润,当然还包括由于侵权造成的对权利拥有人的非经济因素,如道德偏见等。该条虽然总体上确定的是损害赔偿而非获益赔偿。但该条与传统的损害赔偿有较大差别,体现为当事人的获益是损害赔偿计算中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尽管我们很难据此条文认为,权利受害方可直接主张获益赔偿,但是在较为极端的情况下,侵权人的获益应可作为权利主张损害赔偿的主要因素,此时损害赔偿也可能接近或等于获益赔偿。而且法院赋予赔偿时不仅考虑侵权行为人的主观状态,还考虑对知识产权侵权给知识产权人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其他因素,如声誉损失等。该指令所确立的损害赔偿实质上应当高于补偿式理念下的损害赔偿。
三、选择式的立法模式
(一)选择式的立法模式的含义
在该模式下,权利人有权选择以权利人的损害抑或加害人的获益作为赔偿的标的。获益赔偿不以权利人的损害不能确定或难以确定为前提。只要能够证明侵权人获得了收益,权利人即可主张获益赔偿。商标法的相关规定体现了此种立法模式。《商标法》第56条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和“商标法”也采取此种模式。
(二)选择式的立法模式的根据
该模式虽与补充式立法模式不同,但依学界通说,其根据与补充式立法模式的根据完全相同,即获益赔偿是损害赔偿的一种计算方式[8]328。但到目前为止,立法材料和其他学说都没有解释:商标侵权赔偿与著作权、专利权侵权赔偿理念相同,而它们的立法模式却如此不同。特别需要关注的是,2008年的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将2000年专利法第二次修改时获益赔偿的选择式模式改为补充式模式。从此变化过程,我们可探知立法机构背后的一些隐喻。
专利法第二次修订增加《专利法》第60条的根据是: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是专利侵权行为人应当承担的主要民事责任之一,应当贯彻公正原则,使专利权人因侵权行为受到的实际损失能够得到合理赔偿[13]33。按照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的一般适用原则,损害赔偿额的计算通常是以权利人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为标准[13]59。
而第三次将选择模式改为补充模式的理由是:根据本次修改前的《专利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专利侵权赔偿额可以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确定,也可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在两种方式之间没有先后顺序。从实践来看,权利人往往会根据实际案情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主张权利。按照民事侵权赔偿的一般原理,对民事侵权行为首先应当以权利人受到的实际损失作为确定赔偿额的依据,只有在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才应当按照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确定。因此,本次修改根据这一原理,明确规定专利侵权赔偿额首先应当以权利人受到的实际损失来确定,只有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才按照侵权人获得的利益确定[14]。
这次解释有点匪夷所思,因为无论是第二次修改还是第三次修改,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理念并没有改变,都是要体现“填平原则”。如果获益赔偿只是损害赔偿的一种计算方式,选择式立法模式自然就是最佳选择,其自然可以根据哪种赔偿有利来选择,而第三次修改又否认了此点。立法机构作出此种改变的逻辑缺乏说服力。
(三)国际知识产权条约的做法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45条第2款规定:“司法当局还应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其他开支,其中可包括适当的律师费。在适当场合即使侵权人不知、或无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成员仍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其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该款与第1款并列,第2款的适用并不以第1款无法适用或者损害不能或难以确定为前提。侵权人当然有权选择主张损害赔偿抑或获益赔偿。该条约的主要目的在于对知识产权的全面保护。
(四)选择式立法模式的附属问题
如何计算是获益赔偿的主要难题之一,正是这一问题以及因果关系问题导致方斯沃斯(Farnsworth)否认合同法中的获益赔偿[15]。但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在实践中是可以解决的。其实,这个问题解决的难度可能也并不比损害赔偿的计算难度更高。立法或司法主要发展了如下三种制度克服获益赔偿的计算难题。第一是引入专家证人制度。如,若文件是比较复杂以至于只有金融和会计专业人员才能理解,专利持有人可以请求法院任命一个会计专家证人。如果法院肯定了该要求,侵权人有义务与其合作,如解释文件等。但就专利拥有人不能获得的利润,基于本段计算损害的标准就不能适用[16]118第二是在证明责任上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进。如在日本,“利润应当如何计算是有些争议的……由被告证明营业额不等于利润。换言之,一旦被告的营业额得以证明,此数字即被推定为利润的数额,除非被告作出相反证明。”[16]125第三是限缩可扣减的项目。在日本专利法上“最近的一个涉及软件侵权的司法判决只允许被告折扣可变的生产成本以及侵权产品的销售成本。”[16]125
四、获益赔偿立法模式选择的法理
知识产权侵权获益赔偿具有独立的地位,获益赔偿立法模式的选择必须有效体现此点。选择式立法模式显然是最佳的选择。笔者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此进行细化分析。
(一)两种模式优劣的分析
获益赔偿既能够实现权利的完善保护,又能够实现对侵权行为的威慑。就侵权行为而言,权利人的损害与侵权人的获益存在三种情况(不考虑损害和获益的证明):一是损害大于获益;二是损害等于获益;三是损害小于获益。
首先,在权利保护上,选择式立法模式优于补充式立法模式。
在补充式立法模式中,获益赔偿在第一、二种情况下无适用余地,因为权利人只有权主张损害赔偿而不能主张获益赔偿,而且权利人基于自己权利完善保护的需要也会主张损害赔偿。此时,法律只能实现损害赔偿的补偿性理念。在第三种情况下,获益赔偿才可能发挥作用,但在该模式下如果损害能够确定,获益赔偿依然不能适用。如,在一侵权行为中,权利人损害是300元,而侵权人获益是600元,权利人只能主张300元的损害赔偿。事实上,法律确定损害的规则和技术相对比较完善,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获益赔偿适用的可能性。另外,该模式同样赋予了侵权人的抗辩权。即使权利人认为其不能证明损害及其数额,而侵权人可依据法律规则确定损害并能够证明损害小于获益,获益赔偿依然不能适用。因此,该种立法模式在第三种情况下不能实现完善的权利保护以及经由不当获利的剥夺而威慑侵权行为。
在选择式的立法模式中,权利人可选择行使获益赔偿或损害赔偿。如果损害或获益均能证明,权利人在第一、二种情况下会主张损害赔偿,而在第三种情况下一般会主张获益赔偿。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很多情况下很难证明其受到的损害,尤其是实际损害。如著作权人的学术书稿未经同意被一出版商私自出版,除了直接侵犯著作权人的人格权之外,对很多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出版著作不仅不能获得经济利益,而且还必须向出版社交付“出版补贴”(一般在3~5万元之间),此种情形下,权利人很难证明自己因侵权人的行为所受的侵害。出版商是否可依其出版未给权利人造成损害为由进行抗辩从而否定获益赔偿的适用呢?在选择式的立法模式中,该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不能。但在补充式的立法模式中,侵权人的这一抗辩则是成立的。可见,选择式的立法模式更能实现权利的周延保护。
其次,在行为威慑上,选择式立法模式优于补充式立法模式。
就行为威慑而言,如果采用补充式的立法模式,在第三种情况下,根据现行法,著作权人或专利权人只能主张损害赔偿,而侵权人将有权保留余额(获益减去损害),这将不能消除侵权人进行侵权行为的经济激励,不能实现侵权责任法的威慑功能。而选择式的立法模式则可在相同情况下通过剥夺其余额进而降低或消除其从事侵权行为的激励,实现侵权责任法的威慑功能。
综上,两种立法模式在第一种、第二种情况下并无实质差别,而在第三种情况下,选择式立法模式相较补充式的立法模式有明显优势。
(二)慎重对待“推定”的立法技术
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推定是指基于已知或已证明的一个或一组事实,法律推论或者假设一个事实即存在。绝大多数推定是要求在既定案件中产生确定结果的证据规则,除非不利方以其他证据作出相反证明。推定将说服的规则转移给相对方,相对方可以推翻该推定[17]。
推定是法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主要解决的是证明困难问题。实践中,日本知识产权法即采用此种立法技术对待获益赔偿。《日本专利法》第102条第2款规定:“在专利权拥有人或排他性被授权人向明知或过失侵犯专利权或排他性授权的人主张赔偿时,如果专利拥有人或排他性被授权人能够获得任何利润,他的损害应被推定为等于侵权人的利润。”[16]116我国台湾地区商标法学术界也是如此理解的,如“商标法亦规定以侵权人因侵害行为所得之利益,推定为侵害商标权所生之损害。”[8]327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第114条第2款认为侵权人的利润是计算著作权人损害赔偿的一种方式。该规定允许法官推定,著作权所有人的损害额等于侵权人的获得。但该推定基于一个经验规则。如果侵权人证明,权利所有人的实际损害低于侵权人所获得的利润,该推定是可推翻的。
应当说,推定是一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的法律技术。就知识产权侵权而言,知识产权法之所以采取“推定”的技术,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损害赔偿的传统观念。如前所述,现代侵权法认为损害赔偿的观念是填补损害。权利人只有权主张基于其损害而非侵权人的获益而要求赔偿。
第二,获益赔偿无独立名分。如果获益赔偿具有独立地位,那就毋庸委身于损害赔偿。两者相结合,获益赔偿必须以“损害赔偿”的名义出现。在法律技术上实现此结果的就是:经由“推定”使两者在法律上等同。但此“推定”的立法技术有三点值得警醒:其一,如上所述,获益赔偿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功能已经超出了“损害赔偿”的范围;其二,该“推定”可能淹没获益赔偿的一般意义,使其只能成为应对某个具体问题的“应景之作”。其三,如前所述,获益赔偿具有独立性,不依附于损害赔偿,“推定”的立法技术解决了结果妥当性问题,但掩盖了更重要的问题,不足采。
五、结 语
获益赔偿目前只是得到了“个别化”“简单化”的对待,此种对待不仅反映在立法上,也反映在理论解释上。事实上,知识产权侵权中获益赔偿与损害赔偿并行,具有独立的地位。其最理想的立法模式为选择式而非补充式,未来的著作权法和商标法应当依照此模式进行修改。
[1]李明德,许 超.著作权法:第2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33-236.
[2]汤宗舜.专利法教程:第3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44.
[3]温里布.私法的理念[M].徐爱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Enest J.Weinrib.Punishment and Disgorgement as Contract Remedies[J].Chicago-Kent Law Review,2003(78):56.
[5]European Group on Tort Law.Principles of European Tort Law:Text and Commentary[M].Springer,2005:19.
[6]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339-340.
[7]申卫星.期待权基本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20.
[8]曾陈明汝.商标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9]李明德.美国版权法中的侵权与救济[M]∥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2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10.
[10]Paul Goldstein.Copyright,Patent,Trademark and Related State Doctrnines(Revised Fifth Edition)[M].New york:Foundation Press,2004:339.
[11]王 迁.知识产权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16.
[12]Donald S.Chisum,Craig Allen Hard,Herbert F.Schartz,Pauline Newman,F.Scott Kieff.Principles of Patent Law(Third Edition)[M].New york:Foundation Press,2004.
[13]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专利法第二次修改导读[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0.
[14]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导读[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0:82.
[15]E.Allan Farnsworth.Your Loss or My Gain?The Dilemma of the Disgorgement Principle in Breach of Contract[J].Yale Law Journal,1985(94):1343-1350.
[16]Hiroya Kawaguchi.The Essentials of Japanese Patent Law:Cases and Practice[M].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7.
[17]Bryan A.Garner.Black Law Dictionary(9th ed.)[M].Philadelphia:Thomson Reuters,2009:1223.
Research on the Choice of Legislative Model of Disgorgement of Infrin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N Liang-guo
(School of Law,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130012,Jilin,China)
Copyright Law,Trademark Law and Patent Law all regulate the system of disgorgement.Regular opinion thinks that disgorgement is only one kind of measure of compensation.In essence,disgorgement is different from the notion of compensation for damages,which serves the functions of protecting private rights,preventing unjust enrichment,deterring the potential tort,and thus has an independent role.As for disgorgement,current law has two models:supplementary and selective,the former regards that disgorgement is substitute measure of damages,while the latter regards that the victims should select to execute disgorgement or damages.International custom is to choose the selective model which has evident advances over supplementary model on protecting rights and deterring tort and exclude the legislative technique of presumption,so selective model should be preferred in the legisl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amages;disgorgement;legislative model;infrin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F523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1.06.014
2011-06-18
孙良国(1976- ),男,山东省菏泽市人,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法学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0CFX044)
(责任编辑 江海波)
——以《民法典》第1182条前半段规定为分析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