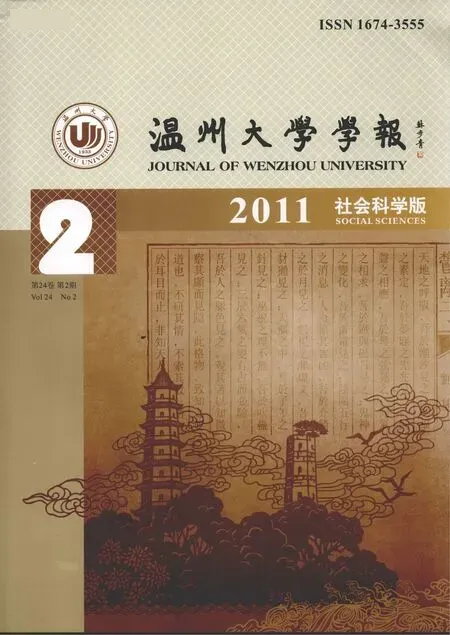影视民俗与中国文化认同
张举文,桑 俊(译)
(1.美国崴涞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美国萨勒莫 97301;2.长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荆州 434023)
影视民俗与中国文化认同
张举文1,桑 俊2(译)
(1.美国崴涞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美国萨勒莫 97301;2.长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荆州 434023)
中国民俗在第五代导演和海外华人导演的影片愈发流行的浪潮中已经显现为重要的媒介因素。这些影片不仅为揭示中国与中国人在新时代的变化提供了信息性和象征性的叙述,而且也为中国人与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的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民俗研究所关注的是民俗学者拍摄的纪录片或有关某些民俗活动的影片,使用的是“民俗电影”这样的术语。电影研究所感兴趣的是民俗在影片中的特定使用方法。尚待界定和研究的是那些只存在于影片中而不一定存在于实践的被创造的民俗。界定“影视民俗”为此类影片中的民俗或类似民俗。这些影视民俗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对中国人与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的建构与重建有着重大影响。
影视民俗;民俗影视(民俗电影);民俗学电影;第五代导演;散居民导演;文化认同
中国民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重构或强化中国文化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通过那些在西方较受欢迎的中国电影也可窥见一斑。尽管对那些反映中国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电影非常感兴趣,但除了一些电影评论外,人们却很难找到与电影中的中国民俗相关的任何资料,中文资料亦很少见①参见: 黄凤兰. 中国民俗影视[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4; 文献[1].。在中国,带有民俗内容的虚构电影(即故事片,fictional films)通常被叫做农村或乡土电影,而那些关于民俗的纪实风格的电影,则被称为记录片(documentary film),它们很少由民俗电影工作者制作而成。目前学界对这一领域非常感兴趣②参见: 黄凤兰. 中国民俗影视[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4; 邓启耀. 视觉表达[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但研究的重点主要还是电影中的民俗事件和民俗的电影表现形式,所使用的术语有如视觉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或影视民俗(或民俗影视,表现于摄影、电影和录像中的民俗)。带有民俗元素的虚构、非虚构电影与民俗电影工作者制作的电影之间的差异还有待区分。
但是,在国外,那些由第五代导演(他们主要毕业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和海外散居民(diaspora)导演所拍摄的带有独特的民俗元素的虚构电影却频频获奖。这些电影进入课堂,激起了人们对中国文化(旅游、商业和政治)的强烈兴趣,同时也为那些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些电影在国内外大受欢迎让民俗学家们开始思考:1)民俗学家应该怎样理解这些广受欢迎(和商业成功)的电影中的中国民俗的电影表现方式?2)除了保持传统,这些电影在建构和重构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3)在这些电影中,中国不同地区的民俗被部分地模仿和再发明,那么它们又给中国人或华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为回答以上这些问题,本文将着重探讨中国民俗的影视表现方式,这里我把它定义为“影视民俗(filmic folklore)”①译注: 这个术语中的“影视”是形容词, 指“影视中的”、“与影视有关的”. 有关民俗影视与影视民俗的概念界定,参见: 文献[2].。跟民俗电影(folklore film)相比,影视民俗是民俗的一个新分支,值得民俗研究和电影研究两方面的重视。我们应该从跨学科的角度来定义这种类型或形式,并建构一个理论体系以作长远研究。为了准确定义影视民俗,本文先回顾民俗和电影研究以及民俗或民俗学电影的理论发展过程。
一、民俗电影或民俗学电影
作为电影研究和民俗研究的一个类型,“有民俗的电影(folkloric film)”随着 1998年莎伦•谢尔曼的著作《记录我们自己》的发表而确立了民俗学学科的定义和研究方法。谢尔曼曾在1977年首次使用过“民俗电影”这个术语。以大量的民俗电影为佐证,该书不仅标明了民俗电影的学科范围,而且该定义也取代了含糊不清的“民俗电影(folklore film)”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民俗电影”这个术语可以上溯至 1934年,当年英国电影学院曾用这个术语来指称跟民俗相关的活动②参见1934年2月出版的Folklore第45卷第4期第290页.,以这个不太准确的定义来概括“跟民俗相关的非商业电影”。在美国,民俗文本的最早文献可以追溯到1935年[3]63。美国民俗刊物上对电影评论的最早称呼直到1974年才出现,杂志中的电影评论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民俗学家对电影的兴趣与日俱增”[3]288。坎宁汉姆写道:“所有的(民俗电影)都有意无意地被制片人、编辑或实地考察者进行了修改,这些人要么要呈现一定的艺术视角,要么要表现资料提供者的想法,要么要捍卫一定的理论立场。”[4]他又写道:“后来他们更是把民俗电影作为新出现的‘纪实电影学的一个亚类型’。”[5]同时,弗恩奇也提醒民俗电影不应该只是用来“强调某种刻板的观点——很显然,‘乡村的’、‘边缘的’和‘民众的’实际上就是同义词”,好的民俗电影应该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客观呈现”[6]。事实上,用先进的电影技术记录民俗或者从民俗学的观点出发把民俗电影当作文本来对待,一直以来就是民俗电影工作者和从事电影的民俗学家的主导思想和努力方向。
但是,谢尔曼对民俗电影的批评、审视采取了新的研究方法,她分析了“民俗电影制作者在电影技巧、主题或内容‘核心’等方面的处理关系”[7]xiv。谢尔曼从聚焦的内容和地点两方面区分了民俗影视与记录影片的特点,她分析了这两种风格的电影中电影工作者的作用,并强调民俗电影的目的“只是记录民俗”[3]63。当电影评论家和学者“坚称这些记录片加入了社会分析,而这些分析会引起社会变化”时,谢尔曼认为民俗电影(作为一种类型)不应该直接参与社会问题,她“希望观众能反视自己的生活,在银幕上找到相似的地方。……民俗电影将民间的活动与事件真实化,而观众再从画面上寻找自我的反射……,因此,民俗电影与录像为理解我们自己提供了一个阐释窗口”[3]260。这种有意义的研究方法把民俗影视作为一种类型来进行研究,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下,在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些影视所进行的阐释中,探讨了电影制作人、电影和观众三者之间互文的与语境的相互联系。对谢尔曼而言,民俗电影的主要目的就是记录我们自己或反映我们自己的生活(不管是从电影制作人的角度,还是从导演、编辑或观众的角度而言)。
“民俗电影”可能会让人产生疑惑和疑问。比如,它是关于民俗的电影?还是电影本身就是民俗,如家庭电影(录像)?为了全面支持谢尔曼的研究,琼斯提出了另一术语“民俗学电影”(folkloristic film)①参见: 文献[7].。2005年,他在私人通信中进一步解释“民俗学电影”不仅包含作为材料的民俗,同时它也遵循民俗学科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另外,琼斯认为,尽管谢尔曼使用了“民俗学电影”、“有民俗的电影”和“民俗电影”三个术语,但这三个术语基本都是指同一事项。和谢尔曼一样,他也分析了民俗学电影与其它类型电影的差异,特别是和人类学电影的异同[7]x:
正如谢尔曼表明的,这类电影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关注民俗,即那些在直接的互动场景中习得的、传授的、展示的或应用的,表现性或象征性的,并被视为传统的行为……当人类学电影倾向于关注非西方世界时,民俗学电影探索的是工业社会中的某群体网络和个体的传统,有时关注的甚至是与电影制作者有关系的某少数民族、宗教、职业,或特别兴趣群体。但更重要的是,电影制作者就所关心的问题而采用的理论观点将民俗学电影与其他任何类型电影都区别开来。
谢尔曼将民俗学电影与记录片、非虚构电影区分开来,她的这一贡献使民俗研究和电影研究都迈上了新的台阶。在民俗学电影研究的短暂历史中,第一步就是要确定电影中的传统元素和考察民俗学电影中民俗文本和语境的相互关系,这会引导人们审视记录在电影中的人们的传统行为方式,而以上这些内容在谢尔曼的书中都有所涉及。不幸的是,在电影研究中,特别是在记录片或非虚构电影中,民俗电影既没有被当作一种类型来进行研究,也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比如,在研究非虚构电影中的修辞和再现时②参见: Plantinga C. Rhetoric and Representation in Nonfiction Film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人们会定义新风格的纪录片,并从理论上对之进行说明,但却没有想到要对电影中的民俗进行探讨。事实上,大多数电影研究者都认为“电影艺术只有两个最主要的分支或形态,即虚构电影和纪实电影”[8]。
民俗学科不仅研究当前的社会和文化变化,而且它本身也在这种典型的跨学科的电影研究中得到了加强,这种电影研究包括记录与保存民俗内容和电影拍摄过程两方面。在回顾过去二十多年民俗学对通俗影视的研究时,寇文指出,“尽管不是民俗学研究的中心,但民俗学家却已经开始研究非记录片的通俗影视的各个方面。”[9]尽管事实上,在大众传媒(虚构电影和电视)的研究中,“寻找母题(motif-spotting)”已成为研究的主要方向。人们尝试运用民俗学的理论模式来研究电影和民俗,并运用民俗学的方法来研究“民俗电影”、“故事片”和故事片中对“大众化的民俗”的“独特改编”[10-11],以及性别角色的处理这些特殊事项[12]。除了研究这些已经呈现在电影中的“民俗”,民俗学家还对虚构电影中运用或创造民俗的意图和作用感兴趣。对那些不是用来记录民俗但却采用了民俗或类似民俗(folklore-like)或模仿民俗(mimic folklore)的元素的电影(比如虚构电影),我们该如何对待?对那些被电影制作者、导演或编剧为了增加噱头而不是为了反映民俗所拍摄的电影,民俗学家又该如何对待?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离不开民俗学电影的理论支撑。籍此思路,我在下文的探讨中认为,影视民俗作为在非民俗电影(如上文所定义)中出现的新现象,它值得民俗学家的研究,而且我还将从民俗学的视角出发,来集中探讨由中国第五代导演和海外华人导演所拍摄的这一类型电影的主要特征。
二、影视民俗
影视民俗,顾名思义,就是只存在于电影中的虚构的民俗,它是虚构电影中被再现、被创造、被混杂的民俗或类似民俗的一种表现。脱离了原先的(社会、历史、地理和文化的)语境,它的功能和民俗电影的功能基本相似。影视民俗强调或强化了某种固定思维(意思形态),它表明了某种生活方式被某族群所认同和拥有(当作“真理”)。影视民俗中的民俗以语言或非语言的形式出现,它可能是一个场景、一个动作、一个事件,或者一个故事情节。
影视民俗是新出现的民俗,它具有传统定义中的民俗的一切特征:它是再现[13],却是在非传统的环境中;它是表演①参见: Bauman R. 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 [M].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1977.,却是在非传统的语言或非语言的语境下;它是艺术交流,却是在非“传统的小团体中”[14],更不用说在这样的民俗表演中电影制作者的作用;而且,它是在非传统的社会中被制作和被传播的艺术、手工艺品及智力创作物[15]。总之,它是一种历史的工艺品(电影本身);是一种可以被描述和传播的存在体(通过电影技术媒介);是文化产品;是一种行为(用电影的形式)②参见: Georges F A, Jones M O. Folkloristics: An Introduction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但同时,它又是一种非历史的手工艺品(电影中的民俗元素);是一种无法描述和无法传播的存在体(对现实中的实践者和观众来说);它只生产影视民俗(或通俗文化),而不是正在传承的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一种非行为(跟事实行为比较而言)。
影视民俗不像“有民俗的电影”那样,反映的是某个时间、某个地点的文化和人物,但它作为一个文化体也同样是对民俗(或民俗性行为)的阐释。影视民俗的电影不以记录民俗为目的,而是通过电影媒介解构和重构民俗,以创造时间之外的时间。反过来,这样的影视民俗也影响了电影制作者、观众和那些实践者,而那些实践者的民俗只是被部分地(带着创造性地)展现给公众。因此,在群体和民族的层面上探讨影视民俗在建构文化认同中的作用是非常有意义的(下面我将要谈到)。比如,福特在他的电影中创造了“好莱坞印第安人”这样一个人为的虚假形象来代表美洲印第安人,而这却“经常让那些不知真相的观众得到错误印象”,把这种虚构的东西当作事实[16]。
通过影视民俗,描绘民俗这个手段本身也成为了民俗,因此,应给予民俗的三个组成部分(民,俗,以及通过媒介而形成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样的重视。跟民俗的传统概念不同,影视民俗利用镜头和屏幕,通过影视民俗的“文本”,建立起了电影制作者和观众(尽管有着不同的文化/语言背景)之间的联系。它用特殊的方式连接着过去和现在,并影响着将来。因此,影视民俗艺术交流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起新的文化认同。
三、影视民俗艺术交流的符号学阐释
影视民俗表明它是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下,为满足电影制作者和观众以及中国文化(就中国电影而言)的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的交流而发展起来的民俗。这种交流的需求在个人和民族的层面上都超过了我们已知的。第五代导演“彻底改革了中国的电影语言,并让中国电影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17]164,同时,海外华人散居民电影(diaspora film)已经“让中国电影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方向”[18]。更重要的是,这些都是对中国文化之根的反映。但这种交流如果脱离了全球化这个语境(跨国投资和发行)也将成为不可能。
通过电影这个媒介进行交流不仅是艺术的,也是文化的;换句话说,它是基本的文化价值观和信仰与新的文化价值观和信仰产生冲突的结果。电影的艺术观超越了那些形象(比如照片)所包含的直接或间接的各种含义。很明显,影视民俗把过去呈现给现在,呈现给将来,跟其它的文化形式一样。同样地,带有民俗的电影更像是记忆或想象,再现的是我们误认为是我们自己的民俗,而我们却无法与之沟通。这些电影可能会勾起我们的怀旧之情。带着这种怀旧之情,我们观看和辨认电影中的影视民俗,“在那个时代我们曾经活着;因为我们梦想我们能活下来——战胜挑战,解决质疑。”[19]我们也观看那些“负面的”或“奇异的”影视民俗或是虚构的民俗(比如,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足按摩或谢晋《鸦片战争》中男人像“猪尾巴似的辫子”),“我们认为我们观看的是过去的历史,它不会影响到现在的我们。”[19]
用民俗学的方法研究影视民俗,我们就能够辨认其中的新、旧民俗元素,而采用符号学的方法研究影视民俗,我们就能够辨析它们在表现那些含义不甚鲜明的民俗中的作用,这也就是巴尔特所声称的“第三意义”①参见: Barthes R. The Responsibility of Forms: Critical Essays on Music, Art, and Representation [M]. transl by Howard 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5.。事实上,影视民俗创造或重构了“意义之网”②参见: Geertz C.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并且给特定语境下某些团体所享有的文化注入了新的意义。在这种交流模式中,影视民俗常常成为阐释过去和反映将来的语境。而事实上,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将影视民俗只当作文本或语境,而应该像谢尔曼所做的那样③参见: 文献[3].,着眼于已记录在电影中的事件、相互关系和进程。
比如,在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的早期电影《黄土地》(这部电影与民俗学和民俗学家做田野调查有着极大关系,但它不是由民俗电影制作者制作的民俗电影)中,就有这样一个有意义的镜头,很多观众会认为这不过是真实场景的再现。镜头里,叫翠巧的女孩站在门前观看婚礼,后面的门框上贴着这样一幅旧春联:“三从四德”。在中国的新春,贴春联是一种民俗,但这里的“三从四德”却和民俗中往门框上贴一些吉利话语的行为不符。很显然,这是电影制作者的“解说”(voice-over)表达,目的是想通过这种日常行为让观众联想起传统中的消极因素。这里,民俗的形式依然存在,但内容却发生了变化,这样,观众就很容易联想到儒家对妇女的教条思想。这种影视民俗的表现方式是为了强调被改变了的传统。在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电影研究的中心主要是其政治和社会变革等方面④参见: 文献[18]; 文献[20]; Clark P. Chinese Cinema: Culture and Politics since 1949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Berry C. Chinese Cinema [R].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91; Cornelius S. New Chinese Cinema: Challenging Representations [M]. London: Wallflower Press, 2002; Berry C. Chinese Films in Focus: 25 New Takes [R].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2003.。只有在这种影视表达中,重要的第三意义或不明显的思想才能被揭示出来。
影视民俗的另一个例子是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而成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在这部电影中,有两处特别吸引观众却又倍受中国影评人批评的地方[21]:在妻妾的房间前面挂起红灯笼表明“男主人”将要恩宠她;并给这位将要被恩宠的女子进行性感的足按摩。这些场景没有中国民俗基础,在小说中也没有这样的描写,很显然这是电影制作者发明出来的。
中国民俗中,在房前或商业区挂红灯笼由来已久。红灯笼是吉祥的象征,在重要的节日,人们(无论贫、富)常常会在房前悬挂红灯笼,今天依然如此。在元宵节,人们更是广为庆祝。挂在餐厅门前的红、蓝灯笼或旗子标明餐厅的级别。挂在妓院门口写有名字的红(或其他颜色的)灯笼则是广告符号,今天在汉语中依然还有“红灯区”这个表达语。红灯笼的作用就是传达信息(日期或地点)和表达象征(在节日期间,追求好运和让各种邪灵、霉运远离居所)。很明显,这部电影也具有影视民俗意义。把妓院的标志性符号红灯笼转换成普通人家的红灯笼,影片所要表达的是社会和伦理道德的沦陷,这不仅表现在红灯区,也体现在富裕人家。把红灯笼从和庭院相连的大门外(日常行为)移到被恩宠女子的房间内外,揭示的是女子的命运依托于男人的喜好。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符号(有意识地或创造性地)再定位,把它转变成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在民俗行为中很难找到),影片让人们从新的视角重新思考所熟悉的民俗符号。
在中国文学和道家哲学中都有对性行为极丰富的描写,但在儒家思想主导的社会中,在公众场合悬挂任何跟性有关的标志都是不道德的,即使是在普通住宅的厅堂里,或是在不恰当的时间面对不合适的群体。但是影视民俗打破了时间、空间和对象的界限,它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让人们有意和无意地释放了心底的愿望。
再如,足按摩对中国观众来说都不陌生,它是传统的医学治疗手段:足按摩时的手势,小木锤发出有节奏的声音,人们所得到的身体享受,所有这一切都让那些曾经做过足按摩的人浮想联翩。更重要的是,《大红灯笼高高挂》采用蒙太奇手法表现出来的感官记忆打破了记忆与愿望(幻觉)的正常界限:足按摩,事实上在医疗诊所或公共浴室主要是针对男性,而在影片中,足按摩的对象却是妇女,而且是在卧室里。影片中所听到的小木锤的节奏声其实是按摩身体其它部位时所发出来的,而在这里却变成了足按摩时的声音(在妇女缠脚的时代不太可能有给女性足按摩这一行为)。观众很容易联系起足按摩后所熟悉的那种身体的满足感,而影片中足按摩的目的却是为了引起性欲。正是这种打破界限和重构民俗记忆刺激和引导了观众,让他们无法辨析哪些是“不完整”的记忆或幻觉,哪些是影视民俗。这种强加给“传统”中国人和社会的形象重铸和比照了正在重构中的新的文化认同。熟悉的变成了遥远的过去,记忆模糊的过去变成了熟悉的,虚构出来的得到了一致的认同,现实生活中的迷惑和抑郁通过熟悉的过去得到了释放。电影制作者的隐含意义即是对(本能的性)欲望的释放和(对传统伦理的)抵制。对这部影片和其它电影所采用的符号学的研究方法[22]与影视民俗一样是新的创造,尽管对它们的分析还不全是民俗学的。
影视民俗在最近由陈凯歌(如《无极》、《荆轲刺秦王》)和张艺谋(如《十面埋伏》、《英雄》)所拍摄的功夫电影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某种程度上,功夫片的流行应归因于李安《藏龙卧虎》的成功(此电影曾荣获多项奥斯卡奖)。
但是,在这种创造和运用影视民俗的潮流中,80和90年代的电影制作者越来越多地用大量浪漫的、充满商业气息的电影(某种意义上是跨国投资的)取代了严肃的社会和文化影片。这种转变可以部分地理解为用隐喻的、浪漫的手法来研究老问题,也可以部分地归因为第六代导演的崛起,他们将电影的重心由传统文化中的“寻根”转变为城乡小群体中的寻求个人认同(如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和《青红》)。对商业成功的憧憬也意味着更多的跨文化交流和更多地运用隐喻性的行为——功夫。再次,我们看到的是由电影制作者通过背景、场景甚至故事情节编造出来的影视民俗(如《英雄》就给“荆轲刺秦王”这个历史事件以不同的解释,如我下面将要谈到的)。功夫小说的流行和随后功夫电影的广受欢迎,这一切都证明了民俗的基本功能是娱乐。毕竟,“民俗揭示的是人类在现实中的挫折感和想要通过幻想逃离社会强加给他的各种约束的种种努力,不管这种约束是性欲的或是其它方面的”[23],这些都可以从功夫电影的狂热中看出来。通过这种熟悉的世界,电影制作者和观众可以像小群体那样地交流;他们发现了同一媒介,可以表达他们的渴望或沮丧。
正是这种在不熟悉的环境中对熟悉的符号的某种熟悉的使用方式,构成了通过影片来传播和转化民俗的影视民俗的特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影视民俗不仅被大多数观众想当然地信以为真,而且被当作怀旧之物给予欣赏。许多观众,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就把这种影视民俗当作是他们过去的个人记忆。反过来,这种被记忆的、虚构的传统也和他们的认同感联成一体。在这个意义上,影视民俗就是某种熟悉的东西。事实上,它的影响可能比那些流行的文化形式(比如“文化衫”)要深刻得多。
这些民俗的影视呈现,不管是长镜头、短镜头或是故事情节,都体现了我所称的影视民俗的特征。它实现了民俗的娱乐功能、社会仪式和伦理价值的强化功能、文化行为的稳定功能。影视民俗本身所提供的是其所基于的文化阐释,而不是解释,但对其它民俗形式而言,学者们提供的却是行为的阐释[24]。同样地,带有影视民俗的电影创造了民俗或文化之体,只不过这些民俗或文化还需要经过学术的检验。它建立起了传统和现代、局内人(中国人)和局外人(非中国人)的对话。它创造了电影制作者和他的观众之间、一种语言(或文化)和另一种语言(或文化)的观众之间的艺术的交流,但更重要的是,它展现、反映和折射出了那些把影视民俗作为娱乐和群体认同的一部分的人的传统行为。影视民俗在很多方面和通俗文化不同,但那是另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话题。不管怎样,它不停地影响着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影响着那些扎根于文化、表现其文化、表达文化认同的日常行为。
四、建构文化认同的影视民俗
民俗学家对文化认同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但认同这个概念却是20年之后才从个体认同、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等方面得到进一步辨析。就像欧林指出的[25]:“民俗这个术语的定义并不能提供与认同概念有关的一系列文化事件”,而且“当认同不再被用于过去时,它就被用来表达它自己,而民俗则被定义为美学上的交流。当认同被当作是一种想象的建构时,民俗学家就开始转向虚构认同的文化产品的丰硕果实”。影视民俗的出现很明显表明了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即新时代跨文化冲突中的中国文化认同问题。
但是,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不应该等同于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否则是很危险的归纳,因为“种族特点”不是一个自然的品质,它是政治和文化的建构[26]。由于这个原因,我在此探讨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借以区分中国国内(如“少数民族”电影)和国外(如美国的散居民或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
对中国人而言,只有当中国文化面临来自局外(在中国国内指汉民族文化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国外的挑战时,文化认同才会变得有意义。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的文化、传统或根基内部的混乱和缺点受到外部(欧洲)的威胁和挑战(在过去的2 500年中,中国一直处于或统一或分裂状态,但这都可以看作是内部冲突)。此时,文化认同感引起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反思和反抗,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20世纪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这种环境下,出现第五代导演的所谓“寻根”电影就毫不奇怪了,“寻根”电影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和“伤痕”文学而出现的。在传统价值和现代观念的冲突中,在中国(经济上贫困)和西方(经济上富裕)的冲突中,在个人愿望和社会(家庭)伦理道德的冲突中,以及在其它各种冲突中,中国人开始思考他们是谁,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他们自己的文化怎么影响着他们的认同。他们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认同。他们发现这种认同只能来源于传统,但传统却又包含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然后他们找到了影视这种可以挑战、探索、释放、满足和娱乐自己的表达方式。“一般来说,第五代导演所拍摄的电影故事的背景都是某个特定时期的中国农村,主要揭露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中的落后面”,可是“他们没能吸引中国的普通观众。”[17]64就像中国电影评论文章所说:“这些电影中的远离了现代文明的农村婚姻和家庭民俗不是民俗的记录,而是一种想象的民俗。这些电影中的民俗不是真的,而是一种策略,一种承载了许多复杂愿望的民俗幻想体。”[1]在这种“寻根”和认同过程中,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传达了“最原始的激情”和中国的文化认同[20],影视民俗成为“修订”传统或记忆以便建立新认同的工具。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最大程度上帮助建构了“第三影院(third cinema,跟传统的类型/风格和摄影技术相对照)”,而这有利于在全球化交流中中国文化认同的构建,也有利于认同的重构,同时也有利于散居民“第三文化(third culture)”的建立。
新认同来源于传统,也反映传统。传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可以归纳出以下这些特征:
(一)灵魂不灭
这是祖先崇拜和其它仪式中的万物有灵论和多神信仰行为。由于有这信仰,中国的祖先崇拜和血缘制度十分稳定。根据刘恒 1987年的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电影《菊豆》就是一部备受争议的电影,因为它表现了“商品崇拜”①参见: 文献[20].、性欲[27]和政治类比[28],但本质上却是通过结婚、取名、抚养孩子和丧礼等传统仪式行为的影视表演再现传统。有如葬礼上死者(名义上的)儿子骑在棺材上,这也是电影制作者的发明。实际上,这种仪式只在极个别的地方存在。但通过该电影,观众得到的印象是“中国传统”即如此。在这部影片中,文化符号超过了恪守传统的期望,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镜头,即一个小男孩坐在棺材上,棺材里躺着传统意义上的男人/丈夫,走在棺材下的是一对活着的夫妇(实际上是男孩的父母,名义上却是男孩的母亲和她的表兄)和被压迫的妇女/妻子和男人/父亲(一个倍受本能欲望折磨和被社会文化观念扭曲的象征性的男人),由他们来继续完成家族所制定的各种“家庭规则”。不管是电影制作者还是观众都希望暴露社会观念的黑暗面,而不只是再现真实的传统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提供了一个颠覆传统的阈限时刻。结果是,这样的影视民俗让观众反思中国的传统信仰。同样地,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也是一部反映现代社会中这种传统信仰的影片。
(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大一统的政治、伦理运用
陈凯歌的《边走边唱》、张艺谋的《活着》都表明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人只有遵循自然(字面义和比喻义)法则才能抵御灾难。根据莫言的小说改编而成的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运用影视民俗表达了追求民族、社会和人性和谐的愿望。比如,影片中有小孩子向酒桶中撒尿的镜头,这就是人的“精神”借助“酒”的比喻用法。这给观众提供了一定的心理基础,让他们接受民俗元素的影视转换,这样影视民俗才能具有另外一些社会和文化的含义。《十面埋伏》中影视民俗的例子是盲舞女随着豆子落地的声音用长袖击鼓这样一个镜头。这种异想天开的表演一般只在武侠小说和民间故事中才能见到。但在电影中,影视民俗综合了传统因素并转换了性别角色(见AT 575母题F 1021.1;AT 592;AT 1812;AT 879B)。同样地,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和张艺谋的《英雄》对同一历史事件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叙述方法,但都使用了影视民俗(比如,传统武侠故事中的幻想和忠诚忠贞的一贯行为)来体现当代的爱国情绪。
(三)趋吉避凶和入乡随俗
这已经成为日常民俗行为中中国文化认同的关键性标志:饮食、家庭情结、占卜和风水[29]。这些民俗和影视民俗在像《黄土地》这样的影片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现(比如,上文提到的春联和把一条木刻的鱼放在餐桌上作为富裕的象征)。散居民电影也很好地反映了这些民俗,如李安电影《喜宴》中,一个人的好运在于他的婚姻和子孙后代,当然也伴随着一系列的象征物和行为。这些民俗例子在其它电影中也表现得特别明显,如《推手》、《饮食男女》、《喜福会》和《浮生》。作为一种德行,这种追求好运的信仰表达的是既要适应他者又要维护自身利益的观念。在跨文化的语境下,受移民和种族观念的相互影响,重建文化认同的过程不仅漫长,而且充满挑战。
综上所述,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中的民俗就是一个在传统民俗元素和基本信仰基础上建构文化认同的过程。这个过程和民族特点、民族主义话语[30]、全球化和现代性的争论[31]、政治异己[32]等一样重要。每部影视民俗电影都有助于文化认同,因为影片中含有大量的中国歌谣和传统形象,这些都已经成为商业目标和部分通俗文化。总之,这些电影表现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独特气质,这有助于国内的中国人、国外的华人达成共识并进而宣传自己的群体认同。不管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的电影风格和主旋律如何变化,影视民俗已经扎根于文化交流,并且对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建构中国文化认同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五、结 论
本文在民俗学电影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民俗的影视表现形式和类似民俗这一鲜人问津的研究领域。通过中国电影和散居民电影,描述了影视民俗的基本特征。影视民俗作为一种新出现的民俗形式,它与民俗研究和电影研究密切相关并值得学者们进一步探讨。影视民俗的兴起是历史和社会的要求,它对重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以及全世界的华人散居民的文化认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影视民俗,尽管只存在于电影中,但它以和行为民俗相同的方式建构和阐释着文化认同,并带来了许多与之相关的新问题——“熟悉感”与“陌生感”、“归属感”与“异化感”。本文力图描述影视民俗现象,探讨影视作品中影视民俗的成文性(entextualization)、互文性和语境化,并建议跨学科研究者应该审视影视民俗在维护传统文化认同和建构新的文化认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1] 尹鸿. 论 90年代中国电影格局[C] // 郦苏元, 胡克, 杨远婴. 新中国电影 50年.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0: 323.
[2] 张举文. 影视民俗(filmic folklore) [J]. 民间文化论坛, 2005, (6): 104.
[3] Sherman S R. Documenting Ourselves: Film, Video, and Culture [M].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8.
[4] Cunningham K. Film Review of The Shakers by Tom Davenport and Frank Decola [J].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1977, 90: 122-123.
[5] Cunningham K. Film Review of On Being a Joines: A Life in the Brushy Mountains [J].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1983, 96: 123-125.
[6] Feintuch B. Film Review of Made in Mississippi: Black Folk Arts and Crafts by William Ferris [J].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977, 90: 252-253.
[7] Jones M O. Foreword [C] // Sherman S R. Documenting Ourselves: Film, Video, and Culture [M].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8.
[8] Cavell S. Words of Welcome [C] // Warren C. Beyond Document: Essays on Nonfiction Film. Hanover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6: xi.
[9] Koven M J. Folklore Studies and Popular Film and Televis ion: A Necessary Critical Survey [J].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2003, 116: 176-195.
[10] Sherman S R. Film, Folklore [C] // Green T A. Folklore: An Encyclopedia of Beliefs, Customs, Tales, Music, and Art.Santa Barbara: ABC-Clio, 1997: 307-316.
[11] Sherman S R. Film and Folklore [C] // Brunvand J H. American Folklore: An Encyclopedia. New York: Garland Pub,1996: 263-265.
[12] Koven M J. Feminist Folkloristics and Women’s Cinema: Towards a Methodology [J]. Literature Film Quarterly,1999, 27: 292-300.
[13] Abrahams R. Towards an Enactment-Centered Theory of Folklore [C] // Bascom W. Frontiers of Folklore. Colorado:Westview Press, 1977: 79-120.
[14] Ben-Amos D. Toward a Definition of Folklore in Context [J].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971, 84: 3-15.
[15] Oring E. The Arts, Artifacts, and Artifices of Identity [J].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994, 107: 211-233.
[16] Nolley K. The Representation of Conquest: John Ford and the Hollywood Indian, 1939-1964 [C] // Rollins P C,O’Connor J E. Hollywood’s Indian: The Portrayal of the Native American in Film.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8: 76.
[17] Zhang Y J, Xiao Z W. The Fifth Generation [C] // Zhang Y J, Xiao Z W.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Fil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18] Semsel G S. Chinese Film: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M].New York: Prageger, 1987: 14.
[19] Cantor J. Death and the Image [C] // Warren C. Beyond Document: Essays on Nonfiction Film. Hanover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6: 23.
[20] Chow R. Primitive Passions [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22.
[21] 戴晴. 《大红灯笼》吓人一跳[EB/OL]. [2005-04-20]. http://archives.end.org/HXWK/author/DAI-QING.
[22] Kong H. Symbolism through Zhang Yimou’s Subversive Lens in His Early Films [J]. Asian Cinema, 1996, 8:98-115.
[23] Bascom W. Four Functions of Folklore [J].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954, 67: 333-349.
[24] Oring E. Three Functions of Folklore: Traditional Functionalism as Explanation in Folkloristics [J].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976, 89: 67-80.
[25] Oring E. The Arts, Artifacts, and Artifices of Identity.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994, 107: 211-233.
[26] Bausinger H. Intercultural Demands and Cultural Identity [J]. Europaea (Journal of the Europeanists), 1977, Ⅲ-1:3-14.
[27] Cui S Q. Gendered Perspective [C] // Lu S. 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7: 303.
[28] Callahan W A. Gender, Ideology, Nation: Ju Dou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China. East-West Film Journal, 1993,7(1): 52-88.
[29] Li Y Y. Notions of Time, Space and Harmony in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C] // Huang C C, Zurcher E. Time and Space in Chinese Culture.Leiden: E J Brill, 1995: 383-398.
[30] Zhang Y J. From “Minority Film” to “ Majority Discourse”: Questions of Nationhood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Cinema [J]. Cinema Journal, 1997, 36(3): 73-90.
[31] Kang L. Is There an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The Debate about Modernity in China. Boundary,1996, 223: 193-218.
[32] Chen X M. The Mysterious Other: Postpolitics in Chinese Films [J]. Boundary, 1997, 224: 123-141.
Filmic Folklore and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ZHANG Juwen1, SANG Jun2(transl)
(1. Center for Asia Studies, Willamette University, Salem, USA 97301; 2.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China 434023)
Chinese folklore has become a key agent for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the films by the “fifth generation” directors in China and the diaspora Chinese filmmakers. These films have not only provided informational and symbolic narratives unveiling the changes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contributed enormously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and overseas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ies.However, folklore studie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documentary film by the folklorists or films focusing on certain folklore practice, using the term of “folklore film” or “folkloristic film”. Film studies have interest only in certain ways that folklore is used. What is left undefined and studied is the folklore that is created to exist only in film, but not necessarily in practice. The term of “filmic folklore” is defined to refer to such use of folklore or folklore-like materials in film which has great impact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and diaspora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globalizing world.
Filmic Folklore; Folklore Film; Folkloristic Film; Fifth Generation Director; Diaspora Director;Cultural Identity
(编辑:赵肖为)
K890
A
1674-3555(2011)02-0051-11
10.3875/j.issn.1674-3555.2011.02.010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2010-07-02
张举文(1963- ),男,山东莱州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散居民民俗,民俗与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