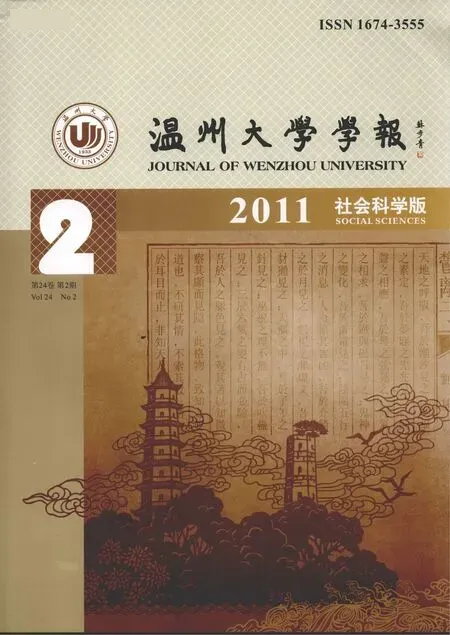咸丰三年钦天监教案考述
王 晓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咸丰三年钦天监教案考述
王 晓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传教士想利用科技达到其传教的目的,清廷对基督教传播的容忍却有限度。有清一朝发生在钦天监的教案共有三次。咸丰三年(1853)钦天监教案的发生不仅仅因为钦天监是西方传教士与清廷角逐的主要场所,还因为咸丰帝上台后内忧外患相交迭起。这次教案仅历经短短三天,并以较为温和的方式草草结案,其原因在于:无证据;钦天监不再是双方角逐的主要阵地;咸丰帝担心从严惩治会得罪西方传教士,不利于自己的统治。
咸丰三年;钦天监;教案;角逐
基督教入传中国,前后共有四次,“第一期是唐代的景教,第二时期是元朝的也里可温教,第三时期是明清的天主教,第四时期是清朝的耶稣教”[1]。如果前三次传播是正常的文化交融的话,那么第四次入传中国则夹杂了太多的武力征服。在正常的文化交融下,碰撞、摩擦已经在所难免,更不用说靠武力征服的文化入侵了。所以,自“南京教难”起,反洋教斗争就未曾停歇过,鸦片战争后,各地教案更是层出不穷。从鸦片战争至义和团运动期间,“仅就有传教士引起的大小教案”就“共达四百余起”[2]之多。有清一朝,仅发生在钦天监的教案就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发生在康熙五年(1666)的“康熙历狱”;第二次发生在道光十五、六年间(1835–1836),由监正敬征查办此事,后以跨越十字,出具甘结①十字即十字架. 据《圣经》言: 耶稣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 随之成为了基督教徒的信物. 在基督徒看来, 跨越十字架是对上帝的亵渎. 甘结是旧时交给官府的一种字据, 表示愿意承担某种义务或责任, 如不能履行甘愿受罚.,稽查备案了事。最后一次钦天监教案发生在咸丰三年(1853)。由于当时正值“多事之时”,为使“习教者知所儆惕,而亦可不致别酿事端”[3]139,此次教案的处理显得波澜不惊,在中外学者的私人著述里,这一案件难寻踪迹。笔者不揣浅陋,参阅相关资料,试图对这一案件做初步探讨。
一、钦天监成为传教士与清廷角逐的主要场所
钦天监,是研究天文历法的专门机构,自古以来在国家机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历代研究天文历法的机构的名称各不相同,直到明洪武三年(1370)才正式更名为“钦天监”。清代沿袭明制,仍称“钦天监”。
明万历年间,中国实行对西方传教士的开放政策,西方传教士开始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这些传教士大多受过西方高等教育,既是传教士,又是科学家,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天文历法学,因此,钦天监成了他们施展才华的最有利场所。偌大的中国,没有比钦天监更理想的位置了,既能发挥他们天文学之长,成为皇朝政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又能接近皇帝赢得皇帝的欢心,以保证中国教务的顺利进行[4]133-134。但对于传教士来说,科技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而对中国皇帝来说,科技是目的,容许他们传教则是手段。一方要传教,一方要科技,自汤若望“掌钦天监事”[5]10020后,双方的这种角力从来没有停止过。
由于钦天监的工作依赖于传教士,西洋传教士便利用其合法身份做掩护进行传教,这使钦天监成为双方角力的舞台。对传教士来说,利用科技保护传教是有效的,但不能肆无忌禅;对于中国皇帝来说,为科技容忍传教是可以的,但也不是没有限度[4]137。天文历法为国所急,而非帝所好[6],清朝统治者在给传教士搭建展示才华平台的同时,从未放松过对他们的控制。
顺治朝时,这种角力就已经开始。顺治七年(1650)清廷赐汤若望银两重建西洋堂,汤若望在《都门建堂碑记》中写道:“……蒙清朝特用西法,定造时宪新历,颁行历务……虔建天主新堂,昭明正教……。”①转引自: 张力, 刘鉴唐. 中国教案史[M]. 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56.可以看出,汤若望有意把治历与传教并提。对这位“玛法”的治历之能,顺治帝极为赏识,曾有言:“……尔汤若望来自西洋,精于象纬,闳通历法。徐光启特荐于朝,一时专家治历如魏文魁等实不及尔……”[5]10020,但对其天主教好像并不感冒,在《御制天主堂碑记》中有言:“夫朕所服膺者,尧、舜、周、孔之道……西译之书,天主之教,朕素未览阅……。”②转引自: 张力, 刘鉴唐. 中国教案史[M]. 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57.汤若望还时常借职务之便,向顺治帝劝教。对“玛法”的多方苦谏,顺治帝曾很无奈地说:“玛法,子之所为,令朕不解……朕若强子从朕,子能从乎?”③参见: [法]樊国梁. 燕京开教略[M]. 北京: 救世堂,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26.由此可见,顺治重视的是汤若望的天文历算之术,对其天主教并无兴趣。顺治出家便是一个极好的证明,虽然出家未遂,但由此可以看出他所钟情向往的是佛而非天主。但为了利用传教士的科技,顺治帝对其传教活动不得不给予一定程度的自由。汤若望时期,外省传教畅通无阻。中国的传教点已从利玛窦去世时的4个增长到28个,教徒从不到2 000人达到24万人[4]133。这不得不说是汤若望与顺治帝周旋的结果。
相比于顺治,康熙对科技的重视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曾一度任用钦天监传教士南怀仁、徐日升、安多和闵明我等给自己讲授科学。康熙帝在学习过程中孜孜不倦、坚忍不拔,曾因用功过度而吐血[7]。而这些传教士们也借谈论欧洲科技的机会“给他讲解基督教的主要教义”[8]232。传教士白晋在给法王的密信中说道:“……要在中国引入和传播基督教,宣传科学是一切必由之途中的最主要一种。到目前为止,上帝要所有的传教士都运用这种手段……。”[8]249传教士洪若翰在写给他教友的信中也曾有言:“我们在来中国之前所学得科学技能现在非常有用,因为这些科学技术就是康熙皇帝准许天主教公开传教的主因。”[4]137为了科技,康熙帝曾一度同意了传教士的恳求,以“适合福音传播”[8]229的方式颁布了传教自由敕令。所以康熙初年,天主教发展迅速,“全国信徒不下数十万人云”[9]。但晚年时候的“礼仪之争”使他改变了对天主教的看法,1719年在他写给传教士利国安的谕旨中说:“尔众西洋人……除会技艺的人留用外,余众西洋人务必逐回,断不姑息。”④转引自: 张力, 刘鉴唐. 中国教案史[M]. 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151.不难看出,康熙帝曾为科技容忍传教,即便是禁教后仍对有技艺在身的传教士深加优容。
天主教在中国所遭遇的困难,雍正帝时最甚。他在召见外国传教士时曾说:“先皇让尔等在各省建立教堂,亦有损圣誉。……朕岂能帮助尔等引入那种谴责中国教义之教义?岂能象他人一样让此种教义得以推广?”[10]不数年间,全国教堂几尽被毁,传教士五十多人悉遭驱逐,唯在京教士二十余人,以服务钦天监之故,得安然居留。雍正在《御制圣谕广训》中有言:“如西洋教宗天主,亦属不经,因其人通晓历法,故国家用之,尔等不可不知。”①转引自: 张力, 刘鉴唐. 中国教案史. 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186.这是允许少数传教士留在钦天监供职的确证,也是中国皇帝在角力中要科技而非传教的明证。
乾隆时,英国来使请求通商和自由传教,被乾隆帝回绝。在给来使的敕谕中有言:“……至于尔国所奉之天主教,原系西洋各国向奉之教……即在京当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与中国人民交结。妄行传教。……欲任听夷人传教,尤属不可……。”[11]嘉庆时期,除了个别精通历法之人仍留职钦天监外,其余之人“俱已饬令回国”,留京之人也只是“听其终老,不准擅出西洋堂,外人亦不得擅入”[12]。在嘉庆看来,天主教灭绝人伦,是为国家最大隐患,“比白莲教尤甚”[13]。可以看出,即使在“百年禁教”时期,为了科技,各帝王也不得不留任在京有技艺之人,只不过控制更加严密而已。
康熙晚年至嘉庆朝的教禁,似疾风骤雨,但天主教仍在暗中滋长。其主要原因是角逐双方各有所需,而己之所需正是彼之所有。清廷因重视西学,对在京任职传教士深加优容,禁教政策稍有松懈,传教士又可秘密传教于中国。钦天监既是西学东渐的主要阵地,又是传播天主教的主要阵地。因清廷重视西学,众多在京官员尤其是钦天监官生“随同西洋人学习算法”[3]137,一时所谓泰西文明竟成了一些士大夫的时髦学问,这些士大夫在潜移默化之下就会受到天主教思想的影响。道光六年(1826),清廷认为钦天监官生已经“深习西法”[5]10025,不必再用西洋人,遂裁撤了所有在钦天监任职的西洋传教士,结束了传教士在钦天监二百年的任职历史。自此,作为角斗场的钦天监淡出了历史的舞台,但传教士在此潜移默化二百年之久,其影响远不会那么快结束。道光十五、六年间的钦天监教案就是在这种影响下的一次余震,而咸丰三年的这次钦天监教案是这种影响下的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余震。
二、咸丰三年钦天监教案始末
此教案的发生源于一道密禀。咸丰三年三月十五日(1853年4月22日),钦天监五官司书王朝柱秘密地给定郡王载铨②载铨: 奕绍第一子, 嘉庆二十一年封二等辅国将军. 道光三年, 晋二等辅国将军. 十一年晋不入八分镇国公.十五年, 晋辅国公. 十六年, 袭定郡王. 二十六年, 任“兼管钦天监事物”. 咸丰三年, 加亲王衔. 四年, 薨, 追封亲王, 谥曰敏.上了一道禀文。禀文中提到了钦天监署比较敏感的话题——官员习教问题。对官员习教,清朝统治者采取了最为严厉的措施,在习教章程中就有规定:“营兵、衙役、书吏、一切在官人等及贡监职员,皆与平民不同。如有入教,应查照各定例治罪。”③转引自: 胡建华. 论咸丰朝的限教政策[J]. 近代史研究, 1990, (1): 66-83.所以,这道密禀也就成了这次教案发生的直接导火线。
五官司书王朝柱通过密禀,指控同在钦天监任职的监左贾洵、五官正方声龄和博士孙锦盛、王士芳等奉习天主教,现已“阖署皆知”[3]138。禀文当中,他还把清军的军事溃败与这件事联系起来,他认为“现在外省府城失守,多系奉习天主教人为内应”[3]138。他认为虽然自己职卑位薄,但稍有天良之人都不能容忍此情形,“消患于未萌”[3]138对京师守卫将大有裨益。这些话分量很重,因为咸丰帝一生中最主要的两个对手都和天主教有莫大关系。一边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殖民尖兵,一边是打着宗教旗号的农民运动。而咸丰三年正是太平天国迅猛发展、占领大半江南的时候。所以,这些话最能触动咸丰帝脆弱的神经。
载铨接到密禀,当天(十五日)便给咸丰帝上了奏折,并表明了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载铨认为:贾、方、孙、王四姓的上辈们“有自前明时即系入天主教者”[3]137,所以他们信教的可能性很大,虽然在道光十五、六年间敬征对钦天监所有官生进行过一次大排查,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情,但载铨认为“阳奉阴违,是所不免”[3]137。
咸丰帝很慎重地对待这个问题,密谕载铨“不动声色”、“严密确查”[3]138,一定要弄清楚贾洵等人是不是真的奉习天主教?王朝柱揭发他们是不是有真凭实据?还是王朝柱别有用心、栽赃陷害?
载铨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了调查。一方面,他将道光十五、六年间那次教案的原稿提出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当即,便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疑点。当时联名出具从未习教甘结的各官生,都“不肯代贾洵等出结”[3]139,这说明身边的同事对贾洵人等传习天主教已有所察觉。虽然当时贾洵等也同样出具了甘结,并有“不习教之语”,但是“阳改阴从,实难保其必无”[3]139。另一方面,他暗中走访了钦天监官生,其结果正如王朝柱所说“此四人暗中习教,实阖署满汉各官生之所共悉”[3]139。虽无真凭实据,但即可断定他们确已习教。至于王朝柱所说“闻逆匪胜举,欣欣然有喜色,闻逆匪败,于伊心有戚戚焉”[3]138之语,载铨认为并无确凿证据。对于王朝柱揭发此事是否别有用心、栽赃陷害一项,载铨“察其本意”觉得王朝柱并无其他用心,无非是想通过调查此案使那些习教者“知所敛迹”[3]139。对此习教之人,载铨认为不可不治,但亦不可重治,重治则“摇惑若辈之心”,不治则“不足服烦言之口”[3]139。应该“饬交刑部”,按照传习天主教之条例“讯明即可”[3]139。但咸丰帝认为现在正值京师严密稽查之时,把此案件交予刑部办理可能导致“外间传闻失实,转启浮言”[3]140。只是密令载铨把贾洵人等召集在一起,让他们跨越十字,出具甘结,备案了事。
十六日,载铨把贾洵一行十二人召至钦天监署中。由监正阎信芳当面看其跨越十字,并出具从未习教甘结。由于生病,载铨未能到场,第二天(十七日)载铨又把贾洵人等召集到自己家中进行了一番安抚,让他们“安分当差,不必心存疑虑”,皇帝天恩浩荡,“断不为浮言所惑”[3]141。贾洵等各官生也都匍匐在地、感激涕零。自此,这个教案以平静的方式了结。
三、咸丰三年钦天监教案原因及特点
此教案的发生有两点深层次的原因。第一,二百多年以来,钦天监一直是清廷和传教士角逐的主要场所。西方传教士在此潜移默化200年之久,早已有了“历史积淀”。虽然道光六年(1826)撤除了钦天监所有传教士的职务,但其影响绝不会那么快结束。道光十五、六年(1835–1836)间的那次钦天监教案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第二,咸丰帝一上台就面临内忧外患的尴尬局面。一边是西方列强加传教士,一边是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这时候的传教士不再考虑用科技去讨好清廷,而是用科技去逼迫清廷,其势更猛。而咸丰三年(1853)也正是太平军横扫大半江南、定都天京和南北对峙的时候。更让咸丰帝担心的是此时西方传教士对太平天国运动抱有很大的幻想,认为这是解决在华传教的最佳机会,一旦革命成功便是“大开海禁以便传教通商”[14]。清廷为了阻止西方传教士与太平天国之间的联系,限教政策执行得更加严厉。清政府一直以来严戒官员信教,借此纯洁官僚队伍,清廷决不允许在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任何离心因素。所以对于身处京城一直深受清廷重视的钦天监官员来说,这种政策的执行只会更严。基于以上两点原因,此次教案的发生在所难免。
但这次教案却大不同于以往教案,仅历经短短三天,并以较为温和的方式草草结案。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特征,分析其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无证据。这可能是最直接的原因。载铨所谓的“阳改阴从”只是推测而已,至于他们暗中习教“官生之所共悉”也只是言语相传,并无真凭实据。最后只能用“跨越十字,出具甘结”这种方法来检验他们是否习教。二,钦天监不再是双方角逐的主要阵地。道光六年,清廷裁撤了所有在钦天监任职的西洋传教士,作为角斗场的钦天监已淡出历史舞台。三,内忧外患的形势。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清廷已无力全面禁教,不得不转向限教政策,最大程度上减少来自基督教的不利影响。咸丰帝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为错综激荡。当他登上宝座的时候,清王朝已经饱受了鸦片的毒害和西方列强的冲击,丧失了主权和领土完整,又要面临着太平天国运动的挑战。内忧外患相交迭起。咸丰帝担心从严惩治会导致“外间传闻失实,转启浮言”的局面,从而得罪西方传教士,不利于自己的统治。
此教案虽小,但它却发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限教”到“容教”的过渡时期。咸丰八年(1858)《天津条约》签订,容教政策被塞进中外条款,规定中国官员对传习天主教之人不能有所“刻求”,“不得刻待禁阻”[15],习教之人“应与不习教者一体抚字”[16]。自此,传习天主教完全合法化,“角斗场”里再无“角斗”,此次教案也就成了最后一次钦天监教案。
四、结 语
传教士东来,其目的在于传教。这与清廷只重其技艺而非传教的态度在本质上有冲突。钦天监成了双方既斗争又融合的纽带。一边要禁教一边要传教这是斗争,一边要科技一边有科技又不得不融合。钦天监成了他们角力的最主要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一搭就是二百年之久。道光六年(1826)后,作为角斗场的钦天监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但它的影响绝不会停滞于此,短时间内消除200年的潜移默化谈何容易!咸丰三年的这次钦天监教案正是二百年“历史积淀”后的一次余震。此教案虽小,但透过它,我们照样能够窥见当时清廷的无奈和踌躇。
[1] 陈垣. 基督教入华史[C] // 陈垣. 陈垣学术论文集: 第1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93.
[2] 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136.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清末教案: 第1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4] 周宁. 大中华帝国[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4.
[5] 赵尔巽. 清史稿: 第 33 册[M]. 北京: 中华书局,·1977.
[6] 陈垣. 汤若望与木陈忞[C] // 陈垣. 陈垣学术论文集: 第1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504.
[7] 左步青. 康乾雍三帝评议[M].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1986: 213.
[8] [法]白晋. 康熙帝传[C]. 马绪祥, 译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 清史资料: 第 1辑.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9] [清]汪荣宝. 清史讲义选录[C] // 孔昭明. 台湾文献史料丛刊: 第4辑第78册. 台北: 台湾大通书局, 1984: 69.
[10] 杜文凯. 清代西人见闻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145.
[11] 中华书局. 清实录: 第27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87.
[12] 程宗裕. 教案奏议汇编[M]. 上海: 上海书局, 1901: 卷首1.
[13] 中华书局. 清实录: 第31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966.
[14] 彭泽益. 太平天国革命思潮[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 79.
[15] [清]贾桢. 筹办夷务始末: 咸丰朝: 第3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1016.
[16] [清]李刚己. 教务纪略[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6: 卷首4.
Investigation on Missionary Case Concerned with Imperial Office in Charge of Astronomy in Third Year of Xianfeng of Qing Dynasty
WANG Xiao
(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China 350007)
The missionaries would like to accomplish their mission by means of technology, while the Qing government could only tolerate the dissemination of Christianity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there were three missionary cases concerned with the Imperial Office in Charge of Astronomy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emergence of the missionary case in 1853, the third year of Xianfeng, was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essential role the Imperial Office in Charge of Astronomy acted i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the Qing government,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situation of internal disorder and foreign invasions following the Emperor Xianfeng’s ascending the throne. This case took only three days and ended mildly and hastily. The reasons were as follows: there was no evidence; the Imperial Office in Charge of Astronomy was no longer the important front for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to compete with the Qing government; the Emperor Xianfeng worried that the stern punishment would offend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it would do harm to his domination.
Third Year of Xianfeng; Imperial Office in Charge of Astronomy; Missionary Case; Competition
(编辑:朱青海)
B918
A
1674-3555(2011)02-0097-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1.02.017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2010-09-22
王晓(1984- ),男,河南平顶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闽台关系史、福建地方基督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