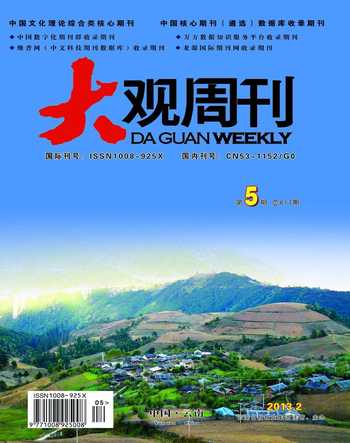李提摩太的教育传教理念及其实践
王京强
摘要:李提摩太通过介绍西方文化来影响和教育中国知识分子,在必要时,采用与中国的文化和宗教相妥协的传教方法,在山西大学堂的创建过程中得到了贯彻和实践。山西大学堂没有被建成一所教会大学,但李提摩太兴办新式学堂让晋省人接受近代教育的构想与实践,对于山西摆脱保守走向近代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李提摩太 教育 传教 山西大学堂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是近代来华著名传教士之一,在华长达45年之久,对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李提摩太在传教过程中是如何运用教育传教方式与近代西方教育理念指导山西大学堂创建的。
一
李提摩太于1870年到山东烟台、青州传播基督教。1876年至1879年间,因华北大旱,他携带12000两赈灾银在1877年从山东来到山西,先后在临汾、闻喜、洪洞、太原等地发放赈款,救济灾民,时人称之为“洋大人”。赈灾期间他在山西所到之处积极传教、介绍西方科技知识,还曾向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筌、张之洞提出修铁路、开矿产等治晋方略,1886年离开山西。1890年7月,应李鸿章之聘,他前往在天津任《时报》临时主笔,次年10月,到上海接替韦廉臣为广学会的督办(后改称总干事)。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他积极活动于上层人士之间,多次建议将中国置于英国“保护”之下,聘请外国人参加政府,企图影响中国政局的发展,结果均未能如愿。他主持广学会达25年之久,出版《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创刊40年间共出版2000种书籍和小册子,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1900年,他接受山西巡抚岑春煊邀请,重返山西解决教案问题,并参与创办山西大学堂,被聘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书斋总理,同时还主持上海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往来于上海与太原之间。清政府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1916年因病回国,1919年在伦敦逝世。
与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的传教方式类似,李提摩太也侧重于以介绍西方文化来影响和教育中国知识分子,在必要时,采取与中国文化和宗教相妥协的方式。但这并非是李提摩太有意模仿利玛窦,而是其在中国传教、赈灾游历过程中逐渐摸索形成的。在山东莱阳,李提摩太曾会见过两位佛教僧侣和一位学者,通过交流讨论,他觉得通过讲授自然哲学基本事实就可以引进比在中国占统治地位要好得多的宇宙知识。“这次出访及其相关的决定,标志着李提摩太事业的另一阶段。他已经看到,如果中国人享有更好的传授知识的条件,那对他们就是一大恩惠,他现在迈出了导致建立山西大学的第一步。”[1]39可以说这是李提摩太在传教过程中广泛接触各界人士,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以寻求有效途径的尝试。此后,在山西赈灾过程中,李提摩太认为“如果赈灾是耶教的任务,教育人们避免灾荒同样是而且是耶教更伟大的使命。如果把几千人从这场可怕的灾难中解救出来是好事的话,使数以百万计的人避免遭受这般惊慌就更加意义非凡。”[1]85 《李提摩太传》的作者苏慧廉为此这样评价道:“经过这场浩劫,他把‘教育这个词镌刻在自己的灵魂里。这个词成了他生命的基调”,决定其将来的传教工作主要应该走教育的路线,“与受教育的阶层广泛接触,因为他们接受事物快,而且是最能影响他人的阶层。”[1]86
李提摩太不仅仅停留于思考或自己的实践,而且还建议当时在华传教团体应该联合起来在中国18个省会,逐渐建立起高等学堂,希望能从此影响大清帝国的要员接受基督教,进而影响他们自己的同胞改变信仰。对于上层传教路线,他直言不讳的指出“我就是紧追上流人士不舍”[1]122。《英国周刊》对其与众不同的传教录像做了相关报道:“如果你抓住了上流人士,也就得到了其他人的支持。中国相对来说,是由少数人统治着——官员们和受过教育的阶层——人数约为10万。我们今天最大的需要,是派出称职的人员去引导,教育,这些正在思考的人士。当我们赢得了他们对基督的信任时,我们就赢得了全体民众”[1] 122。由此可以看出,李提摩太用教育笼络上层人士的路线,有意无意地符合了英国政府欲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思路,这也成为人们认为李提摩太是为英国侵略中国服务的主要依据。
从另一层面来看,李提摩太洞察中国社会的特点是相当透彻的。当时中国社会正是一个典型的士农工商的阶层社会,士高居于上,入者高居庙堂,成为辅佐君王的官僚阶层,退则为乡里士绅,领导县政权以下的地方社会。同时,他们担负着对地方教化保护的职责,如果能将这些人或其子女教化皈依基督,或至少学习近代知识文化,将会大有利于传教事业的展开。李提摩太的教育传教思路是为了与中国这一特色的社会阶层情况相契合,对这些人的笼络将影响整个社会的思想倾向。李提摩太对教育传教法进行着不断努力地思考、探索和完善。
二
李提摩太的教育传教法是从促成山西大学堂建立开始的。1900年,在全国义和团反洋教日趋高涨的形势下,山西发生了杀害传教士的教案,清政府派岑春煊接替毓贤任山西巡抚以图速结教案。面对联军兵压娘子关而山西又没有滞留的传教士能够帮助解决教案善后的情况,1901年4月,岑春煊致电在上海的李提摩太邀“请阁下来晋任委员之职,负责解决晋省教案與商务问题”[2]1,邀请其赴晋协助解决,这为曾在山西有过慈善和传教经验的李提摩太提供了教育传教的实践机会。李提摩太收到电文后很快接受了邀请,并向李鸿章递交了《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提出解决山西教案的七条意见。其中除了惩罚和赔款要求外,第三条指出“共罚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银五万两,以十年为止。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2]12其意在将“庚子赔款”用于学堂建设上。这个章程既可缓解西方列强给清政府施加的压力,也不致于使财源外流,还可推动地方教育的发展。综合评估利弊,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意按李提摩太的提议解决山西教案。李提摩太的教育传教法因解决教案方案的批准而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开始着手筹建大学堂。
在依据章程解决教案之后,双方就开办大学堂事宜展开谈判。岑春煊派洋务局候补知县周之骧赴沪与李提摩太商谈。周提出四个条件:一、晋省所出五十万两银不称罚款。二、西教士在校内不准宣传耶教。三、学堂不得与教会发生关系。四、西教士不得干预学堂行政。很明显,第一条只是措辞问题,容易解决;第二三条事关学堂性质,第四条关学堂主权归属。关于后三条较实质性的问题分岐使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李提摩太对此指出:“关于宗教自由的问题,中国在几个对外条约中都已表示同意。如果岑巡抚现在获得特别授权来更改并废除这些条约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讨论禁止讲授耶教教义这一规定了。”[1]215李提摩太的反驳很有力,显然作为已经形成的条约内容,一个地方巡抚当然无权更改了,中方只得不了了之。但是双方均不愿商谈破裂。在做出一定让步之后,周之骧与李提摩太在1901年11月签署了《晋省开办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该合同对中西大学堂诸如办学宗旨、款项来源、归属期限及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
然而,就在周李谈判之时,清政府推行新政之一部——兴学,“除京师大学堂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与省城均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3]P4719。山西省根据清政府兴学诏书,将省城原有令德堂与晋阳书院合并为山西大学堂。岑春煊积极筹备并制定出《大学堂规则》,规定大学堂分中西学八科,即德行、言语、政治、文学、法科、文科、格致科、医科,其中第四条规定:“各府厅州县学堂一时未能多得西师,无由广传西学,况堂内学生中学根底尚浅,亦未便骤令驰域外之观,只可先行严科中学,而以译介西书作为余课”[2]3。很明显在当时的条件下,新式学堂也只是贯行“中体西用”的实践所,并非以传授近代知识为目的。1902年2月,岑春煊《设立晋省大学堂谨拟暂行试办章程》上奏朝廷提出筹经费、建学舍、选生徒、定课程、议选举、习礼法六条意见。5月8日,光绪帝朱批云“选举一条著管学大臣议奏,余著拟办理”[4]7。不难想象,筹建山西大学堂很大程度上是山西官绅以既成事实来抵制正在谈判中的中西大学堂,存在着地方士绅与西方传教势力在大学堂问题上的博奕。
当李提摩太按上年签订的《晋省开办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于1902年5月带领新聘教习敦崇礼、新长富与华人教习以及仪器设备抵达太原后,发现晋省已成立了山西大学堂并开学上课。在这种情况下李提摩太认为若再办一所大学堂会增加晋省人的抵触,且又增加经费,即向巡抚岑春煊提议将中西大学堂与已成立的大学堂合并办理,名称仍为山西大学堂,但分为两部,一部即已成立的大学堂教授中学由华人主持;一部即将要开学的中西大学堂,教授西学由西人主持。这个提议首先得到冀宁道沈敦和的赞同,并为此起名中斋与西斋。鉴于当时意见不统一,岑春煊以归并与否询问当时大学堂已招学生108人,结果68人赞成,13人反对,其余弃权[2]8。岑春煊在与地方官员士绅反复商讨后,最终意见达成一致,同意将大学堂与中西大学堂合并办理。随之,《山西大学堂创办西斋合同二十三条》签署,同时原《晋省开办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即行作废。“二十三条”中值得注意的有第六条,西斋作为山西大学堂一专斋而具有“中国国家学堂”[2]12的性质,而减弱了其赔款意味。正是在这种“一校两制”的模式下山西大学堂初步开始运行。
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由于山西大学堂具有与西方传教士签订合同的特殊背景,也由于山西大学堂的科目设置基本符合了《章程》中关于大学堂设置标准的要求,所以,山西大学堂作为壬寅办学的唯一幸存者保留下来。1904年,山西大学堂新校舍建成,中西两斋师生整体迁入,新任学台(提学使)宝熙借此机会,对学堂进行了重大改革,特别是根据新学制的规定,对中斋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作了较大的调整,增设了英文、日文、法文、俄文、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博物、历史、地理、国文、图画、音乐和体操等许多新课程,旧课程除保留经学外,其他科目一律取消,并聘请了新教习分别承担新课程的教学,從而,促进中西两斋的融合,使两斋的教学科目和教学方法渐趋一致。至此,一体化的山西大学堂基本形成,并步入了良性发展的道路。
山西大学堂在中西两斋良性竞争融合下运营数年之后,根据二十三条合同之第三条“西学专斋经费除光绪二十七年付过银十万两外,光绪二十八年再付银十万两为开办经费,下余三十万两于光绪二十九年起每年付银五万两至光绪三十四年一律付清”[2]12的规定,李提摩太于1910年决定提前辞去总理职务,并将西斋管理权提前移交山西当局。因为他“深信近代教育已在全省深深扎根。”[2]12巡抚丁宝铨、咨议局议长梁善济接受其辞呈,西斋正式收回,归省办理。传教士影响一直到辛亥革命之后才逐渐退出。
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开办新式学校苦于缺乏教材,“二十三条合同”签订后.西学专斋首任总理李提摩太特从西斋每年经费中拨出10000两白银,在上海设立了山西大学堂译书院以解决教材问题。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初设于上海西华德路,后迁至江西路福慧里210号。最初译书院由李曼教授负责,后又聘英人窦乐安(John Dorroch)博士主持,其中英、日译员及校阅者前后l0余人。山西大学译书院自1902年设立至1908年因经费紧张停办,6年时间共翻译印行多种教科书,根据行龙先生的考证,译书院译书共23种25册[6](也许尚有遗漏者),其中如《迈尔通史》为1900年美国新版书,1902年即译出发行。《天文图志》1903年英文版出版,1906年即出中文译本。译书院的效率可见一斑。译书院的一些译本,民国以后,甚至到2O世纪40年代仍为同类图书中的佼佼者。山西大学堂译书院所译各类教科书,为当时许多大、中学堂所采用,对解决学堂燃眉之急的缺乏教科书问题确实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也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02年山西大学新共和学会出版的《新共和》刊物,其“发刊宣言中称译书院‘颇有贡献于当时的社会国家确非虚语往事如烟” [6]。这些译著便利了当时学术文化交流,倾注了李提摩太的大量心血。
三
作为一名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在华所为无疑是有着政治目的的,其用西方近代文化知识冲击封建顽固思想,使培养的学生对外国在华势力产生认同、助力英帝侵华,但从客观上看,李提摩太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不可小觑。“西斋取得的成就,当时在中国,是无可匹敌的。招收举人、秀才为学子,从ABCD学起,从加减乘除学起,经过七年学习毕业之后,就掌握了他们各自所学的学科,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办学步骤。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其他大学做得到。”[1]224
不仅如此,李提摩太在山西兴办教育客观上推动了山西逐渐摆脱封闭走向近代,当时的《华北先驱报》有文:“从教育方面而言,山西是中国最为先进的省份……在山西50%的乡村都有小学,所有男孩和决大多数女孩都有机会接受近代教育”[1]225。同一刊物上另一文章写到“全省各地,在官府衙门和学校里,都有山西大学堂的毕业生。山西省的警务督办和许多在任的地方官员都是大学堂的毕业生,这些人全力支持巡抚进行改革。无庸讳言,没有他们的精神支持,巡抚将很难推行他的计划。因此,将近二十年后,李提摩太博士的远见卓识正在得到实践的印证。”[1]225
参考文献:
[1]苏慧廉.李提摩太传[M].香港:世华天地出版社,2002.
[2]山西大学百年纪事委员会.山西大学百年纪事[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z]卷169 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4]清实录 德宗实录[Z] 卷498.
[5]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C](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6]行龙.山西大学校史三题[N].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7]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序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