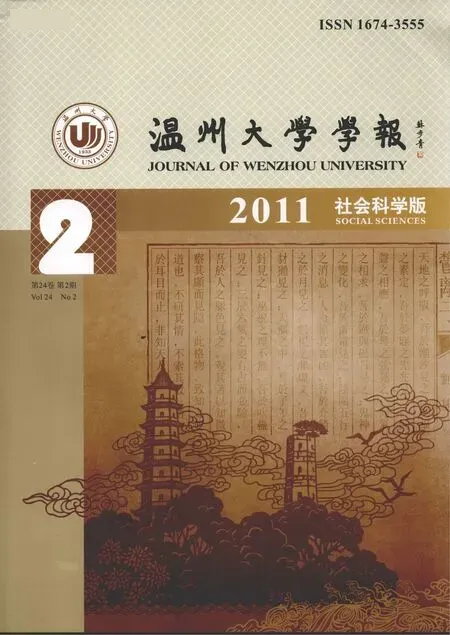民俗研究与翻译研究
利·哈林,杨 柳(译),张举文(校)
(1.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美国纽约 11210;2.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3.崴涞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美国萨勒莫 97301)
民俗研究与翻译研究
利·哈林1,杨 柳2(译),张举文3(校)
(1.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美国纽约 11210;2.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3.崴涞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美国萨勒莫 97301)
每个民俗学学者必须了解自己的学科有多少经典或创新著作是翻译的结果,尽管这个问题常常被隐含了。民俗研究同时也是翻译研究,因为两个领域近年来愈发成熟和关系密切。无论是跨文化或语言研究还是对文化研究都离不开文本的翻译。这种翻译不仅能提供文本,同时也能在研究新的文化时促进文化协商。民俗学者必须面对民俗与翻译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因此,可以通过回顾历史归纳出民俗与翻译研究的四个挑战。
民俗研究;翻译研究;文化混合;文化协商;民俗文本
近期受邀参加一次有关亚洲与美国亚裔族群民俗研究的会议。虽然对此并无太多建树,我却认为这类研究中普遍存在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翻译问题。35年来,我致力于将西南印度洋五大岛群——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留尼汪、塞舌尔和科摩洛的民间故事译成英文。不可避免地,我在一些翻译中加入了评论以帮助英语读者理解异域民俗。我首先努力证明了民俗学是一扇必要的而且是令人心动的窗户。通过它可以感受这些拥有共同的被殖民统治、被奴役和被剥削的历史的地方的文化、历史与价值观。而这些岛屿的核心文化都有其非洲源头。另外,虽然居于世界一隅,我一直非常支持 21世纪人类文明的一项伟大发现:从古至今,人们不断地调整自身的文化去适应语言融合和种族交融趋势。克里奥尔语言学(Creole Linguistics)的发现将这种文化再协商称为:文化克里奥尔化(cultural creolization)[1]。文化克里奥尔化帮助人们辨别种族差异、语言差异和宗教差异。它也正是我们理解全球化概念的关键。数年来,我逐渐认识到,如果说民俗学是作为一种保持文化异质性和持续性的手段而存在的,那么对于其他民族民俗的研究就是源自一种求同存异的目的与希望。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民俗研究就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翻译行为。
异质性对于民俗学和翻译研究来说至关重要。美国诗人查尔斯·伯恩斯坦(Charles Bernstein)认为[2]:异质性就是使用所有我们所掌握的正式的书面词语去干预、激发、诱导、再思考以及选择阵营等社会动力的源泉;异质性对民俗学和翻译研究同样有益。一些学者通过翻译去处理这些异质性,另一些学者则选择对之进行民俗研究。两种方法都认为文化表述是传递不同价值观的有效手段。因此,由上一代德国民俗学家提出的“法尔肯施泰因法则”(Falkenstein Formula)获得了世界民俗学界的认同。该法则认为:民俗学这门学科是将“各种文化价值观(包括它们发生的动因及过程)以主位或客位的形式进行的一种传播,其目标在于帮助解决社会文化的诸多问题”[3]。翻译是文化产品及其所传达的价值观的传播技术之一,是民俗研究实际操作中的一个必须步骤。它对人类学亦是如此——一位著名人类学家这样写道:“文化分析的挑战在于发展翻译与转换的手段,以使不同利益、机遇、权力、需求、欲望和哲学视野之间的差异性清晰可辨。”[4]1
在过去的 40年里,世界上的(尤其是英美两国)民俗研究与翻译研究齐头并进,一同走向了成熟。民俗研究离开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结构主义而另辟蹊径走上了民族志学的道路。当“结构主义作为解释标准大行其道”[5]时,民俗学者选择为民众的权利说话,他们往往更愿意“在一种摆脱理论束缚的自由中去进行自己的研究,……我们最关注的当然是一些更有自主权的东西,例如流派和团体”[6]。最近学者关心的是观察和记录表演,他们将民俗定义成一种社交性的人际互动[7]。假设美国民俗学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的话,那么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等学者在德尔·海默思(Dell Hymes)语言人类学[8]理论基础上提炼出的表演理论就是一只强而有力的手。Richard Bauman称表演理论为美国民俗学者中的流行之法[9]。
同一时期,翻译研究也正在成熟。在回顾俄罗斯思想家与布拉格语言学派早期所做的开拓性贡献时,英国学者苏姗·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写道:“自20世纪60年代早期发生一些重大变化起,翻译研究开始探索新的领域,开始了与文体学、文学史、语言学、符号学与美学的诸多交叉研究。”[10]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撰写并主编了一些颇有影响的专著①参见: 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udie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Venuti L.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0.。这类成果的出版激发了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灵感,他们将2009年的会议(该会议汇聚了约一万名学者)主题设立为“翻译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任务”。随着民俗研究与翻译研究的成熟,二者均开始向一种能为他们的研究提供基本理论依据,亦能帮助理解这个异质性世界的理论进发。
此举的必要性直至20世纪80年代被文学评论家弗兰克·蓝崔卡(Frank Lentricchia)提出时才被人们注意。Lentricchia认为孤立的文学文本是不存在的,同样,民俗学也不存在任何一个孤立的民俗交往。相反,“各种潜在的无穷的模糊的包罗万象的互动关系网络”[5]始终存在着。Lentricchia的关系网络跳出了文学的范畴而进入一种更为广泛的世界,与同样是在80年代由人类学家阿琼·阿巴杜赖(Arjun Appadurai)提出的“文化流动”[11]的经典分类颇为相似。在对“全球化”概念所作的著名分析中,Arjun Appadurai提出了“全球文化流动的五个维度:(a)人种图景,(b)媒体图景,(c)科技图景,(d)金融图景,(e)意识形态图景”[11]。人种图景指移民、难民、游客、外来劳工与流放人员这类流动人群:人们从一地到另一地的不停迁移。媒体图景指图像和信息的传播。科技图景指科学技术的分配与分享。金融图景指全球性的资本流动。意识形态图景则是政治观念与价值观的散布。五种图景共同组成了文化协商的母源。这些术语对民俗研究与翻译研究都有直接的效用。
在Frank Lentricchia的文学理论中,他认为“这种互动的关系网络并不安全,因为它们受制于永不停止的语言能源的运动,”这种运动并不承认“个人的主体权力……”[5]。然而个人主体权力,以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争议不断的有关“社区”本质及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美国称之为民俗)保护中的地位等问题都是翻译的核心问题。最近出版的《非物质遗产》②参见: Smith L, Natsuko A. Intangible Heritage [M]. London: Routledge, 2009.一书中,多篇文章论及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各种概念及其历史。该书涉及观点既包含了原住民的亦采纳了欧洲人的。作者们就所有权提出了许多有待商榷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但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条文中难以找到答案,亦非任何一个签约国能够回答。
Frank Lentricchia不是同样描绘了民俗学和翻译研究两个学科的现状吗?民俗学正被不停地收缩与扩张着的充满活力的语言和文化影响着,翻译研究则在坚持着与个人主体权力的斗争。二者不可避免地产生交集。每一个民俗学者都应看到学科中有多少权威文本或新鲜思想是由翻译得来,是归功于幕后翻译者的。其中著名的例子便是匿名翻译的Claude Lévi-Strauss的《野性的思维》的英文译本。民俗学和翻译研究的交集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开始。在19世纪的民俗学界,德国浪漫主义流派对于翻译的热情就绝不亚于对他们对民俗的热情。对赫尔德(J. G. von Herder,1744–1803)而言,他对于回归“来源”的追求伴随着他对英语文学与古老风俗的开放态度。这两种热情都需要发展“文化习得”(Erweiterung)以及忠实(Treue)。对民俗的忠实意味着本真(Authentic)。这份自我要求也是格林兄弟(本文所提格林兄弟指的是《格林童话》的作者)宣布他们对资料提供者话语忠诚的原因。作为德国古典主义流派的代表,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对翻译的历史性理论提出了一些基本问题[12]41:为什么要翻译,如何翻译,什么应该被翻译。对德国浪漫主义而言,翻译与民俗都是“文化;结构”(Bildung)必需的媒介,它们是对“他异性(alterity of the world)的体会……”。设身处地,将自我定义为他者,就可以准确理解他者。所以德国诗人诺维利(Novails,1772–1801)坚信“今天德国的莎士比亚比英国的更好”①参见: 文献[12]: 105.。
作为两个学科领域,翻译研究和民俗研究已经发展并且成熟起来了。它们的先后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伟大翻译家里士曼•拉蒂莫尔(Richmond Lattimore,1906–1984,他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英文译本被数以千万的美国学生阅读)和著名民俗学家理查德·多尔逊(Richard Dorson,1916–1981,他为印第安大学的民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的预想。如果两个学科领域的发展意味着研究范围的扩大,那么遗憾地甚至无法避免地,将它们的界限划分得泾渭分明就意味着对二者的无知。二者间的联系是如此明显,因此是时候去纠正这种无知了。早已在欧美遭到诟病的格林兄弟对材料的改造和发挥引起了人们对翻译真实和“原生态”语言问题的关注②参见: Ellis J M. One Fairy Story Too Many: The Brothers Grimm and Their Tales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在美国,弗兰兹·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在其民俗学研究初期在笔译和口译方面就十分信赖他的特林吉特语顾问乔治·亨特(George Hunt,1854–1933)。这一点现在已经被每一名民俗学研究生知晓。在西非,奎西·扬卡(Kwesi Yankah)已经向我们证明了作为部落酋长的口和耳,部落发言人是如何翻译的③参见: Yankah K. Speaking for the Chief: Okyeame and the Politics of Akan Royal Oratory: African Systems of Thought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作为一个对过去的表演的重建感兴趣的民俗学家,我希望文本是清晰的,这样我就能辨识那些长期未被提及的资料提供者们的表演策略。但是已出版的文本往往并非如此。这也是为什么语言人类学家Dell Hymes要重新研究并翻译Franz Boas、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以及梅尔维尔·雅各布(Melville Jacobs)留下的文本的原因④参见: Hymes D. In Vain I Tried to Tell You: Essays in Native American Ethnopoetics [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1; Hymes D. Now I Know Only So Far: Essays in Ethnopoetics [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3.。人类学的发展亦有这样类似的阶段。迈克尔·M·J·菲舍(Michael M. J. Fischer)写道,“经典人种学……需要并正通过重新研究与资料整理进行着历史的重新语境化。”[4]3一些传统的民俗学研究也被重新给予了充分的研究,如对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Lord)的《故事歌手》的研究⑤参见: Foley J M. The Singer of Tales in Performance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和对阿诺德·范·根纳普(Arnold van Gennep)的《法国民间故事手册》的研究①参见: Belmont N. Arnold Van Gennep, the Creator of French Ethnography [M]. Coltman D, tran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Dell Hymes在对前人著作的重新研究与翻译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还有哪些材料可供历史重新语境化和重新翻译?过去的哪种民俗研究,在哪一种语言中,应在未来被重新研究?也许是亚历山大·汉格迪·克拉佩(Alexander Haggerty Krappe)的《民俗学科学》②参见: Krappe A H. The Science of Folk-Lore [M]. London: Methuen, 1930.,也许是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的《达荷美的叙事》③参见: Herskovits M J, Herskovits F S. Dahomean Narrative [M].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58.。对民俗学经典作品进行再翻译带来了不盲从于权威的效果:杰克·齐普斯(Jack Zipes)对《格林童话》的翻译④参见: Zipes J. The Complete Fairy Tales of the Brothers Grimm [M].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2.使玛格丽特·亨特(Margaret Hunt)的网上译本被淘汰。然而每个翻译者都要接受着民俗学界的一个共识,即他/她的译作不论长短都是一种异文。这是一个翻译界能够认同的民俗学理念。这两门备受威胁的边缘学科也因此能够理性地在策略上共同进退。
它们有如此多的相同之处。如果还把民俗学与翻译研究看成是薄弱学科,二者就已经在成就和研究价值方面取得了提高。这将使它们在高等院校中获得更多的重视。二者被忽视的老论调在被重弹:当翻译在文学研究中被忽视时,在素材和文体方面对文学、艺术和音乐提供大量帮助的民俗学也被忽视了(仅有文学历史学家提出过“小民俗,大文学”的说法)。然而最新的理论研究认为民俗研究与翻译研究“都有利于促进文化的创造性与社会性特点在发展中的对话”[13]。总而言之,所有的民俗都是翻译。只要一个民间故事或是俗语被从口头表演中记录下来,这个文本就是一种译文。如果调查人使用了另一种语言去记录,那么他/她就成为了一个翻译者。既然语言及其他任何一种书写系统都是一种异质体系,那么处理异质性的手段也就是翻译的手段了。并且,民俗的传播——我前面说过的文化产品的传播——其本身不就是一种翻译吗?例如民间故事的“灰姑娘”(Cinderella)一词,它是由欧洲传入马达加斯加及其他印度洋岛屿的,那些有着多重文化背景的故事讲述者会重新构建这个形象,听众亦会根据克里奥尔文化的特点在心中对之进行着转译[14]。克里奥尔社会的民间故事并不是凭空诞生的,它们是根据已有的主题创作出来的。当前我们对这些民间故事产生方式的了解是广义地理解创造性的关键。克里奥尔化过程本身就是各种翻译的过程,它现在正被许多民俗学者所关注和研究。1993年发表在《美国民俗学刊》上的一系列相关的专门文章,今年将进行更新后以书的形式出版。
美国民俗学者已经开始思考由翻译研究带来的挑战:若说翻译理论的时代已经到来,民俗学者会在这种理论化面前退缩吗?“民俗学者是否会继续将精力集中在进行实证研究并为传统艺术家们培养新的追随者上,还是会不顾相关同行的建议而转向‘宏大理论’的构建?”[13]翻译界提出的另一个挑战是如何传播民俗学的成果。在美国,民俗学被理解为一种交叉学科。交叉发生在人类学、文学研究、心理学及其他领域之间,但又并不要求民俗学者对这些学科有足够的精通。然而,这种学科交叉需要民俗学的概念与方法不断地被翻译,以为我们的同行所用。第三个挑战:有关写作者身份的本质我们现在究竟了解多少?什么是民俗作者,什么又是翻译作者?最后,第四个挑战是一个人类学问题⑤来自作者与Regina Bendix关于民俗学和翻译研究问题探讨的个人通信.:从各民族的历史上看,哪些文化实践事通过族群历史的翻译而延续的,而在当下这种翻译在起什么作用?民俗学用自己的历史与理论为翻译的不同形式提供了大量这种有效的方法。这两门同样备受威胁的边缘学科也就因此能够理性地在策略上共同进退。
[1] Haring L. Cultural Creolization [J]. Acta Ethnographica Hungarica, 2004, 49(1-2): 1-38.
[2] Bernstein C. A Poetics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97.
[3] Dow J R, Lixfeld H. German Volkskunde: A Decade of Theoretical Confrontation, Debate, and Reorientation:1967-1977 [C] // Dow J R, Lixfeld H. Folklore Studies in Transl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3.
[4] Fischer M M J. Anthropological Futures [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5] Lentricchia F. After the New Criticism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189.
[6] Noyes D. Humble Theory [J].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2007, 44(1): 37-43.
[7] Limón J E, Young M J. Frontiers, Settlements, and Development in Folklore Studies: 1972-1985 [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86, 15: 437-460.
[8] Hymes D. Introduction: Toward Ethn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 [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64, 66(6): 1-34.
[9] Bauman R. The Philology of the Vernacular [J].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2007, 45(1): 29-36.
[10] Bassnett S. Translation Studies [M]. London: Routledge, 2002: 14-16.
[11] Appadurai A.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33.
[12] Berman A.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Romantic Germany [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13] Roberts J W. Grand Theory, Nationalism, and American Folklore [J].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2008, 45(1):45-54.
[14] Haring L. Stars and Keys: Folktales and Creo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7: 265-271.
Folklore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LEE Haring1, YANG Liu2(transl), ZHANG Juwen3(rev)
(1. Brooklyn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New York, USA 11210;2.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3. Center for Asia Studies, Willamette University, Salem, USA 97301)
Every folklorist must know how many of the canonical or innovative texts of the discipline are the result of translations, which have often been hidden. Folklore studies are also translation studies because the two fields have grown closer and matured in recent years. Cross-cultural or linguistic studies or cultural studies are all based on translations of texts. Translations provide texts, but also facilitate cultural negotiation in dealing with new cultures. Folklorists must face the rising problems in both folklo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Thus,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four challenges by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this subject matter.
Folklore Studies; Translation Studies, Cultural Integration, Cultural Negotiation, Folklore Text
(编辑:周斌)
K890
A
1674-3555(2011)02-0031-05
10.3875/j.issn.1674-3555.2011.02.007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2010-10-08
利·哈林(1930- ),男,美国纽约人,名誉终身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民俗学,非洲民俗
book=35,ebook=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