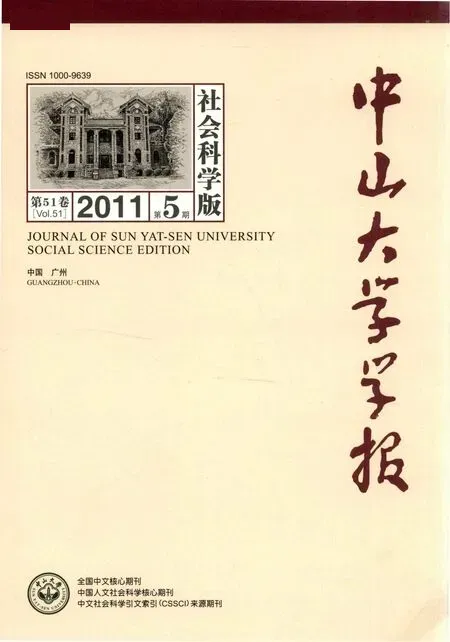20世纪汉语的言文一致问题商兑*
李春阳
一
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①《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57,556页。
这句话,出自鲁迅先生1934年题为《汉字和拉丁化》的文章,署名仲度,初刊于8月25日的《中华日报·动向》,后编入《花边文学》。上引文字而未加引号,试图凸显这两句话在今时语境下的荒诞感——“我们”与“汉字”,只能“牺牲”一端才得留存另一端么?
77年前,是哪一种势力迫使鲁迅写出这样的话:“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②《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57,556页。这等决绝的念头并不始于1934年。1919年鲁迅致许寿裳的信就说道:“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③《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7页。这不是鲁迅一人的想法,而是五四新文化一代人的共识。
1935年12月,上海中文拉丁化研究会发起,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陈望道、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发表宣言《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宣言说道:“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当初是在海参崴的华侨,制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实验结果很好。他们的经验学理的结晶,便是北方话新文字方案……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④蔡元培等:《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1949年,第120—125页。
与其说是新文字运动,不如说是某种隐藏其本来面目的政治运动。所谓新文字,这里指的是拉丁化的拼音文字,相对于国语罗马字,两派在实际的主张上,大同小异,但却弄到势不两立。唐兰在1949年出版的《中国文字学》中说:“民国二十三年跟着大众语运动而来的拉丁化新文字,是一种简单的粗糙的拼音文字,没有四声,所以应用时很不方便(孔子可以读成空子),他们虽然用来写方言,却不能和任何一种方言符合,虽然曾经热闹过一阵,现在似乎已无人提起了。”①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52页。
白话文运动在30年代告一段落,其信号,是大众语运动的兴起。二者的递进与终极目标,是言文一致。文言作为“文言一致”的障碍而被白话替代后,第二障碍即轮到汉字。大众语运动的归宿,一定是拼音化,只有拼音化,才能真正实现“言文一致”。鲁迅在《中国语文的新生》中有句很醒目的话:“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②《鲁迅全集》第6卷,第115页。后来拼音化终未实行,非不欲也,是不能也。
国语运动有两个口号,一是“统一国语”,一为“言文一致”。“言文一致”第一步是书面语去文言、用白话;第二步废除汉字、拼音化。“统一国语”即定北京话为全国通用的国语。在言文一致上,国罗派和拉丁派是一致的,言及“统一国语”分歧就大了。1949年后推广普通话,实际是国语统一的全盘实现,只不过把国语叫做普通话而已。拼音化在此后的三十年里,一直箭在弦上,却始终引而未发。批评汉字落后不易掌握,盲目向往拼音文字的所谓简便和一劳永逸的那套理论,并不复杂高深,但发表的文章数量之众,舆论之强,反对的声音始终不能也未敢发出来,事关民族文化未来,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却如大批判一样,已为最高权力机构的明令做好了准备。
而想知道超越审时度势之上的学术研究者的真正意见,就不得不到民国的别种及后来著述中去寻找。在1939年出版的《文字学概论》中,汪国镇虽承认中国言文分途在普及教育上或不如“西方文字以衍声为主,诚便于教育”,但中西历史和国情毕竟不同:中国领域广阔,方言杂处,“若开衍声之例,则各地不免以方音造字,势必方音不同,文字亦因之而变”;而中国“惟自古及今,各地均用同一之文字,是以语言方音,虽有楚夏之殊,而纸上所书,究无南北之别。故虽北极大漠,南抵儋耳,方音虽异,而文字则同”,其“团结民族,全赖乎此”。汪国镇的观点来自章太炎的相关意见,他们从“国家之统一,民族之团结者,正言文分途之功”来论述“中国言文分途之利益”,显示出与“大势所趋”的“言文一致”论所不同的问题意识③汪国镇:《文字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3页。。
二
若把言文问题进行古今语言转化,便是口语和书面语问题。郭锡良从语言学意义上,阐述了“言文不一致”的合理性。他认为口语和书面语是一种语言的两种变体,各有其特点,差异产生的原因在于,口语通过口耳相传,往往随口而出;书面语是让人阅读的,经过认真思考才写出。具体来说,口语是边想边说,可能有较多的省略,又可能出现一些罗嗦重复或者破碎的、不完整的句子;书面语是靠文字作媒介,用于传远传久的交际工具,没有口语所具有的辅助手段,但可以反复思考,仔细推敲,因此句子一般更加完整,结构更加严密,行文更加简洁。“总体来看,两者的关系只是加工和未加工的区别,就语言系统来说,应该是一致的。其差异主要是修辞表达、言语风格方面的,是属于语言系统之外的东西。所谓‘言文不一致’,不应该是指这种差异,而应该是指语言系统上的不同。”④郭锡良:《汉语史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07页。
就汉语的发展史而言,郭锡良认为书面语同口语自殷商至西汉是一致的。从东汉到唐末,是汉语书面语同口语相分离的一段时期。处于文学语言正统地位的是骈文、古文这种仿古的书面语;而不被当时重视的译经、变文、语录等用的则是一种文白夹杂的书面语。“宋代以后,汉语书面语存在三种情况:一是仿古的文言文,二是在当时口语基础上进行加工的古白话,三是继承唐代以前文白夹杂的混合语。”①郭锡良:《汉语史论集》,第617,616页。
这一结论得自不同时代的语料基础,或可商榷,但若持异议,需研究正反两面的史料据以申说。宋以后的三种情况,第二种指言文一致,胡适为白话文寻找历史根据,正在于此。然而五四白话文运动不过是扩大古代言文一致的份额,并非20世纪的新设想和新要求:“宋元以后整个语法系统已经同现代汉语相差不远,只有少数语法成分或句式衰亡了,五四以后新产生的语法成分或句式很少。所以王力先生用《红楼梦》作为撰写《中国现代语法》的资料,基本上已经够用。词汇方面差距较大,主要是五四前后新产生的词多,消亡的词是少数。”②郭锡良:《汉语史论集》,第617,616页。
曲解、夸大言文一致的内涵,有两种方式。一是强求书面语和口语绝对一致,这在实行上固然做不到,而且也不可能无必要;但“我手写我口”,“明白如话”,包括全民作诗,皆属于“文言一致”想当然的强行实践,晚清白话—五四白话—大众语—工农兵语言,是其形态的演变与极端化过程,一如白话越白越好成为白话文运动的逻辑推进,1950年代之后大量出现农民诗人、工人理论大批判小组即如是。另一方式是以口语强求文字与之一致。切音字—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拼音化,是其基本思路,概括来说,就是去汉字化。然而真正做到文言一致,方言亦须拼音,其后果是语言文字的分裂。语言文字既告分裂,国将不国,这在欧洲是有前例的。而五四英雄不以言文一致为满足,还进一步要求西式的“言文一致”,拼音化于是成了惟一出路。
为何第一种扩大仍嫌不足,还要推行第二种呢?这是一笔旧帐。辜正坤认为:文字一旦产生,会反作用于语言,造成音随字变,义随字生的格局,愈往后,文字的作用力愈强。他说:“文字本身的独立性要求语音的相应单一化,历经数千年的演化之后,这个过程终于完成,汉语的抗拼合或曰抗拼音体系终于完美无缺地建构起来。汉字之演变为拼音文字的可能性也就被彻底地粉碎了。汉语的演变也就从远古的语音制约汉字走到其反面:汉字制约语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视觉语言征服了听觉语言。”③辜正坤:《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6页。现在,语言的听觉功能试图颠倒主从关系,甚至要废除汉字。数千年来,汉语每一语音均被汉字塑造并规约,目不识丁者开口说话,汉字的规约性同步趋随。今天看来,鲁迅所说“我们倒应该以最大多数为根据,说中国现在等于并没有文字”④鲁迅:《中国语文的新生》,《鲁迅全集》第6卷,第114页。,表达的是道德义愤,而非科学判断。即便拼音强行取代汉字,语音中已然渗透的汉字的影响,也不可能消除。
简化汉字本应属于第一种思路的一个环节,简省汉字的笔画,目的在于文字的普及与大众化,间接地扩大书面语的流通范围,但仓促简化汉字却出于第二种考虑:既然改革终点是拼音化,汉字只是过渡性临时性的语言,不合理据似乎也无关紧要,以至未经周详考虑,条件欠完备时,就仓促实行,酿成无可挽回的后果。
综上所述,“言文一致问题”不仅是一个知识命题,也是一个权力命题,表面上是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关系,实际对应的恰是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深层涌动着民粹主义思潮,或曰大众崇拜。且看建国后历次运动,被整治清肃者无不是教授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民众结合,是惟一正当的出路,适可对应“言文一致”运动,换句话说,被语言革命所吞没者,正是早期语言革命的倡导者,知识分子在这场革命运动中,不仅要废除汉字,甚至还要消灭自我。
三
最早提出言文一致的人,是黄遵宪。他1887年完成的《日本国志》,最早将欧洲中世纪早期由拉丁语演成各民族语言、导致文学兴盛的历史经验介绍给国人,并指出西方各国以其母语翻译《新约》、《旧约》导致耶教流行,从中提取“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的主张。同时指出:中国文字“屡变其体”,其走势是“愈趋于简、愈趋于便”;中国“文体屡变”,其趋向是逐渐“明白晓畅,务期达意”;而“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黄遵宪梳理中国字体史的由繁到简和文体史之渐趋明白晓畅,其目的正是要推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今世文体。它是“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的“简易之法”①黄遵宪:《日本国志》,《黄遵宪全集》下卷,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420页。孙民乐认为这段文字至少包含了五项信息:跨文化视域,言文分离意识,借他者眼光而看到的母语的语言文字状况,对于语言和社会教育文化发展之关系的认识,潜在的对于语言改革的期待。参见孙民乐博士论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语言问题》(北京大学,1997年,未版)。。这种思路,也是当时把启蒙理想诉之于文字、文体革新的反映,并成为现代中国语文革新运动的参照——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都与这段文字关系密切。
其后《马氏文通》试从文言文范围更新读写的便易度,并未触及言文不一致的问题。马建忠说:“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马氏文通》于1898年出版,轰动一时,对后来的汉语研究,尤其是语法研究发生决定性作用。陈望道说他被人“忆了万万千,恨了万万千”,但马氏方案当时并未有助于汉语文言的读写问题。孙中山在1918年的看法,颇能说明问题。他认为《马氏文通》证明了“中国古人之文章,无不暗合于文法”,使中国学者知道了文法之学;但马氏之书及继马氏之后所出之文法书,“全引古人文章为证,而不及今时通用语言,仍非通晓作文者不能领略”,因此他进而希望:“吾国好学深思之士,广搜各国最近文法之书,择取精义,为一中国文法,以演明今日通用之言语,而改良之也。夫有文法以规正言语,使全国习为普通知识,则由言语以知文法,由文法而进窥古人之文章,则升堂入室,有如反掌,而言文一致,亦可由此而恢复也。”②孙中山:《建国方略·以作文为证》,《孙中山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29页。
孙中山以马建忠未竟之业而寄望于后来者,但他惟嘱目于语法的发明,在文字改革的大问题上还是保守的,不过他最后的几句话,将言文一致作为改良文法的目标,明确提了出来。持此目标,在《马氏文通》之后,激进主张随即跟进。最早的登场者是“切音文字运动”倡导者王炳耀等人③王炳耀,广东东莞人,著有《拼音字谱》;蔡锡勇,福建龙溪人,著有《传音快字》;卢戆章,福建同安人,著有《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中国新字》、《中华新字》等;沈学,江苏吴县人,著有《盛世元音》;劳乃宣,浙江桐乡人,著有《等韵一得》、《宁音谱》、《吴音谱》等;王照,河北宁河人,著有《官话合声字母》等。。他们主张用“切音文字”取代汉字,以利语言统一。1903年直隶大学堂学生何凤华上书袁世凯:“中国语言一事,文字一事,已一离而不可复合矣。更兼汉字四万余,无字母以统之,学之甚难,非家计富厚、天资聪颖之人,无从问津,此亿万众妇女与贫苦下等之人所由屏于教育之外,而国步所由愈趋愈下也。”他主张:“以语言代文字,以字母记语言。”《一目了然初阶》的作者卢戆章曾经说:“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之不富强也哉!”④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1页。这些晚清书生的主张,正与后来的五四精英相一致。
在论及统一汉语的重要性时,1920年蔡元培说过:“为什么要有国语?一是对于国外的防御,一是求国内的统一……国内的不统一,如省界,如南北的界,都是受方言的影响……言文不一致的流弊很多。”⑤蔡元培:《在国语讲习所演说词》,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26页。这段话把保存国族寄托于言文统一,或可视为“牺牲汉语还是牺牲我们”的温和版了。
四
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原教育部改称)正式公布由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等制定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31年,瞿秋白、吴玉章等在苏联设计的“拉丁化新文字”,可视作晚清切音文字运动的延续。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①1977年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决定,采取汉语拼音字母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即拉丁字母)拼写法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文献工作中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是这版本的副产品,正如炼丹术的副产品是为豆腐。自切音字运动始,其目标始终是代替汉字,而不是为汉字注音。
早在晚清切音字母尚未结果之时,一些留学生便开始呼吁废除汉语,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为首者吴稚晖,其刊物曰《新世纪》。反对者章太炎即于1908年作《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刘师培亦作《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二文均刊于《国粹学报》。章太炎早年从俞樾治小学和经学,于清代朴学大有造诣,自信“若乃究极语言,审定国音,整齐文字,仆于今世有一日之长,一饭之先焉”②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98页。。对“巴黎留学生相集作《新世纪》,谓中国当废汉文,而用万国新语”,章太炎著有专文驳诘,认为中西语言文字的“象形、合音之别,优劣所在,未可质言”。俄国使用的也是合音文字,其识字率却少于中国;日本使用混合文字,杂有汉字,日本人的识读并不怎样困难。开启民智,提高国人识字率,关键在于“强迫教育之有无”,“草木形类而难分,文字形殊而易别,然诸农圃,识草木必数百种,寻常杂字,足以明民共财者,亦不逾数百字耳。”③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94,594 页。道理说得扼要而浅明。
刘师培则认为“妄造音母”的“今人”,“若舍形存音,则数字一音之字,均昧其所指,较之日人创罗马音者,其识尤谬。知中国字音之不克行远,则知中国文字之足以行远者,惟恃字形。而字形足以行远之由,则以顾形思义,可以穷原始社会之形,足备社会学家所撷摘,非东方所克私。”④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第35页。其中“知中国字音之不克行远,则知中国文字之足以行远者”,已将“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的道理说尽了。陈寅恪更将每一汉字视为一部文化史,徐通锵则断言“认知语言学”的大本营是在中国,依据亦同⑤陈寅恪称赞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书:“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徐通锵语出氏著《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5页。。
章太炎对切音文字也有致命的批评。他说“切音文字”只能是注音符号,不能是一种文字。中国方言众多,若以某一方言作标准语,依其韵、纽制成“切音字母”而拼写汉语,大量方言势必消失。而汉语方言是中国文化的活化石,是大量古语、古训的坚实存证,文献的考证与阐释基于其上。而有汉字枢纽在,方言始得杂而不乱,“故非独他方字母不可用于域中,虽自取其纽韵之文,省减点画,以相拼切,其道犹困而难施。”⑥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94,594 页。
章太炎以上的意见当时并未遭遇反驳,甚至没有引起讨论,然而欧洲的一位语言学家,生前默默无闻,身后著作的影响却非太炎先生所可比拟——太炎先生东京讲学之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在巴黎授课。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于1963年由高名凯译成汉语,迟至1980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早在20世纪初,索绪尔所持的语言学观点就对中国的语言学发生了巨大的影响。索绪尔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他明确表述自己的理论“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型的体系”,然而不幸的是,这一理论被尊为汉语语言学的信条:“一个多世纪来,我们遵循口语至上的途径研究语言,将汉字和它所提供的信息完全排除出语言研究的范围,强使以视觉的文字为中心的研究传统转入‘视觉依附于听觉’的轨道。”①徐通锵:《语言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8页。
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后在东京公开讲学,内容三项:中国语言文字之原,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听讲弟子中,钱玄同、黄侃、朱希祖等为文字学家。但太炎先生的语言文字观却未能发生索绪尔式的影响,这与学问传播方式的差异有关。章太炎的方式是国中私人授徒传统,学问思想也被视为传统,虽有报章著述,然未能产生应有的影响。而偏信西方是当时国人的普遍心态,即使语言文字学,洋人的学说也被视为楷模。现代知识生产基本来自大学,而大学模仿西方的样子,普遍开设语言学课程,而将中国的小学束之高阁。
尤可叹者,是章太炎的主张正与晚清时势相悖,新兴知识群体的口语至上和民众崇拜,喧嚣声起,言文一致的深层语法与政治走向一拍即合。1949年唐兰出版《中国文字学》一书,结尾感慨道:“我们也明知道,合理的未必能行得通,通行的未必合理。”②唐兰:《中国文字学》,第155页。这一倾向在此书问世之后的数十年里愈演愈烈。
当年章太炎曾经慨叹:“以冠带之民,拨弃雅素,举文史学术之章章者,悉委而从他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语言文字亡,而性情节族灭,九服崩离,长为臧获,何远之有?”③章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另一位国粹派人物邓实,说得更分明:“故一国有一国之语言文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文存者,则其国存。语言文字者,国界种界之鸿沟,而保国保种之金城汤池也。”④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语言文字独立》;王玉华:《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56页。而在知识和潮流的蒙蔽下,五四一代爱国者及其后继者,竟然自毁长城而不自知。
五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有言:“中国之字无义不备,故极繁而条理不可及;外国之字无声不备,故极简而意义亦可得……然合音为字,其音不备,牵强为多,不如中国文字之美备。”⑤崔尔平:《广艺舟双楫注》,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第27页。且说汉语和汉字的复杂关系,是因欧陆拼音文字与其语言之对应,相形简便,近乎“言文一致”。上引康有为关于中西文字的比较之说,心态尚称平实,省察也颇公允,结句稍有自谀之嫌,无伤大雅,他在专论书法的论著中也略涉此议(贡布里希即曾比拟书法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相当于音乐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
汉语的言文不一致,不仅是文言文与口语的相异。周祖谟认为,汉字与汉语相联系有五种情况。第一,字和词不能完全相应。一个汉字代表或一音节,但有些不代表同一意思,也即并非独立的词。第二,汉字本身不能正确表示读音。除象形字、表意字外,形声字中也有相当数量不能正确地有读音显示,有的是造字之初声符近似,有的后来发生演变,还有一些字,非得靠文字学的专门知识才能辨读形声。第三,口语词未必有相应的字。方言土语的不少词句,往往说得出而无从写出,口说无碍,查无此字,以汉字记录口语,时常犯难。第四,同一词,古今字有不同,成了废字,词有定而字无定,音同字不同,汉字简化后而成多余的“繁体废字”,为数不少。第五,大量的同音字在应用时,必须随不同词语而变更。他认为说汉字就是汉语的书面化,是对错并存的粗略说法:“汉字是一种表意系统的文字,它虽然很早就走向表音的道路,想尽量跟语音结合,可是没有完全脱离表意的范畴,在形体上既要表音,又要表意,这就是汉字特有的一种性质。”①周祖谟:《汉字与汉语的关系》,鲁允中等编:《现代汉语资料选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4页。汉字的字形、字音、字义相矛盾,不是一种“错”,而是汉字系统的本来状态。
康有为说汉字重形轻声,是平实的归纳。汉语音节单纯,总音节数量少。21个声母,38个韵母,4个声调,声韵母构成有音有字的音节计有698个(声调不同的不在内)。少量语音变化不敷区别大量语音的变化,论文字三要素,字音、字义的数量差,有字形变化作为依据,求得平衡——正在这关口,汉语选择了“目视”。
所以当高本汉在《中国语与中国文》中认为“中国语是单音缀的”,唐兰不同意。他说:“这种错误是由于没有把‘字’(Character)和‘语’(Word)分析清楚的缘故。”他认为:“‘字’是书写的,一个中国字,是一个方块,也只代表一个音节。而‘语’是语言的,在语言里是一个不可分析的单位,写成文字时,有时可以只是一个字,但碰上双音节语或三音节语,就必须写两个或三个字。”②唐兰:《中国文字学》,第20页。与西方文字相比,汉语当然音节短,但这是汉语之错、汉语之短么?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赵元任甚至认为中国的“字”在表达上更有优势:
音节词(即我们所说的“字”)的单音节性好象会妨碍表达的伸缩性,但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反倒提供了更多的伸缩余地。我甚至猜想,媒介的这种可伸缩性已经影响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语言中有意义的单位的简练和整齐有助于把结构词和词组做成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乃至更多音节的方便好用的模式。我还斗胆设想,如果汉语的词象英语的词那样节奏不一,如male跟female(阳/阴),heaven跟 earth(天/地),rational跟 surd(有理数/无理数),汉语就不会有“阴阳”“乾坤”之类影响深远的概念。两个以上的音节虽然不象表对立两端的两个音节那样扮演无所不包的角色,但它们也形成一种易于在一个思维跨度中的方便的单位。我确确实实相信,“金木水火土”这些概念在汉人思维中所起的作用之所以要比西方相应的“火、气、水、土”(fire air water earth或pyr aer hydro ge)大得多,主要就是因为jīn-mù-shuǐ-huǒ-tǔ构成了一个更好用的节奏单位,因此也就更容易掌握。③赵元任:《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46—247页。
为照顾汉字形、音、义的三重分隔,汉语的累积过程于是不断创造形声字,汉字的数量,因此越来越多。《说文解字》9353字,据朱骏声统计,形声字8057个,约占80%,今时汉字90%以上属于形声字,但多数形声字并不能据其声符而确定读音。上文周祖谟所说第二条便是。形声字的构造方式是形(义)符加声符,理论上讲,形声字造字的最大数量=声符数×形(义)符数。汉语普通话共有约400个音节,汉字常用部首约200个,如若一个音节只选用一个汉字做声符,可造8万汉字。今天的汉字究竟多少?《康熙字典》4万,《中华大字典》4万8千。之所以未再增多,是今时造词多而造字少。两个或两个以上汉字构成一新词,词汇量于是增之无穷,今后恐怕还会不断增加,但未必需要造新字。
汉字数量的增多过程,历数千年。汉代应用文字一万馀,唐宋时期,韵书所收字数增一倍,明清增至四万以上,常用汉字六七千。劳乃宣所谓“中国文字奥博,字多至于数万,通儒不能偏识”④劳乃宣上西太后《普行简字以广教育折》,光绪三十四年(1908)。,夸大了识字的困难。汉语新词虽增之不已,其实是常用字的组合,词新而字旧。电脑通行后,大大方便了汉语新词的流布,拼音文字却无此便利。美国人统计,英语新词年增量近1000个,多为科技词汇,无论学习使用,是大负担,词典增补速度虽快,亦难追补。汉字总数庞大,但以六七千常用字新造词汇,应对裕如,远较英语便利。
又如汉字所有、西文所无的“别字”,徐通锵序潘文国《字本位与汉语研究》一书曾认为:“别字……使形、音、义三位分离,破坏了汉字作为‘第二语言’的身份,因而为汉语社团所拒绝。”“我们不允许或纠正学生写别字,实际上就是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第二语言’的训练,要求他们‘文’与‘言’一致。”①见潘文国:《字本位与汉语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究其实,据上下文正确用字,是汉语书写的常态。汉语多见音同字不同,消灭别字固然便于规范化,但由此形成汉语修辞的丰富手段之一:“双关”与“谐声”,如“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即或不会再显魅力。西人误解国人缺乏幽默感,其实同音异义的汉字中蕴嵌着无数诙谐之语(《笑林广记》专事辑录这类幽默),既经翻译,就在外语中漏失了,此为翻译永恒的困境。
徐通锵所说“言文一致”,与我们上文讨论的“言文一致”,并非一个意思。汉字从来不随语音,不便记录成口语。刘师培说“有音无字者几占其半”②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35页。,也许夸大了,但在方言土语里的确很多。拼音化主张即据此论证。
六
倪海曙在《旧文字的根本缺点》一文中说:“旧文字是以图画为基础的,不像拼音文字那样离不开说话和容易记录说话,因此它和说话的关系就不密切。话是这么说,文章可以那么写。它造成了文章和说话的分家,使民族的书面语言离开人民语言,使人民难于学习书面语言。”③倪海曙:《旧文字的根本缺点》,《语文知识》1954年第10期。中国文字在近古以后,几乎完全是形声字,“图画为基础”云云,实在是欺人之谈。和西语比较,汉字的确不直接记录口语,但只能说汉语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更复杂,却不能说它们没有关系。《说郛》卷7《轩渠录》载,北宋开封“有营妇,其夫出戍”,其子名窟赖儿,她“托一教学秀才写书寄夫云:窟赖儿娘传语窟赖儿爷,窟赖儿自爷去后,直是忔憎儿,每日根特特地笑,勃腾腾地跳。天色汪囊,不要吃温吞蠖讬底物事。”那秀才无法下笔成书,只好把已收下的费用退还给她。《轩渠录》还说到一位陈姓妇女寓居严州,几个儿子宦游未归,一天她的族侄陈大琮过严州,于是陈氏叫他代作书寄给儿子,口授云:“孩儿要劣妳子,又阅阅霍霍地。且买一柄小剪子来,要剪脚上骨茁儿、肐胝儿也。”大琮迟疑不能下笔,这位妇女讥笑说:“原来这厮儿也不识字。”④转引自徐时仪:《汉语白话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3页。在这两则故事中,营妇和陈姓妇女的口语,毕竟还是通过汉字记录了下来,只是一般秀才所识之字不敷应付罢。记录口语,从来不是书面语的发展方向,它有自己的表达习惯和传统。《红楼梦》将北京口语写得惟妙惟肖,但切不可认为那是对于作者听到的他人对话的记录。
在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看来,文字的功能是记录语言,属于符号的符号,自身没有独立价值。但即使是西方语言,其口语与文字也并不能完全一致。卢梭(J·J·Rousseau)就曾认为:“人们指望文字使语言固定(具有稳定性),但文字恰恰阉割了语言。文字不仅改变了语言的语词,而且改变了语言的灵魂。”在他看来,文字虽以精确性取代了表现力,但“言语传达情意,文字传达观念”,构成语言之灵气核心部分的声音、重音及其丰富变化却无法在文字中得到传达。即使以各种方式扩充书面语来补偿这些特质,但“当它们从书本再度进入口语时,口语则被削弱了。当说就像写一样时,说就是读”⑤[法]卢梭著,洪涛译:《论语言的起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页。。卢梭的见解日后启发了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他在《论文字学》中激烈批判西方语音中心主义。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也认为西方文化中拼音文字的胜利压抑了文字的多种可能性:“它们呈现为对思想意义的直接描述,它们在不同的语言中读法不一,这些文字展示了书写的一种普遍特征,这一特征在拼音文字里也存在,但由于依附于读音而往往被掩盖了。这一特征就是:不仅是记载体,而且是各种记号本身,其形体、位置、彼此间的距离、顺序、线性的安排等等。”⑥见潘文国:《字本位与汉语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
1944年,吕叔湘写成《文言和白话》,确认文字为一独立形象符号,因此“文字的起源大致和语言无关”。他同时又承认:“就现在世界上的语文而论,无一不是声音代表意义而文字代表声音。语言是直接的达意工具,而文字是间接的;语言是符号,文字是符号的符号。语言是主,文字是从。”①《吕叔湘文集》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73,452,76页。前面的结论,是由汉语汉字的具体情况而得出的,后边的话却是在重复索绪尔的观点。西方拼音文字的特殊规律被说成是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普通语言学教程》给中国语言学家的压力是巨大的。
考察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可分两面:中国文言文产生太早,延绵久长,至唐朝以降,白话文开始发育,而口语不可能自外于书面语影响,连西方人也注意到这种关系。利玛窦(Matteo Ricci)的看法是:“说起来很奇怪,尽管在写作时所用的文言和日常生活中的白话很不相同,但所用的字词却是两者通用的。因此两种形式的区别,完全是个风格和结构的问题。”②[意]利玛窦著,何济高、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徐时仪认为,东汉后的文言作品中已收入部分当时的口语,虽然刻意仿求古雅,但在或多或少吸纳当时口语的细微过程中,由先秦至唐宋的语言讯息得以透露,成为研究“古白话”形成的珍贵文本③参见徐时仪:《汉语白话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11页。。吕叔湘在《近代汉语读本》序中说:“事实是,语言总是渐变的,言文分歧是逐渐形成的,此其一;另一方面,言文开始分歧之后,书面语也不是铁板一块,在不同时期,用于不同场合,有完全用古代汉语的,有不同程度地搀和进去当时的口语的。”④《吕叔湘文集》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73,452,76页。在为江蓝生的《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一书所作的“序”中,吕叔湘进一步指出:“以语法和词汇而论,秦汉以前的是古代汉语,宋元以后的是近代汉语,这是没有问题的。从三国到唐末,这七百年该怎么划分?这个时期的口语肯定跟秦汉以前有很大差别,但是由于书面语的保守性,口语成分只能在这里那里露个一鳞半爪,要到晚唐五代才在传统文字之外另有口语成分占上风的文字出现。”“长时期的言文分离,给汉语史的分期造成一定的困难。因此,是不是可以设想,把汉语史分成三个部分:语音史,文言史,白话史?这样也许比较容易论述。文言由盛而衰,白话由微而显,二者在时间上有重叠,但是起讫不相同,分期自然也不能一致。”⑤吕叔湘:《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序”,北京:语文出版社,1988年,第1—2页。这是端正的科学态度。《汉语白话发展史》认为,文言与白话之分始于汉,汉至清两千年,汉语书面语有文有白,文白并存,初以文为主,后以白为主,直到五四白话文运动取代了文言⑥参见徐时仪:《 汉语白 话发展 史》,北京:北京 大学出 版社,2007年,第20,11页。。这种划分与本章开头所引郭锡良的意见,有相当的差距。
在《文言和白话》一文中,吕叔湘认为:每个时代的“笔语”和口语保持着或远或近,甚或大体符合的距离,依据“听得懂和听不懂”的界限,“我们可以用这个标准把一个时代的笔语(文字)分成两类,凡是读了出来其中所含的非口语成分不妨害当代的人听懂它的意思的,可以称为‘语体文’,越出这个界限的为‘超语体文’。”由此建构的“白话”和“文言”在“听”、“视”和“书写”方面的历史与现状,便一目了然了:
白话是唐宋以来的语体文。此外都是文言;其中有在唐以前可称为语体文的,也有含有近代以至现代还通用的成分的,但这些都不足以改变它的地位。白话是现代人可以用听觉去了解的,较早的白话也许需要一点特殊的学习;文言是现代人必须用视觉去了解的。⑦《吕叔湘文集》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73,452,76页。
语体文与超语体文,比文言与白话的界定更准确,更严格,但后者更流行,使用范围更大。事实上,在对文言与白话进行区分之时,“言文一致”的强大律令已经响彻其中。汉字和文言,实在是天然的一对儿。废文言,一定会导致废汉字,肯定汉字,也必然肯定文言。只要追求“言文一致”,就同时既否定了文言,也否定了汉字,那么就只有一条出路——拼音化。推广普通话却是实现拼音化的第一步,没有统一语音在先,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拼音文字。
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人全面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未来人才素质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学生正处在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生理与心理的发育发展,竞争压力的增大,社会阅历的扩展以及思维方式的变化,在学习、生活、人际交往、自我意识等方面可能会遇到各种心理问题,有的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的话将会对他们的身心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使他们出现严重的心理障碍或人格缺陷,故农村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谈到汉语言文关系时,有着权威的表述,对于汉语言文关系的判断,早已超出了学术的范围,而是一种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并为普通话合法性的建立梳理出汉字改革的三段历史道路:其一是古来就和口语直接相联系的书面语——白话——发展起来同“文言”分庭抗礼,构成我们现在民族共同语书面形式的主要源头;其二是宋、元以来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白话”文学作品高度发达,影响到非北方话区域,为北方话的推广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同时“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话也逐渐取得方言区之间的交际工具的地位,被称为‘官话’,但是它的发展速度是落在白话文学的后面”;其三是20世纪以来,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高涨,民族共同语的长期形成过程开始加快,“言文一致”的主张,“白话文”的实践,“国语运动”和“注音字母”的推行,“拉丁化新文字”的提倡,在推行北方话方面也起过一定作用,“这接二连三的运动反映了汉民族共同语以书面语和口语的统一形式在加速形成的事实,‘普通话’这名称逐渐代替了‘官话’,也正是由这种事实决定的”①鲁允中等编:《现代汉语资料选编》,第17—18页。。
在这段白话书面语形成史的梳理当中,关键词是“民族共同语”的“加速形成”,背后起推动作用的则是“革命运动”。数千年来,汉民族的语言文字状况,主要是文言加方言,既有超地域超时代的真正统一的书面语,又有生动活泼各具特色差别极大的方言,“言文不一致”是理所当然的,官话和白话出现得很早,但发展缓慢,明清之后,明显加速,但其进程仍是自然的演变。
“言文一致”的提出,乃是与西方语言接触之后所产生的一种震荡效应。近代以来,由鸦片战争开始的一系列失败,导致知识分子从盲目自大到盲目自贬。五四运动以否定传统文化为旨趣,白话文运动对于文言的否定与对于汉字的否定是不可分割的。
今时的中国语言文字状况就这样造就了,我们没有了真正的书面语——文言,真正的口语——方言也在以极快的速度消亡,通行的是干巴巴的白话和南腔北调的普通话。然而,这二流的白话文和三流的普通话也并不一致!
七
不谈“言文一致”,就口语和笔语而言,即使在文言时代,也决不是毫不相关的,以司马迁、班固、扬雄、王充那样的文笔,平时讲话一定精彩,只是无缘听到而已。他们在文章里援引了多少当时的口语精华不好辨别,却是可以肯定的。文言文中,通常看不到方言色彩,而词汇句式的古今细微变化,似乎在表明口语对于文言的某种渗透。书面语本身又可以认为是一种最大的方言。统一的读书人的方言,随着教育的普及,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融合,始终存在自然的互动过程。韩愈作文有意识地复古,但细察其文句,又与司马迁明显不同,这个差别不是他追求的,而是时风变化、口语变化带来的,他在写作的时候不可能把这些因素排除。所以文言文的古今一致当中,还暗含着诸多细微的差异,而且没有人规定文言文只能依照古人那样写,亦步亦趋。当初鲁迅批评《学衡》和章士钊的古文不地道,其实正说明了他们在古文上不是完全守旧的路子。鲁迅靠近章太炎,古文喜用生僻字,追求古奥晦涩,明显有别于八大家和桐城派,相比之下,半文半白的梁启超,影响更大一些。
白话文固然方便口语的吸取,但口语经过提炼才能成为合格的、优秀的文章语,这是汉语的常态。创作拟口语风格的文体,与放弃书面语,标榜“写话”,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子。梁宗岱说:“言文截然分离底坏结果固足以促醒我们要把文学底工具浅易化,现代化,以恢复它底新鲜和活力;同时却逼我们不能不承认所谓现代语,也许可以绰有余裕地描画某种题材,或惟妙惟肖地摹写某种口吻,如果要完全胜任文学表现底工具,要充分应付那包罗了变幻多端的人生,纷纭万象的宇宙的文学底意境和情绪,非经过一番探检,洗炼,补充和改善不可。”①梁宗岱:《文坛往哪里去——“用什么话”问题》,《宗岱的世界:诗文》,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1页。这番淘洗锤炼的工作,或可审慎地称之为白话文的“文言化倾向”,与写作的所谓“明白如话”相反,它追求精确、凝练、艺术化,精通并调动一切修辞手段,创造新文体。此不独汉语为然,世界各国的文学佳构无不追求这共同的书写境界:偏离规范的原则(deviation from the norm)。若以文学写作为旨归,这种境界才是真正的“言文一致”。
与西方不同,中国文字超出语言的那部分修辞手段,精深优美,为“言文一致”的提倡者所故意忽视,但文章家则从来深味此道。汪曾祺说:“其次还有字的颜色、形象、声音。中国字原来是象形文字,它包含形、音、义三个部分。形、音,是会对义产生影响的。中国人习惯于望‘文’生义。‘浩瀚’必非小水,‘涓涓’定是细流。木玄虚的《海赋》里用了许多三点水的字,许多摹拟水的声音的词,这有点近于魔道。但是中国字有这些特点,是不能不注意的。”②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0页。此经验之谈指出了视觉性语言并非“无声”,精于写作和阅读的人,自会“看”出字里行间的声响。
字与音的关联,蕴藏着丰富的理论价值。“字本位”理论的提倡者徐通锵在习焉不察的语言常态中,生动揭示了字与言的当下真实状态:
什么是字?一般都认为写出来供人们看的才叫字。其实,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字”首先是说的,书写形体只是把说的字写下来而已,现在经常说的“万言书”、“洋洋数十万言”的“言”也可以为此提供一个佐证,因为这里的“言”等于“字”。我们如果要人家讲话讲得慢一点,只能是“你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绝不会是“一个词一个词慢慢说”;“你敢说一个‘不’字”,这句话里的“字”也不能换成“词”。所以我们应该改变“写出来的才叫字”的错觉。③徐通锵:《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第80页。
这里的“言”和“字”两字的换位使用,并不是要混淆口语和笔语的界限。“什么是字”需要辨析的问题,并不能因为这个字的特殊用法而取消。看起来汉语写作者不能回避的书面语和口语的纠缠,在语言学家那里,也不是可以轻易解决的。
“言文一致”的努力,在写作上迄今收效甚微。“怎样说就怎样写”,从未在书写中实现过。朱德熙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写的“汉语”辞条总结道: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一直相当大,五四以前实际上是古今语的区别。他认为:“现代书面汉语是包含许多不同层次的语言成分的混合体。”又说:“白话文学作品的语言并不是真正的口语,而是拿北方官话做底子,又受到明清白话小说相当大的影响,还带着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兴词汇和欧化句法的混合的文体。鲁迅的作品可以作为这种文体的典型的代表。”“总起来看,汉语的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差别是相当大的。对于外族人说,学会了口语不等于学会了书面语。对于本族人来说,学会书面语写作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④《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第132页。
由此,又可从中西思维的差异看中国“语”“文”的“自我”独特性。西方思维通常基于语言符号(语言符号与文字符号基本同一),中国则不然(语言符号与文字符号相异)。刘晓明据此提出了中国文学的三种思维——单文思维、合文思维和语文思维。下表据其《“语”“文”的离合与中国文学思维特征的演进》的主要观点绘制:


该文认为:中国文体演进有一个众所周知而不能打乱的递进序列,决定它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就是文学思维进化。“这一进化又是由思维材料的演变导致的。单个文字为主体的时代,必然会对诗句的言数有所限制,四言诗遂应运而生;而需运用大量组合文字的五言诗、七言诗、赋骈只能产生于合文思维时代;当口语大量进入并能被文字描述时,方有元曲、明清小说。从这个意义说,文体演变的序列早已被思维的演进预先设定了。”①刘晓明:《“语”“文”的离合与中国文学思维特征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以此三种思维的划分并阐述文学史与文体的演变,允称新颖,如若以“单文”“合文”对应思维,似可存疑。思维与语言,思维与文字,密不可分,但汉语的词语弹性很大,指称某一事物,既可用单音词也可用双音词、多音词,比如“日”—“太阳”—“阳婆婆”等等,这些词音节不同,语体色彩也各有差别,择用时取决于上下文,同时构成修辞活动本身。思维状态不可能受制于“单文思维”与“合文思维”,即便擅长文言写作,怕也不是“单文思维”发达——将三种思维合称“修辞思维”,并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随意调整和变换,才能实现充分达意的目标。写作活动如此,思维活动恐也如是。
饶宗颐认为:“古代汉民族圈内,文字的社会功能,不是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语言,在这种情形之下文字与语言是游离的。”②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83页。因此有人提出“汉字思维”,以区分所谓语言主导的西方思维,究其实,并不准确。吕叔湘说:“一部分文言根本不是‘语’,自古以来没有和它相应的口语。”③《吕叔湘文集》第4卷,第67页。文言的一部分确实不是语,但大部分可以是语。唐代的文章有意模古,其实作者不可能不受当时的口语和方言的濡染,在直接当下的语言状态中,不可能尽是“汉字思维”。思维当中的“言”“文”状况,又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识字者与不识字者,思维的差别可能是巨大的,用笔思考,与用嘴思考,不可能完全一致,但也不可能截然两分,说话、写作、口语、笔语,终有差别,但根本上具有同一性。“修辞思维”正是在这一既差异又同一的综合实践中,利用语言和文字的各种有效资源来进行达意的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它包括汉字思维,但绝不会以此为限。
胡兰成在《中国文学史话》中认为:“文字与言语是二,文句与口语有密切关系,但二者有关系,非即二者是一体。而此亦是中国文字的特色。西洋的文字只是符号,符号是代表事物的,符号自身不是事物,所以西洋的文字只是记录其言语的工具。中国文字可是造形的,其自身是事物,所以虽与言语相关,而两者各自发展。”④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31页。与言语相关,而又各自发展,这确是中国笔语和口语关系最重要的两端。须有这样的见识,才能适宜从事笔语的创作。
中国的历史长,传世文本多,成语典故,通行既久,口语当中也经常使用。口语模仿书面语,是国人自古以来的集体习性,不可忽视。我们赞美某人口才好,“出口成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从语言到绘画甚至工艺,“自然模仿人工”是传统文化的特质。立象以尽意,立字以尽言,在国人这里,自然是感受,是材料,而不是模仿的对象。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认为:“语言是我们所知的最硕大、最广博的艺术,是世世代代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无名氏的作品,像山岳一样伟大……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因素——语音的、节奏的、象征的、形态的——是不能和任何别的语言全部共有的……艺术家必须利用自己本土语言的美的资源。”①[美]爱德华·萨丕尔著,陆卓元译:《语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02页。国人思维的特性,艺术感受的独特方式,对于世界和价值的认识、态度等等,隐藏在汉语和汉字当中,数千年来自然而然地透过自己的文字和语言打交道。拼音化取代汉字的运动虽然失败了,但这百年来朝此方向的努力,不会没有任何后果。今天,白话文运动似乎为现代中国创造出某种可以称之为“拼音文字的灵魂”的事物,使我们在使用汉语的时候,仿佛它不是我们的母语,普通话加白话文,使我们的生存漂浮于历史之外,无法认清自己。唐兰在1949年《中国文字学》中有一些话,今天读来比60年前更为痛切:
中国文字果真能摒弃了行用过几千年的形声文字而变为直捷了当的拼音文字吗?一个民族的文字,应当和它的语言相适应,近代中国语言虽则渐渐是多音节的,究竟还是最简短的单音节双音节为主体,同音的语言又特别地多,声调的变化又如此地重要,在通俗作品里含糊些,也许还不要紧,用拼音文字所传达不出来的意思,只要读者多思索一会,或者简直马虎过去就完了。但是要写历史,要传播艰深的思想,高度的文化,我们立刻会觉得拼音文字是怎样的不适于我们的语言。②唐兰:《中国文字学》,第89页。
按理说倡导言文一致,强调口语的价值和语音的重要性,应使今天的国人能言善辩至少能说会道,但是事实却是对于汉语语音的普遍迟钝和缺少辨析力,读者通常能区分四声,但不懂平仄韵律,专业文字工作者,也鲜有能在写作中自觉运用声律手段增加文章的节奏感,提高文章的可读性。五七言诗与四六文和它们对于形音义的讲究,与现代汉语不相关似的,深刻的思想、高度的文化以及历史,大家在写作和说话中一齐来让它马虎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