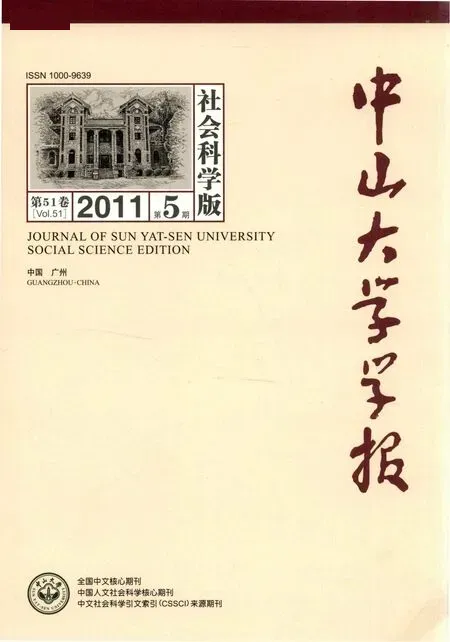“隐逸诗”辨:从田园到山水*
——以陶渊明、王维、谢灵运为人物表
夏中义
一
“田园诗”、“山水诗”作为概念,是文学史家论述古汉诗题材时常用的关键词。若把“隐逸诗”亦当作术语,则它不算常用词,因为自古迄今,它对中国文学史述似不具“关键”性。故钟嵘《诗品》虽早在齐梁时,称陶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①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60页。,然一千五百年过去,海内外学界仿佛依旧视“隐逸诗”是钟嵘偶尔一用的词,而并非一个比“田园诗”或“山水诗”更具文化史信息或价值意蕴的范畴。
在逻辑学框架,“范畴”所涵盖的面既比“概念”宽泛,其思辨层次亦高于“概念”。“田园诗”、“山水诗”作为题材学概念,与“隐逸诗”作为主题学范畴,彼此间在内涵上虽不无交叉,有的几近重叠(如陶渊明“田园诗”即“隐逸诗”);然就学理层次而论,它们不是同类项。这就是说,“隐逸诗”作为范畴,它可概括“山水诗”、“田园诗”中的“隐逸”取向;然“田园诗”或“山水诗”作为概念,对其所蕴含的“隐逸”取向,却无计作单纯指称(如谢灵运“山水诗”并非“隐逸诗”)。
所以要有此设定,旨在界定“隐逸”这一诗学范畴,并不侧重诗人“写什么”,而是侧重诗人“为何写”与“怎么写”。或曰,“隐逸诗”中的这个“诗”,与其说意指贺拉斯笔下的“诗艺”,毋宁说近乎荷尔德林心中的“诗意”。也就是说,“隐逸”之要义,首先指向诗人“如何做人”,其次才关涉其“如何做诗”。从这个角度来反刍“隐逸诗人”这一词组,可悟得钟嵘对陶渊明的这一古老命名,实在回味多多。甚至可将词组拆成“隐逸”、“诗”、“人”三个词素,先单个解析,再整合成型,结果读出钟嵘的潜台词拟是:正是陶潜这位千古一“人”,遂使其田园书写,转为“隐逸”之“诗”。亦即在钟嵘眼中,陶作为一个人的道德存在,是比其诗的审美存在,更具分量。或曰,其田园诗的文学史价值,当源自其人格的文化史价值。所谓“每观其文,想其人德”①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第260,260页。,似近之。
惜钟嵘未细说怎样“想其人德”。毕竟《诗品》所录的,本是钟嵘对汉魏120余位逝者的五言诗的天才印象。此印象是审美直觉,灵动,犀利,直逼根柢,却仍属眉批式评点,并非理论,未见概念化的条理缕析;倒是昭明太子撰《陶渊明集序》,释陶所以“文章不群,词采精拔”,根子盖在其“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②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附录之昭明太子萧统所作《陶渊明文集序》,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614页。。这多少勾勒了陶潜“人德”的个性特征。承接萧统的文脉,笔者更想说,陶所以蔚然而成中国文学史的大诗人,不仅源自他是中古思想史的杰出思想家(陈寅恪语)③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29页。,更源自他是用生命去亲证庄周理念是可被日常践履的伟大先行者。上古以降,典籍固然不乏“安贫乐道”之先贤传说(包括庄子),然真正让后人相信,一个书生若不遵循“读书当官”的传统,而只倾听天性与良知的召唤,一步一个脚印,沾着牛屎、汗渍和血迹在山乡独辟生路,照样可以活出尊严乃至启示历史,这确凿是从陶开始,也只有陶真正做到了④参阅拙著:《释陶渊明:从陈寅恪到朱光潜——兼及朱光潜在民国时期的人格角色变奏》,《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实在不容易。
这在实质上,是已回应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那个悬案:即为何陶诗好读不好学?所谓“好读”,是指陶诗言简旨远,平淡中有深致,用苏轼的话,则谓“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⑤见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苏辙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10—1111页。曹(植)、刘(桢)、鲍(照)、谢(灵运)、李(白)、杜(甫)。。所谓“不好学”,是指陶诗所以难及,是因其冲澹深粹,纯属内心妙谛之自由流露,绝非诗艺(技巧)层面的刻意雕琢。也因此,智慧如苏轼者,已识破陶诗“文学中有人学”,故才会说:“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且立言以陶为人格殷鉴,返照自身,“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⑥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苏辙集》,第1110—1111页。。
二
如此阐明陶潜“隐逸”人格与其田园诗的精神血缘,是被古今一脉的中国文学史述所逼出来的。君不见,自6世纪初钟嵘《诗品》将陶田园诗定格为“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式的“风华清靡”⑦钟嵘 著,曹 旭集注:《诗品 集注》, 第260,260页。,直到20世纪下半叶,中国通编教材仍袭其套路,只须论及陶田园诗,便言必称《归园田居》五首、《读山海经》第一首、《饮酒》第五首、《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和《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因为如上诸诗所贡献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等垂世名句,盖印证了钟嵘关于陶田园诗为“风华清靡”之审美鉴定⑧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中国文学史》卷1《陶渊明的作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30—233页。。钟嵘所欣赏的“欢言酌春酒”一句,亦恰巧出自《读山海经》第一首。
这很容易塑成定式:“陶田园诗=风华清靡”;或倒过来:“风华清靡=陶田园诗”。殊不知,如上契合钟嵘胃口的田园诗,陶大多撰于408年前:其中《归园田居》五首为405年,《读山海经》之一为407年,《饮酒》之五为403年,《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为403年,惟独《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为410年。这是否表示,陶潜田园诗在408年前已大体写完?或曰,诗人408年后的田园咏叹,会因其大多不甚“风华清靡”,而不该算是田园诗?这皆成了问题。这乍看仅仅是审美偏向所致,然深究,则关乎对陶“隐逸”人格的价值体悟。可以说,毋论古今,对“隐逸”一词的丰厚底蕴的觉悟程度,将直接牵制你对陶田园诗的解读深度暨广度。
韩愈(768—824)坦承少时曾不免对“隐逸”识浅:“私怪隐居者无所累于世,而犹有是言。”①韩愈:《送王秀才序》,《韩昌黎全集》,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第288页。意谓人若不奉朝事君,无官一身轻,自然隐即逸,逸须隐了。似乎在少年韩愈看来,“隐逸”这一双声词的两个词素之间,本就包含某种必然律,彼此关系在任何语境,皆无条件恒等。这诚然是将“隐逸”所内蕴的涵义结构看扁了,简单化了。这是“望文生义”。
这就是说,若不仅仅把“隐逸”字样印上书卷,亦让它回到活生生的历史场景和血肉人物身上,你将确信:“隐逸”的内涵结构实是弥满张力的复合型。它至少分两个层次:“角色选择”与“人伦担当”。“角色选择”,拟可称为“纯粹道德”,它属于“知”(价值认知)层面,是为主体所以弃仕归田、遗世任真提供理由或支撑,亦可谓“立命”。“人伦担当”,则拟可称为“实践道德”,它属于“行”(行为践履)层面,是将主体的角色自期转化为可被日常栖居所操作,故亦可说是“安身”。
现在再回到陶身上。405年陶最终拗不过内心的“角色自期”,辞官彭泽令,载欣载奔地“归园田居”,这颇了得。要在历代儒生碾实了的古道车辙畔,另辟蹊径,这无异于“反潮流”,抑或“一个人的精神抗战”。但他慷慨独行,堪称卓越。
然陶在408年后的“人伦担当”,或许更卓绝。陶不屑借“佯隐”来欺世盗名。陶是矢志按其箴言活出圣洁的君子。他明白“隐逸”对己、对眷属意味着什么。他已自绝退路。他选择的路无疑不好走。陶颇努力,农夫下地流多少汗,他也流多少汗:“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归园田居》之二)风调雨顺、身健力强、日子好过时,谁都会羡慕陶的农居之乐,其乐融融,近乎美满。请看:“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和郭主簿》之一)此诗撰于405年左右,未届不惑。
但好景不长,408年一把野火,“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陶本就不厚的家底转眼灰烬,最后落得“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戊甲岁六月中遇火》)。尽管陶豁达如故,移居南村后,该交友时依旧“奇文共欣赏”(《移居》之一),该散心时依旧“登高赋新诗”(《移居》之二),然陶终究将痛感其“角色选择”须支付的代价。特别是遭逢天灾与病衰时,陶在精神上再纵浪大化,不喜不惧,每朝每夕一家老小的生存艰难仍逼得他叫苦,不禁连口占示友时的调子也带哭腔:“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陶对日常生计从不奢求,“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移居》之一)。吃,不过是“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饮酒》之十);穿,更是“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然要命的是,如此起码的温饱也“不能得,哀哉亦可伤”(《杂诗》之八)。
最撩人心酸的,是陶53岁撰《与子俨等疏》,既为遗嘱,也是对一生“为己”与“为父”,即人伦角色难兼的甘苦表白,更是对儿辈的“良独内愧”:“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僶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尽管他旋即感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然当他写到“病患以来,渐就衰损”,“自恐大分将有限也”,而“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时,也只能“念之在心,若何可言”。可见其内心甚苦。
陶最令人肃然起敬的特质,是其人格辞典不刊“苟且”一词。哪怕是在悲怆晚境,他已忍饥偃卧有日,江州刺史檀济道登门慰问,劝陶再度出仕,陶不仅婉拒,且将贵宾所赠粱肉,一概谢绝。嗣后陶撰《有会而作并序》:“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意谓如上举止并非意气轻狂,只缘气节重于肠胃。此几近催人泪下的“英雄造型”,宛如趴守最后一寸焦土的喋血猛士,早已弹尽粮绝,但只要还有一口气,他绝不撒手缴械。
这就表明,在陶心中,纵然乞者也有其不容轻侮的尊严。这不禁让人回味陶另首撰于同年的《乞食》诗:“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当施主的馈赠,并不以轻慢陶之品行暨价值取向为前提时,诗人不仅笑纳,而且感恩。
以上论述,说明了什么?说明陶潜人格为符号的“隐逸”现象,作为历史文化的真实存在,在“隐”与“逸”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无条件恒等的必然律”。这就是说,陶在408年前,他所以能一出樊笼,便寄情村野,与秋菊春酒结伴,将日子过得如鱼得水,如鸟栖林,有滋有味,即“亦隐亦逸”时,那是因为诗人此时的心力、精力、财力和体力,足以支持其“角色选择”;相反,408年后,当其心力、精力、财力和体力有所不济,不足以正常或体面地维系其“角色选择”,其活法再高贵清纯,也不能当饭吃,饥肠辘辘的诗人幽怨,也就不无衰飒之音。与408年前“风华清靡”的田园诗相比,其408年后的田园“叙事”,已谈不上“风华清靡”。
不妨列一清单,以示如上所引有涉陶忧生之嗟的诗文皆撰于408年后,依次为:《戊甲岁六月中遇火》408年;《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418年;《移居》之一408年;《饮酒》之十约408年;《杂诗》之八421年;《与子俨等疏》421年;《有会而作并序》423年;《乞食》423年。
于是,问题就大了:若按钟嵘“诗品”模式,只有408年前“亦隐亦逸”,即“风华清靡=陶田园诗”;那么,408年后另些“隐而未逸”或“不逸仍隐”,即未能“风华清靡”的诗章,是否应注销其“陶田园诗”名分呢?若此,则不仅对陶田园诗的文学史述评有失整体而偏于一隅;而且,更重要的,恐对陶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这一形象,所凝结的文化史重量暨幽邃意蕴,低估了。甚至可能误导国人至今仍将“隐逸”,虚拟为某种无所事事、无所担当、悠哉游哉地混日子的神仙或酒鬼活法。这就未免幼嫩得像8世纪后半叶的少年韩愈了。
三
在“隐逸”文学史廊,能与“田园诗宗”陶潜(约369—427)隔代媲美的,非“山水诗佛”王维(701—761)莫属。若以钟嵘模式来考量,王维的“穆如清风”①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页。,恐比陶潜的“风华清靡”,更具“亦隐亦逸”之情调。
王维山水诗,所以不见陶“隐而未逸”的忧生之嗟,亦无陶“不逸仍隐”的人格卓绝,根子在其“角色选择”策略有别于陶。王不像陶那般决绝地“弃官而隐”,他是“先官后隐”或“亦官亦隐”,给自己留了回旋余地。
诚然,王不是不知陶的故事。727年,王27岁,尚在淇上当小官,曾撰《偶然作》六首探讨了陶的活法。一方面,王不否认陶转为衡门田翁后的闲居诗意:“短褐不为薄,园葵固足美”;“得意苟为乐,野田安足鄙?”但另方面,王对陶纵任天性又不无保留:“自从弃官来,家贫不能有”;“生事不曾问,肯愧家中妇!”“肯”,犹“拼”。意谓陶安贫乐道,纯属“为己”,结果惹眷属清苦,如此勇气,王是不敢有的。由此细读王揣摩陶潜思酒的10行诗句:“九月九日时,菊花空满手。中心窃自思,倘有人送否?白衣携壶觞,果来遗老叟。且喜得斟酌,安问升与斗。奋衣野田中,今日嗟无负。”你委实难分:这是写实性白描,还是动漫式婉讽?
由此背景,再体悟王为何“日夕见太行,沉吟未能去”,也就释然。“太行”,起势河南,北入山西省境,王所在的淇上亦地处豫北,恰巧遥望在目。“太行”在此作意象,当暗喻弃世隐居。那么,仕途不顺的诗人,当年为何仍“沉吟”迟迟,不像陶那般乘风归去呢?他有心理障碍。用其诗语:“世网婴我故。”“婴”,缠绕、束缚也。王是长子,父亲早逝,长子代父,他不忍推诿全家生计之重负:“小妹日长成,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故“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以上引诗,俱自《偶然作》)。毕竟,人各有志。即使皆想“隐”,也各有各的“隐”法。
说起王的“先官后隐”,其内涵,当不仅指其编年史上的行为次序,也蕴藉其价值论水平的自我体认。就行为次序而言,王自15岁离乡赴两都谋生至“安史之乱”(715—756),在此四十年间,他历经了三遭“先官后隐”。
先是721年进士擢第,任太乐丞,协掌邦国祭祀享宴所置乐舞;同年因其所辖伶人舞黄师子违规而连累,被谪济州司仓参军,一呆五年;726年改官淇上,遂生退隐意念。729年索性从大荐福寺道光禅师学佛,后隐居嵩山。此为首次“先官后隐”。
再次“先官后隐”,是王734年献诗宰相张九龄,735年官拜右拾遗;737年奉命出使凉州;738年返长安任监察御史;740年迁殿中侍御史;741年春又辞官隐于终南山。
第三次“先官后隐”,是王742年复出为左补阙;746年为库部员外郎;748年为库部郎中;752年拜吏部郎中(是年改为文部郎中);755年转给事中。于长安奉朝事君之余,王744年始营蓝田辋川山居,景色迷人,每每趁闲暇、休假(含因母居丧两年余)回归小憩,堪称“亦官亦隐”,甚为美满,直到756年“安史之乱”。这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辋川现象”。王维山水诗的经典部分大都撰于此时段。
王“先官后隐”,还有另层价值论含义,是说他只有经此“三官三隐”,人生历练,才逐渐醒悟:“我是谁?”“我最想要什么?”这就是说,“亦官亦隐”作为王的“角色选择”策略,并非一开始就甚自觉或聪慧如此。事实上,从青年时起,王就面临三个选项:“济世”、“食禄”与“安魂”。不是说如上选项宛若分道扬镳的三岔路,彼此间无计兼容;而是说王无法早早辨清孰重孰轻,只是大体懵懂,先应付再说。
“食禄”是王当官的动力,但未必是“第一动力”,更非“惟一动力”。否则,735年王撰《献始兴公》(始兴公,即时任宰相张九龄),重言“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雠。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也就不免矫情。这表明,王虽因张九龄提携而拜右拾遗,然他更祈愿那是丞相出于为国为民的“公议”所致,这样更令自己“感激”,若仅仅“曲私”,就不是自己所希企了。由此可鉴王的人品。他是渴望能在贤相帐中干正事的。
嗣后证实此诗不虚。737年张九龄被奸臣李林甫挤出朝廷,谪配荆州。王即撰《寄荆州张丞相》,倾诉知遇之恩,且示自己无心恋栈:“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并且,近十年后,746年,李林甫的亲信苑咸酬诗言及王久未升迁,王回赠:“仙郎有意怜同舍,丞相无私断扫门。”(《重酬苑郎中并序》)①《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林甫)自无学术,仅能秉笔……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阘茸(鄙贱)者,代为题尺。”《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3866页。这一酬一赠,颇含玄机。若王无原则地热衷仕进,则苑既有心拉拢,王自可顺水推舟,然王偏说丞相(李林甫)“无私”,禁绝请托(即“走后门”)。字面是称颂李,实质是立场依旧,不屑趟此污水。
史实已见证在王的价值天平,“济世”、“食禄”这对砝码并未重于一切;相反,另枚“安魂”砝码倒分量更沉。因为当王警觉“济世”、“食禄”这两项,有玷污良知之虞而无力“安魂”时,他宁肯暂搁置功利。746年婉拒苑咸便是例证。这就是说,此时王实已认准“我是谁”、“我最要什么”了。这儿有两首五言可供比对:一是721年撰《被出济州》;二是744年后撰《漆园》。前后久隔二十余年,然皆有一个“微官”。前者云“微官易得罪,谪去济州阴”,此“微官”当自况,直抒初为人臣时的怨屈。后者“微官”,字面虽意指庄周非“傲吏”,仅仅是无才治国,才愿偃息林下(所谓“婆娑数株树”),其实亦在暗示诗人的自我体认。
也就是说,至辋川时期,王已具自知之明。他把自己看透了。就“济世”或“食禄”而言,他碌碌数十年沿官阶品秩攀援,从太乐丞(八品下,21岁),爬到库部员外郎(六品上,44岁),再转给事中(五品上,55岁),仰侧满朝权贵,这位皤然一老,依然“微官”一个②据《旧唐书·职官志》:“补阙、拾遗之职,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即王维做官,并非有实权的要职,几近是奉和君王的“服务性行业”。。王做官本事不大,形不成大气候。然同时,他洁身自律,小富即安,不擅越轨,这又有碍他在朝廷的私利最大化。总之,吃朝廷这碗饭,不惑之年后,已不是其生平“第一志愿”了。他内心无疑倾向于“隐”。然他很明白“隐”是要花钱的。故为了“隐”得起,他又不得不“官”。“先官后隐”或“亦官亦隐”,也就这样成了王最适宜、最具操作性、亦拿捏得颇具心得的活法。
王“亦官亦隐”,有否“佯隐”之嫌?乍看,不能说一点没有。有人指出,734年“维既献诗九龄求汲引,何以又要隐于嵩山?盖是时玄宗居东都,嵩山地近东都,隐此正可待机出仕耳……如开元时卢鸿隐于嵩山,即被玄宗征为谏议大夫”①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338—1339页。。那么,这与陈寅恪所鄙夷的山涛、王戎之流(“前日退隐为高士,晚节急仕至达官,名利兼收,实最无耻之巧宦也”②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20页。),界限何在?界限仍在:山涛、王戎号称其“周孔老庄并崇,自然名教两是”,旨在“赢家通吃”,所有好处都想抓,脸皮太厚;然王维脸皮偏薄,颇具道德羞耻感,懂自我检点,最怕良知上过不去。其范例,当是王758年冬奏请施辋川庄为寺,以释“安史之乱”后郁积于心的大愧疚③756年6月,安禄山兵陷潼关,寻入长安,玄宗出京,王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被迫任伪职。此前闻安禄山宴其群臣于凝碧池,悲甚,潜赋《凝碧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贼平,附逆官遂定罪。王以《凝碧诗》闻于朝廷,肃宗嘉之,再加其弟王缙请削己官职以赎兄罪,王蒙特宥,758年秋官复原职。然王依旧自惭微节,是年冬奏请施庄为寺,以期“上报圣恩,下酬慈爱”,舍此恐“无以谢生”,遗恨终身。此时离其卒(761年)仅三载矣。参阅陈铁民:《王维年谱》,《王维集校注》,第1362—1369页。,以期“安魂”。
四
现在看来,王维晚年捐庄为寺,颇多象征意味:一是王筑辋川山庄,原初是为母奉佛持戒之用,为己业余隐居习静,倒在其次;二是山庄客观上成了中国文学史的珍贵遗址之一,因为王维山水诗的经典部分悉撰于此;三是无论孝母,还是裨益诗心,山庄(含山水)确凿转为王赖以尽责、寄怀的心灵归宿。综上所述,可见山庄在诗人心中的位置及分量,故施庄为寺,堪称王生前主持的最庄重的“安魂工程”。
这与解读王维山水诗有关系吗?有。其山水诗所以写得“亦隐亦逸”,根子是诗人作为一个人,首先能在现实中活出心安。与此相比,因陶潜408年后在现实中很难活出心安,故其田园诗也就不免“隐而未逸”,却又“不逸仍隐”。陶诗“文学中有人学”,王诗“文学中也有人学”,盖彼此“人学”存异,故其“文学”不一。
据统计,不难测定山水诗在王维平生各时段的分布概况,借此见出山水诗创作与其对应处境暨心境的有机关联。简表示下④简表数据以陈铁民所拟王维诗编年为本,见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目录)》,第1—11页。有些山水诗如《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未入编年诗,是碍于难核实其创作年份,亦可鉴陈为学之慎。就概率而言,已无伤大雅。:

山水诗 开元(715—741) 天宝(742—756)11 23类山水 31 46总篇数 42 69年均比(近似值)纯山水1.615 4.929
几点说明:
1.王是盛唐诗名仅次于李白、杜甫的大师,故简表专列其开元、天宝年间的山水诗数据比对。鉴于王少时诗作撰于开元三载,故表中“开元”自715年始。
2.简表有“纯山水”与“类山水”之型别,旨在明鉴王山水诗创作实况,并非所有山水诗皆“意尽山水”。颇多篇什本属酬赠、家书、挽歌乃至奉圣应制之作,因植入山水元素而灿然养眼,历代诗评“爱乌及屋”,遂将有此名句者通篇泛称“山水诗”。恐欠精当。诸如“林疏远村出,野旷寒山静”本出应制(《奉和圣制登降圣观与宰臣等同望应制》),“秋日光能澹,寒川波自翻”本出挽歌(《吏部达奚侍郎夫人寇氏挽歌》之二),“清冬见远山,积雪凝苍翠”本出酬赠(《赠从弟司库员外絿》),“青草肃澄陂,白云移翠岭”本出家书(《林园即事寄舍弟紞》)。更无须说,千古名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本出记行(《使至塞上》)。这就是说,当历代书生屡屡聚焦于如上典丽诗联,且在瞬间将其虚拟为“江山如画”之特写,堪称美的享受;但此审美纯属心理效应。因为,若对诗章作真实评估,须涉及整体。于是,那些被想像成“特写”的山水元素,一俟返回本文语境,势必还原为“全景”构成之零件,其华彩,也就很难不被非山水的上下文所掩抑①例如“林疏远村出,野旷寒山静”二句“山水诗”,本自《奉和圣制登降圣观与宰臣等同望应制》。全诗为:“凤扆朝碧落,龙图耀金镜。维岳降二臣,戴天临万姓。山川八校满,井邑三农竟。比屋皆可封,谁家不相庆?林疏远村出,野旷寒山静。帝城云里深,渭水天边映。喜气含风景,颂声溢歌詠。端拱能任贤,弥彰圣君圣。”计八联十六句,“山水诗”为其中第五联,第9、10句。故与其称“山水诗”,不如称“山水句”或“山水联”为宜。以此类推。。这就不同于《辋川集》里的“纯山水”,故命之“类山水”。
3.简表已示王在开元年的山水诗“产量”,远逊于其天宝年。前者26年间撰42首,后者14年间撰69首。后者的年均“产量”是前者的3倍多。若计“纯山水”的年均“产量”,则后者是前者的近4倍。不难推测,王在天宝年的日子,要比开元年过得舒心、滋润与闲雅,故寄情山水之诗兴也就丰沛。注意到天宝14年(742—756),诗人有12年(744—756)能常返辋川隐居,“辋川”为何成了中国山水诗的圣地,也就无须赘言。
五
王维诗饮誉历代,诗评当妙语纷呈,然专家言及其山水诗者不丰。相对而论,有“一多二少”。所谓“一多”,是指诸多人从“色(视觉)”角度,来美言王山水诗所以“诗中有画”②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05页。,“着壁成绘”③殷璠:《河岳英灵集》序,转引自《王维集校注》,第1257页。查《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册中所载《河岳英灵集》序,并无“着壁成绘”之语。此语实出自殷璠《河岳英灵集》王维部按语,见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66页。,“如辋川诸诗,真一片水墨不着色画”④王鏊:《震泽长语》,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0页。,盖其“本学佛而善画”⑤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60页。。持此观点者,唐有殷璠,宋为苏轼、张戒,明则王鏊。所谓“二少”,则指很少人能从“声(听觉)”角度,来探询王山水诗境为何能“于澹中含远”⑥贺贻孙:《诗筏》,《清诗话续编》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84页。,甚至“不用禅语,时得禅理”⑦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第68则,郭绍虞主编:《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52页。。清人贺贻孙、沈德潜已触及此案,惜未深究。诚然,能从王山水诗中系统勘探其“隐逸”底蕴,或倒过来,能从其有别于陶潜的“隐逸”取向,推导其山水诗境所以如此的识者,也就更少。
先回应“一多”。历代诗评强调王擅长丹青,苏轼那句“诗中有画”更本出《书摩诘蓝田烟雨图》,缘由是皆看出王有一双“绘画的眼睛”,故其感应山水色泽的才艺,远较他人(含谢灵运)专业。这就很像现代语境中的风光摄影。手携一架“傻瓜机”,任何旅游者都可轻易捕捉山水间的光和影,然只有修炼到家的摄影师才明白,其镜头所截取的山水画面,其实只是素材,如何让画面艺术地呈示自己摁快门时曾有的欣悦或敬畏,还亟需在暗房下苦功。故摄影家的体会是,摁快门不过“咔嚓”一瞬,然一帧摄影艺术精品的诞生,可能不亚于“十月怀胎”,甚至不无“难产”之虞。王孕育一首山水诗恐近之。如何用一个字,将大自然令己微曛乃至沉醉的那份色彩,醒目、传神、灵动、精炼且合诗律地植入韵文,在这方面,或许王独步千古。
请看:“连天凝黛色,百里遥青冥”(《华岳》);“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终南山》);“开畦分白水,间柳发红桃”(《春园即事》);“绿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山居即事》);“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中》);“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辋川别业》);“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新晴野望》);“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书事》)……王不曾表白贾岛式的刻苦:“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也没说过像杜甫为了一句诗,捻断数茎须,但只需留意王山水诗的“产量”:开元年是年均1首半,天宝年是年均5首弱,大多为五言。亦可谓慢工出细活,诗不在多,而贵精。
现代心理学认为,肉眼模糊时,心眼转为尖锐。“心眼尖锐”作为审美心理现象,是指主体屏息凝神于内在“兴奋灶”,而暂时忘却世务俗趣,尽管平素人心往往受其纷扰。“绘画的眼睛”所以迥异于日常视觉,不仅是前者比后者更敏感于对象的“形—色”元素,还在于前者有才艺能将此“形—色”之审美意味,借媒质而使其从个人拥有转为他者共享。此媒质,对美术来讲是线条与色彩,对诗歌来讲是词语和韵律。这对山水诗人而言,则亟待将其表现对象(“形—色”元素)从日常视觉中剥离(又叫“剪材”),使之游离素材的原型秩序,而织入另一诗语秩序去重放光辉。这也是布洛说的“心理距离”,即与功利性视觉经验隔开,旨在为艺术想像腾出更适宜诗艺驰骋的纯粹空间。这就是一般山水诗所以做不到“诗中有画”,而王能啸傲诗史之故。
再回应“二少”。首先,除了贺贻孙、沈德潜,历代诗评为何很少人想从王山水诗谛听另种天籁?根由之一,当是受制于心理活动通则,即人类吸纳外界信息,90%以上是通过视觉。这就是说,除非有特异听觉功能,一般人对因空气振动而飘忽空间、无关自身利害的声音,大多听而不闻(俗称“耳边风”)。故诗评家若未免俗,他也确乎想不到,更想不通,王为何能从大气般弥散山川的原声音响,诸如鸟啼、猿啸、泉咽、松喧、禅钟、人语……乃至寂寂无声的花开花落中,听取另片天地传来的“安魂”之声?
请听:“落花啼鸟纷纷乱,涧户山窗寂寂闲”(《寄崇梵僧》);“啼鸟忽临涧”(《韦侍郎山居》);“雉雊响幽谷”(《晦日游大理韦卿城南别业四首》之四);“谷鸟一声幽”(《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莺啼山客犹眠”(《田园乐七首》之六);“猿声不可听”(《送贺遂员外外甥》);“疏钟间夜猿”(《酬虞部苏员外过蓝田别业不见留之作》)……这是禽兽之音。
再听:“山静泉逾响”(《赠东岳焦炼师》);“谷静秋泉响”(《东溪玩月》);“幽谷泉逾响”(《奉和圣制幸至真公主山庄因题石壁十韵之作应制》);“声喧乱石中”(《青溪》);“波澜动远空”(《汉江临眺》);“跳波自相溅”(《栾家濑》);“泉声咽危石”(《过香积寺》)……这是泉流之声。
三听:“行踏空林落叶声”(《过乘如禅萧居士嵩上兰若》);“松风直似秋”(《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松含风里声”(《林园即事寄舍弟紞》);“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竹喧归浣女”(《山居秋暝》)……这是花木之语。
四听:“夜禅山更寂”(《蓝田石门精舍》);“深山何处钟”(《过香积寺》);“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鹿柴》);“欲投人宿处,隔水问樵夫”(《终南山》)……这是人禅之问。
看来,只有像王那般,让整个身心从朝野脱逸而出,你才可能长出“灵魂的耳朵”(有别于“绘画的眼睛”)。本来,上帝让人耳紧贴脑门两侧,就是为了有助人类倾听灵魂之声。然当人心充塞过多尘世噪音,灵魂要么萎缩,要么从未长大。对每个人来讲,灵魂是什么?是指“主心骨”,是他赖以支撑其主体独立的精神脊梁。这就不是随大流,人云亦云,见钱眼开,仰赖权贵。这是要将有限生涯转为超越性自我实现的价值过程,做自己最想做的事,适性即乐,同时裨益文化与人类。这不是说王维在8世纪便超前拥有马斯洛在20世纪中叶才有的人文心理哲学,而是说王在当年能不汲汲于爵位荣禄(所谓“澹”),盖其内心有不同凡俗的“隐逸”角色自期(所谓“远”)。
故对贺贻孙“于澹中含远”这句话,又宜作“顺向”和“逆向”两度解读。“顺向”是侧重艺术赏析,意谓王的山水交响(此谓“澹”),实在传递另片天地的幽邃(此谓“远”)。这用王的诗语来说,是“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逆向”则着重精神透视,意谓王所以能从松风泉吟觅得灵魂归宿(此谓“远”),是其内心已不将名利看得太重(此谓“澹”)。故又不妨推理,这与其说,是大自然的音响元素唤醒了诗人心中那座沉寂的“终南山”;还不如说,是珍藏于心的“终南山”,在屡屡驱动诗人从高山流水聆听天籁,令其神旺。“君问终南山,心知白云外”(《答裴迪辋口遇雨忆终南山之作》)。终南山在“白云外”,若转成现代诗语,即心灵“生活在别处”(兰波);若换成近代宗教哲理,则迹近“回忆让人即使在家也生出乡愁”(克尔凯戈尔)。甚至可说,克尔凯戈尔撰于19世纪的那句名言,几乎与千年前的王维想到一起去了。因为王也恰巧是在辋川“家”门口“忆”终南山;而终南山在王那儿,又恰恰是作为隐逸者的共同故“乡”来眷恋的。
话说到这份上,再来咀嚼今人董乃斌赏析《鸟鸣涧》,可谓是对沈德潜的“接着说”,且说得很细深、很鲜活、很柔绵,本身宛若散文诗:
这一首(按,《鸟鸣涧》)就几乎可称《辋川集》里《鹿柴》、《辛夷坞》的姐妹篇,把一个静字写得入骨三分。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一静矣,然尚是作者明言之静。“月出惊山鸟”,更静矣,试想无声的月出竟似乎能打破山中之静使熟眠的鸟儿惊醒,那山中之静是到了何等程度!然而作者至此仍不停笔,又来一句“时鸣春涧中”——鸟儿被惊醒,这里那里不时发出鸣声,这声音不但没有使山中变得嘈杂,相反,偶发的鸟鸣声和它的回音,却让这座春山显得更空旷更宁静——静极了的春山中,时不时的鸟鸣,使春涧更静谧,自然的生活竟然如此符合辩证法。而外界的静,是要有一颗宁静的心去发现的,甚至是由这颗宁静的心去赋予的。我们根本搞不清(也无需弄清)这静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是客观的抑或是主观的,这便是禅。①董乃斌编选:《王维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72—173页。
笔者愿补白的是,禅理所以不同于科学逻辑,其根子是科学旨在求真,用概念来陈述对象“是什么”及“为什么”,切忌非知性因子掺杂其间,故需先分清主—客界限。然禅旨在劝戒人为其物欲所累不值得,若此,则俗世趋之若鹜的诸多名利,也就变得不值钱;相反,俗世以为无用无趣、当“耳边风”的“春涧鸟鸣”之类,却撩得王柔肠百转,内心惊奇不已。赋此五言,短短4句,仅20字,竟亦惹明人胡应麟“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此“妙诠”即禅意②胡应麟:《诗薮》内编卷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19页。。这与沈德潜说“王右丞诗不用禅语,时得禅理”,几近同义。仿效鲁迅语式,“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后学亦可说,从王(“纯山水诗”)鼻孔里呼出来的气都叫“隐逸”。
《鸟鸣涧》及《鹿柴》、《辛夷坞》被尊为王“纯山水诗”中的极品,不无理由。你可以说它元气贯注,相生相顾,浑然天成,无雕琢痕;你也可喜其不涉人间烟火,亦无玄言空腔,格调雅秀,寄怀清远。然其根由,则全赖诗人那双“灵魂的耳朵”,能从山水中听出“极静中的极动”和“极动中的极静”。这就把“声(听觉)”元素所蕴函的审美潜质,挥发到了极致。
这般说来,“人闲桂花落”与“月出惊山鸟”,乍看是不相干的两个画面,其实皆写了“极静中的极动”。假如说,人心只有静到极点,才可能听到桂花拂地时轻微得不能再轻微的窸窣声(这是“极静”);然诗人又分明从这山野静谧中领悟到生命的内在脉动:它无需外力推动,全然合着季节的迁移节奏,该绽放时就金灿灿地芬芳,该凋谢时就默默化作春泥,年年如此,轮回不已③参阅董乃斌编选:《王维集》,第140页。,全然不顾涧户有人与否,也不屑吸引朝野眼球,无声无息又坦坦荡荡,这是大自然生命的伟大!这也是诗人所亲证的感动(这是“极动”)!
诚然,悸惊的鸟鸣,末了只是将寂静的春山衬托得更空旷更静穆,这“极动中的极静”,董乃斌命之为宇宙“辩证法”,甚恰。其实还有另种心灵“辩证法”,这就是:能珍重“极静中的极动”的人,自己需先洗去烟火气,无所挂碍,亦即让心境渐入“极动中的极静”,一切才有可能。
六
阐释“极动中的极静”,拟有两条路径:一是宗白华论及的心理美学路径,即布洛“心理距离”说的中国版①宗白华:《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22页。;二是王维信奉的佛学路径,若诱人的物欲本无价值,他就会到非功利的山水间重建精神家园。
也因此,奉王为“山水诗佛”名实归一。因为用心品味其“纯山水诗”,你确可领略到一种禅味:安详、通脱、静谧、睿智,流露一丝释迦牟尼才有的微妙笑意。释迦牟尼拈花微笑之佛像,国人太熟悉了,却未见人诠释,佛为何会在拈花时笑得那般蕴藉?遥想饱经风霜的智慧长老在笑睨膝下儿孙时亦常含颌不语,于是揣测,或许在佛眼中,未脱红尘的芸芸众生所以迟迟读不懂“一花一世界”,也是因其心灵没长大,尚处“类儿孙状态”所致吧?
王心中有佛。故人家是身处江海,心怀魏阙;王是人在朝廷,心存山野。甚至可说,幸亏他在长安城外置有辋川山居,可不时回寓调节或修复心境,否则,他靠什么来缓和朝廷与山水、“官”与“隐”之间的对峙乃至冲突呢?从诗集可以读出,他在辋川时期对朝政已无兴趣,故他写为官奉朝的笔触也就不无揶揄:“晨摇玉珮趋金殿,夕奉天书拜琐闱”,恨不能“卧病解朝衣”(《酬郭给事》),不干了,也就无需拘泥如此。相反,当他写自己重返辋川,其欣慰又雀跃纸上:“不到东山向一年。”小别山居不足一年,然听到乡邻上门探望时,他竟兴奋得“披衣倒屣且相见,相欢笑语衡门前”(《辋川别业》)。连衣冠不正也不顾忌。
又想到王一个用文墨来缔造诗意的巨子,想必他对古汉语所蕴藏的审美潜质,有比一般官宦更多的珍惜与敬畏。若真如此,则当他不时贺表于朝廷,屈膝叩首,咬文嚼字,从“伏惟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陛下”②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1356,1366页。,到“伏惟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陛下”③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1356,1366页。,他的“现场感”到底是什么?仅称呼一回君主,便需耗18或14字,而《鸟鸣涧》、《鹿柴》那样的经典纯诗,一首也不过20字,他会痛感滑稽、无聊、无奈、郁闷,憋一肚子气么?这不是在逼人“异化”么?无怪,一有闲,他便拔腿往辋川跑。这大概是“反异化”的举措之一。想不到青年马克思《1844年巴黎手稿》所说的——无产者只有逃离生产流水线,才稍稍体会到人的自由,而在机器旁,他尊严丧尽,他只是工艺流程的一个物化环节或螺丝钉④青年马克思这样论述无产者被“异化”:“劳动对劳动者是外在的即不属于他的本质,因之,他在他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反而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反而感到不幸,并不展开自由的肉体的和精神的动力,反而使他的肉体受到苦行,并使他的精神陷于荒废。因此,劳动者在劳动外边才觉得在自己一边,而在劳动里面就觉得在自己外面。”《经济学—哲学手稿》,何思敬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5页。——似亦可用在王维头上。
相比较,“弃官而隐”的陶潜便不再遭此窝囊,然其代价则需忍受贫困,408年后田园诗道出了他“隐而未逸”,又“不逸仍隐”。王维无此胆气,他是“先官后隐”,“亦官亦隐”,故其山水诗能写得“亦隐亦逸”。但两者称为“隐逸诗”,皆货真价实,然又同中存异。这又印证,“隐逸诗”委实不是“写什么”层次上的题材学概念,它是系于诗人的价值取向,遂驱动其“为何写”及“怎么写”的主题学范畴。历代诗评无人识破这一点。这也是笔者对“二少”之二的回应。
七
同样写山水,王维不愧为“隐逸诗”,谢灵运(385—433)却不算,为什么?这是本案绕不过的话题。
答案两个字:“不纯”。症候是“三太”。
症侯一:谢纯山水诗“太少”。谢山水诗几乎全撰于这三个时段:任永嘉太守→隐居故乡始宁→任临川内史。简表示下①本表数据以黄节撰《谢康乐诗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为本,且参考胡大雷选注《谢灵运 鲍照诗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两点说明:
1.“永嘉”时段含谢赴任途中的诗作。同理,“始宁”时段含谢425—428年间任京官时偶涉“山水”的篇目,如《从游京口北固应诏》。
2.谢山水诗写作大体为11年(422—433),总篇数42,年均篇数3.818,高于王维在开元、天宝年间的年平均篇数2.707(41年撰111篇)。若就“纯山水诗”而言,则相反,王年均篇0.829(41年撰34篇),谢年均篇0.2727(11年撰3篇),太低了。
症候二:谢山水诗内涵“太杂”。这从其诗章体式便可见出。今人胡大雷已注意到此。谢山水诗大体是押韵的杂感式游记,其文义构成常有“两分法”或“三段式”现象。“三段式”,是指一首诗由叙事、写景、咏叹(抒情或说理)三方合营。“两分法”,则指一首诗分写景与咏叹两块。《过始宁墅》是典型的“三段式”:全诗22句,中间是“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等8句写景;起首10句属叙事,说自己童心“耿介”,却“违志”仕进,直至被贬永嘉;末尾4句则咏叹任满后还乡归隐。枝蔓杂陈,未臻涵浑。《登永嘉绿嶂山》则取“两分法”:全诗20句,上半部分记游观景,“涧委水屡迷,林迥岩逾密”,计12句;下半部分矢志立言8句,想做“高尚邈难匹”的“幽人”。各自为政,裂隙犹存。
不宜苛求谢作为文学史上的“山水诗祖”,在5世纪上半叶,便能写出三百多年后《辋川集》那样的纯美景象和清穆意境。事实上,谢在“始宁”时段所撰“石门”三章已近“纯山水”②指《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登石门最高顶》、《石门岩上宿》三首。,颇清美幽深而枝蔓不多。但就总体而论,谢山水诗仍属南朝刚从“玄言”母腹分娩的婴儿,故其体式还留着“玄言”的胎记。如下二首是例证:一曰《初往新安至桐庐口》,全诗14句,仅中间“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2句写景,其余一头一尾分属感慨、叙事(10句)与抒情(2句);二曰《富春渚》,全诗18句,起首6句虽属记游写景,但后8句抒怀说理,与中间4句古事古语相链接,致使“说理的篇幅大大多过于写景,读来只感到诗人只是以景物为引子来说理罢了”③胡大雷选注:《谢灵运鲍照诗选》,第11页。。
体式驳杂犹如镜子,映出诗人对要表现的各种元素未能融铸于一炉。此炉为诗艺之炉。这就像酿“五粮液”:原料本是各式杂粮,就看你能否炉火纯青,让杂糅之原料发酵,沥出清澈醇和的琼浆。醇,极重要,不仅味厚,且柔绵悠长,入口即化,让气化的芬芳润泽味蕾。不醇,即不纯,粗,似舌尖上有渣。读谢山水诗,往往读出“渣”来;不像吟诵王维,如浅浅抿一口美酒在喉,便颇陶醉。这就是说,谢山水诗功夫不深。看点有两。
1.颇多官场情绪(如遭权臣排挤的愤懑,与未得宋文帝恩宠之失意等),未经时间沉淀与发酵,即跳过王国维所说“由动之静”之审美心理转型④王国维云:“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王国维著,徐调孚注:《人间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92页。参阅拙著:《王国维:世纪苦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3页。,便仓促织入“山水”韵文。韵文未必是诗。这就欠醇,近乎有渣,酷似农家酿米酒,酒糟尚未滤清,便端上桌来。
2.另些“山水”元素本具审美潜质,但也无心咀嚼,匆匆植入诗行,颇让人扼腕叹息。谢423年春游楠溪,见青山空濛,得“空翠”一词,甚妙;入诗《过白岸亭》却成一句:“空翠强难名。”意谓山色碧翠,美得难以言表——这就煞风景了。恰巧,三百多年后,王维亦以“空翠”入诗《山中》:“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有专家诠释如下:
行走在山路上的诗人,实际上并没有遇雨,但山中的“空翠”——那种朦胧不可实指而又丰沛洋溢无处不在的绿意岚色——却把他的衣衫润湿了。这种无道理的事情,只能是心灵的感受,是超越真实的体悟,在王维山水诗中却偏要把这说成事实,其实恰是他最擅长缔造的境界。①董乃斌编选:《王维集》,第159—160页。
王维有本事将谢曾染指的一个词,“体悟”成一个幽美意境。亦即王似是用身子而非脑子,“切肤”地想像此“空翠”不仅悦目(视觉),更是潮润(触觉)。谢无此本领。看表面,这或许是谢缺少一对王维式“绘画的眼睛”,其实不然,是谢未能像王那般寄情山水。艺术想像的内驱力是情,情不深,想像就长不大,浅尝辄止。
再说“灵魂的耳朵”。谢山水诗从来不缺“清晖能娱人”的明媚插图(《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相比较,他对山水间的“声(听觉)”元素不甚敏感。但不是一点没有。谢430年秋撰《石门岩上宿》,似乎也长“耳朵”了,请听:“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致听,殊响俱清越。”②谢429年秋撰诗《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与从弟惠连可见羊何共和之》也有涉“声(听觉)”元素:“秋泉鸣北涧,哀猿响南峦。”430年春撰诗《登石山最高顶》则有:“活活夕流驶,嗷嗷夜猿啼。”但确实不多。可惜,与其说这“耳朵”是“灵魂”的,毋宁说是“认知”的。因为谢仅仅从“鸟鸣”推测它将夜眠,从“木落”确认正在起风。谢确乎听见了“鸟鸣”、“木落”,却未真正听进心里去。或曰,其心依然古井一潭,未起丝毫涟漪。不能说此诗未写出夜山的清寂幽邃,然与王维《鸟鸣涧》、《辛夷坞》相比,又不能不说,谢的“鸟鸣”、“木落”意象又单薄得像两个词。
症候三:谢价值取向“太乱”。莲社慧远曾嫌谢“心乱”③转引自《朱光潜全集》卷3,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52页。朱说:“在诗史上陶、谢虽并称,在当时谢的声名远比陶大。慧远嫌谢‘心乱’,不很理睬他,但他还是莲社中要角。渊明和他似简直不通声气,虽然灵运在江西住了不少的时候,二人相住很近。”《莲社高贤传》不入社诸贤传云:“时远公、诸贤,同修净土之业,因号白莲社。灵运尝求入社,远公以其心杂而止之。”有两点待考。(一)关于“陶、谢并称诗史”。若特指宋初,则真正“并称于史”者是颜延之、谢灵运。所谓“爰逮宋氏,颜、谢腾声”是也(《宋书》卷67《谢灵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78页)。(二)关于“陶、谢交往”。谢431—433年任临川(今属江西)内史,陶曾栖居匡庐山脚,相距不远,然陶卒于427年。。从心理学角度看,“心乱”即无定力,自控力弱,如不系之舟,随意漂流,也就不易入定,不像王维那般全身心地沉醉于山水。故谢“纯山水”也就做得“太少”;做山水诗,内涵也“太杂”。
同样走近山水,王是“零距离”,把心灵交给大自然;谢不过视山水为其心情调节器。前者旨在“安魂”,具价值性;后者旨在“安抚”,是工具性。前者是“恋”,“恋”有精神归宿感或家园感;后者是“赏”,“赏”仅玩玩而已,人一走,茶就凉。用谢的话说:“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意谓华子岗虽让诗人恍惚间生飘飘寻仙之感,但他又很清醒,游山玩水,只为眼下享受,谁在乎成仙成名传古今呢④参阅胡大雷选注:《谢灵运 鲍照诗选》,第86页。。
检索谢山水诗,用得最频繁的动词,也恰是“赏”和“玩”。诸如:“妙物莫为赏”(《石门岩上宿》);“始与心赏交”(《石室山》);“赏心惟良知”(《游南亭》);“表灵物莫赏”(《登江中孤岛》);“赏心不可忘”(《田南树园激流植援》);“赏废理谁通”(《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情用赏为美”(《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心赏贵所高”(《入车道路》)。还有:“对玩咸可喜”(《初往新安至桐庐口》);“乘流玩回转”(《从斤竹涧越岭溪行》);“目玩三春荑”(《登石山最高顶》)。
有人从谢山水诗读出“双重真实”:“一是诗人确有官场忧虑不能排解,二是景物确实使诗人心旷神怡,此二者都是真实的。”①胡大雷选注:《谢灵运 鲍照诗选》,第24,56页。这是人情之常。然返观诗人平生,又见其实不寻常。这就是,谢的为宦之忧,既非王维的“微官易得罪”,亦非陶潜不甘“折腰向乡里小儿”,而是缘于他若当不成大官,就索性不按常规做官。无非是自恃“官三代”,其祖父有军功于晋,世袭特权,又文才俊美,且与宋武帝次子刘义真情缘超常,刘许诺若得志,将命谢为宰相②胡 大雷 选注:《 谢灵 运 鲍照 诗选 》, 第24,56页。,而谢亦“自谓才能宜参权要”③《宋书》卷67《谢灵运传》,第1753,1772,1774页。;谁知宋武帝长子刘义符继位,杀了刘义真,殃及谢在京城也呆不了,出为永嘉太守;后刘义隆即位为文帝,虽召谢返京,仍“惟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④《宋书 》卷67《谢灵 运传》, 第1753,1772,1774页。,未封重臣,谢更愤愤于怀,不是称疾退隐,便是不理政务,不听民讼,聚众遨游,遍历诸县,动辄逾旬⑤谢422年冬撰《斋中读书》:“虚馆绝诤讼,空庭来鸟雀。”称自己对郡事漠不关心,故人迹罕至,门可罗雀。参阅胡大雷选注:《谢灵运鲍照诗选》,第20页。最搞笑的还有,谢曾“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见《宋书》卷67《谢灵运传》,第1775页。。纵逸如此,岂不反常?
稍知谢的底细,再读其山水诗有涉“隐逸”的意象或意念,也就很难当真。不是说他写“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⑥谢《七里濑》诗含隐居意。严子陵,东汉人,曾与刘秀同游学,后刘称帝,严不受官职,隐居富春江垂钓,垂钩处那段江流称为严子濑,在七里濑上游数里。参阅胡大雷选注:《谢灵运 鲍照诗选》,第15页。“任公”,任国公子,《庄子·外物》以神话笔法写他用巨钩钓鱼,“蹲乎会稽,投竿东海”,诱饵是五十头犍牛。见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06页。(《七里濑》)、“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⑦“颐阿”,涵养之貌;“竟何端”,究竟为了什么。“寂寂寄抱一”典出《老子》22章:“圣人抱一。”意谓诗人甘心寂寞,托身于老庄之道。参阅胡选大雷选注:《谢灵运鲍照诗选》,第18页。(《登永嘉绿嶂山》)等句子时,毫无诚意,是“修辞立其伪”;而是说对谢笔下的“隐逸”须谨慎,与其仓促地将其读成一个词,不如小心地把它分作两个字:“隐—逸”。
准确地说,谢无论做人做诗,皆属“逸而非隐”。这便让他同陶潜的“弃官而隐→隐而欠逸→不逸仍隐”,以及王维的“先官后隐→亦官亦隐→亦隐亦逸”,划了一道异质界限。事情所以弄成这样,因为“隐逸”对谢而言,并非是一种像陶、王那般愿以生命去亲证的活法,而更多地是一个说溜了嘴的口头禅,并不想真照着做的。这其中,三分之一是气话,是对其官场重挫后“逆反心理”的激愤放大;三分之一是遁词,是对其玩心成瘾、纵放为娱的斯文修饰;还有三分之一许是撒娇,注意到谢“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名动京师”⑧《宋书》卷67《谢灵 运传》,第1753,1772,1774页。,便不宜排除它对朝廷或含暗示吧。
八
“逸而非隐”,“逸”是真的。拟讲两条。
1.谢的游览癖堪称“一绝”,他为登山发明的“谢公屐”竟成中华典故,先后出现在李白诗《梦游天姥吟留别》⑨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与当代出版的《古书典故词典》⑩杭州大学中文系编写组:《古书典故辞典》第470页收“谢公屐”条目(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2.谢出守地方官,踏遍辖地山水以尽兴,亦属举国罕见。任永嘉太守不足一年,他接踵逛过的附近景点便有:(1)“西射堂”(距永嘉西南二里,为试士习射之地);(2)“绿嶂山”(距永嘉西北二十里,“上有大湖,澄波浩渺”);(3)“岭门山”(在今浙江平阳,山分左右翼,中阙如门);(4)“池上楼”(灵池,后人称“谢公池”,距永嘉西北三里,积谷山东);(5)“东山”(即永嘉郡东北的海坛山);(6)“石鼓山”(永嘉西约四十里,山上有石,扣之则响,故名);(7)“石室山”(位于今浙江永嘉县小楠溪畔,以石、峰、洞闻名,山上最大的山洞为陶公洞,可容数千人,所谓“石室”即此);(8)“白岸亭”(在楠溪西南,距永嘉八十余里,以溪岸有白沙而得名);(9)“赤石”(在永嘉郡南,山名);(10)“南亭”(温州城外一里处)(11)“孤屿”(即孤屿山,在温州南永嘉江中,长三百丈,阔七十步,岛上有二峰);(12)“白石岩”(乐清县西三十里,下有白石径);(13)“瞿溪山”(永嘉城西南五十里,上有龙潭,瞿溪所出)①以上见胡大雷选注:《谢灵运鲍照诗选》,第15—38页。。
再讲“非隐”,“隐”是虚的。依据有三。
1.谢笑谑“隐逸”者的安贫乐道。
这便与陶潜判然有别。陶清贫得让俗世敬而远之,他就到典故中去追随上古遗烈:从伯夷、叔齐、沮溺到商山四皓……尤其“沮溺”,典出《论语·微子第十八》:“长沮、桀溺耦而耕。”即两人并肩而耕,与周游列国的孔子走的不是一路。李泽厚说:“此乃儒、道(隐者)之分,避政(避开坏的政治)与避世(干脆不问世事)之别。”②李泽厚:《论语今读》,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24页。这让陶思慕不已。陶写过“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因为,“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③陶以“商歌”喻干禄。参阅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74页。(《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故“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饮酒》之二)。然谢对“沮溺”不仅不以为然,且极鄙夷,甚至趁寝食之隙“戏谑”:“既笑沮溺苦”,“耕稼岂云乐”(《斋中读书》)。
2.谢缺乏“真隐”的内驱力。
“真隐”者最想在心理上做到“人世两忘”:吾避世,亦望世界离我远点,所谓“惹不起,躲得起”。照理说,谢若甘心“真隐”,其家境比王维好得多,更无须说陶只能“养真衡茅”了。谢系“太子党”二代,享“国公”之后的待遇,食邑二千户,后因改朝而降公爵为侯,仍食五百户。可见家底之厚。故430年春谢在靠近家乡的石门山构筑新居,其景观、规模恐不在“辋川别业”之下:“跻险筑幽居,披云卧石门”,“俯濯石下潭,仰看条上猿。”(《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修竹茂林》)也因此,七年前,423年秋,当谢执意去职返乡时说“庐园当栖岩,卑位代躬耕”(《初去郡》),是对了一半。有能耐置石门“庐园”当隐居之所,此言属实;但另一半说自己“卑位代耕”则嫌过。毕竟,谢不像王维出生庶族,故亦无需像王“为隐而官”。诚然,更要紧处,是谢的“角色自期”愿像王“微官”般低调么?
不,谢性格逻辑只能是:谁让我这辈子不顺心,我得让你这世间不太平。他要做这世界的一根刺,想撩得世道发毛,否则,他内心失衡。对此,白居易是看明白了:“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读谢灵运诗》)此“泄”分“正、负”两类。“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白居易诗),属“正效应”。还有“负效应”,这就是有恃无恐,连官场规则都不讲,横恣纵诞,游放渎职,惊扰县邑,给朝廷添乱,近乎“恶作剧”。
3.谢在山水间找不到“净土”。
“净土”是谢的说法:“望岭眷灵鹫,延心念净土。”(《过瞿溪山饭僧》)那是诗人423年夏秋之交与山僧游处后所撰。谢少时便接触佛教,后又注《金刚经》,写《辨宗论》,故能“以佛学入诗”。其中有一对关键词:“灵鹫”和“净土”。前者是古印度一山名,释迦牟尼曾讲经于此;后者于佛学则指摒弃浊念的清净世界④参阅胡大雷选注:《谢灵运 鲍照诗选》,第39,75页。。故“延心念净土”,转为白话文,即祈愿让自己内心也净化为寂静的乐土。简言之,谢似亦想“安魂”。七年后,谢所以兴土木,筑石门新居,其心思仍在“庶持乘日用,得以慰营魂”(《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修竹茂林》)。有人释“营魂”即心灵,意谓希望能借朝夕居山观景来抚慰悲苦之心⑤参阅胡大雷选注:《谢灵运 鲍照诗选》,第39,75页。。
然纯审美的视觉快感救不了灵魂。山水美感的内核委实是谢所重申的“赏”,而拯救灵魂的要害却是“恋”乃至“信”。“赏”是图瞬间欣悦,“恋”当有精神寄托,“信”则需百折不挠地诉诸日常人伦操行。谢所做不到的,恰恰是对山水为“隐逸”符号的价值活法的“恋”和“信”。
有此铺垫,再来读谢的这四句诗:“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入彭蠡湖口》)也就别样滋味。先看体式,这是两组对仗工整的诗联,却格调不一。前者是谢诗名联,宛如彩色画卷,状溢目前;后者是转入内心,近乎黑白玄言(其“日—朝”为白,“夜—昏”为黑)。你可以说,这是南朝山水诗从百年玄言樊篱突围的遗痕;你亦可说,如此“蒙太奇”组接,倒恰巧凝冻了谢内心挣扎的“类复调”境况。这是另两种“真实”的内在冲突:一方面,谢确凿想借纵娱山水来冲淡心灵焦虑(此谓“真实”);但另方面,风景再美,也无计平息那颗暴跳狂奔的野马之心(此亦“真实”)。所以说是“类复调”,而不是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经典“复调”,是因为陀氏小说所呈示的两种声音皆是有内涵的价值取向,但又冰炭难容;而谢之“心乱”,则属虚妄,与其说这植根于他“要什么”,毋宁说是源自他“不要什么”。“要什么”是根基性价值预设,具建设性;“不要什么”近乎非原则性情绪反弹,有破坏性与溃疡性。有人说:“综观灵运一生,积极谋取政治权势是他内心世界的主导。”①胡大雷选注:《谢灵运 鲍照诗选》“前言”,第6页。这说对了一半。有待说破的另一半或许更重要,此即当谢屡屡揽不着大权,他就不可逆地失态,痞子般撒野,有点“我是流氓我怕谁”。《南史·谢灵运传》称其“猖獗不已,自致覆亡”②《南史》卷19《谢灵运传论》,《二十五史》,第2730页。,也就难免。
不妨重温朱熹一段话:“晋宋间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淡,那边一面招权纳货。渊明却真个是能不要,此其所以高于晋宋人也。”③朱熹:《朱子语类》卷34,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874页。这是在说陶,然亦在说谢。
2011年新春于沪上学僧西渡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