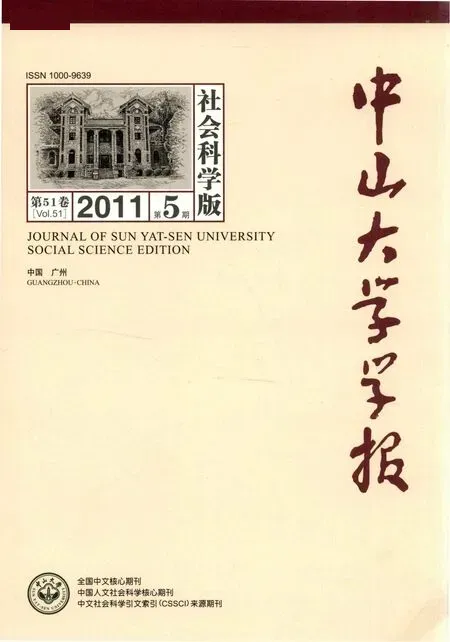回顾围绕“那种”政治神学的争论*
迈 尔著,张羽军译
政治神学而今是常见概念。这个概念即便不尖锐(akut),也在行动(aktuell)。这个概念获得了多声部的公共反响:政治—宗教激进主义的挑动、指向启示信仰的回转以及人们对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的新关注。公众以前从道听途说(Hörensagen)中几乎不熟知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服务于“那种”政治哲学,区分出(Unterscheidung)“那种”政治哲学铺陈哲学生活基础时和理解哲学生活时的捕捉之险(Unterfangen)。在围绕施米特而结束的讨论中,施米特而非其他人的名字与这个概念连成一体,政治神学代表了讨论所冲撞的坚石;这块坚石不得不检验讨论中的论析之真。在上述种种语境中,这个概念的行动基于这个概念实事的行动;历史学家们论及巴枯宁笔下的否定和施米特笔下的论断时,一再为这个概念的实事找来另一种实事:这种实事的规定(Bestimmungen)合并了权威、启示和顺从。只要政治神学这个概念理解了把神性启示宣说(in Anspruch nehmen)为自身终极基础的政治理论或政治教旨,政治神学这个概念就在行动。某种意义上,独独献身政治理论或政治教旨的杂志和年鉴,及无数专著、语言不同的卷集和“指南”、全世界的知识宴会和智识人论坛都从事了政治神学;政治神学在当代的政治辩论中有其地位;政治神学的理论充满了宣说意义,以凭靠信仰的顺从而理解自身,与哲人们攸关。
除了这个实质概念,还有某蹩脚用法,不尊重这个实质的概念,把“政治神学”降为20世纪下半叶侈谈的“世俗化理论”(Säkularisierungs-Theorem),意欲只以“政治神学”中的历史论题(These)为真。这种用法引用了施米特1922年名为“政治神学”的著作中以“政治神学”为标题的第三章第一句,不围绕施米特的立场而以这句为施米特对政治神学的“定义”:“现代国家学说铸就的所有概念是世俗化的神学概念。”依此读法(Lesart),“政治神学”不指包罗万象的(umfassend)理论,不指原理上的基础关联(prinzipiellen Begründungszusammenhang),不指实存的论断。“政治神学”毋宁描绘了维持概念的历史或知识社会学预设;规范和历史“颠覆法则”之间的“结构类比法”处理着这种维持和预设,把这种维持和预设的射程限定于“西方理性主义”和“现代国家纪元”的覆盖区域,或限定于“新时代”(die Neuzeit)。对“政治神学”的蹩脚铺陈,虽然从对施米特的读解(Schmitt-Exegese)中衍生,但没有一次有效地论析施米特的思想。所以,蹩脚铺陈既没有追问施米特凭政治的概念所注目的“具体命题的对立”,也没有想到施米特可能已变“政治神学”概念本身为具有丰富历史结果的“颠覆法则”的对象。至1988年,蹩脚读法还主宰着施米特的解释者们(Interpreten),而“那种”政治神学充满了宣说意义,远未被理解为施米特思想中心(Zentrum)及与其关联的东西。
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和施米特的通信最近发表,许我一瞥铺陈“那种”政治神学的早期立场。1966年,布鲁门伯格在一部举其关切核心为题、内容颇丰的(umfangreich)作品中,针对有关世俗化的诊断和谴责,护卫了“新时代的正当性(Legitimität der Neuzeit)”。布鲁门伯格把对世俗化的诊断和谴责撵回“历史的不义范畴”。出于自我维持的历史必然,布鲁门伯格护卫了现代此世的自我理解和现代此世的善义(Gutes Recht),尤其针对洛维特(Karl Löwith)的《意义与历史》(Meaning and History),而当时,布鲁门伯格并不熟知施米特1950年对洛维特的答复。布鲁门伯格引用了《意义与历史》第三章的第一句,谴责施米特。布鲁门伯格直接使人认识到:历史废弃了“政治首要性(Primat)的化身,新时代的发展赶过了政治首要性的化身:非政治的政治规定——即出让给‘此世’权能的神学规定的类比物”。1970年,在《政治神学续篇》的《后记》中,施米特把布鲁门伯格这本《新时代的正当性》选为现成见证,引至众人眼前,咬住此书,嘲弄此书,并了结此书。施米特澄清了自己的选择,布鲁门伯格的书“绝对”为“绝对虚无”定了法则:
在科学概念的意义上(宗教福祉学说[Heilslehre]绝对地自定法则,继续作用着,颠覆着法则,而科学概念丝毫不算作这种学说)以科学否认每种政治神学,这些被颠覆的法则,对于布鲁门伯格,只是逝去诸纪元悲哀的债权,此世去神学的新—时代清除了这些债权,不留残余。
对于施米特的政治神学,如此否认每种神学、每种绝对宣说、每种无条件的顺从要求,意味着佩特森式政治尝试的又一次“挑衅(Challenge)”——“佩特森指出,‘政治神学’不可能成为神学”;也意味着要按施米特自己的标准,阻止佩特森力挺的政治神学“政治地误用”基督教真理。施米特突出:布鲁门伯格已凭“新时代的正当性”这个标题升起“一面法学旗帜”。施米特看出自己被挑动了,要“从我们搞法学的这边,讲出一些疑难的而今处境”。《后记》不只向布鲁门伯格,这位关注施米特政治神学的读者,亲切提出问题:施米特凭1922年的标题升起了一面什么样的旗帜,高龄施米特而今再次升起了一面什么样的旗帜;还让布鲁门伯格注意:施米特自己讲“从搞法学的这边”言说时,讲出了什么样的话。施米特最后独立出版了最爆炸、最明亮的部分,以如下立场为我们定下法则:以一个暴露无遗的例子检验“搞法学的”天职;正确地整理出在施米特后期作品修辞中扮演显著角色的姿态(Gestus)。
施米特直接答复了布鲁门伯格,回击了布鲁门伯格的进步信仰和对历史上受压制国家的估价。布鲁门伯格绝对地宣说这种国家,“苛求无国界的牺牲意义”,牺牲意义内在地避免了内战。至此,施米特似乎事实上完全作为法学家在言说,不过将政治神学描述为“颠覆法则”;颠覆法则“经典地(Klassisch)”遭遇了某些法学家捏在手中并力挺的教会和国家效用领域的概念。当然,施米特丝毫没有“讲出疑难的而今处境”。施米特就而今处境“从搞法学的这边”不得不讲了什么,稍后述及。因为施米特的答复独独牵扯了“新时代的纪元转折点”上教会和国家之间“经典的法则颠覆事件”,所以,施米特淡化了仅由宗教法学者和法学家们规定、经典的法则颠覆事件之外的所有历史“阶段”。1922年版《政治神学》所冲撞的中心,就是“平行”的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牵扯“经典事件”的要点是,在施米特的描述中,宗教法学者们和法学家们力挺基督教的世界制度,且新时代初始的“法则颠覆”发生于基督教的土地。“法学家们”出于基督教信仰,将诸如全能上帝的神学概念捧着转交给此世的主权者。为了和平与理性,现代公法的世俗文化行动和现代国际法的奠基者们继承了天主教神学家们的遗产,尝试拯救由于信仰分裂而不得不拯救的东西。现代公法和现代国际法的奠基者们答复了历史的“号召”,不再把持神学家们在国家效用领域的沉默戒律,指出了逃离宗教内战的道路。敌基督的意图并没有担负现代公法和现代国际法奠基者们的世俗化行动;完全相反,基督教予世俗化行动以灵感。博丹(Jean Bodin)和霍布斯,被施米特称为“朋友”,在“施米特对他们思想的铺陈”中坚持“不只表面上信仰他们的教父们”。总之,施米特的祈祷锁闭了法学家们在纪元转折点上的灵魂,施米特视这些法学家为实质概念意义上的政治神学家。
施米特的《后记》以对《新时代的正当性》的批判结束了他缔结的政治—神学的文论,认识了“了结每种政治神学”行动着的尝试。“了结”不只予施米特以机会,在辩论中把持住后期作品中的诸论题——欧洲公法中合法批判的历史成就、法则与福音的对立命题、礼法与法则的区分、霍布斯国家学说“所完成的改革”,而且也允许施米特以布鲁门伯格对施米特政治神学基本规定的批判为中介,言说——神迹、敌友区分、系泊于上帝教义的“政治形态”世界、人类称义的必需和拯救的必需。施米特没有逐一格正布鲁门伯格之义。施米特以整体为目的。布鲁门伯格认识“法则的符合”,施米特从中看出对神迹的否定;布鲁门伯格解放“好奇心”,施米特从中看出不再意欲将渎神当真的渎神;布鲁门伯格强调“自我理解”和“自我维持”,施米特从中看出神迹自我授权,以与神性秩序对神迹的束缚相争论。“自我—授权”译成政治—神学的法则,就意味着暴动,即“自闭症”弃绝了对上帝的顺从义务。对于施米特,布鲁门伯格的去神学化包含了世界的去政治化。如果渴求顺从的上帝不再统御世界,世界可能不再是主与对手(Widersacher)所争论的对象,不再是创世上帝和救赎上帝所争论的对象,那么这个世界就止于“政治形态”。如此,上帝的判决所打击的人—世界就只有顺从和暴动。以此判决,施米特针锋相对地论断了他的政治神学和每种政治神学:惟有人自己能反对自己(Nemo contra hominem nisi homo ipse)。
施米特使去神学化世界和去政治化世界的关联生效了;去神学化世界和去政治化世界的关联作为正义的结果,屈从于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政治的概念将政治引溯至一组三维星群(eine triadische Konstellation)——堪为自然、法和超自然三位格——这组星群能够在万物和每个时代中闪现,并定下法则,使政治区分与连体/分离最为表面的紧张程度起作用。敌友区分的导向使政治和神学有共同度。1927年、1932年、1933年三次驱使并修缮政治方案后,施米特才能在1934年第2版《政治神学》的《绪论》中澄清:“从此,我们全面认识了政治。”如果不只通晓敌友区分、对顺从和不顺从的抉择、顺从地合体(Assoziation)或不顺从地解体(Dissoziation)的人—世界,还通晓万物、整体、世界,那么只能全面理解政治。施米特先行“暗示”,他突出地将去神学化和去政治化编织为《后记》的中心。“暗示”强有力地使政治的概念和政治神学交叠,使上述的政治三维星群处于交叠核心。施米特以看起来相当常见的短语“另一暗示”——“政治和政治神学的标准,即敌友区分”——主导了有高爆炸力的星相定位。结果是,施米特尝试将三维星群赶入三位一体,或以三位一体为三维星群的结果。施米特拉来额我略·纳齐安(Gregor von Nazianz)的名位;而佩特森曾唤来这尊“封合基督教三位一体学说”的名位:太一总搅动自身。“这沉重的教条毫不婉转,表达了”,施米特对这位教会学者评注着,“我们一旦感觉到搅动,就遇到骚乱(Stasis)这个词”以及搅动的结果:可能的敌对。施米特诊断出,我们“遭遇了三位一体学说核心中政治—神学真理的骚乱学”,或“遭遇了”敌对之疑难和敌人之疑难。施米特指出“神性本身而非造物的三一(dreieinigkeit)秘密”,不只较迟答复了佩特森对政治神学之非可能性的维持;新时代一劳永逸,克服了“灵知病发(Recidiv)”,同样,施米特针对布鲁门伯格的去神学化行为,抗议布鲁门伯格的信念行为,呼唤了施米特依靠的信仰基础。“圣父和圣子一元,不绝对同一”,虽然“被裹着”,“却是‘一元’”,或者虽然——返回了无基础的上帝,但没有失去力量①《政治神学续篇》:“灵知二元有韧度,难以放倒,并不基于光和黑暗的古代秘说斯形象和隐喻形象;而代表:全能、全知、全善的创世上帝在其创造的世界中与救赎上帝并不同一。奥古斯丁(Augustinus)把神性之困难贮存于被上帝创造、随意(mit Freiheit)布设的人之自由,也如此贮存于创世。而起初,创世凭上帝借出的自由的力量,使上帝不必需救赎的世界变为上帝起初必需救赎的世界。创世立于救赎的必需;人不以事功保自由之真,而以恶行(Untaten)保自由之真。三位一体学说以不绝对同一的圣父和圣子一元围裹了创世上帝和救赎上帝的同一;尽管上帝—人二性(Natur)的二元在人之位格中变为一元,但是圣父和圣子不绝对同一而‘一元’。”,从中,施米特看出创世上帝和救赎上帝的灵知二元。施米特继续写至最后,尝试将“政治—神学的骚乱学”的洞见固化为歌德(Goethe)的格言:惟有神自己能反对自己。施米特相信自己已经发现了这句格言的基督学出身,以基督学阐释了这句格言是圣子的呼告,拥护了圣子一派,是圣子与(gegen)圣父的连体。
经上述准备,施米特再一次将政治系泊于神学,更将政治和神学合并在一起,打算“借敌人的问题提出政治神学的疑难”,以歌德的警句为“一些论题”的导向,并借“这些论题”与布鲁门伯格和隶属布鲁门伯格的论断交锋。施米特形成了七个论题,规定了敌人的论断。七个论题预备了“思想—序列(Gedanken-Reihen)”,而“去神学化和现代—科学”在其中活动,“毫无残余地了结每种政治神学”,如此逮住某不意欲拥有敌人的敌人。施米特坚持影射多伯勒的句子(Theodor-Däubler-Wort):敌人塑造了我们自身的问题。施米特“最后一次勾勒了对手形象,更清楚地认识自身的论断”。这个对手形象显示了一个“新人”,他在不停止的进程—进步中炫耀自己,意欲摆脱自己的敌人,因而必须重新养育“出自虚无的反面创世,即虚无之创世;自我创世的此世,历久弥新,虚无之创世是其可能条件”。读者只要不旁骛对“对手形象”草图的达达主义式抄袭,就不会混淆施米特的嘲弄和严肃进攻,并揪住施米特关于布鲁门伯格论题的七个反论题,围住施米特自身论断的裂口。而重中之重的事件是,施米特甚至操心起精确形成论题和反面论题来。惟有人自己能反对自己这个论题,作为法则结束了反面论断的“思想—序列”;一开始,这个论题作为反面论题甚或反面论题的先在形象,与“惟有神自己能反对自己”这个警句对立,而施米特毫无压力地以这个警句为七个论题的“方向”。而且,施米特先前同样毫无压力地澄清,“对手形象毫无保留地去神学化”,将密封终审判决,从中,他也认识到“实际可能”的敌人。只有上帝能毁灭上帝创造的敌人,施米特基于这个信仰,护卫了政治和政治神学。《政治神学续篇·后记》的末尾,合并了政治—神学;谁还没有忘记施米特在《政治神学续篇》开始处的预示——他也“从搞法学的这边讲出一些”政治神学之疑难的“而今处境”,谁就会细读布鲁门伯格的七个论题,按歌德—格言的基督学式阐释,按三位一体导出的“骚乱学”,知道(wissen)如何接过施米特的教内法学家天职。
布鲁门伯格未反拨施米特的挑动。1974年,布鲁门伯格以《世俗化与自我维持》(Säkularisierung und Selbstbehauptung)为题新订了《新时代的正当性》包含专论施米特政治神学一章的第一部分,将新订本寄给施米特。1971年,在《政治神学续篇》发表几个月后,布鲁门伯格第一次接触施米特。在附寄的信中,布鲁门伯格希望施米特作品“而今能更正义地安置世俗化概念”。布鲁门伯格的答复是历史学家的答复。施米特“以正当的名义规劝”布鲁门伯格“只可颠倒合法的新时代”,而布鲁门伯格从没有见过如此这般的挑动,因为他看到,“正当名义”与他的问题提法和论题的“历史品质”相争。“异见很难有分量。”对于历史学家,没有比规劝不要成为优秀的历史学家更有分量的规劝。布鲁门伯格相应地护卫自己:他“所指的新时代的正当性”是“历史范畴”,因为“纪元的合理性被把握”为“自我维持,而不被把握”为“自我授权”。施米特抛出称义问题,攻击“自我—授权”,而布鲁门伯格意欲以历史挡开施米特的攻击。“纪元观念极度地必需自我维持,以虚无为前定法则自我奠基,并从中走出来——这恰好不叫做:自我—授权。”“纪元观念”以历史为基础。自我维持顺从了历史必然,以自身顺从历史的方式,免除了自我授权的指责。布鲁门伯格相信:历史天职——历史天职被正义地、历史地且只能历史地把握——足以击退施米特的批判。布鲁门伯格将施米特的批评理解成政治—历史的批评:
正当的纪元应该被理解,应该不接续正当纪元的前历史,这使施米特显出了自身教条的抵触,而教条的抵触让施米特不相信:实证法则理性潜在地骚乱着,反对实证法则理性的合法性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可以讨论。
施米特“必须”使新时代的正当性“显出教条的抵触”,因为布鲁门伯格正义地不接续历史,而历史的接续以政治为基础,揪住了不同于布鲁门伯格的施米特;施米特不畏缩,使历史符合施米特的目的,这叫做,高度非历史地铺陈历史、运用历史。
差别的核心是:对于国家理论家施米特,世俗化是正当范畴。偶然的世俗化危及当代,为当代开启了历史的纵深维度。世俗化努力创造同一的历史,而“其他介质”很少发生同一的历史。世俗残余的化身甚至是“那种政治神学”;据称,“那种政治神学”同一地牵引传统,可“那种政治神学”的名称只掩盖了:“政治”据称是“神学”。历史因素必须强行先验地与法学实证主义连成一体,而历史因素抽走了以自为真的实证命题。
政治—神学的攻击以布鲁门伯格为事实法则,却被布鲁门伯格错误认识,因为,布鲁门伯格硬来,提前彻底地占领自身的历史正当和施米特的历史正当。布鲁门伯格而今将世俗化澄清为施米特的“正当范畴”,而《政治神学续篇》的暗示扼要地纠正了新时代纪元转折点的“经典法则更替事件”,公开地、显眼地压住了布鲁门伯格。可是,新秩序几乎没有抓住施米特的“世俗化进程”提法,而早期秩序,让施米特的非正当范畴显现了世俗化,也没有理解施米特的提法。早期施米特没有以同一的“世俗残余”最终有效判断出被法则更替、被类比、被推导的上述非正当历史,晚期施米特也没有让“世俗残余”高贵得担负起正当历史。无论施米特将国家的建立低估还是重新高估为新时代开端的世俗化成果,施米特提出的世俗化整体进程和终末进程,被看成“公共生活去基督化和去上帝化的进步进程”:1922年至1970年还是没有变。世俗化概念服务于早期施米特和晚期施米特,使新时代的发展和神性启示连成一体,将基督历史可能的诸形象转用于神性启示,遭遇了神性启示“阶段”中去政治化和去神学化行动的尝试,“历史地—具体地”处理这种尝试。
但是,相关联的东西决定了:“世俗化残余”是施米特政治神学的化身,而布鲁门伯格将施米特政治神学理解为以政治为目的的神学或带有“其他介质”的政治。正如之前的许多解释者,布鲁门伯格将施米特看作法学家——将施米特,这个力挺“法学实证主义”的不平常变体,看作法学家——抑或,布鲁门伯格宣说一种传统,允诺或伪造正当性,并紧握神学的布景物件,将施米特看成一位尝试掩藏深渊中缺乏基础的政治决断论的国家理论家。布鲁门伯格以“政治神学及续篇”为题,反拨施米特,却没有认识到将掩饰政治派别的神学之外的东西与“政治神学”连成一体。一开始定位施米特的“世俗化理论”,布鲁门伯格还真的有些矜持,注意到:“施米特‘那种政治神学’方法论值得注意”;“‘那种政治神学’本身”赋予“世俗化纽带”以总体“价值”,“因为,我曾指出,政治神学将政治的概念的神学现象性解释为实际政治绝对品质的结果,颠倒了基础关联,其意图易见”。围绕历史现象的正义解释,布鲁门伯格仿佛在求教这位学人,却同施米特这位学人搏斗,否定了与这位政治神学家关联的基础,由于这种基础,政治有了神学基础和神学意义。凭着政治的神学地基,布鲁门伯格立即同施米特的神学严肃天职或形而上严肃天职相争,而在两部论著中独独牵扯到布鲁门伯格的第一部,施米特决没有言说“实际的政治绝对品质”,更没有毫无压力地言说“一切政治的形而上核心”。布鲁门伯格在反拨的末尾停止了开始时的矜持。布鲁门伯格将政治神学澄清为“隐喻神学”,毫不怀疑这位“政治神学家”而今跨到法学家和国家理论家的位置,对布鲁门伯格讲太多,阐释得太多,像一位政治观念家。“历史思考”省去以政治为目的的宗教发明,根据担保布鲁门伯格真理的康帕内拉(Campanella),宗教发明以亚里士多德的后果“马基雅维里主义”为特征,因为这位“政治神学家”敢于担负历史正当的天职,即历史提前发现的、在历史的颠覆法则中持续作用的宗教天职——布鲁门伯格的历史启蒙意欲不裹住这种天职,使这种天职没有力量。布鲁门伯格以“世俗化的采纳”结束了针对政治神学的这一章,而“世俗化的采纳”使这位“政治神学家”提前发现不了推演出来的东西。因为在总体地论析自我理解的政治神学前,布鲁门伯格没有在任何时间点宣说政治神学的真理,没在任何时间点把政治神学降为被神学修饰的政治,所以,布鲁门伯格最终反而只用以信仰为基础的论断为施米特定下法则。这位哲人,因布鲁门伯格的观念论批判而平和,收获了最大的战利品。政治神学的挑动,在概念的实质意义上,为这位哲人宽泛地守住了这份战利品。
1974年10月20日,施米特写给布鲁门伯格一封长信,答复送来的《世俗化与自我维持》。这封信礼貌得字斟句酌,委婉得引人分心,而双方所有通信都有礼貌和委婉的特征。布鲁门伯格重新阐释“世俗化理论”,而施米特对此没提一个词,以沉默代替对布鲁门伯格“神学政治”的批判。在信末“对主题本身”做了“两个简注”之前,施米特都没有讲“世俗化理论”和“神学政治”两项事业。布鲁门伯格瞥向被降为结构类比法概念的“世俗化理论”,并提出问题,而第一个简注便触及到这个问题:
无论一种前形式结构来自另一种前形式结构,还是两种前形式结构来自一种共同的前形式结构,结构类比法不暗中“维持前形式的起源”:如果国家暴力的单一政治化结构和被规定的政治机关暴力的单一政治化结构与神学的全能属性结构同样得到维持,那么,神学的全能属性只还牵扯着与系统关联的一些秩序。共同的全称量词“全能……”标识了这些秩序。但是,神学的全能属性正义得能为“政治神学”的国家理论而言说吗?
此处施米特标注:“我明白的答复(答复得细致清晰,大大令我快乐):对(Ja)。”布鲁门伯格决没有要求施米特献上“细致清晰”,施米特那儿却留着简洁的“对”。施米特将谈政治神学的正义放在了哪,可不难认识。主权者自己宣说了“全能”,其举动为正当化神性全能或篡夺神性全能。施米特的政治神学尝试在竞赛场中把持并安置对手:上帝的主权牵扯着主权者的顺从和反抗。哥伽腾(Friedirch Gogarten)和德·科菲尔维恩(Alfred de Quervain)等新教神学家早就看出:施米特《主权学说四论》(Vier Kapitel zur Lehre von der Souveränität)已窜至上帝的主权,并系泊在那里。第二个简注与第一个简注有区分,既没有答复布鲁门伯格的“一个明白问题”,也没有遭遇布鲁门伯格反拨中的特别位置。第二个简注毋宁包含了施米特对布鲁门伯格那整整一章的答复,并显示,这个“86岁的老头”能如此精细:
四十多年来,我收集着“捕捉(Κατ'εχων即Κατ'εχον)”疑难的材料(Thess.2,2,6);这么长的时间以来,我寻找着倾听并理解这个问题——对于我,是(我的)政治神学的核心问题——的一只人耳。尽管以也许辜负我自己的终极方式,我无法在洛维特那里找到意义,令我哑然,但我有义务不就此对您沉默。
“历史具体”被理解为施米特天职“抓住”的基督教意义;施米特不只毫无压力地限制将“历史具体”误解为继承狄尔泰(Whilhelm Diltheys)的历史类型学说,限制“历史具体”与韦伯(Max Weber)的观念类型任何可能的混淆,还额外为布鲁门伯格铺陈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发表的论文《三种可能的基督教历史形象》。施米特在第二个简注中给出的答复,与他在第一个简注中分担的内情同样明白。如果被保罗式捕捉的疑难是那种政治神学的核心问题,那么,“那种”政治神学既不能被限制为“世俗残余”的“化身”,也不能被限制于现代国家纪元或新时代的射程。“那种”政治神学不能降为结构类比法,不能无害地成为知识社会学的预设。且如果,被捕捉的疑难处理了施米特政治神学的核心问题,然后施米特被他的批评者们理解了,那么布鲁门伯格以《政治神学》及续篇为题,就进一步捕捉了施米特的政治神学,更不用说击中了施米特的政治神学。在围绕“那种”政治神学的争论中,施米特射向布鲁门伯格的最后一句,是与施米特诸立场相应的片段:“那个马姆斯伯里的老人”向对手布拉姆哈尔大主教(der Bischof Bramhall)及其《捕捉利维坦》(The Catching of Leviathan)一书讲:“阁下这会儿没捕捉到任何东西。”
“政治神学”概念的立场一千五百年以来不受剑刺,不允许凭自我性情而转用“政治神学”的概念。奥古斯丁(Augustinus)打下的传统基础,几个世纪以来被大家占有,毫无问题,将“政治神学”降级为神学的政治滥用,或烙上政治欺骗的特征。“三分神学(theologia tripertita)”可回溯至较早的廊下派波赛多尼奥斯(Poseidonios)和帕奈提奥斯(Panaitios),被瓦罗(Varro)的《人神古纪》(Antiquitates rerum humanarum et divinarum)经典地安置;一开始,奥古斯丁就处理了“三分神学”。“三分神学”区分了三种诸神种属(Gattung)——秘说斯出身(génos mythikón)、物性出身(physikón)、政治出身(politikón)——前置了符合秘说斯(或诗术)神学、物性神学和政治神学的三分神学,借此秩序化了诗人们、哲人们和城邦民们。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中定位三种神学①“我现在谈三种神学:希腊文中叫秘说斯神学、物性神学、政治神学;拉丁文中可叫虚幻神学、自然神学、城邦民神学(Nunc proter tres theologias,quas Graeci dicunt mythicen physicen politicen,Latine autem dici possunt fabulosa naturalis civilis)。”参奥古斯丁:《上帝之城》VI,12。,尤其注目于瓦罗和罗马共和国政治神学的杰出代表昆图斯·穆奇乌斯·斯凯佛拉(Quintus Mucius Scaevola)皆知的政治神学的非真理特征。奥古斯丁将这位在罗马享受高声望的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②西塞罗称老师斯凯佛拉为“我邦的非常圣徒和非常完美者(vir sanctissimus atque ornatissimus nostrae civitatis)”。Pro Sex.Roscio Amerino 33。拖入尖刻批判。于是,奥古斯丁言说了对“政治神学”的判决①奥古斯丁:《上帝之城》IV,27 及 VI,5.3;亦参,III,4;VI,2,4 -6,10.3。注意西塞罗《论神的本性》(De natura deorum)III,3。。此后,“政治神学”概念错合了(kontaminiert),未来与私敌特征、对立派别特征、行将了结的论断特征不同,谁还敢转用?——施米特以他的政治神学冲破绝罚,冲撞概念和实事之门,此前,没有一个理论家转用概念以规定自身的论断。
为何施米特不摊开政治神学充满宣说意义的论断,以封合这种论断?我意欲总结对这个问题的答复,1988年和1994年的两本书也答复了这个问题。(1)意欲以凭靠信仰的顺从理解自我的理论家和施米特,拥有首要性以处理他人。施米特作为理论家,其表达以施米特处理的“历史具体”诸目的为比例尺。若施米特形象化了概念,摊开了概念,那结果为,施米特在“时代的秤盘”上展开概念,他会不停地顾及这种效应。在秘密的基础上把持政治神学,或隐藏政治神学至已知程度,处理政治神学的游戏空间就能扩宽,就更可能接纳同盟或赢得外行;如果同盟、捕捉者或外行不得不声援这位政治神学家的议程或理解这位政治神学家,施米特就不会触碰这些同盟或捕捉者。不管老年施米特如何抱怨长年珍藏的关切找不到“人耳”,对于施米特,不让敌人看穿自己,更为重要;任何一个人在与施米特关联的终审级别上有效地理解施米特,即任何一个人像施米特理解自身一样理解施米特,这不重要。(2)施米特害怕作为“业余神学家”论析教会神学家们公开的神学教条。施米特不只受教于前行者们一次次“可悲的事件”,还尤其受教于历史处境所变更出的清算。基督教政治神学的信仰分裂产生了这种清算。施米特跟从政治神学家兼法学家的先在形象德尔图良(Tertullian),带着法学家的面具(Persona)登台,处理其政治神学的意义。天主教和新教职业神学家们分别宣说了诸教条领域乃至原罪诸教义和三一诸问题,而施米特甚至不重视教义原文的保障,径自铺陈、安置这些领域和教义,申明“从法学家们这边”言说。(3)阻碍施米特展开与其政治神学关联的、担负其政治神学学说的最重要基础是——这包括或超过所有其他基础,施米特不意欲一场共同辩论,为所有基础的(施米特的)信仰核心(Glaubenskern)付出代价。施米特如果要真理式地保留信仰中心(Glaubenszentrum)这个“秘方(Arcanum)”,那么最好保护信仰中心。施米特以启示神学的洞见强化自己,可能发现了:若不护卫上帝全能之外的东西,将回落入无基础的上帝全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