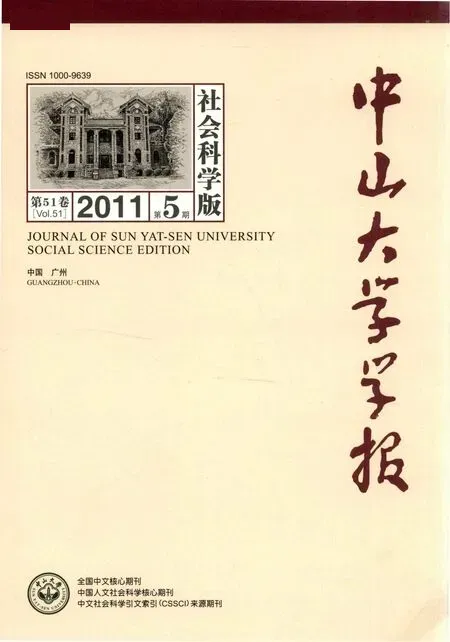伊斯墨涅的面纱之后*
魏朝勇
在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忒拜剧(Theban Plays)中,流芳百世的女性形象无疑是安提戈涅(Antigone),而与安提戈涅共在的妹妹伊斯墨涅(Ismene)几乎难以得到后世思想者的青睐。尼采于其《悲剧的诞生》中提及两位古典女性——安提戈涅和卡珊德拉(Cassandra),认为前者体现了“日神”精神、后者体现了“酒神”精神①参见 Nietzsche.The Birth of Tragedy.in Basic Writings of Nietzsche.trans.Kaufmann.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1968,p.47,n.2.卡珊德拉(Cassandra)则为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中的人物。,但不曾说起伊斯墨涅。西方学界的古希腊悲剧研究中确有不少轻视伊斯墨涅的微辞,伊斯墨涅往往被认为是自私、怯懦和卑微的②参见 Winnington-Ingram.Sophocles:An Interpret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pp.133—134.。然而,这样的观审只是停留于伊斯墨涅的面纱;撩开这层面纱,或能看到一个饶有意味的伊斯墨涅。
一
我们首先要倾听俄狄浦斯(Oedipus)的悲叹。在《僭主俄狄浦斯》③文中凡引自《僭主俄狄浦斯》《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安提戈涅》的原文,主要采用罗念生的译文(《罗念生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但参照Jebb的古希腊文—英文相对照的笺注本(Sophocles.The Plays and Fragments.Part I.The Oedipus Tyrannus.Part II.The Oedipus Coloneus.Part III,The Antigone,notes.comm.and trans.Jebb.Cambridge:At the University Press,1893,1889,1889)对译文作某些改动,并附上一些古希腊文语词;直接和间接引文都随文标注传统行码,古希腊文语词转化为拉丁写法。的“退场”中,已经刺瞎了双眼的俄狄浦斯知道自己终会被放逐,他放心不下一双女儿,于是幼年的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被带进宫中。俄狄浦斯对女儿们泣诉道:
孩子们,你们在哪里?快到这里来,到你们的同胞手里来,是这双手使你们父亲先前明亮的眼睛变瞎的……我看不见你们了;想起你们日后辛酸的生活……我就为你们痛苦……什么耻辱你们少得了呢?“你们的父亲杀了他的父亲,把种子撒在生身母亲那里,从自己出生的地方生了你们。”你们会这样挨骂的;谁还会娶你们呢?啊,孩儿们,没有人会;显然你们注定会不结婚(agamous),不生育(chersous),枯萎而死。[1480—1502]
瞎眼的俄狄浦斯“看”到了女儿们的未来命运。女儿们的命运都是俄狄浦斯铸就的。她们是乱伦的产物,从一出生就违背了人世伦理的自然秩序。“不结婚,不生育,枯萎而死”——对于女性而言,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结局更悲惨。安提戈涅(Antigone)的名字本就蕴有“不生育”的意思①参见 Bernardete.Sacred Transgressions:A Reading of Sophocles'Antigone.South Bend:St.Augustine's Press,1999,p.9.。伊斯墨涅的名字虽不具相似的深意,但她的命运将与她的姐姐有所不同吗?
陪伴俄狄浦斯流浪于异乡的是长女安提戈涅。《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的“开场”里,俄狄浦斯对科罗诺斯的本地居民说:
老乡,我听她——这女孩儿的眼睛(horōsēs)既为她自己又为我看路……[33—35]
在俄狄浦斯说出这番话语的一刻,人们不禁要问——伊斯墨涅在哪儿?为什么只有安提戈涅陪着父亲一道在异乡科罗诺斯颠沛流离?为什么只有安提戈涅才是俄狄浦斯的“眼睛”?
如果我们只怪索福克勒斯创作的偏心,那就过于简单。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的“第一场”便让伊斯墨涅现身了。安提戈涅的“眼睛”确实犀利,她首先看到妹妹飘然而至。安提戈涅说:
我看见一个女人骑着一匹埃特那(Etna)小马到我们这儿来了,她头上戴着一顶贴萨利亚(Thessalian)宽边毡帽,给她遮太阳。那是谁?是她不是她?也许是我想错了吧?说是她,又说不是她,我说不准。啊!那不是别人。她上前来,用炯炯的目光招呼我,她分明是伊斯墨涅。[311—321]
安提戈涅用“眼睛”所描绘的伊斯墨涅像是一个外出旅行的贵族少女。安提戈涅的“眼睛”透出她自己的情绪是复杂的——从疑惑、难以相信到确定。伊斯墨涅一见到父亲和姐姐就激动地说:
父亲啊,姐姐啊!——这两个称呼叫起来使我十分愉快!好容易才找到你们!找到了,又好容易才透过眼泪(lypēi)看见你们!
“透过眼泪(Lypēi)”中的Lypēi本意是“悲伤”。伊斯墨涅见到父亲和姐姐时分明是悲喜交加。俄狄浦斯对女儿问道:
俄:孩子啊,是你来了?
伊:父亲啊,你的景况多么不幸呀!
……
俄:女儿啊,摸摸我吧。
伊:我拥抱你们俩。
俄:同胞的女儿啊!
伊:最凄惨的景况啊!
俄:你指的是她的和我的景况?
伊:也是指我这不幸的人的。
俄:孩子,你为什么而来?
伊:父亲,为了关心你。
俄:是做女儿的怀念?
伊:是的;还亲自给你捎来了消息,同我这惟一可靠的仆人一起来的。[327—334]
俄狄浦斯的语气多少带有“不确定”的质询味道,伊斯墨涅则显得热切。无可否认,父亲与女儿的对话蕴含着一种爱的情愫,可这“爱”中存有微妙的“距离”。虽然不清楚伊斯墨涅当初为何没有跟安提戈涅那样出来陪着父亲一起流浪,却不能就此断定伊斯墨涅对于父亲的爱和家族苦难缺乏一种深切的认识。
在伊斯墨涅说出捎来的“消息”之前,俄狄浦斯数落起了两个不孝之子,并夸赞了眼前的两个女儿。俄狄浦斯对两个女儿有一番这样的评价:
你们当中的一个,自从她结束了幼年的抚育时期,发育成长以来,就一直照看我这老年人,分担我的漂泊生涯,时常饿着肚子,赤着脚在荒林里的迷途中奔走,在暴风雨里,在骄阳下,多么可怜,受尽奔波之苦;她全不顾惜安乐的家园生活,只要能使父亲得到女儿的照拂。
(向伊斯墨涅)至于你,我的孩子,你也曾瞒过卡德墨亚人(Cadmeans),把所有针对我而颁发的神示给我带来;当我被放逐时,你还为我做过忠实的守望者(phylax)。现在,伊斯墨涅,你又给父亲捎来什么消息?什么使命使你离家远行?你不会空手而来的,我知道得很清楚;你一定给我捎来了什么可怕的消息。[345—360]
俄狄浦斯这番话的前半部分说的是安提戈涅,后半部分说的是伊斯墨涅。在后半部分的话语中,俄狄浦斯首先提到伊斯墨涅曾把忒拜城邦针对他的神示传递出来。由此可信,身在忒拜的伊斯墨涅一直心系父亲的流亡命运①前揭 Jebb笺注本,Part II,p.64,n.354,355.。所以,俄狄浦斯强调伊斯墨涅曾做过他的“守望者”(phylax),尽管真正的“守望者”是安提戈涅②参见 Bowra.Sophoclean Tragedy.Oxford:At the Clarendon Press,1944,p.323.——如同俄狄浦斯在前半部话语中所描述的。据说,伊斯墨涅来到异邦追寻父亲的这一举动,与安提戈涅一样在古希腊意义上都具有“非女性化”特征③参见 Bowra.Sophoclean Tragedy.Oxford:At the Clarendon Press,1944,p.323.。
俄狄浦斯关心伊斯墨涅究竟带来了什么“消息”。伊斯墨涅回答道:
父亲,且不说我为了打听你在何处生活而遭受的艰难困苦;因为我不愿意受两次苦:经受了艰苦,又来叙述一次。我是来把你那两个不幸儿子现在面临的灾难告诉你的。
起初,他们两人都愿意把王位让给克瑞翁(Creon),使那城邦不至于受到玷污,他们当时是冷静地注意到我们家族的古老灾祸,注意到那灾祸是怎样缠绕着你不幸的家的。但如今,神的诱惑和邪恶的心灵使他们两个不幸的人发生了凶恶的争吵,彼此争夺王位(tyrannikou)和王权(archēs)。
眼下那血气方刚、年纪轻轻的一个④这是指厄特俄克勒斯(Eteocles)。霸占了那年长的波吕涅克斯(Polyneices)的王位,把他哥哥放逐出境。那流放之人,据我们那里传说,逃到群山环绕的阿尔戈斯(Argos),在那里缔结了新的姻缘,交上了联盾的盟友,有意叫阿尔戈斯很快就使卡德墨亚名誉扫地,或者把那个城邦捧上天。[361—384]
伊斯墨涅表达了寻父的艰辛,她主要告知了两个兄长之间的权力争斗。从伊斯墨涅的叙述中,可以琢磨出她的基本立场:其一,由于家族的乱伦导致城邦遭受污染,她肯定了兄长们起初愿意把城邦王位让给叔父克瑞翁,认为其家族成员应该从城邦的政治权力中退出⑤参见 Hogan.A Commentary on the Plays of Sophocles.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91,p.91.;其二,她否认兄长们争夺王位和王权具有正当性;其三,在她看来,波吕涅克斯即便是被厄特俄克勒斯不合法地抢占了王位继承权,也不应当与阿尔戈斯联姻,攻打母邦忒拜。
伊斯墨涅对于母邦忒拜抱有一种伦理愧疚。她尤为在意兄长波吕涅克斯将要攻打母邦这件事。这件事是其家族苦难的延续,也将使城邦因其家族伦理罪孽遭到的“污染”更难清除。
二
伊斯墨涅祈望父亲俄狄浦斯能够正视她所叙说的状况。在接下来的对话里,伊斯墨涅说道:
伊:父亲啊,我的希望寄托在新的神示(manteumasin)里。
俄:什么神示?孩子,又有了什么预言?
伊:那里的人为他们的繁荣,迟早要把你,不论是死是活,弄回去。
俄:谁能从我这样一个人身上得到什么好处呢?
伊:据说他们的权力(kratē)要依靠你。
……
伊:你要知道,就是为这个,克瑞翁要来找你;等不了多久他就要前来。
俄:女儿,他要干什么?明明白白地告诉我。
伊:他们要把你安顿在卡德墨亚边界上,既把你抓在手里,又不让你进入国境。……
俄:他们会把我埋在忒拜的泥土里么?
伊:不会;父亲啊,杀害亲属的罪过不容你躺在那里。
俄:那他们决不能掌控我(kratēsōsin)。
伊:那么,总有一天卡德墨亚人是要吃苦头的。[387—399]
伊斯墨涅带来了“新的神示”。这个神示关乎忒拜城邦的福祉,又事关克瑞翁等人的“权力”。俄狄浦斯誓言忒拜当权者决不能“掌控”自己。值当此时,伊斯墨涅提醒父亲,如果这样的话忒拜的人民恐怕要吃苦头了。伊斯墨涅纠结于一种两难困境——她既忧心父亲将要面临的不幸,又担心忒拜城邦可能遭致的不幸。
伊斯墨涅难以无视母邦忒拜,她的父亲却要彻底割断与忒拜的纽带。俄狄浦斯向两个儿子发出诅咒,再次吁求科罗诺斯的居民和本地的威严女神一起保护自己。科罗诺斯的居民要求他向那些女神举行赎罪礼,俄狄浦斯希望两个女儿中有一人去帮他祭奠[419—502]。伊斯墨涅主动提出去举行祭奠仪式,她说道:
我去执行任务;可是,安提戈涅,你在这里守着(phylasse)父亲,子女须为父母受累,这是不足挂齿的。[507—509]
向异邦的神举行祭奠仪式,对于俄狄浦斯和安提戈涅来说都不是难题,因为俄狄浦斯的心中不再给忒拜留有位置,而安提戈涅热爱父亲胜于热爱忒拜。但是,这个祭奠仪式对于伊斯墨涅却是个挑战。俄狄浦斯知道伊斯墨涅关心着忒拜城邦,故而暗示伊斯墨涅去帮他举行仪式,以测试伊斯墨涅在城邦与父亲之间如何取舍。伊斯墨涅的反应算是明智,她特地提示姐姐安提戈涅呆在那里“守着”父亲,她理解安提戈涅才是父亲的“守望者”。
就戏剧的语境而言,伊斯墨涅的到来像是为着雅典王忒修斯的到来做准备①参见 Beer.Sophocles and the Tragedy of Athenian Democracy.Contributions in Drama and Theatre Studies.Number 105.Lives of The Theater,2004,p.158.。忒修斯出场后表示要把俄狄浦斯当作公民安顿在雅典的属地科罗诺斯[551—641]。这样,俄狄浦斯于形式上便脱离了一个城邦(忒拜),进入到另一个城邦(雅典)。
正如伊斯墨涅所说,克瑞翁不会放过俄狄浦斯。他来到科罗诺斯劝说俄狄浦斯而未果,便抓走了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忒修斯及其部下救回了俩姐妹,并给俄狄浦斯带回一个新消息——俄狄浦斯的儿子波吕涅克斯要来求见父亲。这时,安提戈涅出面请求父亲恩准波吕涅克斯前来相见[723—1203]。伊斯墨涅却始终一言未发,她的沉默折射出她对波吕涅克斯的疏离。
波吕涅克斯一露面就冲着两个妹妹打招呼,然后向父亲俄狄浦斯表达自己的悔意。波吕涅克斯企图申辩他被厄特俄克勒斯驱逐以及他为何率领阿尔戈斯人攻打忒拜,他的言辞没能获得俄狄浦斯的丝毫同情[1279—1345]。俄狄浦斯向波吕涅克斯发出最残酷的诅咒——
你将把那驱逐你的人杀死,你自己也将死在亲人的手里。[1387—1389]
闻听此言,波吕涅克斯很是绝望,他向妹妹们说道:
父亲的女儿们,我的妹妹们(homaimoi),既然你们听见父亲发出这严厉的诅咒,看在诸神份上,倘若他的诅咒应验了,而你们又回到了家里,请你们,看在诸神份上,不要不尊重我,而是把我埋葬,为我尽丧葬之礼。[1405—1413]
安提戈涅没有无动于衷,她劝说波吕涅克斯把军队撤回阿尔戈斯,不要毁了自己和城邦(polin),不要毁了祖先之地(patran),但被波吕涅克斯拒绝了[1414—1446]。
在这一幕父与子的冲突中,伊斯墨涅依然置身事外,继续保持沉默。需要注意的是,波吕涅克斯从出场到退场都是向着“妹妹们”说话的,伊斯墨涅却没有任何个人的应答。事实上,若是回顾伊斯墨涅向父亲告知两个哥哥权斗时所显现的立场,她肯定会认同安提戈涅对波吕涅克斯的最后劝告——不要毁了自己、城邦和祖先之地。即便如此,伊斯墨涅的沉默仍然映现出她对波吕涅克斯的态度迥异于安提戈涅。《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此处的叙事已经呼应了《安提戈涅》的剧情,因为在后一剧中,为波吕涅克斯尽丧葬之礼的将是安提戈涅而非伊斯墨涅。
波吕涅克斯走后,俄狄浦斯向众人宣告宙斯的霹雳要把他送往冥土;“退场”中的“报信人”报告了俄狄浦斯死亡的消息;俄狄浦斯死得很蹊跷,临行前把两个女儿都支走了,只留忒修斯一人看那发生的事[1456—1666]。父亲的离世使得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极为悲伤。伊斯墨涅决绝地表示——“愿那杀人的冥王使我同我的老父亲死在一起!我未来的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姐妹俩最后一次对话道——
安:亲爱的妹妹,我们赶快回到那里去吧!
伊:去做什么?
……
安:想看看那地下的住所——
伊:谁的?
安:唉!我们父亲的。
伊:怎么可以看呢?难道你不明白?
安:你为什么这样责备我?
伊:难道你连这个也不知道?
安:这又是什么?
伊:他死后连坟墓都没有,也没有人在场。
安:还是把我带去,让我也死在那里。
伊:唉,真可怜!我现在这样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到哪里去过不幸的生活?[1724—1735]
安提戈涅明知父亲生前不让她们去看他的死亡之地,可此刻她不仅执意要去看,甚至说也要死在那里。伊斯墨涅之前表示愿跟父亲一起死,只是以一种言辞方式来诉说内心的丧父之痛,而安提戈涅可能真想就此死去。伊斯墨涅正是觉察姐姐忽然间有了一种激烈的情绪,才阻止她去这么做。不难猜想,伊斯墨涅定是相信父亲生前的宣称——他的死都是神的安排,所以她觉得贸然去那神秘的死亡之地,不仅违忤了父亲的遗愿也悖逆了神意。换句话说,伊斯墨涅认为安提戈涅的激进之举“不合法度”①前揭 Jebb笺注本,Part II,p.265,n.1731.。
三
从事件自身的历史时间看,《安提戈涅》的故事是在俄狄浦斯死后发生的。《安提戈涅》一开场,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对话道——
安:啊,伊斯墨涅(Ismēnēs kara),我的同胞至亲的妹妹(koinon autadelphon),你看俄狄浦斯传下来的诅咒中所包含的灾难,还有哪一件宙斯没有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使它实现呢?……
现在据说我们的将军刚才向全城的人颁布了一道命令,是什么命令?你听见没有?也许你还不知道敌人应受的灾难正落到我们的朋友们(philous)身上?
伊:安提戈涅,自从两个哥哥同一天死在彼此手中,我们姐妹失去了他们以后,我还没有听见什么关于我们的朋友们(philōn)的消息,不论是好是坏;自从昨夜阿尔戈斯军队退走以后,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好转还是恶化哩。
……
安:克瑞翁不是认为我们的一个哥哥应当享受葬礼,另一个不应当享受吗?据说他已按照正义(dikaiai)和律法(nomou)把厄特俄克勒斯埋葬了,使他受到下界鬼魂的尊敬。我还听说克瑞翁已向全体市民宣布:不许人埋葬或哀悼那不幸的死者波吕涅克斯,使他得不到眼泪和坟墓……
听说这就是高贵的克瑞翁针对着你和我——特别是针对着我——宣布的命令……谁要是违反禁令,谁就会在大街上被群众用石头砸死。你现在知道了这消息,立刻就得表示你不愧为一个出身高贵的人(eugenēs);要不然,就表示你是个贱人(kakē)吧。
安提戈涅开口招呼伊斯墨涅——“我的同胞至亲的妹妹(koinon autadelphon)”。koinon本意是“共同的”,安提戈涅与伊斯墨涅当然有“共同的”血缘。Koinon这个词在整个俄狄浦斯的故事语境中虽暗指“乱伦”①参见 Bernardete,ibid,p.1,n.2;另参 Griffith.Sophocles:Antigon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120.,但就安提戈涅这句开场白而言,koinon和她这段话的最后一个语词“朋友们”(philous)首尾呼应,指向了一种“共同的爱”——philous本意即是“爱”。安提戈涅既用koinon一词向伊斯墨涅示意“共同的爱”,也是用philous一词抒发她对兄长的“共同的爱”。这“共同的爱”将随着“俄狄浦斯传下来的诅咒中所包含的灾难”而曲折延伸吗?
伊斯墨涅知道安提戈涅的意思,开口便说两个哥哥自相残杀,意指父亲俄狄浦斯的诅咒应验了。伊斯墨涅也关心“我们的朋友们(philōn)”的消息,表明她一定程度上接受“共同的爱”。但是,伊斯墨涅马上就感叹自己的命运将不知是好还是坏。伊斯墨涅不是第一次担心自己个人的命运了,她于父亲死后也曾感叹自己孤苦伶仃;这些心思是否说明她是自私的呢?伊斯墨涅固然爱其家人,可她的内心一直对家族乱伦怀有罪感,这在《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已见端倪;正是这罪感意识致使她时有一种从“共同的爱”中挣脱出来的萌动。
安提戈涅对于家族“共同的爱”从来都是义无反顾。两位兄长死后,安提戈涅注意到城邦的新王者克瑞翁按照“正义”和“法律”安葬了厄特俄克勒斯,却下令禁止埋葬波吕涅克斯。何种“正义”?什么样的“法律”?安提戈涅显然不承认克瑞翁的禁令是合法且正当的。
安提戈涅讥讽克瑞翁的“高贵”,并要伊斯墨涅表明自己是一位出身高贵的人还是低贱者。安提戈涅不在乎父母的乱伦婚姻,她认信父母及其儿女们都是高贵的②参见 Bernardete,ibid,p.8.。这正是伊斯墨涅与安提戈涅在基本伦理准则上的一个区别。
当伊斯墨涅得知姐姐要她帮着一起埋葬亡兄波吕涅克斯后,第一反应便是忧惧于这种行动违背了克瑞翁的禁令;安提戈涅坦言她自己会为哥哥尽义务,也是替伊斯墨涅尽义务,并声明克瑞翁没有权力阻止她同亲人的接近[39—48]。
伊斯墨涅向安提戈涅说道:
哎呀!姐姐啊,你想想(phronēson),我们的父亲死得多么令人憎恶,多么不光彩,他发现自己的罪过,亲手刺瞎了眼睛;他的母亲和妻子——两人的名称是一个——也上吊了;最后我们两个哥哥在同一天自相残杀,不幸的人啊,彼此动手,造成了共同的命运。现在只剩下我们俩了,你必须想想(ennoein chrē),如果我们触犯法律(nomou),反抗国王(tyrannōn)的命令(psēphon)或权力(karatē),就会死得更惨。首先,我们得记住我们生来是女人(gynaich hoti ephymen),斗不过男子;其次,我们处在强者的控制下,只好服从这道命令,甚至更严厉的命令。因此我祈求下界鬼神原谅我,既然受压迫,我只好服从当权的人,不量力就是丧失理智的呀(ouk echei noun)。[49—68]
如何面对克瑞翁的禁令,伊斯墨涅提请安提戈涅“想想”(phronēson)——彰显了伊斯墨涅试图借助“健全的理性”①Griffith,ibid,p.132,133.。在伊斯墨涅的这段讲辞中,她运用了三个语词表达理智与审慎:phronēson(想想),ennoein chrē(必须想想),ouk echei noun(丧失理智的)。这三个语词指向了三种思考的内容②参见 Bernardete,ibid,p.9,10.。
伊斯墨涅首先要安提戈涅“想想”的是父亲、母亲和兄长们的命运。伊斯墨涅为什么说父亲的死令人憎恶、不光彩呢?当年在科罗诺斯,伊斯墨涅不是曾为父亲的死而肝肠寸断吗?不能说伊斯墨涅的态度起了变化,她其实是指父亲的死在城邦中仍被认为是“不光彩的”;这是她们家族的伦理罪孽和不幸的源头。伊斯墨涅自始至终都为着家族的伦理罪孽而负疚,她无法像安提戈涅那样寻获一种道德正当,去对抗城邦及其统治者。
对抗城邦统治者会导致什么结果?伊斯墨涅请安提戈涅“必须想想”——“触犯法律,反抗国王的命令或权力,就会死得更惨”。伊斯墨涅没有区分“法律”、“命令”和“权力”三个语词。据说“法律”与“命令”的混淆趋向于一种民主的僭越,而“法律”和“权力”的混淆即是僭政③参见 Bernardete,ibid,p.9,10.。伊斯墨涅并非蒙昧地混淆三个语词,她只是道出了现实政治本相;她明确用tyrannōn(僭主)称呼新王克瑞翁,她知道克瑞翁的统治就是一种僭政。但伊斯墨涅恐怕不认为克瑞翁的僭政是多么的不合法,因为家族伦理罪孽以及父兄们的死亡使得克瑞翁的当权变得自然而然。伊斯墨涅要安提戈涅“必须想想”,乃是望她承认城邦的现有政治秩序。
伊斯墨涅接着劝说安提戈涅不要“丧失理智”。伊斯墨涅说出两种服从体系④Griffith,ibid,p.132,133.:一是女人服从男人——所谓“我们生来是女人,斗不过男人”;一是臣民服从统治者——所谓“我们处在强者的控制下,只好服从这道命令,甚至更严厉的命令”。两种服从归根结底是一种臣服——即弱者向强者的臣服。这是何其令人熟悉的政治原则。在古希腊现实的政治生活中,雅典帝国领导者不就信奉“正义的原则就是弱者向强者臣服”吗?⑤参见魏朝勇:《自然与神圣——修昔底德的修辞政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2—141页。倘若说这便是伊斯墨涅的理智或审慎,现代人肯定会嗤之以鼻的。但我们不能忘了,伊斯墨涅言辞中的第一个“想想”(phronēson)是她最终结论的伦理前提。在她看来,其家族的伦理罪孽已自行破毁了家族“共同的爱”的正义基础;一旦源于乱伦的“共同的爱”与城邦政治秩序发生纠葛,就没有绝对正义可言。职是之故,在对待克瑞翁的禁令的问题上,伊斯墨涅只得承认一种“自然的必然”⑥参见 Ahrensdorf.Greek Traged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99—100.,更何况波吕涅克斯还犯了叛国罪。
安提戈涅断然否定了伊斯墨涅的说辞,她回应道:
我再也不求你了;即使你以后愿意帮忙,我也不欢迎。你打算做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吧;我要埋葬哥哥。即使为此而死,也是件高贵的事(kalon);我做一件合乎神法的罪事(hosia panourgēsas),倒可以同他躺在一起,亲爱的人(philē)陪伴着亲爱的人(philou);我将永久得到地下鬼魂的欢心,胜似讨凡人欢喜;因为我将永久躺在那里。至于你,只要你愿意,你就藐视诸神所珍视的东西吧(ta tōn theōn entima)。[69—77]
安提戈涅想寻求一种“高贵”(kalon),“做一件合乎神法的罪事(hosia panourgēsas)”;hosia panourgēsas即指“合乎神法”而“不合乎人法”的事。也就是说,安提戈涅觉得为兄长而死便能获得伦理道德上的荣耀;埋葬波吕涅克斯乃是符合“神法”①有关古希腊的“埋葬”的神圣性,参见Ahrensdorf,ibid,pp.101—102.,不管这行为是不是违反“人法”,甚至不管这种行为中所蕴含的“共同的爱”有乱伦的暧昧——所谓“亲爱的人陪伴着亲爱的人”②Bernardete认为这句“似乎是在说情人的话”,见ibid,p.13.。安提戈涅要为“共同的爱”而献身,她没有伊斯墨涅那样的伦理罪感,更不在意人世的法律,她追求另一个世界的永生,相信诸神将会报偿她的“正义”和“高贵”。
伊斯墨涅没有放弃对姐姐的劝说,她与安提戈涅继续对话道——
伊:我并不藐视诸神所珍视的东西,只是本性上(ephyn)没有力量和城邦对抗。
安:你可以这样推脱;我现在要去为我最亲爱的哥哥起个坟墓。
……
伊:无论如何,你得严守秘密,别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我自己也会保守秘密。
安:呸!尽管告发吧!你要是保持缄默,不向大众宣布,那么我就更加恨你。
伊:你是热心(thermēn)去做一件寒心的事。
安:可是我知道我可以讨好我最应当讨好的人。
……
伊:不应该去追求(thēran)不可能的事。
安:你这样说,我会恨你,死者也会恨你,这是活该。让我和我的愚蠢(dysboulian)担当这可怕的风险吧,充其量是高贵的死(kalōs thanein)。
伊:你要去就去吧;你可以相信,你这一去虽是不理智(anous),你的亲人们(philois)却认为你是可爱的(philē)。[78—99]
伊斯墨涅表明自己不是不虔敬,只是不认同安提戈涅的虔敬,伊斯墨涅再度在现实政治层面上强调女人的“本性”(ephyn)。安提戈涅以替“最亲爱的哥哥起个坟墓”的决心再度突显她的“共同的爱”(这“爱”已不包括伊斯墨涅了)。伊斯墨涅期求安提戈涅最好隐蔽地埋葬波吕涅克斯,她显然不愿看到安提戈涅因公开对抗城邦法令而被处死。安提戈涅却挖苦地叫伊斯墨涅去“告发”。这一挖苦说明安提戈涅是希望埋葬哥哥的行为能够得到公开的见证,好显扬她的“光荣”③参见 Griffith,ibid,p.137.。
伊斯墨涅说安提戈涅“是热心(thermēn)去做一件寒心的事”,告诫她“不应该去追求(thēran)不可能的事”。“寒心的事”与“不可能的事”都是一样的事,即为埋葬波吕涅克斯而死;thermēn(热心)和thēran(追求)的词根是相同的,意含欲望和热爱。安提戈涅正是要由“共同的爱”去实现一种“高贵的死”。安提戈涅还自嘲自己的“愚蠢”,实指伊斯墨涅不懂得一种超越维度上的高贵和死亡。
伊斯墨涅真的不懂吗?她称安提戈涅的“这一去”虽是“不理智”(anous),“亲人们”却认为她是“可爱的”。所谓“不理智”是指安提戈涅的行为不合现世政治伦理的自然秩序,所谓“可爱”是指安提戈涅的行动在某种意义上符合“共同的爱”。
安提戈涅埋葬波吕涅克斯的事情终被克瑞翁破获,伊斯墨涅也被误作共犯捉拿了[384—526]。伊斯墨涅想要分担罪责;但安提戈涅对她说——“口头上说爱的人(logois philousan)我不喜欢”,伊斯墨涅则企望——“让我和你一同死,使那死者获得尊敬吧”;安提戈涅回绝了她,并说——“你愿意生,我愿意死(katathanein)”;伊斯墨涅转而劝说克瑞翁不要杀自己儿子海蒙(Haemon)的未婚妻安提戈涅,克瑞翁的回答是——“死亡为我破坏了这婚姻”[543—576]。
伊斯墨涅是不是一个只把“爱”挂在口头上的人?她是否改变了初衷,也想成就“高贵的死”?伊斯墨涅言语的修辞仍是想让姐姐能够得以保存,她理解但难以苟同安提戈涅追求死后的永生和高贵。伊斯墨涅对于家族成员的“爱”确实是选择性的,因为她不认为家族“共同的爱”具有绝对的伦理正当。伊斯墨涅的“爱”的方向是指向此世的承受而非来生的拯救,这似乎是她作为人或作为女人的局限吗?
那么,一个“非女性化”的英雄主义的安提戈涅是否就突破了人的限度?安提戈涅终于死了,可她死于自杀。安提戈涅临死前曾像一个真正的女人一样悲诉——
……可是,哥哥呀,克瑞翁却认为我犯了罪,胆敢做出可怕的事。他现在捉住我,要把我带走,我还没有上过婚床(alektron),没有听过婚歌(anumenaion),没有享受过婚姻的幸福或养育儿女的快乐;我这样孤孤单单,无亲无友,多么不幸呀,人还活着就到死者的石窟中去。我究竟违犯了什么神法呢……我这不幸的人为什么要仰仗神明?为什么要求诸神保佑,既然我这虔敬的行为得到了不虔敬之名?……[912—928]
安提戈涅的诉说展露了她从此前追求“高贵的死”的誓言下降到了一种哀怨——“没有上过婚床(alektron)”、“没有听过婚歌”(anumenaion),她甚至抱怨诸神为何不给予她报偿。我们无需苛责安提戈涅的脆弱和彷徨。即将赴死的时刻,安提戈涅完全退回到了人或女人的自然本性,她并没有获得超越。
伊斯墨涅在克瑞翁判处姐姐安提戈涅死刑之后,再也没有出场了。索福克勒斯似乎无意交代伊斯墨涅的结局。不过,我们需要记得:“不结婚,不生育,枯萎而死”是伊斯墨涅和安提戈涅的共同命运,她们的父亲俄狄浦斯早就做出了预言,这是其家族伦理罪孽肇造的结果。但我们没有听见伊斯墨涅对此有过悲号,尽管她尤其表白自己“生来是女人”。因此,在现世的伦理和政治意义上,与其说伊斯墨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①Winnington-Ingram,ibid,p.132。,不如说她以一种在世的承负去面对命运的悲苦。伊斯墨涅的形象仿佛最大地诠释了亚里士多德的命题——“女子以愿意服从为勇敢”②Aristotle.The Politics.1260a20—23.trans.Lord.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53.另可参吴寿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