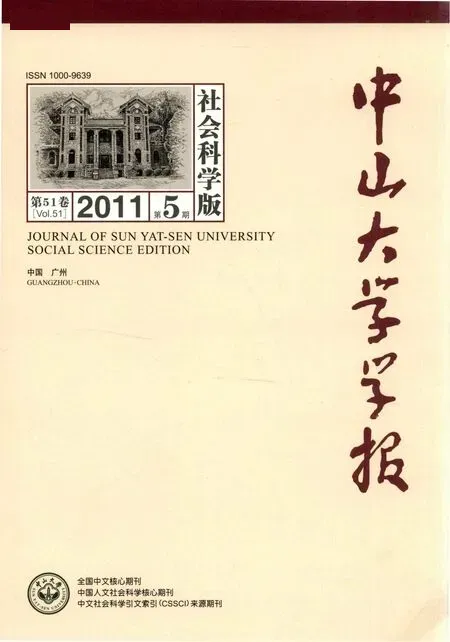清季学制改革下的学堂与经学*
朱 贞
经学原本作为中国传统学问的大道,然而民初以来,体现中国学问独特性的经学转至若存若亡。究其原因,与清末分科观念的引进以及有系统的学堂取代旧学关系密切。“经过清季和民初的两度分科教学与分科治学,中国的所有思想学术文化被按照西洋统系分解重构”,从此以后,普遍而言,中国固有学问有无统系,已经成为问题①桑兵:《分科的学史与分科的历史》,《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单就经学而言,自清末壬寅、癸卯学制出台,以西方学术分类衡量中国固有学术,破坏了经学本身的地位价值②见蒙文通:《论经学遗稿三篇·丙篇》,《经学抉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9页。钱穆也持有类似观点,认为若把近代西方学术分类眼光加以分析,便没有了经学独立的存在。见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四部概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5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3页。。要了解这一变化,就要考察壬寅、癸卯学制及其指导下的新式学堂从无系统到有系统所带来的转变。
一、无系统时期的学堂与经学
近代中国,自西式学堂诞生以来,中西学如何一统于学堂就成为问题。清廷最后确立了“中体西用”的解决方案,但实际上,学堂是先有了“西用”之学,然后再逐步确立“中体”观念。反映在学堂课程层面,语言、技术类学堂初兴之时,重在引进西学,经学并未成为科目。甲午后,肄习普通学的新式学堂开始大量出现。分科观念为官方办学所接受,与西学对应的中学内容在一些学堂中被不断界定,经学也成为按照西方学术观念被分解的中学课程之一。随着学务进程的开展,在建立新学制的呼声中,设经学成为官方定论。
早期的在华教会学校为了吸引中国学生,已经注意到中西课程并重,加授经学等中国传统知识。1890年在华传教士大会上,以潘慎文为首的一批传教士,明确提出教会学校的教学计划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即基督教书籍、中国经书和西方的自然科学。甚至一些传教士头痛的已经不是是否教授儒学经典的问题,而是应当怎样教授的问题①胡卫清:《传教士教育家潘慎文的思想与活动》,《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这些学校的教学内容虽然各有安排,大体上经学多习四书,程度较高的兼及五经。由于采取西方分科、分级设学的办法,这些教会学校不仅有经学教育的内容,而且有了层级安排。像山东登州文会馆分备斋、正斋两级,大致对应小学、中学程度。备斋程度较低,主要学习《孟子》、《诗经》、《大学》、《中庸》。程度较高的正斋,则有《礼记》、《书》、《左传》、《易》等②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校印刷所,1913年。。这无疑会对人们的观念造成一定影响。不过,一般而言,清政府对于外国在华学校一直采取既不承认也不管辖的方针③参见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22页。。中国人自办的新式学堂,有着自己的理念用意和发展轨迹。
同治元年(1862)开办的京师同文馆,被视为中国近代新教育的肇端④丁韪良:《同文馆记》,《教育杂志》第27卷第4号,1937年4月10日。。同文馆的创办初衷,是应对外交需要培养外语人才,故所教所学仅限于外国语言文字⑤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7,第18页。。所谓“阁束六经,吐弃群籍”,于中国旧学一概不问⑥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陈景磐、陈学洵主编:《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39页。。是为新式学堂中“西用”早于“中体”的明证。之后相继开设的语言、技术学堂也标明学习西学。这样安排,看似与中学无涉,可是随着西学的社会地位不断上升,中学开始受到冲击。
朝野上下,关于中、西学的问题被不断拿出来讨论。被称为早期维新派的冯桂芬为了“攘夷”,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⑦冯桂芬:《制洋器议、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49—57页。。之后,郑观应等人也提出类似主张。直至1898年张之洞《劝学篇》问世,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的观念系统阐发⑧参见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522页。。戊戌期间,冯、张二人的著述由光绪皇帝先后诏发,风行于世,“中体西用”的观念为朝野上下所接受。在这一观念逐步确立的过程中,一些新式学堂随之将经学等中学课程增设起来。官员在举办技术类学堂时,重申可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不可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⑨《沈文肃公政书》,卷4,《奏折》,第6页。。中体的问题进入学堂。尤其是甲午战争前后,电报、医学、铁路、矿务等技术学堂相继创办,开始贯彻中体西用思想。两广电报学堂规定,学生除学习西学外,兼课四书五经,以知礼义。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江南储材学堂的学生也要兼习经史,习《春秋》、《左传》等。
起初,无论新式学堂还是书院,课程中的经学、经史等名目,不过是相对西学而提出的中学“代表”,分科还只是一个模糊的观念。办学堂者一面抱有中国传统不分科的治学取向,一面拼合西学。甲午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梁启超所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流行语。此前中西学的主辅位置明确,此后却强调二者不可偏废,是为甲午后的新知⑩参见罗志田:《西潮与中国近代思想演变再思》,《变动时代的文化履迹》,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11页。。朝野上下也逐渐接受西方的学术分科观念,各书院开始“定课程”,以大学堂为首的普通学堂明确将中学分科设置。
甲午战后出现学习一般西学知识的普通学堂,且发展很快⑪据统计,1895年至1899年间创办的100余所新式学堂中,普通学堂占84所。见乐正:《从学堂看清末新学》,中山大学1985年硕士论文。。其课程设置不同于语言技术类学堂,中西学课程的种类大幅度增加,在西学课程中增添了政治、伦理等内容,在中学课程中废除了八股词章,增加了掌故、史地、通鉴、律法等内容。1896年,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提出学问宜分科,不立专门,终无心得。分科治学,成为朝廷办学的方针。人们不断尝试用分科的办法来规划中学,导致中学课程名目渐多①《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卷5,《学校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78辑第771册,第376页。。戊戌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为应对新学不得不讲而中学过于繁难的状况,提出易简之策以救中学。所列举的中学各门,为经学、史学、诸子、词章、理学等,并寄希望于学堂专师以之纂成专书,初步显示了其主张的中学课程分类②《守约》,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卷270,劝学篇一,保定: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726—9732页。。大学堂章程将普通学课程分为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和初级的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以及文学、体操等十种,为全体学生必修科目③后孙家鼐因课程门类太多,有所精减。将理学并入经学为一门,诸子、文学皆不必专立一门。见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第4155—4157页。。至此,中学划分的课程名目已先后有经学、史学、文学、掌故之学、舆地之学、理学、诸子学等数种。此后,传统学术在学堂中所分学科大致未脱离这个范畴。
中学既然已经分科,那么各科孰轻孰重的问题自然走上台面。经学地位重要,在一些学堂的开办章程和办法中得到体现。大学堂确立以中体西用为立学宗旨,明文规定经学是各学根本,“经学所以正人心,明义理,中西学问皆以此为根柢。若不另立一门,何以为造端之地?”④《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32辑第317册,第285页。湖南正始学堂章程规定,立学中西并务,以经义为归宿,故先学群经。不能遍者,则以六经为卒业⑤《正始学堂大概章程》,《湘报》第176号,1898年10月14日。。但一些学堂设课时,标榜为各学基础的并不仅仅是经学,而是经、史等学并列,经学的地位并未凸显。像天津中西学堂中学课程就强调讲读经史之学⑥盛宣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卷5,《学校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78辑第771册,第389—390、394—395页。,南洋公学章程也规定,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⑦《皇朝政典类纂》学校十五,第4294页。。这固然是由于时人分科观念模糊,中学的经、史划分不清,也因为经、史等传统学问的地位在清季发生了转变,这一点在日后的学制章程中得到了体现。
分科设学下的经学教育,与旧时相比有了明显变化,注意到中西教法的差别,提出用新法教授初学蒙童⑧钟天纬:《学堂宜用新法教授议》,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82页。。方法上开始强调讲解,主张“略变从前教育之法,减其记诵之功,益以讲解之业”⑨《论说·拟教育办法画一条例》,《湖南官报》1902年5月30日。。形式上一些学堂尝试分级设置,经学等中学课程有了简单的层级分别和衔接。天津中西学堂为最早分级设学的新式学堂。其二等学堂即“外国所谓小学堂”,主要讲求四书等学。头等学堂即“外国所谓大学堂”,在熟悉四书的基础上进一步讲求经史。除了分级设学外,一些独立的一级制新式普通学堂,还初步与其他学校形成衔接关系。1896年,钟天纬设立上海三等公学,内分蒙馆、经馆,实为外国的小学堂。按其规划本意,依南北洋头、二等学堂例,经馆即三等学堂,蒙馆即四等学堂⑩《上海三等学堂重刻本》(1903年),《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578、590页。。其中,蒙馆以识字明义为主,经馆则专读四书五经,兼习英文。实则自蒙馆、经馆、二等、头等学堂诸阶段,将小学至大学堂各阶段衔接起来,而经学教育在经馆以上各阶段课程中得到贯彻。
整体来看,这一时期新式学堂的经学等课程,仍旧呈现混乱状态。虽然中体西用的办学取向得到官方认可,但人们认为各专门学堂不过是在书院之外另设机构专习语言文字、机械制造、农工商矿等类知识,“操众事以效其职业”⑪《胡聘之请变通书院章程折》,《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156页。,偏重专门之学,经学等中学课程仍多不设。早期师范学堂的情况略有不同,但结果一样,如南洋公学师范馆虽然规定中西兼学,因来学者“于国学素具根底,故国学并不上课”①《杨耀文记各院(班)概况》,《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526页。。各普通学堂兼顾经史,自成一统,科目课程五花八门,以何经启蒙,各阶段应读何书,多自定章程,互不衔接。随着学堂数量的增加和学务规模的扩大,制定全国统一学制,资为程式,来规范全国各级各类学堂的科目、学级与学时设置,便成为新教育发展的内在需求。
制定壬寅、癸卯学制很大程度依赖于对日本学制的借鉴,但日本设学,经学被放入哲学科和文学科内的汉学来研究,与中国情形不同。而当时日本的教育界人士对于中国新学制内是否设经学,态度、意见并不统一,“此邦有识者或劝暂依西人公学,数年之后再复古学;或谓若废本国之学,必至国种两绝;或谓宜以渐改,不可骤革,急则必败”②《答贺松坡》,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3册,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407页。。
事实上,随着对中学消亡的忧虑,新学制中要不要设经学,清廷早有定论。戊戌年皮锡瑞考察时务学堂试卷,就感慨道:“今观诸生言洋务尚粗通,而孟子之文反不通,中学将不亡耶?”③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转引自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637页。1903年恽毓鼎科考阅卷时,也发现“各房二场卷,往往颂扬东西国为尧舜汤武,鄙夷中国则无一而可,至有称中朝为支那者。西学发策之弊,一至于此”④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20页。。
朝堂之上,“亡中学”的趋势引起重视,并设法采取挽救措施。1901年发布的新政改革上谕,重申三纲五常不可变⑤《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第460—462页。。之后奏准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实际上成为具体变革方案,其中《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列举了学制改革的草案,再次重申经学万不可废的主张,“总之,中华所以立教,我朝所以立国者,不过二帝三王之心法,周公、孔子之学术”。并规划了立学的简单办法,将经学融入各阶段课程,还有了将经学独立列为高等学校专门一科的想法⑥《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张之洞全集》,卷52,奏议52,第1396—1398、1401页。。
对各地学务管理权限极大的各省督抚,主张在新式学堂中设经学等课程以保存中学,且付诸行动。他们遵旨条陈新政,讲求实学、不废经学成为共同呼声⑦《致西安行在军机处》,《张之洞全集》,卷83,电奏11,第2217页。。1901年11月,袁世凯奏办山东大学堂办法,仿照小、中、大学堂程度,分备斋、正斋、专斋三等,另设蒙养学堂。经学作为要项,出现在各阶段课程表中⑧杨凤藻编:《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5,《学校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79辑第781册,第365—379页。。各地参照山东模式,兴办学堂之风遍及全国。而作为大学堂程度的专斋在江苏得到实现,经学成为其中一科⑨《江苏学政李殿林奏为江苏江阴南菁书院遵改学堂墐拟试办章程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文教类,04—01—38—189—06。。张之洞于湖北规划了简单的学制体系,专门学堂有农、工、师范、方言、仕学院等项,普通学堂则按文武之分,有小学、中学、高等三级。在普通学小学、文普通中学、文高等学各阶段,都有经学课目的设计。并于办学要旨中明确提出“幼学不可废经书”为学堂防弊要义⑩《张之洞全集》,卷57,奏议57,第1488—1502页。。
然而,学堂各阶段经学课程如何规划,并未取得一致。先不论专门与普通学堂的区别,就在小学堂是否要读经的问题上,也有所争议:或谓四书、经、史乃根本之学,要办小学堂,先以四书、经、史、政治专书为主⑪《各省公牍·扬州府秦州罗牧猷通禀兴建小学堂章程》,《湖南官报》1902年5月26日。;或言学生未进中学之先,旧学功课十当去九。“即都不事,亦无不可。”⑫《论说·拟教育办法画一条例》,《湖南官报》1902年5月30日。这篇文字是严复所作,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书信,第562—565页。归根到底,还是缺少统一详细的学堂章程,来规划各地学务。
二、壬寅学制与经学课程的设置
在张百熙的主持下,中国首个统一学制诞生。《钦定学堂章程》规划的壬寅学制,主要仿照日本设学办法,划分普通学堂与专门学堂的体系,并以分科观念对原有中学课程进行规划。设经学虽然是官方定论,具体到各类各级学堂是否设置、如何设置,仍是新学制要解决的难题。
新学制中设不设经学的问题,张百熙早有判断。在1902年的《奏办京师大学堂疏》中,他主张大学堂先办预备科,功课“略仿日本之意”,以经、史隶属政、艺二科下之政科,“四书五经……自应分年计月,垂为定课”①张百熙:《奏办京师大学堂疏》,《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832—835页。。显示其已有在分科观念下设立经学课程的主张。学制出台前,张百熙曾与张之洞电商内容,获得后者提示新学制下设经学的粗略办法:就内容而言,四书五经以及注疏解说等皆列为学堂课程;就层级而言,小学堂主要读四书,中学后兼习五经,而中小学阶段只习专经,通大义,直到入专门学后,再循序渐进,博考群经传注、诸家解说②《张之洞全集》,卷249,电牍80,第8745页。。这些建议,在学制中有一定程度的反映。
壬寅学制整个系统分为普通、专门两种。普通学划为三段七级:初等教育分为蒙学堂和小学堂两级,儿童自六岁起先入蒙学堂,小学堂分为寻常与高等两级。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一级。高等教育设高等学堂和大学预科、大学堂以及大学院。专门教育则主要包括实业学堂和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分为简易、中等和高等三级,分别对应高等小学堂、中学堂与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程度。师范学堂附设于中学堂,师范馆附设于大学堂。另为已入仕途之人员考虑,于大学堂附设仕学馆。
经学课程的规划在各种学堂的章程中得到体现。整个学制体系中,普通学堂除大学院(不立课程)以及高等学堂艺科、大学堂预备科艺科外,其余各阶段皆设经学课程。专门学堂则规定师范学堂按照大学堂师范馆章程办理,列有经学课程。实业学堂偏重专门,大学堂仕学馆学生于经史诸学素有研究,皆不设。各学堂所设经学课程名目分别为:普通学堂的中、小、蒙学堂称为“读经”,高等学堂政科与大学堂预备科政科称为“经学”;作为大学分科之一的文学科下设经学目。专门学堂的师范学堂与大学堂师范馆课程也称为“经学”。
与上述张之洞的建议相似,经学的教学内容中小学阶段只是读经,至高等与专门学堂阶段,再修习传注解说③《张之洞全集》,卷249,电牍80,第8745页。。学制章程秉承清代重理学④清代官方重视理学,把理学作为承祧道统的学说。详见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55、60 页。和书塾大都以四书开蒙的传统,普通学堂蒙小学堂阶段先读四书。小学堂至中学堂,读完五经。中学堂毕业,则十三经读毕。高等学堂阶段,续讲各经自汉以来注家大义。分科大学因未办理,未定课程,但其预科下的政科与高等学堂程度相同。在分科大学阶段,专列经学目。专门学堂中的师范学堂仿照大学堂师范馆章程办理,列有考经学家家法一项。自小学堂、中学堂而至高等学堂、大学堂预备科,经学的传授以定钟点、定内容的方式在学制体系内得到贯彻。
就经学教授办法与考验办法而言,各阶段不一。蒙学堂阶段改变了传统经学的传授方式,强调教授之法,以讲解为要,诵读次之⑤中国初始经籍简少,故汉名士有读书精熟之说,魏经生有读书百遍之法。自六朝尚对策、唐取帖经,两宋尚词科并记注疏子史,北宋又设神童科,幼稚即记多经,于是学童读书务为苦读强记(见《张之洞全集》,卷57,奏议57,第1488—1502页)。此后,传统书塾教学注重背诵经典,强调成诵为终身受益。。为保护儿童脑力,背诵只须择紧要处试验,严戒遍责背诵。但为免儿童遗忘,又督令每天、每月均要温习所授课程,实则仍在强调熟记,只不过条件放宽。小学堂、中学堂阶段读经课程,则无此要求,仍将经书成诵视为可遵循的办法。至高等学堂阶段后,重在修习传注解说。大学院则主个人研究,不主讲授。至于各阶段经学课程考验办法,蒙学堂主要就平日讲授,随举问之,使学生口答或笔答。除常日间日考问外,每旬每月又须多发数问考验所学。并有升学考试一项。自小学堂以上各阶段,除日常考课外,又有升班考试、年终考试与卒业考试三种,经学等各门功课分数计算办法,就平日与考试分数平均核算。相较于旧日,书塾只有日常考课与科举考试,新式学堂的经学“应考检验次数”实际上有所增多。
将经学课程系统规划到各级各类学堂中去,是壬寅学制的首创。因为西方学科中并无经学,所以其全盘规划只能自我统筹,无成法可资借鉴。而且相较于旧学教育有很大不同,书塾、府州县学到国子监并无层级的递升,新学制将经学课程纳入从蒙小学堂到大学堂各阶段的系统教学中去,有了教学内容、学时安排与层级次序的递升衔接,使得经学成为类似西式教育的课程门类和分科。学堂教习须按照统一规定实施教学,不能全部听塾师、山长的一家所言。
在新学制的框架内,各阶段教学安排的重心明显不同。就课时比重看,层级越低,中学课程的比重越大。随着学堂层级渐高,西学课程比重相应提高,超出中学课程。详见下两表:

表1 壬寅学制中、小学堂“中学”各科时刻表① 本文各表均依据《钦定学堂章程》与《奏定学堂章程》(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编》所影印章程)内容制定。《钦定学堂章程》蒙学堂、寻常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以十二日为一周,但六日即完成一个循环,故表1蒙学堂、寻常小学堂、高等小学堂每周总时刻以六天计算。中学堂每周总时刻则按星期计算。其余各表每周时刻均按星期计算。

表2 壬寅学制高等学堂、大学堂预备科“中学”各科时刻表
高等以上各学堂课时安排,显然西学多,中学少,这与张百熙及其所用拟定章程之人的态度有关。张百熙在应新政改革上谕的奏疏以及进呈学堂章程的奏折中,显示了对于“参考西制”的偏重。其重用的参与谋划学制章程的沈兆祉、李希圣等人,也勇于革新,使得时人谓“北京大学堂中皆新党人物”②见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4页。。这些因素反映在学制课程中,就是“新”多于“旧”,“西”多于“中”。尤以大学分科章程表现最为明白,仿照日本设文学科,将经学列为文学科七目中之一目。即经学虽列入学堂课程,却以西学分科办法来处理,大学分科所定的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更像是学术分类,“中学”只能依附其中。而高等学堂艺科与大学堂预备科艺科不设经学内容,政科所习中学内容不到三分之一,显示了在分科越来越细的高等以上学堂,重心在学习专门西学。大学堂师范馆学生后来回忆,当时所读课程并非传统经典,“现代科学是占最大成份的”③邹树文:《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960页。。
细察中学的各分科课程,经学在传统中学的重要性也没有得到体现,史学和文学的地位却有所提升。从上面两表来看,经学的课时安排相对较少,占每周全部课时的比重分别为蒙小学堂1/6,中学堂3/37—3/38,高等学堂政科与大学堂预备科政科2/36,大学堂师范馆1/36。读经课程的课时相较文学与史学持平甚至不如。
这一情况,一方面不能忽略桐城派的影响。吴汝纶被张百熙礼聘为首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有学者认为:受其影响,教育界直隶一脉多宗桐城古文。在直隶人脉作用下,壬寅学制较少读经内容①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第186页。。赴日考察教育期间,吴汝纶提出学堂设中学的办法,“国朝史为要,古文次之,经又次之”②《桐城吴先生尺牍》第四,第55—58页。。这大不同于张之洞等人所宣扬的“中体西用”以经学为宗的论调,将史、文的地位在学堂中加以提升。古文重要性的宣扬,显然与吴汝纶桐城派大家的身份有关,据其弟子所言,他治经主张“因文以求经意”,“欲穷经者必求通其意,而欲通其意必先知文”③贺涛:《桐城吴先生经说序》,《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1168页。。甚至认为习古文才是学堂保存中学的关键,并以姚选古文为学堂必用之书,“即西学堂中亦不能弃去不习,不习则中学绝矣”④吴汝纶:《致严复》,郑逸梅、陈左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9集,第23卷,《书信日记集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76—77页。。
另一方面,新学制经、史课时的安排与吴汝纶提出中学“以国朝史为要”的大背景,正是清季经学地位的式微和史学地位的上升。据梁启超1902年所言:“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显示在近代修习西学,史学具有较易比附的学科优势。而科考改章,废八股,改试策论,使得史学地位得到提升。经世之风与国粹思潮,也让史学显得日益重要⑤关于经学和史学地位嬗变的问题,可参见章太炎《论经史儒之分合》,并参考周予同《有关中国经学史的几个问题》(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95页)关于经史关系的阶段分期和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3—341页)对清季经史关系以及从“通经致用”到“通史致用”的梳理。。原来作为实学而并称的经史之学,在西方学术分科视野下的学堂科目设置中,又进一步各自独立为经学和史学课程。
壬寅学制出台后,其经学课时比重偏低以及趋新的取向,先是引起朝臣不满,有报纸刊出枢臣在朝房痛诋学堂章程、课程不善的消息⑥《时事要闻》,《大公报》1903年3月18日。。清廷也做出反应,增派荣庆为管学大臣,《清史稿》认为朝廷此举用意在“百熙一意更新,荣庆时以旧学调剂之”⑦赵尔巽:《清史稿·荣庆传》,卷439,列传226,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401—12402页。。各地接获章程后,也出现了质疑的声音。张之洞依据湖北学堂办法,对学制中的读经安排明确提出两个问题:学堂功课既繁,是否需要限制读全经?读经定有次序,但学生程度不同又当如何处理?⑧《致京管理大学堂张尚书》,《张之洞全集》,卷256,电牍87,第9029—9030页。
1903年6月,张百熙与荣庆会奏请派张之洞会商学务,以补《壬寅学制》之不足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5036—5037页。。在张之洞的主持下,新的癸卯学制诞生了。
三、癸卯改制与经学课程的调整
癸卯学制,是张之洞在借鉴日本学制的基础上,将湖北办学经验与个人治学观念结合,对壬寅学制进行修订的产物。相比壬寅学制,不仅修订了中学的分科办法,调整了各类各级学堂经学课程的比重和内容,并在学堂不同阶段分别撰述通例或研究办法,完善了学科化的授经办法。更创设经科大学,将各经专门研究。鉴于章程中有着太多张之洞的办学经验和治学办法,以至于有人指学堂章程“名曰章程,实公晚年学案也”⑩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4册,第95页。。
实际上,奉命会商学务的三大臣之间关于经学课程的主张并不统一。张之洞对经学课程的设计,荣庆与张百熙的意见就截然不同,暗合《清史稿》对二人新旧的划分:荣庆认为初等小学读经功课,课时仍旧太少,建议增加①《癸卯十一月十三日致荣华卿尚书》,《张文襄公函牍未刊稿》,所藏档甲182—393。;张百熙及其下属则认为经学、词章内容增加过多,隐约抵制②《时事新闻》,《大公报》1903年8月1日、8月17日、8月21日、8月24日。。各方意见不合,会议多次,未能定议。不过,张之洞奉旨会商学务,实际上成为新学制的主持者,终究以其意见行事③《时事新闻》,《大公报》1903年8月17日。。
1904年1月奏准的《奏定学堂章程》(因是年是癸卯年,又称癸卯学制),无论整体系统还是经学设置,都承接了壬寅学制的部分内容,如仿照日本学制,学堂统系分为普通、专门两块,学科设置采取分科办法规划中学,读经次序方面主张先以四书开蒙,中小学堂阶段只是读经,高等以上各学堂才开始研究经学注疏,读经方法小学阶段都强调讲解,以及增加考试作为检验经学教学效果的办法等。但两者在各阶段的教授内容、办法等细节方面,存在很多差异。
癸卯学制普通学教育层级与壬寅学制不同,先设学前教育性质的蒙养院,再分为三段六级。第一阶段初等教育,分为初等小学堂与高等小学堂两级。第二阶段中等教育,包括中学堂一级。第三阶段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分科大学与通儒院。师范教育分为初级与优级,程度分别对应中学堂与高等学堂。实业教育进一步细化,各项实业学堂均分为高、中、初三等。此外,还有译学馆、进士馆、仕学馆等。
整体看来,普通与专门学堂的经学课程内容都有所增加。普通学堂除蒙养院与政法、文学、医、格致、农、工、商等七个分科大学外,自小学堂至经科大学皆设经学课程。高等学堂阶段不像壬寅学制有政科、艺科设与不设的区别,所分三类皆设经学课程。壬寅学制中文学科目下的经学更是直接列为分科大学之一,通儒院也将经学列入专科。专门学堂则初级师范学堂完全科设读经讲经,简易科不设;优级师范公共科与分类科皆设,加习科不设。大学堂师范馆,照优级师范章程办理。实业学堂分为农、工、商三种,仍旧偏重专门,与学生素有根柢的大学堂进士馆、译学馆等皆不设经学课程。
各学堂所设经学课程名目也有所变化:普通学堂中、小学堂经学课程名为“读经讲经”,高等学堂为“经学大义”,经科大学分为十一门:周易学、尚书学、毛诗学、春秋左传学、春秋三传学、周礼学、仪礼学、礼记学、论语学、孟子学与理学。专门学堂则初级师范学堂完全科设“读经讲经”,优级师范公共科设“群经源流”,分类科设“经学大义”。
同时,癸卯学制比壬寅学制更加详细地制定了中小学堂读经的步骤和教授办法,将学生每年应读经书字数标出,使得各学堂便于掌控学生的读书进度。就各阶段教授办法而言,小学堂时期为保护儿童脑力,强调经学课程以讲解为最要。但与壬寅学制不同的是,不强责背诵的对象,只是“记性较钝学生”,一般学生仍主张“每日所授之经,必使成诵乃已”。故小学堂每星期经学课程十二点钟,一半时间来读经,一半时间用来挑背及讲解。中学堂科目增多,每星期读经六点钟,挑背及讲解只有三点钟。为加深记忆,中小学堂均有每日半点钟温经时间,属于自习性质,不计入学堂时刻。高等学堂以上阶段,转为讲授经学大义。到了经科大学,各经的专门研究重在自学而非授课,“为教员者不过举示数条以为义例,听学生酌量日力,自行研究”。
各阶段经学课程,张之洞皆订有通例或研究办法,实际上完善了新的教育系统内的授经办法:中小学堂讲经,主张先明章指,次择文义,务须平正明显,切于实用,忌“繁难”与“好新恶奇”。高等学堂则由于经义奥博无涯,学堂晷刻有限,只讲诸经大义④所谓讲大义,即“切于治与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凡大义必明白平易,若荒唐险怪者乃异端,非大义也”。《守约》,《张之洞全集》,卷270,劝学篇一,第9727页。。直至分科大学阶段,才开始研究。大体上遵循三个主要步骤,即先明各经源流及流派;次以群经、诸子和史学等以证该经;再次以外国科学等证该经等。由于张之洞一方面兼采汉宋,另一方面则主张中西会通,各阶段课程并无明显划分汉宋壁垒⑤这一做法也有可能受到作为其幕友的陈澧弟子梁鼎芬的影响。,又注意将西用之学与经学研究结合起来。同时强调通经致用,将群经总义定为“宜将经义推之于实用”,各经研究“务当与今日实在事理有关系处加以考究”。
至于经学课程的检验办法,因各学堂考试种类较壬寅学制增加,分为临时、学期、年终、毕业、升学五种,使得考试检验随之增多。其中毕业考试内容规定尤其细致,分内、外两场。外场口试各学科分类,内场笔试则头场须试经论。经学课程的检测方式,一方面继承了科考形式,一方面增加了口试与检查学科讲义的内容①关于学堂考试与立停科举的关系,详见关晓红:《殊途能否同归:立停科举后的考试与选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9期。。
此外,癸卯学制修订了壬寅学制中小学阶段的课时比重,经学课程大幅度增加,蒙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分别由1/6、1/6、3/37—3/38,增加到2/5、1/3、1/4左右。详见下表:

表3 《奏定学堂章程》中、小学堂“中学”各科时刻表
高等学堂阶段取消原来政科、艺科设与不设的区别,各分类皆列有经学课程。更创设经科大学,列有专经研究。除了普通学之外,专门学堂的经学比重也有所增加。初级师范学堂完全科经学授讲课时、程度等同于中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分类科程度等同于高等学堂,课时略减。但无论初级师范还是优级师范,经学课时比重都超过壬寅学制中大学堂师范馆的规定。显示中学分科首重经学。故该章程的立学宗旨阐明: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奏折,文教类,学校项,7213—44,胶片号:537—3258。。作为全学纲领的《学务纲要》也多处提到经学万不可少,明确表示对经学的偏重。
癸卯学制虽然整体增加了各阶段经学课程,但中小学堂阶段诵读的经书内容,却较壬寅学制有所减少。这是因为在中西并学的情况下,张之洞主张要保存中学,必须守约易简以救之③《守约》,《张之洞全集》,卷270,劝学篇一,第9727页。。在学堂功课既繁的情况下,不得不限制读全经④《致京管理大学堂张尚书》,《张之洞全集》,卷256,电牍87,第9029—9030页。。壬寅学制规定,自中学堂后,十三经全部读毕。癸卯学制则规定至中学堂毕业为止,春秋只读《左传》,《礼记》、《仪礼》、《周礼》只读节本,尔雅不读。实际上十三经中只读十经,且有三经只读节本,所学内容减少甚多。详见下表:

表4 壬寅、癸卯学制中小学堂读经内容比较表⑤
到了高等学堂以上阶段,讲授经学大义的内容也有变化。张之洞早于《书目答问》经部下阐明:“经学、小学书,以国朝人为极,于前代著作,撷长弃短,皆已包括其中”①范希曾补正,徐鹏导读:《书目答问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页。。故一反壬寅学制读汉以来注家大义的规定,主张各经注疏等以国朝诸家之书为要。详见下表:

表5 壬寅学制、癸卯学制高等学堂经学科目内容比较表
癸卯学制的章程条文,大都认为出自于陈毅之手②胡思敬:《大臣延揽不慎》,《国闻备乘》,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55页。另见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教育世界》1906年第118、119号。。但其中经学课程的规划,据张之洞身旁幕僚所记,全部由张亲自操刀,“学务纲要、经学各门及各学堂之中国文学课程,则公手定者也”③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4册,第87页。。此言确非泛论,学制中的一些主张,“张氏烙印”极为明显,在张之洞早期著述和奏稿中都有所体现。如没有放弃作《劝学篇》时对康有为借公羊而谈变法的警惕性,言讲《公羊》,必须《公羊》、《穀梁》、《左传》三传并习。小学堂读经主张讲解经文宜从浅显,深奥者入高等学堂再研习,并强调高等小学堂必读《诗》、《书》、《易》数经的做法言论,可寻迹于张之洞此前所上《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④该折提出:“经文古奥,幼年读之明其义理之浅者,长大以后渐解其义理之深者。若幼学未经上口,且并未寓目,中年以往必更苦其奥涩厌其迂远,岂耐研寻。”见《张之洞全集》,卷57,奏议57,第1488—1502页。。而中小学阶段读《周礼》、《仪礼》与《礼记》主张用节本,也早在接获壬寅学制时便已提出⑤《致京管理大学堂张尚书》,《张之洞全集》,卷256,电牍87,第9029—9030页。。通过癸卯学制,张之洞得以将湖北经验和个人治学办法落实到全国的学务规划中去。
壬寅学制未及完全施行,癸卯学制颁布后,新旧教育的衔接转换开始走向实践。作为旧学代表,分科设学下的经学课程,无疑会引起时人的关注和讨论。
四、反应与评议
经学课程设置是要按照西方学制整合传统旧学,因而成为新学制被关注的焦点。经学规划是否合适,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怎样,众说纷纭。学制中经学课程的规划,立意很高,但最终要落于实处。作为学堂教育参与主体的教习与学生,展现了各自对于经学课程的接受程度。随着学制的推行,经学课程的实施效果,背离了张之洞的初衷。时人评价,也出现了怀疑和否定的倾向。
学制立意强调分科治学,但在实际规制中,经学却存在于多处学科课程之中。如修身、人伦道德等科,主要内容就是四书等经学大义。史学与中国文学等课程的开展,也离不开经学。如保存中国文辞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读古经籍;研究中国文学,也离不开群经;研究史学,《左传》等是重要内容等等。这显示了新学制中分科治学的精神,并不能完全掩盖与中学本身的关联。却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经学作为学科存在的独特性和必要性,引发对经学与各科关系的讨论。
关于经学与各科关系的讨论,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经学、伦理与修身的共存问题。修身、伦理内容多取自四书、五经大义,与读经课程有一定程度的重复,“夫四书五经,何者非修身,何者非伦理?吾不知此外更以何者为修身、伦理也”⑥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九日,第250页。。故时论认为,或将经籍大义归并入修身⑦《奏定小学堂章程评议》,《时报》1904年5月22日。,或将修身、伦理归入读经课①《上学务大臣条议》,《专件》,《湖南官报》第603号,1904年3月25日。。一是经科、文科大学的分置存在争议。两次学制对分科大学的规划本就不同,壬寅学制参照日本大学分类办法,经科纳入文学科下。癸卯学制则将经学与理学放入专为中国固有学术而创设的经科大学,史学与文学放入可以对应西学分类的文科大学②这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史学和文学在西学学科内找得到对应学科,放入仿照日本制度而设的文科大学;而经学和理学乃中国独有,找不到对照的学科,故放入新设之经科大学。。王国维在看过大学堂分科章程后,认为经学与文学内容联系密切,“必欲独立一科以与极有关系之文学相隔绝,此则余所不解也”③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教育世界》1906年第118、119号。。不赞同将经科与文学科分列,主张废置经科,仍放入文学科下。若想表达尊经之意,则将文学科置于各分科大学之首即可。
虽然对于分科规划有不同意见,但癸卯学制对于经学的注重,却是显而易见的。一些趋新的报刊,认为奏定学堂章程过于强调旧学,必强学生读十三经、二十四史,“更令萦心于旧学之经说”④《时评》,《警钟日报》1904年8月1号。。王国维则进一步揣测张之洞的本意,认为分科大学、经学文学二科章程为“张尚书最得意之作”,不惮于“学术上所素娴者”忠实陈其意见,且公忠体国,以扶翼世道人心为己任,惧邪说之横流、国粹之丧失,故详订教授细目及其研究法,“于此二章程中尤情见乎辞矣”⑤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教育世界》1906年第118、119号。。
除了在野舆论,朝堂之上对于学制中经学课程也有所关注。清廷早在新政初期,就已将不废经学的办学态度明确下来。所以,各种官方讨论皆在设经学的前提下进行。癸卯学制出台前,三位会商学务大臣虽主张不同,分歧只是在如何设的问题上。学制颁布后,言官对学制提出的商榷,也在此前提下进行。御史左绍佐奏称学堂关系重要,措置当不厌求详。并片奏称学生宜专习一经,不可删改经文,与学制章程规定“各学堂课程,四书五经皆读全文”之意吻合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奏折,文教类,学校项,7213—51,胶片号:537—3276。。御史张元奇也奏请:“蒙学但课中文,俟考入中学堂后再习西国语言文字。”实际上是要求小学堂不习洋文,以免占学生读经时刻⑦《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02,学校9,第8609页。。
抛开设制的立意高远与议论的纸上谈兵,学制颁布影响最大的,其实是“今之学林”无不由新章而变⑧语出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时人评价张之洞参与学制规划一事,“今之学林,殆无不由公而变”。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4册,第162页。。学堂的教习与学生才是直接感受新学制所带来变化的主体。他们对待经学课程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此时的经学教习,多系旧学出身。张之洞等人奏准的递减科举折预想到,“经生寒儒,文行并美而不能改习新学者,可选充各学堂经学科、文学科之教习”。从一些学务调查的结果来看,旧学的功名程度往往决定其所传授学堂的层级,一般中小学堂经学教习举、贡、廩、增、附皆有,高等学堂以上则多为举人出身。而有一定门第、文名之人,更易获得教席⑨公奴:《金陵卖书记》,《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399页。。多数经学教习入学堂后,因少经师范熏陶⑩直隶省视学1906年查视天津各学堂情形,发现学堂教员多非师范毕业者。《直隶教育杂志》1907年第4期,第39—40页。,不过将原来应试的东西拿出来宣讲充数而已。如某地中学堂宣讲经学一门,由教习将向所撰述经解等类抄给阅看⑪《本国纪闻》,《警钟日报》1904年7月13号。。保定广昌县小学堂以举人李得龄为教员,日以经义课士⑫《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234页。。湖北所设之南省中学,其教习类皆八股老秀才,竟不知黑板为何物①《学界纪闻》,《警钟日报》1904年12月5号。。这样的情况相当普遍。一些地方要专为这些教员补习速成师范②光绪三十年九月张之洞札湖北学务处开设鄂省师范传习所,目的为“以便各属选派备充小学堂教员之举贡生员,来省分入各师范传习所,讲授教育学管理法及初等小学堂各科学之要旨大义,俾粗谙师范规程,从事教育不致茫无措手”。《张之洞全集》,卷150,公牍65,咨札65,第4255页。。情况稍好一点,则教习等稍微接触西学知识,如江西高等学堂教习唐咏霓,即以周礼发问,与西政、西艺相比附③杨士京:《前江西高等学堂革命运动之回忆》,《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652页。。有文名之经师宿儒,常就自己所宗,抒己所长。王闿运执教江西大学堂(实为高等学堂),“所讲论语独辟思想”④《学界纪闻》,《警钟日报》1904年9月6号。。
各地主讲席者,不乏怀抱“宗经卫道”自觉的人。苏州中学堂聘曹元弼为经学教习,其说“要以黜异端、息邪说为宗主”⑤《本国纪闻》,《警钟日报》1904年7月23号。。甘肃文高等学堂教习刘尔忻主讲经学,声誉甚高,平时对学生也很爱护。但一旦发现学生有“欺君罔上、叛道离经”的言行,即严加责打⑥《清末甘肃文高等学堂的片段回忆》,《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672、675页。。为了挽世道人心,有人甚至主动在学堂讲授经学。1905年,河南禹州三峰实业学堂山长王锡彤,自发为实业学堂学生教《论语》⑦王锡彤:《抑斋自述》,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5—117页。。恽毓鼎则打算修改小学堂章程,专以四书五经为主⑧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九日,第250页。。
学堂学生对经学课程的态度,略有差异。革命性较强的《警钟日报》认为新的学制章程悉以“压制学生、闭聪塞明为宗旨”⑨《学界纪闻》,《警钟日报》1904年9月3号。。一些趋新的学生,如河南高等学堂和杭州武备学堂学生反对阅读《小学》、《孝经》或他们认为是“不急之务”的性理书,甚至哄堂罢课⑩《河南高等学堂》,《国民日日报汇编》三。。但这一时期的多数学堂直接由书院、书塾转化而来,学生对修习熟悉的经学课程并无不适。且中学、高等以上各学堂开办之始,无合格生源,只能招考秀才、廪生等入学,使得各学堂学生有功名之人极多。如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6年共有学生321人,旧学功名出身者243人⑪房兆楹:《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第78—136页。。这些学生已具文史根柢,反而对于西学知识有陌生感。故多能接受经学课程,沉静好学,有“尊经”遗风⑫陆殿舆:《四川高等学堂纪略》,《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618页。。像杭州府中学堂学生对经史课程乐于听讲,并以笺注《春秋大事表·序》获誉而引以为荣⑬项士元:《杭州府中学堂之文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549页。。甚至出现过完全相反的情形。保定直隶高等学堂本来注重国学,因总教习注重西学,而师生皆不满,与其“长久存在着矛盾”⑭《北洋大学事略》记直隶高等学堂,《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630页。。
科举的存在,也影响了学堂学生对经学课程的态度。癸卯学制虽然规定凡在各学堂肄业学年期内,均不得应科举考试,却准予毕业学生参与乡会试,使得经学课程可作为学生毕业后应试的积累。而科举只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累年之研究”,相较之下,通过科举考试,对一些渴望更快得到出身的学生来说,诱惑更大。各地对在读学生参加科考没有一律采取严格禁令,即便严格的地方,也有学生改名应试⑮报纸曾经登出台州官学堂学生为应试改名事情,见《学界纪闻》,《警钟日报》1904年12月15号。。故一些地方的学堂学生,对读经课程的态度因有利举业而颇为踊跃。每逢考试之期,学生花费精力读经温经,且转移其他科目时间于读经上。淮安县山阳小学1904年县考在即,“上英文课者不过居十之二三,上算学课者不过十之四五,每月逢各书院开课之日,则无一上英文算学课者”,学生莫不手持经义一册,“揣摩吟诵焉”①《地方纪闻》,《警钟日报》1904年4月23号。。
在张之洞看来,新的学制章程,一方面增加新学,“皆科举诸生之所未备”;另一方面则科举所尚之旧学,“皆学堂诸生之所优为”,使得新式学堂兼具“中体”和“西用”之学。且就经学而言,较旧时“讲读研求之法皆有定程”,尤加详备,有序有恒。显然他对新学制下的学堂育才和旧学训练,都有很高的期望。不过各地对分科设学的理解和实施需要时间,新旧知识和教育机构的并存也非轻易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都导致学制实行的情况,效果不佳,其教授办法和教育质量渐为人所诟病。立停科举后,学堂成为维系经学教育的惟一渠道,当人们习惯性地用科举时代的标准去衡量学堂中的经学教育时,对其成效的评价很容易走向怀疑和否定,详情另文再论。
随着学制的推行,再度引发对于经学消亡的忧虑。恽毓鼎认为“南皮总督真吾道罪人也”,理由即是“近来中外学堂皆注重日本之学,弃四书五经若弁髦,即有编入课程者亦不过小作周旋,特不便昌言废之而已”。并由此预言:“不及十年,周孔道绝,犯上作乱,必致无所不为。”②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九日,第250页。而分科太多,显然减少了学生修习经学的精力。刘汝骥在1906年慈禧召见时,指出直隶办学的毛病,除了糜费太多外,要项之一,便是“中学堂以上学科太杂,于经学反多荒废”③刘汝骥:《丙午召见恭记》,《陶甓公牍》,卷1,示谕,第1—2页。。1906年孙家鼐也提出:“学堂偏重西学,恐经学荒废,纲常名教,日益衰微。拟请设法维持。”④《德宗景皇帝实录》(八),卷563,第5158—5159页。张之洞规划学制经学课程时,曾经自信地表示:“若按此章程办理,则学堂中决无一荒经之人,不惟圣教不至废坠,且经学从此更可昌明矣。”但学制实行一年多,显然与他的预期差之甚远。
梁启超总结清代办学历程,点出新式学堂发展的关键所在:“吾国自经甲午之难,教育之论,始萌蘖焉。庚子再创,一年以来,而教育之声,遍满于朝野上下。”⑤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下册,第479页。其中教育一词,明显是西式分科教育的观念。甲午之后,中学在新式学堂中被划分为经学、史学等几项课程。壬寅、癸卯学制的出台,使得学堂分科成为共识。学制框架内的经学,在各阶段学堂中有了内容、层级安排的衔接和递升。随着新学制在各地学堂的实施,经学在“以西方学术之分类来衡量”的路上也越走越远。接踵而来的立停科举,使得原有王朝学校体制废除,“不废经学”的责任更多的落在了学堂的经学课程上。但学制实际执行的效果不如人意,变成一科的经学,很难担负维系圣教和支撑中学的重任,于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保存旧学的办法,存古学堂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