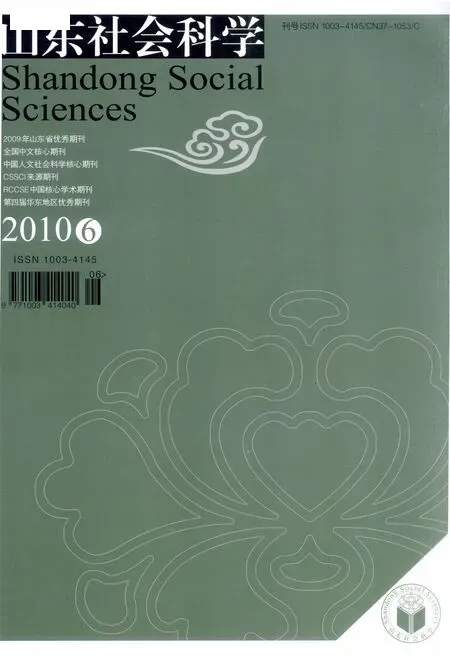中国佛学的否定性思维①
石义华
(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江苏徐州 221008)
中国佛学的否定性思维①
石义华
(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江苏徐州 221008)
佛学的思维方式是非实体性的,是对同一性的破斥,它充满异质性特点,从而走向否定。佛学的否定性思维通过对“空”或“无”的强调而实现,它是对“成见”、对一切既有理论的否定,是对概念拜物教的否定。这种持续的否定带有本体性特点,它使佛学理论得以不断自我更新,为人的思维拓展出无限的、自由的空间。
佛教哲学;思维方式;否定性;空;无
传统西方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是实体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在近代以后的西方备受质疑的思维方式。实体作为一个同一物意味着肯定。后现代主义以对差异的强调在同一物中插入了异质性因素,从而摧毁了实体的同一性,摧毁了实体的总体性,使实体“碎片化”了。摧毁也就是否定,后现代主义中的否定是持续不断的。和后现代主义一样,否定性思维在佛学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带有“本体性”特点。
一、本体论化思维的转向
本体论化思维致力于寻找万事万物的同一性,以及寻找作为这种同一性依据和事物存在依据的最后根源。思维的同一性是其特点。但是人们很少想到自己的认识能力是否能够胜任这个工作。不可否认,有一些思想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比如中国战国时代的著名思想家庄子,他曾经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庄子·养生主》)庄子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二者的矛盾显而易见,所以,人不可能认识无限。在《庄子》一书中,多次考察了人的认识能力,《秋水》中写道:“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泗,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子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垒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睇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伯夷辞之以为多,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庄子列举了“井蛙”、“夏虫”之类的有限之物,落脚点在于以此类比人——“曲士”认识上的有限,人们自以为自己知道得多,其实不过是像“河伯”的自大一样可笑。只有当人们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时,它才超出了自己原先的有限性,无限就存在于这种对有限的不断的否定之中。在西方,康德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了考察,他宣称理性一旦超出现象界的范围就会发生自我矛盾的情况,现象界是康德为人的理性所划定的最后界限。本体作为物自体,是人的理性无法认识也无法加以论证、说明的,形而上学的追寻终极存在依据的努力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人们应当转换哲学认识的方向。
后现代主义尽管流派众多,但在对本体的态度上却惊人地一致,都自觉地避免本体论化思维,他们或是绕过对形上之物的追寻,或是干脆宣布其无意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清除一切本源性的思想,如泰勒斯创立的始基概念,柏拉图所谓的理念世界等等,总之是要转变寻求作为中心、始源、基础之类的在场的思维方式,可以说,解构主义要解构的从根本上说就是本体论化思维方式和建立在这种思维方式基础之上的形而上学。
西方哲学的新方向和佛学的方向有很大的一致性。佛学并不着力于寻找万物同一性,不去寻找本体性的存在物。它认为整个宇宙,三千大千世界都不过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中的“缘起”,它们互为依据,但人们永远也找不到一个不变的、最后的依据。因此佛学否定现象,也否定本体,它是没有本体论的,但这只是说它没有实体性的、固定不变的本体,如果非要找出一个佛学的本体,那么,就是否定。否定取代了各种形式的始源的地位,具有了“本体性”。因为佛学不承认有常住之物,它对于实体的否定是一贯的,它否弃了不变的主体,否认了“色”或“法”的真实性,除了“否定性思维”本身,什么都是被否定的。真如、藏识、佛性等等,都不过是为了言说的方便安立的“假名”而已。与其说他们是真实的存在,不如说他们是一个“无”,一个“空”。真如、藏识、佛性等等也可以说就是中道,中道就是一个否定,否定“有”也否定“无”;否定“生”也否定“灭”;否定“常”也否定“断”;否定“一”也否定“异”。而“胜义中道”连“中”也不要,就是说,中道对待自身的态度也是否定的。天台宗有云:“弃边取中,如舍空求空”。中道也好,空也好,其本身也同样要舍弃。这可以说是一种彻底的否定,是带有本体性的否定。
中道也就是般若,般若作为智慧是一种否定性思维。般若所得到的认识是实相。“实相非相”,实相虽称为实,仍是非实。般若“见相非相”才能破除对象化思维,领悟“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道理,才能让自己保持不着于物的虚寂状态。
佛学的否定性思维和异质性思维有着内在的联系。因为佛学概念、范畴都包含着自己的对立面,就使得每一个概念都指向内涵又游离于内涵,走向自己的反面,这就是否定性的根源。否定反对任何对意义的肯定性把握,在持续的瓦解中释放被同一性压制的内容,展现出生命的无尽的意义。
二、作为否定性的“空”与“无”
佛学主张万物皆空,被称为“空门”。但对于万物皆空的说法,人们不能只把它当成一个现成的结论看待,它体现着的是一种否定性思维原则。“空”与“无”意义相当,都是否定。佛教的“空”或“无”否定了本体,否定了万物存在的真实性,否定了人的理性认识,甚至否定了佛法自身。
本体是肯定性思维的最大“成果”,但它也不过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者,而非存在本身。因为存在不是一个肯定性的东西。海德格尔受尼采的影响但超过了尼采,他不仅极为严肃地,而且也许是在西方历史上最深刻地理解“无”的问题。他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是“存在”的遗忘 (seinsvergessenheit)的历史,他试图询问存在本身 (sein selbst)的意义,在他看来,这是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而上学中所理解的存在者之存在 (sein des Seienden)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虽然存在者之“存在”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存在”是从存在者方面来理解的。它被看作好像正对着我们“在那儿”。存在没有从它自己的方面、根据它自身来被理解。就在以这种客观的方式询问存在者的存在时,亚里士多德及其以后的西方形而上学隐蔽和遗忘了“存在”本身。为了洞察“存在”本身,而不只是存在者之“存在”,海德格尔坚持要在我们自己存在的深处来领悟无(dasNicht s)。直面无就是克服存在的遗忘性。无揭出存在本身。这又同佛教对于空的理解惊人地相似。①[日]阿部正雄:《禅与西方思想》,王雷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年版,第157页、第155页。亚里士多德的存在是一个圆满自足的自我同一物,它拒绝任何不同于自身的因素,显示出与董仲舒所说的“道”一样的僵化性,这样的存在实际上是一个存在者而非存在本身。海德格尔的“存在”则是一个带有否定性的概念。海氏从隐藏于存在者深处的无来破斥存在者的僵死性,破斥存在者加之于存在的束缚,恢复存在作为无的本来面目。无就是对存在者的否定,是能揭示出存在的东西。
“在佛教中,拯救所必不可少的不是用善去克服恶,并分享至善,而是从善与恶的存在性对立中解放出来,并悟到优先于善恶对立的空。在对空的存在性的领悟中,人们可以征服善与恶,而不是被它们所奴役。在这个意义上,领悟真空是人类自由、创造活动和伦理生活的基础。”②[日]阿部正雄:《禅与西 方思想》,王雷泉 、张汝伦译,上海译 文出版社 1989年版,第157页 、第155页。一般的宗教都悬拟一个至善的意义世界,劝人崇善抑恶,但佛教以其否定性显示出与一般宗教不同的特点,它虽然也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但这也不过是佛教随顺众生思维方式的方便说法,非究竟意,究极言之,佛教否定恶,也否定善,善并无优于恶的崇高地位。这是因为佛教释放出隐藏于善、恶以及各种现象中的空或无,释放出现象中蕴含着的否定性,以摆脱知性思维对人认识的束缚,破斥凝固化的存在者,进入超越善恶之上的真空境界,与存在同在。佛学用以解放人们思想的武器是无,是否定,因此说领悟空与无是人类自由的基础。
(一)无我——对主体和自我中心主义的否定
中国佛学对于”我执”是持否定态度的。唯识宗认为“我执”是烦恼的根源,窥基大师说:“且烦恼障品类众多。”我执“为根生诸烦恼,若不执我无烦恼故。证无我理我见便除。由根断故枝条亦尽。此依见道,乃究竟位断烦恼说。”①[唐]窥基:《唯识论述记》卷一。烦恼的种类多种多样,唯识宗对于烦恼的分类也非常详细,兹不赘述。窥基大师认为,烦恼的根源就在于人有对于“我”的执着,我见象是树木的根,烦恼是枝条,除去我见就是除去了烦恼的根本。因此“无我之心虽不称境,违于染故名非颠倒”。②[唐]窥基:《唯识论述记》卷一。无我之心正是对治染心的有效手段。“此空无我所显真如,离有,离无,离俱有无,离俱非有无,心行处灭,言语道断。”③[唐]窥基:《唯识论述记》卷二。否定要否定存在,否定非存在,对亦有亦无,非有非无一同否定,停止人的知性思维,否定所有语言表述。真如就在彻底的否定中呈现自身。
天台宗对于”我执”的态度也是否定的:“今观法性即空一切皆空,空中无我。是名凡夫倒破枯念处成;法性即假一切皆假施设,自在不滞我义具足,是名二乘倒破荣念处成。”④智顗:《摩诃止观》。
法性是空的,我是空的,一切皆空也是空的。法性也不过是一种名言施设,不意味着实有此物。真正的自在者不滞于物,也不停留于“自身”,它是一个否定,一个无限。当自我设定自己并处于与他者二分的状态时,它以自我为中心,开始奴役他者,排斥他者,使自我与他者处于无法融合的割裂状态。对他者的奴役与排斥,结局是演变成对自己的强暴,变成自役。
三论宗把我和无我同等看待,显示出般若学对他们的影响。吉藏写道:“《楞伽经》说无我为如来藏,涅槃说我为如来藏。此两文复若为配当耶,本有始有其义亦尔。是故涅槃云:我无我无有二相。”⑤吉藏:《大乘玄论》。如来藏就是无我,是我中蕴含的否定性。但正如异质性思维所揭示的,否定的同时有肯定,肯定的同时有否定,因此《楞伽经》说无我为如来藏,《涅槃经》说如来藏即是我意,他们都是正确的。其它如佛性本有还是始有的认识都是如此,说明绝对的否定和绝对的肯定二者相通。无是否定,也是“完成”,可以称之为“否定的完成”,而否定的完成或达成正是后现代主义解构策略的真谛。
禅学也主张无我,黄檗说:“无人、无我、无贪瞋、无憎爱、无胜负,但除却如许多种妄想。”⑥《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见《古尊宿语录》卷三。人我之见都是空的,是人的妄想。除却人见、我见才能得到解脱。司空山本净禅师说:“四大无主身亦无我,无我所见与道相应。”⑦《景德传灯录》卷五。四大没有实体性,人也没有实体性,与道相应的见解就是否定”我执”、“我见”。
(二)无相——对物与现象的否定
人们日常所见的各种现象在佛教看来都是假相,但是佛教又否认实相是在此假相之外的,佛教的中道关键是能认识到“实相无相”,用僧肇的话说就是“即万物之自虚”。佛教之所以说“实相无相”,是为了破斥人们心头的执着之心。
关于万物,关于佛学“本体”如真谛、中道的真实相状,吉藏说:“真谛中道,无名无相。”⑧吉藏:《大乘玄论》。真谛无相,不可道说。天台宗的谛观也认为“常境无相”、“无相而相”,就是说佛境没有相状,无相就是佛境的相状。唯识宗的窥基也认为“胜义谛中一切无相诸法皆空”。⑨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卷第一。华严宗对于真如是这样认识的:“当知真如自性非有相非无相非非有相非非无相非有无俱相。言非有相者,明真离妄有也。惑者云:既其非有,即应是无。释云:我非汝妄有故说非有,非说是无,如何执无,故云非无也。惑者闻上非有,又闻非无,别谓双非是真如法。释云:我非汝谓有说非有,非谓法体是非有。非汝谓无、说非无。非谓法体是非无。如何复执非有非无?故云非非有非非无也。惑者又云:我上立有立无,汝并双非,双非若存,即有无随丧。今双非既非,我有无还立。释云:我非汝双非故说非非,非许双是,如何复执?故云非有无俱也。“①法藏:《大乘起信论义记》卷中。真如自性非有相,这是为了让人们远离假相。说非有并非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双遣也不是真法,说非非是为了对治双遣法遗留的弊病,不能由此得出亦此亦彼的“双是”结论,法藏说“真如自性非有相非无相非非有相非非无相非有无俱相”的目的是持续的否定。
(三)无言:对语言的否定
中国佛学中除后期禅宗的少数人外,一般对于语言从根本上说是持排斥态度的。僧肇说:“有无之称,本乎无名,且至趣无言,言必乖趣。”②僧肇:《肇论·答刘遗民书》三论宗吉藏法师云:“若以名求真去真远者。”③吉藏:《大乘玄论》卷一。天台智顗说:“假名无实,无实故空,名空门。”④智顗:《摩诃止观》卷一。华严宗法藏说:“夫真心寥廓,绝言象于筌蹄。是故一切法从本已来,离心缘相,毕竟平等。”⑤法藏:《大乘起信论义记》卷上。窥基认为佛境是:“心行处灭。”⑥窥基:《唯识论述记》卷一。佛的境界是无相的,也是难以言诠的,如有言说,就背离了佛教至理。佛教至理是无相无言的,所以佛教才被称为空门,要觉知佛教真理,就应“离言说相离名字相”,或说是“言语道断”。但是佛教中真与假之间并无确定的界线,实相不离假相,因此说言说是假也是一种假说,持续的否定使佛教返回原点,因此佛教在否定言说之后往往又重新肯定语言的意义。和对语言的否定相联系的是对知性思维、佛法的“否定”。佛教的内空就是要否定主观认识,包括对佛法的认识,如果人们执着于佛所说法,法也就成了魔障。
三、清除前见与成见
理解建立在前见的基础之上,但由于新情况的出现,往往使人既有的认识不能适应新的现实,执着于现有的认识,也使人被现有的认识所束缚,无限的东西不会停留于任何的确定知识。同时,既有知识对于人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也可能会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后现代主义主张对既有结论进行不断的解构,打破知识体系静态化的逻辑结构,打破其总体性,使知识变成流动着的“碎片”。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知识理论也是持解构态度的,因为人们一旦把一种思想当做万古不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真理”就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变成谬误。所以马克思的精神就是怀疑一切;恩格斯也告诫人们,他和马克思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非教条;列宁在一次病愈后挥笔写下一句谚语:“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但后来出现了背离马克思主义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凝固化的情况:“阿多诺明确指认道,同样将辩证法变成一种立场的还有斯大林式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随着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形式成为一种文化财富,它的非唯心主义形式却退化成一种教条”。这是阿多诺理解的马克思辩证法诠释史上的一出悲剧。这种同样是同一性体系哲学的“唯物辩证法”,甚至放弃了黑格尔已经使哲学获得的“具体地思维的权利和能力”,而让哲学再一次成为一种对现实世界“漠不关心”的“既空洞又特别无用和无聊的认识形式的分析”。⑦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版,第83-84页。这是一种倒退。阿多诺和他的后学后现代主义者都强调流动性,反对那种僵化的真理观,他们不迷恋任何既有知识,为防止知识绝对化,他们甚至拒绝使用“真理”术语,而代之以“话语”。
以概念、判断和推理为基本形式的逻辑思维对于人来说是整理自己认识的思维形式,但它也无法真实描述世界万物的面貌。因为形式逻辑的细胞——概念并不能把它所代表的事物全部装入自身,建立在它之上的判断、推理因此也只是事物的近似反映。弗洛姆把语言逻辑看成是过滤器,它帮助我们留住了一些东西,同时也漏掉了更多的东西:“经验要想被觉知到,只能是在它能够凭借一个概念系统及其范畴而得到理解、得到关联并变得合理有序的条件下才能办到。这个概念系统本身乃是社会进化的结果。每一个社会都通过其自身的生存实践,通过种种关系模式、情感模式和理解模式而形成一个范畴系统并以此决定其觉知形式。这一范畴系统的作用就仿佛是一个受社会制约的过滤器;经验要想被觉察到,除非是它能够穿透这个过滤器。”⑧埃里克·弗洛姆:《精神分析与禅宗》,见《禅宗与精神分析》(弗洛姆等著,王雷泉、冯川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119-120页。语言、逻辑充其量是人们认识的凝固化表现,它们作为过滤器遮蔽了真实的生命之流以及事物的本来面目。并且形式逻辑所遵循的因果律对于人来说,也是不得不如此的必然,人在它面前绝无自由,人要重获自由必须摆脱这种因果性的支配。
弗洛姆认为,由于社会禁忌,由于害怕社会惩罚,尤其是害怕被社会遗弃导致的孤独,在语言、逻辑外人还受到第三种过滤器——经验内容的影响。一个人的社会经验就是冒犯禁忌会受到社会惩罚,而对于彻底孤独的恐惧,“有效地阻止了一个人意识到种种禁忌的情感和思想”,①埃里克·弗洛姆:《精神分析与禅宗》,见《禅宗与精神分析》(弗洛姆等著,王雷泉、冯川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125页、第30页、第30页、第151页。更多的内容被压抑为潜意识,“既然意识只代表由社会塑造的一小部分经验,而无意识则代表具有普遍性的人的全部丰富深邃的经验,那么压抑状态必然导致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偶然的、社会的人的我,被分割在作为整个人性的人的我之外。我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陌生人。我被割裂在人性经验的广阔领域之外,自始至终是人的一块碎片,是一个畸形人,仅仅体验到于己于人来说都是真实的东西的极小一部分”。②埃里克·弗洛姆:《精神分析与禅宗》,见《禅宗与精神分析》(弗洛姆等著,王雷泉、冯川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125页、第30页、第30页、第151页。压抑造成的后果就是统一的意识分裂为意识和无意识或潜意识。人丧失了丰富的、完整的体验,由完整性的存在沦为碎片化的存在物;由自由的存在沦为有限的存在物。
“意识和无意识是受社会制约的。我能够察觉到我的一切情感和思想,只要它们能够顺利通过 (受社会制约的)语言、逻辑和禁忌 (社会性格)这三种过滤。所有那些不能通过过滤器的经验将永远留在知觉的外面,也就是说,它们将始终是无意识。”③埃里克·弗洛姆:《 精神分析与 禅宗》,见 《禅宗与精 神分析》(弗洛姆等著,王雷泉、 冯川译),贵州人民出 版社 1998年版,第125页、第30页、第30页、第151页 。语言、逻辑使人自隔于宇宙实相,再加上由于社会的原因在人们心目中造成的压抑,扭曲了人们的心灵,因此人们要想如实认识事物的真相,就必须消解三种社会过滤器,摆脱语言、逻辑思维对潜意识的压制,让事物的真相呈现。
所以后现代主义否认概念有确定的内涵,力图把人从概念拜物教中解放出来,使“所指”成为一个延迟到场之物,从而使语言和思维具有对应于绝对运动的流动性。由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以文本为对象,是在文本中进行的,所以德里达采用的办法是“写上去又划掉”,显示它对于既有认识的否定。佛学则力图否弃知性思维,破斥必然性的逻辑对人精神的束缚,对于它不得不借助语言表达的佛法,往往在长篇大论之后又否认自己有所认识,有所表达。这与德里达的做法不谋而合。后现代主义许多看似怪异、极端的做法在佛教中常能找到“知音”。后现代主义和佛教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清除那些扭曲、异化了的所谓知识以及导致这些认识的三种“社会过滤器。”。
撤除三种“社会过滤器”,对已有的认知做减法运算,走出“已知”的陷阱,还世界以本来面目;把人从各种遮蔽中解放出来,归还给他自己,从而使人重新居有自身,恢复自己意识的完整性;恢复人对世界把握的完整性,“如果我能达到把这过滤器撤除的程度,我就能以一个宇宙的人的身份来体验我自己,亦即是说,一旦消除压抑,我就与我生命中最深的本源沟通,这就意味着与一切人性沟通。如果一切压抑都被消除,就不再有与意识相对的无意识;有的只是直接的体验。由于我对自己不是陌生人,也就没有任何人和物对我陌生”。④埃里 克·弗 洛姆:《精 神分 析与禅 宗》,见《 禅宗与 精神 分析》(弗洛 姆等 著,王 雷泉 、冯川 译),贵州 人民出 版社 1998年 版,第125页、第30页、 第30页 、第151页。重新为人所把握的世界不再是被三种“社会过滤器”隔断的主客二分的世界,而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主客统一的世界。这时候“他不再囿于片面的、有限的、受限制的、自我中心的存在中的自我。它已经走出了这个监牢”,⑤玲木大拙:《禅学讲演》,见《禅宗与精神分析》(弗洛姆等著,王雷泉、冯川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20页。成了“随处做主,立处皆真”的自由人。让我们用阿部正雄的一段话作本文的结尾:“总之,在西方,像存在、生和善这样的肯定性原则在本体论上优先于像非存在、死和恶这样的否定性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否定的原则始终是作为次要的东西被理解的。相反,在东方,尤其在道家和佛教中,否定的原则不是次要的,而是同肯定的原则相平等的,甚至可以说是基本的和主要的。这在领悟否定性对于揭开终极实在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意义上,及在无名的道或空被领悟为相对意义上的肯定与否定原则两者的根源的意义上,都是如此。简而言之,在东方,在肯定与否定的对立之外的至上者是从否定性方面来领悟的,而在西方则是从肯定性方面来领悟的。”⑥[日]阿部正雄:《禅与西方思想》、王雷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年版,第156页。
(责任编辑;周文升 wszhou66@126.com)
B94
A
1003—4145[2010]06—0038—05
2010-03-21
石义华 (1969-),男,江苏徐州人,哲学博士,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佛学、中西哲学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