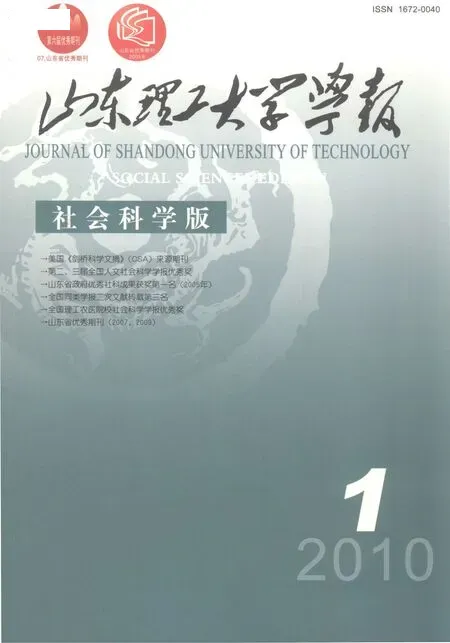论魏晋正始时期士人的生命意识
杨纪荣
(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山东淄博255049)
生命问题是人类面对的最古老的问题之一,因为一切生物都本能的“恋”生“畏”死。而对“生”“死”的自觉,使人类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荡,因而萌发出喜“生”悲“死”的情感,激发自己求生的意志,从而延续、张扬生命,远离、逃避、抗拒死亡,并相应的亲近、利用一切有益于“生”的东西,正是在这种基础上,生命观念才得以发展,生命意识才得以成为人类精神世界的一个核心主题。所谓生命意识,主要包括生命本体意识和生命价值意识两重意义。生命本体意识主要是指对生命本身的性质的认识,即对自我生命的体认、肯定、接纳,生命价值意识则是在肯定生命本体的基础上,对生命应有价值的一种把握和判断。本文从魏晋时期士人的生命意识切入,魏晋时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若从建安元年算起,到刘宋建立,这段时期共持续了224年,其间经历了曹魏代汉,司马氏代魏,八王叛乱,五胡乱华,王敦、苏竣等的叛乱,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等等重大事件,乱世杀夺,生命无常。哲学思想的多元与社会政治的专制、逼人就范的正统礼教与邪说异端的流行广布、统治政权的双重价值与士人的各行其是和独特丰姿、官场的名利杀戮与方外的旷放玄远,时代的苦痛使这段时期呈现出一种奇芳异彩。在这历史的苦痛中,士人所依存的外在空间(社会)与内在空间(心灵)的厮杀,也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度与深度,所有的一切都激发了魏晋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尤其到了正始(241~249)①正始是魏废帝曹芳的年号(240~249),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时期”,还包括正始以后直到西晋立国(265)这一段时期。时期,魏明帝死后,嘉平元年正月,太傅司马懿发动兵变,残杀曹爽、曹曦及何晏、丁谧、邓飏等大批名士,致使天下名士减半。第二年,司马懿之子司马师又残杀了夏侯玄、李丰等名士领袖,将齐王芳废掉而立高贵乡公曹髦。然而仅隔短短五年,司马师之弟司马昭又将曹髦屠杀于血泊之中,司马氏在角逐和杀戮中完成了魏晋易代的过程。在政治地位的角逐和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中,广大士人内心受到的摧残和精神上受到的震撼,程度之深,强度之烈,可想而知。正因为司马氏政权的确立是建立在弑君的血的杀戮的基础上的,政权的建立不忠不义,所以正始时期的政治生活中,充满了猜忌、欺骗、残忍、虚伪、狡诈和屠杀,使这时期的士人不但在心理上,在现实生活中也失去了热情和希望,现实的环境是难以依托的,士人在对现实的失望和冷淡中,走入了一个建立在玄学哲学基础上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们要超越物质生活引发的痛苦,实现精神上的解放和自由,并寻求实现一种君子人格理想。
一、玄学影响和士人对精神世界的建构
魏晋玄学的产生,是汉末儒学的日渐衰颓和道家自然主义思想日益兴起的一种自然演变的产物。它萌芽于汉末与魏初的清谈思想,所讨论的问题,多是从《周易》、《老子》、《庄子》三本经典而来,以老庄思想为骨架,探索的是万物根源、本体等层次的观念,以及宇宙人生的哲理。正始之前,清谈之习已在汉末的谈论中发展起来了,到了正始年间,由清谈而转为谈玄之风大盛,它不但影响了士人的精神面貌,而且也促使了士人生命价值观的改变。正始玄学,从何晏、王弼的“贵无论”开始,到竹林七贤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正是一种时代要求的哲学反映,说到底,它的出现,要解决的就是政治与人生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就是人生,即生命的价值如何体现,理想的人格怎样实现。“贵无派”玄学探讨的最主要问题是圣人的理想人格,但其实蕴含着普通人的理想人格的实现,它正好与阮嵇后来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暗合,形成了正始时期士人生命意识的主调。
正始玄学的开始就是从对“名”和“为”的思考开始的。“贵无派”主张的是“体无以用有”,主张无名无誉的自然之治。何晏《无名论》说:“为民所誉,则有名者也;无誉,无名者也。若夫圣人,名无名,誉无誉;谓无名为道,无誉为大,则夫无名者,可以言有名矣,无誉者,可以言有誉矣。”[1]411以无名为名,以无誉为誉,即是圣人的名誉。他们所议论的这种理想人格的内核,不管“无名”还是“体无”,都缘于道家的生命观,体现的是一种对现实的超越,对名誉地位的舍弃,也就是说,个体首先要放弃求名意识,只有放弃了个体的名誉观念,才能做到无名无誉,那种通过建立功业来实现荣名显达的思想是和这种无名无为的原则相背的,何晏对《论语》中“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提法做了这样的新解:“君子为儒,将以名道;小人为儒,则矜其名也。”[2]2478意思也是个体只有与道合一,才能以道为名,而不是世俗矜名之名。这种理论可以说是玄学影响群体生命价值观的第一步,因为它本身并没有否定行为本身,也没有否定伦理价值观,它否定的只是在实现这种生命价值观的过程中所派生出来的个人的“名”。对个体而言,无名的追求,就是为而无为。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种纯粹思辨的结果,但其实,它是对建安时期以来崇尚名节、渴望建立“金石之功”以求不朽的荣名观的一种反思,是对统治者以卑鄙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私利私欲,对政客之间互相倾轧的腐朽政治行为的一种批判。它追求的是摆脱现实的名誉、地位、金钱的桎梏,实现一种理想的生命境界。
如果说正始玄学只是影响甚至改变了士人群体生命价值观的第一步,那么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名士们所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则对生命意识的改变又推进了一步。这种生命哲学已经抛开了伦理价值生命观,而将基础建立在了老庄哲学之上。所谓“名教”,即儒家所鼓吹的三纲五常的教义,而“越名教”就是要抛弃、超越儒家的伦理教义规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儒学的虚伪和其礼法是对理想人格的阻碍和束缚。阮籍在他的《大人先生传》中曾这样揭露名教的虚伪:
且汝独不见乎虱之出乎裈中,逃乎深缝,匿夫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染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3]167
在这里,他指出名教是一种束缚个体生命的枷锁,若遵从礼法,循规蹈矩,只会陷入灭顶之灾。他们追求的“任自然”,就是放弃对外在功名利禄的追求而进入逍遥的精神王国遨游,追求真正的无为无名的生命境界,不再是“处有体无”,而是将人生至于无、玄的境界,放弃现实的生命价值,寻求一种超现实的生命价值。阮籍又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理想人格:“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于内,而浮明开达于外。”[3]165在这里,他强调,大人先生的形象是完全与“道”和“真”冥和的。“道”和“真”于何、王所说的“无”是同一的,也就是理想人格的根本。个体处在“有”的世界中,要弃“有”体“无”,才能体悟宇宙自然中的“道”。体道,追求一种绝对自由的精神世界,其实就是超越现实世界的伦理生命价值内涵,而进入了自然的人生境界,它并没有失去个体价值存在的标志,只是以体道自足,对伦理型的价值生命观予以否定,倡导一种在道家思想指导下的理想人格。这种理想的生命境界,希望能彻底摆脱荣名的束缚,超越礼教,高扬自我,在一种超越时空的精神世界中逍遥遨游。可以说他们强调的这种“自然”,其实是一种本性,一种理想的自由存在。
何、王强调要无名无誉,否定了名,个体在道中泯灭;而以阮、嵇为代表的正始士人则是将“道”作为实现个体性的内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两者追求的都是超现实价值的生命观,然而这种超现实主义的理想人格在现实中是很难达到的。否定了名,也就相应的导致对名教的否定,因为凡是符合传统伦理价值观的东西都在名教的范围之内,舍弃名教就无法求荣名,个人的生命价值也就难以实现。在此基础上,阮、嵇又对名教的价值观念提出质疑,指出名誉和礼法是虚伪的渊薮,有违生命自然之理,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已同汉魏以来蹈厉发扬以求功名的人生旨趣完全不同,“咸以为百年之生难至,而日月之蹉无常,皆盛仆马、修衣裳、美珠玉、饰帷墙,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矫厉才智,竞逐纵横,家以慧子残,国以才臣亡”。[3]151正是因为正始时期的政治,已经成为统治集团之间的阴谋倾轧,所以阮、嵇只能从这种政治中超脱出来,寻求一种生命状态的本真。他们对名教价值观的否定,归根到底是对现实的批判,他们希望可以论证一种合理的生存方式,使日益浇薄的社会重返淳朴的状态,所以,在他们追求超现实生命价值的同时,又有着很深的现实关怀,这就不能不陷入一种困惑、焦虑和痛苦的矛盾之中,因为在他们内心,既有传统的儒家生命价值观深深扎根,又有社会责任感的召唤时时折磨着他们的心灵,所以他们不可能完全超越社会现实而进入到他们所建构的具有理想色彩的精神王国中,这种生命的现实价值和超现实价值之间的选择,对正始士人来说,是一种不堪忍受的内心折磨,要承受精神上的巨大孤寂,阮籍终生都在这种痛苦中挣扎、煎熬,孤独悲郁,无人能解,而嵇康则慷慨赴死,凛然悲壮。而其他的竹林士人最终也都放弃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命价值追求,返回到传统的建功立业的伦理生命价值观上去寻求自己的归宿。
二、“外坦荡而内淳至”的放达人格追求
正始时期的士人,向往的是超越现实的生命价值而达到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然而他们又有真切的人格关怀,所以,他们的人生态度往往用一种放达的行为表现出来。他们处处与礼法之士反其道而行,追求任情逍遥的人生境界,把返归自然变成一种人生实践。一方面,这种放达的行为,是对黑暗、腐朽的现实社会的一种反叛,另一方面,这种放达的行为,也包含着以阮嵇为代表的正始士人对生命价值的特殊的理解和追求。
(一)“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中,正在我辈”
正始士人不仅重视外在形容之美,对内在风韵也很注重。而当时的人物品鉴也多集中于对人物的仪态风神的赞誉。《世说新语·容止》云:“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5]607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5]607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5]607
这种对风神、仪表、才调等的重视,正是对个体价值高度重视的一种表现,也是对自我意识高度重视的曲折表现,这是魏晋时期生命意识的重要转变。从建安时期就已开始了这种转变,但到正始时期,这种转变更为广泛和深入了,一直持续到东晋,对人的风度姿容和品藻都成为一种风潮。
注重作为人的美,不仅是形容和神韵,还包括人的感情。阮、嵇的生命哲学,首先是站在自然的基础上,嵇康在他的《声无哀乐论》和《养生论》中都强调名教对“情”的压制,为人类的自然之情而辩护,力图挣脱功利的束缚,将道家的个性自由、任情率真的特点与儒家传统的仁义与善良结合起来,他们强调的是“真情”二字,即要求感情的自然流露,没有任何的矫情伪饰,纯任自然,爱憎分明。所谓“机心不存,泊然纯素,从容纵肆”。[4]234
《晋书·阮籍传》载:
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棊,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脊骨立,殆至灭性。[6]1361
阮籍至母丧之时,饮酒食肉,虽以方外人士为托词,但仍可见其不拘于礼,率性而为。然而其哀痛之深笃,又非俗士可比。又如:
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坐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齌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6]1361
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6]1361
王隐《晋书》又说:“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5]730
《晋书·嵇康传》中载:
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煅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颖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煅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6]1373
阮、嵇二人的内心感情极为鲜明,所以表现的也极为真切,他们对世俗的虚伪、狡诈极为厌恶,所以他们的行为都不以礼俗为修饰,率性而发,唯任己心,本色流露,与一般世俗的礼法之士背道而行。
(二)“越名教而任自然”——放达言行中追求的理想人格模式
以竹林名士为代表的正始士人,深知司马氏集团的虎狼本质,明白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无异于纵身跃入浊流。但是面对司马氏的高压手段,却又不能完全与之脱离,既知其统治的乖戾,又要与之周旋,以求自保,可以说放达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士人对自己真实政治态度的一种遮蔽。
竹林名士的放达行迹史书多有记载。阮籍“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6]1359嵇康“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6]1374刘伶“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6]1375从生命意识的追求来说,名士的放达首先是为了摆脱世俗的陈务和政治罗网的羁绊。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6]1360
《晋书·刘伶传》载:
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插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6]1376
《世说新语·任诞》说: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行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5]730
刘伶借其醉酒之态,放行恣肆,其中展示的却是玄学回归的自然状态,也许惊世骇俗,但他在狂饮的过程中确实超越了生死、荣尊等世俗观念,只留下了精神意念间的自由快乐。
与刘伶不同,阮咸的放达行为似乎有“玩世”的意味。《世说新语·任诞》记载:
诸阮前世皆儒学,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旧俗:七月七日,法当晒衣,诸阮庭中,灿然锦绮。咸时总角,乃竖长杆,挂犊鼻裈也。[5]732
阮咸以此种放达行为,显示了自己虽家贫而人格犹贵的天然之质,即玄学所讲的“超然物外,不为物累”的观念,借以反讥名教那种用外在之物来显示自己的虚荣矫饰。
同时,正始士人的放达行为也与玄学的理想人格的追求是一致的,它试图超越世俗社会的伦理政治的枷锁和伦理观念的束缚,形成一种不同于世俗的超越人格,获得自然的人格和精神上的解放,所以这种出世态度其实是一种对人的内心内容的有机把握。阮、嵇等人意欲保持自己内心的真纯,返朴归真,保护自己的真性灵,以便在与司马氏集团的政治周旋中不被污染,这种放达行为正好能够维护他们的这种真感情和真性灵。
嵇康“隐而傲世”,不愿为世俗的准则和规范来扼杀掉自己的性灵,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到自己的“七不堪二不可”:
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骚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法,此甚不可二也。
嵇康不愿与司马氏合作,完全看透了“富贵尊荣”对人生的异化和误导,所以他不但避而远之,还写出“七不堪”“二不可”这样的鄙视之辞,以示与礼法社会的决裂。从《世说新语·简傲》篇中的一段文字,可以看出嵇康那种纯任自然、自足于怀的生活:
康性绝巧,能锻铁,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环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煅。家虽贫,有人就煅者,康不受值。唯亲旧以鸡酒往,与共饮啖,清言而已。[4]119-123
嵇康因为明确表示了不与司马氏合作,他的放达行为与当时的礼法社会产生了正面的冲突,尽管他素有“恬静寡欲,含苟匿瑕,宽简有大量”[6]1369之称,却不为统治者所容,最终被杀害。
阮籍虽与司马氏虚与周旋,但他的放达行为,维护自我内心任情率真的心态却与嵇康是一致的。在《文士传》中载:
籍放诞有傲世情,不乐仕宦,晋文帝亲爱籍,桓与谈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籍尝从容曰:“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愿得为东平太守。”文帝悦,从其意,籍便骑驴径到郡,皆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然后教令清明。[5]736
阮、嵇等正始士人的这种放达的生活方式,之所以能够负载人格力量,关键在于它体现着“外坦荡而内淳至”的内涵,言行自然随意而发,却不违乎大道,实则是真君子,“至性过人,与物无伤”。[6]1371但是,他们在险恶的现实环境中,在与司马氏集团的政治对垒中,无疑是处于弱势,这就使他们这种放达的行为方式,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但仅靠现实的道德修养不能完全支撑这种压力,必须要有超现实的力量来给予补充。阮、嵇等以其诗人的超凡的想象力和对生命存在的深刻体验,将他们对生命的关注凝聚在诗文中,在超现实的审美境界中获得了精神力量和人格支撑。
三、阮、嵇诗文中的生命情怀
阮籍少有“济世志”,深受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的影响,然而,在现实的政治舞台上,布满了血腥、不义和残忍,世不可为,所以他对现实基本是持否定态度的。悲剧的现实,使阮籍在追求超现实生命价值的同时,内心充满了挥不去的悲哀和孤独。
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襟。高鸟翔山冈。燕雀栖下林。青云蔽前庭。素琴凄我心。
崇山有鸣鹤,岂可相追寻。[3]340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3]210
于心怀寸阴,羲阳将欲冥。挥袂抚长剑,仰观浮云征。云问有玄鹤,抗志扬声哀。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3]285
在这些诗里,我们看到的是,他内心的苦闷和孤寂,他的痛苦不是无法施展抱负的痛苦,而是如何在现实中保有独立人格、维持高尚的节操的痛苦,社会是黑暗、残酷的,纵有冲天的壮志,却无从施展,因为此家园并非他的理想家园,此环境并非他心灵可以栖息的归宿,他只能将他对生命的理解和追求,融化在诗歌里,写黑夜、写黄昏,写孤鸿、写山岗、写浮云,在这其中,生命的呈现很脆弱,很短暂,因为缺乏对生命把握的能力。它不同于建安士人功业难成的短暂感,正始士人更多考虑的是他们自身生存的可能,由于社会环境的变易,使他们对生命的短促和毁灭理解得更深,对自身生命可能性的把持也就愈小,在日复一日,一昏一晨中,对生命的宝贵和脆弱的呼号也格外明显:
盛衰在须臾,离别将如何。(咏怀二十七)
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咏怀三十二)
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咏怀八十)
阮、嵇并非是真正的隐士,他们时时关注着现实,然而现实的丑恶,使他们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因而在他们的诗文中也体现了那种洁身自好、高尚其志的人格情怀。
梁东有芳草,一朝再三荣,色容艳姿美,光华耀倾城,岂为明哲士,妖蛊谄媚生。轻薄在一时,安知百世名。路端便娟子,但恐日月倾。焉见冥灵木,悠悠竟无形。[3]392
面对世俗的丑闻和官场的黑暗,诗人认为应该像冥灵木那样独立于世俗之外,悠悠无形,葆有自己的节操。
慷慨思古人,梦想见容辉。愿与知己遇,舒愤启幽微。岩穴多隐逸,轻举求吾师。晨登箕山巅,日夕不知饥。玄居养营魄,千载长自绥。[7]489
嵇康的这首《述志诗》也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在远离尘世的地方,获取自己自由的生命境界。阮籍《咏怀诗》四十六云:
学鸠飞桑榆,海鸟运天池。岂不识宏大,羽翼不相宜。招摇安可翔,不若栖树枝。下集蓬艾间,上游园圃篱。但尔亦自足,用子为追随。[3]338
诗人认为,虽不能如大鹏一样,扶摇九天之上,然学鸠翔于桑榆间,也能自足自乐,就很满足了。在日常生活里如果可以寻找到这种幸福,就可以了。嵇康却把生命的境界引入到了长林丰草间,在游身自然中,实现他向往的自由,得到生命的解脱。他在《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中说: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7]483
嵇康在此诗里表达了他心中的理想世界,那就是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在寻求身外的自然中,求得内心自然的安顿。
综前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魏晋正始时期士人的生命意识。一方面,士人的自我觉醒了,生命情绪达到了一种空前的浓度,他们实现的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达的人格追求;另一方面,玄学生命观对士人的生命价值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改变了他们生命体验的方式,他们向往的是放弃外在功名利禄的追求而进入到逍遥的精神王国,去寻求一种超现实的生命价值。
[1] 严可均.全三国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 阮元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陈伯君.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5]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6]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王弼名教思想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