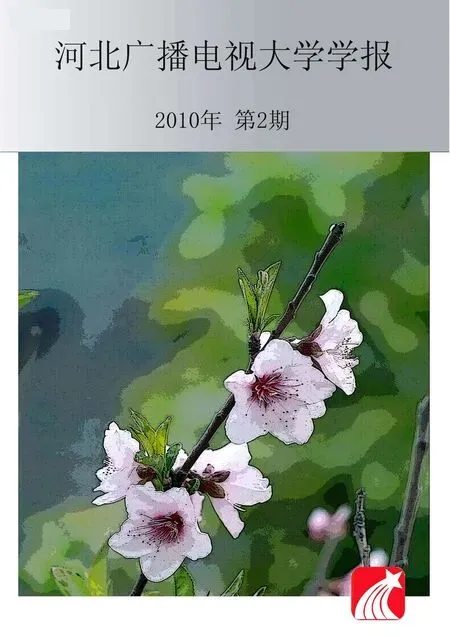高校教师优秀筛选模式新思路探索*
孟祥林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河北保定 071003)
高校教师优秀筛选模式新思路探索*
孟祥林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河北保定 071003)
传统的高校优秀教师的年度筛选遵循比率分配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全校范围的各部门内部平均分配优秀教师名额的制度,其间由于将更大的操作权转移给了部门管理者,会加大部门领导变通制度的自由度,最终由部门推举到学校的所谓优秀就有可能偏离真正优秀很远,所以用无弹性高平台的优秀评选法替代传统的比率法就很重要,以绝对替代相对应该成为高校教师年度选优的新思路,这不但体现了学校对教师劳动的尊重,也是确立正义的校园文化和学校领导树立权威的需要。
比率分配;无弹性高平台;优秀教师;高校
一、比率分配模式下高校教师的传统选优模式
高校每年都要对教师进行优秀的筛选,因为涉及每个人的名誉和利益,所有教师都对这件事情非常关注,品质优秀的教师希望通过这样的选优过程将自己在年度内的优秀表现得到制度上的确认,品质不是很好的教师也希望自己能够被选上,以便能够得到不菲的收入。高校教师的选优可以给选上的教师带来双重收益:被评选上优秀教师不仅可以享受到很高的荣誉而且还有比较丰厚的物质回报,所以不但高校的校领导把此事作为重要事情抓,而且部门管理者也非常看重这件事情。能否把真正优秀的教师从众多的教师中筛选出来,是所有教师所瞩目的,尤其是在一学年以来认真工作并努力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教师对年度评优更是关注,因为这些教师正在成长,如果自己真正被评为优秀教师,不但可以得到一些物质上的回报,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努力能够在制度上得到部门领导乃至校领导的认可。虽然由于各个高校的情况稍有不同会导致在评选优秀教师的制度上有差别,但基本情况是一样的。一般是学校按照多年以来事先规定的标准将优秀和良好的评选比例按照学校的每个部门的具体人数敲定进而额定每个部门应该呈交到学校的教师的名额,名额可以略高于学校事先规定的数量,这可以使学校在一定范围内有淘汰或入选部门提交上来的名单的最后一名或最后两名教师的选择权,排在名单后面的教师能否被选上取决于部门管理者的偏好以及学校管理部门的决策动机,所以部门提交到学校的教师名额的排序很重要,如果学校在最后敲定的人员中决定淘汰为数不多的人选,则从名单的最后开始按照逆序向前淘汰。所以被淘汰的往往是部门呈给学校的名单中排在后面的教师[1]。在这样的优秀筛选过程中表面上看最后结果是学校和部门管理者的共同决定结果,但实际上学校所做的事情只是分配名额和淘汰末位,优秀教师的具体名额以及名额的排序均由部门管理者完成,所以教师能够被选为优秀从根本上讲并不取决于学校,而取决于部门管理者,部门管理者具有根据自己的好恶选择优秀教师的筛选权。所以在这样的评优方法中有几点需要提起注意:①学校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优秀教师评选的,该比例在所有部门是一样的,所以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在全校范围内按照一定比例推选出优秀教师。按照比例评选,表面上看在所有教师之间存在着竞争,但对于全校而言并没有竞争,因为所有教师的整体水平无论是高还是低,总会有一些教师被选拔为优秀,就是“矬子里面拔将军”。②优秀名额在不同部门间的绝对数会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仅仅是由于各部门的教师绝对数量的差别造成的,不能表现出哪些部门真正总体水平高或者总体水平低,从而不能体现部门之间的竞争,也不能体现部门管理者管理水平的横向比较。③学校只是作出宏观选拔政策,具体选拔谁并且将之推选到学校是部门管理者的事情,虽然学校按照比例挑选教师的思想在全校内是一致的,但各个部门在进一步挑选优秀教师的时候会对学校的总体思路做变通,即各部门评选优秀教师的标准会有差别,有的部门可能更加看重教师的专业水平,有的部门可能还会看重教师与部门管理者的亲近程度。所以部门最后呈现给学校的优秀教师数额虽然都在学校规定的比例范围内,但教师是否优秀只能各个部门管理者才知道[2]。④部门管理者“蝉联”优秀教师只为利益不为荣誉。由于部门管理者具有选择优秀教师的自由度,所以往往部门管理层成员循环选拔为优秀教师,这些教师一般年长资深,被选拔为优秀教师的目的不在于其所赋予的荣誉(因为这样的荣誉对于这些人已经无所谓),而在于荣誉背后绑定的物质收益。其他教师进入“优秀教师圈”的希望就非常渺茫。
二、比率分配模式下优秀教师选拔存在的问题
1.优秀评价制度简单化损坏管理者形象
学校只是简单地用比率的方式在全校范围内评选优秀教师,看似指标被硬化并且也做到了足够的公平,但由于部门管理者的二次操作造成了更多的优秀教师被排斥在优秀资格之外,这实际上是学校将制度详细化的成本让教师进行承担。由于制度的细化过程由部门管理者完成,而部门管理者在履行其职能的过程中又会以自己的好恶为中心,致使一些本应该得到优秀待遇的教师没有受到相应待遇,从而成为学校制度不合理的牺牲品。学校的这种做法是对教师的不负责任。教师能否得到学校制度设计下给予的相应待遇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还在于教师一学年以内的工作有没有在制度上得到学校高层的承认。教师需要得到这种承认并被给予相应的物质回报,因为这是教师应该得到的,但是该得到这些报酬的教师并没有得到[3]。正像教师努力为学校工作而不需要得到校长的感激一样,教师得到相应的回报也不需要感激校长,因为校长和教师一样都是在为学校的成长而付出努力,二者在所有问题上的利益都是一致的,双方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由于校长与教师群体数量的差异从而造成了替代弹性的巨大差别,即校长的替代弹性非常小,而教师的替代弹性却非常大,教师不可以随便选择校长,而校长却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教师,所以在校长与教师之间教师是弱者。当以校长为核心推出如上选择优秀教师的不合理制度时,也正是在这种不对称的替代机制下完成的,教师尤其是真正的优秀教师必须无奈地接受来自校长给予的不公平待遇,但是校长的正义化身与代表教师利益的形象会逐渐被削弱,校长不是代表所有教师而是代表部分教师尤其是自己身边教师利益的代表。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合理,校长就成为渔利绝大部分教师利益给小部分教师利益的代言,由此会进一步助长不健康的同事关系、师生关系乃至校园文化受到影响,而这些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得到完善和改变的。
2.优秀选拔的实施过程软化了硬性指标
优秀筛选的整个实施过程采用了量化指标,但是从量化指标的评分过程看,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评分标准,且大部分列入优秀筛选的指标如教学效果、师生关系、师德规范、教师修养和教研能力等均是软指标,软指标的评价过程中不免会掺杂个人感情因素,并且有时感情因素的成分非常高,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损失了量化指标的精确性。以不精确的指标来对教师进行精确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就会严重损失其价值。笔者认为软指标本身就不太适合量化,强行使软指标量化只能使得硬指标软化,表面上看是在对教师进行量化优秀筛选,实际上量化的根据已经失真:由原来的客观依据转变为感情依据。因为每个人的知识结构、价值观、感情和态度等的不同从而对同一件事情的认知会产生很大的偏差,所以不完全的根据必然会导致不完全的结论,以不完全的结论来对教师进行评价必然会对教师的行为产生不正确的导向,使得教师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不理解:自己努力程度很高但得不到较好的评价,没有作出很大的努力却得到了很好的评价,教师会注重评价者感情因素的培养。教师普遍认同:感情培养=价值创造,于是更多的人会更多地注重人际关系建设而偏离了优秀筛选奖勤罚懒的初衷。理论上认为可以进行量化的指标是那些客观性比较强的因素,而这些软指标的选取缺乏足够的客观性。
3.部门内优秀筛选加大了部门之间的不平衡
教师优秀筛选的基础是教师的日常表现,对教师日常表现的评价是在各个部门内部分别进行的,这样的优秀筛选方法只能将本部门小区域内部的教师进行等级划分,是在小范围内部的比较而并不是整个学校全体教师的比较,这样就严重扩大了部门之间优秀筛选的不平衡,即在一个部门(假设是A)整体状况不如另一个部门(假设是B)的情况下,会使得B部门选出的优秀者与A部门同样多,同时也可能出现B部门中比A部门还优秀的人员没有被选上,而A部门中不如B部门优秀的人员却被选上了,这种优秀筛选过程会损失教师的积极性,会使教师怀疑优秀筛选的公平性。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学校高层只是提出一个各部门优秀筛选的指标,但没有在全学校进行统一优秀筛选,即优秀筛选指标分到各个部门去贯彻,优秀筛选结果被平均分配到各个部门,全部教师范围内的平均主义转化为部门间的平均主义,全部教师范围内的竞争转化为部门内部教师之间的竞争。优秀筛选的结果看起来非常准确和公平,实际上缺乏科学性。教师优秀筛选应该是着眼于整个学校效率的提升,优秀筛选自然就应该在整个学校平台上来进行,但是现在是以部门为优秀筛选平台,就会使得一个部门(高水平部门)的收益转化为另一个部门(低水平部门)的收益,低水平部门的教师是依靠学校优秀筛选过程的政策优势获得不公平的收益[4]。这种制度的长期实行就会起到鼓励低水平部门长期低水平而遏制高水平部门进一步发展,实际上是降低了整个学校的工作效率,延缓了学校的发展速度。
4.优秀筛选的制度不合理强化了部门管理者的权力
从理论上讲制约机制建立的各方权利越对等,制约机制本身的功效就越强。当制约机制涉及的各方发生权力不对等时,其中就会出现一方依权力优势而在制约结果中占优势。从实践上看,优秀筛选过程本来就存在一个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权力不对称,即管理者对教师的认识总是不全面的并且在优秀筛选过程中教师和部门管理层的权力与地位是不对等的。所以在优秀筛选过程中就不免会存在以教师工作成绩以外的事情部分取代工作成绩本身从而再优秀筛选,同时管理者对教师的单方面优秀筛选也会损失优秀筛选机制的高效率。在优秀筛选中恰似建立了一种优秀筛选制度,但实际上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机制扭曲,造成不同层级的优秀筛选标准不一样。对于最高层的管理人员只存在比率设计的问题,同时也会产生最终选上谁对自己都无关紧要的思想,所以会懒于进行完善的制度设计,多年来遵循路径依赖,主张“存在就是合理”的歪理。教师优秀筛选的高效率从整体上看固然存在,但在教师中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利益不对称,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制度损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没有一个公开的、透明度很高的、对所有教师(包括各层级的管理者)普遍使用的优秀筛选方法。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建立一种优秀筛选制度将优秀筛选的绝对指标转化为相对指标,使得这种指标对不同层级的管理者和教师都适用,形成一种制度。只有所有人都按照这样统一的一个标准去做的制度才是真正的制度,部门管理者在其间不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使得学校内的所有人员感到制度的公平性和优秀筛选结果的公平性,不然就会由于优秀筛选机制本身的不完全而在层级优秀筛选中使这种“小”的不公平性逐级“放大”,不利于评价出最优秀的人才并使其成为学校所有教师的榜样。
5.优秀筛选系数的分配方法破坏了团队精神
很多学校的优秀筛选规则规定:各部门要在优秀筛选的结果上,对教师的月度、季度、年度奖励工资按照每个教师被核定的系数进行分配,这实际上是加剧了部门内部教师间的竞争。如果优秀筛选系数与教师奖惩相挂钩,则奖励系数在教师间的分配实际上就是奖金的分配,学校整个范围内的竞争演变为部门内部教师间的竞争,部门间的竞争会减弱甚至消失,部门内的竞争会增加,不但会影响部门内部的团队建设,而且会损失整个学校的进步效率。分配优秀教师系数无论对于部门内还是部门间都是不公平的。对于部门内部而言只是既有“蛋糕”的重新分配,“蛋糕”本身并未变大。我国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祖宗文化,优秀筛选机制的预期收益会由于该祖宗文化而部分被抹杀,存在两种情况:①一些教师会因上一筛选期多努力工作而未分配到预期优秀系数致使其在该筛选期内不再如上期那样努力工作;②部门内部成员间的竞争会使得少拿到酬金的教师认为其所损失正是高酬金系数的教师所得,教师间的关系于是被激化。
三、无弹性的高平台法取代比例评优法的实施对策
根据前文,比例评优方法通过制定低指标和比例分配的方式在组织中进行优秀教师的评选,由于低指标可以让更多的教师具有优秀候选人的资格,所以部门管理者就具有了在候选人平台上进一步筛选的权力,在此过程中部门管理者会有更多的机会用专业成绩以外的指标筛选教师,其中更多的时候会用感情指标来取代正常优秀筛选标准。当这种事情发生时,专业非常优秀的教师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教师评优的制度设计上给了部门管理者钻空子的机会。为了让真正优秀的教师得到公正的待遇,合理和严格教师评优制度就非常关键。在制度设计上不要给部门管理者有私下裁定的权力[5]。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需要用无弹性的高指标取代比例评优方法,笔者称之为无弹性高平台法。简单讲,就是把教师评优的平台定得足够高,让能够跳到这个平台上的教师足够少,宁缺勿滥,并且在挑选优秀教师的时候不能进行人为地操作指标,只要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都是优秀,没有达到标准的教师不具有评选优秀教师的权利。部门管理者在优秀教师的筛选过程中就无须再评选,只需要按照优秀教师的筛选条件选拔就可以了。于是教师优秀的选拔就由原来的选评法转变为了审核法。低水平的教师就不可能再与高水平的优秀教师掺在一起进行二次筛选,部门管理者就不具有再次筛选的可能。为了使无弹性高平台方法可操作,学校高层需要着手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事情:①标准的确定要切实可行。制定高标准的目的是为了让部门管理者好操作的同时不让其有变通制度的机会,而不是让所有的人不能选为优秀,所以筛选标准不能定得过高,否则会使所有人均不能选为优秀,这对于低水平教师自然无所谓,对于高水平教师仍然是不公平的。②标准要随教师水平的提高逐年变化。教师都具有被选拔为优秀的愿望,所以无弹性高平台方法实施后会有更多的教师向着这个方向努力,如果有更多的教师经过努力达到了这个平台后就会选拔为优秀教师。于是优秀教师的评选就失去了意义。为此评选平台需要逐年变化,根据教师总体水平的上升逐年上调,以便使得评选过程具有更多的挑战性和使得评选结果更加具有荣誉性。③不同部门要有切合自己的指标。高校一般包括了多个院系,各院系的情况又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全校范围内制定一个整齐划一的指标对所有教师进行一刀切,有时候对于某些院系并不合适,所以指标的制定需要结合各个院系的具体情况作出裁定,但要通过专家团的同意并且在指导思想上要与学校保持一致。④标准应该具体明确。以绝对指标替代相对指标,就改变了传统评优方法思路下按照一定比例评选优秀教师的方法。按照统一的方法在全校内部评定就有可能出现一些院系有较多的优秀教师,而另外一些院系的优秀教师数量很少甚至没有。部门管理者要认识到这种结果正是公平的表现,是将比率评选方法条件下按照平均主义方法分配给本部门的优秀教师名额转移到了真正水平高的院系中应该被评为优秀的真正优秀的教师,自己部门的优秀教师很少或没有被评上优秀是受到了公正的待遇,从另一个方面看,也是本部门管理水平较差的表现,所以该种评选方法有助于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管理者管理水平的横向比较,从而也是学校高层淘汰劣等部门管理者的依据。
[1]孟祥林.影响因素与对策:基于博弈理论的高效教学过程分析[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7,(2).
[2]何刚.高校教师优秀筛选误差产生的原因及对策[J].江苏高教,1997,(6).
[3]杨福治,徐先旭.当前教师优秀筛选评价机制构建过程中应着重强化的五个观念[J].山东教育科研,2000,(11).
[4]李辉生.高等学校的管理创新与创新教育[J].中国行政管理,2007,(2).
[5]詹向阳.高等教育管理主体:一个新模式下的解读[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G645.1
A
1008-469X(2010)02-0073-04
2009-12-11
注:本文为华北电力大学“长城计划”课题《以学生为本的服务型管理模式的构建》(课题编号:20080013)的研究成果之一。
孟祥林(1969-),男,河北保定人,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经济理论与区域研究、人力资源开发与教育过程分析研究。
(责任编辑 宋 悦)
——张 焘
——记全国优秀教师朱阿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