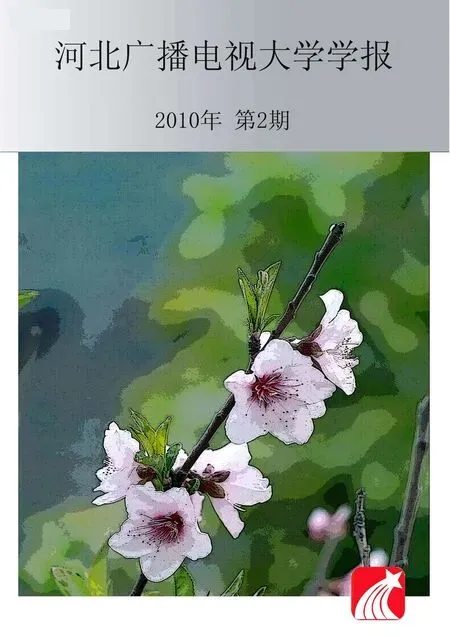中西文化的特征对各自科学发展的影响*
杨 帆,付玉成
(1.河北金融学院社会科学部,河北保定 071051; 2.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93)
中西文化的特征对各自科学发展的影响*
杨 帆1,付玉成2
(1.河北金融学院社会科学部,河北保定 071051; 2.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93)
文化的起源、文化传统的不同,致使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文化的“静心”特征造就的中国文化注重人伦、轻理性;西方文化的理性“紧张”形成的西方文化的逻辑严密、科学的文化氛围。从这一角度来看各自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西不同的传统文化的特点、文化与科学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把握传统,发展科学。
文化传统;静心;紧张;伦理;理性
一、引言
文化的起源、文化传统的不同,致使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有着很大的不同。本文将从中西不同的传统文化特点,尤其是中国文化的自然“静心”与西方文化的理性“紧张”方面来讨论其对于各自科学发展的影响。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以血缘为基础,宗法为机制的家国一体的社会形态,使中国文化更多地注重血缘、情理,而较少关注民主、科学。文化成熟及对日后产生重大的影响当数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这一历史阶段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热,思想文化处于由原始向文明的转变过程中,社会失范,行为失序,整个社会陷入战乱无序的状态中,处于这样战火纷飞的中国童年,由大痛苦也就产生了大智慧,而这种智慧也就相应地倾向于一种根深蒂固的秩序情结。于是对于自然的体察,也就更加注重一种求得内心平静的状态,中国人将其称作静心。
相比之下,西方完全打破了血缘关系,建立了城邦制,以地缘来划分城邦、公民。最为典型的当数古希腊,城邦的建立,使得大家变成公民,人们更多的是强调权利、意志、理性、法、正当。而不似中国古代注重的人伦关系、血缘亲情。这种文化渊源下的人们的思想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自然都有着高度的陌生感和紧张性,理性的纯粹性使得西方文化的这种理性紧张更加深化,由此,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更有利于客观性极强的自然科学的萌芽发展与进步。
二、地理环境与政治体制对文化传统、科学技术的影响
中西方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方面,显现出巨大的不同,我们将其归结为文化传统的不同,一个是重情理,一个是重理性;由此形成的人们的思维方式的迥异,一个是伦理的思维方式,一个是科学的思维方式;进而,近代的西方出现了科技革命,而技术发达的中国却逐渐落后于西方。
从地理环境看,中国是一个大陆型国家,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人们有着共同的祖先,由此,血脉是相连的,古代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熟人社会的结构框架。长江黄河养育着中华儿女,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土地肥沃,无须为衣食担忧,无须冒险航海,人口的迁移十分不频繁,人们之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血缘关系。这种社会形态使得人们安于现状,很少会考虑物质的本原之类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就算是有,如老子,其对于自然的态度仍然是建立在宁静、追求平和的自然思想之上。古希腊的面积远远小于中国,而且散布在海洋之上,使得人们对水、对海洋有着别样的情怀。同时,土地资源没有中国的富饶,势必在衣食上形成一种紧张,航海、通商的发达亦由此而生。由于这种紧张,加之不同地区的频繁交往,人口流动必然比中国大很多,陌生人的社会因此而形成。人们之间的陌生导致不信任,人们的交往总是处于一种紧张陌生的状态下,没有血缘亲情的担保,形成了契约式的交往生活方式,民主的思想、理性的思维模式逐渐建立。
从政治体制的建立看,中国以血缘为纽带,宗法为机制、家国一体的封建官僚体制的建立,使得中国的文化重情理、轻法理,形成的伦理文化以入世为人生手段。人们追求的是“学而优则仕”,这使得中国的文化知识本身没有独立价值形态,而是附属于伦理道德。追求知识,真理也主要是为履行道德义务,有德是中国人生存的目的也是能在中国古代社会更好生存的手段。由此,形成了浓厚的重道轻器,重政务轻技艺的氛围。中国人对于严密的逻辑推理与论证主要是用于形而上的问题,如佛教的缜密思辨逻辑,而对于科学技术方面的抽象的逻辑推理却是少之又少。再有,中国人重实用,对于科学技术,中国人的观点是“致广大高明而不离乎实用”,这种实用的思想,使科学技术很难上升到理论高度。而西方一开始就彻底打破了血缘的纽带,建立了以城邦为单位的民主政治体制,从而形成了西方人的“公民”意识,建立起一套契约供大家遵守,使社会成为可能。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同时又通过契约与他人交往、通商。契约的进一步演化就是法律,生人社会中,法的运用和实施不仅可能而且十分必要。民主、自由、法理,这是西方文化的元素,在人们的思维中根深蒂固,从而,使得西方人的逻辑思维、理性精神比中国浓厚许多。逻辑推理,理性抽象形成了西方的科学精神,为日后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静心”特性对科学的影响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儒家的这一思想有利于科学世界观的进展。李约瑟曾说:“注重理性,反对一切迷信,甚至反对宗教中的超自然的部分。”但是,这种思维倾向却被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价值观代替,“使得他们只对‘事’的研究而放弃一切‘物’的研究”。
中国文化另一个重要的派别当数道家。道家强调“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万物统一的自然观,最终一切归于永恒常在、自本自根的道。道家体察自然,求得内心平静,“在科学发展初期,他们觉得只要能将种种威胁人类的自然现象予以区别分类,为之命名,并研究其起源性质和将来的动态,以建立一套自然论时,则人类的能力和信心必然加强,这种得力于原始科学的内心的平静,中国人称之为静心”。李约瑟的这种解释不无道理,在《道德经》中讲道:“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在《庄子·天地第十二》又道:“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记曰: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这种体察自然的思想必然作科学的观察,这无形中就接到了经验主义的线索,经验主义是中国科学与技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因素。
但是,综观中国文化历史长河,我们看到,最终建立的是儒、道加之后来的佛三位一体的情理主义文化体制。而血缘为基础的传统文化,重家庭伦理,轻理性民主,人们缺少纯粹理性的思考。因此,对于自然科学关注较少,科学潜能无由生长,经验主义的成分相反地加强了。春秋战国的大动乱形势下,哲学家们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安抚人心的原则,而古希腊人所关注的自然科学则没有进入他们的思维领域,进而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四、西方传统文化中的理性的“紧张”性对科学的影响
希腊哲学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科学思想在哲学思维中相应的萌发。西方哲学家在讨论任何事物时首先要达到的是一种纯粹的思考,并且更多的是一种形而上的理性思考。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发现物质的本质。“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利士就把水看成本原。他得到这个看法,也许是由于观察到万物都以湿的东西为养料,热本身就是从湿气里产生、靠湿气维持的(万物从而产生的东西,就是万物的本原)。”
这种用自然来解释自然意味着理性萌芽的产生,它来自西方人传统文化中理性的紧张性,这种紧张性又是思维逻辑严密性的重要前提。并且,理性的增长主要表现在数学的发展和对逻辑的研究上。毕泰戈拉派认为数学的本原就是万物的本原。“由于这些本原数目是最基本的,而他们又认为自己在数目中间发现了许多特点,与存在物以及自然过程中所产生的事物有相似之处,……所以他们认为数目的某一种特性是正义,另一种是灵魂和理性,另一种是机会,其他一切也无不如此;……一切其他事物就其整个本性来说都是以数目为范型的,数目本身则先于自然中的一切其他事物,所以他们从这一切进行推论,认为数目的元素就是万物的元素,认为整个的天是一个和谐,一个数目。”作为希腊自然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在其《工具论》中,重点讨论了以三段论为核心的演绎法。策勒尔说亚里士多德首先发现三段论式是一切思维运动的基本形式,而且给它定下了名称。“三段论式是由某种前提必然得出新结论的一种论述方法。在三段论式中从一般得出个别,这是演绎推理。……因此,有确实根据的或科学的论证永远采取三段论式的形式,它是三段论式的和演绎的。……在三段论式中结论依赖前提,而这些前提又是其他前提的结论,如此等等。但是,这种过程不能前进不已,最后必然达到不能演绎的予以证明的命题或原则,这些命题或原则却有绝对的确定性。……每一种专门科学都有它自己的这种原则,此外还有一切科学所共有的普遍原则,即太初哲学的原则或形而上学。”在这里,“研究事物根本的或初始的原因的科学或哲学,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太初哲学,我们叫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研究本然的存在,各种科学研究存在的某些部分或方面”。
希腊的哲学、科学思想丰富多彩,每一位思想家都兼有着科学思辨与哲学气质。从上述思想家的观点不难看出,对于自然的深邃探究与理解、逻辑的严密思维方式反过来进一步造就了西方文化传统的理性紧张特点,而科学的发展进步最重要的是为依赖理性的思维建构科学体系。它为今后西方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和文化氛围。
五、结束语
中国文化归于求善为目的的伦理型,而同西方以求真为目标的科学型大相异趣。著名的伦理学家樊浩曾言:“科学型文化,把宇宙论、认识论、道德论加以区分别向纵向研究、探索各自的发展系统,而且对道德问题的研究也是从哲学与科学出发,用哲学的方法进行论证与阐发,因而道德认识实际上成为科学认识、哲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征。”它注重的是理性的严密、思维的缜密,始终有着精神、文化的一种紧张型,更进一步讲,总是贯穿着精神的一种张力、力度。中国文化系统里,有关宇宙和认识问题的探讨,往往都是从属或立足于伦理问题上,把伦理宇宙化,宇宙伦理化,显然,缺少科学研究应有的那种张力紧张型、理性,更多的是求静、通向内心平静的一种伦理化思维方式。
通过上述对于中西文化传统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地理环境、政治体制的不同,造就了中西不同的传统文化特点对于科学思维、科学发展的影响。二者没有好坏优劣之分,只是中西文化传统的不同表现。分析中西文化传统对于各自科学发展的影响,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文化与科学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把握传统、发展科学。
[1]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著.罗经国等译.世界文明史(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英)李约瑟著.陈立夫等译.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3](宋)朱熹.四书集注[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4.
[4]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美)梯利.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6]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 陈 蕊)
G04
A
1008-469X(2010)02-0103-03
2009-12-16
杨帆(1982-),女,河北保定人,助教,哲学硕士,主要从事伦理学、中国伦理与经济伦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