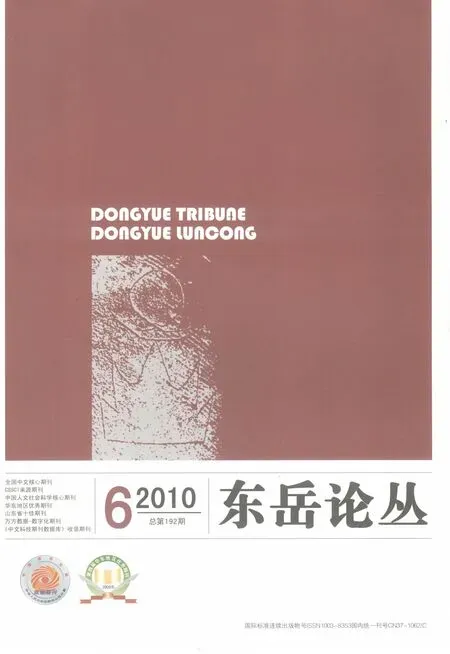外来文化中国化规律的先期探索——从汤用彤的文化双向交流理论看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赵建华,赵建永
(1.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2.天津社科院哲学所,天津 300191)
外来文化中国化规律的先期探索
——从汤用彤的文化双向交流理论看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赵建华1,赵建永2
(1.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2.天津社科院哲学所,天津 300191)
汤用彤之所以能在同辈学者所未予重视的学术领域独辟蹊径,原因在于他对文化双向交流问题有深入思考。他借用文化人类学有关文化移植的前沿成果应用于思想层面,认为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接触必须经过冲突与调和的三个阶段,才能在本地生根。他以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为例来说明外来文化必须经过很大改变以适应本地文化,方能被国人广泛接受。总结这项研究,不仅有助于理清以汤用彤为中坚的学衡派的文化运思理路,而且对于外来文化中国化规律的探索和当今的和谐文化建构以及解决“文明的冲突”都极富启迪意义。
汤用彤;中国化;文明冲突;双向交流
文化建设路向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知识界。面对中西文化的危机,汤用彤先生藉其广博学识,抓住了外来文化的本土化这一关键问题,提出了文化冲突与调和的三阶段理论。“昌明国故,融会新知”的治学宗旨是汤用彤解决此问题的理路,贯穿于他毕生的学术研究。如果说汤用彤的道教和魏晋玄学研究是就中国思想自身发展方面立论的,即“昌明国故”,那么他佛教史和西方哲学研究则意在探索外来文化中国化的过程,即“融会新知”。“融会新知”实际上就是中外文化双向对话、交流与影响的过程。这种文化观实际上也代表了学衡派的共同观点。
一、汤用彤的“文化移植”论对外来文化中国化规律的探索
汤用彤基于其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深入研究,从文化发展一般规律的高度探讨了不同文化接触后所发生的种种问题,并于 1943年 1月《学术季刊》一卷二期文哲号发表《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一文,对文化建设路向问题做了解答。他认为,中国自与西洋交通以来,因为备受外族欺凌,对本民族的文化前途产生了困惑。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接触,有两个问题应引起重视:“一方面我们应该不应该接受外来文化,这是价值的评论;一方面我们能不能接受外来文化,这是事实上的问题。”①汤用彤:《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汤用彤全集》第 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 277、277页。在汤用彤看来,无论是本位文化、全盘西化,还是中国该不该、能不能接受外来文化问题,牵涉的范围都太广,问题也过于复杂。他不愿在没有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不着实际地空谈文化问题。因此主张应先对历史有确切的认知,从中获得对当前处境的启示。他说:“过去的事,往往可以作将来的事的榜样。古人说得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虽不能预测将来,但是过去我们中国也和外来文化思想接触过,其结果是怎么样呢?这也可以供我们参考。”②汤用彤:《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汤用彤全集》第 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 277、277页。在以古证今的同时,他又以今释古,引进了文化人类学最前沿的文化移植理论,阐明了如何接受外来文化,即原有文化如何融合外来文化获得新知的问题。
文化移植是指一种文化进入另一文化环境中的成长过程,亦即不同类型的文化遭遇后所发生的情形。当时文化人类学前沿正对文化移植问题展开积极探索,但多偏于器物和制度层面。汤用彤将文化人类学有关文化移植问题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思想的层面。由于孕育于自身独特环境里的各种文化皆具有各自的特性,因而他首先确定了人们都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共识——“一种文化有它的特点,有它的特别性质。根据这个特性的发展,这个文化有一定的方向。”③汤用彤:《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汤用彤全集》第 5卷,第 278页。对于文化特性及其发展方向这一问题,汤用彤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开篇做了更为详细的阐发:“各民族文化各有其文化之类型,一代哲学思想各有其思想之方式。盖各种文化必有其特别具有之精神,特别采取之途径,虽经屡次之革新与突变,然罕能超出其定型。此实源于民族天性之不同,抑由于环境之影响,抑或其故在兼此二者,……。”《汤用彤全集》第 4卷,第 379页。以此为出发点,即在承认民族文化的本位性的前提下,他进一步讨论文化移植过程中所包含的两个问题:(1)外来文化异地移植是否会对当地文化产生影响?(2)外来文化是否会完全改变本土文化的特性和发展方向?对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答案是明确的,“因为一个民族的思想多了一个新的成分,这个已经是一种影响。”①汤用彤:《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汤用彤全集》第 5卷,第 278、278、279、280页。不同文化相遇,发生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对第二个问题,意见则有根本分歧。如,关于佛教对中国文化影响的程度就有两种对立的评价:照宋明儒家的说法,中国文化自三代以来有不可磨灭的道统。虽经外来佛学捣乱,但宋明儒学仍是继承固有的道统,终究未改弦易辙。与之相反的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中国思想因印度佛学进来完全改变,宋明儒家也是阳儒阴释,假使没有佛学传入,宋明儒学根本无由发生。对外来文化是否会改变本土文化原有特性和发展方向这一历史性难题,汤用彤没有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是通过比较分析文化人类学中三种文化移植学说,给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汤用彤首先批驳了关于文化移植说的两种理论:(一)比较早的主张是 1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盛行的演化说,即认为“人类思想和其他文化上的事件一样,自有其独立之发展演进。”②汤用彤:《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汤用彤全集》第 5卷,第 278、278、279、280页。此说推到极端则认为本土文化应独立发展,完全与外来思想无关。上面宋明儒家的观点与之相类。这种主张排斥外来思想的输入,易形成狭隘的民族主义,造成融会新知的障碍。(二)19世纪末叶很流行的播化说则走向了另一极端,强调“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思想都是自外边输入来的”,以至有人提出世界文化同出于一源(埃及)之说。一种文化的本源或主干归根到底都是外来的,“文化的发展是他定的而非自定的”。依此可推论,外来思想总是完全改变本土文化的特性或方向。本来外来文化能产生影响是没问题的,但此结论推得太过,而与演化说同样偏颇。此说与中国文化因佛学而完全改变的观点相仿,易使人产生自卑情绪而有“全盘西化”的论调。这虽是对传统文化感情深厚的汤用彤难以接受的,但他没有以主观好恶轻下判断,而是根据历史事实客观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汤用彤认为此两说各执一端,皆非确论,而是赞成新兴的批评派和功能派的学说,因为他们主张两种文化接触,其影响是双向的,而决不是片面的。
汤用彤特别强调,外来文化在移植中决不至于完全改变本土文化的根本特性和方向。原因在于一种类型的文化往往有一种保守或顽固的性质,虽有外力压迫而不退让。既然本民族文化的特性不是随便可以放弃的,因而外来文化若不能适应本地环境,便会遭到本土文化的排斥。这样,外来文化就必须在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中与之相调适。他说:“因为外来文化必须适应新的环境,所以一方面本地文化思想受外来影响而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因外来文化思想必须适应本地的环境,所以本地文化虽然发生变化,还不至于全部放弃其固有特性,完全消灭本来的精神。”③汤用彤:《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汤用彤全集》第 5卷,第 278、278、279、280页。可见,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接触,其影响必然是双向的。对本土文化来说,它吸收外来文化,使之成为自身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此种变化并不能根本改变原有文化的特性与方向。
当时国人一般只认识到中国文化要适者生存,汤用彤没有否认这一点,而是进一步指出,西方文化若要扎根于中国,且长久发生作用,同样也面临着适者生存的问题。因为外来文化要对本地文化发生影响,就必须找到能与本地文化相合的地方,并为适应本地文化而有所改变。就像葡萄与棉花分别从西域、印度移植而来,但中国产的葡萄、棉花,已经不再是移植以前的样子。因为它们须适应本地新环境,才能生长在中国,最终变成国产的了。尽管这是就器物层面而言的,然而同理,外来思想要被本土接受而能生存就必须有所改变以适合本国的文化环境。因此,“本地文化虽然受外边影响而可改变,但是外来思想也须改变,和本地适应,乃能发生作用。”④汤用彤:《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汤用彤全集》第 5卷,第 278、278、279、280页。佛教之所以为国人所接受,是因为融入了中国固有的观念。其间经冲突与调和,终为本土文化所同化。他举两个简单而典型的例子予以说明:一是无鬼轮回。中国灵魂和地狱的观念不是完全从印度来的⑤汤用彤《太平经》研究涉及中国本土的灵魂和地狱观念。余英时在汤用彤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系统阐述了这一问题(《中国古代死后世界观的演变》,《燕园论学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第 177-196页)。。但佛经所讲的鬼魂极多,地狱组织也非常复杂,中国的有鬼论深受其影响。然从学理上讲,“无我”是佛教的基本学说。“我”指灵魂,即通常所谓鬼。“无我”就是否认灵魂存在⑥印度哲学关于“我”的学说、无我与轮回问题,详见《汤用彤全集》,第 3卷,第 583-597页、第 194页。。我们看见佛经讲轮回,以为必定有种鬼在世间轮回。其实没有鬼而轮回,正是印度佛学的特点。二是念佛。按佛教原义,念佛是坐禅的一种形式,并非口唱佛名。而中国人把念字的意思本土化,理解成口念佛名,因此便失去佛教原意①念佛形式的中国化过程,参见《汤用彤全集》第 1卷,第 279-280页;第 598-601页。。但佛家为方便传教,还是听之任之。由此他得出一重要结论:“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思想实在有他的特性,外来文化思想必须有所改变,合乎另一文化性质,乃能发生作用。”②汤用彤:《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汤用彤全集》第 5卷,第 281页。从总体上说,虽然外来文化加入本土文化,并产生深刻影响,但本土文化的特性仍将会在新陈代谢中得以延续和光大③据 汤用彤的知友吴芳吉记述:1918年,汤用彤留学美国时已敏锐的注意到了一战后世界文化正走向对话的历史趋势,已产生了中外文化平等交流互动的想法。(吴芳吉:《吴芳吉集》,成都:巴蜀书社 1994年版,第 1275页。)这种见解在“五四”之前是难能可贵的,当时的新文化派和国粹派均未达此认识水平。汤用彤坚信文化交流是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随后他在长期坚实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提出的文化双向交流理论,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后来哈贝马斯“主体间性”的术语,但实际上早已表达了这一观念的核心意思。。
本土文化的保守性导致冲突,适者生存的需要导致调和。基于这种认识,汤用彤提出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融合必须经过冲突和调和两个过程④汤用彤:《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汤用彤全集》第 5卷,第 279、281、279页。。调和是因为两种文化有相同或相合之处,冲突则因为有不同或不合。双方必须有相同点才能调和,如果不明了两者相同之处,其相异之处也难以彰显。不知道两者相异的调和是非常肤浅的,这样的调和基础不稳固,必不能长久。深知其异再去调和才能使外来文化在本土文化中生根。汤用彤把外来文化的输入,分为三个阶段:
(一)因为看见表面的相同而调和。(二)因为看见不同而冲突。(三)因再发现真实的相合而调和。这三段虽是时间的先后次序,但是指着社会一般人说的。因为聪明的智者往往于外来文化思想之初来,就能知道两方同异合不合之点,而作一综合。⑤汤用彤:《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汤用彤全集》第 5卷,第 281页。谢灵运《辨宗论》折中儒释,即是于佛学初来,便知中印同异之点,而作的综合。
总体上,这是一种由表及里、由浅及深、由分到合的文化发展模式。汤用彤总结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规律,与黑格尔所谓正反合的哲学史发展过程不谋而合。第一阶段的“调和”是一种尚未深入的浅层认同,如格义、“佛道”现象等。第二阶段,外来思想逐渐深入,社会已将其看做一严重事件,如白黑论争、毁法等。第三阶段,“外来文化思想已被吸收,加入本有文化血脉之中了。……不但本有文化发生变化,就是外来文化也发生变化。”⑥汤用彤:《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汤用彤全集》第 5卷,第 279、281、279页。两种文化接触时所发生的这种双向选择和改变就是“融化新知”的必由之路。只有经历这一因看到不同而冲突、排斥、改造的过程,“外来文化才能在另一文化中发生深厚的根据,才能长久发生作用”。而且只有在这种“融会新知”的过程中,“国故”才能更加“昌明”。这种调和意味着创造性地整合与转化,但决不意味着本土文化根本特性的丧失。他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作为个案研究,以说明外来文化必须经过很大的改变以适应本地文化,才能被广泛接受。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相合或相近的部分能得到发展,反之,不合或不相近的则往往昙花一现,难以为继。像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天台、华严宗势力很大,而法相宗保持印度本色,结果虽有伟大的玄奘法师在上,也不能长久流行⑦汤用彤:《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汤用彤全集》第 5卷,第 279、281、279页。。隋唐以后,外来佛教已经丧失部分本色而成为中国化的佛教,而中国文化也因融合佛教而成为不同于以往的新文化。
至此,前面关于佛教对中国文化影响程度的两种对立意见,汤用彤虽然没有直接回答,但通过他对文化冲突与融合规律的阐述,我们自然能得到圆满的解答。两说虽各有所见,但都有局限,前者正确地看到了外来佛教并没有改变中国文化的走向,失误在于无视佛教对理学的深刻影响;后者有见于佛教对理学发生的关键作用,但错误地认为中国文化因印度佛教的传入而根本转向。汤用彤合而观之,正得其全。在移植中这种双方的改变是不同文化融会贯通的过程。由是以进,其逻辑结论自然是主张在融合古今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独立的民族新文化。
二、文化双向交流理论的现实意义
虽然中外文化在交汇过程中互有消长,但是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同化往往在整个文化传播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外来文化中那些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的部分,得以继续生存发展,而不适应或与本土文化相悖的部分,则自动退出文化传播的过程。这说明汤用彤是在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前提下,主动吸收外来文化来不断为中国文化输入新鲜因子并使主体增强再生功能,从而保持中国文化的持续生命力。可见“文化移植”之终的是外来文化被纳入“本有文化血脉中”。他关于主客文化的综合把握与选择的见解,意在强调要以本民族文化为主体,积极整合外来文化,从而发展民族的新文化,这与文化人类学的新近观念是相合的。现代文化人类学研究认为一种文化有如一个人,表现为多少一贯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各民族文化都是一种内含整合机制的独立文化模式。文化融合的过程也是特定文化模式丰富发展的过程。
汤用彤对“文化双向选择”的阐释,深化了学界对文化移植规律的认识。他以适合本国的国情作为文化选择的判断标准,并将之纳入文化冲突与调和的一般规律中加以考察,故其见解愈显精辟①乔清举:《日本近现代史中传统与现代化的四重关系》,《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 3期。。此一基于历史的概括,旨在将文化史的研究导入“真理之探讨”的堂奥,其结论确实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后来,张岱年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正是对这种文化理路的丰富、具体和深化。乔清举教授以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为典型,从经济、政治和观念三个层次分析后发掘国家中“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指出日本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经历了一个相互选择和适应的双向互动过程,并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选择和利用阶段,即选择和利用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有利因素,接受西方近代文化;二是“全盘西化”的阶段;三是融合阶段;四是日本原则的提出阶段。我们认为,四个阶段就其实质内容而言仍与汤用彤的文化融和三阶段理论相一致。中国现代革命史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中国化,才能真正实际地发挥作用,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汤用彤从对文化史的研究中,所得出的上述结论,也可作为借鉴,以提高我们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自觉性②汤 用彤病逝前,曾于 1963年劳动节晚应邀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由周恩来总理导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询问其身体状况,说自己阅读过汤用彤“所撰全部文章”,嘱咐他量力而行继续写短文。(孙尚扬:《汤用彤年谱简编》,《汤用彤全集》第 7卷,第 683页。)毛泽东对汤用彤著述的肯定,当与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和汤著对外来文化中国化规律总结的共鸣有关。。
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对待中印文化交流史与现实中西文化的关系?印度佛教的成功中国化与西方文化的中国化是否具有可比性?对于这类问题,汤用彤借《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司马迁的名言“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作了精辟的回答:“过去的事不能全部拿来作将来的事的榜样。……不过仅仅推论已往历史的原委以供大家参考而已。”③汤用彤:《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汤用彤全集》第 5卷,第 281页。他没有断定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必定与佛教的中国化一样,而是指出了解以往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是将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加以对照。在他看来,文化发展具有连续性,所以可以借鉴;但历史又有一维性,所以又不可生搬硬套历史经验,即“未必尽同”。这辩证地阐明了探索中西文化交流的规律何以要“志古之道”以自镜。理解此二点,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方能真正成为智慧之源。汤用彤正是以西学、佛学、玄学及三教关系的全部研究为背景,通过中外文化交流史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和智慧来探寻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并用以指导现实的文化建设。他对于佛教中国化规律的总结有助于我们了解外来文化的吸收、融合的机制,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认识,有助于实现文化的自觉。蒙培元教授认为:汤用彤的这种中外文化观是建立在大量事实观察与理论分析之上的,因而有说服力,对于当前中西文化的争论具有直接意义④蒙培元:《大师风范,学者胸怀——写在〈汤用彤全集〉出版后》,《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 2期。。
汤用彤揭示的文化冲突与调和的命题敏锐地把握住了近现代中国文化的主题。中体西用、本位主义、西化论都是在此视域内的重建方案。在汤用彤看来,中国文化的开展就是在吸纳西学基础上的重建,自觉吸纳外来文化与重建中国文化应为一致的过程或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此种融贯中西的文化观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倾向于发扬传统文化,与国粹派的抱残守缺、西化派的激进反传统划清了界线,突显了鲜明的个性,并超越了传统的体用框架,是为汤用彤的文化建设方略卓异于时人之处。因此,总结汤用彤的文化观不仅有助于理清以汤用彤为中坚的学衡派的文化运思理路,而且对于外来文化中国化规律的探索和当今的和谐文化建构以及解决“文明的冲突”都极富启迪意义。
赵建华,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赵建永,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B26
A
1003-8353(2010)06-0079-04
[责任编辑:杨晓伟]